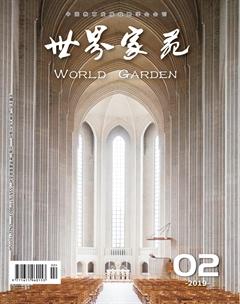论《羊脂球》和《我在霞村的时候》中女性的悲剧色彩
林静
摘要:《羊脂球》是法国作家莫泊桑的成名之作,在这部作品中他写了一位因为爱国而不肯委身于德国军官的妓女羊脂球的故事。《我在霞村的时候》是20世纪初中国女性作家丁玲写的关于慰安妇题材的小说。两部作品都曾受过毁誉参半的评价,除此之外,两部作品中的女主人公身上都被作者赋予了浓厚的悲剧色彩,在此基础之上,两部小说中蕴含的更深层思想都是希望唤醒女性沉睡千年的女性主体意识。本研究希望通过对比分析两部作品中的部分细节来深入剖析论证《羊脂球》和《我在霞村的时候》中女性的悲剧色彩。借此研究希望可以使人们站在更高的层次上去理解、关注和感悟女性的情感、生命及内心世界。
关键词:《羊脂球》;《我在霞村的时候》;女性悲剧色彩
纵观中外名著,伟大的作品往往都是关于女人的故事,尤其是那些具有争议身份的女人,如《安娜·卡列尼娜》中出轨的女人安娜、《茶花女》中上流社会的交际花玛格丽特、《羊脂球》中的妓女羊脂球以及《我在霞村的时候》慰安妇贞贞。除了身份备受争议之外,她们还有另外一个相通的特征——具有浓厚的悲剧色彩。她们生性善良,心灵高尚,但最终结局却是或绝望的卧轨自杀,或凄凉孤独的一个人死去。那么是谁造成了她们充满悲剧色彩的一生呢?
在中国千百年来的男权社会中,女人一直被视为男人的依附而存在,从古人对妻子的称呼就能略见一斑:“内人”“贱内”“糟糠之妻”。“内”,“屋内之人”便能看出女性在社会中地位的低下,这就注定了男性为女性冠上的悲剧色彩。丁玲是新时代的女性,她有个性、有才情,这注定她的一生定然是不平凡的。她珍视闺蜜之间的友情甚于爱情,于是她放弃了爱情只为她更为看重的友情,丁玲说:“剑虹是世界上最珍贵的人”。但当她把一生不可替代的闺蜜交付于翟秋白仅7个月后,她便香消玉殒,在人生最后的阶段,她人生中最重要的两个人都不在她身边,丁玲就这样匆匆赶来上海,又匆匆带着遗憾和心痛离开,不到半年,翟秋白又与他人结婚,丁玲发出一声长叹,叹闺蜜的不值得,叹男人的善变,叹自己的无能为力。于是她也终于失去了人生中最重要的两个人。悲剧从一开始就在丁玲身上酝酿。她不懂得什么叫做“三从四德”,不遵守什么“三纲五常”的伦理道德,于是她同时爱上了两个男人,提出三人同居,在这那个年代是多么的大逆不道,为天理所不容,为此,她被贴上各种难听的标签,面对各种流言蜚语,她说:“什么思想解放?我们那个时候,谁和谁好,搬到一起住就是,哪里像现在这样麻烦!”这种丰富的人生经历就决定了她笔下的人物必然是深刻的。于是她写出了中国第一部以慰安妇为题材的作品——《我在霞村的时候》。故事中的女主人公是一个身份备受争议和诟病的慰安妇,这种污秽的女人也配成为歌颂的主角吗?文学圈中有人提出了这种狭隘的质疑和偏见。在我看来,贞贞要比当时深受封建思想毒害的麻木的村民伟大的多,在某种程度上丁玲继承了鲁迅先生关于国民性批判的思想。
我常在想,有时候,女性的悲剧色彩不仅仅源于男权社会,更深的根源在于女性自己身上。同为被男性压迫的群体,为什么不能联合起来为自己发声呢?甚至女性对女性的压迫比男性对女性的压迫更为苛刻。张爱玲说一个女人如果得不到异性的爱,也不会得到同性的尊重。得不到异性的爱本来就已经有点悲凉凄怆的女性,在此刻还要接受来自同性的冷言冷语,难道此刻女性不应该是来安慰被男性品头论足的女性,霸气地对她道一句:“他,配不上你!”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而是张爱玲所写的那样。她的这句话准确地道出了女性对女性的无情刻薄。
在古代,我们都说是男权社会,男性带给了女性无穷的痛苦和压迫。女性在男性面前只有服從。但我看到的更多的却是女性与女性之间的勾心斗角、尔虞我诈。在后宫中,女性受到种种陈规旧俗的毒害,饱受失去自由之苦,生活已经够辛苦了,但她们彼此之间不懂得惺惺相惜,互相取暖,反而是为了取悦一个男人而争得头破血流、你死我活。在大家族中,婆婆也是从媳妇的身份走过来的,其中的苦想必她们也都懂得,但当自己一跃成为婆婆的身份时,可曾想过不要如此苛待自己的儿媳妇,因为她善待的不仅是自己的儿媳妇,更是曾经的自己。将心比心、换位思考,或许女性的悲剧色彩不至于如此这般浓厚。她们不仅要受男性的压迫,更有自己女性同胞投来的异样眼光。丁玲在《我在霞村的时候》写了这样一句话:“尤其是那一些妇女,因为有了她发现对自己的崇敬,才看出自己的圣洁来,因为自己没有被敌人强奸而骄傲。”这些妇女比鲁迅笔下冷漠麻木的看客更为让人气愤。看客也只是麻木不仁的“看”,而霞村的妇女们却以谁能说出最恶毒最具侮辱性的言词为荣,仿佛自己是代表世上最纯洁正义的人来讥讽别人的不幸,站在道德制高点来谴责他人。正常来说,身为女性应该更加同情与理解女性, 但在落后保守的霞村中,妇女们不仅如此冷漠的对待贞贞,甚至还把自己当作一个“高尚圣洁”的旁观者,别人越不幸,她们莫名的优越感就越强烈。实质上,她们也是在无形中“吃了几片自己的肉”,竟还浑然不知,并为此津津乐道,殊不知,她们只是为伤害女性连同自己增添了几把柴火而已。女性不仅是一个字眼,更是一个性别群体。霞村妇女自以为圣洁地旁观自己的同胞,是长期在男性主导的社会中压抑自己而产生的精神枯萎状态。只有女性才能拯救女性,每一个受害妇女都应该值得被同情与理解,更何况贞贞还只是一个受害者,只是一个小女孩。在花一般的年龄却被如此蹂躏践踏,难道不值得同样饱受摧残的妇女们的一丝怜爱吗?不难理解, 贞贞的仇恨中还饱含着霞村妇女对女性话语权轻易放手的绝望,她们甚至没有为自己争取话语权的意识,这种在男权期望下的贞洁观实质上是对女性的伤害,霞村妇女将自身的话语权双手奉出,恭敬顺从地交给男性,不仅扭曲了女性群体的意愿,也丧失了为自己发声的权利。
女性难道不更应该为女性发声和呐喊吗?但霞村的妇女们按照男人的喜好,磨平自己的棱角,拔掉保护自己的刺,装扮成男人喜欢的模样,忠贞、温顺,只为迎合男权主义者的青睐和欢心,在男权社会中,她们完全丧失了自我,她们只为他们而活。所以当叛逆的贞贞不愿磨平自己的棱角来迎合男人们的喜好时,她便受到了男性和女性一致的否定,没有人站在贞贞的立场上思考她的不幸,甚至包括数千年来深受男权压迫的女性同胞。如丁玲所说的那样, 女人更应懂得女人的苦, 更应理解与同情不幸的女性,而在霞村妇女们选择默然旁观的那一刻,她们就已经沦为男性的附属品,再也无法从封建思想中解放出来了。身为女性的丁玲非常敏锐地意识到了这一点,才是她在《我在霞村的时候》这部小说中蕴藏的潜在话语。张爱玲的作品中也蕴含着浓厚的女性主义思想,《色戒》里的王佳芝为了刺杀特务头目易默成假戏真做,失身于此前有过嫖娼经验的同学梁闰生发生关系,一切原本都是为了救国锄奸,然而她不仅并未因此得到同学们的理解和关爱,反而却遭到同学们的窃笑。她采取的则是冷冷地撕下蒙在故事上的温情面纱,暴露出人物千疮百孔、残缺不全的人生,以一种令人满心悲酸的方式来唤醒沉睡千年的女性主体意识。
莫泊桑笔下的《羊脂球》以一位妓女为主人公,她虽然从事着最低贱的工作,但她有一颗善良高尚的心。同行的车中尽管伯爵、伯爵夫人这些贵族人士都对与她这样一个低贱的妓女同行为耻,但羊脂球在他们饥肠辘辘时仍然慷慨的分享了自己所有的食物。反观那些虚伪市侩的上层阶级一个个丑态百姿的吃相,以及“吃了人家的东西就要跟人家说话”的虚伪势力心态,羊脂球倒显得更为真实纯粹。车上的男人对羊脂球作出各种献媚挑逗的轻浮之举,那些高贵的夫人们在知道羊脂球的妓女身份后,很快就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在她们看来,她们在这个不知羞耻的低贱妓女面前应该齐心协力的扮演好为人妻的神圣角色,因为不合法的自由爱情往往被合法的爱情看不起。羊脂球不仅要忍受男人们的各种轻佻之举,还要忍受女人们的各种污言秽语。这使她本来就已经悲惨的生活经历更显凄凉。她选择善良的对待他们,分享自己所有的食物,但在那些自私自利的贵族们面前,羊脂球还是被他们无情的推向了德国军官的床上。他们是一群从来都不擅长知恩图报的人,更加不想懂得羊脂球的牺牲是因为他们。在国家兴亡之际,伯爵们口上大谈仁义道德、家国责任,但在敌人面前,便把家国大义全都抛诸脑后,他们觉得自己高贵的生命要比尊严和爱国情怀这种东西来得更为重要一些,更何况只是牺牲一个低贱妓女那本来就早已被玷污了的清白。如果德国军官要求强占的是那些夫人们中的一个,这件事或许更好解决,因为一方面他们的丈夫定然是更珍惜自己高贵的命,另一方面則是这些夫人们大概也愿意献身给这个潇洒帅气的德国军官,毕竟她们都觉得这个军官不错,竟而还惋惜他不是法国人,否则所有的漂亮女人都会对他着迷。另外在她们心中,爱国这种高尚的情怀只是放在面子上说说而已的场面话,而对于羊脂球来说,她是绝不肯委身于这些侵略践踏自己国土的德寇的。但在这群无耻之徒的威逼利诱下,羊脂球的最后一道精神防线被摧毁了,她被他们推入火坑,去屈从德国军官的兽欲,得以保全他们自己。在阴谋得逞危机过去后,他们不仅不同情、不安慰羊脂球的难堪和屈辱,反而过河拆桥,以加倍的轻蔑和鄙夷来讥讽牺牲色相替他们解围的她。当她意识到他们先是把她当成玩物利用,然后又像抛弃垃圾一样的抛掉她时,她不禁在饥饿和屈辱中悲愤交加,哭泣不已。在《马赛曲》曲调的烘托下,羊脂球的悲剧色彩更显浓厚。
参考文献:
[1] 袁良骏.丁玲研究资料[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
[2] 徐艳蕊.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二十年[M].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3] 莫泊桑.羊脂球[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4.
[4] 陈思和.文学中的妓女形象[M].人民日报出版社,1990.
(作者单位:中央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