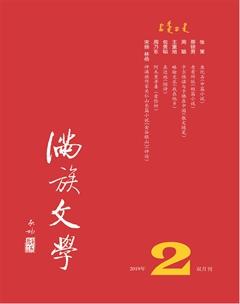卡尔维诺与卡佛在中国
周聪
卡尔维诺:寓言·生存困境
伊塔洛·卡尔维诺(1923—1985)是意大利著名的作家,也是对世界文学做出过重要贡献的作家之一。卡尔维诺的作品几乎与马尔克斯的作品同时进入中国,但直到九十年代中后期,才逐渐在中国热起来。进入新世纪,卡尔维诺的作品系统地被翻译到中国来,首先是2001年译林出版社出版了吕同六和张洁主编的《卡尔维诺文集》(5卷6本),为读者提供了较好的范本。在相隔十一年之后,译林出版社又推出了《卡尔维诺经典》(16种19册)。近年来,译林出版社又陆续推出《在你说“喂”之前》《美洲豹阳光下》《圣约翰之路》以及《一个乐观主义在美国》《文学机器》《论童话》《收藏沙子的旅人》《文字世界和非文字世界》《困难的爱》,使得卡尔维诺的作品成为更多读者讨论的对象。
卡尔维诺赢得了许多当代作家的喜爱和赞赏,他被称为“作家们的作家”。王小波是一个明显受到卡尔维诺影响的例子,孙郁认为他“是有意无意地对卡尔维诺的呼应”,其他学习卡尔维诺的作家“未必读懂了那位意大利人的世界”,“未必能进入王氏所说的精神的游戏里”。洁尘则非常推崇卡尔维诺的《千年文学备忘录》,因为这本书给大家提供了有效的写作指导,她将自己喜欢卡尔维诺的原因归结为:“在他的这些带点‘恶作剧意味的作品中,看到了一个对读者充满了温柔情感的作家。”此外,周大新也是卡尔维诺的忠实读者,他在一篇文章中将卡尔维诺的写作总结出三个特点:“顽强地不停地寻找新的表现方法”,“在寻找写作题材时视域极其广阔”,“在作品中思考的东西透彻而深刻”。这三大特点事实上也是卡尔维诺小说深受作家们追捧的重要原因之一。除了王小波、洁尘、周大新之外,残雪、王安忆、薛忆沩等作家对卡尔维诺的文本有一种近乎疯狂的痴迷。薛忆沩探讨卡尔维诺《看不见的城市》的随笔集《与马可·波罗同行》,便是明证。
卡尔维诺的想象天马行空,他的大多数小说具有强烈的童话和寓言色彩,读完后给人一种奇特的审美感受。他在谈论自己创作时的兴奋点与聚焦处时说:“我感兴趣的是那种历史逻辑的荒谬机制。我在政治报刊上登载的小说在慢慢地失去现实的体积,但增添了叙述的线性成分,增添了能够获得一致的对称,增添了像寓言或童话般精准的几何学,而这正好发生在——请您注意好了——其时的政治理念最能来滋养我那些小说的时候。”卡尔维诺强调历史、天文、几何等学科背景的融合,在我看来,将这种理念落到实处的是于晓威的《圆形精灵》(《收获》2005年第1期),因为它“融合了传奇、笔记、史料、报道、议论等多种文本,通过颇具意味的拼贴形式组合在一起,举重若轻地探讨了时代人的‘魔症,似乎超出了一个短篇的思想容量”,与卡尔维诺的追求有著相似性。
卡尔维诺的写作是一种寓言式的写作,在《分成两半的子爵》《不存在的骑士》《树上的男爵》这几部作品中,卡尔维诺以一种寓言式的想象,对现代人的“分裂”“虚无”“孤独”等命题进行了深刻剖析。事实上,“寓言式”的写作在新世纪的短篇中可以找到一些影子,比如张惠雯的《水晶孩童》(《收获》2006年第2期)、冉正万的《纯生活》(《人民文学》2010年第5期)、甫跃辉的《巨象》(《花城》2011年第3期)、龙仁青的《水晶晶花》(《中国作家》2011年第2期)等作品都具有某种寓言的因子。虽然我们不能断定这些作品是受到卡尔维诺的影响而写,但它们在审美上与卡尔维诺的短篇有着某种相似性。对于“寓言式”的写作模式,洪治纲认为是“对一切现实的客观逻辑来一点小小的反动,小小的剥离,小小的提升……正是这种小小的不同寻常,却使叙事轻松地脱离了纯粹的写实层面,进入各种想象的空间。它既解放了作家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又使叙事话语在剥离写实之后获得了诗性的气质,呈现出飞翔的状态。与此同时,他还非常善于以点带面,以小载大,以轻击重,以一个小小的人物或事件,将思考延伸到某些巨大的命题之中”。权聆的《处女公墓》(《作家》2006年第10期)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这篇小说“将卡尔维诺式的想象与‘聊斋式的传说发挥得淋漓尽致”,可以说,卡尔维诺对想象力的解放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当代短篇小说作家的创作,洪治纲认为在残雪的《贫民窟》《月光之舞》、权聆的《鹅美人》、童若雯的《古美人的微笑》、骆以军的《杀妻者》《神弈》等作品那里,都可以发现卡尔维诺式寓言的影子,在某个侧面证明了卡尔维诺对中国当代作家的影响之广泛。
在此,我们以卡尔维诺的《一个士兵的奇遇》为例,探讨他的这个短篇是如何被中国优秀的作家们借鉴来表现中国式经验的。《一个士兵的奇遇》是卡尔维诺《短篇小说集》第三卷“艰难的爱情”中的首篇,它讲述的是一个名叫托马格拉的步兵休假回家时在火车上对女人的欲望之旅,小说在一种紧张急促的氛围中进行叙述,托马格拉对该寡妇的窥探,并故意一步步地制造的身体轻微触碰等,始终是伴随着托马格拉的想象与试探展开的。当然,卡尔维诺的叙述很有节制,他将步兵托马格拉的这种欲望冲动与心理恐惧结合得十分巧妙,不留痕迹。故事的最后,托马格拉看到寡妇的目光“明晰而严肃”,心底萌发出更大的恐惧。
毫无疑问,《一个士兵的奇遇》是一篇典型的心理小说。它书写的是旅途中人们共通的心理欲望与想象,在中国作家笔下,也有着一些明显模仿卡尔维诺这篇小说的佳作。例如,盛可以的《缺乏经验的世界》(《大家》2008年第1期),该小说讲述的是在火车上一个成熟女人对一个男孩的引诱,但对于女人来说,她缺乏男孩世界里所拥有的经验。值得注意的是,《缺乏经验的世界》和《一个士兵的奇遇》写的都是火车上的奇遇,着重表现主人公的欲望与内心冲突。不同之处在于,盛可以对卡尔维诺的人物设置进行了一定的变动,在卡尔维诺那里,是士兵对寡妇的欲望,而盛可以的笔下则是那个成熟女人对男孩的勾引。这样的变动难免隐含着创作者心里深处的性别意识差异。旅途的欲望冲突同样可以在铁凝《伊琳娜的礼帽》(《人民文学》2009年第3期)那儿得到印证。这篇小说讲述的是伊琳娜和一个瘦子男人在飞机上的欲望之旅,小说在行文的过程中对这对男女的亲密动作有了精准的描绘。有意思的是,他们的行为在作者的笔下没有一丝鄙俗的气息,反而增添了许多浪漫和诗意的色彩。将这篇小说与《一个士兵的奇遇》进行比较,不同之处在于故事发生的地点变成了飞机上,相似之处在于两篇小说都对主人公内心的隐秘欲望进行了精准的呈现,尤其是在刻画主人公的行为动作上下笔颇重。
倘若将上述三篇小说置于一起探讨,我们能够发现三者的关联与差异。在文学史上,书写路途人的内心欲望与心理的小说非常多,它们多选择火车或者飞机为故事发生的地点,主人公的设置往往为一男一女,透过一个个故事,挖掘他们的内心隐秘,或者由此引发对婚姻以及人物内心的关注,这些小说在审美上有着某种相似的精神追求。新世纪短篇小说中,王秀梅的《关于那只纸鸽子的后来》(《花城》2010年第4期)以及徐则臣的《这些年我一直在路上》(《收获》2010年第4期)也是类似的作品,在此就不做赘述了。
其实,在卡尔维诺《短篇小说集》第三卷“艰难的爱情”里还有一篇名为《一对夫妻的奇遇》的小说,它对胡学文的《关系》(《作品》2011年第6期)有着很深的影响,洪治纲在《2011中国短篇小说年选》的序言里就指出这一点。《一对夫妻的奇遇》讲述的是一对白、夜班颠倒的男女的故事,工人阿尔都罗·马索拉里上夜班,妻子艾里德上白班,两个人在家只有短暂的碰面机会,但是这对夫妻的交流因为为彼此暖床而变得非常温馨和真挚。胡学文的《关系》是建立在《一对夫妻的奇遇》的基础之上的,这篇小说讲述的也是一对夫妻白、夜班颠倒的故事,“我”在郊区的玛钢厂守夜,妻子宋佳在白天开公交车,“我”和她平时的交流是写字条,也会创造一些条件调休约会。然而,我们平静的生活被对门的一对夫妻干扰,他们经常吵架,甚至在一次吵架中男人被女人所杀,“我”被拉去法院做证人。于是,对门的这个女人嵌入了“我”和宋佳的生活,成为我们生活中隐形的障碍。在一次作证中,“我”被迫说出和宋佳调休是为了过夫妻生活,这引起了“我”的领导的关注,将“我”调整为白天上班。遗憾的是,宋佳因为精神恍惚开车追尾,被调至夜间调度室工作。最终,“我”和妻子又落入白、夜班颠倒的生活圈套之中。应当说,《关系》的框架是建立在《一对夫妻的奇遇》的基础之上的,胡学文在一定程度上将卡尔维诺落笔的地方进行自己的创作,通过对门夫妻的介入,将这种与我们并无关系的他者是如何影响、干扰我们生活的过程展现得淋漓尽致,在一定程度上是对《一对夫妻的奇遇》的借鉴与超越。
由此我们不难发现,卡尔维诺短篇小说对新世纪短篇小说文体发展产生的巨大影响,但更令人敬佩的是,卡尔维诺的中篇或长篇作品同样具有这种魅力,影响着一些中国当代作家们的创作。比如,徐则臣就以《看不见的城市》为题写了一个短篇,发表在《北京文学》2013年第10期上。再如,冉正万的《树上的眼睛》(《厦门文学》2009年第2期)就明显受到了卡尔维诺的《树上的男爵》的影响。冉正万曾经在一个访谈里提及他喜爱的作家时说:“我还喜欢福克纳的某些書,还有卡尔维诺。”在此,我更感兴趣的是《树上的男爵》是如何对冉正万的这个短篇产生影响的?也就是说,冉正万是如何学习卡尔维诺的?他是如何将卡尔维诺幻想式的写作嫁接到中国式的经验上的。我认为是人物形象的作用。
卡尔维诺曾经谈到过《树上的男爵》这个小说的写作过程,他说:“我开始写幻想小说时,并没有考虑理论问题,只知道我写的每一个故事都有个视觉形象为依据。例如,有个分为两半的人的形象,他的两个半身不仅不死,而且还独立地生存着;另一个形象是,一个青年爬到树上,在上面攀来攀去,不再下到地面上来……”并进一步指出自己的创作方法是“把幻想中自发出现的形象与语言思维中的意图统一起来”。显然,那个名叫柯希莫·皮奥瓦斯科·迪·隆多的人物,深深印在了冉正万的脑海里。不同的是,柯希莫从十二岁爬上树之后,直至死再也没有下树。而舅舅在所谓的餐饮娱乐项目开发后,再也不愿意呆在树上。舅舅的下树行为实则是个人内心的诉求让位于现代文明对传统乡村的侵蚀之上的,值得人们深思。饶有意味的是,冉正万在《树上的歌声》(《山花》2013年第12期)写到了一个在树上唱歌的思敏的人物,足以看出柯希莫形象对于他的创作的深刻影响。在笔者的阅读中,朱山坡的《鸟失踪》(《天涯》2009年第3期)中那个对鸟无比迷恋的孤独父亲形象,也颇有点柯希莫的固执和倔强,在氛围的营造上与《树上的男爵》第24节中有一些相似之处。
卡尔维诺对新世纪短篇小说作家的影响是多方位的,不论是寓言式的书写,还是其想象力与创造力,抑或是诸如人物设置与心理描摹等写作中的细部处理,卡尔维诺都为作家们树立了良好的典范,他是一个既注重写作形式,又强调情感重要性的作家,正如他所言:“我们专注于内容,但从来没有像我们这样执迷的形式主义者;我们宣称写作应该客观冷静,但从来没有像我们这样澎湃的抒情诗人。”这句话也许道出了卡尔维诺在写作风格上的重要特点。
卡佛:现实世界·失意者的生存镜像
雷蒙德·卡佛生于1938年,是继海明威之后美国最伟大的短篇小说家,他的前半生是在失业、酗酒、破产、妻离子散、友人背弃的生活中度过的,被称为“写失败者的失败者,写酒鬼的酒鬼”。贫苦的遭遇给了他丰厚的人生阅历,这一切又都成为卡佛创作的素材。卡佛五十岁时因为肺癌去世,却留下了六十余个短篇小说、三百余首诗歌和一些杂文、评论文章,其主要短篇小说集有《大教堂》《当我们谈论爱情时我们在谈论什么》《请你安静些,好吗?》《我打电话的地方》等,透过这些作品,我们能够真切感受到卡佛“极简主义”的行文风格。
卡佛的作品在中国流传约是1992年,那一年花城出版社推出的于晓丹翻译的《你在圣弗朗西斯科做什么》是其较早的中译本,后来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出过卡佛的短篇小说集,台湾也有人翻译过卡佛的作品。2009年1月,肖铁翻译的《大教堂》由译林出版社出版,译林社并陆续推出了卡佛系列作品,包括:《大教堂》(2009年1月)《当我们谈论爱情时我们在谈论什么》(2010年1月)《需要时,就给我电话》(2012年9月)《火》(2012年9月)《请你安静些,好吗?》(2013年5月)《我们所有人》(2013年5月)以及《新手》(2015年6月)。此外,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出版的小二翻译的《雷蒙德·卡佛短篇小说自选集》(2012年7月人民文学出版社以《我打电话的地方》命名重新出版,有王安忆序言)也是目前中国读者读到的重要中译本之一。卡佛作品的陆续翻译为更多的读者和研究者提供了方便,也掀起了阅读卡佛、谈论卡佛、模仿卡佛的热潮。
应当说,卡佛自从翻译到中国后就逐渐受到了中国翻译家、作家、评论家的喜欢。卡佛的翻译者于晓丹、肖铁、舒丹丹等人都有关于卡佛小说或诗歌的评论文字发表。在新世界出版社推出的“影响我的十部短篇小说”中,余华、莫言、王朔、苏童进行了推荐,王朔和苏童各自列出的十部作品中就分别有卡佛的《你们不是我丈夫》和《马辔头》,说明卡佛对一些中国当代小说家的写作产生过重要的影响。李洱在一个访谈中也表露出对于卡佛的喜爱,他认为《大教堂》有很强的寓言色彩,“大教堂”是明顯的隐喻。与王朔、苏童、李洱的激赏不同,70后作家徐则臣在肯定卡佛的同时,又表达了不同的看法,他“认为卡佛没那么好”,“缺少我理想中的大师应有的世界观。他的目光平常,局限于日常的人情和伦理。”同样,在评论家那儿,卡佛也得到了大家的关注。例如,李敬泽对卡佛的诗歌《你们不知道什么是爱》及其短篇小说进行了阐释,并认为卡佛的极简主义“与其说是卡佛的创造不如说是编辑的创造”。张新颖的《“我可以看见最细小的东西”——雷蒙·卡佛的〈羽毛〉和〈软座包厢〉》(《长城》2013年第3期)和石华鹏的《忘不掉的雷蒙德·卡佛》也是阅读卡佛后的思考。
卡佛的作品被称为“极简主义”,辨识度较高,被称为具有“典型的‘卡佛风。语言平淡、硬实,不堆砌、不张扬,追求精确,不忌重复,富于韵律,有着一种着意克制的‘言外诗意;人物一如既往地微不足道,在晦暗、封闭的世界里处处碰壁,活得无助无望却认真得让人心疼,用卡佛自己的话说,可谓‘竭尽全力”。例如卡佛的《他们不是你的丈夫》讲述了厄尔·奥伯在听见顾客谈论妻子多琳的身材后,一心要求妻子减肥,当妻子减肥成功,厄尔·奥伯试图与其他顾客谈起妻子的身材时,再也无法引起别人的关注。这种细节的错位在某种程度上折射出人物的生存困境与心理状态。而在《杰瑞、茉莉和山姆》中,阿尔背着贝蒂和孩子丢弃狗之后,以为生活会得到变化,却陷入了更大的困境之中。卡佛的这篇小说让笔者想到了薛荣的《扫盲班》(《芳草》2007年第5期):“我”爸爸让“我”跟踪妈妈,想扫除妈妈婚姻生活的盲区,结果却使“我”陷入了更大的盲区。两篇小说在精神内核和审美旨趣上都是展现现实世界中人的生存际遇。
在短篇小说中,一些作家的作品明显受到了“卡佛风”的影响,它们与卡佛的短篇小说在文体上有着深厚的渊源。例如,河南作家老海的《你怎么不说话》(《文学港》2012年第5期)《它没有长出翅膀》(《莽原》2013年第2期)《两个老者》(《福建文学》2012年第3期)《图么缺缺》(《朔方》2013年第1期)等短篇的命名,就很有点卡佛的味道,我们只需看看卡佛的《没有人说一句话》《你们为什么不跳个舞》《他们不是你的丈夫》《阿拉斯加有什么?》等小说,就不难发现二者之间的关联。老海非常喜欢卡佛,他甚至还写了一篇名为《你爱卡佛,你没法让他们也爱卡佛》(《莽原》2013年第2期)的小说,以小说的形式向文友们推荐卡佛的小说。
应当看到,老海并非只是简单地对卡佛的小说命名进行着模仿,在精神旨趣和审美维度上,老海的上述作品也具有浓烈的卡佛式意蕴,老海将中国式的经验与卡佛式的表达结合得十分巧妙。例如,《你怎么不说话》写的是一个男人在妻子出差后与两个女性的交往,一个女性求他替离婚出谋划策,另一女性则求他帮忙跑官,老婆得知男人的行为后,觉得他有着出轨的嫌疑,小说最后在妻子的“你怎么不说话”质问中结束,留下了空白。在题材的选择上,这篇小说明显受到了卡佛的《阿拉斯加有什么?》的启发,《阿拉斯加有什么?》讲的是两对夫妇间的一次聚会,卡佛以谈话的方式呈现出人物真实的生活状态,卡佛小说中类似的构思方式还有《把你的脚放在我的鞋子里试试》。值得注意的是,上述的小说都是以聚会、交谈的形式展开的,在行文中穿插着生活中的种种困顿与纠葛,主人公渴望解决矛盾,却陷入更深的困境之中。在人物那里,现实就像一个巨大的黑洞,吸附着苦苦挣扎的人们。
接下来讨论《它没有长出翅膀》。这篇小说讲的是主人公带着媳妇一起回乡照顾病重的父亲,在家乡,他带着她一起重返儿时的记忆:美丽的自然风光、两孔废弃的窑洞、梅子树、桃花洼相亲……他的讲述得到了她的补充,因为他曾经对她讲过一部分故事。有意思的是,他的讲述看似精准,实则充满了悖论:比如在返乡之旅中,他去桃花洼走错了路,并非当年的地方;又如他故意忽略被姐妹俩玩弄自己性器官的细节,事实上他是怎么也不会说给她听的。《它没有长出翅膀》的处理有点类似于卡佛的短篇《小木屋》,《小木屋》中主人公哈罗德先生离开家去一个地方钓鱼,住在旅馆里,也是利用空余时间重返自然,渴望寻找内心的宁静,最终还是得返回现实之中。可以说,不论是记忆或者是承载着记忆的自然风景,都只是主人公短暂的休憩之地,他们最后还是得回到现实中来。这一点也就是《它没有长出翅膀》与《小木屋》在精神内核上的相通之处。
诚然,老海的《你怎么不说话》和《它没有长出翅膀》除了在选材及审美上具有卡佛的味道之外,在语言上也追求简洁,着意写对话,表明了作者从内容到形式上都是卡佛的追随者。石华鹏在评价老海的这两篇小说时说:“除了这些标题很‘卡佛外,老海小说的内容和叙事策略也很‘卡佛——‘我在小说现场、琐碎的生活、简洁的叙事、没完没了的对话、看似平静的叙述下面波涛汹涌,以及小说意义的暗示等等,这些十足的‘卡佛标签在老海的小说里均有迹可循。”这一评价还是比较公允和到位的,足以体现老海对卡佛的热爱与模仿。
除了老海的小说之外,范小青的《我在哪里丢失了你》(《作家》2009年第4期)与卡佛的《你是医生吗?》在构思上有一些相似之处。在两篇小说中,女主人公都是通过电话联系上男主人公到家与自己谈话,这一细节呈现出生活中的某种无聊与偶然性。范小青曾经提及过阅读卡佛的感受:“在阅读卡佛的那一片刻,我感觉到某一种关系又产生了,我的内心又遭遇了撞击,那是无比美妙的撞击,那是心领神会的撞击。”
此外,广西的作家朱山坡也十分重视卡佛的作品,他在一篇文章里说:“余华并不是唯一赐我钥匙的人。后来我遇到了马尔克斯、福克纳、博尔赫斯、胡安·鲁尔福、奈保尔、卡佛……我用不同的钥匙打开不同的门,走进了一间又一间房子。”朱山坡的《最细微的声音是呼救》(《文学界》2010年第6期),明显就是他用卡佛这把钥匙打开写作之门的表现,因为卡佛的短篇《我可以看见最细小的东西》和《学生的妻子》就是朱山坡《最细微的声音是呼救》的“底版”,他们在精神血缘上颇有渊源。具体说来,《我可以看见最细小的东西》讲述了“我”听见细微的声音无法入睡,起来发现山姆在撒药粉杀鼻涕虫,和山姆交谈几分钟后“我”回去睡觉,躺下了却发现院子门还是没有闩。《学生的妻子》中主人公南因为迈克的呼吸声而彻夜失眠,她可以听见许多常人无法觉察到的细微的声音。与此相似,朱山坡的《最细微的声音是呼救》讲述了一个老太太多次听到呼救声并报警,却找不到声音的源头,最终民警小宋经过排查找出声音来自一个废弃的小水塔。小说中老太太对声音的敏锐感知,与卡佛的这两篇小说如出一辙。其实,对于声音敏感的捕捉也同样在卡佛的其他作品中有着呈现,比如诗歌《窗外的人》的句子:“但后来有天晚上/卧室窗外有个人——/也许某个东西,呼吸着,挪来挪去。/我弄醒妻子,吓坏了,/在她的臂弯里战栗到天亮。”《窗外的人》可以印证《学生的妻子》这篇小说,体现出卡佛对细部的敏锐观察和感知能力。
应当承认,卡佛对当下中国小说家的写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大多小说家们在写作中接受着卡佛的艺术滋养。苏童的话较有代表性:“我之所以喜爱雷蒙德·卡佛,完全是因为佩服他对现代普通人生活不凡的洞察力和平等细腻的观察态度,也因为他的同情心与文风一样毫不矫饰……我们总是可以感受到他用一根粗壮的手指,轻轻地指着我们大家的灵魂,那些褶皱,那些挫伤,那些暧昧不清的地方,平静安详就这样产生了力量。”王安忆、肖复兴等作家也多次流露出阅读卡佛的愉快体验,这些也显示了卡佛小说巨大的艺术魅力。
〔特约责任编辑 王雪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