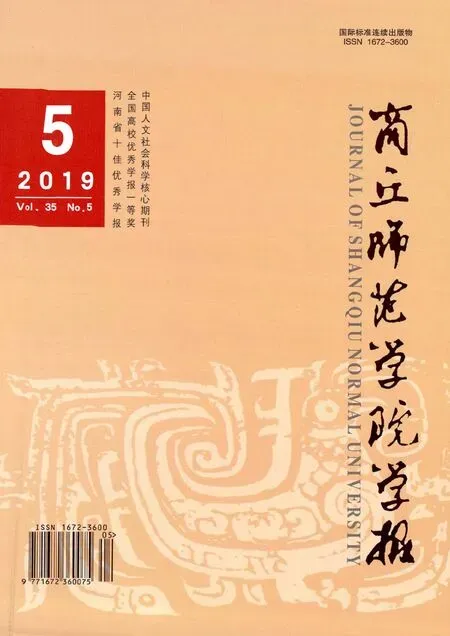“疏”的文学性:论成玄英《庄子疏》之文学特征
赵 俭 杰
(陕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陕西 西安 710119)
初唐道士成玄英所作《庄子疏》是庄学史上的一部名著,对“成疏”的研究目前仍集中在哲学思想层面,然以文学视角观之,我们发现它的哲学思想与文学形式结合完美,与《庄子》一样,皆有很高的文学审美性①目前学界对于“注疏体”之文学特征和文体形态的研究并不充分,如研究成玄英《庄子疏》的文学性,就笔者所见资料显示,仅有方勇《庄子学史》、史慧硕士论文、吕洋与刘生良师的单篇论文等寥寥几篇文章,涉及论题只有:成疏对《庄子》内外杂分篇的诠释、字词训诂、名物考索、譬喻章句的揭示、三言的阐释评论等几个方面。究其实,这类研究多以《庄子》为本照观成疏,较少从成疏文本自身的文学性出发。其中,仅史慧从成疏本身略作分析,指出成疏具有质朴、圆融的文风;以实写虚的形象描写;成疏的散文体式。参见方勇《庄子学史》第二册,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史慧《〈庄子〉成疏的文学性阐释》,2011年辽宁大学硕士学位论文;吕洋,刘生良《唐成玄英对〈庄子〉文学的阐释》,《唐史论丛》第二十辑。。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提示和总结《庄子》所使用的辞格;二是对《庄子》名物、史实的文学阐释;三是“成疏”文本本身的文学特征。正因此,成氏《庄子》文学阐释对明清《庄子》散文评点影响甚夥,对后世《庄子》注疏文体影响甚大。
一、提示和总结《庄子》所使用的辞格
《庄子》文学成就之高,其一就是修辞多样化,然因著述旨趣和体例的不同,魏晋学者对其辞格的使用未予重视,直至唐代成玄英才予以揭示,从而为人们更好地理解庄文寄寓在辞格之后的真实意图提供了便利。
清人宣颖有言:“庄子之文,长于譬喻。其玄映空明,解脱变化,有水月镜花之妙。且喻后出喻,喻中设喻,不啻峡云层起,海市幻生,从来无人及得。”[1]1确实如此,在《庄子》使用的辞格中,用得最多、最好的便是“譬喻”,成玄英疏解最多、最好的也是它,诸如“此起譬也”“此举譬也”“此解譬也”“此合譬也”“此结譬也”“此起喻也”“此合喻也”一类疏语,每每可见②诚如方勇先生所言,此类提示语,每每可见,俯拾皆是。他还指出成玄英《庄子疏》中所谓“起譬”,相当于现代修辞学所说的比喻形式上之喻体;所谓“合喻”,相当于比喻形式上之本体。参见方勇《庄子学史》第47页。。
成疏对《庄子》譬喻的揭示,全面而具体。它既揭示具体比喻,如疏《齐物论》的“大言炎炎”时说:“夫诠理大言,犹猛火炎燎原野,清荡无遗。”[2]58又揭示整体比喻,并以“起譬”“合譬”“结譬”指出譬喻所在,且将其贯穿于章句疏解的同时,还从“起譬”到“结譬”,或从“起喻”到“合喻”,具体指出《庄子》使用譬喻的完整过程。如《天运》篇“颜渊与师金问对”章“尸祝斋戒以将之”句下,疏云:“此下譬喻,凡有六条:第一刍狗,第二舟车,第三桔槔,第四楂梨,第五猿狙,第六妍丑。”[2]516这既指示了譬喻,又梳理了层次。又如《达生》篇“列子与关尹问对”章“是故遌物而不惜”句下,疏云:“‘自此已下’,凡有三譬,以况圣人任独无心:一者醉人,二者利剑,三者飘瓦。”接着,分别在“彼得全于酒而犹若是”句下云“此则是初(喻)”;在“复仇者不折莫干”句下云“此第二喻也”;在“虽有忮心者不怨飘瓦”句下云“此第三喻也”[2]638。这也不但揭示了譬喻,而且疏通了行文脉络。
成疏指出譬喻、串讲章句、疏理文脉的做法,在此前的庄学著作中并不多见,在后世林希逸、陆西星、林云铭、宣颖、方人杰、胡文英、刘凤苞等人的庄学作品中越来越多。
“譬喻”之外,成玄英对《庄子》所使用的假问、重复、寓言、互文等辞格也予以揭示。
成疏中的“假问”是“假设疑问”和“假设问对”的简称,前者指“反问”,有问无答;后者指“设问”,有问有答。如《至乐》开篇的“天下有至乐无有哉?有可以活身者无有哉?”成氏即疏:“此假问之辞也。”继而疏曰:“今欲行至乐之道以活身者,当何所为造,何所依据,何所避讳,何所安处,何所从就,何所舍去,何所欢乐,何所嫌恶,而合至乐之道乎?此假设疑问,下自旷显。”[2]610又如《齐物论》篇,疏“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恶乎至?”为“假设问对,于何而造极耶”,疏“有以为未始有物者,至矣,尽矣,不可以加矣”为“答于前问,意以明至极者也”[2]82。复如《齐物论》篇,疏“彼是莫得其偶,谓之道枢”为“前则假问有无,待夺不定;此则重明彼此,当体自空。前浅后深,所以为次也”[2]74。这既指出假问,又揭示重复。
成疏也指出了《庄子》所使用的“重复”辞格,且指明重复辞格之所指。如《齐物论》的“咸其自取,怒者其谁耶?”句下,疏曰:“此则重明天籁之义也。”[2]57又如《庚桑楚》的“南荣趎问老子”章,各段末都有“是卫生之经已”的句子,疏云:“(此)重举前文,结成其义。”[2]791复如《德充符》的庄惠论人有情无情,庄子重复说着“道与之貌,天与之形,恶得不谓之人?”的话,疏曰:“欲显明斯义,故重言之也。”[2]228这些“重明”“重举”“重言”之类的提示语,意思都是重复言说,都在指出文章运用的重复这一修辞手法。
成疏还揭示了《庄子》使用的“寓言”辞格。如《田子方》的“庄子见鲁哀公”章,疏曰:“庄子是六国时人,与魏惠王、齐威王同时,去鲁哀公一百二十年,如此言见鲁哀公者,盖寓言耳。”[2]719又如《齐物论》的“罔两问景”章,疏云:“庄子寓言以畅玄理,故寄景与罔两,明于独化之义。”[2]117复如《至乐》的“庄子之楚,见空髑髅”章,疏曰:“庄子适楚,遇见髑髅,空骨无肉,朽骸无润,遂以马杖打击,因而问之。欲明死生之理均齐,故寄髑髅寓言答问也。”[2]619
《庄子》中的“寓言”实际也是一种“譬喻”,因此,成疏除用“譬”“喻”,又以“寄”“托”等词,来揭示《庄子》所使用的比喻辞格和寓言手法。如《养生主》的“庖丁解牛”章,郭象无注,成疏直言“寄庖丁以明养生之术者也”[2]126。该篇的“秦失吊老聃”章,疏曰:“此盖庄生寓言耳,而老君为大道之祖,为天地万物之宗,岂有生死哉!故托此言圣人亦有死生,以明死生之理。”[2]135
另外,成疏还指出《庄子》的“互文”修辞手法。如《逍遥游》篇疏曰:“彷徨,纵任之名;逍遥,自得之称;亦是异言一致,互其文耳。”[2]47又如《至乐》篇的“芒乎芴乎,而无从出乎!芴乎芒乎,而无有象乎!”句下,疏曰:“覆论芒芴,互其文耳。”[2]615后者,指出庄文使用互文;前者,表明自成互文。
总之,成玄英对《庄子》辞格的揭示,是比较全面具体的,这为读者体会辞格之后的深意提供了便利,也凸显了《庄子》异于其他旨在阐发哲学思想类著作语言的文学特征,又使其从文学角度疏解《庄子》成为可能。
二、对《庄子》名物、史实的文学阐释
四库馆臣称郭注“大半空言,无所徵实”,成疏以郭注为本,故多“无注之疏”[注]郭象自谓其注“宜要其会归而遗其所寄,不足事事曲与生说,自不害其宏旨,皆可略之耳”(《逍遥游》注),故其注文,过于简省,成疏依郭注而外,作有大量“无注之疏”(方勇语),其一便是对《庄子》名物、史实的详证。,即郭象未予关注,而玄英加以索解。成疏对《庄子》中大量的名物、史实,详加辩证,又广引“典籍、时语”,态度审慎;而对《庄子》中大量虚实不定或完全虚构的部分,成氏又以文学手法来详其字、比其实,令其疏解全面、翔实,其中虽有穿凿之处,但对我们理解庄文,不无裨益。因此,成氏对《庄子》的名物考证具有承启之功,不仅继承了郭象注、陆德明音义等成果而更为翔实,而且开启了后世如俞樾《庄子人名考》等名物考证之风。
考释人名之细,可以“南郭子綦”为例。对《齐物论》的“南郭子綦”,郭象无注,《释文》仅引司马彪“居南郭,因为号”之语,而成疏云:“(南郭子綦)楚昭王之庶弟,楚庄王之司马,字子綦。古人淳质,多以居处为号,居于南郭,故号南郭,亦犹市南宜僚、东郭顺子之类。”[2]49此疏称南郭子綦字号,言之凿凿。
然据《徐无鬼》篇,“仲尼之楚,楚王觞之。孙叔敖执爵而立,市南宜僚受酒而祭”[2]851。考诸史册,孙叔敖为楚庄王相时,孔子尚未出生,故此篇盖寓言也。又据《左传》哀公十六年所载的“市南有熊宜僚者,若得之,可以当五百人”之语,则确有以居处为号的“市南宜僚”。而且,不仅《齐物论》提到颜成子游师事南郭子綦,在《徐无鬼》与《寓言》篇中也有颜成子师事南伯子綦、颜成子游师事东郭子綦之事,则南郭子綦、南伯子綦、东郭子綦应是一人,而有些虚构成分,故成玄英说南郭子綦“亦犹市南宜僚、东郭顺子之类”[注]方勇先生亦持此论点。参见《庄子学史》第45页。。总之,此疏不仅指出《庄子》人物常以居处为号的惯例,而且点明《庄子》使用虚实相参之手法,也体现出成玄英疏解文献时审慎的态度。
我们知道,《庄子》中还有大量完全属于虚构的人物,而成玄英也一一疏解其名字所包含的深刻寓意,所用的正是文学虚构之法。
如其所说,《德充符》中“伯昏无人,师者之嘉号也。伯,长也;昏,暗也。德居物长,韬光若暗,洞忘物我,故曰伯昏无人,以彰德充之义也”[2]205;《则阳》中“智照狭劣,谓之少知。太,大也;公,正也。道德广大,公正无私,复能调顺群物,故谓之太公调。假设二人,以论道理”[2]909。前者,类指“才全而德不形”之人;后者,以“少知”比喻智识狭劣之人,以“太公调”比喻道德广大之人。成氏结合思想特点来疏解人物名字的做法,比较合理。
又如其在《至乐》篇的“支离叔与滑介叔观于冥伯之丘,昆仑之虚,黄帝之所休”句下,疏曰:“支离,谓支体离析,以明忘形也。滑介,犹骨稽也,谓骨稽挺特,以遗忘智也。欲显叔世浇讹,故号为叔也。冥,暗也。伯,长也。昆仑,人身也。”[2]618因为,只有忘智忘形才能苟存于浇薄之世,方可抵达至乐之境,故其疏解人名,颇合文意。
然如《德充符》篇的“鲁哀公问于仲尼”章的“与为人妻宁为夫子妾”句下,疏曰:“妻者,齐也,言其位齐于夫。妾者,接也,适可接事君子。”[2]214此类疏解又显得迂阔,妄测题意,背离文心。

《庄子》所及地名,最引人入胜者莫如“姑射山”。然后人多方考证,亦难确其址,成氏则以文学手法疏之,曰:“藐,远也。《山海经》云:‘姑射山在寰海之外,有神圣之人,戢机应物。’时须揖让,即为尧舜;时须干戈,即为汤武。绰约,柔弱也。处子,未嫁女也。言圣人动寂相应,则空有并照,虽居廊庙,无异山林,和光同尘,在染不染。冰雪取其洁净,绰约譬以柔和,处子不为物伤,姑射语其绝远。此明尧治盛德,窈冥玄妙,故托之绝垠之外,推知视听之表。斯盖寓言耳,亦何必有姑射之实乎,宜忘言以寻其所况。”[2]32
成氏对于不少自然物象和抽象术语,也能结合其思想特点加以疏解。如《在宥》篇疏“云将”“鸿蒙”“扶摇之枝”为:“云将,云主将也。鸿蒙,元气也。扶摇,神木,生东海也,亦云风。夫气是生物之元也,云为雨泽之本也,木是春阳之乡,东为仁惠之方。举此四事,示君王御物,以德泽为先也。”[2]397读完成疏,才明白“云将、鸿蒙”寓言紧承上段“黄帝与广成子”之论,同样在讲逍遥无为而万物自化的道理。
又如,人们困惑于“逍遥”之含义,成疏:“彷徨,纵任之名;逍遥,自得之称;亦是异言一致,互其文耳。不材之木,枝叶茂盛,婆娑阴映,蔽日来风,故行李经过,徘徊憩息,徙倚顾步,寝卧其下。”[2]46疏用诗意笔法,摹写逍遥之义,原来“逍遥”是指无为虚淡、适性自由的一种人生态度。
成玄英为使其疏翔实,还引用了大量典籍、俗语。如开篇《逍遥游》疏“北冥有鱼,其名为鲲”句时,即引汉东方朔《十洲记》与晋郭璞《玄中记》为证。他处又引《大戴礼》《列子》《老子》《老君经》《淮南子》《尔雅》《山海经》《管子》《西升经》等各部典籍达十余种。这不仅有助于明了《庄子》文学阐释史,也无疑增加了成疏的可信度。
总之,《庄子》中的名物多有其特定含义,必须结合思想特点加以阐释,成氏这类“因名释义”之疏虽不免穿凿,然其既利于我们理解庄子名物之用意,也是成玄英哲学思想和文学手法的一种表达。而且这种方式,在成疏以前,并不多见,在成疏之后,近乎惯例。
三、成疏文本本身之文学特征
《庄子疏》序云:“自古高士,晋汉逸人,皆莫不耽玩,为之义训;虽注述无可间然,并有美辞,咸能索隐。玄英不揆庸昧,少而习焉,研精覃思三十矣。依子玄所注三十篇,辄为疏解,总三十卷。虽复词情疏拙,亦颇有心迹指归;不敢贻厥后人,聊自记其遗忘耳。”[2]9其中,一者,可见成疏用力颇深;二者,可见玄英注意文辞。因此,成疏本身也具有较高的文学性,取得了较高的文学成就,却长期不为人重视。笔者抛砖引玉,试揭示如下几点。
(一)语汇丰富且准确生动
语汇的使用,成疏较郭注更丰富,也更浅近平实。
如《齐物论》篇的“百骸、九窍、六藏”,疏曰:“百骸,百骨节也。九窍,谓眼耳鼻舌口及下二漏也。六藏,六腑也,谓大肠小肠膀胱三焦也。藏,谓五藏,肝心脾肺肾也。”[2]64成疏并未因袭旧注,而是结合当时的医学概念来疏解这些名词,显得生动具体。又如疏《齐物论》之“出生入死”的生死观时,曰:“从无出有,谓之为生;自有还无,谓之为死。”[2]111总体来看,成玄英仍以道家哲学为本位,故其用特定的“有”“无”概念进行疏解。
成玄英虽为道士,却熟读佛典,精通佛理,故疏中常有佛家语汇流出。如其在《齐物论》中,以佛教“诸法皆空”理论疏解庄子“齐物”思想时,曰:“知三界悉空,四生非有,彼我言说,皆在梦中。”[2]113其中,“三界”谓“欲界、色界、无色界”与“四生”谓“卵生、胎生、湿生、化生”等,皆佛家语。为抵“诸法皆空”之境,成氏要以“遗六根”(《达生》疏)为前提,且告诫人们“莫染根尘”(《养生主》疏),佛家谓“眼耳鼻舌身意”为“六根”,又谓“色声香味触法”为“六尘”。这些佛家语汇的羼入,使得成疏更为圆融。
成疏的解释细致入微,分析鞭辟入里,语言浅近平实。
(二)句式多变且富于韵律
我们仅在《逍遥游》一篇之中,就能看到成疏时而全用骈句,时而全用散句,时而骈散互用,此类手法,每每可见,生姿妙笔使其文情摇曳。
全用骈句者,如:“初赖扶摇,故能升翥;重积风吹,然后飞行。既而上负青天,下乘风脊,一凌霄汉,六月方止。网罗不逮,毕弋无侵,折塞之祸,于何而至!良由资待合宜,自致得所,逍遥南海,不亦宜乎!”[2]9又如:“夫四生杂沓,万物参差,形性不同,资待宜异。故鹏鼓垂天之翼,托风气以逍遥;蜩张決起之翅,抢榆枋而自得。斯皆率性而动,禀之造化,非有情于遐迩,岂措意于骄矜。”[2]7上段纯用四言,富于律动;下段四六相参,极具美感。
全用散句者,如:“夫翻覆一杯之水于坳污堂地之间,将草叶为舟,则浮泛靡滞;若还用杯为舟,理必不可。何者?水浅舟大,则黏地不行故也。是以大舟必须深水,小芥不待洪流,苟其大小得宜,则物皆逍遥。”[2]8
骈散互用者,如:“鱼论其大,以表头尾难知;鸟言其背,亦示修短叵测。故下文云未有知其修者也。鼓怒翅翼,奋迅毛衣,既欲抟风,方将击水。遂乃断绝云气,背负青天,骞翥翱翔,凌摩霄汉,垂阴布影,若天涯之降行云也。”[2]4此段四言为主,杂以多言,词约义丰,极写鲲鹏驰聘之状。
《人间世》的“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章下,疏曰:“山中之木,楸梓之徒,为有材用,横遭寇伐。膏能明照,以充灯炬,为其有用,故被煎烧。岂独膏木,在人亦然。”[2]194先言山木,次言膏火,末句落笔于人,词语变化,层次分明;句式齐整如四言诗,协律可歌。
又如《齐物论》有疏云:“夫智慧宽大之人,率性虚淡,无是无非;小知狭劣之人,性灵褊促,有取有舍。有取有舍,故间隔而分别;无是无非,故闲暇而宽裕也。”[2]58句中既有丫杈句法的使用,又在对比中强调。
从语句来看,成疏有骈句、散句、杂句;从韵律来看,大都协律可歌,利于记诵。总之,成疏句式具有严整而疏朗、多变而谐和的特点。
(三)辞格多样且恰切得体
成疏在揭示和总结《庄子》所使用的辞格时,又自觉地将这些辞格运用到自己的疏解之中,其比喻、对比、反复、顶真、反问等修辞方法的使用,得体而恰切。
成疏回环往复,说理透辟,见解深刻。如《齐物论》有疏曰:“言夫六根九窍,俱是一身,岂有亲疏,私存爱悦!若有心爱悦,便是有私。身而私之,理在不可。莫不任置,自有私存。于身既然,在物亦尔。”[2]64先分说,后总说,分说时,四面夹击;总说时,一锤定音。
又有顶真者,如《齐物论》疏曰:“世皆以他为非,用己为是。今欲翻非作是,翻非作是者,无过还用彼我,反覆相明。反覆相明,则所非者非非则无非,所是者非是则无是。无是则无非,故知是非皆虚妄耳。”[2]72是非颠倒,反复无极;论述有序,便于明理。
对比之中,亦有正对反对者,如:“夫水不深厚,则大舟不可载浮;风不崇高,大翼无由凌霄汉。是以小鸟半朝,決起榆枋之上;大鹏九万,飘风鼓翼其下也。”[2]9此段对比,上句正对,下句反对。
成玄英在疏“至人、神人、圣人”时说:“至言其体,神言其用,圣言其名。故就体语至,就用语神,就名语圣,其实一也。诣于灵极,故谓之至;阴阳不测,故谓之神;正名百物,故谓之圣也。”[2]25可以看出,既然“至言其体”且“诣于灵极,故谓之至”,那么,成疏认为《庄子》最为推崇“至人”的态度不言自明,这是异;既然言至、言神、言圣,只是体、用、名的差异,那么,成氏持“至人”“神人”“圣人”只是境界不同而无本质区别的观点不言而喻,这是同。成疏正是以对举手法揭示了《庄子》所标举的人之三重境界的异同。
(四)情景交融,语义丰赡,意境饱满
这与上文提到的,成疏多用辞格、句式变化等文学手法的特点有关,如释《逍遥游》中的“野马”一词,郭注仅云:“野马者,游气也。”《释文》引司马彪“春月泽中游气也”与崔譔“天地间气如野马驰也”之语,而成玄英说“野马”是“言青春之时,阳气发动,遥望薮泽之中,犹如奔马,故谓之野马也”[2]7。郭象点出野马即游气的实质,司马彪承郭注又释“野”为“春月泽中”,而成疏不仅将“野”字具体到时间和空间,还指出了万物奔腾的原因在于阳气涌动。这就把鹏鸟驰骋于天地的自由跃动状态展示得更加形象了,构成了一个阔大、飞动、变化、富于生气的完整画面,也再现了庄子使用“野马”一词来写天地浑茫一气之状的真实用意。可以说,庄子用的妙,玄英的阐释更妙。
在《则阳》篇中有段极美丽的文字,即“旧国旧都,望之畅然;虽使丘陵草木之缗,入之者十九,犹之畅然。况见见闻闻者也,以十仞之台悬众间者也!”然而这段极富丽之文字,来的却很突然,使人茫然不知所云。再看成疏:“国都,喻其真性也。夫少失本邦,流离他邑,归望桑梓,畅然欢喜。况丧道日淹,逐末来久,今既还原反本,故曰畅然。旧国旧都,荒废日久,丘陵险陋,草木丛生;入中相访,十人识九,见所曾见,闻所曾闻,怀生之情,畅然欢乐。况丧道日久,流没生死,忽然反本,会彼真原,归其重玄之乡,见其至道之境,其为乐也,岂易言乎!”[2]884原来,此段形象化描写喻指失性丧道之人见性返道时的畅然,而且,疏文相较原文更美,映出背景,细节丰富,情感饱满。
综上所述,成氏从文学角度透视《庄子》而使其文学特征得以凸显,又以文学手法写作《庄子疏》而使其成为类文学文本,成为庄学史上的名著,成为治庄者无法绕开的经典。笔者撰成此文,意在抛砖引玉,希望学界关注“注疏体”本身的文学特征和文体形态及其学术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