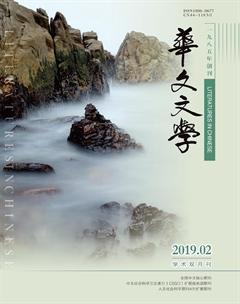对话:论莫言近作①的诗学价值
张丽凤
摘要:莫言新作是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自我创作的进一步推进,是其“艺术辩证法”的第三个阶段“把自己当自己写、把自己当罪人写”的实践。这一实践不仅发展了莫言以往以对立姿态建构对话的努力,还在实践中以本民族文化精神为基础真正地完成了对话。莫言新作展示了其对巴赫金对话诗学的创造性借鉴,同时也是其诗学真正完成的一个标志。
关键词:莫言新作;对话;诗学价值
中图分类号:I207.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677(2019)2-0103-08
早在2003年,李敬泽就断言莫言已成“正典”,并同时指出莫言在当代文学中的境遇,“身处剧烈的文化冲突的时代,莫言始终面临各种偏见和误解,他有固执的反对者,但无论反对他或支持他,人们都很难确定一种简明的、自足的立场,莫言过于宽阔,人们难以确定他的要害。”②2012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这种嘈杂的争论声音较之前有过之而无不及。以至于诺奖后莫言发表新作品时,“莫言新作的意义似乎超出了新作本身”,这观察莫言的误区本身再次提醒我们应该坚持“回到文学的莫言”③。然而,“回到文学的莫言”似乎也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翻开一系列的文学史教材,可以发现作家好像就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被放置在不同的文学思潮之中,寻根文学、先锋文学的抢夺,新历史主义与民间立场的封号,以及乡土作家的归类④,无不显示出研究的局限以及莫言创作自身所蕴含的丰富性。这些概念虽然都不同程度地概述了莫言创作的特征,但终究没能成为撬动莫言文学王国的万能钥匙,并未形成一种创作范式或创作理论的探索。所以当莫言新作出现时,张志忠从“现实与历史的双向拓展”肯定其价值,张清华感叹“在艺术的谱系上,《锦衣》的复杂性更是难于匆促说清”,⑤显然对莫言新作的意义还难以从创作的整体脉络上确定其价值。张清华注意到莫言在新作中看取历史与人物的视角与方式,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变得更加宽容,更加具有‘历史的和解意味,原来政治的紧张关系、伦理的紧张关系、经济与财富方面的对立关系,个人之间的爱恨与恩仇,都变得松弛和暧昧了,更具有戏剧性的意味,时间呈现出了巨大的容纳与悲悯,这些都有效地整合了原有的一切”⑥。莫言何以从对立走向统一,有没有体现其一贯的美学追求?
此時,我们似乎听到了巴赫金的警语,“评论家和研究者的脑子里,至今塞满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主人公的思念观念”,“作家的艺术意图,没有获得明确的理论上的阐释”⑦。面对这样一个多产而又具有鲜明风格的作家,如何在“坚持自己风格的基础上努力建构独特文学世界”⑧,其存在本身就是一个值得分析的文化现象。为了完成作家诗学的建构,巴赫金提出要从作家的“基本艺术任务出发,才能理解他的诗学的深刻的必然性、一惯性和完整性”⑨。因此,当我们想对莫言的新作给以恰当的定位,必然要将之放置在莫言的诗学探索之中。
莫言创作中的“对话”诉求
莫言在30多年的创作历程中,每一段时间都有不重复但重量级别不减的作品呈现,这除了他“同化”社会各方资源的能力外,显然与其开发乡土资源时的诉求相关,与其设计的“基本艺术任务”相联系。莫言在苏州大学的一次演讲中提出“真正的民间写作就是‘作为老百姓的写作”,是“写自我的自我写作”⑩,几年后当他再次谈论民间与底层时又再次强调“其实,写什么,怎样写,都可以忘记,只要记住‘人就行了。”{11}1985年,当莫言凭借《透明的红萝卜》真正地走上文坛,小说中那个皮肤黝黑眼睛透亮却绝不言语的黑孩成为莫言创作中不容忽视的“药引子”,黑孩的沉默不语使莫言在后来的创作中竭力创造话语、发出声音且一发而不可收,显示了莫言特有的对话诗学追求。
面对莫言小说中多重声音的塑造,不少学者将巴赫金诗学中的“复调”概念作为一个契入点给予定位。如周卫忠认为“莫言创作中生命主体在场的肯定,对主体思维话语的突出强调,其内在精神与逻辑视角与巴赫金复调理论中的对话思想相吻合”{12}。张灵从肌理与结构特征上对莫言小说中的“复调”与“对话”给予分析,既看到了两者的相似之处,又指出两者之间不同的表现{13}。然而,不管是强调两者相吻合还是不同,其本质上依然是巴赫金对“复调”、“对话”概念的论述,没有注意到莫言小说中的“对话”与巴赫金所述“对话”之产生根本不同。胡凤华虽然注意到莫言小说中对话的完成性与巴赫金“对话的不可完成性”有根本的不同,并认为以写声音为追求的《檀香刑》{14}“不是一部巴赫金意义上的对话小说”{15},却没有深入分析莫言建构对话的诉求及独特价值。莫言创作中的对话诉求源于其强烈而自觉的现实观照意识以及与现实对话的愿望。正如其当年创作《红高粱》是为了实现自我创作思想而“老同志多半不以为然”{16}的交代。几乎每个时期,莫言都怀着“作为老百姓的写作”理念与历史和现实对话,竭力挖掘被主流历史文化掩盖的声音。巴赫金认为“辩证法是从对话中产生的,然后辩证法又让位给对话,但这个对话已是高一级的对话,是较高水平的对话”{17}。与巴赫金的辩证法产生于对话不同,获诺奖之前莫言小说及话剧中的对话多产生于辩证法思维下的建构。莫言从不讳言自己曾受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影响,其关于辩证法的表述无论在小说创作中还是创作谈中都非常普遍。关于辩证法,莫言一开始就表现出他独特的理解而形成典型的莫言式辩证法。1988年,莫言在《我痛恨所有的神灵》一文中明确提出对“辩证法”的认识,“生活中处处充满这种对立,既对立又统一,果然是辩证法,人也是既对立又统一的物体,追求、厌倦、再追求、再厌倦……至死方休。人大概都如此,否则无创造、无进步,也无文学。文学是不是矛盾的产物、是对立两极相撞时迸发出的火花呢”{18}?莫言对“完整的世界”的构想就是极端对立事物的共同存在,虽然他对人生的认知有“对立又统一”的认识,但很快就显示了他所认识的“矛盾”与马克思主义“对立统一”之矛盾的差异。如“文学是不是矛盾的产物”与“是对立两极相撞时迸发出的火花”的表述是并列的同构关系,也就是说,在莫言那里,“矛盾”就是“对立两极”,而文学则是“矛盾的产物”,是“对立两极相撞时迸发出的火花”。后来,莫言对文学可能是“对立两极相撞时迸发出的火花”这一诗性表达进一步明确简单化,并将之作为自己艺术创作的核心动力。他认为自己的写作“第一个阶段把好人当坏人写,好人不是好得完美无缺,坏人也不是坏得一无是处;第二阶段,把坏人当好人写,也就是把坏人也作为人来描写。……往后的阶段是把自己当自己写,把自己当罪人写。”{19}如果说上述表述还重在呈现其创作的历史阶段性,那么“把好人当坏人来写,把坏人当好人来写,把自己当罪人来写,这就是我的艺术辩证法”{20}的表述则直接而明确地概括了莫言创作辩证性的艺术构思。莫言的艺术辩证法,并不是简单的技术手段,而是隐含着以现实为基础的“对话”诉求,表达被主流历史掩盖的声音,地主的勤劳善良,贫下中农的无赖奸诈都属此类。
巴赫金在论述复调小说时,特别提出“一切都是手段,对话才是目的”{21}。为了更好地表现对话,莫言除了用辩证法的思维建构对话,还采用话剧的形式表现对话。有学者早就看到了莫言对“五四”时期知识分子推崇话剧的价值意义,某种程度上“是戏剧这一文体‘形式的道德决定了他们对其倚重的态度”。{22}“形式的道德”就是赋予每个人物以“主体性”,发出自己的声音。莫言的文学创作极为注重对人物声音的寻找和呈现,而以话语为主的戏剧为其提供了非常便捷的形式。早在1987年,莫言在中篇小说《红蝗》中曾藉助女戏剧家的口吻充分表达了这一点:“总有一天,我要编导一部真正的戏剧,在这部剧里,梦幻与现实、科学与童话、上帝与魔鬼、爱情与卖淫、高贵与卑贱、美女与大便、过去与现在,金奖牌与避孕套……互相掺和、紧密团结、环环相连,构成一个完整的世界”{23}。可见,戏剧之于莫言,不仅是文学文体的实验,在某种意义上还是其认识世界、表达自我的一种方式。莫言对话剧一直有着深深的迷恋,不仅处女作是一部名为《离婚》的话剧{24},其小说《檀香刑》《蛙》等也多借用戏剧元素,显露出浓郁的戏剧趣味。
与以往“把好人当坏人来写,把坏人当好人来写”对立姿态下建构对话的形式探索相比,莫言在新作中对完成“对话”及其途径做了极为重要的探索。从创作理念及创作内容看,莫言的新作恰恰是其“艺术辩证法”第三阶段中“把自己当自己写,把自己当罪人写”的实践。莫言新作则以现实生活为基础,借助“锦衣”式的媒介以及自觉的自省意识,完成了真正的对话,实现“天下太平”。对话作为莫言创作中的一个核心诉求,对巴赫金诗学理论是一种创造性的借鉴,“对话”在莫言的创作中已“成为‘现象文本之下具有生产、生殖能力的‘基因文本的构成元素”{25}。以往的作品建构对话展现了莫言对现实不同声音的挖掘,新作中对话的完成又展现了其对中国生命文化的肯定,不仅别于巴赫金诗学中“对话的不可完成性”,而且展现了中国人特有的生命觀。《故乡人事》《等待摩西》中诸多人物以地道的生活话语登台露面,亦以平和的方式完成对话,往日极端对立的情感此时已汇成一首生活的曲子:“最柔和的和最坚硬的,最冷的和最热的,最残酷的和最温柔的,混合在一起,像一首激昂高亢又婉转低徊的音乐。这就是劳动,这就是创造,这就是生活,少年就这样成长,梦就这样成为现实,爱恨情仇都在这样一场轰轰烈烈的锻打中得到了呈现与消解”{26}。《锦衣》借助“锦衣”这一媒介以隐喻的形式完成了革命话语与民间话语的对接,使对立的两种文化在某种程度上完成对话。不管是获诺奖之前建构对话,还是新作中完成对话,都带有鲜明的价值诉求,莫言期望通过对话意识观照历史与现实,揭示现实生存中人性与文化的复杂性。正如新作小说《等待摩西》“本来已经结尾了,但时过境迁,因为小说素材所涉及的人物原型的故事又往前发展了,小说本身也就有了再生长的需求”{27}而重写。《高粱酒》的戏剧改编则是针对媒介发生变化的现实,为了让大众乃至世界范围内的读者更好地接受与传播而做出的改变,这其中隐含着“更高的目标追求”{28},恢复和发扬民族特有的艺术文化,同时以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方式完成新的文化与思想的传播。
莫言新作对“对话”途径的探索及完成
为了建构对话,莫言有意以极端对立的方式结构自己的作品,他完全不在意别人的不解与误解,不理会那些残忍的刺激、语言的毫不节制以及“以丑为美”的批判。那时候他的文学生命形态就像挥舞着长矛的“堂吉诃德”在文学疆场上冲撞,无所顾忌。然而,获得诺奖之后,面对更加复杂的读者环境和社会环境,超出文学本身的批评与责难一度让作家百口莫辩。这时候作家似乎想起早在2004年的一次采访,当记者问“您谈到过自己很怕谈思想,思想很可怕,您觉得一个作家可以不靠思想来写作吗?”时,作家才警觉地发现现实中有很多“听话不听音儿”的读者,他们看不到夸张、反讽、象征背后隐含的深意,当时作家明确表示“一个作家,不可能没有思想”,同时认识到“看起来今后我应该改变说话的方式,不应该使用这种反讽的腔调”{29}。所以在新作中,莫言更加注意读者的接受,也从以往以极端对立方式建构对话过渡到对完成对话途径的探索。新作中的人物形象以鲜明的自我意识及反省意识展现了莫言对其创作理论“艺术辩证法”的推进和实践,即“把自己当自己写,把自己当罪人写”。莫言的新作少了建构对话的痕迹,本色地展现各个人物的话语,并在主体本色的呈现中处理好各种关系,完成对话。无论是《故乡人事》《锦衣》《七星曜我》,还是后来的《天下太平》《等待摩西》以及改编的话剧《高粱酒》、歌剧《檀香刑》,都在以往构建对话的基础上继续推进对话,小说中的“我”不仅少了强烈诉说的欲望,对“他人”亦给予自觉的理解,对不同层面的文化也试图借助合适的媒介完成沟通,最终借助“锦衣”完成了“天下太平”的对话。
在对话的本色出演中,《左镰》的开场具有典型的代表性,小说中对“我爷爷”“老三”“老韩”“赵大叔”等人话语的描述,可谓神来之笔,每个人的话语平实简练,没有以往“辩论赛”的痕迹,寥寥数语已将人物的情感思想展现无遗,细看又不过是从现实生活中截取一段而已。作为木匠的“我爷爷”与铁匠“老三”和“老韩”之间更是在冲突的对话中完成了真正的对话。
“老爷子,”老三道,“你就放心吧,大到铡刀小到剪刀,没有我们干不了的。”
我爷爷问:“绣花针能打吗?”
“绣花针打不了,”老三笑着说,“老爷子,咱们不是同行吧?您是木匠。”
“新打一把,一块钱;这旧斧头儿翻新,一块五。”老韩道。
我爷爷说:“你们三个别打铁了,去劫道吧。”
“中就放下,不中就拿走!”老韩斩钉截铁地说。
“好,”我爷爷说,“你们可要看好了,我这把斧头可不是一般的斧头。”
“鲁班用过的?”老三嬉笑着问。
“鲁班是个传说,管二是个真人。”我爷爷说。{30}
人物本色出演之所以能完成对话,就在于人物的所有本色出演中并不是过分地强调“我”,而是隐含着对“自我”的审视与对“他人”的理解。人不仅能意识到自我的存在,同时能在“我”与“你”以及“我”与“它”之间形成一种认知,在“关系”中完成对话,才是对话的根本。正如马丁·布伯在讲“对话”时特别指出,“存在”并非“我”自身所具有,而是发生于“我”与“你”之间,个体“我”不应当把他者视为客体而形成“我——它”关系,而是应当建构平等的“我——你”关系,使人与世界、与他人之间构成平等的相遇,这种“我——你”关系和敞开心怀便被称之为“对话”,最终“人于对‘它之世界的反抗中走向超越,人于关系中实现了超越”{31}。从这个意义上讲,莫言的新作正是对“把自己当自己写,把自己当罪人写”理念的践行,同时还是对实现对话可能性途径的探索。
自觉与自省作为主体意识中最鲜明的部分,往往是处理“我”与世界关系极为重要的方面,也是可以完成对话的根本。小说《地主的眼神》与《左镰》中对“我”当年行径的羞愧与审视,恰恰显示了作家的自省意识以及在自省中与历史、现实完成的对话。莫言不仅写“我”的自省与自觉,他对所有的人物都赋予这样的自省与自觉。如《锦衣》中婆媳关系的书写,就呈现了婆媳之间既有冲突又能相互体谅的现实。在第七场“母悲妻盼”里,季王氏屡次使唤春莲,将“公鸡”当成春莲的丈夫:“你去抓两把高粱,把你那丈夫喂喂呀!”从不顶嘴的春莲每次都从自我的主体性出发坚决地给予否认:“娘,我的丈夫在日本留学,它是一只公鸡。”季王氏后来也只好改口。而面对婆婆的不关乎个体身份价值时的责骂,春莲则又能继承传统的孝道,没有反驳,多次说出“儿媳知错了”“儿媳听娘吩咐”“儿媳听娘的”。对婆婆这样一个角色,作家不仅写出她的苛刻,还也写出她对儿媳的关爱,如悄悄地察看儿媳的状态。这里呈现的婆媳关系和《丰乳肥臀》中尖刻恶劣的“婆媳关系”显然不同,前后发生的变化恰恰反映了莫言在“关系”中寻找“对话”的可能、和解的途径。人与人之间最终要走向的不应该是一方压倒另一方的“对立”,而应该是互相的让步与理解。在“关系”中完成相互理解的“对话”,在《故乡人事》《天下太平》等新作中得到了更为全面的展现。如果说诺奖之前的莫言创作更强调“作为老百姓的写作”,面对以往的历史主流和文化,有一种建构“对话”的冲动,因而有意以反叛传统的方式写作,那么获得诺奖之后的新作则以极为平和的心态来观照现实。虽然他依然执着地写高密东北乡那块土地,但是如何完成对话却成为他着意探索的方向。如他不再刻意强调高密东北乡杀人越货的土匪文化,在话剧《高粱酒》中将历来被大家称赞充满野性的余占鳌改编成了不违法的人物形象;他也不再像书写《天堂蒜薹之歌》那样强化尖锐的官民对立,而是以民众理解官府的角度写出现实中的《天下太平》;他也不再像《良药》那样执着地坚持乡土文化的自在,而是以“锦衣”为媒介探索互相隔膜的民间文化与革命文化互通的途径。甚至面对《生死疲劳》中六次轮回都不甘心的“斗士”地主西门闹,在新作《斗士》中,作家不禁祈愿:“他那颗被仇恨和屈辱浸泡了半辈子的心,该当平和点了吧”{32}。
除了从对话的内涵探索对话的可能性,莫言还颇为注重对话形式的探索。与以往借助话剧形式建构对话一样,莫言在新作中更加注重对话剧这一形式的运用,并借助话剧的形式探讨传统与现代、官与民对话的可能,话剧《锦衣》的创作较为鲜明地展现了这一诉求。莫言说,“我想把这样一个清末民初时山东学子留日归来闹革命的事件跟‘公鸡变人故事结合在一起”,把原来的神话解构掉而完成现代的改造,“即革命党人利用民间传说,把自己的妻子变成了一个革命道具,引诱满清的县令带着他的武装出来处理公鸡变人的荒唐案件,而革命党则乘虚而入攻下县城,完成了高密县的革命”{33}。革命话语要想在乡间被接受,必须借助“锦衣”的外在装扮,同时借助传统文化中鸡精故事的爱情完成现代的革命转化。所以,与其说《锦衣》的书写是因为“莫言十分钟爱这个民间故事,为了让其具有现代意义,他以辛亥革命前期为故事背景,以推翻清朝统治、建立民主共和为立意,让旧瓶装上了新酒,达到了化腐朽为神奇的艺术至境”{34},不如说莫言借“锦衣”的故事完成了一种革命文化的叙事,锦衣式的文化对接也显然成为完成文化“对话”的重要方式。正如春莲“嗔怒”地说出“哪个是你的娘子?”后,已经将“你”和“我”联系起来,同时也将“鸡精”与“革命党的首领”的身份联系起来,“我是鸡精的娘子……你是革命党的首领……”{35}。如果我们足够细心的话,会发现《锦衣》中对话形式的探索恰恰是革命红色经典“白毛女”故事的变异。
如果说莫言前期的创作是以辩证法的思维建构对话,其新的剧作与小说则是在前面创作的基础上完成真正的对话,是在更高一层意义上完成了“复调”。从这个意义上讲,莫言的新作是其“艺术辩证法”诗学思想的实践,将“文学的莫言”推进了一步,完成了一次质的飞跃。
莫言“对话”诗学的民族文化特征
莫言的对话诗学与巴赫金的诗学,不仅发生的缘起不同,最终追求的目标也不尽相同。巴赫金认为陀思妥耶夫斯遵循的最高的思想准则是“要忠实于一个权威人的形象”,思想探索的结果应是“出现一个理想人物的形象,或者是基督的形象,应该由这个形象或这个上天的声音来圆满地完成这個多种声音的世界,由它组成这个世界、支配这个世界”{36}。而莫言诗学的完成在于将文学真正地还诸于生活,最终在认识生活的过程中完成自我情感的安放以及自我与世界关系的认知。正如新作《七星曜我》一样,作家“以独特的才情与见识,与当代世界文学大师对话,这更像是一种隐喻:今日的世界格局中,中国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中国文学的影响空间也变得日渐阔朗和通透”{37}。莫言在新作中完成的对话诗学,展现了其对民族文化的深层次认知与书写,以及其面对世界时的文化自信。
莫言对话诗学完成的重要标志就是笔下的每一个人物不仅实现了“用自己的腔调说话”,作家自己也在文学的世界里“大闹一场”之后归于书写平静的日常生活,完成了其以往论述的观点——“真正的有用的思想其实都是从生活中抽象出来的大实话”{38}。以建构对话始,以完成对话终,莫言在建构与完成之中实现了对其创作理论“艺术辩证法”的完整呈现。这不是回到原点,而是通过几十年的探索完成了一次更深切的认知。正如其早期的小说因为积郁太深的感情,往往是“一旦得到了宣泄的机会,其势也就如大河奔流,滔滔不绝,泥沙俱下”{39},并形成不能节制的语言而被人诟病。而在新作中则以“更显平静”和“节制”的形式“传递了复杂的人生况味”{40}。当他以极端对立的姿势建构对话,写出“人的成长与觉悟”与“人的困境与无奈”后,却未能在现实中建构起支撑自我的内在力量。正如“当带有悲剧美和崇高美的荆轲被还原为一个普通人,甚至更低一些的时候,我们获得了一个批判的现实,但同时我们的批判也失去了支点,就是还需要得到一种建构”{41},而此时的作家也不知道人生的意义,生活的真谛,只能呼唤“高人”来点化自己:“高人啊,高人,你说过今天会来,执我之手,伴我同行,点破我的痴迷,使我成为一个真正的人”{42}。而到了新作,莫言一改以往创作的夸张、变形、象征,以无比平静的样式沉到生活之中,完成了对以往的探索与追问。《我们的荆轲》中“天问”式的迷茫,在新作《左镰》中已是心平气和的认知,“这就是劳动,这就是创造,这就是生活”{43}。也像《等待摩西》里描写的那份安静与谐和:“我看到院子里影壁墙后那一丛翠竹枝繁叶茂,我看到压水井旁那棵石榴树上硕果累累,我看到房檐下燕子窝里有燕子飞进飞出,我看到湛蓝的天上有白云飘过……一切都很正常,只有我不正常。于是,我转身走出了摩西的家门”{44}。
莫言诗学的完成体现在其面对世界时的文化自信。“正是通过与‘自我和‘他者的双重性、多层面的‘对话,成就了莫言及其文学世界的‘文化自信”{45}。“莫言的作品植根中国本土文化、接续中国文学传统,融贯中西、连接古今,其文学作品的流变和海外传播与接受恰是中国文化愈发自信的体现”{46}面对世界上的文学高炉,莫言不仅没有被灼伤,而是像一个淘气的孩子一样喊出“福克纳大叔,你好吗?”这种文化交流的自信,正是源于对生存的体悟,对人类普遍命运的关怀,正如莫言喊出这句话时不止是因为他读了福克纳的作品,更是因为看了有关福克纳的图册后的身心震撼:“他的这副形象一下子就把我送回了我的高密东北乡,他让我想起了我的爷爷、父亲和许多的老乡亲。这时,福克纳作为一个伟大作家的形象在我的心中已经彻底地瓦解了,我感到我跟他之间已经没有了任何距离,我感到我们是一对心心相印、无话不谈的忘年之交,我们在一起谈论天气、庄稼、牲畜,我们在一起抽烟喝酒,我还听到他对我骂美国的评论家,听到他讽刺海明威……”{47}对人类普遍的生存图景的发现与关注,让莫言与世界上的文学家们心气相连。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托马斯·英奇特别指出,即使莫言没有读过福克纳,他也很可能会写出同样的内容。因为两位作家有着类似的以农村大地为生活背景的经历,并且承受了20世纪的政治、工业变化带来的类似的影响。不管是汇合还是影响,对于莫言来说,重要的是福克纳的启示,即对传统的讲故事方法的挑战和改变的自觉精神,他的那种通过叙述关于某个特定地区的故事反映全人类的普遍性问题的能力以及那种相信人类即使在最艰难的条件下也能生存、忍耐并延续下去的信心,而不是照搬他的内容和技巧。如果我们继续借鉴英奇对福克纳的评论来概述莫言,似乎并没有什么不妥,尽管“写的是某一个特定地区的人和事,但道出的却是整个人类的命运史、人类社会的‘螺旋发展史”{48}。就像小说《等待摩西》所展现的那样,因为历史形势柳摩西改成了柳卫东,因为时间的沉淀柳卫东又改为柳摩西,看似是回到了原点,实际上则是30多年的生活使主人公终于完成了一个被建构到反叛再到自我定位的过程。
莫言的诗学价值在于他以自己特有的艺术辩证法,建构对话并最终完成对话。在这一建构与完成之间,莫言是对文化知识权力的一种深刻认知,既具有世界性的意义,更有民族文化的独特性,最终走向和解更显示了中华民族文化绵延至今的一种血浓于水的亲情。如小说《等待摩西》,这与其说是宽恕与原谅,不如说是中国人生命本身的一种状态。从表面看马秀美作为东北乡所有教徒中最虔诚的信徒终于等来了自己的“摩西”,而“摩西”也皈依了基督教,但这并不代表莫言想让人物皈依基督教,基督教不过是莫言为自己的作品穿的又一件“锦衣”而已,这从马秀美向驶往全国各地的车上贴的“寻人启事”中可见端倪。信中对柳卫东的呼唤没有借重一丝所谓的羔羊返途,而是一封充满了传统亲情味儿的信:“卫东,孩子他爹,你在哪里?见到这封信,你就回来吧,一转眼你走了快三十年了,咱的外孙盼盼都上小学三年级了,可他连姥爷的面还没见过呢。卫东,回来吧,即便你真的在外边又成了家我也不恨你,这个家永远是你的……我把家里的电话和女儿的手机都写在这里,你不愿理我,就跟女儿联系吧……”{49}借助孩子他爹、外孙、女儿等亲情身份对柳卫东给予“招魂”,而马秀美在向上帝祈祷的时候,其面向的绝对不是信仰问题,而是现实中的实际问题,“上帝”也不过是她要找回自己丈夫的一个工具而已。莫言这种中西文化精神的融合,《十月》杂志社的宁肯一开始就捕捉到了,正如其阅读之初感觉到这个作品“关键是一种大的情怀,一种大的精神视野,一种中国现实、中国氛围、中国的讲述传统与以基督教文明为基础的西方文化如此自洽、水乳不可分的融合;大悲悯,大善恶,东方的,西方的——天作之合。”{50}当生命在现实中完成对话的时候,作家放弃了以往作为文学王国里做国王的自信与狂妄,“我能想象出马秀美对抛弃了她和孩子35年后又突然出现的柳卫东的态度吗?我想象不出来,又很想知道,那怎么办?很简单,去问。”现实中的马秀美不是我想象中的“腰背佝偻,骨瘦如柴,像祥林嫂那样木讷”,而是“身体发福,面色红润,新染过的头发黑得有点妖气,眼睛里閃烁着的是幸福女人的光芒”。所以此时我意识到“我知道我什么都不要问了”{51}。
巴赫金对世界的描述是未完成的,因为“民间文化对于世界的理解持一种未完成性的态度”。与巴赫金的这种未完成状态不同,莫言在几十年的历史中检验跟踪人物,最终让他们在生活中完成真正的对话,显然这是对巴赫金诗学理论的突破,也是最能展现中华民族文化特色的地方。面对磨难,中国人总是以强韧的生命力生存着;面对仇恨,他们又总是以最大的善意在时间中谅解。不管是被父亲砍掉右手的田奎,还是30多年来一直苦苦等待突然失踪了丈夫的马秀美,他们在生命的谱系中就是“我爷爷”“我奶奶”,是为了生存抗争的孙丙和上官鲁氏,也是六世轮回都不放弃自证清白的西门闹和敢于与历史潮流对抗坚持单干的蓝脸。即便是获得国际大奖之后,莫言仍然非常谦卑地回到家乡,走到老百姓之间,和他们聊天、开玩笑,听他们讲村里的故事,并不以个人的艺术想象改变现实。“一切都很正常,只有我不正常”{52}。莫言以对话为诉求,通过艺术辩证法写出“对话”的多层次性与可能性,最大限度地展现了“人”的存在状态。其新作对实现对话途径的探索,在当下中国乃是冲突不断的世界范围内,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① 这里的近作包括:《故乡人事》(《地主的眼神》《斗士》《左镰》)《收获》2017年第5期),《天下太平》(《人民文学》2017年第11期);戏曲文学剧本《锦衣》和诗歌《七星曜我》(《人民文学》2017年第9期)《等待摩西》(《十月》2018年第1期)《檀香刑(歌剧)》(《十月》2018年第4期),戏曲文学剧本《高粱酒》(《人民文学》2018年第5期)
② 李敬泽:《莫言与中国精神》,《小说评论》2003年第1期。
③ 吴永强:《莫言:锦衣与故乡人事》,《齐鲁周刊》2017年第38期。
④ 以较为典型的文学史为例:朱栋霖、丁帆、朱晓进的《中国现代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1版与2012年第2版)在介绍“80年代小说”时将莫言与军事作家徐怀中放在同一节。洪子城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将之归入“市井、乡土小说”系列。陈思和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从民间立场角度将红高粱视为“对战争历史的民间审视”。金汉的《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上海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雷达的《近三十年中国文学思潮》(兰州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陶东风、和磊的《中国新时期文学30年(1978-2008)》(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孟繁华、程光炜的《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以及《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第二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吴秀明的《当代中国文学五十年》(浙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都将莫言归入寻根文学系列。需要说明的是,同样由吴秀明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写真》(浙江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则将莫言和马原放在同一章讲,并认为莫言小说“涉及面宽,既有战争,又有乡习民俗、地域风情,既有历史寻踪,又有现实生活造像,若硬将其归入哪类题材皆不合适且不明智。”王庆生的《中国当代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高玉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第二版)(浙江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樊星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则将莫言纳入“先锋”系列,董健、丁帆、王彬彬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新稿》(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将莫言纳入“中国式‘现代主义写作”。
⑤ 张清华:《莫言新作〈锦衣〉读记:说不尽锦衣夜行警世真幻》,载2017年9月4日《光明日报》。
⑥ 张清华:《主持人的话》,《小说评论》2018年第6期。
⑦⑨{17}{36} [苏]巴赫金:《巴赫金全集》第五卷,白春仁、顾亚铃译,河北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59页;第6页;第539页;第126页。
⑧ 朱寿桐:《汉语新文学通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版,第314页。
⑩ 莫言:《用耳朵阅读》,作家出版社2012年版,第70页。
{11}{29}{38}{39} 莫言:《碎语文学》,作家出版社2012年版,第313页;第255页;第255页;第247页。
{12} 周卫忠:《复调理论与生存世界的主体间性——从巴赫金诗学看莫言小说的复调叙事》,《齐鲁学刊》2017年第5期。
{13} 如文章认为莫言的复调表现较为隐蔽,是微型和不完整的对话,是结构方式的对话,有主题泛化的特点。张灵:《莫言小说中的“复调”与“对话”——莫言小说的肌理与结构特征研究》,《江汉大学学报》2010年第3期。
{14} “在本书创作的过程中,每当朋友们问起我在这本书里写了些什么时,我总是吞吞吐吐,感到很难回答。直到把修改后的稿子交到编辑部,如释重负地休息了两天之后,才突然明白,我在这部小说里写的其实是声音”莫言:《檀香刑》,作家出版社2001年版,第518页。
{15} 胡凤华:《“对话的不可完成性”质疑——巴赫金对话理论解读与评析:以〈檀香刑〉为参照对象》,《山东外语教学》2005年第1期。
{16} 莫言:《关于〈红高粱〉的写作情况》,《南方文坛》2006年第5期。
{18} 莫言:《北京秋天下午的我》,海天出版社,2007年,第316页。
{19} 张旭东:《我们时代的写作——对话〈酒国〉〈生死疲劳〉》,上海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第171页。
{20} 杨娇娥:《莫言之言》,《一代大家莫言的黄石情缘》,载2012年10月12日《东楚晚报》。
{21} 钱中文:《难以定位的巴赫金》,载1996年2月2日《文艺报》。
{22} 马兵:《亦史亦野亦锦绣》,《齐鲁周刊》2017年第38期。
{23} 莫言:《食草家族》,作家出版社2012年版,第197页。
{24}{42} 莫言:《我们的荆轲》,作家出版社,第208页;第87-88页。
{25} 郭洪雷:《个人阅读史、文本考辨与小说技艺的创化生成——以莫言為例证》,《文学评论》2018年第1期。
{26}{30}{32}{43} 莫言:《故乡人事》,《收获》2017年第5期。
{27}{33} 莫言张清华:《在限制的刀锋上舞蹈——莫言访谈》,《小说评论》2018年第2期。
{28} 张志忠:《论莫言对现实与历史的双向拓展——以其新作〈故乡人事〉和〈锦衣〉为例》,《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3期。
{31} [德]马丁·布伯:《我与你》,陈维纲译,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9页。
{34} 黄大军:《空间与地方:莫言剧本〈锦衣〉的文化政治解读》,《当代戏剧》2017年第6期。
{35} 莫言:《锦衣》,《人民文学》2017年第9期。
{37} 施战军:《卷首语》,《人民文学》2017年第9期。
{40} 《卷首语》,《十月》2018年第1期。
{41} 唐凌:《我们的荆轲,以何种面容出现?——深度访谈〈我们的荆轲〉编剧莫言》,《艺术评论》2011年第10期
{44}{49}{51}{52} 莫言:《等待摩西》,《十月》2018年第1期。
{45} 丛新强:《文化自信:与“自我”和“他者”的对话——以莫言及其文学世界为例》,《东方论坛》2018年第1期。
{46} 宁明:《文化自信·本土化·全球化》,《东方论坛》2018年第1期。
{47} 莫言:《福克纳大叔,你好吗?》,《文学界》2000年第5期。
{48} [美]M.托马斯·英奇:《比较研究:莫言与福克纳》,金衡山编写,《山花》2001年第1期。
{50} 宁肯:《〈等待摩西〉以及作者的那些事儿》,《小说评论》2018年第6期。
(责任编辑:黄洁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