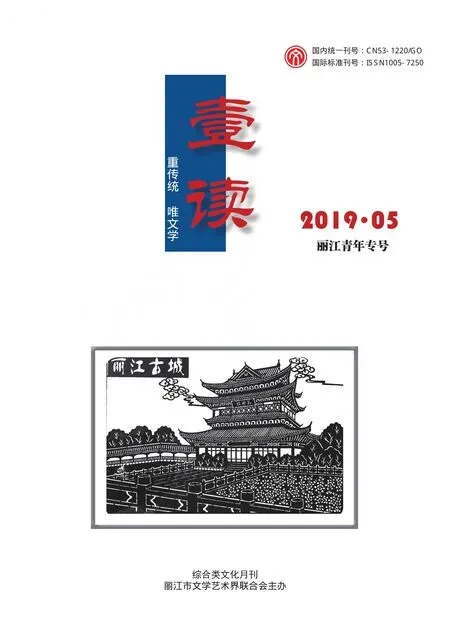童年
◆肖亚豪
一
我们赶着牛羊回村的时候,太阳刚刚爬上光加阿别山,露出小半边脸来。晨光筛过松木的间隙,柔柔地落在坑坑洼洼的泥泞路上,羊粪蛋子显得亮晶晶、滑溜溜的。牛粪堆旁临时挖掘的洞穴里,屎壳郎还在睡懒觉,洞穴旁堆积着松软的细土。狗尾巴草的叶片上流转着一粒粒晶莹饱满的露珠。过了村口,阿芝姆挥着牧鞭呦喝一声。牛羊开始自动分流成若干群,往自家的圈子里走去。我听到奶奶呼唤羊崽子归圈的声音。她立于院坝前的柴禾堆上,手掌拱成半圆形,搭在唇边,
往屋后叫唤着。屋顶飘荡着炊烟,隐约传来“滋滋”的声音,我知道小姑正在做菜,我闻到了洋芋丝煮干酸菜的香味。把牛羊赶入圈,只见暖和的日光下,一只母鸡领着十几只鸡仔在院坝中悠闲地踱步。
屋里爬满了早晨的阳光,暖洋洋的。梁木上悬着一根长长的铁钩,钩头挂着水壶。火苗翻卷着舌头,舔舐着壶底。水涨了,撞开壶盖溢出来,喷溅在火塘里,木炭灰飞腾了起来。爷爷坐在竹席上,把天菩萨盘在头顶,开始煮茶了。他用火钳敲出一块粑粑茶,放在茶罐内,用火红的木炭烘烤,一种浓郁的香气在屋里弥漫开来。他吃一口燕麦粉,喝一口酽酽的粑粑茶。喝完茶,爷爷才开始吃早饭。他不和大家在一个锅里吃菜。他把饭菜舀进一个小饭盒,置于火塘边,用炭火烤一烤再自个儿慢悠悠地吃起来。
按照惯例,我今天的任务完成了。早在年初,我们兄弟俩就已经商量妥了。我们干不了什么农活,只能帮着爷爷放牧而已。空宗伊德村每天放牧两次。早晨趁着朝露未干之时赶着牛羊去村子外围的野地里放牧,据说吃了朝露后,牛羊容易长膘。等太阳出来的时候,把牛羊赶回圈里。吃过早饭,再赶到更远的林子里,白天漫长的放牧时间才正式开始。大哥爱睡懒觉,早上由我放牧,白天的任务交给他。我虽牺牲了睡懒觉的时间,但整整一个白天我就自由了。今天,我要跟着小伙伴们去户外的油菜地里捉熊蜂。
我们村有大片大片的油菜地,花开了就一片金黄。今天,各色的蝴蝶和蜂子闹哄哄的。有好些种蜂子,我叫不上名来。黄蜂的刺儿有毒,被蜇了,痛痒难耐,不过艾草叶似乎可以解毒,我记不真切了。听奶奶说,驼背蜂毒性最烈,能让人腹痛而亡。最好欺负的是熊蜂,个头大,动作慢,笨拙得紧。我们那儿有两种熊蜂,一种颈部雪白,一种橙黄。后一种居多。金黄的油菜花上伏着各类蜂儿,远远的看不着,走近时才发现花瓣间有蜂儿在蠕动,给人一惊,飞起来,嗡嗡然绕着我们的头顶盘旋两周再落到近旁的油菜花上采蜜去了。脱下外衣,往熊蜂落着的油菜花上一罩,便罩住了,把它的屁股置于拇指上,轻轻一摁,毒刺就挤掉了。找一条细线,系住它的后腿,放飞了玩,能玩上老半天。
阳光很毒,有微风,路边的琉璃草绽开淡蓝色的小花朵,摇曳着。穿过油菜地,包夹在洋芋地与苦荞地中间的一大块陡坡上,连片生长着泡儿刺。浅红的枝干上,稀疏的叶片间,挂着一粒粒血红娇艳的果实。抓住一株杂草,腾出一只手来,摘一粒放入口中,嫩滑多汁,甘甜微酸,极爽口。吃够了,撇一片肥大的苍耳叶片,卷个卷,用草茎缝合,能装好多泡儿刺。奶奶缺牙,顶爱吃泡儿刺。带一些回去给她,她保管高兴。
二
布谷鸟叫了,我们背着炊具到了光加阿别山后的山涧边。溪水哗啦啦流着,茂密的林子里传来黑头鸪欢快的叫声,颠颠雀飞到溪水旁,磕头拜礼似地跳了一阵又飞走了。阳光洒在溪水里,反射出一道道粼粼的波光。水底的石子儿光滑圆润,水草生长在石缝间,水绵绿油油的,随着水流飘荡着。用石块搭好灶台,解下披毡和斗蓬,铺在溪边的草坪上。找来干柴枝,划开火柴,点烧一把干枯易燃的榕叶,冒一股浓烟,火苗子腾腾的,接着是哔哔剥剥的燃烧声。架好锅,开始煮饭。我们闲不住,爷爷准许我们去玩一会儿,顺便看看牛羊。我们在溪边拣了一兜小石子作为弹弓的弹药,转身钻入了身后的林子里。大山雀,斑鸠,百灵,白鹡鸰,画眉,我们那儿的鸟可真多。有几种鸟不能动,布谷鸟,喜鹊,杜鹃是吉祥鸟,要保护。乌鸦,猫头鹰也不能打,否则不吉利。我们捉得的山雀多些,斑鸠最不容易捕获。除了用弹弓,有时还用套具,那是用马尾编结的简易套环。将其固定于鸟巢上,鸟儿觅食归巢时,欲入巢而不得其径,只好把脖颈伸入套环中喂幼仔。缩颈时,就被套住了,鸟只好扑腾,套环随之缩紧直至让它无法动弹。此时,它只好束手就擒了。祖父只捕山鸡,那种大鸟很难捕,有一套专门的复杂的程序,小孩子是不得要领的。我曾经喂养过几只雏山鸡,个头小小的,像黄色的小鸡。可惜很挑食,养不活。这片林子里的鸟很怕生,人一来,躲得老远,我们没有捕获一只鸟。只好收了弹弓,去附近吃索玛花。小小的山坡,被掩映在红白相杂的花海中,蜜蜂嗡嗡地闹着。一种醉人的花香弥漫在空气中。摘一朵索玛花,扯下花瓣放入口中,薄薄的甜意布满舌尖。
爷爷吹一声哨,我们就回来了。饭菜已煮熟,今天是放牧节,每年就这一回,我们把家里珍藏的最好的腊肉和香肠都带来了。吃完了,趴在溪水边,喝口水,收拾好炊具,已过了正午。太阳挂在正空中,天空瓦蓝深邃。在堆满松针的阴凉处躺一阵,等阳光的毒辣劲儿一过,我们钻出来,看看时间还早,于是再次生火,去松林里砍下松塔,在篝火里烧,一熟,照头撕下来,松籽如雨点般落了下来。
太阳从西边的山头落了下去。远处的山坡被夕阳染红了。我们赶着牛羊过了村口。今天颇有收获,每个人都提回了一大袋松籽。夜间,围坐在火塘边,点上松明唠嗑的时候,松籽是难得的零食。
三
惊蛰一过,雨开始淅淅沥沥地下了起来。几场夜雨之后,马屁泡如肿胀的小肉瘤,突然间摇头摆脑地钻出了地面。等雨水稍丰沛一些,各种野菌相继破土。四叔家的后山坡有一大块冷杉林,林子很密,但冷杉的叶子多半长在树干的腰部以上,地面很开阔。新雨初霁的午后,猫着腰,小心地拨开冷杉的枝叶,探着脑袋往林子里一看,只见冷杉树底部开阔的地面上,正簇拥着成片的谷黄菌,菌帽上流转着一粒粒晶莹透亮的水珠,在阳光的映照下闪烁着迷人的光芒。进入雨季后,那片冷杉林俨然成了四叔家的菜园子。每天早晨和傍晚,四叔总要进入林子里摘一些谷黄菌,或炒或煮,一成不变的菜肴,吃来吃去总不嫌腻味。有一天傍晚,我跟着爷爷放羊回来,路过一片白杨林子,偶然发现一丛白色的菌子簇拥在一根枯萎的木桩上,爷爷喜出望外,告诉我那是平菇,极难找到。当晚,和猪肘子一起炖,真香。
我们村还有好些种菌子,青盖子模样最俊,天蓝色的盖子顶着天蓝色的天空,阳刚而不乏灵秀之气,味儿也好,其口感与谷黄菌只在伯仲之间。只不过谷黄菌宜炒宜煮,而青盖子宜烘烤罢了。大红菌外部火红,里部素白,烤熟后,入口有一种似咸非咸,似涩非涩的感觉,仿佛放了过量的味精似的。辣菌呈白色,不过色泽稍暗,表皮粗糙,口感次,有辣味,我很少吃。奶浆菌呈淡红色,用手轻轻一捏,便渗出一些乳白色的汁液来。可以生吃,蒸煮或烤熟后反而没味儿了。鸡油菌和鸡屁股菌也少见,鸡油菌个头伶仃,黄黄的,味道如何,我却记不真切了。鸡屁股菌色泽暗红,个头与鸡油菌相仿,味道极好,有嚼劲儿,汤汁鲜极了。黄盖伞有毒性,但毒量小,只要熟食,不碍事儿。黑虎掌菌味苦,但世间偏有人嗜苦。爸爸就极爱吃黑虎掌菌,雨天煮一锅洋芋,先把黑虎掌菌烤熟,撕成片状,加盐、葱、蒜,拌匀,就着洋芋吃,他将其视为人间至味。
这些菌子都价贱,价格贵的当属松茸和牛肝菌。松茸的生长地点极其隐秘,产量也小,但只要保护好生长环境,不要过度采摘,来年还可再生。有经验的人知道多个不为人知的松茸生长点。所以找松茸凭经验,找牛肝菌则靠运气,我不知道松茸生长地,也没有经验,从来不奢望找到松茸。但只要细心,多少总能收获一些牛肝菌。一个暑期下来,通过卖牛肝菌,能积攒三四十块钱。邻村放电影,票价大约是五毛钱,只要白天找野菌时勤快一点,运气不要太背,晚上的电影票钱总会有着落。
我那时嘴真馋。有一次,爷爷拾回一袋青头菌,我偷偷地烤了吃。由于没有烤熟,吃坏了肚子,腹泻得厉害。后来送到乡镇医院挂了好几天针水,吃了不少药才见好。但肠胃落下了毛病,只要饮食稍不注意,便有旧病复发之虞。我自此不敢再乱吃野菌了。
四
傍晚,天边挂着大朵大朵火红的晚霞。我们坐在屋后的陡坡上,一边听妈妈讲故事,一边等爸爸回家。爸爸是我们村里唯一吃公家饭的干部,他在乡镇中心上班,很少在家。要过彝族年了,他大约要回家了吧。等了好几天后,某个落霞满天的傍晚,爸爸穿着西服,系着领带,手提公文包,披着火红的晚霞出现在村口那片燕麦地中间的小路上。
第二天,爸爸带着我们将每间房间彻底清扫一遍后,抬着一把矮凳在院坝内坐定,面前摆着一块磨刀的大砂石,左右两边是许多明晃晃的刀具,他嘴里叼着一根香烟,悠闲地吐着烟雾,嚯嚯地磨砺起刀具来。
这天夜里,我怎么也睡不着。好不容易睡去后,朦朦胧胧地听得外面窸窸窣窣的微响,猛地睁开眼,细听之时,是妈妈在生火了。我赶紧爬起来,拉开房门。外面仍是一片朦胧的景象。爸爸开始在院内挖烧水用的临时土灶了,他抡着铁锄,脸上洋溢着欢喜的神情,耐心地挖着。不一会儿,便挖出一个内豁外窄的土灶。架上大铁锅,装满水,生火烧水。妈妈则在厨房内做荞饼,她怀中盘着一个圆盆,盆内是素白的荞麦粉,旁边的矮凳上是一瓢温水,她偶尔腾出左手,拿起那一瓢温水,往荞面中倾倒着,同时,右水轻轻地捏着竹筷,手指灵活快速地转动了起来,转瞬间,便把盆里的荞面糊倒入灶上预热着的铁锅内,锅里响起“嗞,嗞”的声音,盖上锅盖,隔一段时间,翻转,不一会儿,荞面就烙成了。整个早晨,妈妈尽是忙碌着烤荞饼了。等到天大亮时,已烙好了一堆如小山一般高的荞饼。今天来的人多,不怕烙饼剩。妈妈烙荞饼,手艺极精,她烙的荞饼,呈淡绿色,有清香,入口时有韧劲。
四叔站在后院那个土坡上,开始呦喝大家杀年猪了。备好麻绳,套住猪脚,将其赶出猪圈,用力一拉,年猪轰然倒地,众人蜂拥而上,将它按住,合力抬至院坝宰杀。有时,遇到不听话的年猪,可就没那么顺利了,倘若年猪逃出院坝,可就更麻烦,大家只好追着年猪满山跑。我们爬上草垛,尖叫着,欢呼着。二叔是捉年猪的高手,他胆大心细,往往第一个冲出去。三叔怕猪,他见年猪被别人完全制服后才装模作样地冲上去,或者干脆咪着他那双小眼睛,站在一旁看热闹。杀好年猪,抬至临时挖好的土灶旁,以沸水浇烫,褪猪毛,洗涮干净后,开膛取内脏,那是第一道祭品,不能马虎。取内脏时,我们都争抢猪尿泡,取下之后,不能立即吹胀,须将其置于一块光滑平整的石块上,用力揉搓,等它变薄软之后,找一根荞梗,从通口插入,猛吹,吹成气球状,再找一根细绳,封口。这个肉球很有弹性且不易被刺破,可以当球踢。不觉间,已过正午。休息,吃过午饭后,爸爸忙于腌腊肉,妈妈灌猪肠。当晚要做冻肉,将猪肉剁成碎末后煮至烂熟再冷却凝结起来即告结束。这一晚,我们将床铺搬到厨房,以防夜猫偷食祭品。
凌晨四点多钟的时候,祭过先祖,撤下牌位上的祭品,爸爸开始在菜板上用力剁猪肺,下锅煮熟,再将我们兄妹仨叫醒,吃一点才让我们继续休息。白天是做腊肠。这一天,我们的脖颈上挂着用细绳串贯的一只煮熟的猪肘子和一块荞饼,正午时分,解下各自的猪肘子与荞饼,盘膝围作一团,一起聚餐。
妈妈要回娘家探亲了,我们哭闹着央求跟着她去外婆家,一来可以得一点压岁钱,二来可以和久别的表兄弟们相聚。从我们家到新营盘搭车需要走很长一段山路。天蒙蒙亮的时候,爸爸妈妈带上小妹开溜了,在村口被我赶上,我攥住妈妈的裙子哭闹着,死活不肯松手。最后妈妈允诺我回来时给我买一双小皮鞋,我才动摇了。
五
老实说,我真不知道学校什么时候开始上课。每天早上,妈妈喂完猪食后,给我绿色的帆布书包里放一块荞饼,叮嘱我路上不要贪玩之类的话,然后我就上路了。我们村没有学校,要去两公里开外的莫忍就西村上学。我们在路边立了一根木杆子,地上画了一条线,只要影子过了线,就离上课时间不远了。只是阴天就不灵了,真闹心。我想我什么时候才能有一块属于自己的手表呢?那样我上学的时候就不会迟到了。
翻过一个小山坡,路边一个醒目的地方,一棵大榕树立在那儿。我远远地看见早晨的阳光投在榕树上,一粒粒水珠从树叶上淌下来。树底下隆起一个圆圆的土坡。这地方我不敢走近,据说榕树底下封了厉鬼。它害死过好些人,后来请来一个大毕摩才降住。它被装进一个瓦罐,埋在榕树底下,上面盖一口铁锅,再用泥封起来。每次上学经过榕树旁的山路,我总是瘆得慌,心里毛毛的。幸亏没走几步路就看见了木栅栏,里面的洋芋花正开得灿烂。这说明我们进入莫忍就西村了。村口有一座荒废的土墙,墙根的小洞中经常有田鼠出没。墙角的荒草丛中零星分布着矢车菊,喇叭花,鬼针草,还有灰灰菜。矢车菊绽开淡蓝的花朵,很漂亮。喇叭花却耷拉着脑袋,附在墙角边,显得很萎靡。我还看到灰灰菜上有一些尘土。一只小蜥蜴迅速从墙根蹿到荒草中去了。
沿着村舍中的小路拐几个弯,就到学校了。大门是木制的,通了好几个洞,白色的围墙年久失修,有好几处已经摇摇欲坠了。刚入校门就传来了上课铃声。老师拿一块石头敲击系在墙上的钢板,铃声就是从钢板上传来的。我们学校有三种铃声,下课铃缓慢,敲一声停一下,上课铃敲三声停一下,集合铃声则叮叮当当,密如雨点。课程有语文和数学。我讨厌上语文课,因为背不出课文,放学后老师要把我们关在教室里。一年级要背生字表:“一三五七九,二四六八十,日月水火,山石田土方,人耳目舌足,上中下大小了 ,刀子尺文生白 ……”接下来要背“下雪了,下雪了,雪地里来了一群小画家,小狗画梅花,小鸭画枫叶,小马画月牙……”有好几回,由于背不出生字表,放学后,我被关在教室里。我们村的小伙伴们都走了,我独个儿回家,经过大榕树旁时,害怕得哭了起来。最后是从林子里绕了过去。
六
一下课,大家都在吃圆根。圆根的皮有的淡红,有的雪白。正中有一条细长的尾巴,要吃以前才能揪下来,照着圆根敲两下,喊一声“香又香,甜又甜”,圆根就好吃了。入冬后,妈妈亲手给我织了一件毛线衣,我觉得暖和了一些。我找了一个小铁碗,装了几块火炭,用细线拴了提着去上学。不能让炭火熄灭,一路上得甩开膀子转圈儿,火炭被风煽得一闪一闪的。教室里,每个人的胯下都摆着一小盆炭火。不过,冒烟子可不成,要被老师骂的。太阳光照到学校后,炭火就不顶事了。收起来,第二天早上又用。午休时间很长,大家就玩啤酒盖儿。啤酒盖儿有好几种玩法,最时兴的玩法是当转轮玩。把盖沿捶平,凿两个孔,穿上线,转起来呼呼响。找一个阴凉的地方,吃完从家里带来的荞粑粑,我们就靠着墙根睡着了。我梦见自己飞了起来,放学回家,我告诉妈妈我梦见自己飞起来了。妈妈说,这是因为长个子的缘故。小孩子一长个子就会梦见自己飞起来的。我想我得多做这样的梦,不然以后就长不高了。
一下雪,就不上课。我们只能呆在家里。有时,雪下得大些,能淹没兔脚时,就可以牵着黄狗去撵野兔了。爷爷背上鸟枪,牵着黄狗走在前头,我们跟在他后面。到了户外,一发现兔子,我们就将兔子围起来,追着满山跑。狗叫声,鸟枪声和我们的叫喊声响彻整个山林。堆雪人,打雪仗也颇有趣,我们的小手和脸蛋被冻得红扑扑的。但我们不怕冷,一边堆雪人,一边往手上呵气。滚完雪球,塑成人形之后,赋予雪人各种表情,有时我们还会给它戴上一顶惹眼的红帽子呢。撵完兔子,回到家里,透过窗户可以看见,空中正飘转着团团飞舞的雪花,飘飘洒洒地不断坠落,宛如亿万只白色的蝴蝶一般,停息在屋瓦上、远山和林木上。朔风呼啸着,屋里却暖暖的。火塘边的茶锅内腾腾地冒着雾气,爸爸觑着眼,正在一片氤氲的热气中忙着给家人煮油茶。
七
爷爷病了,吃不下任何东西。爸爸带他去镇医院住了几天院才回来。一连几天,我家聚集了好多人。三叔在外地上班,那几天也回了家。有一天早晨,爷爷的病比平常好了一些,大家都说他的病要好了。三叔很开心,眼看要过年了,前些日子忙着照顾爷爷,过年用的松明子还没有准备呢。三叔带上我去光加阿别山上砍松明子。天气真好,三叔在林子里扯着嗓门唱歌。他是公鸭嗓,声音真难听。隐约传来了拖着彝腔哭丧的声音,只见我家院落前那个高高的陡坡上,已搭建起灵堂,黑白两色的布料迎风招展。三叔“哇”地哭出声来,撂下背篓往家里跑去。那天放了许多鞭炮,大家哭成了一团。我在屋后拾未燃尽的鞭炮,玩得正欢。大家说爷爷临死前曾回光返照,说想吃一碗面条,没等做出来就咽气了。不久,我就跟着爸爸去乡镇中心上学去了。没过几年,爸爸下岗失业,我家搬到了新营盘。离开空宗伊德村后,我的童年生活基本结束。我不知道自己怎么稀里糊涂就长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