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诺笔下的陕甘苏区
李荣珍
斯诺是中国人民的亲密朋友,他的一生与中国结缘。早在1936年,当世界上大多数人不知道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是否还存在的情况下,斯诺在宋庆龄的安排和帮助下,冲过重重封锁,进入陕甘苏区(当时陕甘苏区刚扩大为陕甘宁苏区),采访了这块土地上的许多人和许多事,用生花之笔,向世界介绍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们和他们率领下的陕甘苏区军民,介绍了举世无双的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他对中国革命作出了超过一个记者职责的杰出贡献,中国人民是不会忘记这位老朋友的。
陕甘苏区是红军长征的落脚点,这块红色区域很长时间不为人知。斯诺是向世界介绍陕甘苏区的第一人,在他的笔下,我们看到了陕甘苏区的成长史,看到了创建这块根据地的英雄刘志丹等人,也看到了党中央落脚后,这块苏区发生的新变化。
斯诺将陕甘苏区的创建人刘志丹比喻为“罗宾汉”
斯诺在他著名的《西行漫记》一书中,有专门的篇章,即第六章名为“红星在西北”,是专门写陕甘苏区的,其中的开篇标题叫“陕西苏区:开创时期”,通篇写了被斯诺称作“现代侠盗罗宾汉”——刘志丹的事迹。

1979年版《西行漫记》
斯诺笔下,说到江西、福建、湖南的共产党人逐步建立反对南京政府的根据地时,中国其他地方到处都出现了红军。而在“西北方向的远远的山区里,另外一个黄埔军校生刘志丹当时正在为目前的陕西、甘肃、宁夏的苏区打基础。刘志丹是个现代侠盗罗宾汉,对有钱人怀有山区人民的一贯仇恨。在穷人中间,他的名字带来了希望,可是在地主和老财中间,他成了惩奸除恶的天鞭”。文章告诉人们,在南方,共产党人在创建根据地,同样在偏远的西北,也有刘志丹这样的共产党人在创建根据地。
在叙述了刘志丹的身世和他领导的起义后,直接进入介绍刘志丹创建陕甘红军和陕甘边根据地的艰难过程:“刘志丹在一九二九年到一九三二年的生涯仿佛一个万花筒,其间历经各种各样的失败、挫折、捣乱、冒险、死里逃生,有时还官复原职,不失体面。他率领下的小支部队几经消灭。”斯诺写了刘志丹的传奇,写了他的出生入死,也写了他为之努力所换来的成功。“到一九三二年刘志丹的徒众在陕北黄土山区占领了十一个县,共产党特地在榆林成立一个政治部来指导刘志丹的军队。一九三三年初成立了陕西的第一个苏维埃,设立了正规的政府,实行了一个与江西类似的纲领。”从这些描述看,斯诺的采访确实非常深入,了解到很多陕甘边根据地初创时期的情况。虽然个别史实略有出入,但轮廓大致是对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确实初创于1932年,3月底至4月初,在甘肃正宁县的寺村塬成立了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这可以视作陕甘边的第一个苏维埃临时政权,而根据地的确立是以政权为标志的。但这个根据地在当年8月就失去了。1933年4月,在陕西铜川的照金再次成立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根据地已发展到方圆400余公里,涉及旬邑、淳化、三原、耀县、宜君、正宁等县域。而这时的根据地正如斯诺所说,是“正规的政府”,实行的是和江西的中央苏区一样的纲领。

周恩来欢迎斯诺到陕甘苏区
斯诺写到了苏区的发展:“到一九三五年中,苏区在陕西和甘肃控制了二十二个县。现在在刘志丹指挥下有二十六、二十七军,总共五千人”。“在南方红军开始撤离赣闽根据地后,陕西这些山区红军却大大加强了自己,后来到一九三五年,蒋介石不得不派他的副总司令张学良少帅率领大军来对付他们。”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大发展是在第三个时期,即1934年,在甘肃华池南梁地区又一次建立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成为这一地区的苏维埃临时革命政权,紧接着在苏区大发展的基础上于11月成立了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这是正式的苏维埃政权形式。政府主席由被称为“娃娃主席”、只有21岁的习仲勋担任,陕甘边区军委主席是刘志丹。到1935年2月,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和1935年1月成立陕北省苏维埃政府的陕北革命根据地的领导人坐在了一起,在周家硷召开联席会议,成立了中共西北工委和西北军委,由刘志丹任军委主席。接着,在刘志丹指挥下,红二十六军和红二十七军并肩作战,连续打下延长、延川、安定、安塞、保安、靖边六座县城,把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和陕北革命根据地连在一起,形成陕甘革命根据地。斯诺笔下虽然没有细写到这种程度,但从他的叙述中已能看到苏区发展的端倪。
虽然后来陕甘苏区发生的错误“肃反”背景有些复杂,但斯诺提到了这件事,并写出了毛泽东带领的党中央到达陕甘苏区后对这次错误的纠正。斯诺写到:“就是在这个奇怪的事情發生的时候,南方的红军先遣部队,即在林彪、周恩来、彭德怀、毛泽东率领下的一军团在一九三五年十月到达。他们对这奇怪的情况感到震惊,下令复查,发现大多数证据都是无中生有的”。“他们立即恢复了刘志丹和他所有部下的原职。”陕甘苏区的“肃反”发生在中央红军到达前一个月,当时新成立的陕甘晋省委下令在苏区进行“肃反”,结果把刘志丹、习仲勋等陕甘苏区的党政军领导人抓捕起来,有些人遭到杀害,错误“肃反”给陕甘苏区带来严重危机,好在党中央率领中央红军及时到达陕甘苏区,毛泽东下令“刀下留人”,并速查真相,解决了错误“肃反”问题,释放了刘志丹、习仲勋等人,解救了苏区危难。

刘志丹
斯诺写到了刘志丹的牺牲:1936年为抗日而进行的东征,刘志丹“在那次战役中表现杰出,红军在两个月内在那个所谓‘模范省攻占了十八个以上的县份。但是他在东征途中牺牲的消息,不像许多其他类似的消息那样不过是国民党报纸的主观幻想。他在一九三六年三月领导游击队袭击敌军工事时受了重伤,但红军能够渡过黄河靠他攻占那个工事。刘志丹被送回陕西,他双目凝视着他幼时漫游的心爱的群山,在他领导下走上他所坚信的革命斗争道路的山区人民中间死去。他葬在瓦窑堡,苏区把红色中国的一个县份改名志丹县来纪念他。”斯诺这段文字充满了感情,赞扬刘志丹在东征中创立的不朽功勋,惋惜他真实的牺牲,并说到他在走上他引导的革命斗争道路的陕甘苏区人民中长眠。这句话正印证了毛泽东为刘志丹的题词“群众领袖民族英雄”。党和人民为了永久纪念刘志丹,将他的出生地保安县改名为志丹县,让他的英名与世长存。

斯诺的坐骑驰骋在陕甘宁边区
陕甘苏区的发展与刘志丹等人的正确领导是分不开的,但斯诺从个体作用看到了更广阔的视角:“虽然西北这些苏区是围绕着刘志丹这个人物发展壮大的,但不是刘志丹,而是生活条件本身产生了他的人民这个震天撼地的运动。要了解他们所取得的任何胜利,不仅必须了解他们所为之奋斗的目标,而且要了解他们所反对的东西。”这一点也恰恰点明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总纲领,就是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社会。由此看,斯诺确实不仅仅是一个新闻记者,而且是有着敏锐眼光的观察家,更是中国共产党人最诚挚可靠的朋友。
斯诺笔下处处可见、生动鲜活的陕甘苏区军民
斯诺在陕甘苏区的采访不受任何限制,在苏区和前线,从领袖、红军将领,到广大干部、群众和士兵,斯诺广泛接触各类人员。他不仅能采访到苏区领导人,也能接触到苏区的普通人士,因此,他笔下的陕甘苏区多姿多彩,人物生动有趣。难能可贵的是,1936年7月底到9月下旬,斯诺和马海德医生还亲自在前线目睹了彭德怀率领红军主力部队浴血奋战的场景。《西行漫记》不仅在当时让人大开眼界,即使让今天的读者看来,依然读趣盎然,引人入胜。
“打倒吃我们肉的地主!”“打倒喝我们血的军阀!”“打倒把中国出卖给日本的汉奸!”爱憎分明的口号,是给斯诺进入红区的第一印象。而这种印象,随着斯诺深入苏区,越来越深刻。
斯诺发现,红军住在村庄,与老百姓和睦相处:“红军能够这样不惹人注目地开进一个地方,是不是红军受到农民欢迎的原因?附近驻扎一些军队似乎一点也没有破坏农村的宁静。”斯诺和一群只有10岁左右的孩子们攀谈,他问孩子们对共产党员的印象,孩子们说:“共产党员是帮助红军打白匪和国民党的人”,“他帮助我们打地主和资本家”。斯诺又问,苏区还有地主和资本家吗?孩子们说跑了。为什么跑,孩子们说,是因为“怕我们的红军”。这让斯诺认识到,共产党员在苏区是多么受欢迎,孩子们引以为自豪的主观世界里,也拥有属于我们自己的红军。

在陕北时期的斯诺
斯诺在《西行漫记》里,以专门的篇幅写了他曾经看到的西北等地受灾后的种种惨景,写了人民深受地主盘剥的悲惨生活,也写到人们想改变旧社会的心愿。他笔下,写出了西北农村特别是陕甘边境地区土地问题的实况:“在陕西,一个农民有地可以多达一百亩,可是仍一贫如洗。”为什么这样说呢?这里人口不密集,人均占有土地多,但因为丘壑纵横,自然条件不好,能用于耕作并能生产出果实的庄稼地并不多。所以,习仲勋主政的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在土地政策的制定上也是符合实际有自身特点的,比如土地政策中的分川地不分山地,青苗与土地一起分等具体规定,这就让农民拥有真正的可耕土地,也能看到收成的前景。这样做的结果必然是赢得民心,广受欢迎。因此,斯诺写道,“我们得悉共产党人在西北特别受人民欢迎,是不应该感到奇怪的,因为那里的情况对于农民群众来说同中国其他地方一样,都没有根本的改善。”这里说没有根本的改善是指国民党统治下地主、富农的盘剥不可能改善的实际状况。而在共产党领导下一切都不同了。
人民把红军看成是自己的队伍,动员自己的子弟参加红军,参军的目的也很明确,大多数人参加红军是“因为红军是革命的军队,打地主和帝国主义。”斯诺采访了许多红军战士,有原红一方面军的,有原红二十五军的,更多的是原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的战士及当地新入伍的战士,这些战士们抢着回答斯诺提出的各类问题,有的回答很精彩。其中一位战士说起人民群众对红军的帮助:“我在刘志丹的二十六军里在定边作战的时候,我们的小分队保卫一個孤立的岗哨,抵抗国民党将领高桂滋的进攻。农民们给我们带来了吃的和喝的。我们不用派人去搞给养,人民会帮助我们。高桂滋的军队打败了。我们俘虏了几个,他们告诉我们,他们有两天没水喝了。农民们在井里放了毒逃走了。”一个甘肃农民出身的战士说:“人民在各方面帮助我们。在作战的时候,他们常常把小股敌军缴了械,切断他们的电话电报线,把白军调动的消息告诉我们。”从这些回答中可以看出,陕甘苏区军民关系多么融洽和谐,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深厚鱼水关系,兵民为胜利之本的道理在这里得到充分证明,陕甘苏区之所以能够得以发展巩固,正得益于有着雄厚的可靠群众基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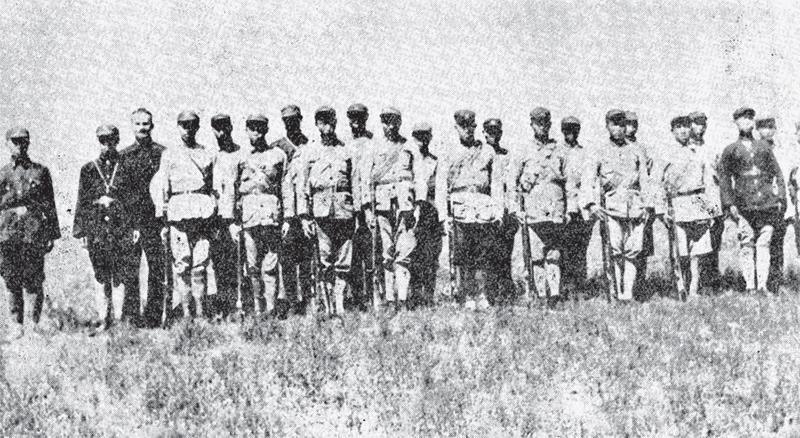
斯诺和红军指战员在一起列队
斯诺了解了陕甘苏区人民反对的是什么,拥护的是什么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这里,肯定地说,存在着早已成熟的实行变革的条件。这里,肯定地说,存在着人们要起来反对的东西,即使他们还没有斗争的目标!因此,当红星在西北出现时,难怪有千千万万的人起来欢迎它,把它当作希望和自由的象征。”
斯诺看红军长征落脚陕甘苏区的意义所在
对于刚刚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来到陕甘苏区的中央红军,斯诺为之震撼,他满怀钦佩之情,对长征这一伟大事件做了激情澎湃的报道。他说:“冒险、探索、发现、勇气和胆怯、胜利和狂喜、艰难困苦、英勇牺牲、忠心耿耿,这些千千万万青年人的经久不衰的热情、始终如一的希望、令人惊诧的革命乐观情绪,像一把烈焰,贯穿着这一切,他们不论在人力面前,或者在大自然面前,上帝面前,死亡面前都绝不承认失败——所有这一切以及还有更多的东西,都体现在现代史上无与伦比的一次远征的历史中了。”斯诺经过采访,认为长征的统计数据是触目惊心的,“红军一共爬过十八条山脉,其中五条是终年盖雪的,渡过二十四条河流,经过十二个省份,占领过六十二座大小城市,突破十个地方军阀军队的包围,此外还打败、躲过或胜过派来追击他们的中央军各部队。他们开进和顺利地穿過六个不同的少数民族地区,有些地方是中国军队几十年所没有去过的地方。”斯诺笔下的长征历程,有详细的叙述,从“举国大迁移”起,长征途中的战斗,经历的苦难,走过的雪山草地,斯诺写来都如同亲身所历,叙述真实感人。斯诺已完全被长征这一壮举所吸引,他告诉每一位读者:“不论你对红军有什么看法,对他们的政治立场有什么看法(在这方面有很多辩论的余地),但是不能不承认他们的长征是军事史上伟大的业绩之一。”在《西行漫记》里的“长征”这一篇中,斯诺是以毛泽东抄写给他的一首诗作为结束语的,这就是毛泽东非常著名的诗篇——《七律·长征》,而这首诗恰恰是毛泽东对伟大长征所作的诗意的总结。

斯诺和红军指战员在一起列队
斯诺在马不停蹄的采访中,既记录下每个时段、每个细节,也时时作出历史的思考,作出一些判断。从他的笔下,可以看到对长征胜利伟大意义的叙述,也可以看到长征落脚陕甘苏区后,中国将发生新的变化。斯诺说:“他们筋疲力尽,体力已达到无法忍受的程度,终于到达了长城下的陕北。一九三五年十月二十日,即他们离开江西一周年的日子,一方面军先锋部队同早在一九三三年就已在陕西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小小根据地的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军会师。”这里,斯诺点明的小小根据地和二十六、二十七军恰恰说的就是陕甘苏区和陕甘红军,再次印证陕甘苏区对红军长征落脚的重要作用。斯诺说:“共产党人认为,而且显然也这么相信,他们是在向抗日前线进军,而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心理因素。这帮助他们把原来可能是军心涣散的溃退变成一场精神抖擞的胜利进军。进军到战略要地西北去,无疑是他们大转移的第二个基本原因,他们正确地预见到这个地区要对中、日、苏的当前命运将起决定性的作用。后来的历史证明,他们强调这个原因是完全对的。这种宣传上的巧妙手法必须看成是杰出的政治战略。在很大程度上,这是造成英勇长征得以胜利结束的原因。”这是斯诺独到的眼光所在,一个是北上抗日的万里长征,另一个是到达能够实现北上抗日的战略区域。这些正是红军长征胜利后,能够尽快投入抗日战争的原因和基础,斯诺用他的笔又一次见证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高度政治预见性。
斯诺笔下也可看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端倪。他说:“但在他们借用的过程中也有不少改动,俄国的思想或制度很少有不经大加改动以适应具体环境而仍存在下来的。十年的实际经验消灭了不分青红皂白一概进口的做法,结果也造成苏维埃制度中带有完全是中国式的特点。”实际上,长征历史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渐进式发展的见证。红军长征中的转折点就是遵义会议,会议确立了毛泽东的正确领导地位,使中国共产党能够摆脱教条主义影响,独立自主地解决自己所面临的问题。

写作《西行漫记》时的斯诺
斯诺在即将离开苏区时,再一次与毛泽东深谈,毛泽东谈话里有着重大的信息,这就是抗日战争即将开始,中国共产党人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后,中国时局将起重大变化。毛泽东对斯诺说:“我们坚持的团结的基本原则是抗日民族解放的原则。为了要实现这一原则,我们认为必须建立一个国防民主政府。这个政府的主要任务必须是抵抗外国侵略者,给予人民群众公民权利,加强国家的经济发展”。斯诺问这样一个政府的法律是否也会在苏区实施?毛泽东的回答是肯定的,他说,这样一个政府应该恢复并再次实现孙逸仙(孙中山)的遗嘱,和孙中山在大革命时期提出的三个“基本原则”,即联合苏联和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联合中国共产党;保护中国工人阶级的基本利益。毛泽东认为,如果国民党里开展了这样一个运动,“我们准备同它合作并且支持它,组成反帝统一战线,像一九二五年到一九二七年那样。我们深信,这是拯救我国的唯一出路。”在对时局变化产生重要影响的西安事变尚没有发生前,中国共产党就提出了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主张,这是伟大的家国情怀,是中华民族的希望所在。因此,斯诺说:“这肯定地必须认为是你们党近十年历史中最重要的决定”。
斯诺为时四个月的采访,改变了他的一生,他在与陕甘苏区军民的密切接触中,终于看到并深刻认识到中国的希望所在是中国共产党。他之所以能成为中国共产党最忠诚的朋友也就是历史的必然。他以自己的生花之笔,宣传史无前例的红军长征,宣传充满希望的红色中国,宣传中国共产党人的所思所想所为。他的报道,贵在真实可信,打破了国民党方面对共产党、对红区的长期的歪曲宣传,西方媒体也出于好奇大量刊发了斯诺的真实报道,使得红军的事迹、中国共产党人的为民主张以及在陕甘苏区的实践能够在国内外广泛传播。(编辑 黄艳)
作者: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