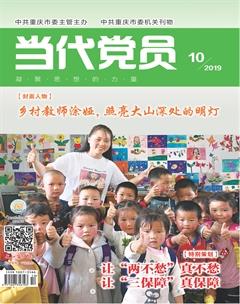以水为伴,一家三代跨越半个多世纪的“接力”
李绿桐 段贵华
1月17日,綦江区石角水文站。
白云山脚下,滚滚蒲河流淌不息,在丛丛芦苇后,隐隐约约能看见一栋标有“重庆水文”的小楼。一踏进这座水文站,便闻到阵阵腊梅冷香。

这个水文站只有一个正式编制。谭波,是这里唯一的职工。
今年,是谭波到石角水文站工作的第16个年头。
很多人并不知道,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谭波的母亲和外祖父也曾在这里工作。
每天早晚8点,谭波都会准时去蒲河边观测水位和降水量。
从站点到蒲河边,这40米长的梯坎路在谭波脚下延伸,让他追随着外祖父和母亲的人生道路,和身旁蜿蜒的蒲河—路平行着延伸向远方……
以水为伴:跨越半个世纪的“接力”
早上7点56分,谭波拿着记录表来到河边,开始做每天例行的第一项工作——观察水尺,掌握水位情况。
“这里有两把水尺,立式水尺是枯水期使用的,这把斜式水尺是丰水期使用的。”谭波说,“小时候,我最喜欢的事就是帮妈妈扶水尺、计算水位了”。
谭波从小在石角水文站长大。而他和水文站的渊源,缘起于外祖父。
从1942年起,谭波的外祖父张源开就在基层测站点从事水文工作。在外祖父从事水文工作的30多个年头里,外祖父带着全家辗转了10多个基层测站点,其中就有石角水文站。
外祖父退休后,母亲张素英接过了父亲的“接力棒”。1984年,张素英正式成为石角水文站的一员。
“当时工作是非常艰苦的,不像现在有一些自动化机器可以操作,那时就只能全靠人工操作。”谭波边说,边用河水清理水尺上的淤泥。
“我母亲常常告诫我,水文工作是人命关天的大事,水文数据直接影响着上级部门对水情的整体分析判断,是一项对时间要求极严、数据精确度要求极高的工作。”
母亲的话一直萦绕在谭波的脑海中。
2000年,谭波又接过母亲的“接力棒”,正式成为一名水文工作者。起初,他在南川区鸣玉水文站工作了3年,后又被调回了从小生活的石角水文站担任站长。这一千便是16年。
算算时间,从外祖父到母亲再到谭波,祖孙三代坚守石角水文站已有半个多世纪,见证了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巨变。
他们早已把水文站当成了家。
以水为家:16年坚守“河岸之家”
上午9点58分,石角水文站操作间。
在这个8平方米的操作间里,只有一个全自动操作台。
“这个操作台就是操作河面上吊着的铅鱼仪器,它是用来固定流速仪的。我每天除了测量水位,还要记录流速、观测降水量。”说着,谭波站起身走向屋外,“以前测速都是用的手动缆车。现在技术越来越发达,我们也用上了自动缆车,测降水量也是用的自动雨量计。”
回到办公室,谭波记录下当天的观测情况。
几百页的记录本,正是谭波从事水文站工作的“缩影”。
“水文工作天天都跟数字打交道,一下雨,就要通过演算得出一系列的数据,预防山洪等各种险情。这些数据是枯燥的,但又影响到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谭波望着记录本上的数字说道。
水文站是江河的“哨兵”——丰水期,要与洪水赛跑,上演“生死时速”;枯水期,更要抓紧时间在站整编资料。
而作为“哨兵”的职责,就必须由一次次不分昼夜的测报来完成。
这座离镇上有5公里距离的水文站,周围鲜少能见到人家。为了这一个个看似简单的数字,谭波必须常年值守在站上,即使是綦江城里的家,谭波也不常回去。
“站就是家,家就是站。选择水文,也就是选择寂寞。从小我就在水文站长大,耳濡目染的是水文测报的方方面面。小时候就看到外祖父和母亲从站点、河边往返忙碌的身影,深知选择以水为伴就是选择了责任和奉献。”谭波坚定地说。
以水为荣:护佑一方平安
上午11点,水文测井工作间。
谭波指着旁边柱子上标着的“2016”印记说:“看,那就是2016年涨到的最高水位。每年丰水期,就是我们一家人上战场的时候。”
看到这个“2016”的标记,谭波的思绪仿佛回到了2016年的6月。
2016年6月,受超强厄尔尼诺现象影响,綦江发生了自1998年以来的最大洪水,作为綦江支流的蒲河,在一个月内出现了两次超保证水位、一次超警戒水位的洪水。在三次洪水测量中,每一次洪水几乎都要持续两天一夜,在这三个两天一夜的时间里,谭波丝毫不敢松懈。
“在那一个月里,流量施测达到了64份,占到全年施测次数的一半。”提及此,谭波颇有感慨。
由于水文站人手不够,洪水来临时,谭波一家三口全部“上阵”。白天,母亲负责发报,父亲负责接听电话、清理河面漂浮物等,晚上谭波就独自应战,顶着大雨、闪电和雷鸣赶往河边观测雨水汛情并发送给上级部门。
“当时降雨量太大,水位、降水量、流速都必须实时观测,这个数据要及时上报给防汛部门,稍有偏差就会给沿岸近万居民造成生命财产威胁。”说到这里,谭波指向了河对岸的山坡。
“由于洪水涨速太快,投放铅鱼可能会造成缆道断裂,我们就利用对面山坡两觇牌间的位置标志,使用了浮标测流。父亲在一头投下浮标,我就负责画辐射线,母亲在另一头传送浮标到达信号并记录浮标流经时长。”
2016年6月28日上午10点,当最后一次洪峰水位出现时,谭波悬了三天的心终于放下了。
洪水慢慢退去,谭波也收到上级消息:由于抢测的流量资料及时,石角水文站下游的石角镇安全转移了4000多人,且无一人伤亡。
那一刻,巨大的成就感驱散了谭波的疲惫。
“作為基层水文工作者,必须发扬‘团结、进取、求实、奉献的水文精神,我的工作能为党委、政府进行防汛抢险决策提供科学依据,能守护一方百姓平安,我为之自豪。”谭波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