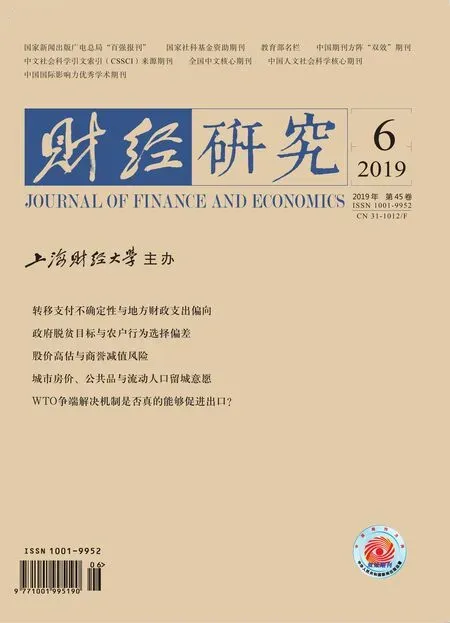居住模式、幼年子女数量与已婚女性的劳动供给—基于儿童看护视角的讨论
孙继圣,周亚虹
(上海财经大学 经济学院,上海 200433)
一、引 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人口红利”(尹银和周俊山,2012)。而“人口红利”终将消失,“人口负债”会随之出现。当前,中国人口的生育意愿大幅降低(侯佳伟等,2014)。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我国15-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已经开始减少,这会给我国经济在未来一段时间造成不小的压力。提高劳动参与率可以在短期内有效缓解我国可能将要面对的“人口负债”。一般来说,男性的劳动参与率比较稳定,几乎所有具有劳动能力的男性都会选择进入劳动力市场。单身女性一般通过工作获得劳动收入,已婚女性则要在家庭与工作之间进行权衡取舍。因此,现有文献在研究劳动参与率问题时,关注的几乎都是已婚女性,本文也是如此。
国内外学者从不同角度研究了已婚女性劳动参与率的各种影响因素,包括丈夫的收入水平、女性的工资潜力、生育率、离婚率、家庭老年照料、幼儿看护等。而关于居住模式(本文探讨是否与家中老人合住)对已婚女性劳动供给影响的研究文献相对较少,因为西方国家的文化比较注重个体的独立性,几乎都是夫妻双方与未成年子女共同居住,“多代合住”现象非常少见(Kolodinsky和Shirey,2000)。受传统文化影响,我国“多代合住”现象较为普遍;同时,由于思想观念的转变,与老人分开居住也较为常见。因此,我国家庭的居住模式比较多样。东亚国家在居住模式的选择上与我国类似,Ogawa 和 Ermisch(1996)、Sasaki(2002)和 Oishi以及 Oshio(2004)研究了对日本的情况,而国内相关讨论(杜凤莲,2008;沈可等,2012)则比较少。
随着国家人口政策的调整,将有更多的家庭生育二胎。幼年子女数量的增多会增加家庭的经济负担,促使母亲外出工作获得收入,但同时也会增加照顾子女的压力,而女性往往承担主要的照顾责任,这又会阻碍其进入劳动力市场。家中老人与子女共同居住时会分担已婚女性照顾幼年子女的压力,使其更有机会进入劳动市场。但共同居住也有可能给双方生活带来不便,因而很多家庭选择与老人分开居住。基于以上分析,居住模式并不是外生的,这是因为:一方面,可能存在一些共同的不可观察因素,如家庭的文化等,影响居住模式的选择和已婚女性的劳动供给;另一方面,已婚女性是否工作也会影响其居住模式的选择,已婚女性选择工作会使其照顾幼年子女的时间减少,从而更有可能与家中老人合住。
由于已婚女性是否参加工作和居住模式(是否与老人合住)都是虚拟变量,传统工具变量Probit回归的方法难以有效解决两者之间的内生性问题。本文使用特殊解释变量回归的方法解决了二值选择模型中内生变量是离散型的问题。本文进一步考察了居住模式对已婚女性劳动供给的影响可能因幼年子女数量不同而具有的异质性,发现与家中老人合住可以显著提升我国已婚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对有且仅有1个幼年子女的已婚女性而言,影响最明显。最后,考虑到是否参加工作是已婚女性自我选择的结果,本文使用Tobit回归的方法,发现与家中老人合住还可以显著提升我国已婚女性的劳动时间。本文从儿童看护的视角出发,丰富了国内关于居住模式对已婚女性劳动供给影响的研究,并针对两者之间的内生性问题,在计量方法上做了改进。本文的研究也为女性生育福利和劳动供给相关政策的制定和优化提供了参考。
二、文献综述
关于已婚女性劳动参与的已有研究关注了家庭外部的社会因素,如丈夫的收入(Mincer,1962;姚先国和谭岚,2005)、女性自身的潜在工资水平(Joshi等,1985;Smith 和 Ward,1985;马双等,2017)和社会的离婚率(Michael,1985;陈钊等,2004)等,以及子女数量(Rosenzweig 和 Wolpin,1980;Angrist和 Evans,1998;Jacobsen 等,1999;张川川,2011)等家庭内部因素。这些研究为我们了解已婚女性的劳动参与决策提供了重要的参考。然而,上述影响因素往往是由社会环境或者家庭(至少短期内)无法改变的因素所决定的。因此,家庭几乎无法通过改变这些影响因素来提升已婚女性的劳动供给。
近些年,有学者开始研究居住模式对已婚女性劳动供给的影响,研究结果对普通家庭有更强的现实指导意义。学者首先关注了已婚女性在家庭劳动和社会工作之间的时间分配问题,其中家庭劳动主要包括照顾家中老人和幼年子女。Ettner(1995,1996)、Pezzin 和 Schone(1999)以及陈璐等(2016)研究了女性照料家中老人对其劳动供给的影响。考虑到照料家中老人特别是无自理能力的老人与女性劳动供给之间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他们使用了工具变量的方法,发现照料家中老人会大幅降低女性的劳动参与率。Ettner(1996)及陈璐等(2016)关注到是否与家中老人合住的因素,但样本主要是无自理能力的高龄老人,因此研究的只是已婚女性照料家中老人这一行为,而没有考虑到我国很多老人可以照顾幼年孙子或孙女以及提供其他家庭劳动的事实。因此,他们的研究结论并不完全适用于我国的实际情况。
国外学者从儿童看护视角研究了居住模式对已婚女性劳动供给的影响。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探讨日本的问题,发现与家中老人合住可以显著提升日本已婚女性的劳动供给(Ogawa和Ermisch,1996;Sasaki,2002;Oishi和 Oshio,2004)。国内相关研究则比较匮乏,而且在计量方法上有需要改进之处。杜凤莲(2008)在研究幼儿看护成本对我国已婚女性劳动供给的影响时,考虑了居住模式的因素,将父母与子女的居住地分为三种情况:同一个社区或更近、同一个县和不同的县。她使用1989-2004年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数据,发现父母与子女居住地越近,已婚女性的劳动参与率越高。但她的研究忽视了居住模式与已婚女性劳动供给之间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将居住模式直接看作外生的,因此研究结果可能存在偏误。沈可等(2012)注意到了这一内生性问题,与Sasaki(2002)以及Oishi和Oshio(2004)类似,以是否有在世的兄弟和子女在家中的排行作为工具变量,使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进行了分析。他们将2002年中国老年人健康长寿影响因素调查(CLHLS)数据与中国家庭动态社会调查(PSFD)数据进行匹配,发现与家中老人合住使我国女性的劳动参与率显著提高了24.3%-40.4%。而考虑到女性是否参加工作这个被解释变量是0-1型的,如果直接使用线性模型来处理这个二值选择问题,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决这一内生性问题,但是在计量方法上仍有很多不妥之处。
三、理论模型
已婚女性在工作、休闲和家庭劳动之间分配时间(Killingsworth,1983),目标是实现整个家庭的总效用最大化(Becker,1990)。父母不仅考虑自己的效用水平,还关心子女的效用水平,并将子女的部分效用计入家庭总效用(Blanchard和Fischer,1993)。与陈璐等(2016)类似,我们建立理论模型来解释已婚女性如何决定其时间的分配,以及居住模式如何影响已婚女性的劳动供给。

其中,C表示夫妇的消费,l表示已婚女性的休闲时间,K表示幼年子女的消费,hk表示幼年子女受到照顾的时间,包括母亲的照顾时间hk1和祖父母或外祖父母的照顾时间hk2。假设已婚女性是否与家中老人合住heju会对老人所能提供的照顾时间hk2产生直接的影响,合住(heju=1)所能提供的照顾时间明显多于不合住(heju=0),即有 hk2(heju=1)>hk2(heju=0)。夫妇选择 C、K、l和 hk1,实现整个家庭的总效用U最大化。家庭的总效用等于夫妇的效用u(C,l)和子女的部分效用δv(K,hk)之和。假设 u(C,l)和 v(K,hk)都是可导的,且一阶导数大于 0,二阶导数小于 0,这一假设的经济学含义与我们的直觉相吻合。
夫妇在做决策时必须满足两个约束条件,一个是货币支出的预算约束,一个是时间的自然约束。Pc和Pk分别表示夫妇消费及其幼年子女消费的价格,则家庭的总支出等于Pc×C+Pk×K。家庭的总收入来自夫妇双方的劳动工资,以及其他的非劳动收入和转移支付。w表示已婚女性的潜在工资水平,H表示已婚女性的全部时间,用于工作、休闲和照顾幼年子女。已婚女性的工作时间为hw=H-l-hk1,工资收入为w×(H-l-hk1)。A表示其丈夫的工资收入及其他所有的非劳动收入和转移支付。家庭的总收入等于w×(H-l-hk1)+A。家庭货币支出的预算约束为总支出不大于总收入。如果hw=0,则说明已婚女性没有进入劳动力市场;如果hw>0,则说明其进入了劳动力市场。
为了求解上述的最优化问题,我们构造了如下的拉格朗日函数:

分别对C、K、l和hk1求一阶导数,我们可以得到如下的Kuhn-Tucker条件:

根据λ2取值情况的不同,我们可分两种情况对上述Kuhn-Tucker条件进行讨论:(1)如果λ2=0,那么hw=H-l-hk1>0,说明已婚女性进入了劳动力市场工作,最优化条件满足。此时,自身消费、幼年子女消费、休闲以及照顾子女给家庭带来的边际效用都相同。(2)如果λ2>0,那么hw=H-l-hk1=0,说明已婚女性没有进入劳动力市场工作,最优化条件满足。此时,自身消费或幼年子女消费的边际效用小于休闲或照顾子女的边际效用。
我们可以通过比较静态分析来探讨是否与家中老人合住对已婚女性劳动供给的影响。对于不与家中老人合住(heju=0),但进入了劳动力市场的已婚女性,最优的消费及时间分配选择为(C0*,K0*,l0*,),满足,其中=+hk2(heju=0)。如果居住模式发生了改变,变为与家中老人合住(heju=1),那么与之前的稳态相比,照顾幼年子女的时间将变多,即=+hk2(heju=1)>=+hk2(heju=0)。由于假设 u(C,l)和 v(K,hk)的一阶导数大于 0、二阶导数小于0,与原稳态相比,此时照顾幼年子女的边际效用将变低。为了达到新的稳态(C1*,K1*,l1*,),使其仍能满足均衡条件,自身消费、幼年子女消费和休闲给家庭带来的边际效用需降低,即与原稳态相比,夫妇及其幼年子女的消费增多,即 C1*>C0*,K1*>K0*,已婚女性的休闲时间增加,即 l1*>l0*;同时,照顾子女给家庭带来的边际效用需提高,已婚女性照顾幼年子女的时间减少,即<。在新的稳态下,各边际效用都有所降低,因此幼年子女受到照顾的总时间将增加,即=+hk2(heju=1)>=+hk2(heju=0)。
根据上述分析,夫妇及其幼年子女的消费都增多,由货币支出的预算约束条件(Pc×C*+Pk×K*-A)可知,已婚女性的工作时间将增加,即h1w*>h0w*。这说明与家中老人合住提高了已婚女性的劳动供给。
四、研究设计
本文的数据来自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的“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ina Household Finance Survey,CHFS)数据库,现已对外公布2011年和2013年的调查结果。由于2013年关于家庭成员基本信息的调查问卷中,没有像2011年那样直接询问“该家庭成员是否与受访人居住在一起”,因此我们无法准确识别“居住模式”这一核心解释变量。本文使用了2011年的CHFS数据,样本分布在全国25个省、直辖市、自治区,80个县,320个村(居)委会,有效样本共8 438户,具有全国代表性。根据研究的需要,本文对原始数据进行了简单处理,并剔除了数据缺失的样本,实际使用的是1 723位20-49岁已婚女性的样本信息。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是已婚女性的劳动供给,主要指是否进入劳动力市场工作,同时也研究了其劳动时间的变化。本文中“是否参加工作”是已婚女性自己做出的选择,已婚女性因身体残疾等的原因而丧失了劳动能力,或者想参加工作却无法找到工作等情况,都不在本文的研究范围内。本文中“不工作”的定义是,主动选择成为家庭主妇或者根本不愿意参加工作。
本文的实证研究对象是我国20-49岁已婚女性,这里对年龄的限制主要基于两个原因:一是根据我国《婚姻法》相关规定,女性的法定结婚年龄是20周岁,因此把年龄下限设定为20岁;二是本文研究幼年子女数量对已婚女性劳动供给的影响,因而只保留育龄女性的样本,而通常对育龄女性的年龄限定是15-49岁,因此把年龄上限设定为49岁。
本文对幼年子女的定义是小学及以下即不满12周岁的子女。本文中超过2个12岁以下子女的样本非常少。考虑到幼年子女数量可能对已婚女性的行为决策产生影响,本文对没有幼年子女、有1个和有2个幼年子女的已婚女性进行了分样本研究。
家中老人的健康状况决定了其提供“隔代照料”,还是需要被其子女照料,从而可能会对本文的研究结果产生很大的影响。遗憾的是,我们并不能很好地观察到家中老人的健康状况这一指标。不过,样本中与子女合住的老人平均年龄约为62.47岁,刚刚步入老年阶段,相对比较年轻。我们有理由相信,与这个年龄段的老人合住,老人更多的是提供“隔代照料”,而非被照料。
表1给出了本文的变量定义及样本描述性统计结果。样本中已婚女性的丈夫大多参加工作并领取工资,但仍有少数没有工作从而没有收入,我们使用丈夫的实际收入加上1元后取自然对数来刻画其收入水平。为了解决居住模式与已婚女性劳动参与之间的内生性问题,本文选取了丈夫的受教育水平和兄弟姐妹数作为工具变量。丈夫的受教育水平可反映思想观念,对居住模式的选择会产生影响,因而是一个可行的工具变量。本文中大多数的合住样本是与男方父母共同居住,因此丈夫的兄弟姐妹数作为一个外生变量会影响居住模式的选择(丈夫的父母选择与哪个子女合住)。Ettner(1996)和Sasaki(2002)也都使用了兄弟姐妹数作为居住模式的工具变量,并被证实是一个比较好的工具变量。

表1 变量定义与样本描述性统计
表2给出了在全样本和不同子样本下,已婚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和合住比率的描述性统计结果。从中可以直观地观察到2个有趣的现象:(1)随着幼年子女数量的增加,已婚女性的劳动参与率降低,有2个幼年子女的已婚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只有47.42%。(2)对没有幼年子女和有2个幼年子女的家庭而言,是否与家中老人合住对已婚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几乎没有影响;而对有1个幼年子女的家庭而言,影响比较明显,已婚女性的劳动参与率从72.68%升至81.07%。这说明居住模式对已婚女性劳动供给的影响可能因幼年子女数量不同而存在异质性。

表2 样本劳动参与率和合住比率的描述性统计
五、经验分析
(一)传统模型
1. 基本模型设定
本文以已婚女性是否进入劳动力市场工作来度量其劳动供给,核心解释变量包括其居住模式和幼年子女数量。我们先从简单的线性模型(记作模型1)入手进行讨论,设定如下:

其中,控制变量Xi主要包括已婚女性的年龄agei、城乡rurali、受教育水平highschooli和collegei以及丈夫的收入水平lnhincomei。
考虑到被解释变量已婚女性是否工作worki是一个虚拟变量,我们构建了如下的Probit回归模型(记作模型2),用非线性回归的方法来更好地刻画我们的问题:

描述性统计分析表明,居住模式对已婚女性劳动供给的影响可能在幼年子女数量上具有异质性。我们进一步在模型2中加入了居住模式和幼年子女数量的交叉项,新模型(记作模型3)设定如下:

其中,onekid表示已婚女性是否只有1个幼年子女,onekid=1表示有且仅有1个幼年子女,否则onekidi=0。类似地,twokids表示已婚女性是否有2个幼年子女。
表3给出了上述3个模型设定下的回归结果。模型1和模型2的回归结果相似,从模型2中各解释变量的边际效应来看,与家中老人合住可以提高我国已婚女性7.5%的劳动参与率。模型3以没有幼年子女的家庭作为对照组,heju以及heju×twokids的系数都不显著。这说明对没有幼年子女和有2个幼年子女的家庭而言,居住模式不会对已婚女性的劳动供给产生显著影响;而对于有且仅有1个幼年子女的已婚女性,与没有幼年子女的情况相比,与家中老人合住可以显著提高8.1%的劳动参与率。这与我们在样本描述性统计时观察到的现象一致。

表3 居住模式对已婚女性劳动参与的影响

续表3 居住模式对已婚女性劳动参与的影响
2. 控制函数的方法
由于居住模式选择与已婚女性劳动参与之间可能存在内生性,模型1-模型3的估计结果都是有偏的,分析结果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居住模式和已婚女性劳动参与之间的因果效应(Causal Effect)。我们将对模型2中的内生性问题进行思考和处理。
对于模型2这种二值选择模型的内生性问题,经常使用控制函数的方法(Control Function Method)进行处理,其中最常见的就是工具变量Probit(IV-Probit)回归。具体来说,假定一个已婚女性是否工作worki这一可观测变量的潜变量(Latent Variable)wor,并构建一个线性模型:

其中,核心解释变量hejui是内生的,显变量worki和潜变量wor之间存在如下的关系:

针对内生变量hejui的决定形式,我们构建如下的线性模型:

其中,工具变量Zi包括式(9)中的所有外生变量以及丈夫的兄弟姐妹数hsibi和受教育水平hcollegei。假设式(9)和式(11)中的扰动项(ui,vi)服从期望为 0 的二维正态分布,刻画影响已婚女性劳动参与的不可观察变量与影响居住模式选择的不可观察变量之间的相关性,由此解决内生性问题。具体来说,我们将ui的标准差单位化为1,σv表示vi的标准差,ρ表示两者之间的相关系数,则有:

在进行上述工具变量Probit回归之前,必须检验工具变量的有效性。我们首先进行过度识别检验,考察所有工具变量是否都外生,即与扰动项不相关。Sargan检验的P值为0.5285,我们可以接受所有工具变量都外生的原假设。我们进一步考察工具变量与内生变量的相关性,检验式(11)中工具变量的系数是否等于0(原假设为工具变量的系数都为0)。F检验的P值为0.0384,我们可以在5%的水平上拒绝原假设,认为工具变量与内生变量是相关的。
表4给出了工具变量Probit回归结果,主要发现与表3中模型2的结果类似,不再赘述。为了使用工具变量Probit回归的方法进一步检验幼年子女数量对已婚女性劳动供给的异质性影响,我们在表4中汇报了幼年子女数量分别为0个、1个和2个时,是否与家中老人合住对已婚女性劳动供给的边际效应。与表3中模型3结果不同的是,在三种情况下,与家中老人合住都会显著提升已婚女性的劳动供给,这一提升效果对有1个或2个幼年子女的家庭而言更大。
式(9)和式(11)中扰动项(ui,vi)相关系数ρ的估计结果是否显著,直接说明了内生性假设是否成立。表4中没有直接给出ρ的估计结果,而是给出了ρ的反双曲正切值,即的估计结果。它的估计结果不显著,说明在工具变量Probit回归模型架构下,我们没有理由认为居住模式这一解释变量是内生的。

表4 居住模式对已婚女性劳动参与的影响:工具变量Probit回归
3. 控制函数方法的不足
控制函数方法的一个基本局限在于,它要求内生解释变量必须是连续的,而不能是离散的、断尾的,或者其他形式的非连续型变量。以上述的工具变量Probit回归模型为例,我们假设式(11)右边的扰动项vi服从正态分布,这一假设只有在hejui也服从正态分布时才是合理的。然而,我们这里的内生变量hejui不是连续型的,而是个0-1型虚拟变量。因此,使用工具变量Probit回归来处理本文的问题显然不合理。
该方法的另一个局限在于,它要求第一阶段模型(即本文的式(11))必须被正确、详细地给出。这就要求我们在第一阶段模型设定中,不能只是给出部分的工具变量,而必须是全部的正确工具变量,否则最终得到的结果就是不一致的。然而,这在我们的实证分析中几乎不可能实现,由此得到的结果往往也不一致。这是因为,假如第一阶段模型的残差项vi满足控制函数方法的假设要求(即式(12)),任何工具变量Zi的缺失都会改变vi,从而违背了控制函数方法结果一致性所需要的条件。
(二)特殊解释变量回归模型
1. 模型设定、识别和估计
Lewbel(2012)、Lewbel等(2012)以及 Dong 和 Lewbel(2015)提出了特殊解释变量回归的方法(Special Regressor Method)。特殊解释变量回归方法可以解决二值选择模型中内生变量是离散型的情况,而且无需像控制函数方法那样构建详细的第一阶段模型并对其残差项做出严格假设,因而可以弥补控制函数方法的上述不足。一般模型设定如下:

其中,被解释变量D是一个0-1型虚拟变量,V和X都是解释变量,为简单起见,将V的系数标准化为1。“特殊解释变量”就是这里的V,它需要满足以下2个特性:(1)V是外生的,与扰动项ε条件独立,即ε⊥V|Z,Z表示除V以外包括式(13)中外生变量在内的所有工具变量;(2)V|Z是连续的,且有一个很大的支撑集(support),其目的是识别和估计不可观察潜变量W*(下文中将定义)的分布函数。X是其他的解释变量,它们可以是外生的,也可以是内生的;可以是连续型变量,也可以是离散型变量。下面我们将简单介绍特殊解释变量回归的识别和估计方法。
我们用潜变量W*表示式(13)中除V以外其他所有可观测与不可观测变量对被解释变量 D的影响,即 W*=X'β+ε,则式(13)可以被改写为 D=1{V+W*≥0}。我们容易得到:E(D|V=w*)=Pr(D=1|V=w*)=Pr(W*≥-w*)=1-FW*(-w*)。潜变量W*的分布函数就可以被识别,FW*
(w*)=1-E(D|V=-w*)。我们也可以看出,之所以必须假设V是连续的,且有一个很大的支撑集,正是因为在识别W*的分布函数时,需要V能取尽W*的所有可能值。利用W*的分布函数,就可以识别W*的无条件期望E(W*)。类似地,我们还可以识别W*的条件分布 FW*|Z(w*|z)和条件期望 E(W*|Z)。
2. 平均指示方程
作为一个非线性模型,这里的系数β并没有实际的经济学含义,我们关心的是其边际效应,Lewbel等(2012)定义了平均指示方程(Average Index Function,AIF)来刻画这里的边际效应。为了书写更方便,我们将式(13)重新写为D=1{X'β+0},这里的解释变量X是包括特殊解释变量V在内的所有解释变量。平均指示方程被定义为AIF=E(D|X'β)。与刻画非线性模型各解释变量的边际效应时常用的倾向得分(Propensity Score,PS)E(D|X)和平均结构方程(Average Structural Function,ASF)F-ε(X'β)相比,平均指示方程AIF的经济学含义可能没有那么明显,它指的是在给定所有解释变量X的线性投影的情况下,个体进入处理组(即D=1)的条件概率。
Lewbel等(2012)之所以选择使用AIF,主要基于以下2个原因:(1)当模型中所有解释变量都外生,即 ε⊥X 时,PS、ASF 和 AIF 三者是相同的,即有 E(D|X)=F-ε(X'β)=E(D|X'β)。此时,AIF 与倾向得分PS有相同的经济学解释:给定解释变量X的情况下,个体进入处理组的条件概率。(2)而当存在内生解释变量时,PS和ASF的估计是非常复杂的,而AIF的估计简单很多。此时,我们只需进行一个D在X'β上的一维而非多维的非参数估计即可,维数的降低大大简化了估计的繁琐程度。
对于解释变量X对样本进入处理组概率的边际效应,我们只需对平均结构方程AIF关于所有解释变量X求一阶偏导数即可,其平均边际效应可以表示为 E (m(X′β))β。采用非参数估计的方法不难得到mi的估计值(详细过程可以参见Lewbel等(2012)),对其估计结果计算样本均值,就得到平均边际效应的估计值。
3. 估计结果
对于式(13)的设定,被解释变量D是已婚女性是否参加工作work,特殊解释变量V选取丈夫的收入水平lnhincome,把它看作外生、连续、拥有大支撑集的,直觉上比较合理。X是包括内生变量heju在内的其他解释变量,工具变量Z包括模型中的外生解释变量以及hsib和hcollege。
表5给出了特殊解释变量回归结果,汇报内容是通过平均结构方程AIF估计出的边际效应。从中可以看到,核心解释变量heju的边际效应与表3中模型2存在很大差异。由表3中模型2的估计结果可知,与家中老人合住平均可以提高我国已婚女性7.5%的劳动参与率;而根据表5的结果,这一提高效果高达48.7%。这一差异的产生原因主要在于,表3中模型2忽视了居住模式与已婚女性劳动参与之间的内生性,可能存在一些不可观测因素,如家庭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程度等,会对是否与家中老人合住和已婚女性是否参加工作产生同向的影响(杨永春等,2012;刘爱玉和佟新,2014),从而居住模式影响我国已婚女性劳动供给的因果效应被低估。
对于其他控制变量,每多一个幼年子女,我国已婚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平均下降4.9%。这符合我们理论分析得到的结论,也与现有文献(张川川,2011)一致。从年龄上看,我国20-49岁的已婚女性每增加1岁,劳动参与率平均下降0.4%。城乡因素并不显著,说明对我国已婚女性而言,无论来自城镇还是农村,在劳动参与方面并没有显著的区别。在受教育方面,已婚女性是否高中教育水平highschool并不显著,说明高中教育水平还不足以提高我国已婚女性的劳动参与率,而高中以上教育水平则能使已婚女性的劳动参与率显著提高3.5%。与一些现有文献(Mincer,1962;姚先国和谭岚,2005)不同,我们发现我国已婚女性的劳动参与和丈夫的收入水平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丈夫的收入每提高1%,我国已婚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平均提高0.03%。这说明在我国,“离婚威胁”理论发挥了主要作用,丈夫收入的增加使已婚女性出于“自我保护”的目的提高了自身的劳动参与率(Michael,1985;陈钊等,2004)。
4. 幼年子女数量的异质性影响
居住模式对我国已婚女性劳动供给的影响可能因幼年子女数量而存在异质性。为此,根据幼年子女数量,我们将样本划分为3个,对每个子样本进行特殊解释变量回归,结果见表6。从中可以看到,对于没有幼年子女和有2个幼年子女的家庭,是否与家中老人合住并不会对已婚女性的劳动供给产生显著影响;只在有1个幼年子女的家庭中,与家中老人合住可以显著提升我国已婚女性37.6%的劳动参与率。对于有且仅有1个幼年子女的家庭,与家中老人合住对我国已婚女性劳动供给的影响最明显。

表5 居住模式对已婚女性劳动参与的影响:特殊解释变量回归

表6 幼年子女数量的异质性影响:特殊解释变量回归
5. 与女方父母、男方父母和双方父母合住的异质性影响
为了进一步探究不同的合住形式对我国已婚女性劳动供给的异质性影响,我们区分了3种合住形式:只与女方父母合住、只与男方父母合住和与双方父母合住,将这3种合住形式的样本分别和不与家中老人合住的样本来构造子样本1-子样本3,对每个子样本进行特殊解释变量回归,结果见表7。从中可以看到,和不与家中老人合住相比,只与女方父母合住可以显著提升我国已婚女性89.5%的劳动参与率,只与男方父母合住可以显著提升53.4%,而与双方父母合住则没有显著影响。这一结果说明,只与女方父母合住可以最大程度地缓解我国已婚女性的“照料压力”,减轻因代际冲突而产生的家庭矛盾(童辉杰和吴甜甜,2017),从而最大程度地提升我国已婚女性的劳动参与率。

表7 不同合住形式的异质性影响:特殊解释变量回归
(三)居住模式对已婚女性工作时间的影响
除了劳动参与率外,我们还可以使用已婚女性的劳动时间来衡量其劳动供给。这里我们将被解释变量替换为已婚女性每周的工作时间hour,探究居住模式对我国已婚女性劳动时间的影响,同时也可作为上文研究结果的稳健性检验。
我们只能观察到参加工作的已婚女性的劳动时间,而是否进入劳动力市场是已婚女性的自我选择(Self Selection)。直接使用参加工作的已婚女性样本进行OLS回归,而忽视不参加工作的已婚女性的信息,将产生选择性偏差(Selection Bias)。为此,我们构建了如下模型:

其中,houri*表示已婚女性潜在的工作时间,可以取负值。但现实中时间是不可能为负的,一个选择负劳动时间的已婚女性,现实中就表现为不进入劳动力市场工作,我们实际观察到其工作时间为0。控制变量Xi与式(6)相同。我们使用Tobit回归方法对上述模型进行估计。
表8给出了上述模型的回归结果,主要结论与上文关于劳动参与率的研究一致。具体来说,与家中老人合住使我国已婚女性每周的劳动时间显著增加4.024个小时,本文样本中参加工作的已婚女性每周平均工作48.69个小时,因此这一提升效果约为8.26%;而每多一个幼年子女,已婚女性每周的劳动时间显著减少6.016个小时,幅度约为12.36%。

表8 居住模式对已婚女性劳动时间的影响
六、结 论
提高我国已婚女性的劳动供给,可以有效缓解“人口红利”消失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负面冲击,也有利于增进自身及家庭的福利,并通过代际转移促进子女的教育和成长。现有文献很少从儿童看护的视角研究居住模式对我国已婚女性劳动供给的影响,而且在计量分析上也没能很好地处理居住模式选择与已婚女性劳动参与之间的内生性问题,因此存在很大的改进空间。在此背景下,本文首先建立理论模型进行了分析,然后使用2011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做了实证检验。
本文使用特殊解释变量回归的计量方法,有效解决了二值选择模型中内生变量是离散型的问题。研究发现,与家中老人合住可以显著提高我国已婚女性48.7%的劳动参与率,这一结果可以被理解为两者之间的因果效应。居住模式对我国已婚女性劳动参与的影响因幼年子女数量而存在异质性:对没有幼年子女和有2个幼年子女的已婚女性而言,影响较微弱;而对于只有1个幼年子女的已婚女性,影响非常大。此外,不同合住形式(与女方父母、男方父母和双方父母合住)的影响也不同,其中只与女方父母合住能最大程度地提升我国已婚女性的劳动参与率。最后,居住模式也会对我国已婚女性的劳动时间产生影响,在考虑了自选择问题后,与家中老人合住可以使我国已婚女性每周的工作时间显著增加4.024个小时,幅度约为8.26%。
基于本文的研究结果,对我国普通家庭,尤其是只有1个幼年子女的家庭而言,应对“多代合住”持更加开放的态度,促使更多的已婚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改善家庭的经济状况,提高家庭的福利水平,同时也不会因此而减少对幼年子女的照顾。对政府而言,应鼓励“多代合住”,一方面,可以加大宣传力度,让人们更加了解“多代合住”对自身福利的改善作用;另一方面,也可以给予“多代合住”家庭适当的经济激励,使更多的家庭有动力选择“多代合住”的居住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