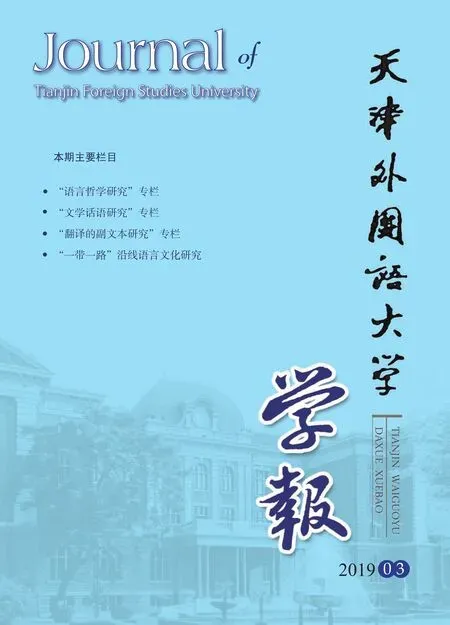普特南论概念相对性
沈学甫
普特南论概念相对性
沈学甫
(天津城建大学 外国语学院)
从阐释普特南早年为探究意义与真理问题而提出的认知对等出发,进而分析了其语言哲学中的概念相对性论题。普特南早年坚持形而上学实在论并承认存在唯一完整的真实理论来描述世界,而在后期他坚持实用主义多元论并认为描述世界的理论与方法显现出多元性。普特南的概念相对性学说承认对于相同的现象存在着不同的既对等又矛盾的描述。然而,我们也不能混淆普特南考察概念相对论所使用的概念图式与戴维森的概念图式。普特南在后期哲学中深受后期维特根斯坦的影响,通过质疑真理一元论而走上了多元主义道路。他在晚年回归到美国的实用主义传统是必然的。
概念;约定;相对性;多元性;实用主义
一、引言
希拉里·普特南(Hilary Putnam,1926-2016)是美国当代著名哲学家。他在许多作品中都探讨了概念相对性(conceptual relativity)学说并多次为其辩护。2001年10月,他在意大利的佩鲁贾大学(University of Perugia)主持赫尔墨斯讲座(Hermes Lectures)①,并发表了《为概念相对性辩护》(A Defense of Conceptual Relativity)一文,那时他的这一主张已完全成熟。概念相对性是普特南后期哲学的核心论题之一,但是该学说与普特南以嬗变著称的性格似乎有些不相符合,因为他在自然实在论时期放弃了许多在内在实在论时期坚持的观点,却依然坚持概念相对性观点。这便使该学说成为普特南一直保留到生命最后的理论之一。普特南刻意使概念相对性与他在自然实在论时期的认识论立场保持一致,以便为他在后期哲学中回归实用主义传统提供足够的辩护。智利学者何塞·托马斯·阿尔瓦拉多(José Tomás Alvarado,2008:164)②博士认为,“概念相对性对于普特南的实用主义来说极为重要。然而,我这并不是坚决认为概念相对性是普特南实用主义的全部内容,但显然这一主张至少是可以使普特南值得享有真正的实用主义者这一称谓的最有特征的观点之一。那么,对于实用主义本身的任何当代可行的提议来说,概念相对性中的任意困难都应该可能看作是严重的困难。”本文从普特南早年考察意义与真理问题而提出的认知对等(cognitive equivalence)出发,进而研究其概念相对性问题,同时考察普特南从内在实在论一直到自然实在论坚持概念相对性的困难及其解决路径。
二、事实与约定的相互渗透——概念相对性的提出
概念相对性学说的雏形出现在论文《对等》(Equivalence,1983)中,普特南那时提出了认知对等(cognitive equivalence)的说法以便考察关于意义与真理的问题。那时他认为,存在着可能在认知上对等却在表面上矛盾(cognitively equivalent but incompatible at face value)的描述。然而,实际上存在的问题是不管我们选择哪一种描述,我们都可以把它看成是一个约定(convention)问题。我们不妨把约定问题视为普特南提出概念相对论学说的一个预先假设。美国卡拉马祖学院(Kalamazoo College)哲学系的珍妮弗·凯斯(Jennifer Case)教授在20世纪与21世纪之交时曾经发表两篇论文:《论概念图式的正确观念》(On the Right Idea of a Conceptual Scheme,1997)和《普特南多元主义实在论的心脏》(The Heart of Putnam’s Pluralistic Realism,2001)。凯斯(2001:429)认为,普特南倡导的概念相对论学说完全可以被“事实与约定的相互渗透学说”来替代,“理解普特南的多元主义实在论需要理解事实与约定的相互渗透学说”。然而,在自然实在论时期,普特南对于凯斯的这种说法进行了进一步更正。尽管普特南(2001:436)同意如下观点,概念相对性意味着事实与约定的相互渗透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们依然可以有许多种约定,这些约定不仅仅包括“认知上对等但看起来似乎矛盾的描述”。普特南在对后一篇论文的回应文章中还承认凯斯的这两篇论文对他后来提出实用主义多元论(pragmatic pluralism)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
普特南(1981:49)在前期哲学中坚持形而上学实在论,他认为:“世界由独立于心灵对象的某种确定的总和构成。关于‘世界的存在方式’,只存在一种真实且全面的描述。真理乃是语词或思想符号与外在事物以及事物集合之间的某种符合关系。”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普特南便开始反对形而上学实在论而转向内在实在论。与形而上学实在论恰好相反的是,内在实在论不主张有固定的对象的总和存在。此时,普特南认为,对象仅仅存在于一种理论或者描述中,这些对象的事态可以在某种明确的概念图式(conceptual scheme)中存在,而这种概念图式则由理论或描述所给予。
1985年,普特南在保罗·卡若斯讲座(Paul Carus Lectures)中正式提出“概念相对性”这一术语,旨在考察“当人们谈到不同种类的实体‘存在’时在做什么”这个问题。他认为,内在实在论只是坚持主张实在论与概念相对性并不矛盾,一个人既可以是实在论者又可以是概念相对论者。他说:“我描述了概念相对性现象——它像我用过的其他现象一样有简单的解释,然而却已普遍深入到当代科学中。存在着对何为(以某种方式)‘对等’而又(以某种方式)‘矛盾’的‘相同事实’的多种描述方式,这是引人注目的非经典现象。”(Putnam,1987:29)在保罗·卡若斯讲座中,普特南已经非常明显地拒斥了形而上学实在论,他开始把概念相对性发展成为一个哲学学说,该学说不承认存在唯一完美的真实理论来描述世界,而描述世界的理论与方法则显现出多元性,所有这些理论和方法既矛盾又对等。换言之,在普特南看来,概念相对性认为对于相同的现象存在着不同的既矛盾又对等的描述。
为了解释概念相对性现象,普特南在《理性、真理与历史》和《实在论的多副面孔》中都曾举了一个关于世界的例子。这个世界由x1,x2,x3等三个个体组成。普特南站在本体论层面提出了一个问题,即世界中有多少对象存在。我们在该世界中可以应用两种完全不同的概念图式,一个是卡尔纳普的图式,另一个是波兰逻辑学家③的图式。

我们可以说在卡尔纳普的概念图式下世界中有三个对象存在,而在波兰逻辑学家的概念图式下世界中有七个对象存在。波兰逻辑学家坚持分体论,按照这种算法,每两个给定的粒子之间就有一个对象存在,即总和,因此,如果我们把空对象(null object)也包括在内的话,则世界中有八个对象存在。也就是说,如何选择概念图式对于弄清世界上有多少对象存在来说非常重要。在普特南看来,对象存在的数目是外在事实,并且我们可以说出这些事实是什么。但他却指出:“我们不能说的——因为这没有意义——是在独立于所有概念选择的情形下什么是事实。”(Putnam,1987:33)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认为,世界中有多少对象存在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我们如何选择概念图式。然而,概念图式是相对的,如何使用对象这一语词在以上两种情况中是有区别的,而这种用法内在于我们所使用的语言。也就是说,世界中有多少对象存在这个问题外在于我们所使用的语言,即独立于我们所想所说的东西。
在上面这个例子中,关于对象的演算方式也就是我们谈论世界及对象的所使用的语言,首先属于卡尔纳普的语言,其次属于波兰逻辑学家的语言,而且演算方式的区别存在于如下四者之间,即我们在语言中言说的东西、我们可以认识的东西、可以为真或为假的东西以及语法。显然,这类似于后期维特根斯坦提到的那种我们在语言中所说所想的东西存在于“语法”当中。需要注意的是,形而上学实在论企图要求语法与实在的一致,并且承认世界本身是唯一确定的存在,但是却不可能意识到存在着概念图式的相对性这一现象。普特南(1987:19)对此评论说:“经典形而上学实在论处理这样问题的方式是非常有名的。也就是说,存在一个单个的世界(把它看作一块面团),我们可以用不同方式把它划分为不同部分。然而,‘甜饼切分’(cookie cutter)隐喻的发明者提出了下面这样一个问题,即‘这个面团的“部分”是什么?’如果答案是O,x1,x2,x3,x1+x2,x1+x3,x2+x3,x1+x2+x3都是不同的‘部分’,那么我们没有一种中性的描述,却有一种倾向性(partisan)的描述——恰恰是华沙逻辑学家的描述!形而上学实在论不能真正认识到概念相对性现象并非偶然——因为该现象依赖于下面这个事实,即逻辑初始自身(the logical primitives themselves),尤其是对象及存在等概念有许多不同用法,而非只有一个绝对‘意义’。”因此,要想回答普特南所问的那个形而上学实在论问题,即世界中有多少对象存在,我们必须首先给定描述概念图式的版本。换言之,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对象的存在依赖于概念图式,这是非常典型的内在实在论观点。普特南通过概念图式相对性论证,恰当地反驳了形而上学相对论(metaphysical relativism)的观点,即认为世界由诸多已经存在的、给定的且可以自我识别的对象所构成的整体组成。
三、概念相对性与概念图式问题
根据概念相对性学说,世界可以不由自我识别的确定对象的总和构成,普特南通过这一论证拒斥了形而上学实在论。但是要想完全理解概念相对性论证光做到以上这些还不够,我们有必要对上面这个例子中的概念图式与普特南所说的概念相对性作进一步区分。概念图式这个观念来自于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提出的纯粹知性概念的图型法。康德(2004:140)曾说:“我们将把知性概念在其运用中限制其上的感性的这种形式的和纯粹的条件称为这个知性概念的图型,而把知性对这些图型的处理方式称之为纯粹知性的图型法。”显然,图型在任何时候都先于我们对世界的描述而存在。20世纪中叶,概念图式的观念从大陆跨过海峡传到英美,在分析哲学家斯特劳森和戴维森那里得到系统的阐释。概念图式对于普特南在内在实在论时期坚决主张概念相对性现象也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普特南上面所指的关于世界的例子中,我们不能简单地把卡尔纳普与波兰逻辑学家的两个概念图式的区别归咎在每个概念图式所使用的自然语言(natural languages)那里。普特南也并没有要求我们必须使用两种不同的自然语言来描述世界。这个例子中的波兰逻辑学家可以是莱茨涅夫斯基,当然也可以是别人。因此,不管是谁,只要他能够清楚部分与整体的演算方式,他就可以使用波兰逻辑学家的概念图式并回答普特南提出的那个本体论问题。但是不同的人使用波兰逻辑学家的概念图式可能会用到不同的自然语言,这样便不能决定我们仅仅使用两种概念图式来描述世界。
戴维森(1973-1974:6)认为:“我们可以接受如下学说,它把具有一种语言与具有一种概念图式联系起来。我们可以对这种关系进行如下假设:概念图式有什么不同,语言就有什么不同。然而,假定在不同语言之间存在一种翻译方式,那么讲不同语言的人就可以分享一种概念图式。因此,研究翻译的标准便成为集中心思研究概念图式的同一性标准的一种方式。”显然,戴维森把概念图式与自然语言联系在一起了。这样的话,我们拥有不同的概念图式就意味着自然语言的多元性。凯斯在论文《论概念图式的正确观念》中驳斥了戴维森的观点并指出,普特南与戴维森对于概念图式理解的不同之处。“戴维森是如下这样解释他自己观点的:把具有一种语言与具有一种概念图式联系起来,同时按照语言的可翻译性来确定概念图式同一性的标准。当戴维森含蓄地把语言与自然语言等同起来的时候,他便把语言的可翻译性与自然语言的可翻译性等同起来,这使他得出如下结论:任意两个概念图式都是不可通约的。然而,语言无须与自然语言等同起来。普特南讨论概念相对论的例子就可以表达出这种观点的重要性。讲波兰逻辑学家的语言乃是运用分体论总和的概念图式,而不是讲波兰语。讲波兰语的人在一个场合可以用波兰逻辑学家的概念图式,在另一场合也可以用卡尔纳普的概念图式,而他却始终在讲波兰语。”(Case,1997:10-11)所以,概念相对性问题从根本上说是分体论(mereology)与存在的约定问题。
为了与戴维森的自然语言进行区分,凯斯把普特南的例子中卡尔纳普和波兰逻辑学家使用的语言称作选择性语言(optional languages)。凯斯认为,如果具有一种语言与具有一种概念图式相联系,它应该与具有一种选择性语言相联系。我们可以把戴维森的说法修改为概念图式有什么不同,选择性语言就有什么不同。凯斯在这里抓住了问题的关键,她用选择性语言清晰地区分了戴维森所理解的概念图式与普特南所理解的概念图式。也就是说,事实未必如戴维森所说的那样,即概念图式有什么不同,语言就有什么不同。因此,如果某人只掌握一种自然语言,那么它可能会具有许多选择性语言,也就会具有许多不同的概念图式。在这个意义下,有些语词会有许多种可能的用法,而没有哪一个语词具有形而上学实在论中的那种绝对用法,我们对语词含义的理解也不是固定的。把这种对含义的理解扩大到语词所在的句子也同样如此,句子的真假依赖于概念图式。
四、两难困境与矛盾的解决
如果我们考察普特南用概念图式的例子来阐述其概念相对性观点时,我们便可以说那两个(或所有)概念图式都可以生成一种形式化语言。由此可见,如果我们在两个认知上对等的描述中使用具有不同含义的同一个语词,按照这两个描述,语词所在的句子就既可能为真又可能为假。如果我们进一步把这两个句子放在一个概念图式中就会产生矛盾,这时我们就必须要面对概念相对性了。实际上,普特南的概念相对性学说就是承认存在着多种描述实在的方法,而这些描述彼此之间既相互对等又相互矛盾。尽管如此,普特南还是听到了一些不同的声音。2001年,他在赫尔墨斯讲座中说道,他提出概念相对性学说之后,有人批评说这一现象实际上是一种两难困境。这种批评观点是要么普特南在谈论含义的纯粹改变,要么他说的就是不可理解的。如果莱茨涅夫斯基说:“存在一个对象是x1,x2,x3的分体论总和”,而卡尔纳普说:“不存在作为x1,x2,x3的分体论的和”,并且在这两句话中“存在”一词的含义相同,这两个陈述则相互反驳。如果不相互反驳的话,他们两个人的谈论就互相越过对方,也就是说“存在”一词在两句话中的含义不同。普特南认为这种批评其概念相对性学说为两难困境的情况是不存在的,尽管这种批评从表面上假设了分体论总和的存在。很明显这一说法中关于存在的含义是针对普特南的,这是自然语言中的正常现象。
普特南在形而上学实在论时期坚持语义外在论。他认为,语词的意义不在人的大脑之中,在自然语言中一个语词如果有多个含义,不同的含义应该对应不同的语词。为了回应这种批评,普特南对“意义”(meaning)一词进行了澄清。首先,他认为语词的意义是词典上的或符合语言学的定义;其次,语词的意义还有一个更为松散的观念,这个观念则出自后期维特根斯坦(2005:25-26)在《哲学研究》中的那段著名讨论:“在使用‘含义’一词的一大类情况下——尽管不是在所有情况下——可以这样解释‘含义’:一个词的含义是它在语言中的用法。而一个名称的含义有时是由指向它的承担者来解释的。”④这时询问语词的意义就不是询问其词典上的定义,而是了解其用法。因此,在那个关于世界的例子里,不管是在卡尔纳普的概念图式中还是在波兰逻辑学家的概念图式中,从语言学角度上来看,“存在”一词意义相同,而在维特根斯坦的那里的意义则不同。在我们每天都说的语言(即自然语言)中,语词的意义是开放的,呈现出多元性特征。
值得一提的是,普特南对意义的澄清也极大程度地呼应了上文中凯斯用选择性语言来区分戴维森所理解的概念图式与普特南所理解的概念图式的做法。这样一来,在戴维森的意义中,波兰逻辑学家使用的“存在”一词与卡尔纳普使用的同一个词的含义则相同,区别只在于他们二人是如何使用“存在”一词的。因此,如果我们粗暴地将两个表面上似乎矛盾的陈述结合起来而不考虑它们在各自所属的选择性语言中的真实用法,那么,我们肯定会人为地制造矛盾。但是,如果我们经过理性思考并把看起来相互反驳的陈述中的每一个都归属到不同的选择性语言,同时承认约定因素存在的话,那么这样的陈述之间实际上并不矛盾,因为不矛盾的东西乃是约定而不是陈述本身。我们不能像康德那样把这个矛盾的问题当作一个“二律背反”(antinomy)从而束之高阁,我们应当把在选择性语言中作出的选择视作约定,这样,一切便顺理成章而且豁然开朗了。因为不同的描述会有不同的目的,所以我们对于世界可以有虽不相同却都同样正确的描述,这是美国实用主义的一个深刻洞见。普特南在后期哲学中完全接受了这一点。
五、从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说”到实用主义多元论
普特南在前期哲学中坚持科学实在论,崇拜从科学视角描述不同的世界版本。自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他又极力提倡概念相对性学说以及更加宽泛的概念多元论(conceptual pluralism)学说。概念相对性学说贯穿普特南的整个后期哲学。自然语言的多元性特征与概念相对性的例子引出的问题之间是有深层联系的。我们从普特南的概念相对性学说可以看出,他在后期哲学中非常关注后期维特根斯坦并深受其影响,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说给普特南带来了极大的启发。但是,我们不能简单地把概念相对性误认为概念多元论。概念多元论认为实在可以用多种不同的方式描述,而所有的描述方法都是正确的。但根据上文可知,概念相对性学说却不是全部如此认为。也就是说,尽管概念相对性可以意味着概念多元论,但反之却不亦然。因此,概念相对性是一个比概念多元论更加宽泛的概念,普特南(2004:48)对此进行了如下的解释:“在刚刚解释过的意义上,下面这个事实不能算作概念相对性的例子,即一个房间容纳的东西能以两种完全不同的词汇来部分描述,因为概念相对性总是包含认知上对等(在下面的意义上,即任何能够在一种选择性语言中可以得到解释的现象在另一种选择性语言中有相应的解释)但表面上矛盾的描述(这些描述不能简单地结合起来)。然而,下面这两个事实在任何方式上都不‘矛盾’,甚至在表面上也没有,即一个房间容纳的东西能够以场和粒子的术语来部分描述这个事实,以及这个房间可以通过说桌子前面有一把椅子来部分描述这个事实。下面两个陈述甚至听起来也不‘矛盾’,即‘这个房间可以通过说桌子前面有一把椅子来部分描述’和‘这个房间能被部分描述为由场和粒子组成’。它们在认知上并不对等。”
不仅如此,从概念相对性与实在的关系来看,我们也没有必要评判普特南所举的那个例子中关于两个世界的版本哪个正确、哪个不正确,因为我们无法提出一个合理的评判标准。二者实际上都正确,或至少看起来正确。进一步来讲,我们可以从实用性角度出发来考虑这个世界版本,例如,我们在哪种语境下可以描述世界,这些描述所处的环境和进行描述的人们以及他们的信念或兴趣各是什么。不言而喻,我们进行这种描述的环境即实用主义语境。“实用主义以其拥有巨大的包容性而闻名,因为根据实用主义准则,凡是经过检验确能带来积极效果的观念、思想、信念、理论、学说等都可以为我所用。”(李国山,2016:121)所以,由于我们的信念或兴趣的差异,我们对世界作出的描述也会是多种多样、五花八门的,我们通过这种描述而收获的就是以实际行动参与了活生生的现实世界中的实践活动。而事实上,普特南所说的概念肯定来源于生活实践,人们在学会用语言描述世界之前就已经在实际生活中掌握这种概念了。
正如普特南所认为的那样,如果对象的存在依赖于概念图式,而概念图式又依赖于其所在的实用主义语境,对象在一定程度上就依赖于这种实用主义语境而得以存在。因此,从某种程度上来讲,世界具有一个不可还原的部分,这个哲学史上一直争论不休的观点来自于人们的心灵活动,而概念相对性似乎也属于这一问题的某个分支。用普特南(1981:xi)自己的话说也就是“心灵并不简单地‘摹写’(copy)一个可由唯一真理论(one true theory)所描述的世界。当然我的观点也不是说心灵构造了世界(或使世界构造屈从于‘方法论原则’和独立于心灵的‘感觉材料’所强加的制约)。如果非得使用隐喻来表达不可,那么这个隐喻可以这样说:心灵与世界一起构成心灵与世界(或者,使这个隐喻更加黑格尔化一些,宇宙——与在构造中发挥特殊作用的心灵一道——集体地——构造宇宙)”。如此一来,我们可以说,心灵活动与实在相互依赖、相互交融,二者离开对方之后都是不可理解的,也就是说概念相对性是依赖于概念图式的。我们使用不同的概念做出不同的陈述,从而从不同的视角和水平上描述世界。这样,概念相对性便经由所进行描述的语境而与实用主义关联起来。
普特南(2004:49)所指的选择性语言涉及到关于世界的多种科学映像,诸如上文提到的分体论和粒子物理学的语言。我们可以使用普通语言和这种科学的描述“而不需要把其中一个或两者都还原为某种基本的和普遍的本体论”。这就是普特南在后期哲学中开始提倡的实用主义多元论(pragmatic pluralism)原则。他在赫尔墨斯讲座中说道:“与实用主义者和维特根斯坦一样,实用主义多元论不需要我们去寻找语言游戏背后的那个神秘且超感觉(supersensible)的客体;当我们在运用语言时,真理能够在我们实际参与的语言游戏中被讲出来,而哲学家给那些语言游戏添加的膨胀则是如维特根斯坦所说的——使用一种相当实用主义的措辞——‘引擎空转’的例子。”(Putnam,2004:22)普特南主张我们可以在日常语言中使用不同种类的话语,这些话语有着不同的逻辑及语法特征,它们既服从不同的标准又有不同的应用。我们把这些不同种类的话语视作维特根斯坦所说的不同的语言游戏,不同的话语有不同的用法。这种多样性类似于语言游戏的多样性,它不是一成不变的。如果有新的话语产生,也就会有新的语言游戏产生,因此,不可能仅存在一种语言游戏能够满足对所有实在的描述。普特南在后期哲学中反复求助于后期维特根斯坦的思想,尤其是关于“语言游戏”的学说,从而为自己的实用主义实在论增加筹码。
普特南受到詹姆斯、杜威以及维特根斯坦等人的影响,在后期哲学中对真理一元论表示不满,他更多地关注语言和文化的多元现象,同时倡导概念相对性的存在。陈亚军认为,“由科学实在论到内在实在论再到自然实在论,普特南思想演变的轨迹正好构成了一个正反合。自然实在论纠正了内在实在论的反实在论色彩,重新恢复早先形而上学实在论的追求,重提真理符合论;然而它又继承了内在实在论对于形而上学实在论的批判,祛除了形而上学实在论的超验前提,在常识而非形而上学的基础上重新确立了实在论的信念”(陈亚军,2001:58)。普特南的后期哲学已经非常明显地摆脱了前期的科学主义并走向人文主义,他企图通过超越主观与客观的界限来寻求一条中间道路,从而避免像罗蒂那样陷入相对主义的困境,最终摆脱了二元论的思维方式,回归到了美国实用主义传统。
注释:
① 该讲座一共四讲,全部收录在《无本体论的伦理学》(,2004)一书中。《为概念相对性辩护》()为该系列讲座的第二讲。
② 何塞·托马斯·阿尔瓦拉多(José Tomás Alvarado)博士是智利瓦尔帕莱索的庞蒂菲卡尔天主教大学(Pontificia Universidad Católica de Valparaíso de Chile)的助理教授,是拉丁美洲从事分析哲学研究的著名学者,主要擅长分析的形而上学、语言哲学以及认识论等领域,著有《希拉里·普特南:实在论模型理论论证》(,2002)一书。
③ 这里的波兰逻辑学家是指莱茨涅夫斯基(Lezniewski),他创立了分体论(mereology),即探讨部分与整体的演算方式的理论。
④ 在2009年出版的德英对照版《哲学研究》中,编译者哈克(P. M. S. Hacker)和舒尔特(Joachim Schulte)把德文Bedeutung一词译成英文的meaning。陈嘉映先生是根据美国麦克米伦出版社1953年德英对照版《哲学研究》翻译的,他把该词译作“含义”。考虑到维特根斯坦前后期哲学术语的一致,并参考了该书的其它中译本和《逻辑哲学论》的几个中译本,笔者认为,这里把该词译作“意谓”较为合适,以便与德文Sinn(英文译作sense,中文通常译作“意义”或“含义”)一词加以区别。因此,我们在这里的引文中保留陈先生的译文不变,在正文中也不采用“意谓”这一说法,而是按照学界约定俗成的说法把该词称作“意义”。这样做也与普特南在《“意义”的意义》(“”)一文中的说法保持一致。
[1] Alvarado, J. 2008. Conceptual Relativity and Structures of Explanation[A]. In M. Monroy, C. Silva & C. Vidal (eds.)’[C].Amsterdam: Rodopi.
[2] Case, J. 1997. On the Right Idea of a Conceptual Scheme[J]., (1): 1-15.
[3] Case, J. 2001. The Heart of Putnam’s Pluralistic Realism[J].,(4): 417-430.
[4] Putnam, H. 1981.[M].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5] Putnam, H. 1987.[M]. Illinois: Open Court.
[6] Putnam, H. 2001. Reply to Jennifer Case[J].,(4): 431-438.
[7] Putnam, H. 2004.[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8] Davidson, D. 1973-1974.[J]., (47): 5-20.
[9] 陈亚军. 2001. 论普特南后期由内在实在论向自然实在论的转变[J]. 哲学研究, (2): 52-58.
[10] 李国山. 2016. 维特根斯坦与实用主义[J]. 社会科学, (4): 116-123.
[11] 伊曼努尔·康德. 2004. 纯粹理性批判[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2] 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 2005. 哲学研究[M]. 陈嘉映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Hilary Putnam on Conceptual Relativity
SHEN Xue-fu
Starting from Hilary Putnam’s cognitive equivalence, which he put forward in order to elucidate meaning and truth in the early years, this paper analyses the doctrine of conceptual relativity in his philosophy of language. He starts his philosophical career on a scientific realist position which sticks to metaphysical realism and acknowledges that there is a complete and real description of the world. In his late philosophy, Putnam advocates pragmatic pluralism and regards that the theories and ways of describing the world demonstrate a kind of plurality. Conceptual relativity acknowledges that there are different equivalent and contradicted descriptions of the same phenomenon. However, the conceptual schemes of Putnam and Davidson cannot be confused, since the former is used to investigate conceptual relativity. Deeply influenced by late Wittgenstein, Putnam advocates pragmatic pluralism in his later philosophy through questioning truth monism. It is necessary for him to go back to the philosophical tradition of American pragmatism.
concept; convention; relativity; plurality; pragmatism
B712.6
A
1008-665X(2019)3-0048-09
2019-03-03;
2019-05-03
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当代西方哲学思想中翻译理论在中国的接受性研究(1976-2016)”(TJZX16-003)
沈学甫,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现代英美语言哲学、文献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