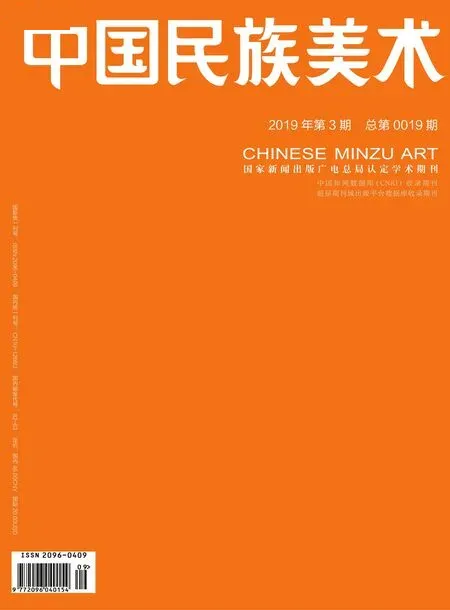从故乡到家乡—锡伯族西迁人的日常生活
文/图:关锁芹 锡伯族 山东理工大学教师

帮雇主装苜蓿的人们 新疆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2018.6)
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为加强边疆驻防力量,清廷从盛京(今沈阳)等地征调锡伯族官兵1000多人,连同他们的亲属3000多人到新疆伊犁屯垦戍边。这支队伍的西迁之路漫长而艰苦,他们经过15个月的长途跋涉,最终抵达伊犁河谷的官兵和亲属有5000余人。这条西迁线路大部分横穿现在的蒙古国,途经乌兰巴托、乌里雅苏台,翻越阿尔泰山脉进入新疆。这是中国历史上一次悲壮的亲人告别,一个民族迁徙的传奇经历,一部民族文化传承与融合的经典史诗。他们从东北到西北,不仅带去了帐篷、粮食、马匹、狗,还有粮种、菜种、族谱。
清代皇帝并没能信守“锡伯营六十年一换防”的口头承诺,这支西迁的队伍再也没有回到他们的故乡。历史走过了256个春秋,而中国西北边陲的伊犁地区便成了他们赖以生存的家乡。
作为一个普通的锡伯族儿女,西迁到西北的那些族人,在我心里一直都朦胧模糊,但却难以割舍。我想,如今的他们是不是仍然穿着长袍马褂?是不是还在骑射狩猎?而那里的族人每每见到我们东北的锡伯族人,开口就问:你们还会说锡伯族话吗?
退休后时间宽裕了,我便怀着对母族的深深敬畏,启动了思考多年的锡伯族摄影项目,分别到西北和东北的锡伯族聚居区静静地去凝视体悟,想借此机会走进母体语境里,深入了解并重新认知自己的母族。
一

在图公祠祭祀的锡伯族祖孙 新疆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2018.6)
长期以来,由于远离锡伯族集聚区,我对自己民族的历史文化一直都是非常欠缺的。我从大学毕业工作后,记得有一次单位搞活动,去的地方是沈阳锡伯族家庙,在那里我才了解到许多阅历之外的东西。1999年,我调到山东理工大学工作,结识了一些锡伯族同胞,他们有从东北来的,也有从新疆来的,每年到“西迁节”我们都聚会聊天,我感受到从未有过的母族同胞间的那种亲情与友谊。随着对族内许多事情的了解,我也开始想:我能为母族做些什么呢?
我想:我喜欢摄影,也有一些实践经验,就从摄影入手吧。自从有了拍摄锡伯族的念头后,我还真踏踏实实地做了一些准备工作,把它当作一个课题来看待,只不过没有和任何人说起过。我当时就想,若按照学术研究的方法去实施,首先得确定一个大概的研究方向,然后根据研究方向查阅文献,在一定的文献储备基础上制定研究方向,设计实验步骤,最后是付诸实践。在实践过程中有可能会遇到各种问题,甚至与当初拟定的方向有所背离,但课题本身就是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
因在学校工作之故,借阅图书比较方便,前几年我几乎翻遍了学校图书馆里关于锡伯族、民族学、社会学、摄影艺术、当代艺术等方面的书籍。有时候,看到社会上有与之有关的图书也会买来翻阅。就这样,我不仅对锡伯族的历史文化和现状有了初步了解,还对摄影艺术和当代艺术有了新的认识。而每每看到书中描述锡伯族西迁的艰辛,以及锡伯族人的各种遭遇后,我曾无数次以泪洗面、感慨万分。当时我就发愿,一定要克服一切困难,排除一切障碍,运用当代艺术手法,站在面向未来的立场上进行视觉体验和内心观看,以人类性、通融性为表达的主诉求,最终呈现出一个崭新的锡伯族视觉文化艺术文本。
关于摄影,我一直认为它是真实的再现,但有时候也会看到一些非真实的照片。我为此疑惑,就去请教书本。后来《摄影小史》给出了我想要的答案——因为在摄影中,“精神战胜了机械,将机械获得的精确结果诠释为生命的隐喻”。在好的照片中,被拍的人在生活中苦心经营的面具遭到了摘除,透过这张照片,我们看到了“活生生的人”。
哦,原来摄影的所谓真实是这样的,那个活生生的人是加引号的啊!还有,“真实”是不能复制的,摄影只是凝固了时间,撷取了现实表象中的残影及痕迹,它不能取代真实。于是,我恍然大悟:那些以写实或新闻为主要表达向度的图像,比如宣传图像、新闻图像、纪实图像等,理论上都应该是不干涉拍摄对象或改变环境原貌的视觉框取;那些以写意或观念为主要表达向度的图像,比如视觉图像、观念图像、广告图像等,则可以应用各种媒介和手法进行添加取舍和加工改变。这就是纪实影像和艺术影像本质上的区别。以前总把两者混为一谈,用此门类的原则和方法去限制要求彼门类,从而制约了摄影艺术的发展,扼杀了艺术家的才性流露与本心本性。
弄明白这些以后,我的内心轻松了许多,锡伯族项目似乎就有了点眉目。
二
摄影艺术原本应该与人的内心有关,作品也应该与作者的生命体验有关,没走心的拍摄是浅薄虚伪的,是留不下来的,也注定走不进历史。在实施锡伯族项目之前,我通过读书和走访族人,对锡伯族的历史文化有了许多感性认识,加之自己有锡伯族血缘,面对族人的时候,仿佛就是和家人在一起,自然而然就有亲和力了。所以,我不仅期望能够在作品里体现出这种人与人的关系,还希望表达出我与他们的亲情关系。于是,在《西迁人》第一部分“锡伯族西迁人的日常生活”里,就有多幅作品直接表达出这种族人之间相互依存、携手而行的场景。在第三部分里,我运用艺术植入与行为相结合的方法,希望能将我深切的怀念和时光的穿越有机地结合起来,以情感为线将怀古、回忆与现实、展望连接起来,表达出我的认知和思考。
有人说,摄影走向独立探索才是正途,当摄影师独立后,世界就完全不一样了。在今天的摄影实践中,聪明的摄影师是用怀疑的眼光观察世界的,他们反思曾经的历史与已有的经验,但那是少数人,他们独立且不依附于圈子,与社会中的各类人进行深度交流。他们对社会进行独立思考探索,其过程既枯燥单调,又充满惊奇,结果更是出乎意料。如果我们还没有出发就已经知道结果了,那说明你的探索还没有真正地独立,只是用一种老套路来应对多变复杂的世界。而独立探索并不是孤立探索,需要在探索过程中保持人格独立、思想独立,还要不断地与各类人进行交流。内心贴近大地与人群了,就会听到更多的声音,见到更多从未见过的新奇视角,会发现更多的线索,独立探索的乐趣自然就魅力无穷了。在世界多元化的数字时代,中国的摄影已不再是传统固化的某一类艺术形式,它是一个充满包容性、开放性、系统性的媒介和学科,在当代科技发展和艺术文化背景下发展迅速。我们稍有疑惑,就会落在别人后面无所适从。
当我站在锡伯人赖以生存的土地上,深切感受到,那是一个有历史、有故事、有温度的地方。特别是晚上,当我站在那片土地上仰首眺望,便看到了最广阔无垠的苍穹和最明亮的星辰。我镜头所框取的每一个瞬间、每一张笑脸,都是有故事的,有感情的,有温度的,若把这一切都编织到我现在的视觉基因密码里,无疑显现的是一个现实的当下而非艺术的当下,但那一定与我进行这个锡伯族项目的初衷是相悖的。其实,我的这个项目只是一个个体,对母族的深情怀念与美好祝愿,影像是其最终呈现的主要载体,而对项目完成度的理性推进是核心问题。
面对题材的限制和空间的局限,为避免作品平庸无趣,体现当代性和艺术的前瞻性,并兼顾现实性,我在项目推进过程中选择了避重就轻的原则,既采用了传统的写实拍摄方法,更多的则运用当代介入、借用或抽离的手法,力图使作品体系形成一个线索性的发展趋向,从传统性朝当代性过渡,最终扎扎实实地落在当代性的范畴里。所以,这才有了这么一个朝向当代艺术方向发展的整体呈现。
三
摄影出现之前,人们的观看以文字、绘画、语言、表演等进行留存和展示。摄影出现之后,人们的观看多了一种以影像的方式留存和展示——无论是动态的视频还是静态的图片。我的《西迁人》系列作品共分五部分,其中一部分是纪实性非常强的,三部分的作品属于当代艺术理念下的作品,还有一部分干脆抽象了。记得前些年有个法国著名艺术家曾断言,今后摄影将朝抽象发展,就像当年摄影将绘画逼向抽象一样,将来的抽象摄影又会将抽象绘画逼到墙角另谋出路。
《西迁人》的第一部分作品,全部采用直接摄影的方法,拍摄于新疆锡伯族人生活的地方,未对拍摄对象进行任何的干预;第二部分作品,是在现场采集素材后,根据需要将两幅画面并置在一起,形成互动关系,缩短距离感;第三部分作品,采用的是介入、置入或借用手法,加上自己直接参与其中构成一种行为艺术,进而组成一个递进的、复杂的表达链,人为地将时间、事件和空间揉捏在一起,再加上相关文字的配合,试图营造一个多维度、多视觉、多空间并存且不确定而又游离其间的视觉表达;第四部分作品,是将拍摄于西北和东北的相似场景并置在一起,希望找到锡伯族人之所以能在两地生存延续的地理支撑和文化背景,是为表达需要所做的“视觉去异求同”;第五部分作品,则以视觉的抽象化模拟出梦境般的情绪,希望能表达出锡伯人对西迁亲人的思念和远方族人生活的朦胧感受与想象。
我是一个摄影新手,许多问题是在项目的推进过程中逐渐清晰明了的,很多作品还很幼稚浮浅,表达也不够准确到位,技术支撑上还有待进一步提高,特别是在当代摄影和艺术观念上还要下功夫学习。总的来说,我的这个项目不以旅游宣传为诉求,它的初衷只是一个普通人希望为自己的母族奉献一点什么。所以,大家不要对我的呈现期望值过高,也别让我肩负这责任、那理想了。
从作品的呈现方式上来说,也许我无意中应用了一些新客观主义或后现代主义的手法,至于它究竟是什么路数,那就要看理论家们怎么说了。大家都明白,摄影在提供一种观看的同时,必然会屏蔽另一种观看,在这里也不例外。我以为,艺术介入某个领域后人们应该宽容一些,其携带的任何事物和信息,我们没有必要说它是无中生有,也不要说它是无病呻吟,那是进入表达体系后的必然流露。从作品体系的建立过程来看,每一个风格或流派的产生,都是在吸纳、借用、批判乃至完全推翻已有经验后建立起来的。也就是说,一个人的思想、观念和作品的生成,就是在这样的吸纳、借用、发展、批判,乃至推翻中生成的。所以,简单地谈理论或作品,就像鸡和蛋哪个在先无解一样毫无意义。但我清楚地记得,中国著名的艺术批评家鲍昆对当代摄影有一个自己的看法:“1.摄影师必须‘发明’新的主题,仅仅是‘发现’已经不够了;2.可以自己选择以什么样的方式来表现,甚至可以利用别人的经典作品作为出发点;3.基于摄影师的意图,一切技巧都可以被接受;4.对于照片的后期加工是被允许和鼓励的;5.不强求技术上的完美;6.关于作品创造性方面的评价,应该基于作品对传统摄影关于真实、客观性及现实主义等传统主张的破坏能制作芨芨草扫把的吴扎拉坚 新疆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2018.5)力来评估,以及对事物赋予一种新意义的能力来评估。”

驯马的贺耶尔文忠 新疆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2018.5)

爬上苜蓿草垛劳作的唐别勒克 新疆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2018.5)
还有,有人提出当代艺术有三个重要特点:第一,抛弃了之前艺术的单一媒介,诸如绘画和雕塑的局限性,尝试以一种跨媒介的方式展开。因此,我们曾经依赖的对单一媒介的技术和美学的理解,就不能适用于当代艺术。第二,把古典和现代艺术的“静观”转变为当代艺术的“剧场性”,也就是说,当代艺术更强调与观者的互动。当代艺术家往往把展览场地变成一个剧场,通过场面调度,邀请观众参与到作品中去,甚至使观众成为作品的一部分。第三,当代艺术的作品具有极强的“场域特定性”,也就是说,它常常只能在它被创造出来的空间中存在,如果空间变换了,它的意义就会面目全非,甚至完全丧失。
我的《西迁人》系列作品之所以有这样的递进关系,就是赞同了前面的这些艺术观点,并进行了深刻的艺术思考与严肃的探索实践。

帮雇主插秧的男子 新疆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2018.6)

在伊犁河边拉网的江海和他的朋友们 新疆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2018.6)

退休后住在伊犁河边打渔的顾尔嘉宝昌 新疆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2018.6)

给30亩麦子地浇水的吴扎拉西文昌 新疆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2018.5)

守护伊犁河原生态河滩地的老人 新疆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2018.6)

在伊犁河边撒网的男子 新疆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2018.6)

西迁节家庭聚会上跳舞的人们 新疆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2018.6)

闲暇时弹琴的96岁老人安德荣·新疆察布查尔县(2018.6)


在家中供奉的“喜利妈妈”前为家族祈福的巴叶尔新芳 新疆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2018.5)

歌曲《小白杨》的原型程富胜在自家院中的岗楼上怀念军旅时光 新疆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2018.6)

打渔归来 新疆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2018.6)

从伊犁河里打到鱼的人们 新疆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2018.6)

查看秧苗的妇女 新疆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2018.6)

制作芨芨草绳子的人们 新疆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2018.5)

在伊犁河湿地撒网的男子 新疆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2018.6)

大风后在玉米地里查看秧苗的吴扎拉志坚 新疆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2018.6)

在自家苜蓿田里招呼商贩的巴叶尔忠清 新疆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2018.5)

到察布查尔大渠龙口祭拜先祖图伯特的锡伯族青年新疆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2018.5)

铺设网线的的男子 新疆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2018.6)

放养火鸡的老人 新疆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2018.6)
——评《全球视野下的当代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