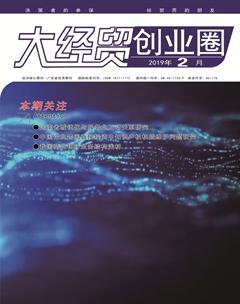透视我国代孕合同的司法需求
吴琳玲
【摘 要】 代孕是一个需要严肃对待的社会现象,我国对代孕技术的应用是不支持,却也未用法律明确代孕等辅助行为的违法性。这种法律“真空”下,代孕已成为一个无法管控的暴利黑色产业。在现代社会科技进步的背景下学界认识到约束代孕行为的必要性,更加关注到解决此类案件实际追求的公平。本文在分析案件判处结果的基础上,提出几点涉及代孕的司法需求。
【关键词】 代孕 代孕合同 立法
一、代孕的社会现状与立法问题
(一)社会现状
儒家传统文化根植至今千年不朽,如宗族血亲的重大责任为首就是“传宗接代”“天伦之乐”,从闭塞落后的村庄“买妻”到纸醉金迷的城市“养小三”,求子传承现象屡见不鲜。随着科技的发展,人工辅助生殖技术进入了社会市场,也一脚踩上了人伦道德和法律领域的边界,其中试管婴儿已被国家所认可,而代孕在法律上仍“讳疾忌医”。
持支持的观点在于代孕是生育权和隐私权的延伸,即生育权的内容应当随着社会发展和生育政策调整而拓展,且认定生育方式的选择纯属个人隐私权的范畴,国家无法过多干涉。但应当明确基于权利进行立场站定,也会因权利不甚具体的法律内涵而产生争议。反对派则认为代孕视女性为生育机器,把人类当工具使用是在践踏人格尊严。如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在判决著名的“客体公式”:当一个具体的个人被贬抑为课题、仅是手段或可替代之数值时,人性尊严已受伤害。然而,无论是完全代孕还是部分代孕,其本质都是借用(无偿代孕)或者租用(有偿代孕)女性身体的一部分,这就是将女性的身体工具化,甚至是商业化,贬损了代孕女性人格尊严。
(二)立法问题
目前我国代孕的态度还是抵制的。卫生部2001年颁布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第三条规定:“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不得实施任何形式的代孕。”第二十二条规定:“对实施代孕技术的医疗机构,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给予警告、三万元以下罚款,并给予有关责任人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追究刑事责任。”2015年6月份各个省市的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印发了“打击代孕专项行动方案”,同年12月27日通过了《中国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修正案)》却又删去了“禁止代孕”的相关条款。对于国家来讲,人口问题一直是国家大计,从原先的独生子女政策到如今的二胎开放鼓励,可见人口减少失衡严重。关于代孕的文件散见于部门规章和政府工作文件中,这些仅有行政规章,不能形成规范的法律规范体系,与其他部门法中的有关规定不能很好的衔接,显然与其重要地位不相符,难以起到应有的保障作用。
国内立法现状在代孕方面是缺乏的,存在很多问题:一是立法步伐缓慢,实践当中涉及案件不少,却仍未有法律及时调整和规范;二是制定的行政规章效力较低,发挥的作用也是很有限的,况且至今没有相关的法律或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决定等出台,以支撑这些行政规章,它们的效力犹如空中楼阁,无法落于实际;三是仅有行政规章,没有形成一定的法律规范体系,与其他部门法中的相应规定不能很好的衔接,显然与其重要地位不相符,难以起到应有的保障作用。虽有正当性,但执行起来很是困难;四是缺少专门的管理机关,同其他机关的行政管理通病一般,哪个行政部门负责管理,如何管理并没有做出明确的规定,权责也不明确,实际的管理效果必然不佳。
二、代孕案件分析
科学技术的双重性本就是一把“双刃剑”,代孕技术亦不例外。现今的技术要为人类发展贡献力量,需要得到正确的对待,而不是盲目的禁止。关于代孕合同的效力以及代孕行为本身,我国还未用以法律确认或者予以禁止。查阅近年来我国各地法院审理的代孕案件,可得出现今法律主流的立场。选取了四个案件,分别是08年广西南宁市江南区法院、10年的广东佛山市顺德区法院和湖南常德市鼎城区法院、12年福建厦门市思明法院,除了湖南一案是妊娠型案件外,其余三件是基因型代孕案件(即所需卵子来自于代孕母,所生孩子与代孕母有生物学上的亲子关系)。
从上述裁判结果来看,妊娠型案件中的代孕协议有效,而基因型案件都以代孕协议违反公序良俗原则认定无效。总体来看代孕协议的主流观点是,法院认为基因型代孕协议中,因婴儿同代孕母有血缘关系,代孕母等同于将自己的亲生孩子卖给他人,显然是具有了贩卖人口的色彩,虽然代孕母自身或许不这么认为,但这确实是社会上很难被容忍的。反观,妊娠型代孕中,认定协议合法的依据在于代孕母出售的是服務,而不是婴儿。既然实践中的处理方式已经出现,将“妊娠代孕”(完全代孕)纳入法律规制的范畴予以合法化,才是解决问题的最佳途径。
三、司法应何为?
对代孕合法化最有吸引力的辩护是一种法律经济学的分析,即基于传统道德伦理和公序良俗等“常识”的代孕管制是没有效率的,它无法禁绝代孕行为,与其如此 ,还不如“去管制化 ”,放开代孕并承认代孕协议的可执行性。有社会民意调查显示,代孕的支持率与被采访者所处城市的开放性程度、受教育程度成正比, 与受访者年龄成反比。可以预测,随着时代的更迭和思想的开放,社会对于代孕的接受度会逐渐提高,也不是竭力抵制。
基于以上这些分析,本文认为因自然生殖困难而求助于代孕的社会现象,合理的做法并不是一味禁止,应是“变堵为疏”。在立法上:一是应将“妊娠代孕”定位为生育的辅助手段,将代孕限制在有限的范围内;二是明确“妊娠代孕”协议的性质是属于人身关系方面的委托代理合同,而不是所谓了“人口买卖交易”,代孕行为的客体是代孕母代替他人生育的行为;三是确认代孕协议的效力,但这个协议的效力要经有关部门核准登记后才具有法律效力;四是规范协议的内容,用法律的方式确定下双方的权利义务。因为这种协议具有人身性,不可强制履行,法律可以规定一定数额的金钱处罚的方式来“迫使”代孕母履行义务。
【参考文献】
[1] [美]斯蒂文·沙维尔:《法律经济分析的基础理论》,赵海怡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2] 周平:“有限开放代孕之法理分析与制度构建”,载《甘肃社会科学》2011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