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腊的演说术与修辞术之辩(上篇)
刘小枫
(中国人民大学 文学院,北京 100872)





我国古代的政治生活中未见有演说,我们今天的政治生活方式虽然已经相当西化,演说仍然未见得有多重要,“作报告”(和听“报告”)才重要。从形式上看,作“报告”像是演说,实际上不是。反观当今欧美国家,演说不仅形形色色,而且在各种层次和样式的政治活动中都起着重要作用。我们若不了解何谓演说术,恐怕很难准确理解西方人的政治言辞,与西方人打政治交道时也未必能得体地表达自己。
关于古希腊的演说辞和修辞术,我国学界已经积累了为数不少的翻译文献,但这不等于我们已经理解了古希腊的rhetorikē。比如,这个语词应该译作“演说术”还是“修辞术”,迄今仍然是个问题。严格来讲,译作“演说术”或译作“修辞术”都未见得准确(罗念生,2006;安提丰,2016;尼采,2018;马鲁,2004;波拉克斯,2014)。
从概念的语义分析角度讲,演说术明显仅仅是修辞术中的一种。但在古希腊的智术师那里,rhetorikē的确仅仅指演说术,或者说修辞术即演说术。对于苏格拉底来说,情形绝非如此。从柏拉图的作品中可以清楚看到,在雅典民主时代,演说术与修辞术之辨曾演化成一场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政治思想冲突,而我们迄今仍未深入探究过这场冲突的政治史乃至政治思想史含义。
1 城邦政体与演说术
演说是针对大庭广众的言辞行为,用今天的话说叫公共言辞行为。除了古希腊之外,我们在其他古代文明的政治生活中并没有看到类似的行为,也没有看到大量演说辞流传下来。为何古希腊文明乃至后来的欧洲文明会形成一种演说文化传统,这个问题并不容易回答(金志浩,1995;Kai Brodersen,2002;柏克,2003;费伦,2002;刘亚猛,2004;麦科米斯基,2014)。
演说所需要的“技艺”即演说术是古希腊智识人的发明,史称这类智识人为智术师。通史类的史书告诉我们,演说术兴盛于雅典城邦的民主政治时期。可是,我们断乎不能说,雅典城邦的民主政体是古希腊演说术形成的土壤。因为,发明演说术的智术师们没有一个是本土出生的雅典人,而泛希腊城邦也并非个个都是民主政体。
毋宁说,城邦政体本身才是演说形成的土壤。从政治史学上讲,城邦是小型的自主政治单位,即以城市为中心加上地域相当有限的周边村社构成的政治体(雅典城邦约两万人),城市平民是政治生活的主体——与此形成对照的是部落型政治体。演说出于城邦生活的需要,这意味着,演说总是与聚生在城市的民众相关。反之,部落政体没有城市,也就没有民众,从而无须演说。换言之,要掌握城邦或者说掌握民众,就需要演说术。

略知西方文明成长史的人都知道,无论在古希腊—罗马还是中古尤其近代时期的西欧,作为一种独立政治单位的城市政体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帕克,2007)。古罗马共和国仅仅是小小的罗马城,凭靠与意大利地区的其他部族建立“拉丁同盟”,罗马城人才获得地缘扩张的体能。尽管意大利地区的诸多部族为罗马城市政体的权力扩张做出了巨大贡献,却没有罗马公民权。公元前一世纪初,意大利地区的一些部族造反,要求获得罗马公民权,罗马城人与周边的意大利部族因此爆发了内战,史称“同盟战争”(Bellum sociorum,前91—前88年)。
公元前90年,罗马元老院被迫通过“尤里乌斯法案”(Les Iulia),宣布凡不曾造反的意大利部族都可获得公民权,战事才逐渐平息。至公元前70年,罗马城的居民比战前增加了一倍(达91万)。可见,在此之前,罗马共和国虽然打赢了诸多战争,其政治体的核心不过是人口不到50万的罗马城市。正是在这样的政治体中,演说成为一种政治传统(撒路斯提乌斯,1994,2009,2011)。
当然,严格来讲,有政治生活就难免会有演说,毛泽东在三湾镇改编秋收起义队伍时站在树下发表的演说就非常著名。大大小小的政治动员都离不开演说,问题在于,有演说未必一定会产生演说术。演说之术作为一种政治性知识基于城邦人对政治生活的认识,而这种认识只能来自少数智识人。著名演说家高尔吉亚(约前485—前376年)是演说术的发明者之一,他的生平颇能说明这一点。
高尔吉亚出身在西西里的希腊殖民地勒昂蒂尼城(Leontini),早年曾跟从自然哲人恩培多克勒学习,而他的本行是医术。高尔吉亚在自己的城邦成名很早,但不是靠他的医术,而是靠他的政治才干即能言善辩。当勒昂蒂尼城面临叙拉古城的兼并威胁时,高尔吉亚已经年过六旬,仍受城邦重托,率领使团到雅典求援。
古希腊的政治状态由众多分散而自主的城邦单位构成,并没有形成更高一级的政治单位(国家)将各城邦统一起来。可以设想,若雅典城像后来的罗马城那样,成功建立起一个希腊人同盟,没准也会搞出一个雅典共和国。事实上,不仅雅典,斯巴达和忒拜城邦都曾有过这样的政治企图。
高尔吉亚在雅典的政治演说让雅典人着迷,这促使他留下来开办演说术学校,而他并非在雅典开办这类学校的第一人。高尔吉亚到雅典的时候,时逢施行民主政体的雅典崛起,他的学生包括雅典民主时期的三代名流:伯利克勒斯、修昔底德算是老一辈学生,克里提阿、阿尔喀比亚德、阿尔基达马斯(Alcidamas)等政治名流算中间辈,演说家伊索克拉底和肃剧诗人阿伽通最年轻。高尔吉亚还游走希腊各城邦发表演说,名满泛希腊,名利双收,获得大量财富而且高寿。高尔吉亚去世之后,据说希腊人还在庙宇为他立了一座金塑像(沃迪,2015)。
看来,雅典的民主政体的确为演说术提供了更大的用武之地,或者说,演说术在民主的雅典才得以发扬光大。就像如今大学开设实用性学科一样,“社会”有此需要,智术师们发明的演说术才有“市场”。毕竟,由于雅典城邦推行“平等议政权”,训练城邦民在公民大会上的演说能力就成了一种政治需要。
2 演说辞与修辞技艺
无论是外邦人高尔吉亚、普罗塔戈拉、忒拉绪马霍斯、伊索克拉底还是雅典人德摩斯忒涅,他们作为演说家其实就是如今的政治家。毕竟,演说无不涉及城邦事务,并具有显而易见的政治效用。然而,演说术等于政治术吗?或者说,智术师们把演说术视为政治术是什么意思呢?
原则上讲,每个雅典城邦民都有“平等议政权”,从而在城邦生活中有演说的权利,但事实上并非每个城邦民都愿意或有能力演说。这意味着,即便把城邦事务交给城邦民,提倡如今所谓参与式民主,真正有兴趣而且有能力演说的人始终是少数。


在民主的雅典,没有演说能力的城邦民若要上法庭或参加公民大会,就得请人代写演说辞。高尔吉亚或普罗塔戈拉这样的外邦来的智术师既擅长写演说辞也擅长发表演说,但著名演说家未必是实际的演说家,而是写作演说辞的高手。吕西阿斯(Lysias,前445—前380 )作为演说家在雅典非常著名,由于是外来移民,没有完全公民权,他的才华只能用来替人写演说辞或教人写演说辞。伊索克拉底同样是外来移民,而且生性羞涩,
由此可见,演说虽然是一种口头言辞行为,却基于文章写作,或者说,演说术首先是一种文章写作技艺。在雅典城邦,演说辞已经成为与诗歌、戏剧、论说、叙事(散文)并置的一种文类。正因为如此,rhetorikē这个语词在今天也被译成“修辞术”,因为,演说术教材所讲的内容的确有不少涉及如今所谓的修辞技艺。但我们不能反过来说,如今的修辞学相当于古希腊的演说术。
智术师们撰写的演说术小册子没有一本流传下来,今人能够看到的关于演说术的一手文献,仅有亚里士多德的《修辞术》。严格来讲,这部讲稿的书名应该译作“演说术”。但亚里士多德不是智术师,而是反智术师,他讲授演说术想必有其特别的用意。



中古时期的基督教学者为了传授写作技艺,按这三种体式(Genera)来划分维吉尔的诗篇,或者说用维吉尔的诗篇作为三种体式的范本:《牧歌》(Bucolica)属于“平实体”;《农事诗》(Georgica)属于“适中体”;《埃涅阿斯纪》(Aeneis)则属于“宏大体”。按这样的文体框框来归类维吉尔的诗作肯定属于削足适履,但这种划分让我们看到,古希腊演说辞的写作规则对古罗马文人以及后来的欧洲文人的影响。如果对比刘勰(约465—约520)的《文心雕龙》中的《体性》篇对文体风格的区分(八种体式:典雅、远奥、精约、显附、繁缛、壮丽、新奇、轻靡),那么我们会说,古希腊智识人的文体风格分类不如我国古人精细。但我们应该意识到,演说术仅仅涉及演说辞文体。

无论哪种类型的演说辞,也无论演说辞针对何种具体事情,其实践目的都不外乎ad persuadendum(具有说服力),让人信以为真。要实现这一目的,演说者首先需要有雕琢言辞的能力。在演说术学校的五项基本课程中,“措辞”技艺最为繁复,专业术语也特别多。

狭义修辞的最高境界是恰如其分或得体,单纯追求文饰是一种缺点。演说术课程会教导何时使用及何时舍弃文采,若要让说辞客观得有如实录(如在法庭上提供证词的演说),文饰就必须省着些用,叙述显得平实才更令人信服。
文饰仅仅是最低层次的修辞技能,更高层面的修辞技能还涉及运用各种文体。比如,在叙述文体中插入对话体,不仅可以使得叙述生动活泼,还可以借人物的言辞(对话中的言辞)在他人的面具下表达自己。
一篇演说辞无论局部还是整体,文体和言辞都要善于通变(variatio),这是一条修辞规则,如《文心雕龙·通变》所说,“文辞气力,通变则久”。
3 演说辞的修辞性推论

吕西阿斯因是外来移民,不能上法庭替人发表诉讼演说,但有一次他不得不亲自出庭为自己发表演说。此事的起因是雅典民主政治制度时期著名的“三十僭主复辟”,吕西阿斯是民主派分子,当时他贿赂前来拘捕他的人才得以逃命,而他哥哥珀勒马科斯(Polemarchos)则被判饮鸩而死,家族财产全被没收(三套房子、大笔钱财、120个奴工和一批工场制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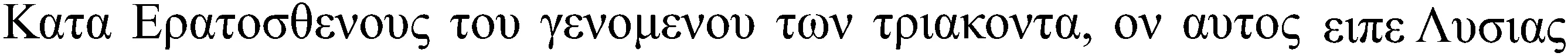
全篇分四大部分,结构谨严,层次分明,呈现了诉讼演说的修辞性推论的基本结构(Dover, 1968; Kirfel, 1978; Todd, 2007)。

随后,吕西阿斯直接针对厄腊托斯忒涅本人提出指控。第一,介绍厄腊托斯忒涅其人:他本人及其朋友出庭(22);第二,详陈对厄腊托斯忒涅故意杀人罪的控告(23)。

额外证据(extra causam):被告为自己辩护过后,吕西阿斯进一步指斥被告在过去的所作所为(37-78)。首先,吕西阿斯指控厄腊托斯忒涅卑鄙无耻,从未做过任何一件好事来弥补其罪行,他还想为自己辩护,可见寡廉鲜耻之极(37-41)。随后,吕西阿斯从正反两个方面揭露,厄腊托斯忒涅一贯与民主政体为敌。
正面揭露:厄腊托斯忒涅在骚乱时期亲自参加颠覆活动,还曾在赫勒斯塝海峡为寡头政体制造舆论,一度从船上开了小差(42)。具体举证:第一,Aigospotamoi战役之后,厄腊托斯忒涅成了五人督察官之一(43-47);第二,作为寡头统治成员之一,他从未做过一件减轻民众负担的事,却参与了三十僭主的所有罪行(48-52);第三,三十僭主倒台之后,他同斐东(Pheidon)一伙企图破坏和谈(53-61)。
反面揭露:厄腊托斯忒涅称自己是忒腊墨涅(Theramenes)的同志,这并不能减轻他的罪责,因为忒腊墨涅是民主政体的叛徒。证据有二:第一,作为四百人团的头目,此人背叛了自己的同志(65-68);第二,作为和谈代表,他使雅典落入斯巴达人之手,三十僭主复辟才得以得逞(69-78)。
(3)结论(79-91):陈述被告罪无可赦的理由。第一,被告不应受到宽赦,作为30僭主之一,对厄腊托斯忒涅的惩罚只能是死刑无异于代替法官做出判决(81-84);第二,要不是指望得到有权势的熟人帮助,厄腊托斯忒涅不会向法庭自首(84-85)。因此,此案的嫌疑人还有:1)那些为厄腊托斯忒涅说情的人(85-86);2)为其免罪作证的人(87-89);3)将他无罪释放的法官再次对法官施加压力(90-91)。

4 葬礼演说与激励城邦
雅典城邦有一种政治传统,即以公共仪式吊唁在战争中牺牲的同胞,赞美死者,抚慰家属,激励城邦民的致悼词(Epilaphios)是首要的仪式,即著名的葬礼演说。修昔底德记载的伯利克勒斯为伯罗奔半岛战争早期的牺牲者所致的悼词非常著名,甚至已经成为政治思想史上的经典文献。
吕西阿斯没有资格发表葬礼演说,但他写过教人如何写这类演说的范文。悼词开头少不了要回顾牺牲者们的丰功伟业,吕西阿斯的这篇葬礼演说辞是虚拟的,因此,他以希腊历史故事代拟:首先提到雅典人反抗亚马族人的战役,接着讲述了七将战忒拜的故事。
阿德腊斯托和珀吕内克攻打忒拜,在战斗中身亡,忒拜人不想让死者得到安葬。雅典人却认为,就算是这些死者行了不义,他们也因为死而遭受到最大的惩罚,何况冥府的神们会得不到本来属于自己的东西,而天上的神们也会因为(自己的)圣地受到玷污而受到亵渎。于是,雅典人先派出传令官,要他们去请求允许安葬死者,因为,雅典人认为,是好男儿就该去找活着的敌人报仇,对自己没信心的人才会用死者的尸体来证明自己勇气。
因为请求未能实现,雅典人就向忒拜人开战。其实,从前从来没有与忒拜人闹过不和,雅典人也并非要讨好活着的阿尔格维人,毋宁说,雅典人冒这样的险,不过是因为他们认为,应该让阵亡者得到按礼法应有的东西。他们针对其中一方,为的却是双方:一方为了这些忒拜人不再犯错,拿更多阵亡者去亵渎神们,另一方则为了阵亡者们不会再如此这般地回到自己的故土——既没有父辈的荣誉,又被剥夺了希腊人的礼法,还分享不了共同的希望。
雅典人就是这样想的,当然,他们很清楚,打起仗来,机运对所有人都一样,何况他们招惹的敌人为数众多,但正义在他们这边,经过一场奋战,他们赢得了战斗的胜利。
就内容而言,这段说辞属于历史叙述。可以看到,在演示性演说中,回顾历史的目的是政治教育。为了实现这一目的,演说家必须以修辞性推论的方式重述史实(Shear, 2013: 511-536)。由此可见,如今的修辞学绝不等于古希腊的演说术(rhetorikē)。因为,演说术绝非仅仅是如何应用文辞和谋篇布局的技艺,毋宁说,演说家承担了塑造城邦民的政治德性的责任和义务。
5 《海伦颂辞》与修辞性推论

我们还是看智术师自己怎么说。
罗马帝国时期的雅典智术师菲洛斯特拉托斯(Philostratus,170-247)在其《智术师传》(VitaeSophistarum,1.9)中称,高尔吉亚是“智术之父”,在演说术方面,他为智术师们开了先河,做出了努力,开启了“吊诡法”“一气呵成”“夸大”“断隔句”“入题法”等等,他还利用了有装饰并且庄严的充满诗味的辞藻。

可见,古希腊人关于“海伦事件”的说法长期说法不一。高尔吉亚的《海伦颂辞》利用这一事件来阐发他的演说术理论,堪称选材精当。
开场白是一段言辞华美的大道理,高尔吉亚说:
这话听起来像是在说,政治生活中有是非、对错和高贵与低劣之分。但是,在现实生活中,要区分是非、对错和高贵与低劣,实际上很难。高尔吉亚随即引出“海伦事件”,以此证明这一点:
关于这个女人,听信诗家的听众所持的信念,以及关于这个名字(已成了一次灾祸的铭记)的流言,都是一致同声。我愿意用辞章给出某种合理考虑来为这个坏名声的女人涤除罪咎,去演示那些谴责者都在骗人,要指出真相,终结无知。(《海伦颂辞》2)

但是,这仅仅是权力之争吗?高尔吉亚在一开始就说,政治生活中有是非、对错和高贵与低劣之分。换言之,演说家与诗人之争涉及应该如何正确引导人民这一大问题。不难设想,这样一来,区分政治生活中的是非、对错和高贵与低劣,的确成了首要问题。
高尔吉亚通过这篇演说辞建议应该放弃这种区分,让我们来看他如何论证这一点。

这无异于说,对“美”的“爱欲”支配了所有能人,从而可以说是对人性下了定义。我们应该问:富豪、贵族、美男子和有智慧的人心目中的“美”会是同一个“美”吗?苏格拉底会说,在热爱智慧的人眼里,海伦固然漂亮,但绝对算不上纯粹的“美”,因为血肉之美无论如何不会是纯然精粹的美(比较《会饮》和《希琵阿斯前篇》)。
高尔吉亚并没有说,不同类型的人对“美”有不同的看法。他接下来就说:
接下来高尔吉亚提出了自己的论题(“立题”):海伦可能去了特洛伊,是由于帕里斯用言辞说服(等于欺骗)了她。这个论题转移了主题:从“爱欲”转向了“言辞”,而“美”的魅力是连接的关键——言辞同样具有令人难以想象的魅力。

这段说法有三个看点:首先,对海伦的赞颂变成了对帕里斯的言辞能力的赞颂,或者说对言辞行为本身的赞颂;第二,言辞行为的作用是“说服”灵魂,而这与“欺骗”灵魂是一回事;第三,所谓“说服”或“欺骗”灵魂的具体含义是,让世人的灵魂摆脱“恐惧”或“痛苦”,产生“喜悦”并变得温软。
高尔吉亚进一步论证说,人生活在言辞之中,因此并不存在什么“事情的真实”或“事件的真相”。所谓“事情的真实/真相”都不过是人们的说法,这些说法仅仅体现了人们对事情的“意见”,世人不得不生活在种种意见之中,毕竟:

依据这一观点,高尔吉亚提出了一个重要论断,即认可言辞的看似如此的作用:


第三种是哲学论辩式的言辞,即从正到反、由反到正地考辨意见。这种言辞看似在求真知,其实同样是一种试图说服他人的强迫行为。
可以看到,虽然区分了三种言辞样式,在高尔吉亚看来,自然科学和哲学论辩式的话语究其实质与政治话语没有差异,不外乎凭借言辞强迫人们“信服”某种道理,这有如对人的灵魂下药:

高尔吉亚关于“演说术”的说法让我们看到了他对城邦生活的认识,用今天的话说,他的演说术的确属于一种政治术,即让民众的灵魂进入一种沉迷状态。如苏格拉底一针见血地指出的那样,高尔吉亚“并不关心正义与不义”这类首要的政治问题:
作为雅典城邦民,苏格拉底关切城邦的德性,他不得不坚决抵制高尔吉亚以及其他外邦来的智术师,由此引出了演说术与修辞术之辨(施特劳斯,2017)。
6 苏格拉底的演说与修辞术
雅典民主时代早期的演说辞大都没有流传下来,但在修昔底德的《战争志》中,我们可以看到各类演说辞,最为著名的即伯里克勒斯的“葬礼演说”。由此可知,演说家在雅典的民主政治制度时期的确曾起过重要的政治作用(Heldmann,1982;魏朝勇,2010)。因此,雅典在伯罗奔半岛战争中最终战败,人们把罪过归咎于演说家:


即便这类说法是后人编的,我们也可以从中看到:第一,演说能力的确曾是做政治家的条件;第二,在民主的雅典城邦,政治家尤其得凭借演说能力;第三,能说会道的演说才干并不等于政治才干,或者说,演说术的确不等于政治术。施特劳斯在解读色诺芬的《上行记》时提到,色诺芬是苏格拉底的学生而非智术师的学生,在政治的危难处境中,他挺身而出,率领一万将士化险为夷,成功返回希腊。相反,高尔吉亚用演说术训练出来的将领却惨遭自己部下杀害。
在柏拉图笔下,苏格拉底一生从未发表过公共演说,直到70岁时在法庭上面对代表城邦民的陪审团发表自辩演说。从柏拉图的记叙来看,苏格拉底对法庭辩驳演说的修辞程式和套语非常娴熟,应用自如(Meyer, 1962: 45-64)。看来,苏格拉底否定智术师的演说术,不仅是因为有人凭演说才干成为政治家会给政治共同体带来覆亡危险,还因为别的原因。
在柏拉图的《会饮》中我们看到,客人们各显才智发表演说颂扬“爱欲”,呈现了演示性颂扬演说辞的各色典范,但轮到苏格拉底发表演说时他拒绝了。从苏格拉底陈述的拒绝理由来看,他与智术师的根本分歧在于:智识人究竟应该如何引导民众的灵魂。
柏拉图的《普罗塔戈拉》记叙了苏格拉底还不到40岁时与普罗塔戈拉的一场论辩。当普罗塔戈拉就应该如何教育雅典城邦民发表了一通类似议政演说之后,苏格拉底对在场的听众说:
我有个小小的地方没想通。显然,普罗塔戈拉轻易就能开导(我),既然他开导了那么多的事情。毕竟,如果有人就同样这些事情与任何一个民众演说家——无论伯利克勒斯,还是别的哪个铁嘴——讨论,大概也会听到这样一些说法。可是,如果还有什么要进一步问,(他们)无不像书本那样,既不能解答,也不能反躬自问。如果有谁就所讲的东西中哪怕小小的一点儿问下去,(他们)就会像被敲响的铜盆响个不停,直到有谁摁住它。那些演说家们就这样,要是有人问一丁点儿,他们就会扯出一段长篇大论。(《普罗塔戈拉》328e3-329b2)
这段说法被视为苏格拉底反对演说家和演说术的最早证据,其中有两个要点值得注意。首先,演说是针对民众的政治行为,演说家要么是民主政治的领袖,要么是试图掌握民众的智识人(如普罗塔戈拉),苏格拉底不是这两种人,所以他拒绝演说。
第二,演说家的演说行为表明,他们没有“反躬自问”的德性。用今天的话来讲,演说家就像如今的“公知”,他们的心性特征是自以为是,“拎着学识周游各城邦贩卖”,夸赞自己贩卖的东西,向有欲求的人兜售。其实,他们“并不知道自己贩卖的每样东西对灵魂有益还是糟糕;同样,从他们那里买的人也不知道,除非他碰巧是个灵魂的医生”(《普罗塔戈拉》313d5-e3)。
从《海伦颂辞》中可以看到,高尔吉亚本人就让自己显得是“灵魂的医生”。问题在于,他是什么样的“灵魂的医生”?
在柏拉图的《斐德若》中,苏格拉底与迷恋言辞的青年斐德若就这个问题展开过深入讨论。这篇作品也被视为关于古希腊演说术/修辞术的经典文献,其中就提到约公元前五世纪末在西西里岛创建第一所演说术学校的叙拉古人泰熙阿斯,相传他是高尔吉亚和吕西阿斯的老师。苏格拉底说,在演说术的发明者看来:
看似如此的东西比真实的东西更值得看重。凭靠语词的力量,他们(能)搞得让渺小的东西显得伟大,让伟大的东西显得渺小,把新东西搞得陈旧,把陈旧的东西搞得很新——他们还发明了就任何话题都既能说得极短又能拖得老长(的能力)。(《斐德若》267a6-b2;比较《高尔吉亚》452d-453a)

在我看来,谈论老年和贫穷扯得来催人泪下,那位卡尔克多尼俄斯人(忒拉绪马霍斯)的力量凭技艺威力才大呢。这男人厉害得能让多数人激愤起来, (然后)靠歌唱般的言说再哄激愤的人们(昏昏欲睡)——这是他自己说的。而且,无论是诽谤(他人)还是摆脱随便哪里来的诽谤,他都极为得心应手。(《斐德若》267c5-d3)
《斐德若》一开始呈现的情景是斐德若对吕西阿斯的一篇带私人性质的演说辞着迷。我们难免感到奇怪:难道私人之间也有演说?演说不都是面对公众的言说行为吗?
斐德若迷上的这篇演说辞未必真的出自吕西阿斯手笔,毋宁说,柏拉图以此笔法表明,在苏格拉底看来,智术师们的演说术忽略了言辞行为的一个重要维度。在《斐德若》中,苏格拉底两次仅仅对斐德若一个人发表演说,而且极富表演姿态。这意味着,在苏格拉底看来,言辞行为的演示性不仅可用于引导众人的灵魂,而且可用于甚至首先应该用于引导个体的灵魂。
与斐德若讨论修辞术时,苏格拉底一开始就说:
《斐德若》中有三篇演说辞,主题都是“爱欲”,而高尔吉亚的《海伦颂辞》同样涉及爱欲:

高尔吉亚并没有进一步辨析爱欲在不同的人身上的伦理品质差异,在《斐德若》中,苏格拉底则让我们看到,爱欲有多种灵魂样式,或者说有高低不同的德性品质,高尔吉亚的演说术恰恰无视爱欲品质的德性差异。
在《会饮》中,斐德若提议在座各位各自发表一篇演说颂扬爱欲,这无异于提议就颂扬爱欲展开演说竞赛,而他自己也第一个发表演说。《斐德若》的戏剧时间在《会饮》之后,这意味着,苏格拉底试图通过自己的修辞术救护斐德若的灵魂。由此可以理解,《斐德若》的场景为何是私人性交谈,而苏格拉底为何对斐德若一个人发表演说。显而易见,苏格拉底更看重rhetorikē对个体认识自己的爱欲的作用,这才是真正的灵魂教育。因此,苏格拉底提倡的rhetorikē不妨称为“爱欲修辞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