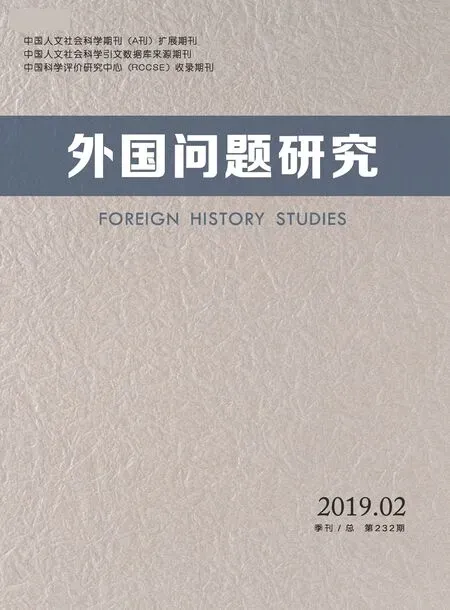日本学术思想史的变革
连清吉
(日本长崎大学多文化社会学部,日本长崎8528521)
宫崎市定(1901—1995)于所著《东洋的近世》中①宮崎市定《東洋的近世》一文,首先由教育タイムス社于1950年11月出版,其后分别收入《宮崎市定アジア史論考》上巻,東京:朝日新聞社,1976年;《東洋における素朴主義の民族と文明主義の社会》(東洋文庫508),東京:平凡社,1989年;《宮崎市定全集》巻2,東京:岩波書店,1992年。本文以东洋文库版为底本而论述。强调历史学的任务是探索历史发展的新公式,而不是以既成的公式梳理历史的事实。历来在架构世界史的体系时,大抵采取西洋为主,东洋为辅的立场。然而综观世界史的事实,西亚波斯帝国是世界史上首先出现的古代帝国,其次是中国的秦汉帝国,最后是西洋的罗马帝国。象征近世的文艺复兴(Renaissance)也先后出现三次,首先是8世纪在西亚发生,其次是10到11世纪的中国宋代,然后是14到16世纪的欧洲。以东西洋对等的观点,才能客观详实地厘清历史发展的事实。至于世界史的轨迹,也不是东西世界各自发展形成,而是相互交涉影响的历史循环。
宫崎市定主张文艺复兴的历史是中世进入近世的关键。文艺复兴的历史既是人类文化高度发展的结晶,中世长期停滞的必然趋势,也是社会进化的标准。换句话说,文艺复兴不仅是思想飞跃的产物,更是在社会综合进步的基础上所形成的精神和社会的象征。东洋社会在10、11世纪的宋代即发生文艺复兴的现象,宋代社会经济的跃进,都市的发达和知识的普及,都与欧洲文艺复兴有并行同步的发展。其在所著《东洋的文艺复兴和西洋的文艺复兴》②宮崎市定:《宮崎市定全集》巻19,東京:岩波書店,1992年。一文中,从哲学、文学、印刷术、科学发达、艺术发达的现象,说明东西文艺复兴都具有复古、创造、进步和文化普及的精神。宋儒于新儒学的构筑,古文家的古文复兴和反映都市经济生活之讲唱文学的盛行,是继承传统的开新,火药、罗盘的发明则意味着自然科学的进步,南北画的大成,远近构图的技法不但是中国山水画的基础,也为东西绘画创作所祖述。至于象征文艺复兴初期阶段的印刷术,在宋代高度发达,不但中国境内汉籍出版文化事业发达,还传播到朝鲜、日本,促进朝鲜版和和刻本的刊行而形成东亚文化圈。就此意义而言,东洋社会比欧洲社会较具有先进性。
历史研究是事实的论理,而事实论理的方法,则以通变古今,横贯东西之时空坐标的设定,究明中国历史的发展轨迹,确立中国历史在世界史上的地位。换句话说,以“复眼的视域”,即以时间为经,通变古今历史的沿革,以空间为纬,横跨东西世界的交涉,才能辨析历史文化的因革损益及其地位。神田喜一郎(1897—1984)于所著《日本的汉文学》中说到:“日本汉文学史具有两面性,既是日本文学史的一环,又是中国文学史的再现。探究日本汉文学的推移及其因革中国文学的究竟,既不薄日本汉文学的转益更新的精彩,也爱中国古典文学的英华,如此乃能客观论述日本文学史的定位。”①神田喜一郎:《神田喜一郎全集》巻9,東京:同朋舍,1984年,第132—184頁。兹以中日学术思想交涉的“复眼的视域”,抽绎日本学术思想史上划时代的关键,论考其变革的究竟。
一、大化革新:日本学术文化的唐化
应仁天皇十六年(285)百济博士王仁来日,携来《论语》十卷、《千字文》一卷。继体天皇十年(516)五经博士汉高安茂、马丁安,钦明天皇十五年(554)五经博士王柳贵、易博士王道良相继渡海东瀛,传授以《五经》为中心的儒学。推古天皇十二年(604)发布圣德太子用汉文撰述的《十七条宪法》。根据武内义雄(1886—1966)的考证,《十七条宪法》第一条“以和为贵”出自《礼记·儒行》和《论语·学而》“礼之用和为贵”,“上和下睦”出自《左传·成公十六年》“上和下睦”和《孝经》“民用和睦,上下无怨”,第三条“君则天之地则地之”出自《左传·宣公四年》“君天也”,“天覆地载”出自《礼记·中庸》“天之所覆,地之所载”,“四时顺行”出自《易·豫卦》“天地以顺动,故日月不过而四时不忒”,第四条“上不礼而下不齐”出自《论语·为政》“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第五条“石投水”出自《文选·运命论》“其言也如以石投水,莫之逆也”,第六条“无忠于君,无仁于民”出自《礼记·礼运》“君仁臣忠”,第七条“贤哲任官”出自《尚书·咸有一德》“任官唯贤材”,“克念作圣”出自《尚书·多方》,第八条“公事靡盬”出自《诗·鹿鸣四牡》“王事靡盬”,第九条“信是义本”出自《论语·学而》“信近于义”,第十二条“国靡二君,民无两主”出自《礼记·坊记》“天无二日,士无二王”,第十五条“背私向公是臣之道矣”出自《韩非子·五蠹》“仓颉之作书也自环谓之私,背私谓之公”和《左传·文公六年》“以私害公非忠也”,第十六条“使民以时”出自《论语·学而》“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应仁天皇至推古天皇的三百余年间,以《五经》为中心的儒学浸润于日本朝廷,《五经》《论语》《孝经》等儒家经典广为王室硕学鸿儒所熟读,故能引经据典而制作日本最古的宪法。武内义雄又根据仁井田升(1904—1966)《唐令拾遗》,比较唐令与养老令(718)的大学教学科目:

养老令 唐令大经:礼记、春秋左氏传 礼记 春秋谷梁传中经:毛诗、周礼、仪礼 春秋左氏传 (以上各为一经)小经:周易、尚书 毛诗 孝经 旧令 孔安国、郑玄注(以上各为一经) 周礼 新令 开元御注孝经 孔安国、郑玄注 仪礼 论语 郑玄、何晏注论语 郑玄、何晏注 周易 老子 旧令 河上公注(学者兼习) 尚书 新令 开元御注

春秋公羊传 (学者兼习)
养老令以唐令为本,斟酌日本国情而修订。①武内義雄:《日本の儒教 その一——明経博士の學業》,《儒教の精神》,東京:岩波書店,1939年,第133—143頁。《十七条宪法》于中国先秦经典文字的征引,律令的制定取法于唐令,明经博士以五经、孝经和论语的修习为宗尚,是知日本古代以汉唐注疏为学问的根底。
二、应仁之乱:日本文化形成的契机
一般以为“应仁之乱”(1467—1477)是日本室町时代末期,京都发生的大乱。将近十年的战乱,使京都几乎变成废墟,幕府失坠、庄园制度崩坏,是中世黑暗时代,“下克上”的叛乱。但是内藤湖南主张:“应仁之乱”的十年间,地方武士的势力强大,因而加速了战国大名领国制度的发展。又由于公家(即公卿大夫)避难到地方,造成文化普及至地方,是日本文化创生的契机。
日本学术文化的发展颇受中国的影响。自圣德太子以后至平安朝接受的是汉唐注疏之学与唐代的文化。德川时代的二百五六十年则是宋明理学、宋代文化与清朝考证学。就学术文化的性质形态而言,前者是贵族文化、宫廷文学;后者则是庶民文化,而学术也由朝廷普及至民间。此一学术文化转型的契机则是应仁之乱。内藤湖南从日本文化独立的历史背景、殚精竭虑于文物的保存与文化的传播等事例,说明应仁之乱是日本脱离中国模式而创造日本独特文化的重要关键。
有关日本文化独立的历史背景,内藤湖南认为藤原时代到镰仓时代的四、五百年间,②藤原时代是指平安后期遣唐使废止(894)以后的300多年间。政治上是摄关、院政、平氏掌政的时期。学术文化上“唐风”(即中国色彩)逐渐淡薄,宗教上则是净土宗盛行。镰仓时代(1185—1333)的文化特色是武士阶级吸收公家文化,进而创造出反映时代性的新文化。影响所及,皇族公卿也产生思想改革的自觉。日本的社会形态起了巨大的变化,即武士的势力急剧扩张,逐渐形成“下克上”的局势。政治社会的情势如此,思想文化也产生由下往上,即由武士庶民的文化影响到皇族公家的现象,造成日本思想文化革新的机运。内藤湖南认为后宇多天皇(1267—1324)到南北朝(1336—1392)的100年间,是日本文化独立成型的重要关键。至于独立文化之所以产生,内藤湖南认为有内在和外在的因素。后宇多天皇以后的南朝系的天皇具有改革的思想,因而孕育了革新的机运,是日本文化之所以能独立的内在因素。而蒙古军队攻打日本九州北部,即所谓“文永、弘安之役”是日本文化独立的外在因素。内藤湖南说:“后醍醐天皇继承其父后宇多天皇革新的观念,思想独立与创造独立文化的理想已经根植于心。在学问研究方面,认为汉唐注疏之学仅止于字句训诂而不能发挥经典的义理。宋代理学恰好可以体现其学术宗旨,因而以宋学作为经典诠释的根据。”③内藤湖南:《日本文化の独立》,《日本文化史研究》(下),東京:講談社,1976年,第31頁。
由于宋学的影响,在后醍醐天皇的时代对于经书有了新的诠释。至于佛教的解释也不墨守所谓传统佛教的真言或天台的教理,而以镰仓时代兴起的禅宗为归宗。换句话说,由于后醍醐天皇提倡宋学和禅宗,当时学术界乃呈现出新思想、新解释的学问思潮。这是日本学术文化革新而趋向独立的内在因素。至于“文永、弘安之役”何以是日本文化独立之外在因素,内藤湖南说:“蒙古来袭的防御是日本开国以来的大事件,因此举国上下无不祈求神佛以免除国难。结果神灵显验,九州北部地区飓风突起,蒙古船只沉没殆尽而败退。中华文化是日本的根源,宋朝仍不免为蒙古所灭亡,而日本却得到神佛之助而免于蒙古的迫害。由于此一战役,日本产生‘日本为神灵之国’而且是世界最为尊贵的国家的思想,也助长日本文化独立的趋势。……虽然足利时代是日本文化发展的暗黑时期,文物毁于战火,古老的文化也荡然无存。虽然如此,龟山后宇多天皇到南北朝之间所产生的‘日本为神灵之国’的新思想与日本文化革新独立的理想,即以日本为中心的思想依然存在着,终于在德川时代构筑了日本独立文化的原型。此一新思想与文化独立的理想之所以能维系不坠,主要是因为应仁之乱时公卿学者于文物保存与流传的苦心经营。”①内藤湖南:《日本文化の独立》,第27—31頁。
关于应仁之乱之际时人如何殚精竭虑于文物保存与文化传播的情形,内藤湖南说:“应仁之乱虽然是日本历史上的黑暗时代;当时的贵族士人却竭尽所能地保存古来相传的文物、传播可能失传的文化与技艺,因此应仁之乱也是日本独特文化形成的时代。”在文物保存方面,内藤湖南说:“目录学不但是图书分类、书目品评的学问,也是拥有悠久文化的表征。”《本朝书籍目录》是足利时代所编纂的图书目录,从编目看来,有中国传来的,也有日本固有的书籍,虽然未必能显现出日本绝无仅有的独特性,却足以证明在混乱时代中,日本人极尽可能地保存古来相传的文化。②内藤湖南:《日本国民の文化的素質》,《日本文化史研究》(下),東京:講談社,1976年,第96—97頁。如一条兼良为避免所藏的书籍遭到战火的焚毁,将充栋的书籍藏之于书库。丰原统秋为了家传的笙谱能传诸后世而撰述《体源抄》一书。可见于扰攘之际,尽力保存古代文化之一端,是当时公卿士族共同的理念。在保存中华文物上,中国人也未必如此费心,就此意义而言,日本人竭尽心血以保存古来相传的文化得以传之后世,而将其称之是日本的文化。③内藤湖南:《応仁の乱について》,《日本文化史研究》(下),東京:講談社,1976年,第73—74頁。再者知识技艺的传授,固然是应仁之乱后,公卿贵族用以糊口的手段,却由于时代思潮的影响,形成日本独特的文化。如神道的传授,从奈良时代到平安时代的神代记事,并没有哲学性的思考。到了镰仓时代末期到足利时代之间所形成的神道,则用佛教的教义解释《日本书纪》神代卷的记述,神道因而具备了哲学的意义。吉田家的神道即是如此。又由于吉田神道具有形上架构,吉田神道乃建立其权威性,即非得到吉田家的传授就不是正统的神道。其他的技艺传授,如和歌亦然。换句话说,由于尊敬专业性、正统性与权威性而形成所谓“某家”“某道”“某流”之“文化正统”的观念,是在应仁之乱前后的时代。④内藤湖南:《日本国民の文化的素質》,第98—100頁。
三、江户文化:日本文化的文艺复兴
辻达也(1926—)在所著《江户时代的研究》中说到:“近代以来,论述日本文化始终强调明治维新,明治的文化与精神。”其实现代的日本文化与江户时代的近世文化关系最为密切。日本独特的文化大抵形成于近世,即使发生于近世以前,也到近世才定型,普及于民间,具备日本的特质。元禄(1688—1704)至享保(1716—1736)年间的文化诸相是近现代日本文化的原型。儒学是江户时代德川幕府政教施行的根据,《四书五经》是儒者武士的学养,“寺子屋”“塾”、藩校的教育设施普及。所谓“临济将军,曹洞土民”的禅宗流行,住宅出入“玄关”,起居于“书院造り”的居家生活;一日三餐,享用“天ぷら”(天妇罗)、“すき焼き”(寿喜烧),“江户前”(“握り寿司”的外卖)的饮食方式;象征商业发达,形成都市文化的歌舞伎、“寄席”“落语”(相声·讲谈)、“三味线”的艺能;浮世绘的艺术,长袖宽带和服的穿着,都是17世纪的文化现象,而当代日本的日常生活也是如此。⑤辻達也:《“日本的”文化の形成》,《江户時代を考える》,東京:中央公論社,1988年,第10—60頁。
以宫崎市定的“文艺复兴论”来考察日本近世文化的诸相,元禄享保年间的学术文化可以说是日本的文艺复兴。宫崎市定认为14世纪到16世纪欧洲形成的“文艺复兴”是区分中世与近世之划时代的重要关键,欧洲“文艺复兴”是中世黑暗的觉醒,以古代再生为媒介,而创出近世的文化,其中心思想是回归希腊、罗马古典黄金时代的复古思想,于文学表现形式既有古代拉丁语的复兴,也有以方言创作文学(但丁《神曲》)的产生。因印刷术传入书籍出版得到普及,因罗盘和火药传入科学得到发展。绘画、雕刻与建筑是艺术的尖峰。欧洲文艺复兴的精神是复古、艺术与科学。宫崎市定又说:“文艺复兴的精神与文化现象不但是东西共通具存,而且中国在10世纪到11世纪已有儒学复兴,古文运动,口语文学的流行,印刷术的发明,版刻流传而文化普及,泼墨山水,文人自由挥洒独具风格之滚动条字画,殊异于中世重视师承之碑刻书法,金碧辉煌之壁画。又由于大运河连接南北交通贸易,陆路与海上丝路畅通,文化交流活络,经济贸易发达,宋代的中国成为东西文化经贸的据点。”①宫崎市定的东西文艺复兴论,见于《東洋のルネッサンスと西洋のルネッサンス》,《宮崎市定全集》巻19,第3—50頁。宋代是“东洋的近世”,见于《東洋的近世》,《宮崎市定全集》巻2,第134—241頁。
德川幕府以林家朱子学为官学,伊藤仁斋(1627—1705)以为朱子学不能体得孔孟思想的真义,著述《论语古义》《孟子古义》《语孟字义》,以古典回归的理念,提倡“古义学”。荻生徂徕(1666—1728)转化明代王世贞、李攀龙“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文学理论,运用于“四书五经”的思想诠释,著述《论语征》《辨道》《读荀子》,提倡“古文辞学”,诸子研究与诗文创作盛极一时。至于早稻田大学出版的《汉籍国字解全书》是江户时代的儒者以“国字”和译中国典籍的“先哲遗著”,记存儒者民间讲学,普及教育的史实。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有复兴拉丁文的觉醒,“国字解”的讲述或许可解读为中国汉学日本化的先驱。而“和刻本”的出版,既是文化事业发达的象征,也是教育普及与学术精进的根底所在。浮世绘是日本绘画艺术的结晶,“寄席”的讲谈,“三味线”的演奏,都是日本独特风格的创意艺能。元禄享保年间的文艺复兴,日本独特的文化形成,继承发展而延续至今。
四、明治维新:日本文明开化
明治维新,全盘欧化,文明开化,建立近代化国家是众所周知的史实。至于明治近代汉学的沿革,町田三郎先生(1932—2018)的《明治的汉学者》②町田三郎:《明治の漢学者たち》,東京:研文出版,1998年。是日本近代汉学史论的重要著作。町田先生将明治的汉学区分为四期:
第一期:汉学衰退与启蒙思想的隆盛(明治1年—10年初)
第二期:古典讲习科与斯文会的活动(明治10年初—22,23年)
第三期:东西哲学的融合与对日本学术的注视(明治24,25—35,36年)
第四期:中日学术的总和《汉文大系》与其他(明治37,38年)
町田先生洞察四十五年间关键性的述作编辑,进而明晰日本近代思潮与汉学动向。
町田先生撷取竹添光鸿(1842—1917)《栈云峡雨日记》与冈鹿门(1823—1914)《观光纪游》两篇以汉文书写的中国游记,说明日本近代文人中国观的改变及其推移的原因所在。竹添光鸿于明治9年(1876)5月2日到8月2日,从北京出发,北上黄河流域,翻越秦栈蜀道,下三峡,游历两湖,达于上海,斐然成章。俞樾作序赞叹:“山水则究其脉络,风俗则言其得失,政治则考其本末,物产则察其盈虚。……历历指陈,如示诸掌……足以观其学识矣”。禹域游踪之旅,舟车劳顿,苦不堪言,然而竹添光鸿的日记,以“古人有言,得陇望蜀,余既涉陇之境,又尽蜀之胜矣,而意犹未餍焉,人实苦不知足矣”作结。盖以明治开国,游历中国的喜悦,又以对中国历史文化的憧憬,饱览关中巴蜀南北山川风土的珍奇妙趣,感动之情溢于言表。冈鹿门《观光纪游》10卷,载记明治17年(1884)5月到明治18年(1885)4月,游历上海、苏杭、燕京、粤南、香港的见闻。冈鹿门于《观光纪游·例言》记述:“是书记中土失政弊俗,人或议其过什。顾余异域人,直记所耳目,非有意为诽谤,他日流入中土,安知不有心者或取为药石之语乎。”目睹清朝末年政治混乱,社会失序,而以明治维新,遂行近代化国家之先进性,直言封建守旧,鸦片烟毒,科举消耗心血的弊端。町田先生分析二人中国观的差异,竹添光鸿年轻而热情洋溢,冈鹿门年长而老成冷静,是原因之一,而主要理由则是日本政治变革,国民意识随之变化。明治10年(1877)西南战役以后,日本国内统一,近代化国家的体制逐渐形成,日本的视野朝向亚洲各国。竹添光鸿旅行中国之际,明治新政府尚未稳定,无暇环顾邻国,冈鹿门之时,日本政治稳定,则以亚洲先进国家的立场,审视清国积弱不振,列强虎视眈眈的危机情势,而直言不讳。①町田三郎:《明治初年の中国旅行記(その1)-竹添井井“桟雲峡雨日記”-》《明治初年の中国旅行記(その2)-岡鹿門“観光紀游”-》,《明治の漢学者たち》,東京:研文出版,1998年,第27—61頁。町田三郎:《明治的汉学家》,连清吉译,台北:学生书局,2002年,第29—68页。
町田先生认为,历来对于丛书的编辑不甚重视,然丛书的编辑既是出版文化取得社会发言权的象征,也是考察时代学术思潮取向的根据所在。《汉文大系》与《汉籍国字解全书》是探究日本近代汉学如何评价中国明清与日本近世汉学的重要文献。由服部宇之吉编辑的《汉文大系》刊行于明治42年(1909)到大正5年(1916)的8年间,共22卷、收载38种汉籍,由富山房出版。《汉文大系》的编辑目的有二:一为系统地介绍具有代表性而且是常识性的中国古典及其精审的注释;二为搜集日本幕末到明治时代儒学者的研究成果。《汉文大系》所收集的中国古典注释不但有唐宋及其以前的注解,更值得留意的是清人注释的收集,如孙诒让的《墨子间诂》、王先谦的《荀子集解》。至于日本江户儒者的注释,特别是诸子的注疏,如安井息轩的《四书注》,太田全斋的《韩非子注》等,亦有收录。因此,《汉文大系》的编辑固然可以代表日本近代学术研究的成果,更重要的是,随着日本近代化国家确立的时代背景,在学术研究上,日本也有足以与中国最新学问、即清朝学术比肩的研究成果,特别是诸子研究,日本的研究未必逊于清朝。兼收中国明清与日本于汉学研究成果,进而显示日本汉学特色,或许是服部宇之吉编辑《汉文大系》的用心所在。《汉籍国字解全书》于明治42年(1909)到大正6年(1917)的9年间,由早稻田大学出版部出版。收集江户时代的“先哲遗著”,特别是以代表日本汉学之顶点的元禄(1688—1704)至享保(1716—1736)年间的先哲译注与近代学者的翻译。所谓“汉籍国字”解,是以日语译注中国古典,其意义在于保存日本文化的遗产与发扬近代日本学术研究的成果,不只是可以作为江户到明治大正期汉学史的参考资料,更是探究日本近代学术文化的重要依据。至于汉学日本化的所在与日本文化意识的显扬,或许是《汉籍国字解全书》的编辑目的。②町田三郎:《“漢文大系”について》《“漢籍国字解全書”について》,《明治の漢学者たち》,東京:研文出版,1998年,第185—230頁。町田三郎:《明治的汉学家》,连清吉译,第209—257頁。
井上哲次郎(1855—1944)的汉学三部著作《日本阳明学派之哲学》《日本古学派之哲学》《日本朱子学派之哲学》,是理解日本近代东西哲学的融合,如何以西方哲学的思想体系诠释与重构江户儒学之启蒙性著作。井上哲次郎在《重订日本阳明学派之哲学·序》指出:“近来我邦虽有继承欧美思想,倡导各种主义,于道德的实践则付诸阙如。于哲学的思索虽深远,却拘于坚白之辨,执着于虚理,鲜以东洋之灵动去除其枯燥。至于耽溺于东洋训诂之学者,于西洋哲学掩耳不闻,又不足论。融合东西哲学而转益求精,乃今日学问之急务”。町田先生强调井上哲次郎的汉学三部著作不但旁搜博引,严密著录,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记述体例亦异于历来语录摘要,以学案的形式,记载江户儒者的生平传记,主要论著,思想要旨,品评得失,论述传承发展的脉络,确立其于近世思想史上的地位。以哲学的思想体系论考日本近世儒学思想的流变,是明治30年代论述日本近世儒学最精善的著作。③町田三郎:《井上哲次郎と漢学三部作》,《明治の漢学者たち》,東京:研文出版,1998年,第243—244頁。町田三郎:《明治的汉学家》,连清吉译,第272—273頁。
五、京都中国学:日本近代中国学的文艺复兴
明治以来,以京都中国学的学者祖述清朝考证学而树立以古典文献考证为宗尚的日本近代中国学。岛田虔次(1917—2000)说:“京都中国学的学风是与中国人相同的思维和感受,来理解中国。”④吉川幸次郎:《留学まで》,《吉川幸次郎全集》巻22,東京:筑摩書房,1975年,第332頁。吉川幸次郎(1904—1980)以为树立此一学风的是狩野直喜(1868—1947)与内藤湖南。至于二人之所以抱持与中国人相同的思维与感受,作为学问研究的态度,是对江户汉学与东京墨守江户儒学的批判。狩野直喜以为江户汉学有褊狭与歪曲的流弊,江户儒学以宋明理学为主体是褊狭,不能洞察中国学问的全貌,以《唐诗选》《古文真宝》《文章轨范》为读本是歪曲,不能体得中国文化儒雅的本质。内藤湖南不但以江户汉学,尤其是宽政2年(1790)异学之禁以后的儒学极为歪曲褊狭,继承江户汉学的东京大学汉学科亦未能顺应“文明开化”的时代需求,了无崭新突破的展开。狩野直喜与内藤湖南之所以取向清朝的学问,乃二人皆曾接触西洋的学问,而以为清朝学问的实证性近似西洋的学问,亦即通过西洋的媒介,确认清朝考证的实证特质是中国传统学术中,最精进的学问。狩野直喜推崇顾炎武的学问,于乾嘉经学尤有专攻,讲述“中国哲学史”,于“清の学术と思想”,论述“汉学预备时代”之顾炎武、黄宗羲、浙东学派的学问,“乾嘉时代の汉学”和“道光以后の学术と思想”;又讲述“清朝の制度と文学”,①狩野直喜:《清朝の制度と文学》,東京:みすず書房,1984年。开启清朝研究的风气。论述“两汉学术考”“魏晋学术考”②狩野直喜:《両漢学術考》,東京:筑摩書房,1964年;《魏晋学術考》,東京:筑摩書房,1968年。与“清朝学术”,而树立“学术史”的新领域。内藤湖南讲述清朝史学而推崇章学诚的史学,开清朝史学讲述的风气之先,而“清朝史学通论纲目”③内藤湖南:《清朝史通論綱目》,《清朝史通論》,東京:平凡社,1993年,第259—294頁。则为研究清朝学术的纲领。因此,京都中国学可以说是代表明治新时代的“新汉学”,所谓“日本近代中国学”即是京都中国学。关于京都中国学的内涵,吉川幸次郎说:“王国维送狩野直喜欧游诗(1912)的‘自言读书知求是,但有心印而无雷同’,最能体现京都中国学的特质。”④吉川幸次郎于狩野直喜《支那学文藪》解说中说:王国维是狩野直喜平生第一知己,“读书求是,有心印而无雷同”是狩野直喜学问宗尚所在。《支那学文藪》,東京:みすず書房,1973年,第504頁。
(一)读书求是
吉川幸次郎绍述狩野直喜的学问,提到“师弟授受,以一字之教为始,一字之教为终”是狩野先生对文学一贯的态度,一生最极力主张的方法。先生文学鉴赏的方法是细密咀嚼的尊重,⑤吉川幸次郎:《狩野先生と中国文学》,《吉川幸次郎全集》巻17,東京:筑摩書房,1969年,第248頁。或为“自言读书知求是”的旨趣所在。至于“读书求是”的方法,则是武内义雄祖述王引之“为三代之舌人”⑥武内义雄《王引之》一文,引述龚自珍《工部尚书高邮王文简公墓表铭》,《武内義雄全集》巻10,東京:角川書店,1979年,第284—286頁。而树立的“中国学研究法”。武内义雄强调中国学研究方法的根底是文字学,唯其所谓的文字学既非语源研究,亦非文字形音的探究,而是归纳使用例,以正确解读古典的文字训诂学;又主张读中国先秦古书,必先考镜其传承源流,以回归汉代之旧,再上遡先秦的原初本貌;于先秦诸子的研究,必先旁捜各种版本,判别取舍而得精善版本,解析文本篇章脉络文义,对照先秦诸子,探寻他书的引述,然后判定精确的文本。其《老子的研究》即是以历代图书目录和日本的古抄本,考究异本源流,判别正确文本的著作。武内义雄以为《老子》有王弼注本、河上公本和唐玄宗御注本三个系统,校定各系统的祖本而取得最古且最正确的原本,才是精善致密的校勘。又校定正确的文本之外,还需要对原典进行批判性的修正。其所以校定《老子王弼注》,盖以《王弼注本》缺乏善本,乃参考王弼的注文,考察本文押韵的关系,探讨思想内容,修正《王弼注本》。⑦金谷治:《誼卿武内義雄先生の学問》,《金谷治中国思想論集》下巻,東京:平河出版社,1997年,第423—426頁。其以清朝训诂学,尤其是王引之“舌人意识”为底据,审慎地解释古典的文句,又兼容训诂学、校勘学、目录学,以辨章中国学术的发展,考镜典籍著录的源流。此古典文献考证的学问方法亦可谓之为京都中国学“读书求是”的指向。⑧武内义雄《支那学研究法》分《第一总论》《第二文字学》《第三目录学》论述“中国学研究法”,参见《武内義雄全集》巻9,東京:角川書店,1979年,吴鹏译《中国学研究法》,台北:学生书局,2016年。
(二)有心印而无雷同的“心得之学”
吉川幸次郎说:“狩野直喜率先引进清朝精细的实证学,并作为学问起点,既严守清儒‘不误不漏’的方法,审慎征引,正确标注典故出处,又尊崇‘心得之学’,于前人之言不能完全共感,绝无苟从。平生之所以最敬爱宋王应麟《困学纪闻》与清顾炎武《日知录》,以二书皆为‘心得之学’。”狩野直喜祖述顾炎武的“世风”说,重视文学形成的时代精神,重新选别时代主流的文学体裁,讲述汉魏辞赋、六朝骈文、宋元戏曲杂剧、明清小说。又比较世界主要文明,强调中国文明的价值在于感性的尊重,“儒雅”是中国文学的本质,“儒”是古典文学所内涵的理性和知性,“雅”是洗练(法文的raffine)而蕴藏着优雅郁郁的芬芳。经过理性与知性锻炼的致密诗文才是中国古典文学的上乘。沉潜于中国的古典文学的蕴涵,主张“儒雅”与“文雅”的融贯是中国文明异于其他文明的特质所在,或可说是狩野直喜的“心得”。①吉川幸次郎说:狩野直喜的学问具有“创始”“洞察”的意义,以“心得”体认中国文学“儒雅”特质。又重视“风神”(法文“raffine”)而嫌恶“粗略”(法文“sauvage”),故以为明代文学粗略,不是中国文学的本质。狩野直喜:《支那文学史》,東京:みすず書房,1970年,第461—472頁。
吉川幸次郎自述留学中国(1928—1931)的意义是理解中国人的价值观,受黄侃所说“中国之学,不在发现,在发明”的启迪而体得中国学的真义。中国学的真谛不在文献资料的搜集归纳,而在于文献内在意义的发掘。大正初期,日本京都中国学者以为权威的罗振玉、王国维的学问是倾向于资料至上主义的“发现”。所谓“发明”是钻研重要的典籍,发掘其中的要义,亦即发挥前人的学说,而以自身的见解论证究明,进而转益精进,或突破前人的论述而提出崭新的学说,或从事新领域的研究。②吉川幸次郎:《留学まで》《留学時代》,《吉川幸次郎全集》巻22,第331—425頁。
朱子说“五经疏中书易最劣”,然吉川幸次郎则强调《五经正义》中,以《尚书正义》最善。《尚书正义》所选定的《尚书孔氏传》虽是伪古文经,却是现存最古的《尚书》注本,也是汉代《尚书》注释的集大成。孔颖达奉勅撰述《尚书正义》的论证虽烦琐,却是六朝以来议论驳辩折冲抗诘而得持平稳定的传疏,允为科考准据的经典注释。或有不合经义的所在,却是探究中国中世人文精神史的史料。《尚书正义》所表述的论理是愚者恶人存在,且绝对无法救济的思维,而异乎中国传统人性本善的人性论。亦即《尚书正义》虽是《尚书》经传的义疏,却也反映六朝至唐初人为命运所支配,有极多限定的思维方式,吉川幸次郎称之为“决定的运命论”(天生命定)。天生命定的言说,首见于《论语·阳货》的“子曰,惟上智与下愚不移”,最上的智者与最下的愚者的性格是天生不变的。《尚书正义》则曰“中人”或有变化的可能。上智圣人不胡作非为,不必戒。下愚无可匡济,天生命定,戒之无益。又《多方》“圣必不可为狂,狂必不能为圣”是天生命定论,“谓之为圣,宁肯无念于善,已名为狂,岂能念善”,则强调上智圣人与下愚狂者的两极差异。至于经传所谓“无念于善”与“狂人能念于善”则有堕落或迁善之可能的论述,是曲解人间存在的实情。上智与下愚是天赋气质与习性而不可变易,乃《尚书正义》的哲学。故“决定的运命论”(天生命定),是中世思想的具现。③吉川幸次郎说明《尚书正义》的价值和体现中世思想的论述,见《〈尚書正義〉訳者の序》,《吉川幸次郎全集》巻8,1970年,第4—11頁。又,吉川幸次郎于《吉川幸次郎全集》巻10《自跋》中主张中世是“决定的命运论”思想的时代,参见《中国文学に現れた人生観》,《吉川幸次郎全集》巻1,1968年,第105—111頁,强调中国中世文学颇多记述人生的不安限定和人是微小存在的诗文,所呈现的是悲观倾向的人生观,盖能理解吉川幸次郎对中国中世思潮的立场。有关吉川幸次郎的中国中世思想论,参见连清吉:《〈尚书正义〉反映“天生命定”的思惟》,《杜甫千年之后的异国知己:吉川幸次郎》,台北:学生书局,2015年,第73—115页。
(三)京都中国学是日本近代中国学的文艺复兴
明治33年(1900),内藤湖南说:“东西学术荟萃的日本宜居于创造第三新文明的地位,然汉学耆老墨守德川末期的弊风,毫无进步。清朝学者则俨然如‘欧西近人之学士’习得合理性的学问方法。日本学界应将学问提升至清朝考证学的水平,确立研究方法,开拓东洋学术,甚至世界文明的新局面。”④内藤湖南:《讀書に關する邦人の弊習附漢學の門徑》,《内藤湖南全集》巻2,東京:筑摩書房,1971年,第166—170頁。町田三郎先生说:“在中国学研究的领域,实现以科学合理的精神为根底,将研究成果提升到世界学问水平是大正9年(1920)以内藤湖南、狩野直喜为中心而创刊的《支那学》杂志。《支那学》的创刊是明治中末期以来,胎动确立近代中国学之各种活动的结晶,尤其是内藤湖南与狩野直喜所谓的新学风,是以与中国当代考证学之学风同步的学问为目标,既非守旧的汉学,亦非盲目骛新之轻薄学问的主张,是具有说服力的。”①町田三郎:《明治漢学覺書》,《明治の漢学者たち》,東京:研文出版,1998年,第23頁。町田三郎:《明治的汉学家》,连清吉译,第25页。《支那学》杂志14卷(含《还历記念号》1巻、《东光支那学别卷》1巻),1920年9月—1948年10月于東京弘文堂发行,刊载日本(京都)与中国(罗振玉、王国维、张尔田、罗福成、钱宝琛、郭沫若等)关于中国学的论述,介绍中国当代学术消息,为近代中日学术交流是的贵重史料。内藤湖南与狩野直喜欲于明治新时代树立新学问是文化使命感,批判江户时代与继承江户学术之东京近代的学问有褊狭和歪曲的流弊,不能作为引领新时代的学问,是文化自觉。选别具有西洋实证合理性格的清朝考证学与世界汉学的取向,用以开创“新学先驱”的“日本近代中国学”,其首倡研究的中国戏曲杂剧古典小说是大正至昭和前期中国文学研究的显学,钻研敦煌学与世界汉学并驾齐驱,清代历史与文学的研究早于中国与欧美学界。又提出无雷同于中国既成定说的述作,则是以清朝考证学为媒介,与世界汉学接轨的意识而成就古代的再生。若以宫崎市定的文艺复兴论,定位京都中国学,或可谓之为日本近代中国学之文艺复兴。
结语:日本近代学术的开展与中国当代学术的取向
内藤湖南以气象学的观点,说:“地球同一纬度的气温移动是波浪的曲线,中日文化思想的传播与影响亦然,中国的学问经过一百五六十年后,在日本流传结实。”②内藤湖南:《履軒學の影響》,《先哲の學問》,東京:筑摩書房,1987年,第144—145頁。古代是汉唐学术文化的远绍,中世是隋唐佛学,近世是宋明理学,近代是清朝考证学的选别发展。对于中日学术文化的关系,内藤湖南既取譬于混沌状态的豆浆,加入“卤水”点化后,凝聚形成豆腐的过程,说日本文化的原型像豆浆,中国文化是日本文化的“卤水”,凝聚形成的日本文化是豆腐。③内藤湖南:《日本国民の文化的素質》,第101—103頁。又架构“螺旋循环史观”,说明日本受容中国学术文化后,与时俱进,像螺旋状的向上飞跃精进。④内藤湖南:《學變臆説》,《内藤湖南全集》巻1,東京:筑摩書房,1970年,第351—355頁。桑原武夫于内藤湖南《日本文化史研究》的解说中指出:内藤湖南的天体运行螺旋循环说,类似意大利哲学家詹巴蒂斯塔·维柯(Giambattiata Vico,1668—1744)的螺旋循环史观,唯内藤湖南的论述较为明晰。《日本文化史研究(下)》,第175—176页。关于内藤湖南的螺旋循环史观,参见陈凌弘:《内藤湖南近世文学地势二元中心论》,《东亚汉学研究》第7号,东亚汉学研究学会,2017年,第456—468页。近代以来,融合东西学问的精华,沉潜转化而成就如王国维所说的“有心印而无雷同”⑤王国维:《送日本狩野博士游欧洲》,《观堂集林》卷24,第3—4页,收于《王国维遗书》四,上海: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的日本近代中国学。宫崎市定以为内藤湖南“螺旋循环史观”,可推演为文化空间之横向往复循环,东亚文化中心之中国学术文化既正向传播到汉字文化圈的周边地区,周边地区受到中国文化影响刺激而产生文化自觉,创造独自的学术文化,周边地区新生的学术文化或以政治外交与经济贸易为媒介,反方向的流入中心所在的中国。⑥宫崎市定演绎内藤湖南的东洋史观说,认为东亚文化的中心在中国,中原文化首先流传到周边的地区,周边民族受到中国文化的刺激,也形成文化的自觉。中世以后随着周边民族的势力增强,文化扩张的运动也改变其方向,逐渐由周边向中心复归。此正向运动与相反运动,作用与反作用交替循环即是东亚文化形成的歴史。中国与周边地区的文化发展固然是横向发展的轨迹。参见宫崎市定:《独創的なシナ学者内藤湖南博士》,《宮崎市定全集》巻24,東京:岩波書店,1994年,第254—255頁。关于内藤湖南的学问,参见连清吉:《日本近代的文化史学家:内藤湖南》,台北:学生书局,2004年。
近代以来,对中国学的研究,有武内义雄在东北大学开展先秦诸子的研究,金谷治(1920—2006)、町田三郎先生继起,钻研先秦两汉诸子学。又有九州二程子之称的冈田武彦(1908—2004)、荒木见悟(1917—2017)两位先生对阳明学的再体验与儒佛会通的阐述,皆有独见精到之处。津田左右吉(1873—1961)旁通中国经学、先秦诸子学与日本文化史学,或可谓与内藤湖南分庭抗礼于日本东西的中国学界。①增淵龍夫:《歷史家の同時代史的考察について》,東京:岩波書店,1983年。东洋史学是代表明治时代的新学问,宫崎市定认为东洋史学是明治期日本人创立的学问,具有“日本的”,特别是“明治的”特色。②宮崎市定:《宮崎市定全集》巻2《自跋》,第339頁。那珂通世著述《支那通史》(1888),创立新史学,桑原騭藏《中等東洋史》(1898),羽田亨创刊《東洋史研究》(1935),而宫崎市定为“东洋史学巨峰”,参见《宮崎市定全集·刊行にあたって》,東京:岩波書店,1990年,全集刊行记事转载于礪波護:《東洋史学宮崎市定》,《京大東洋学の百年》,京都:京都大学学术出版会,2002年,第224頁。对于日本近世的学术,或从文化史学的视角、传统儒学史的远绍,探究日本儒学史的流变,或用西洋哲学史的方法,析理江户时代各学派的哲学,或以思想史的视野,架构日本思想史,或以“日本汉学问的两面性”“国文学”的观点,撰写日本汉文学史皆为近代学术的展开,树立新的学问领域。③内藤湖南《近世文学史论》以时地为文化形成的经纬,通辨江户儒学的变迁与地域风土所蕴育的学问特质。西村天囚主张日本儒学发轫于萨摩,著述《日本宋学史》。安井小太郎《日本儒学史》以学案的体裁,综述日本江户儒学各学派的流变。井上哲次郎与蟹江义丸编《日本倫理彙編》十卷,收录江户儒者著述,又以哲学史的观点,论述《日本朱子学派之哲学》《日本阳明学派之哲学》《日本古学派之哲学》。和辻哲郎以“人类于社会存在之理法”的“伦理学”论述《日本伦理思想史》。村冈典嗣则从思想史的视野,论述《日本思想史研究》。源了圆及其东北大学的门下弟子,研究“德川思想史”。冈田正之、久保天随、神田喜一郎等人从中国文学与日本汉学问的关系,著述《日本汉文学史》,日野龙夫则从“国文学”的观点,著述《近世文学史》,中村幸彦编辑《近世の漢詩》,著述《近世文芸思潮論》。至于西洋哲学虽非中国学的领域,明治以来百余年的翻译诠释与梳理钻研,尤以西田几多郎(1870—1945)融合东西哲学而成就“西田哲学”为中心之“京都学派”的论辩述作,则是日本近代学术的结晶。
如果内藤湖南以气象的流动,说明中国学问于一百五六十年后,漂洋渡海影响日本,以螺旋循环史观,论述中日学术相互影响,是中日学术文化交流史的事实,则民国以来,研究百年的中国学,或当代高呼的“新国学”与“新汉学”,是否能在21世纪成为东亚汉字儒学文化圈之中国学研究者的研究对象,甚至影响其思维方式与论理结构,则是当今中国研究者的历史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