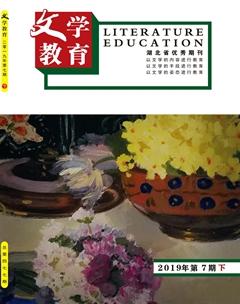游走中的精神镜像:《迟桂花》与《茵梦湖》之比较
内容摘要:郁达夫《迟桂花》与施笃姆《茵梦湖》呈现出极大的艺术相通性,其中最突出的一点便是作品主人公游走过程中的自我精神镜像。这种自我精神镜像具体表现在旅行者自我形象的特殊化叙写、景观文化想象中的个体投射与旅行者自我生命意识的升华与救赎等三个方面。
关键词:《迟桂花》 《茵梦湖》 旅行者 游走 精神镜像
《茵梦湖》是德国作家施笃姆创作的小说,作品诗意的叙述中浸润着主人公对失而不得的美好爱情的凄清追忆。《迟桂花》则是中国现代作家郁达夫创作的一篇具有田园牧歌情调的小说,作品将如诗如画的自然风光与人的生命之美巧妙地糅合在一起,具有独特的审美风格。比较这两部作品,不仅看出它们共同的浪漫主义色彩及后者所受前者的影响,而在两部作品的主人公身上,都鲜明地折射出游走过程中他们作为抒情主人公的自我精神镜像,显示出一些共同的艺术质素。
一.自我形象的特殊化叙写
旅行犹如一面镜子,旅行者在游走过程中不断探索生命与超越自我,找寻自我精神家园。《茵梦湖》与《迟桂花》的一个共同点,便在于展示旅行者身与心的双重旅行。在《茵梦湖》中,身在异乡的孤独老人莱因哈德所回忆的往事便是不断穿梭于故乡与异地的旅行,《迟桂花》则描绘主人公老郁在杭州翁家山拜访故友时一场自我肉体与灵魂的双重旅行,而两场旅行中的旅行者都展现出强烈的主体意识与诗性气息,化身为别具一格的主人公形象。
在《茵梦湖》中,莱因哈德作为回忆主体,在记忆中的故乡与异地穿梭游走,在当下与过去游历,显现出浓厚的情绪化与心灵化特征,找寻着以往甜蜜又凄清的生活与爱情。在这个过程中,他的自我形象渐渐清晰明确,既呈现出浪漫多情的诗人气质,又表露出时代边缘人的形象。他的诗人气质,表现在他的文学爱好与理想追求上。莱因哈德不仅在童年时期为美丽的伊丽莎白作诗,更在长大后广泛收集民歌民谣。他的人生目标便是成为诗人或艺术家,诗歌、民谣等艺术载体作为莱因哈德内心情感的外化而存在。而作为时代边缘人形象,他在追寻伊丽莎白无果时选择离开并回归原有的社会秩序,无疑是与时代格格不入的。
《迟桂花》以第一人称“我”的人物视角进行叙述,完美地诠释了人物的主观感情与心理动态。有学者曾指出:“以个人旅行的方式来表现自我,是‘五四时期文学中重要的现象。”[1]旅行在“五四”新文学中的人物形象刻画中起着非常突出的作用,往往成为人物思想、情感与性格发展演变的路径与轨迹。作为郁达夫后期创作的名作,《迟桂花》采用第一人称叙述者的旅程自述,是人物内心情感的凸显和心灵的外化,是作家在表现人物形象与内心情感的特殊化叙写与表达。小说的情节与内容明朗清晰,但却在这狭小的时空里构成了“我”与翁莲同游时自我思想斗争的高潮,形成了强烈的叙事张力。杭州翁家山清雅幽美的风光与翁家兄妹纯朴灵动的人性,反衬出“我”与翁莲同游时所萌发邪念的丑恶,显示了“我”的心理动态变化过程。此时的“我”不仅是在历经了自己的翁家山之旅,同时也是一场属于心灵的净化之旅。
二.景观文化想象中的个体投射
旅行是一个感知空间的过程,在空间环境的不断转换中,呈现出不同的景观,这些景观投射到旅行者的心理、情感中,不仅使旅行者形成独特的心理、情感体验,而且凝聚或承载着独特的文化意义。这种景观文化想象中的个体投射在《迟桂花》与《茵梦湖》中有着突出的表现。
《茵梦湖》通过对旅行者游走过程中美好景观——“睡莲”的描写,折射出主人公内在的精神世界与人格特征。一方面,“睡莲”颇为美丽动人,它与宁静湛蓝的湖水、洁白无瑕的月光,构成了一幅栩栩如生的田园画,共同象征着莱因哈德与伊丽莎白过往岁月中美好的成长经历与甜蜜的情感生活。另一方面,“睡莲”还暗示着两人转瞬即逝、触不可及的爱情。虽然“他和睡莲之间的距离老是没变似的”,莱因哈德却始终不能接近,这景物只能是水中月、镜中花,犹如莱因哈德徒劳无功的青春爱恋。在一定的层面上,文本也通过景物指向德国的社会制度。这“睡莲”始终孤独地躺卧在黑黝黝的水面上,似乎隐喻着已嫁作商人妇的伊丽莎白并不幸福——她是时代的落难者,是德国封建制度残余下的牺牲品。莱因哈德在重游故乡中,既是景观文化的见证者,又是情感世界的生成者,这为小说增添了含蓄而优美的诗意,也使得旅行者对自身文化进行反思。
在《迟桂花》中,作者借自然之景“迟桂花”来反衬具有丰富内涵的人性之美。众所周知,郁达夫前期的小说对性心理无节制的暴露多为人诟病,在后期创作中一改以往风格,《迟桂花》便是他的一次成功尝试。在文本中,郁达夫多次借旅行者老郁之口提到“迟桂花”,“迟桂花”从“一种说不出的撩人的桂花香气”的自然景观,到促使老郁潜意识中“起性欲冲动”的爱昧意象,进而转变成“但愿得我们都是迟桂花”这种超越肉体欲望的精神符号,透露出“迟桂花”这一景观文化想象不断向内作用于旅行者老郁,促使其感悟生命之美、探索灵魂之真。同时,“迟桂花”正象征那“同高山上深雪似的心”的翁莲,老郁借助“迟桂花”这一景观文化与“翁莲”这一他者形象,在文化对照与反思中,完成了自我灵魂的净化与超越。
三.自我生命意识的升华与救赎
旅行是一个游走的过程,旅行者的价值观念及精神世界随着叙述时空的位移而变化,并通过“皈依”或“救赎”的方式来达到自我生命意识的升华与灵魂的超越。这一点,《迟桂花》与《茵梦湖》也作出了较为精彩的描述与解释。无论是莱因哈德还是老郁,都在经历对他者文化的认同后,形成自我文化反思,完成了自我精神蜕变的过程。
在《茵梦湖》中,莱因哈德的游走之旅既是对自己出生的田园、传统文化的皈依,也是对精神家园的追慕。主人公被置于自然环境与文化环境的双向互动与对话之中,以类似基督式的精神救赎,照应自我生命意识的生发与转化。作为小说的旅行者,起初他在当下生存空间里重现伊丽莎白的美丽恬静,童年趣事的纯真美好,以及长大后两人感情的黯然失色。随着时空的变幻,他沉迷往事之中久久不能释怀。他一生也许都在做着一个相同的梦,梦中只有伊丽莎白转瞬即逝的身影和茵梦湖上那朵洁白孤寂的睡莲。因而对莱因哈德来说,他在游走的异域生活中衍生出自身精神的困顿与迷茫,身处文化边缘而导致精神上的痛苦与孤寂。经历了无从适应的内心挣扎后,莱因哈德“他头也不回地快步往前走去”。最终,莱因哈德选择永远离开伊丽莎白,对应传统文化的回归。正是这种在游走中生发的独特生命意识拯救了他,这种类似基督式的救赎使得文本具有一种克制而净化的诗意美,也使作品具有较高的审美价值。
对《迟桂花》中老郁来说,旅行也是一次身心的救赎之旅。郁达夫曾把他作品中的身体叙事归结为“性的要求和灵肉的冲突”。[2]与《沉沦》等作品一样,《迟桂花》也表现了人的欲望与精神的冲突。然而,作品中作为异地文化的旅行者老郁,在灵与肉的矛盾斗争中,灵以强大的人性之美战胜了肉的本我欲望,而其力量源泉自然是翁莲。翁莲是作者心中美的化身,小说中反复写到翁莲生活在荒僻偏远的翁家山中,却天生一副姣好和善的容颜和丰润成熟的身体,这与五云山清幽淡雅的自然环境一起,构成了一幅明媚和谐的画卷。老郁在与她同游时竟“看得要簇生异想”,生发出一种强烈的本我生命意识,这是一种与自然美不相和谐的本我因素。但经历过父死、家衰及夫亡的翁莲却始终不为所动,仅仅以一种纯洁、率真的天性不动声色地感化同行者,还“满以为我是在为她设想”。她如同那绽放稍晚的迟桂花,愈久弥香,傲然独立。在这种他者身份的对照下,老郁不禁为自己的邪念感到羞耻,其结果是将充满欲望男女之爱升华为纯洁真挚的兄妹之爱。此时,旅行者在他人感化中促使本我欲望向超我形象的转变,到达精神世界的彼岸,实现了自我救赎与他人救赎的双重意义。
总之,《迟桂花》与《茵梦湖》都提供了旅行者在游走过程中的自身镜像反射这一关系模式。两者虽略有不同,但都体现了旅行者寻觅精神家园、渴求寻得内心净土的终极价值。在这充满磨难与痛苦的灵魂净化与自我超越游走中,旅行者无疑被赋予了特殊的含义——一个对心之所向精神家园的追求者。由此,这丰富深厚的文化意蕴与优美纯净的自然风光一起,构成了两篇作品的诗意化审美特征,让读者感受到了文本独特的艺术魅力。
参考文献
[1]李欧梵:《现代性追求》,北京: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74页。
[2]郁达夫《〈沉沦〉自序》,《郁达夫文集》第7卷,广州:花城出版社1982年版,第149页。
(作者介绍:李素洁,中南民族大學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2016级本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