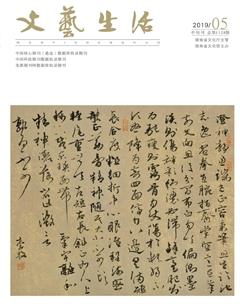浅析李嵩的《花篮图》
卢蕾

摘要:花鸟画是宋代绘画的一个重要题材,而李嵩的《花篮图》则是其中少见的院体盘花样式,与插花艺术的联系十分密切。本文试图从插花艺术的角度来分析李嵩《花篮图》春花册的题材、形式和花卉寓意,探讨研《花篮图》所体现的丈人情趣,再将《花篮图》与同时期花篮题材的绘画作品进行比较,来进一步分析《花篮图》的风格样式。
关键词:李嵩;花篮图;文人精神
中图分类号:J2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9)14-0145-01
花卉与人的生活联系十分密切,它不仅仅是作为一种物质文化,有着可入食入药的实用价值,并且它还是一种精神文化。历代以来,无数的文人骚客寄情于花卉草木,抒发自己的抱负理想,以花卉为题材的诗词歌赋层出不穷,楚国文人屈原在《楚辞》中便多次通过讴歌花木香草的方式来抒发自己的浪漫情怀。而且中国人对于花卉草木往往有着一种别具一格的泛人化的感悟方式,人们通常把自身的价值取向加在花木身上,以花木来喻事比人,例如我们所熟知的岁寒三友(松、竹、梅)和花中四君子(梅、兰、竹、菊)等。
周敦颐的《爱莲说》中写到:“予谓菊,花之隐逸者也;牡丹,花之富贵者也;莲,花之君子者也”。可以发现这些花卉的自然习性被赋予了人文精神。陶渊明隐于农田,便以菊自立,表达自己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高尚品质,而杨柳依依往往被人们认为是送别时的不舍情意,“柳”立似“留”,所以离别之前贈柳便有了挽留的寓意。更有清代曹雪芹在《红楼梦》中将各类人物形象与花木进行作比,用花木所代表的特殊寓意在整部作品中穿针引线,吸引人们反复咀嚼文句来得其深意。在花卉入丹青后,其所拥有的托物言志意义仍在发挥作用,郑思肖在《墨兰图》中以“露根兰”来体现自己的“无根”,表达自己的亡国之痛。总之,花卉在不断地被人们注入思想和情感,并融入生活和文化的方方面面。
南宋时期,统治阶级安于东南一隅,追求享乐生活,并且在宋代“重文”的影响下,士大夫阶层快速崛起,导致当时的思想文化氛围较浓厚。而文人逸士往往有着闲情雅致,生活悠闲,在当时理学的影响下,人们更注重花的寓意,注重人伦教化,于是花卉变为了风流蕴藉的清物。宋代大兴造园栽花之风,盛行插花,并在皇家有专门的赏花活动。民间赏花活动也十分热闹,有花卉市场、“花户”和“花行”这样的行业组织。赏花变成了不同阶层和不同地域社会生活里的一个普遍活动。在这样国富民安的经济现状、雅事盛行的文化特质还有精微雅致的生活方式之下,李嵩的《花篮图》孕育而生。
现存于世的《花篮图》有三,分别描绘了春、夏和冬的应时花卉。三幅绘图都是居中呈三角形构图,以竹编篮为盛器,画面饱满,每一幅花篮图都有五种花卉,有闻香和赏色的不同分工。三图皆有项子京鉴藏印,并且花篮的提梁朝向均是和款识方向一致。而本文旨在剖析《花篮图》春花册一幅。
我们可以先从插花艺术的角度来分析《花篮图》春花册。首先是容器的选择上,画面以竹编篮筐为盛器,竹本身就被赋予了文人气质,苏东坡曾言:“无肉令人瘦,无竹令人俗”,说明竹子在当时的文人雅客心中是高雅的象征。在精神文化层面,竹节被认为是有着节节向上的积极意义,“竹子精神”也是诗歌和文人画中常见的题材,它象征着自强不息、顶天立地的精神,清雅脱俗,不作媚世之态。而且竹子清凉自然,所以用竹为盛器,它和花卉的和谐搭配会形成一种有机组合,更能体现生活意趣,刚好与花卉的自然倾向相统一。其次是花卉的摆放,插花时花卉如何摆放的问题要视容器的规格而定,因竹篮并不像瓶、筒等容器高度较高,所以插花时应照顾四面八方,这点与《花篮图》中花卉的摆放朝向均是四周放射状一致。最后是花卉的搭配,我们可以看到画面的主花体量较大,如果用体量小的花作为主花的话,整个画面撑不起来,并且画面中还需要有散状花材进行点缀,起着烘托、陪衬和填充的作用,增加了插花的层次感,比如《花篮图》春花册中的散状花材是含苞的垂丝海棠。
再看画面,《花篮图》春花册图页高21cm,宽26cm,一朵重瓣黄刺玫居于画面的纵轴中心位置,左下角有黄色连翘与其相呼应,白碧桃萦绕在黄刺玫周围,互相衬托,并且与压在画面下方的林檎颜色相呼应,紫色的垂丝海棠穿插在各花之间,平衡画面。我们可以发现画面上的花卉颜色十分协调,整个画面主次分明,点缀得当,花卉颜色搭配丰富而不跳脱,并且在摆放时特别注重颜色呼应,笔者在研究画面时,发现在花卉颜色呼应方面似有“x型”的规律。《花篮图》春花册中叶子和花所占的比重相差不大,叶子十分灵动飘逸,作曲折逶迤状,外延向上的枝叶展示了春天万物复苏生长的蓬勃生命力。总的来说,《花篮图》春花册的花卉摆放看起来十分的“满”和“活泼”,花的颜色更加俏嫩,花篮的颜色也较浅淡,突出了花的活力。
黄刺玫,蔷薇科植物,花期为5月至6月之间,所以大概能推测该画是在春末所画,画面中黄刺玫的盛开、半开和含苞欲放等形态均有,并且黄色给人以高贵豪华之感,更何况《花篮图》本身就具有当时隆盛院体花特色。而画面中的白碧桃应该有着吉祥纳福的寓意,人们常说的“桃花运”和唐朝崔护的“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等,都是用桃花来写对爱情的期待,而且春天也是爱情萌芽的季节。连翘耐寒耐干,不择土壤,甚至在石缝中和风化的岩石母质上都能生长,生命力和适应性都极强,这种强健的生命力不就是体现了春天的生机盎然吗?王仁裕在《开元天宝遗事》中记述了唐玄宗曾将杨贵妃比作会说话的垂丝海棠,后来垂丝海棠常用来比喻美人,在春天丛花盛开的时节,与美人坠入爱河,岂不美哉?在笔者认为,《花篮图》春花册不仅通过对五种春季花卉的描绘体现了春天的盎然生机,更是在一年初始之计,表达了对以后生活的美好祝福。
宋代除了李嵩的《花篮图》外,也有其他的描绘花篮的画作,比如藏于上海博物馆的佚名《花篮图》、还有现存于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的传为北宋赵昌所画的《花篮图》等。我们可以发现这些花篮图的构图都是一致的,呈居中三角形构图,也都是用的勾线晕染的工笔手法。但是在插花艺术方面,明显是李嵩的《花篮图》插花搭配技术很高超一些,佚名《花篮图》虽有些破损,但我们还是不难看出花卉的颜色搭配较简单,传为北宋赵昌的《花篮图》所选取的花卉也只有两种,并且以提梁为分界线,一边为牡丹,一边为雏菊,没有李嵩的《花篮图》画面感这么丰富。
笔者在研究的过程中发现,牡丹的花期为四到五月,有“国色天香”之称,象征着富贵吉祥。在宋代牡丹被称为“天下之冠”,欧阳修的《洛阳牡丹记》也称“洛阳家家有花”,那既然世人如此喜爱牡丹,李嵩的《花篮图》春花册之上为何不画?这个问题还值得再多做研究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