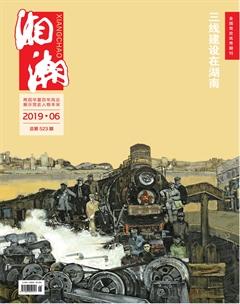朱德:“抚育部曲亲如子,接遇工农蔼如风”
史全伟
被毛泽东誉为“意志坚如钢,度量大如海”的朱德,他不仅为中国革命做出了杰出贡献,同时也给世人留下了宽厚质朴的形象。朱德习惯称自己是“广大群众的代表”。他认为,既然代表群众,就首先要成为群众的一员。和群众心连心。不管是在艰难困苦的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建设时期,朱德始终不忘初心,从不摆架子搞特殊,和蔼可亲,平等待人。“抚育部曲亲如子,接遇工农蔼如风。席间笑谈胸襟阔,最从平淡见英雄。”杨朔的这首诗,真实形象地刻画出了朱德的博大胸怀和宽厚长者的风范。
是总司令。又是普通一兵
战争年代,身为总司令的朱德为人和蔼,生活简朴,穿着和普通士兵别无二致。为此,不认识他的人往往弄不清他的真实身份,有时还闹出笑话。
1928年11月,朱德和毛泽东率领红军打下新城以后,部队在新城附近进行短暂休整。由于数个月行军作战,红军指战员的衣服脏了,袜子破了,头发长了0休整期间,朱德除了布置军事训练和政治学习之外,还留出时间让指战员们处理个人事务。
一天,数名战士来到新城南门的一家理发店理发。理发店的黄师傅很热情,他一边给红军战士理发,一边跟大家聊天。说话间,朱德也来理发了。他见理发的人多,就悄悄地排在几名战士后面等候。朱德衣着和普通战士一样,所以也没有人注意到他。
一会儿后,有个战士理完发了,翻好衣服领子走出来,猛地看见朱德排在后面,吃惊地叫起来:“朱军长,你也来理发?”战士们一听,立刻站起来,争先恐后地说:“军长,你先理。”黄师傅回头一看,才知道此人就是朱德军长,连忙拿着白围布走过来,说:“朱军长,我先給你理。”
朱德笑着摇了摇头,说:“不,不,你先给他们理,千什么事都有先来后到嘛。我还是排在后面吧。”
康克清回忆当年她第一次见到朱德时的情形:“只见一位中等个头,体格健壮,忠厚长者模样的人,正向我们走来。走近了,才看清楚他身穿灰里透白的军服,脚穿草鞋,一身风尘,面带微笑,威武中透露着慈祥。朱军长给我的第一个印象,是他很平易,平易得像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一个普通的红军战士和威名远扬的军长之间的距离,瞬间就缩短了。当时我并不理解,这正是他的特点,他的气质,他的伟大所在。”
抗日战争爆发后,朱德率军东渡黄河,开赴抗日前线。当时,八路军总司令部在西安东南的云阳镇,司令部里的人听说朱德总司令要来上任了,就派几名年轻干部去迎接。这几名干部一大早赶了三四十里路,来到一条河的桥边上等候,这是部队必经之路。来接的人虽久闻朱德总司令的大名,却没有见过面。他们都在猜想总司令一定骑着高头大马,威风凛凛,一派与众不同的将帅风度。
不一会儿,一支部队出现在桥上,都是一样的打扮——穿灰军装、腰扎皮带、脚蹬草鞋,没有谁特别一点,更没有骑大马的。迎接的人以为这是打前站的部队,连问都没有问—下,蛮有把握地等候后面的部队过来。
可是他们等了半天,也没看见后面有部队过来。这是怎么回事?他们开始惶惶不安,是不是总司令没有走这条道。还是日期变动了?于是就派了两个人先回司令部汇报,其他人继续在桥头等着。这两个人赶回司令部,一进大门就高声报告:“我们到现在也没有看见总司令,是不是总司令改变路线了,还是……”
“嘿嘿……哈哈……”
他们的话还没有说完,就听到满堂大笑。
“我看见你们站在桥头,还以为你们赶路赶累了在休息呢。哪儿知道你们是迎接我的?让你们多走路了。”朱德笑着说。
这位朴实的老兵就是八路军的总司令!他们愣愣地望着一口浓重四川口音的朱德,脸“腾”地一下红了。不用说,总司令就是在自己眼皮底下走过去的。
1940年的一天,时任八路军总司令的朱德带着身边的几名警卫战士,跟着向导来到荒凉的南泥湾,打算勘察—下当地的自然地理环境。南泥湾的中心地带前不着村、后不着店,附近十几二十里没有人烟,看看天将擦黑,朱德决定就在附近宿营。
这个地方真是要啥没啥,大家费了好大劲才找到两孔破窑洞。这窑洞没门也没窗,与野外山洞没什么两样。战士们正商量另寻地方,身后传来朱德洪亮的声音:“这里还可以嘛,不要再找了。”大家一齐走进洞内,朱德看了一遍后,乐呵呵地说:“不错,比战壕里强多了!”几个警卫战士跟着朱德七手八脚找来了树叶和茅草,很快在窑洞里搭好了简易地铺。大家千完活后,围坐在一起吃起干粮来。
那时候不管是在哪里,都有很大的危险性,所以在吃干粮的时候,几名警卫战士商量了站岗的时间,还让其中一名同样姓朱的警卫战士和朱德总司令住在一个窑洞,大家都叫他小朱。睡觉时,考虑到朱总司令年纪大,又奔波了一天,大家就让他睡在窑洞里边的铺上,小朱睡在洞口的铺上,这样下半夜招呼小朱换岗也方便些。安顿好后,大家就睡下了。
经过几个人的轮换,下半夜换岗的时间到了。警卫员小李轻手轻脚来到朱德睡觉的那个窑洞口,轻轻推了推靠近洞口睡的“小主”说:“该换岗了。”听到“小朱”应了一声,便回自己铺位睡觉去了。
第二天清早,向导起床看见朱德站在窑洞前,以为他在想事情,没敢过去打招呼,就回去叫醒了其他人,说总司令千吗呢?大家便起床跑到朱德面前诧异地问:“首长怎么不睡觉啊?”朱德微笑着反问:“你们站岗放哨睡不睡觉啊?”战士们一听先是一愣,再往窑洞里一瞧,发现警卫员小朱还在里面睡得正香呢。这下,大家全明白了,昨晚站了半夜岗的人竟然是总司令!原来,昨晚睡觉前,朱德跟小朱调换了—下铺位,这个情况小李不知道。小李叫小朱换岗实际上是叫的朱德。朱德没有埋怨任何人,也没做解释,而是以普通一兵的身份站了半夜岗。
言传身教诠释军民鱼水情深
朱德在《八路军抗战二周年》一文中总结了八路军抗战两年来的经验。他明确指出,凡是党政军民团结一致的地方。凡是民众运动有成绩的地方,我们就能取得胜利。晋察冀边区、晋冀豫边区和晋绥边区之所以成为华北抗战的坚强堡垒,靠的就是这些。
1939年春天,八路军一一五师六八七团驻扎在山西省潞安府以西20里的西大营休整。这天。朱德来部队作军事报告。傍晚,他外出散步,看见一个战士在和老百姓争吵,便走过去问道:
“同志,怎么和老乡吵起来了?”
“借个东西用用,他就是不借。”那个战士气呼呼地答道。
“同志,好好地讲,不能和老乡吵架呀!”
战士没见过朱德,上下打量了一番,看他衣着和普通战士没什么两样,以为不过是个老八路,就没理睬,继续和老乡赌气。
这时,朱德耐心而严肃地说:“向老百姓发脾气是不对的,我们是革命军人,和老百姓是鱼和水的关系……”
“你是谁呀?”本来就在气头上的战士有点不耐烦。
“我是朱德。”
说话间,一位团长跑过来,向朱德行了个军礼:“总司令怎么一个人出来散步呀?”
这时,战士才恍然大悟:“啊!您是总司令!”
第二天,吃完早饭,朱德问团长:“昨天那个和老乡吵架的战士害怕了吧?”
“是啊,他昨晚上说了一夜梦话,什么‘我错了呀,什么‘我要受处分呀……今天连早饭都没心思吃了。”
“怎么不早告诉我?赶快把他找来,我和他谈谈,就什么事也没有了。”朱德没等团长把话说完,便催促道。
战士怀着恐慌不安的心情来了,在朱德屋门外犹豫了好久,才硬着头皮进去。他以为朱德会发脾气,给他处分。但进屋后,朱德亲自给他倒了一杯水,请他坐在自己身边。战士惭愧地说:“总司令,我错了,今后一定改,处分我吧!”朱德笑了,和蔼地说:“知错就改,这就是好同志,今后可不能对老乡耍态度。记住,我们的一切都是人民给的,有事情要和群众商量着办,不能强求……”
朱德和风细雨讲的这些道理,让这位战士深受教育,明白了和老百姓鱼水情深的道理,同时也没有了心理负担。
当时,八路军总部驻在太行山西麓的武乡县王家峪。由于粮食不足,部队只好采食驻地的榆树皮和榆树叶。朱德发现把老乡的榆树采得太厉害,便对司务长说:“老乡们的生活也很苦,我们采光榆树,老乡们吃什么?”司务长听后,就带着战士们去寻找野菜,把榆树叶留给乡亲们。
1939年麦收时节,一队八路军从一个村边行进,骑着马走在前面的是位营长。
这时,一位大娘背着一大捆麦子,艰难地从对面走来,与营长擦身而过,那营长仍然骑在马上,没事似的往前走。
朱德正好路过,将这一幕全看在眼里,粗重的眉毛拧到一起,快步上前拦在了马头前,略带怒气地问那个营长:“你担任什么职务?”
營长不认识面前的拦路人,上下打量他,见他灰军装已洗得发了白,戴的单帽是用棉帽改的,以为是个老战士,就毫不在意地说:“我是营长。”
朱德又问:“你现在的任务要紧吗?”
营长望着这位表情庄重的老同志,仿佛感觉到了什么,连忙跳下马,说:“不十分紧。”
朱德听后,用手指着老大娘说:“那么,你让队伍前头走,拉着你骑的马到村里套个车,帮大娘把地里的麦子都拉回家去。”
营长遵从了“老同志”的话,帮老大娘把麦子拉回了家。
事后,这位营长才知道“老同志”就是朱德总司令,不由得十分紧张。
几天后,朱德亲切地找他谈话:“你见老大娘背着麦捆是那么吃力,自己却骑着马不下来,是不对的。我们当干部的,只要有点空儿,有一分力量,就要尽量帮助群众。要特别注意自己的作风,事事要为群众树立一个好的榜样,决不能损害八路军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
营长听后连连点头,并响亮地保证说:“总司令,我今后一定要设法帮助群众,做一个受人民热爱的子弟兵。”
1939年的一天,总政治部的天星剧团来武乡县砖壁村演出。傍晚,剧团在村里临时搭起了简易舞台,前面一字排开摆放了许多矮凳、圆木、砖石,等待着朱德和其他首长前来观看演出。
天黑下来后,大家陆续入场,朱德也兴高采烈地走了过来。他环顾会场,发现坐在场内看戏的全是部队的干部、战士,没有一个老百姓。
朱德不解地向值班岗哨询问,战士回答说:“我们是刚从前线回来的三八六旅的战士,对村上的人不太熟悉,为了首长和大家的安全,就只让部队人员入场了。”
朱德听后,马上去找民运科长,耐心地对他说:“毛主席常常教导我们,每到一地都要爱护群众、关心群众,和群众打成一片。咱们的总部设在这里,平时给老百姓添了很多麻烦,现在剧团来演出,却不让老百姓来看,你说合适吗?”
民运科长一听,觉得这样做确实不利于军民团结,便遵照朱德的要求,立即把村里的人请过来一同看戏。这时,朱德又亲自领着十几位上了年纪的大爷、大娘,把他们安排在前几排的位置上,笑着说:“你们年岁大了,离台子近才能看好听好。”他刚刚安排好老人,转身又去招呼抗日小学的老师,让其把儿童团的队伍也带到前边来。
一切都安排好了,大家聚精会神地看着节目。而朱德自己却悄悄走到后面,找了个位置和战士们坐在了一起。
吃穿住行自奉清俭
朱德主张艰苦朴素,不只是教育别人,首先是自己身体力行。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直到他去世,朱德在吃、穿、住、行各方面,处处自奉清俭。对此,不仅他身边的人称道,凡是接触过他的人都交口称赞。
先说吃的方面。给朱德做过厨师的邓林说:“一般人以为朱老总是中央领导,吃饭是特灶,标准一定很高。可实际上,从解放进北京到1971年我生病离开中南海,老总、康大姐和我3个人加起来的伙食费平均每月都不过四五十元,就是按当时的标准,也只是一般中层干部的水平。”平时,康克清在机关食堂吃饭,在家里吃特灶的只有朱德自己,每顿都是一小碗米饭、三小盘菜、一个汤。三小盘菜中,一盘是带点鱼和肉的荤菜,其余两盘都是普通的素菜,汤则是一碗普通的青菜汤或鸡蛋汤。晚饭更简单一些。几乎天天如此,从来没有超过这个标准。有时来了客人,朱德留吃饭也只是嘱咐添一两个简单的菜,不够就上一点泡菜、咸菜等小菜,从不铺张浪费。
邓师傅最初给朱德做饭时,总想多做一些,好让他多吃点,心想吃不完倒掉就算了。可是没过几天,她就发现这样做不行。朱德每次吃饭总是尽力把饭菜都吃掉,连一点菜汤一颗饭粒都不愿剩下。有时剩下了饭菜,到下顿吃饭的时候朱德总要问剩菜哪里去了,如若听说倒掉了,马上就严肃地批评说:“这是浪费人民的血汗。”并且一再嘱咐,剩菜剩饭一点不能倒,一定要留给他下顿吃。邓师傅曾想把朱德的伙食搞得好一点,荤菜里放的肉多一点。一次,朱德饭后到厨房对邓师傅笑呵呵地说:“同志,你是不是资本家出身啊?”邓师傅赶紧说:“首长莫开玩笑,我哪里是什么资本家啊?”“不是资本家怎么那样阔气呀?不要天天都成席嘛!要吃家常便饭。我们这些人过去都是农民,是吃杂粮、小菜长大的,身体也很健康。我不让你每天做大鱼大肉,不是怕花钱,主要是要养成俭朴的习惯。”
20世纪50年代中期,有一天,机关供应站来了一批对虾,邓师傅知道朱德爱吃鲜鱼虾,就买了几个,精心烹好后端到饭桌上。朱德一见,就问是从哪里来的、多少钱一斤。邓师傅如实回答了。朱德听后,说:“老邓啊,对虾是好吃,可你知道吗,一吨对虾到国外就能换回好多钢材哟!我们国家穷,缺钢材,对虾少吃一口有啥关系,进口钢材更要紧。以后记住,再有对虾你就不要给我买了,买了我也不吃。”邓师傅说:“您是国家领导人,就是顿顿吃对虾又能吃多少?”朱德说:“国家领导人就更要想着国家,能节约一点就节约一点,反正以后不要吃就是了。”在以后的几年里,朱德在家里再没有吃过对虾。
三年经济困难时期,朱德也紧缩了自己的饮食标准。他减少了粮食定量,也很少吃肉,有一段时间干脆不吃肉,常吃一种把米和菜煮在一起的“菜糊糊”。他家里由于来往的客人多,有段时间粮食亏空了50多斤,工作人员想报请机关行政部门把短缺的粮食补上,朱德坚决不同意。一天,他亲自指导厨师做了一顿“菜糊糊”,请身边的工作人员吃。他对大家说:“今天请你们吃这顿饭,是让大家不要忘记过去战争年代那种艰苦奋斗的精神。现在国家经济困难,人民生活艰苦,我们要想到全国人民,和人民一起渡难关,能节约一点是一点。”这样,他坚持和家里人_起吃“菜糊糊”,硬是用“瓜菜代”的办法,把短缺的粮食补了回来。
再说穿的方面。朱德的衣着非常朴素,有的衣服穿了多年,领口、袖口、肘部和膝盖处都打了补丁'还继续穿。有两身较好的衣服,他也只有接见外宾、参加大的国事活动或外出时才穿,一回到家里,就又换上旧衣服。如果想给朱德做件新衣服,不知要费多少口舌。有一年冬天过后,天气逐渐转暖,到了要脱棉衣换呢制服的时候了。康克清帮助朱德找了半天,竟然没有找到一件合体的呢制服,那些已经有年头的毛料衣服不是破旧得厉害,就是太小不能穿了。于是,大家就说服朱德做一件新衣服,但他死活不答应,硬是让康克清将两件小的改为一件大的。可是衣料的年头太久,已经无法再缝制了。后来大家一起劝说,朱德才勉强同意,但是不让做面料太贵的服装。就这样,已经80多岁的朱德才添置了一件新衣,此后直到去世,他再没有做过新衣服。
住的方面,朱德也处处体现着一贯节俭的作风。朱德卧室的陈设很简单:一张旧棕绷床,一个旧床头柜,一个旧衣柜,一张木桌,一张旧式沙发,墙上挂着毛泽东像和毛泽东诗词、语录。他的床单、被褥,都是用了二三十年,打了补丁的。他坐的那张沙发很旧,也很矮。晚年的时候,因为行动迟缓,他常常是坐下去,再站起来就很吃力。工作人员早就提出要换个新的,但他坚持不让换。为了起坐方便,朱德就自己想出个主意,他让工作人员用4根木头把沙发腿接高了一截,照样使用,还风趣地称这个沙发是“土洋结合”。就是这张接了腿的高沙发伴着朱德度过了晚年。朱德住处的卫生间窄小,洗澡盆又高又笨,每次进出都很不方便。特别是他年纪大了,手脚本来就不灵便,还有病,澡盆又高又滑,太容易发生意外了。考虑到他的安全,组织上几次要把澡盆改装一下:放得低一些,上面再加个喷头好让他坐着淋浴。其实这只是花几个工时,用不了多少钱的事,朱德却始终不同意。他总是说:“国家用钱的地方多得很,我这里已经很好了嘛,再修,又要浪費钱财。”直到1976年6月底,朱德因病住院了,工作人员才趁机悄悄地把澡盆改装了。深知他脾气的工作人员,为了这件事,还做了等他出院后挨批评的准备。结果,这番心思白费了,朱德还没有使用过一次就与世长辞了。
行的方面,朱德向来主张轻车简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朱德去各地视察,常常带着自己的行李——战争年代开始使用的绿色的被褥、绿色的挎包、绿色的搪瓷缸,即使招待所预备了被褥、用具,他也不用。招待所桌上备了茶叶,他不喝;备了水果,他让撤下去。他每天起得早,当服务员来整理房间时,他早已把自己的铺盖叠好,将房间收拾干净了。
朱德去外地视察,出于对他的崇敬,地方的同志有时会送一点土特产,对此他坚决不收。有一年秋天,朱德去山东视察工作,正是水果收获的季节。地方上的同志知道朱德喜欢吃莱阳梨,就想让朱德带一些回北京吃。可又怕当面给他不收,就装了两筐,在朱德离开前悄悄抬到了火车上。火车开动后,两筐梨被朱德发现了。他马上把随行人员叫来,批评说:“我们下来是工作的,不是来搜刮的,怎么能随便收下边的礼呢?今后订下一条,下来工作,不许接受礼物;谁接受了,就让谁原封送回去。”接着他又吩咐。这两筐梨一个都不能动,到下一站火车停住,就把梨抬下车,派人送回去。
1960年,朱德在回仪陇的路上,人们送给他一些家乡的特产,他一样也没有带走,只是在临离开故乡时,自己在街上买了两双草鞋。有人问:“买这干啥?”朱德意味深长地说:“草鞋穿起来舒服,过去我在家里劳动,穿的就是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