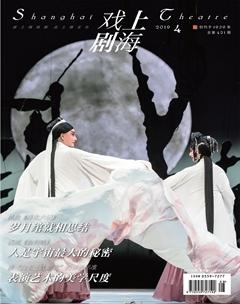双重桎梏下的“美国梦”观小维克剧院《推销员之死》
梦珂
英国导演界的超级明星玛莉安娜·伊利特在西区性别转换版《伙伴们》大获好评后,她与米兰达·克伦威尔(Miranda Cromwell)今年在小维克剧院共同执导的《推销员之死》再一次征服了伦敦的剧评人和观众。笔者在今年稍早的时候,曾于本刊撰文表明对性转版《伙伴们》的些许疑问,并认为其性转的设定虽然耳目一新,却多少有些逻辑尚且无法自圆其说之处。然而,这次《推销员之死》尽管使用了类似的手法,其张力却不可同日而语。伊利特将罗曼一家设定为下层中产阶级的非裔美国人,在保持了米勒的原作对“美国梦”的质疑和批判的同时,也将种族问题和资本主义糅合在了一起。按照剧评人马克·申顿的说法,这样的选角策略“让一切都改变了,同时一切都没有变”。与此同时,让美剧《火线》中的维德尔·皮尔斯来扮演威利,笔者认为也有意凸显威利身上的男性气质(masculinity)。换句话说,该版《推销员之死》所展现的是,当资本主义和种族主义的话语合谋时,“美国梦”所推崇的男性气质又是如何将包括男性自身在内的每个个体拽入无力解困的深渊。而其选角策略和制作,则让它的切入角度不仅十分合理,完成度亦可圈可点。
在本剧中,尽管皮尔斯也有意体现威利这个角色于人前佯装的幽默,但是给笔者留下较为深刻印象的是他身上尽力显露的男性气质。尽管威利的精神反复无常,但皮尔斯似乎有意将威利塑造成一个在商场上充满拼搏精神,在家中充满威严,遇到困难咬紧牙关、绝不示弱的典型男子汉形象。这种形象既符合我们对美国男性的传统刻板印象,也与美国文化向来所推崇的拼搏精神息息相关。可以说,“只要努力拼搏,你就能实现自己梦想”的叙事话语,不仅是所谓美国梦的蓝图与基石,更是高度性别化的,从源头上默认了“美国梦”的男性视角。一般来说,在不同文化体系的规训下,男性气质通常会有不同的描述,比如在古代中国的儒家伦理体系下,一名传统的男性知识分子通常被要求同时做到忠臣、孝子、节夫。在西方社会,全力赡养家庭、拥有职业热情,乃至精于体育运动,则被认为是中产男性所应该具有的男性气质。在当代社会,我们仍然可以看到这些男性气质是如何对男性进行规训的。而近些年来,随着女性主义运动和性别研究的发展,“有毒的男性气质”(toxic masculinity)一词被逐渐带入社会视野。“有毒的男性气质”通常被认为是在某种特定的社会文化下,对社会以及对男性自身带来伤害的性别特质,比如厭女症、恐同症、强奸、家庭暴力等等。随着对男性气质的深入研究,不少人也逐渐发现,那些被认为是男性美德的优秀品质,包括但不限于“坚强”“勇敢” “韧性”“自强”,也时刻有可能转化为伤害的枷锁,因为对那些在种族和阶级上处于从属地位的男性来说,这些优秀品质所带来的后果,通常是对自我认知的失调,对情感的压抑,以及耻于开口求人的羞愧感。
因此,由非裔演员出演罗曼一家,也为这个剧本赋予了种族与阶级的叙事视角。所谓“美国梦”,不仅只是资本主义的游戏,更只是中产白人男性的叙事。在阶级的话语下,老板的儿子瓦格纳依然是老板,而作为长辈的威利依然是打工仔。而种族的历史又让阶级如此牢不可破,在这样的前提下,威利的努力拼搏看上去更显得滑稽和可笑。在威利对过去亦真亦幻的幻想中,他的长兄本·罗曼及他传奇的淘金经历,亦不再仅仅是“美国梦”的象征和“成功”的榜样,也同时是男性气质和拼搏文化的体现,是对丛林法则作为人类生存法则的本质认同。他作为美国国家意识形态的代言人,向威利许下了诱人的承诺:“我进入了丛林,我找到了钻石,我成功了,我变得富有了。”——他的潜台词是,威利,你也可以。如果说文学批评对威利的批判指向他从未怀疑过本的真实性以及自己成功的可能性,那一个非裔版的威利至少是在试图去合理化威利的坚信不疑:本作为黑人,实现了阶级跨越。同时,该版本着力彰显的男性气质,也试图给“美国梦”本身合理化的解释。为什么“美国梦”非要实现不可?为何他一定要成功?就像威利的妻子琳达问的那样,“为什么他一定要拼搏”(Why must he fight)?因为事业上的成功可以确保威利的男性气质牢不可破,他需要这样的男性气质,来确保自身的价值。
就是这样的男性气质,令资本主义、白人至上和父权制的霸权话语变得密不可分,也同时让威利成为了霸权的代言人和霸权的受害者。在家的时候,尽管威利也有温情的一面,但绝大多数时候他可以说简直是一个暴君。从“瑞士奶酪”与“美国奶酪”之争那一幕伊始,他在家中暴戾、反复无常、歇斯底里的形象就在笔者脑海里深深扎根,那句“我下命令了!”(I gave you an order!)更是他在家中作为绝对父权权威的体现。然而,至高无上的父权也终会有不管用的一天,这一天这就发生在威利和“弗朗西斯小姐”偷情被大儿子比夫撞见的场景。事实上,包养情妇的行为本身也是威利对自身男性气质的一种再确认。英国著名剧评人麦克·比灵顿尽管对本剧的非裔卡司多加赞赏,却对威利的白人情妇颇有微词。他怀疑,作为黑人的威利,是否真的有这个胆子,和一个白人女性多一桩风流韵事呢?笔者倒是认为,在二战后的40年代,最能让一个下层中产的非裔男人体现他的男性雄风的,就是通过性来实现“种族超越”。威利在几乎全都是“上等”白人的商界里所遭受到的是歧视与侮蔑,他用征服白人情妇的方式来发泄。而他的男性自尊,又从金发的白人情妇那边获得了“补偿”。然而,威利有毒的男性自尊,在比夫的眼泪前被彻底瓦解。比夫的眼泪是对威利男性气质的反噬,它代表着一切为男性气质所不允许的品格,比如眼泪作为真情实感的流露,通常会被认为是软弱的表现。而向他人求助的行为,也会被认为这是一个不强大的男人。威利对比夫再三下令,命令比夫不许哭,这种沟通方式其实也是威利作为父权制实体的体现。但是,比夫没有听从于他,而比夫身上的这些反男性气质的特质,更预示着将来,在威利自杀前夕,比夫将威利所信奉的一切全部毫不犹豫撕裂的行为。
比夫所撕裂的,正是威利他个人所认同和维护的社会机制。它通过精英领导制(meritocracy),又通过本作为其象征不断向威利强调成功的必要性,和阶级话语一起,已经内化为威利内心的信仰。这使得他同时又是一个可悲的受害者。作为一个年长的黑人雇员,他在年龄和自己儿子一般大的白人小老板面前毫无尊严。当威利和小瓦格纳握手的时候,瓦格纳那一瞬间本能的抗拒,以及当威利摸了摸瓦格纳新买的有线录音机,瓦格纳无意识地用手帕擦了擦威利摸过的地方,或许都可以更好地回答威利早些时候思考的问题:为什么别人不能接受他的外貌?因为大家无法接受他的肤色。当威利因为迫于生活一瞬间无法控制自己,朝着瓦格纳大吼大叫的时候,又不知有多少人会激起“黑人就是易怒”的刻板印象呢?当那顿重要的晚餐被餐厅服务员斯坦利安排在远离舞台正中、靠近舞台边缘的位置,这个“特意安排的座位”,又有多少人会意识到这就是正在发生着的种族隔离呢?也或许有不少人会无法理解为什么威利死到临头也无法接受查理伸出的援助之手。因为对威利而言,他深陷于身边所有人扭曲的微观权力关系中,妻子、儿子、老板,甚至情妇。只有自己与这位牌酒不离身的邻居之间的关系,是他唯一相对平等的关系。
在米勒本人描写女性角色并不出彩、我们甚至可以说他对女性角色毫无兴趣的前提下,无可置疑的是,由克拉克扮演的琳达令人印象深刻。在戏份远少于皮尔斯的情况下,她完成了毫不亚于皮尔斯的精彩演出,塑造了一个立体而丰满、同时具有灵魂和诗意的琳达。她在绝大多数时候都是个体贴而善良的妻子与母亲。当“暴君”威利喊她闭嘴不让她说话的时候,她也对威利毫无怨言。当只有威利和她两人的时候,心中生出一丝迷惘的威利面朝观众席,望着半挂在空中的窗户,开始怀疑自己是否真的能够获得成功的时候,琳达的歌声不仅抚慰了四肢无力、心灰意懒的威利,更抚平了观众焦躁的内心——因为,尽管对剧情早已熟知,我们却依然希望威利能够获得救赎。琳达少有的情绪激动,是她奋力地敲着桌子,说道“应该注意”。尽管她并没有打破第四堵墙直接向观众奋臂疾呼,坐在台下的我们,却感到这确实应该是我们的责任。我们要注意的,不止是精神恍惚、自言自语、在崩溃边缘的威利,更要引起我们警觉的,是造成威利如此的这个社会。本剧的尾声,琳达跪在威利的墓前唱着灵歌。再一次地,尽管她并未打破第四堵墙,她的歌声,是观众所能收到的最真切恳求。
与此同时,笔者也认为,作为一名观众,我们不能仅仅感动于克拉克塑造了一个忠贞且“伟大”的妻子形象,更应该意识到这种形象同时是一种无形的枷锁。依托于本剧的语境,倘若说“有毒的男性气质”是对成功的痴迷和执着,那附着其上的“有毒的女性气质”,就是毫无节制的奉獻。这两者的结合仿若形成了某种永动机,让罗曼一家无边无际永无止境地翻滚在这个由资本主义和白人制定游戏规则的“丛林”里。如果我们都承认琳达是整部剧中唯一“正常”的人类,是一个好女人,那加诸她身上的盛赞必是压迫的勋章,因为她不得不扮演好妻子和母亲的角色,不得不安慰支离破碎的威利,她也不得不努力维系这个早已摇摇欲坠的家庭。在电话里,她叮嘱比夫千万不能搞砸今晚的重要晚宴,因为这将“拯救”威利的性命,她对自己的儿子感恩戴德。安娜·弗拉切尔设计让比夫以银幕剪影的方式投影在舞台后方,伴随着略显滑稽的爵士配乐,比夫仿佛一个泄气的玩偶,暗示着琳达的寄托与希望终将以失败告终。
米勒原先想把《推销员之死》剧命名为《在他脑内》(Inside of His Head),这也表明了本剧固有的意识流特征。在舞台设计上,根据《纽约客》的采访,米勒原先也想把舞台设计成四方的幕布。当幕布向上升起时,观众就能看到这个男人的脑内,以及人们如何在他的脑内走动、对话、交流。但米勒也认为他的舞台设计太过“呆板”,所以他放弃了。而之前一些《推销员之死》剧的排演版本,比如早至1983年北京人艺的版本,肖尼剧院2014年的版本,黑衣修士剧院和美国埃弗里曼剧院2016年的版本,在舞台设计上都选择了现实主义的路线。而安娜·弗拉切尔的舞台设计以灰色的空旷舞台作为基调,呈现出一种简洁的美感,其工业感其实某种程度上也贴合了男性气质的主题。而悬挂着的时而上升时而下降的门、窗框和桌椅,一方面算是一定程度上还原了米勒原本弃而不用的设计,为这“工业灰”增添了流动的质感,让整部剧可随意地“流淌”在现实和威利的意识流之间;另一方面,这些门窗框框也暗喻了资本主义等级制和种族制度如何作为无形的监狱,将威利和罗曼一家禁锢其中。在表现威利脑内回忆的时候,由亚利特·多尔设计的慢动作和定格,通过“姿态”(Gestus)的手法,将罗曼一家曾经的日常行为以一种类似幻灯片的形式一幕幕播出。这些慢动作式的回放不仅体现了这些场景在威利心中的重要性,也对角色之间的社会关系进行了揭示。
男性气质的危机可能是一个当下时兴的话题,但是这个版本却提醒了我们米勒七十年前就创作了《推销员之死》。每个男性角色都因为他对男性气质的需求而支离破碎:赚钱,成为精英,毫不示弱。令人沮丧的是,男性个体被这种价值评估是荒谬的。而这种价值体系,在当今,依然有着痛苦的回响(painfully resonant)。
——《独立报》剧评人霍利·威廉姆斯如此总结道。
而令人心灵感到痛苦的又何止是这种有毒的男性气质呢?伊利特这版非裔卡司的《推销员之死》试图向我们展示的是,我们无法割裂地看待任何一个问题,性别的,种族的,阶级的,因为它们的压迫来自于同一个根源的压迫。而在2019年的当下,去提醒人们压迫根源的同一性,显得尤为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