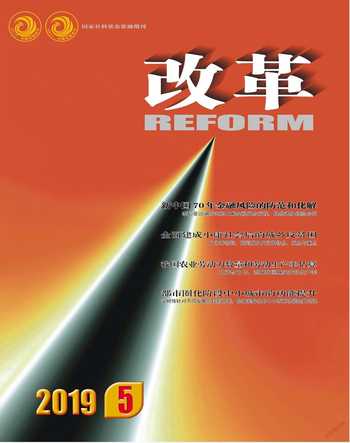我国创新驱动经济发展的机制构建与制度优化
王定祥 黄莉





内容提要:当前我国创新驱动经济发展的核心依然是技术创新驱动,其路径既包括技术创新的投入产出过程,又包括创新成果应用于社会生产的投入产出过程。在这两个过程中,市场机制和政府机制均存在失灵,需要协调处理好政府、市场的功能定位和有效分工,充分发挥市场机制、政府机制、政府和市场耦合机制的驱动作用,并健全配套的科技投融资制度,创新人才培育与管理、创业平台优化、知识产权保护、成果交易转化等制度,以构建创新驱动经济发展的长效机制。
关键词:创新驱动;经济发展;制度优化
中图分类号:F06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543(2019)05-0080-12
现阶段,主要发达国家积极推进创新驱动战略,全球创新版图与世界经济结构加速重构。2013年,韩国提出“创造经济战略”;2014年,德国推出“高技术和工业4.0战略”,英国发布《我们的增长计划:科学和创新》;2015年,法国启动 “未来工业战略”,日本启动“新成长战略”,美国启动“美国创新战略”,等等。可见,全球已进入高强度研发时代,创新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核心源动力。数据显示,1996~2016年,全球研发投入翻了两番。如果不加快创新步伐,我国就难以在未来的国际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正因为如此,早在2006年初,我国就制定了《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继而,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走自主创新道路和实施创新驱动发展”的新战略,党的十九大报告更是提出了建设“创新型国家”的目标,为我国转换经济增长动力、应对国际竞争挑战指明了前进方向。在国家创新战略与政策推动下,近年来以科技为代表的创新成果呈井喷式增长。据科学技术部的数据显示,2006~2016年,我国国内专利申请量从57.3万件增长到346.5万件,增长近5倍;国际科技论文(SCI收录)发表数从7.1万篇增长到22.4万篇,增长3.6倍;全国技术合同成交额从1818亿元增长到11 407亿元,增长了5.3倍;高技术产品贸易进出口总额从5287亿美元增长到11 000亿美元,增长翻番;高新技术产业主营业务收入从4.2万亿元增长到近15万亿元,增长近4倍。
图1(下页)展示了近10年来我国科技创新成果的增长态势。尽管大多数科技创新指标均呈现高速增长,但高技术产品贸易进出口总额增速波动较大,且从2014年开始持续出现负增长,究其原因,关键在于我国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问题较为突出,高新技术产品进口不断遭遇国际封锁,在国际技术贸易市场缺乏主动权。据权威机构评估,我国在重点领域相对处于“领跑”地位的先进技术仅占全球的17%左右,且主要是“单维突破创新”,比如核电、高铁、超算等,其他参与国内外市场竞争的核心技术创新多显得稀缺而被动,自主创新实力不足。从国内市场来看,相较于美国等创新大国高达70%以上的科技创新贡献率,我国2017年的科技创新贡献率只有57.5%,要实现2020年步入创新型国家行列的任务依然紧迫而艰巨。
从学术界的理论研究来看,自熊彼特提出创新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1]以来,经济学界对创新引领经济展开了广泛讨论,基本一致的结论是,创新驱动经济发展不仅需要合理的机制设计[2-6],而且需要有与之相适应的制度与政策配套[7-8]。国内学者也结合我国实际,提出了完善创新体制机制的思路。如成思危认为,处理好法治和人治、公平和效率、政府和市场、集权和分权的关系,是建立创新驱动体制机制的核心要义[9];辜胜阻等认为,通过构建合作创新、利益引导、风险分散、人才激励和文化促进五大机制能够激活企业和国家的创新源泉[10];王刚等提出,创新政策对创新本身和创新机制都有正向作用[11];吕岩威和李平则认为,我国应该加快建立以企业主导技术创新的体制机制[12];洪银兴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为出发点,提出供给侧和需求侧共同拉动的创新驱动战略[13]。
综上可见,近年来学者们对我国创新驱动机制和政策给予了高度关注,但较少聚焦创新驱动中政府与市场机制作用及其关系机理的研究,也缺乏对当前我国创新驱动动力不足的深层次讨论。毫无疑问,要实现我国在世界创新经济版图中的赶超和飞跃,达成2035年跻身创新型国家前列的宏伟目标,迫切需要加速优化我国创新驱动的体制机制与政策体系。为此,本文在探讨我国创新驱动经济发展内涵与机理的基础上,论证创新驱动中政府和市场机制的有效性及失灵,进而提出创新驱动经济发展的机制设计与制度优化思路。
一、创新驱动经济发展的理论内涵与实现机理
在当前国家供给侧创新驱动经济发展的战略部署和现实背景下,创新驱动的范围不仅指国家政策推动的公益性或准公益性技术创新,而且指激活私益性技术等多维度创新驱动活力;创新驱动的路径不只是单纯意义上的技术创新,而是包含技术转化的创新驱动实现过程。
(一)创新驱动经济发展的内涵界定
理论与实践反复表明,经济发展是人类社会追逐的永恒主题,具体包涵适度的经济增长、生态环境的改善、社会治安与福利的改进等内容[14];只有实现了经济发展,才能通过丰富的物质与精神产品的交易性供给,不断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促进人类进步与社会福利改进。显而易见,經济发展的基础在于追求高质量经济增长,为此需要摒弃纯粹依靠要素投入规模扩张的粗放式经济增长模式,实施创新驱动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集约式经济增长,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与经济绿色发展。
那么,何谓创新驱动经济发展呢?根据熊彼特的定义,在人类的经济活动中,创新包括原有生产要素的重组、建立新的生产过程、原有技术的改进和新技术的研发、组织设计和新组织的培育、产品改进和新产品研发、服务流程优化、生产经营制度创新等[1]。它从供给层面不断给人们带来新的产品或服务,产生新的产业和新的就业,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和社会长久进步。由此可知,驱动经济发展的创新具有多样性,包括要素组合创新、生产组织创新、生产流程创新、经营管理创新、制度创新、产品创新、技术创新等。而在这些创新中,尽管大多数创新都是由生产经营主体(如企业等)来完成的,只有影响生产经营的外部法律制度创新是由政府来完成的,以及部分技术创新是由科研院所和高校来完成的,但创新驱动链条客观需要多元化的创新主体协同推进创新成果转化与应用于企业生产经营过程,最终形成社会生产力。因此,在全社会凝聚浓厚的创新意识、创新精神和创新文化,形成万众创新格局,对于持续推进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建立创新型国家,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在推动经济发展质量提升的各种创新中,技术创新是最具有社会变革性的、里程碑式的、垄断性的核心创新,是形成企业和国家核心竞争力的关键所在。而推进技术创新,需要制度创新与之协同发挥作用,因为依赖于政治、经济、社会的制度创新可以为以文化、科学、知识为内容的技术创新创造良好的经济社会条件,并激发技术创新主体的活力和积极性。具体来看,推进国家经济发展的技术包括国防技术、军事技术、学科技术、信息技术等具有较强公益性的基础技术,以及囊括生产技术、管理技术、制造技术等具有较强经济效益(即私益性)的应用技术。此外,还包括兼具公益性和私益性的技术(即准公益性技术),如大数据技术、高铁技术、航空航天技术、核电技术、互联网技术等。在这些技术中,基础技术创新可为应用技术创新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而基础技术创新成果则需要借助应用技术创新才能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
(二)创新驱动经济发展的作用路径
基于上述内涵界定,创新驱动经济发展的作用路径实际上就是在政府制度与政策激励下,引导各种创新要素向各类创新平台集聚,开展技术等创新过程,并借助市场中介将创新成果转化为社会生产投入要素而实现产出增长与经济发展的过程。
图2(下页)详细展示了创新驱动经济发展的作用路径。该路径总体可分为两个投入产出阶段。
一是技术创新的投入产出过程。创新函数为A=t·f(k,l,s)。其中,A代表技术创新成果,t代表实验技术,k、l、s分别代表促进创新的资本、人才和制度等投入要素。在该阶段,政府通过知识产权专利制度与科研激励政策创新,诱导创新人才、资本要素向创新平台如企业、高校、科研院所、智库基地等集聚。其中,科研机构、高校等创新机构基于理论和学科优势,侧重基础技术和准基础技术的创新;而创新企业和创新大众则受市场竞争与利润最大化的驱使,主要展开应用技术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规模企业凭借其雄厚的资金实力和技术基础,往往成为应用技术创新的主力军;而创业大众更多的是凭借工匠精神、传统技术、历史沉淀等文化传承,成为生产工艺的传播者和创新者。智库基地通过应用性创新研究主要为政府和市场主体提供有重要价值的决策咨询参考。
二是创新成果应用于社会生产的投入产出过程。其社会生产函数为:Y=A·f(K,L,S)。其中,Y代表经济产出;A代表引入的创新技术,K、L、S分别代表实现经济产出的资本、劳动力和制度等投入要素。在该阶段,借助技术应用转化平台,及时将创新成果向企业生产经营过程转化,是创新驱动经济发展的重要环节。在此基础上,生产型企业将技术创新等成果作为投入要素,再匹配相适应的资本、劳动力等要素,共同投入生产经营过程,生产出新的商品或服务而投向市场,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需求,继而获得创新价值增值,促进经济发展。不论是初创企业还是规模企业,新技术在生產中的应用由于其经济效益的不确定性,客观需要更加优惠的产业政策、财政金融等政策支持。因此,创新价值的实现需要政府提供适当的风险补偿激励。
在现实中,由于创新主体构成的复杂性和技术创新的专业性,往往导致技术与生产严重脱节的“死亡谷”①。对此,我国各地积极搭建了技术创新转化平台,通过实现信息、技术、资本、优惠政策等资源的集聚,线上线下齐头并进,助推我国科技成果转化。具体而言,线下平台包括创业园区、产业孵化园、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等主要依靠政府力量推动的转化平台;线上平台又可分为全国技术转移公共平台、国家科技成果转化项目库、中国高科技成果转化信息网等信息统筹平台,以及全国农业科技成果转化交易服务平台、中国(浙江)医药卫生科技研发转化平台等专业性科技服务平台。近年来,除了上述线上转化平台外,依靠互联网金融发展起来的线上创新创投平台,例如京东众筹、天使汇、蚂蚁达客、顶呱呱一站式商业服务等,对我国创新成果向经济价值的成功转化亦发挥了重要作用。总的来说,创新驱动经济发展,需要依托创新平台集聚创新要素,形成创新力并向社会生产经营过程转化,完成生产力与经济价值的对接,进而驱动产业升级与经济发展。
(三)创新驱动经济发展的实现机理
由于技术创新在驱动经济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狭义的创新驱动经济发展往往指的就是技术创新,因而这里不妨以技术创新为例,并借鉴Mackinnon[15]模型说明创新驱动经济发展的实现机理。
在图3(下页)中,假定国家经济总量是由企业或个体单一经济量加总而来,且基于经济发展进程,只考察我国经济主要由自然资源和人口红利推动的要素驱动期和创新驱动期。在要素驱动阶段,从事生产经营的企业和个人受高利润的驱使,会改进原有的生产模式而增加投资。图中横轴表示企业或个人生产经营中的创新投入量N和对应收入R。要素投资期的创新实力升级会增加创新驱动期的经济增长,这里用纵轴表示。在驱动经济发展过程中,假定企业或个人的经济增收只依靠技术创新成果的驱动:TT'代表原有的生产技术模式(对这种模式的投资,从T开始出现递减的投资收益);TT'表明在未发生重大生产技术转变下,企业或个体会减少要素驱动期投资而增加新技术开发以维持较高的投资收益。相比之下,TT'代表企业或个人生产所需要新的创新技术(如新机械、新能源的换代升级),在企业或个体从新技术中获得任何产出之前,因为需要进行TT投资,就存在一个收入缺口——这与创造新技术所需的前期投入有关。然而,一旦这种要素驱动期的新技术发生,创新驱动期的收益就会很高,而且只有沿着T2T'2进入第二象限,收益才开始递减。显然,弥补TT的投资缺口需要财政资金、信息整合、技术引导等政策制度的及时创新和迎合。只有当企业或个体使用固有的生产技术时,在B点的平衡状态,两个时期的经济效益才是正数; I1和I2常见的“凸状”代表着企业或个体的生产无差异曲线,两个周期的生产投资一定都是正数,可以预见,这个投资约束因素在受自然环境恶化和人口红利消失影响的经济下行环境被严格地限制了,受制于投资约束和落后的生产技术,生产主体封闭在B点的低级技术中。如果能获得金融、财政等资金支持,企业或个体就能运用D点的新技术完成创新驱动期的经济增长。由此可见,企业或个人生产主体为了增加其在要素驱动期的收益和保持在创新驱动期的原有投资水平,就需要在资源要素驱动期通过财政、金融支持以及其他服务政策的补充,来创造逐利性企业或个人创新所需要的所有高级技术,而不是沿用传统的低级技术。
那么,如何冲破B点的传统技术,产生D点的新技术呢?这就是创新主体通过要素投入引起技术进步的过程。为此,我们通过借鉴Grossman & Helpman[16]以及朱保华[17]对技术改进的模型来分析。通常地,一次成熟的新技术是关于多种技术的集合A=(A0,A1,…Ak),其中A0是初始技术,其余是所需的新技术。假定技术创新均表示为技术质量改进,而每一次质量改进都可用大于1的q表示,也就是说,每一次技术进步的平均质量的序贯等级为q。如果第j种技术的质量改进(等级)用参数kj表示,则可能投入生产的第j种技术的平均质量等级就由1,q,q2,…qkj构成。进而假定技术的质量改进是序贯发生的,每次质量改进只能上升一个台阶。那么,经过质量改进的技术投入Ajt就可定义为:
Ajt=∑qkAjkt(1)
式(1)定义了经过质量不断改进的各种技术Aj的集合,意味着不同质量等级的j技术在生产过程中需要经历各个阶段,第j种技术投入量Ajt是不同质量等级的第j种技术投入量qkAjkt的加权和。在质量改进的技术进步中,我们可以设定随时间变化的参数kj表示与研究开发活动相关的第j种技术平均质量改进的模型。如果t0期的第j种技术的最高质量为1,tk期的第j种技术的最高质量用qk表示,则图4(下页)描述了第j种技术的最高质量的演进过程,第j种技术最高质量qk的延续时间为tk+1-tk。而j技术的产生,除了随着A0…Aj-1的技术基础以外,还需要资本、人才、制度等研发要素的投入,统称为研发成本ηA,η表示研发技术A所需的参数,研发成本一定程度上决定着新技术的改进升级。这里存在着两种情况,随着技术等级的提高,研发边际成本可能递增[18],也可能递减[19],但总的来说,不论递增或递减,研发成本都是新技術产生的必要投入价值,投入总量随t递增。正是所有研发要素的质和量同步推进,才能促进新技术A的生成。
二、市场机制与政府机制在创新驱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与失灵
实施以技术创新为核心的创新驱动经济发展战略,离不开市场与政府的双轮机制。因为在推进创新中,无论是政府还是市场机制,都不是完美的,均具有各自的优势与不足。下面不妨借助供求关系模型[20]予以说明。
(一)市场机制在创新驱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与失灵
从创新演进的角度来看,市场最大的功能就在于在竞争、价格和利润机制作用下自发地培育创新,即市场过程是一个依赖竞争机制对技术创新进行自我强化的过程,也是对私人创新成本与创新收益进行比较的过程,只有预期创新收益大于等于创新成本,创新才可能不断发生。具体来看,在市场价格机制作用下,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企业不仅会自发地进行最优要素重组、新产品开发、新的生产线引入,而且会自发地投身于应用技术创新,为市场提供迎合人们需求的新产品,甚至通过先导性创新技术研发新产品,以创造新的需求。即使存在高创新风险,由于有高收益期望的驱使,企业往往也愿意加大应用技术创新投入,以期利用创新产品的市场价格优势获取更多的经济利润。另外,市场价格也是消费者需求的“显示器”,创新型企业通常会借助技术改进、产品升级、加大供给以迎合市场需求。随着需求的减少和供给的增加,价格的变化又会促使企业寻找现有资源的替代品或不断创新技术,以减少现有资源的使用。因此,市场不仅能够催生应用技术创新,而且能引导企业进行生产经营创新。
在促进创新中,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并不是万能的,集中表现在对基础技术的创新及其转化中。一方面,在具有公益性、政策性、战略性的基础技术创新方面,如农业生产技术、社会基础设施构建技术、国防安全技术、军事技术、航天航空技术等,市场机制存在明显的动力不足和效率缺失。图5中,纵轴代表基础技术创新成果所表现的市场价格P,横轴代表基础技术创新成果供给量Q。由于技术创新资本边际收益递减,因而具有正外部性的基础技术需求曲线(AB)总是向下倾斜的。由于基础技术存在广泛的“搭便车”使用现象,私人企业对基础技术的边际创新成本明显高于社会的边际创新成本,从而私人主导下的基础技术创新成果的均衡数量为Q1,社会需求主导下的基础技术创新成果均衡数量为Q2,出现创新成果供给量的短缺(Q2-Q1)。与此同时,私人企业主导的基础技术创新的均衡供给Q1对应着相对较高的技术转让价格P1。虽然通常相对较高的市场技术价格会诱使企业持续地进行创新投入,但其收益具有较大的正外部性且需要巨大的创新成本,这将大多数企业内生性地排除在外。可见,市场机制主导的基础技术创新成果和动力显然是不足的。另一方面,如果市场机制不能准确反映基础技术的市场信息,其创新成果将得不到有效的转化与应用。而基础技术的创新信息大多掌握在科研院所、高校等专业性研究机构手中,与市场需求者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这就制约了创新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因而需要政府的介入以构建良好的科技成果转化体制机制。
(二)政府机制在创新驱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与失灵
显然,在正外部性和信息不对称特征显著的基础技术创新中,政府的主导作用是必要的。这不仅是因为政府有雄厚的财力作创新投入支撑,而且通过资助科研院所和高校开展基础技术创新,以满足全社会对基础技术的需求,增强国家的核心竞争力,也是政府的基本职责和义务。因此,政府有能力(财政实力薄弱的地方政府除外)根据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安全的需要,按社会边际创新成本与需求曲线决定的均衡创新成果供给量进行投资和引导,同时为基础技术创新主体提供基础技术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所需要的制度和市场条件,以满足创新驱动经济发展和国家安全的需要。
同样地,政府机制在创新驱动经济发展中仍然存在失灵的可能,主要表现在应用技术创新成果供给不足。如图6所示,横轴表示应用技术创新成果的供给量Q,纵轴表示对应的技术价格P,AB为需求曲线。应用技术需要借助企业直接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应用技术的研究则需要立足市场需求,摸清技术市场竞争状态,评估技术创新成本、收益和风险,等等。所有这些均涉及技术创新资源有效配置的信息,都需要政府部门深入市场,了解消费者、企业的微观需求,这将产生巨大的信息搜寻成本。政府往往无暇顾及,且不少地方政府财力薄弱,也无力支撑所有应用技术的创新,因而会导致较高的边际社会创新成本,与社会需求曲线相交决定的创新成果供给量为Q3,其价格为P3。相反,企业对应用技术创新的成本、收益、风险和市场行情等信息了解更多,信息完全化程度较高,更能有效配置创新资源,因而企业应用技术创新边际成本远低于社会创新边际成本,与社会需求曲线相交决定的创新成果供给量Q4大于Q3。可见,政府在主导应用技术创新中存在失灵或不足。当然,在不同的所有制企业,创新效率也存在显著差异。如政府出资下的国有企业存在行业垄断、创新压力不足、激励机制不到位、管理流程冗长、制度约束较多等低效管理特征,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其边际创新成本明显高于民营企业的边际创新成本。国有企业凭借国家从资金到政策上的诸多优势拥有稳定的高额利润,这种非市场因素导致的超额利润获取,使得国有企业无需高度关注市场需求与竞争;即使创新能带来超额利润,但受制于行业准入、监管压力、融资受限等因素制约,民营企业也可能有心无力。可见,市场准入制度对企业创新能力具有重要影响。
三、我国实施创新驱动经济发展的机制设计
由于在我国创新驱动经济发展中市场和政府均存在失灵,因而只有协调处理好政府、市场的功能定位与有效分工合作,才能构建起创新驱动经济发展的长效资源配置机制。
(一)创新驱动经济发展中市场机制的功能定位
在创新驱动经济发展中,创新资源要素配置和创新成果的交易凸显了市场机制的重要性,其功能定位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一是主导应用技术创新。市场机制在应用技术创新中是最富有效率的,这就决定了市场机制在推动企业创新中应发挥决定性作用。换句话说,在市场价格、竞争与供求机制作用下,资本与科技实力较为雄厚的企业主体,能够自发通过新技术和新产品研发、生产要素重组、机械设备更新、产品与服务升级、品牌文化培育、商业模式升级等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并通过持续的创新进行新旧技术替代,以维持可持续的竞争力优势,获得超额经济利润。因而,应用技术创新应主要依赖于企业等市场主体,通过市场机制加以引导。
二是主导创新资源要素配置。人才和资本是最主要的创新要素。这些要素在市场供求、价格、竞争和奖惩机制作用下,可凭借其掌握的信息,自动筛选创新平台,并向风险较小、持续高效的创新平台和企业集聚,转化为内在的创新动力,从而提高科技创新资源配置效率。由于应用技术创新有明确的成本和收益边界,技术价格清晰,因而市场机制完全可以有效主导应用型创新要素的配置。
三是诱导创新制度有效供给。市场不仅能够引导应用技术创新,而且能够汇聚、反映技术创新行业发展动态,进而催生制度不断创新、不断完善的现实需求。目前我国应用技术创新市场过度集中于互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等高科技技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或国有企业,中小企业创新实力和创新资源严重不足。这种创新资源配置的市场失衡可以诱导政府改革相应的制度,激励创新资本、人才等要素向中小企业集聚,以促进创新资源要素适度均衡配置。
(二)创新驱动经济发展中政府机制的功能定位
创新驱动经济发展也需要政府积极介入,政府的功能定位应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一是主导基础技术创新。作为创新驱动的端口,具有公益性的基础技术创新更多地应依靠政府行政、财政、监管职能的推动。政府理应根据国际科技发展趋势和国家发展需求,对重点高校、科研机构等创新主体的基础技术创新进行战略谋划、出资、调控、监管与奖励,鼓励其充分发挥基础学科优势,不仅要促进理工科技术创新走在国际前沿,而且要注重人文社科类的创新进程,坚持多样性、专业性、规模性的学科发展,在深度和广度上同步创新,为应用技术创新、试验、应用奠定坚实的理论后盾。
二是加强创新要素培育、配置调控与成果奖励管理。创新人才培育与引进具有明显的外溢效应。政府除了应加强各层次教育资助与管理外,还可通过完善各种人才工程计划,建立科学的人才引进与科研考核制度,加强地区间创新资源要素配置的宏观调控,实施科学的科研成果奖助体系,完善科研诚信制度,促进创新资源的有效配置,提升创新效率、效益和效能。
三是主动加强创新基础条件和制度的有效供给。从我国实际情况来看,首先,政府应加大重点科研院所、高校基础技术创新投入,完善一流学校、一流学科建设与支持考核机制,促进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创新协同发展,加强科技创新平台建设,为基础技术创新提供必要的公共基础条件。其次,完善创新保护与奖惩制度,促进知识产权保护和技术转化,借助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不断培育高层次创新人才。再次,借助自身政策引导和调控优势,加强科技创新融资体系建设,建立功能健全、运行高效、风险可控的科技投融资机制。最后,积极引导创新技术转化平台成为集聚创新要素、整合跨界资源、支撑产业技术创新的关键载体,从而助推创新技术成果的市场化交易。
(三)创新驱动经济发展中政府与市场机制的耦合
一是创新成果转化中政府与市场机制的耦合。创新成果的转化过程就是市场筛选技术以促进经济增长的出清过程,然而市场的优化配置受阻于信息不对称,必然需要政府和市场机制的有机耦合。一方面,通过市场价格反映与政府财政补贴等成本补偿耦合,驱动基础技术创新成果向应用领域靠拢,以降低企业现有技术的投入成本,促使基础技术的应用转化;另一方面,政府可通过建设创新產业园区、创业孵化园、创投交易网、创新成果交易中心等中介服务平台,实现高校、科研院所与市场主导的生产企业、创业企业与创投资本的对接,提高基础技术创新成果驱动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二是创新投资与风险承担中政府与市场机制的耦合。创新过程的复杂性、创新主体的多样性、创新投入的高风险性、创新驱动的长周期性等特点,容易挫伤创新主体的积极性和可持续性,因而需要发挥政府和市场的耦合作用,协调处理好政府与市场投资和分担创新风险的关系。以创新基础技术为主的科研院所和重点高校,应更多地承担公益性、战略性强的基础技术创新。这些创新技术溢出效益明显,应由政府承担大部分基础技术创新与转化成本,在转为应用技术后则由生产企业承担投入成本。而以创新应用技术为主的企业,其技术创新过程是生产效率提升的自我改进过程,企业在追逐潜在高收益的同时,还需承担创新可能的高风险,政府仅需通过财政补贴弥补部分创新损失,并改善相应的制度,提供良好的创新融资环境。
三是在准公益性技术创新中政府与市场机制的耦合。准公益性的技术创新成果应用转化不仅具有显著的社会效益,而且有一定的经济效益,属性介于基础技术与应用技术之间。其成果转化的社会效益特征决定了政府支持的必要性,经济效益特征决定了私人资本投资的必然性。其创新投资规模较大,一般企业的资本实力受限,难以满足投资需求。如果全由政府出资,又会加重政府负担,加之成果具有应用价值,决定了政府主导必然存在信息不对称,影响创新资源配置效果。可见,所有准公益性技术,如果单靠政府和市场任何一方创新,均可能面临供给不足。于是,需要建立市场与政府耦合投资与创新机制。即要么由市场主体与政府联合投资创新,要么由政府投资并借助各种智库基地创新,创新成果由市场购买,或者市场投资创新、政府补贴或奖励等,从而形成市场与政府共同促进公益性技术创新的长效机制。
四、我国实施创新驱动经济发展的制度优化
结合我国实施创新驱动经济发展的现实状况,下一步应着力从创新资本、人才、平台、知识产权保护、成果应用转化等方面进行制度优化。
(一)完善科技投融资制度
近年来,我国不断加大技术创新投入力度。2016年R&D经费总量为15 676.70亿元,较2015年增长10.6%,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2位;企业R&D经费支出达到12 144.02亿元,占全部R&D经费的77.51%;我国R&D经费投入强度(即占GDP的比重)达到2.11%,已超过欧盟平均1.96%的水平,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但与部分发达国家2.5%~4%的投入强度相比还有差距。针对我国创新资本投入不足的现实,应加大财政投入力度,健全科技金融支持体系,构建基础技术创新以财税支持为主、应用技术创新以企业投资和金融支持为主的科技创新投融资制度。
第一,建立稳定预期的科技财税制度。目前我国处于创新驱动发展初期,应通过构建稳定预期的科技财税扶持制度,加强对高校、科研院所等创新驱动平台建设和运营的财税支持,持续加强对基础技术研发、高科技产业、文化创新产业、创业投资产业的财政支持力度,为创新型企业和大众创业提供税收减免、特殊补助等优惠政策。建立事前立项、成果购买、事后奖励、税费减免等多样化科技财政支持方式,加强成果质量考核验收,简化科研财务制度,建立符合创新规律的科研经费管理机制。
第二,构建直接与间接融资协调发展的科技金融制度。推动有条件的银行建立科技金融事业部制,探索设立政策性科技金融机构,开办政策性科技信贷、保险和担保业务,建立科技型企业产权交易市场;设立种子投资引导基金、天使投资引导基金等,开展股权投资服务,引导和撬动社会创投资本投资创新创业;建立知识价值信用评级体系、信用风险补偿基金等,推动创业投资平台提供债权融资服务,帮助初创企业与金融机构快速建立借贷关系;积极发展具有公信力的線上众筹平台,吸引更多的小规模市场资金向科技创新行业靠拢。
(二)健全创新人才培育与管理制度
根据OECD统计,中国R&D研究人员全时当量从2010年开始超过美国,位居全球第一,至今仍保持总量上的优势。但是,我国研发人力投入强度在国际上仍处于落后水平。而创新人才的培育与管理,需要政策性激励和引导,确保创新人才个人与社会双重价值的实现。
第一,完善创新人才培育与引进协同化制度。人才是第一战略资源,要坚持培养和引进相结合的方式,大力实施人才振兴战略。学校应着重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和综合素质,提高各层次教育质量。实施开放式人才战略,积极引进国外优秀人才,健全校企校政联合培养人才机制,发挥各种领军人才创新团队建设的作用。针对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应从科研经费、户籍、住房、教育、社保、医疗保健等方面为创新人才提供优良的保障条件。
第二,落实差异化的创新人才激励制度。激励制度主要包括薪酬激励和科研奖励两个方面。应探索建立有考核任务、富有弹性的工资薪酬制度,有条件的企业可以通过股权、期权、收益分配等新型分配方式,补充创新人才的经济价值;结合不同的科研技术,形成多层次的科技奖励制度。对于先进制造、互联网、大健康、新能源、新材料、生态环保、现代农业等世界产业变革的聚焦领域成果给予重点奖励;根据创新主体的不同,对高校、科研院所、大型企业采取集中高额奖励,对中小企业或创业大众采取散点式奖励。省级政府应推行两年一届的科技成果奖励周期,缩短教学科研创新成果奖励时间,依据财力增长提高奖励力度。
(三)优化创新创业平台制度
构建技术创新与交易平台,不仅是吸引创新要素集聚的基础,而且是有效解决技术供给与需求脱节的关键。结合我国的实际,建议从以下两个方面加以完善:
第一,完善专业性的技术创新平台制度。除高校、科研院所、创新企业本身技术创新实力的升级外,还应提供架接各类创新主体的技术创新平台的资源共享、信息对接、技术测评等专业性创新服务。就科学技术硬实力而言,应依托校企、研企合作机构积极搭建学科门类的专业性研究平台;就文化技术软实力而言,应加强高校、研究机构对传统文化历史积淀的保护,积极开展商业化文化创新园区,激发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融合。加快建立创新平台成果考核机制,完善平台创新经费奖助体系,积极探索线上创新平台的创建与管理,尽可能培育和维护其创新活力。
第二,构建服务创新创业全过程的平台制度。创业平台集中服务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在创业前期,应全方位拓展创新模拟、创业论坛、创业大赛、文化创业园区等,大力培育大众创新创业意识;在创业初期,集中为小规模创业大众提供场地、信息、资金服务,并配备相应的税收优惠制度、投融资制度、技术奖励制度;在创业成熟期,创业平台应积极引入市场背景的资金方,为创新企业提供市场化融资服务,政策性金融服务则应择机退出,税收、技术、信息等服务继续保留。此外,结合当前互联网、大数据发展趋势,应积极鼓励市场化的线上创业中介平台创建,同时做好平台信息真实化、日常监督严格化、问题处理法律化,健全创业网站规范管理制度。
(四)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
知识产权包括专利权、商标权、著作权以及专有技术和商业秘密的所有权、使用权与收益权等。知识产权保护制度能够有效规避技术溢出对创新主体造成的经济损失,是保护创新积极性的重要手段,需要激励与约束机制并存。
第一,健全规范化的激励保护制度。加快完善应用技术专利申请、专利审核、专利授权等技术保护制度,并通过制定标准化的专利技术转让合同,形成规范化的专利技术应用市场,确保创新主体的技术和经济利益得到双重保护。而对科研院所、高校等技术创新主体形成的外溢性较强的基础技术创新成果,应健全给予研究团队在研究经费包干使用、署名权、奖励证书、奖金激励、职称评定等方面的激励措施,以维护研究团队的创新激情和经济利益。
第二,形成法制化的约束保护制度。针对我国知识产权约束保护制度的严重缺位问题,严格的行政监管和法律手段同步推进是关键。不论是基础技术还是应用技术,一旦被使用,都必须经过创新主体同意,并注明出处或支付一定金额的使用费用,依靠行政与司法监管,对冒用、领用、盗用技术等违规行为追究法律责任或经济重罚。只有通过法律手段严处,在全社会形成知识产权意识,才能充分发挥制度化的产权激励和保护措施的效用。
(五)健全创新成果交易转化制度
以2016年为例,我国的发明专利授权量为40.4万件,实用新型专利授权量为90.3万件,外观设计专利授权量为44.6万件,但全年仅签订各类技术转让合同32.0万项,占比只有1/6左右。基于此,实现创新驱动经济发展,需要构建创新成果交易转化制度,借助成果转化中介,实现创新成果在供需主体之间有效对接。为此,需要完善以下两种制度:
第一,制定引导功能突出的市场准入制度。应准确把握全球创新发展趋势,在人工智能、量子科学、基因编辑等一些重大科技创新领域,建立严格的准入制度,主要依靠国有大型企业或科研机构承担国际创新赶超任务。基于现有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在科技创新资源上的不平衡,国内创新市场迫切呼唤更为宽松的准入制度,类似能源行业可以适当采用混合所有制,给予民营企业更多的创新机会。基于专业技术的信息不对称,应积极推动产学研结合的校企合作平台的自主创新,助推应用技术的内部对接。基于财政资本的巨大压力,应积极鼓励市场资金进入高校、科研机构的研发团队。
第二,构建政策性与市场性并存的技术转化平台及交易制度。创新成果的转化分为基础技术向应用技术转化和应用技术向经济价值转化两个部分。这都需要借助技术转化交易平台及其交易制度规范来实现。创新成果转化平台应区分政策性和市场性的中介服务平台,主要提供技术成果信息发布、技术指导、研企对接服务、标准化技术转让合同、技术转让法律顾问等服务。前者应以线下平台为主,并凭借地方政府的政策资源推动技术的转化和交易;后者应以线上平台为主,建立由市场供求关系决定价格的机制,结合创新成果定价与交易制度,真实反映技术的稀缺性及其经济价值,加快创新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
参考文献
[1]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M].叶华,译.北京:九州出版社,2006:106-161.
[2]Kaldor N. A Model of economic growth[J]. The Economic Journal, 1957, 67(268): 591-624.
[3]Romer P. Growth based on increasing returns due to specialization[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87, 77(2): 56-62.
[4]Lucas R. On the mechanic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J].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1999, 22(1): 3-42.
[5]Nelson R, Winter G. Evolutionary theorizing in economics[J].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002, 16(2): 23-36.
[6]Palley T I. Old wine for new bottles: putting old growth theory back in the new[J]. Austrian Economic Papers, 2010, 35(67): 250-262.
[7]Peterz C. Structural change and assimilation of new technologies in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systems[J]. Futures, 1983, 15(5): 357-375.
[8]Castellacci F. Evolutionary and new growth theories: Are they converging?[J]. Journal of Economic Surveys, 2010, 21(3): 585-627.
[9]成思危.深化改革要靠制度創新驱动[J].中国软科学,2014(1):1-5.
[10]辜胜阻,李洪斌,王敏.构建让创新源泉充分涌流的创新机制[J].中国软科学,2014(1):11-18.
[11]王刚,李显君,章博文,等.自主创新政策与机制——来自中国四个产业的实证[J].科研管理,2015(4):1-10.
[12]吕岩威,李平.科技体制改革与创新驱动波及:1998~2013[J].改革,2016(1):76-87.
[13]洪银兴.以创新的经济发展理论阐释中国经济发展[J].中国社会科学,2016(11):28-35.
[14]保罗·萨缪尔森,威廉·诺德豪斯.经济学[M].于健,译.北京: 人民邮电出版社,2013:106-161.
[15]Mckinnon R I. Money and capital in economic development[M].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1973: 679-702.
[16]Grossman G M, Helpman E. Innovation and growth in a global economy[J]. Economica, 1993, 1(2): 323-324.
[17]朱保华.新经济增长理论[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9:216-218.
[18]Romer P M. Endogenous technological change[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89, 98(98): 71-102.
[19]Jones C I. Times series tests of endogenous growth models[J].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2001, 110(2): 429-525.
[20]王定祥.农地适度非农化进程中的市场与政府的分工[J].改革,2009(7):105-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