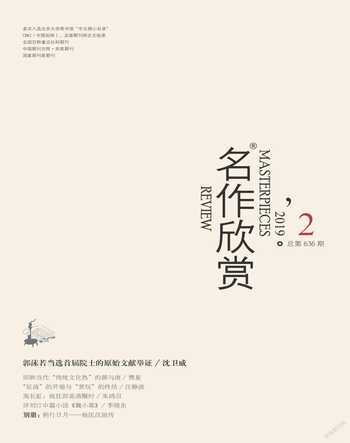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
沈德康
摘要:郑山明散文集《乡愁的滋味:那年·那事·那人》对故园的深情叙写所蕴含的那种鼓励人试着用超然的、非功利的眼光欣赏劳动者及其生活本身的态度,让我们领悟
到人的本质处境即“诗意地栖居”。关键词:郑山明《乡愁的滋味》技术时代诗意地栖居
《乡愁的滋味:那年·那事·那人》是郑山明创作的一部散文集。此书语言简洁、流畅,笔触细腻、节制。作者饱含深情的追忆,让“湘南故园”的风俗礼仪、世态人心、鸟兽虫鱼在读者心中熠熠生辉。
“薄暮时代”的乡愁
每一个人都有令他魂牵梦萦的故园。郑山明笔下的故园,有难熬的春荒与秋旱,有糯米酒里氤氲出的醇香、“花喋婆”中飘出的闲适,也有舂水河畔的乡民们直面生存困境、挑战无常命运时表现出的勇敢、坚韧与善良。
作者平实、质朴的文字,饱含着对故土的眷念。这眷念,根植于作者早年与土地、田野的交道。作者写道:“从来没有人比农民更能接近春天,从来没有什么活儿比割草更能感知春天。”当把碧绿的狗尾草或开着小白花的“马儿杆”割下、捆扎起来背回家一把把喂给家里饲养的白兔、马驹、牛羊或鸡鸭,此时此刻,你的心里会升起一种唯有当过母亲的人才能体会到的温柔与充实。
农人的生活的确艰辛,在作者笔下,“双抢”“抗旱”“打石灰”“挑煤”等营生让每一个劳动者遍尝生活的苦楚。如作者所言,在“双抢”时节,“割禾是很累的事。连续几个时辰弯腰劳作,腰板又酸又胀,伸一下腰就能听见腰椎嘎嘎的爆响声”。但是,那种与春水、山风以及默默奉献的泥土打交道的过程,确实又饱含着浓浓“诗意”。这种“诗意”根源于農人的生存境遇:在无限而神秘的长天与大地之间,在无数个寒来暑往、朝晖夕阴的轮回中,农人领会并确认了那“生于大地又归于大地”的宿命,他们默默地接受大地母亲丰厚的馈赠,也默默地承受突如其来的洪涝、饥馑与死亡。
作者的乡愁具有时代性、普遍性,绝非孤例。任何一个从农村进入城市并在时代洪流的裹挟下不得不修正甚或放弃传统道德或信仰的人,都会不由自主地怀念那个业已消逝了的、只存在于理想之中的、闪着金光的世界。忍不住地思念,根源于难以忍受的现实。因为不安,所以憧憬。哲学家说这是一个“悬于深渊的世界”,是漆黑的“夜半时代”;诗人说“我们的习惯意识越来越局促于一座金字塔的顶尖上”,因而全然忘记了“我们是‘不可见者’的蜜蜂”这一实情;小说家则认为现代人的幸福都是“被幸福”……因而,我们已很难体会到生命的神圣或神秘,也很难体会到“命运”这个词究竟意味着什么。
何处是家园?
何处是家园?诗人说:“充满劳绩,但人诗意地栖居在这片大地上。”“家园”不仅仅是用来遮阴避寒的栖身之地,它还是思念的方向,是浩荡乡愁的策源地,是一开始就树立在心田上引导我们不断抵近理想人格的路标,是将天地四方的神灵与大地之上的有死之人建立起联系的无比强烈的希望与诗意的想象……此时,笔者也想起了湘南传统民居庭院中常见的采光、采雨的“天井”,还有村落中不可或缺的“祠堂”,以及祠堂门口半月形的“池塘”中亭亭净植、香远益清的“莲花”。从乡村孑遗的古迹中,从天、地、神、人水乳交融的格局中,从风雨临庭、家燕栖梁、荷香四溢的意象中,我们才能明白何为“家园”。
“家园”的确是一种滋味,在作者细腻又充满韵律的文字中,我们可发现“家园的味道”并不仅仅驻留在舌尖,而是需要我们通过“身体力行”的方式去参与、去欣赏才能获致。对此,笔者以书中的一段文字为例:
豆腐师傅把石膏碾成粉末,和点豆浆存放在一个大缸里。看着锅中的纯豆浆煮开了,立即将其装入两个木桶里,两个青壮劳力提起木桶站立在大缸两侧,豆腐师傅用手搅动缸里的石膏浆,速度越来越快,搅得石膏沾满缸壁时突然将手抽出,大喝一声“倒”,两个木桶的豆浆顷刻冲入缸中,“啪”的一声将大缸盖好。几分钟后,在人们焦急的等待中,豆腐师傅慢慢地掀起缸盖,将浮在表层的泡沫除去,原来液体状的豆浆已变成晶莹白嫩的豆腐脑。
从上面这段引文,我们可以发现:人的生活之所以如此美好,那是因为人不仅活着,更关键的是人还能用欣赏的姿态来审视生活,用客观、冷静的态度来反思生活。与其夸赞他们的技艺如何精湛,还不如说他们已经学会了用一种超越性的、非功利的亦即诗意的眼光来看待生活。
“家园”何在?按作者的意思,“父母在哪里,家就在哪里”。故我们的“家园”必然也是生长“爱”的沃土。对此,作者深有同感,他在书中这样写道:“那时,学生们没有被当作一个个装知识的容器,而是作为一个个完整的有灵性的人来培养的……那时读书最大的特点,就是学生始终没有脱离大自然,没有脱离日常生活,也没有脱离简单质朴的家庭关爱。”@
现代文明是高度社会化、集约化的文明。文明的两大支柱——“人的生产”与“物的生产”——在我们时代都是十足计划性的。如学者刘易斯·芒福德所言:“机械化(机械技术)和严格的社会组织管理(社会技术),这两者本身在历史上并非是新花样,新的仅是这种机械化和严格管理现在已是有计划地、有形地在统治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在这种“整体主义”和“激进主义”倾向的“计划”中,与过去相比,社会的细胞——“家庭”的位置是极大地下降了,或者说传统家庭葆有的“德育”的内涵被时代的浪潮冲刷掉了。于是,“德”也在世人对“才”的狂热追求中丧失了其作为“帅”的主导地位。故而我们时代的缺憾,用作者的话来说即:“他们没有学到比父辈更多的东西,却丧失了许多祖辈传承守望了一代又一代的东西。”因此,我们不难意识到,秉有传统教育观念的严父、慈母对于儿女健康人格的养成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正如作者在书中所言:“每隔一两个月,我就会抽空回老家看看他们,陪父亲喝两杯,和母亲说说话,看到他们幸福愉悦的样子,我仿佛找到了自己生命的价值和生活的意义。”由此可见,我们的“家园”是“爱”的象征,是从伦理道德的维度指向生命意义和人生价值的坐标。
烟波江上的“返乡之思”
在今天,那种浪漫主义的“乡愁”往往因其保守主义的倾向而被视为不合时宜。但是,如学者芒福德所言:“浪漫主义所代表的理想的力量是现代文明的必要组成元素,我们今天需要的是把它转换成可以在现实社会生活中体现出来的模式。”所以,在这部散文集中,所有那些对家园的美好追忆其实都散发着理想主义的光华,追忆过去则是为了更好地憧憬未来、创造未来。
在这个逐渐泯灭和混淆“人性”与“物性”之本质差异的时代,“社会技术”在各个层面都“机械技术化”了,人和由人构成的社会失去了应有的神性,人们以对待物的方式对待人,人们以操纵一台机器的方式来管理社会。对于这个时代,最彻底、最深刻的批判来自《共产党宣言》:“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宗教虔诚、骑士热忱、小市民伤感这些情感的神圣發作,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一种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代替了无数特许的和自力挣得的自由。”或许,当我们读懂了这本关于我们时代的“病历”,我们对作者书中的美好追忆才能有更深切的体会。
在作者的追忆中,我们的“机械技术”还没有“高级”到把一个有尊严的人变成单纯的“交换价值”,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在书中描绘出的作为嫁妆的呜呜吟唱的旧式纺车上看到。在纺纱织布的同时,含辛茹苦的父母也将一曲关于乡愁的歌谣送到了数十年后的游子耳畔。在那个“没有使用农药的年代”,田里种的是高梗水稻,圈里喂的是土猪,所谓的“良种”还未大行其道,人们在河里摸鱼、田里抓鳝,感受到“煎鱼送饭,锅底刮烂”的生活况味。
在这个崇奉“商品拜物教”并将“工具理性”视为至高价值的时代,我们把“物”的位置放得有多高同时也就决定了我们把“人”的位置放得有多低,我们把测度、加工和评价“物”的方式视为至高价值,这也就决定了我们必然以对待“物”的方式来对待“人”。对于这样一种普遍“存在”却尚未“自觉”的悲惨状况,此书中对传统手工技艺的诗意描写就像是一剂解毒剂:
这时补锅匠左手拿一块叠了好几层的小布块,迅速从地上掏一层草木灰在上面,大拇指在灰上面压一小坑;……右手放下铁钳,快速拿起一支用破布扎成的布柱,将布柱蘸上水对准那粒“月偏食”压下去,“滋”的一下布柱被灼热的铁水烧出一道火苗。
从这段引文我们可以看到其中有诗意的劳动者,事实上,周围还有一群诗意的观赏者。劳动创造价值,但是劳动创造的价值绝不仅仅是单纯的经济价值。劳动值得赞美,但是我们不能仅仅在功利算计的层面赞美。如果我们完全不用伦理的、审美的眼光看待劳动,那我们就跟非人的动物没有任何区别。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的哲人才始终强调:“栖居是以诗意为根基的。”对于这一点,笔者在前文中已多次谈到。但是,笔者此时还是非常愿意用作者对美好生活的畅想来印证这个看法:
阳光从窗户射进来,男人又在火塘上架起桌子,取一块腊肉切成薄片,和青蒜、辣椒一起烹炒,肉和大蒜的清香夹杂着酒香袅袅飘飞在雪后初霁的湛蓝天空。一壶酒,一场雪,一个咸淡的冬季。人生如此,夫复何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