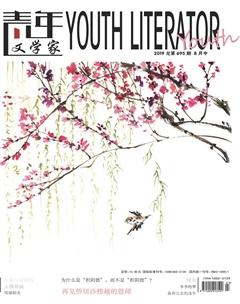河南地方戏《卷席筒》的叙事组合与聚合
孙伯翰
摘 要:《卷席筒》在河南戏曲界已经流行了40年且未有降温的迹象,这种现象在建国后新创作的河南地方戏中是十分罕见的,可是纵观全剧,我们可以看到《卷席筒》情节结构较为简单、人物性格单一、叙事手段单调,故事本身似乎没有什么特色,但是紧靠演员的演技能够让一出戏火爆四十年似乎也不大可能,小苍娃的最著名扮演者“海连池”在舞台生涯中塑造形象众多,可大多数观众记得的还是他扮演的“小苍娃”。结合叙事学与符号学的手段分析《卷席筒》可以解决为何简单的故事同样可以吸引河南观众这个疑问。
关键词:卷席筒;标出性;丑脚
[中图分类号]:J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9)-23--02
一、作为叙事组成的丑脚
《卷席筒》虽然是大团圆结局,但细读剧本可见其中有一些不够团圆的因素,抛开家产尽失不说,小苍娃与曹宝山的父母双双死亡就为整出戏增加了几分悲剧色彩,因为家产问题弄得家破人亡的故事在各类文艺作品中屡见不鲜,但是像《卷席筒》这样把这种故事演成喜剧的确是少见。这至少说明了两个问题,首先,在《卷席筒》中,“悲”或是“喜”的效果并不由整个故事的人物命运决定,更大程度上是由叙事者的叙事视角决定,观众只会在意被叙事者强调的那个人物,也就是主人公的最终命运,只要叙事者认定主人公高兴,即使主人公父母双亡,观众依然会将此剧作为喜剧来看待。《卷席筒》能够让观众完全被叙事者牵着走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主人公小苍娃所使用的脚色行当是“丑脚”。在戏曲观演的实践中,丑脚更能够吸引观众的注意力,而在戏曲观演的默认规则中,丑脚本身就意味着该人物的行为可以超出日常社会的行为价值规范,对该人物的评价也要超出日常社会的伦理体系,更重要的是,在传统戏曲中,丑脚相对于剧中其它人物大多有着较强的独立性,似乎游离于剧情之外,即使使用丑脚的剧中人物与其它剧中人物有着亲属、朋友、同事之类的关系,这种关系相比其它脚色行当构建的关系也不够紧密。在观剧时,由于小苍娃“使用”了“丑脚”这一行当,因而整体上观众们便不会太在意该人物相关的其它人物。在此可以发现,至少在河南地方戏中,脚色行当对叙事的效果造成了重要影响,应当像“情节”、“性格”、“视角”一样被列入戏曲叙事的诸要素之中。
《卷席筒》中得小苍娃为丑脚,而丑脚在众戏曲脚色之中有其特殊之处。其在产生只时就不是为了塑造人物形象或是推动叙事而出现“丑脚之命名大抵因其前身副净色表演风格轻松笑闹,以出丑、卖乖的喜剧形态示人,后又吸收了纽元子的伎艺之长,加之戏曲舞台上滑稽演员往往搽灰抹土,较旁人略显丑态,于是,此多重因素共同造就了一个‘丑字。”[1]总的来看,丑脚是对叙事文本的一种修辞,而修辞的词汇自身多数是抽象的而非具象的。在句子中这点最为明显,我们说“这是一支丑陋的笔”或是“几个漂亮的小姑娘在跳舞”当中作为修辞的词不可能是有具体形象的存在,扩展到戏曲文本,在观众对丑脚的认定中,丑脚被默认为修饰其它脚色或是整个剧情的存在,(例如,插科打诨对故事显然是一种修饰作用)因而其人物可以抽象化而不必成为剧中实存的角色。
二、以伦理为导向的叙事
《卷席筒》中,主人公本身缺乏足够的行动动因,也缺乏性格的变化,小苍娃唯一的行动动因就是“义”,对与其没有血缘关系的兄弟“曹宝山”及其妻儿之“义”,这点上照常理可以有文章可做,从故事情节来看,小苍娃的亲生母亲,以为小苍娃夺得财产为动因去谋害“曹宝山”之妻儿,而小苍娃为了“义”而保护“曹宝山”之妻儿,这里涉及到了“血亲”与“仁义”之冲突,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血缘关系是建立社会关系的基础,而孝道则是最重要的为人原则,而仁义则是社会伦理的最高原则,对于这些原则之间的关系讨论千年来争论不休,孔子似乎也面临过类似的选择。《论语·子路》中有这么一段话,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显然,以孔子为代表的传统儒家文化更注重血亲关系。《卷席筒》中,小苍娃明显是放弃了“血亲”以及建立在血缘基础上对亲生母亲的“孝道”而不假思索地选择了“仁义”。甚至有悖孝道的对母亲施以暴力行为,在母亲看望他时咬了母亲。即使母亲有罪,但是这种暴力也是在传统文化中难以接受的,又为何能在民风保守的河南地区得到认可呢?倘若从叙事符号的“标出”[2]原理来看,这种现象便很好解释,所谓标出,指的是在一对对立的范畴/项中,人们通常会把具有特殊意义的范畴/项加以标出,给与特别描述。在《卷席筒》出现的“血亲”与“仁义”这对项中,作者显然更想要突出“仁义”的意义,故而会将人物的行为做出更有利于表现“仁义”的特殊处理,而不是像《哈姆莱特》这样的文艺作品中常用的那样,让人物处于矛盾中摇摆不定,将内心的冲突展现给观众,进而引发观众的思考。“标出原则”与“展现内心冲突”除了会产生艺术效果差异之外,更多是文化差异,前者的目地在于利用“标出原则”建构观众的价值观,而后者在于通过“展现内心冲突”引发观众对人性的思考;前者是叙事者给予观众价值观,后者是叙事者引导观众自行产生价值判断。
三、叙事的背后是身份认同
戏曲艺术自身也是整个社会文化的象征符号,不同类型的戏曲、不同的脚色行当背后都隐喻着不同的社会身份。我们现在说中国传统戏曲中少有以丑脚为主角针对的是大剧种,而地方二小戏、三小戏其实有很多都是以丑脚为主角,但这类戏曲主要是以抒情而非叙事为目的。但曲剧的一大特征就是叙事,《卷席筒》最早产生于曲剧之中,开启了河南地方戏对于小人物的叙事,使得作为民众符号的丑脚从修饰语上升到了主语。但是作为主语的丑脚是建立在“众”而非“个体”基础上的。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历史意味着权利,意味着最高价值。唯有有身份的人物才能于叙事中作为主角,拥有有个性的权力。身份卑微的丑脚则多被塑造成类型化的人物,即使成了主人公,这一特征也难以改变。与此相关,出现在中国叙事中的“民众”不大可能有个体精神,这是中国文化之传统,也是中国艺术的传统, 如果想让作为修饰符号的丑脚以及其所代表的“大众”上升为主语,就必须赋予其某种“大众”某种共同认定的性质的理念,使其具有抽象品质的代表性。小苍娃似乎是观众自身某一理想的外在投影,而这种理想显然是基于“众”之基础,“众”不同于个体,只能是一般性的,抽象性的。从历史叙事的角度来说,无论是作为大历史叙事(历史剧),还是生活历史叙事(家庭剧),只可能是单线索的,单一视角的,观众与叙事者与主角三位一体的。这是一种对于生活真实而非艺术真实的追求,更深层次则是对自我认同的追求。一个与自己相似的“人”能够出现于舞台当中,便是身份上的承认。与此相对,切换叙事角度、区别叙事者与主角则很难让观众找到自我身份的投射点。无论是历史剧还是家庭剧皆是如此。
最后,河南观众在一开始就预设了他们理想中得戏曲模式中,一定要带有伦理价值判断,且伦理观念必须符合当地人的理想,不容任何质疑。一些剧目即使在产生之初破坏了传统伦理价值,也会在演出過程中被逐渐“修正”。例如,《李豁子离婚》本是为了宣传婚姻自由,以及女性的离婚权利,但是在不断的改编中已经成了对“李豁子”的同情,以及对离婚的讽刺。而这似乎可以解释为何在一些《卷席筒》演出中小苍娃咬其母亲的情节消失了,这个情节显然与多数河南农村观众(尤其是作为主要观众群体的家庭妇女)之伦理观念有所冲突。由此可见,由抽象理念外化成的角色是河南许多地方戏观众的要求,他们要在戏剧中看到自己群体“众”外化出的理想。
参考文献:
[1]丑脚与纽元子关系辨析[J].韩淑帆,四川戏剧,2016,04,48.
[2]参见赵毅横:符号学原理与推演[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