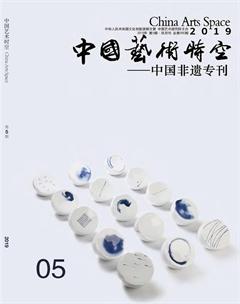南疆行
江东



2018年7月25日 周四 晴 和田
“中国艺术研究院舞蹈研究所南疆非遗舞蹈传承现状学术考察团”于今天启程。
第一站:和田。
下午,在和田机场,我迎来了大部队:从北京来的团队第二批团员们——刘青弋、廖燕飞、金娟、张提振、王诏。而我是前一天从乌鲁木齐和新疆师范大学音乐学院舞蹈系主任戴虎以及陈喆、桑巴一起飞来和田打前站的。
这趟南疆之行从几个月之前就开始计划了。院里主管非遗工作的王福州副院长从春節后就希望我们计划今年度(2018年)的舞蹈类项目,我就报了赴新疆考察非遗传统舞蹈传承现状的提案,得到了全力支持。闻讯加入的,还有山西长治学院的柴广育老师和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的郭小虎教授夫妇。
考察团最终于2018年7月26日相聚和田。
在当地文化馆的安排下,我们一行十几人首先参观了由文化馆布置的非遗陈列室。正值暑假,文化馆面对小朋友们开设了各种培训班,有手工艺、乐器和舞蹈。
文化馆楼梯墙壁上悬挂着一幅幅粮食画。一位维吾尔族手工艺术家发明了一种用粮食作物拼贴而成、以图案为主的美术作品。作物有核桃壳、各色豆类和米类。工作室里,一群维吾尔族小朋友围在这位艺术家周围,正在认真地排列粮食颗粒,煞是专注。
我问:哪个小朋友会跳舞?居然就有落落大方的小姑娘主动站出来了,手机里的音乐一响,她们立刻开始了扭动。且慢,且慢!你们跳的这是啥舞啊?怎么一点维吾尔族的民族风味都没有?原来她们跳的是流行舞蹈。再问她们这是从哪里学来的,答日:“抖音”。这时,一旁的维吾尔族长辈呵斥她们停下来,要她们为我们表演民族舞蹈,她们顺从地改换了。不过我想,舞蹈文化还能承继民族的文化血脉,对她们而言恐怕是一种无法理解的思维内容。看着她们那率真的表情,我还是坚持让她们按自己的心性去选择跳舞的方式,毕竟,对她们来说,舞蹈能带给她们快乐是最重要的。别的,等她们长大了再去理解、觉悟吧。
旁边就是一问舞蹈室,一群小朋友在学习民族舞蹈。从新疆艺术学院中专毕业的小老师在有模有样地教他们,虽然动作尚不是很复杂,但小孩子们的眼界和心灵都已被民族舞蹈所占满,相信这样的强化能让他们年幼的心灵上长满民族艺术的绿荫。
文化馆旁边就是和田歌舞团,但剧场上方的大字告诉我们,它的名字叫“新玉歌舞团”。后来得知,这是周总理当年给和田歌舞团起的名字,并一直沿用至今。听说了我们的背景和此行的目的,团领导立即拍板晚上九点为我们专门做一场表演。
这是一场非常有民族风情的歌舞晚会,显示了新玉歌舞团的水准,不错的阵容和对民族艺术的传承态度。虽然在理解和处理非遗传统的方法上还有待进一步提升,但其状态和规模,都超出了我的想象。这台作品使用了大量的当地非遗舞蹈素材,很开眼界,但过于舞台化的表达,在某种程度上让“非遗”的意味有所减损。这样的结果在全国范围内,倒是还蛮明显而普遍的。因此,如何处理非遗的传统,看来仍需在观念和方法上予以普及和引导。新玉歌舞团居然是两项国家级非遗项目的保护单位,其中,“莱帕尔”是一种融歌舞和表演于一体的艺术形式,非常活泼幽默,又被该团改编成颇具现代风格的形式,还上过央视春晚,一度名声大噪。
看完演出并与团方座谈之后已接近半夜。我们一行乘车连夜赶往需三小时才能抵达的于田县。
7月26号晴于田
于田县给我的印象跟和田市差不多,也是满地灰尘,这倒始终提醒着我身处的是沙漠边缘。上午我们驱车到了于田县文工团。于田县居然还有个文工团!这倒是出乎我的预料。
表演在一问有些密不透风的排练厅里举行,节目一个接一个地展开,大部分舞蹈都是当地非遗项目改编而成的,基本方法跟新玉歌舞团异曲同工。不过仔细想来,好像全疆的此类作品大同小异——同样的观念、同样的眼界、同样的手法。看来新疆的舞蹈若想有所突破,的确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表演分为两个部分,一是由县文工团的专业演员表演的创作性作品;二是由当地民间艺人表演的民间艺术形式。也真奇怪,县文工团的帅哥靓女们身着各色考究的服装,群舞人数众多,气势十足,却很少能感动我们。可那几个衣着简单、形象普通、且已不再年轻的民间艺人的表演,却让我们大呼过瘾。
于田赛乃木的自治区级传承人有四位,大都在六十出头的年纪。他们那充满自豪的神情和富有特色的表演风格,让我们看到了非遗项目的无穷魅力。他们的表演十分质朴、毫不做作,更没有过多的包装粉饰,完全靠舞蹈和音乐至纯的表现打动观者。它是通过形式来打动观者的,且形式又因地而异,多元的地域格局自会让艺术形式呈现出多元化的态势。而一个多元化的艺术格局,是世界的福音,本身便积淀着不同种族和不同地区人们的智慧。这,或许就是非遗保护事业的意义吧,它会让世界文化多样性不仅仅只是一个口号,而是可以用它独特的姿容来装扮我们这个世界的最佳材料。
下午,于田县文化馆馆长胡吉又把他们几位艺人聚在了于田郊区的农家乐,就上午的表演展开进一步探讨。只是,这些已经年过花甲的传承人,如何将自己的艺术传衍下去呢?这是我们提的问题,也是他们头痛的问题。现在的维吾尔族年轻人能够专注于此的后生可谓是凤毛麟角,民间艺人的技艺需要通过一些行政的手段才能让其获得传承的效果和结果。非遗项目的传承,可谓是头等大事,这也是设立传承人制度的初衷。而除了资金上的问题之外,年轻人的思想意识和好恶选择,都制约着这项工作的广泛开展。面对新的时代带来的挑战,还是应该多动动脑筋,设计出一些行之有效的方法。
于田博物馆被写成于阗博物馆。于阗国在历史上的演变,也让我们对于田这个地方在丝绸之路南线所起的作用非常感兴趣。这条路上,曾出现过从朱世行到法显再到玄奘等一干僧人的足迹,印度文明出了印度国之后进入中华大地的第一站,就是这里。因此,这里的佛教遗迹不少,甚至在于田文工团的演出中居然还有《佛国于田》的群舞。这里是中印古文明交汇的前沿阵地,也是丝绸之路南线的重要关口。于田,一个多么有意味的文化要地!
于阗博物馆的规模及其布展远比昨天在和田市看到的和田博物馆显然要好上许多倍(和田博物馆正在搬入新馆,由北京援建的新馆从外表看,条件应该还不错)。其中的展览非常不错,我们看到了一个曾经的于阗。一位维吾尔族解说员现身说法为我们展示了于阗的女式服饰,其中有一件深色的女式袍服,胸问的七道横杠说是跟萨满教或道教有关。可见曾经的于阗有佛有道,是一个文化多样性突出的地方。
晚九点返回和田的时候,天上开始落雨,当地人十分欢喜,沙漠里的雨水,宝贵如油。
7月27日沙尘墨玉
一早醒来,窗外一片浑浊。早饭后来到沙漠公路观景台,那天地一色的混沌,才让我们真正感受到沙漠的存在是何等不容忽视。
下午来到距离和田市20公里左右的墨玉县。
墨玉县是新疆的第二人口大县,去之前便得知该县的民间艺人非常多。墨玉文化馆馆长介绍说,墨玉经过摸底普查,共命名了339位民间艺人。他们大都是地道的农民,个个练就一身绝技,或演唱,或奏乐,或舞蹈,透露出维吾尔族人民在艺术上的天然禀赋。
四五十名民间艺人为我们表演,其中既有艾捷克弹唱、民间舞蹈、巴拉曼演奏,也有大型的麦西来普。麦西来普表演时,表演者全体登台,一干乐器悉数亮相;后面是乐队奏唱,前面是男女即兴捉对而舞,活脱一幅农家乐舞的现场展示。艺人们显然会彼此刺激,相互竞争,因此,现场气氛越来越激昂,情绪越来越高涨。难怪我们中有人说:真是高手在民间啊!
高手们身怀绝技,弹拨乐、打击乐、弦乐、管乐、演唱、舞蹈,无不精彩。其中弹奏艾捷克的老者是自治区级非遗传承人,他技艺精湛,演奏入神,不论是弹奏还是演唱,都让我们看到了传承人的那份自信和自足。巴拉曼是一种用硬质芦苇做成的吹奏乐器,形状像个小十字架,声音很是别致,特别有维吾尔族音乐的声音气质。吹奏者的年纪看上去并不大,显然这一项目传承有望。
麦西来普有不同的种类,主要是因为地域的分别让它们在形式上有了些微的区别。这个就像赛乃木和木卡姆一样,不同地区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就拿赛乃木来说,全疆有九种赛乃木,比如哈密赛乃木、于田赛乃木、库车赛乃木、喀什赛乃木等。木卡姆也是一样,我们最为熟知的是“十二木卡姆”,这种形式早已蜚声全球,成为人类非遗代表作之后,更多的人见识了它的精彩。除此之外还有刀郎木卡姆等。
墨玉也有一个木卡姆传承中心,是自治区政府拨专款修建的,硬件非常不错,体现出当地保护和传承木卡姆的决心。只是如今空间寥落、活动稀少,不知最终会如何发展。
晚上与新玉歌舞团联欢,大雨居然下不停,让我们本来计划在庭院中举行的“麦西来普”也只好进了房间。
新玉歌舞團的乐手舞者们,水平委实不凡,让我们在几天前见识到他们舞台上的艺术魅力之后,又见到了现实生活中他们的表演风采。新疆舞协副主席夏热帕提。热合曼是新玉歌舞团舞蹈方面的台柱子,也被称为“新疆舞蹈皇后”,她有着扎实的舞技和修养不凡的舞风,的确让我们看到了维吾尔族舞蹈的顶尖表演水准。正是凭借着这种舞艺,让新疆维吾尔族舞蹈自康巴尔汗自成一体的舞风之后一直延续至今,成为了一个十分完善的完整系统。
雨还在下,干涸的大地正在接受着上苍的慷慨赐予,而我们也正在用一颗饥渴的心,吸吮着维吾尔族文化的甘霖。
7月28号阴和田一莎车
早上九点离开和田,到达莎车时已是下午四点。
莎车县文广局对我们这次考察十分重视,午饭后我们便前往县政府,张副县长安排了非常正式的会议,县里相关部门的领导都来了,喀群赛乃木国家级传承人伊明。依比布拉也来了,据说他是当地该项目的核心人物。传承中心主任依拉木江介绍了喀群赛乃木的艺术特点和申报情况。他说:喀群赛乃木的动作比较柔软,这跟同地区其他项目中的舞蹈动作是有一定区别的,也是这个项目所独具的。
听完介绍我们越发急切希望一睹喀群赛乃木的真容。刚好县里为游客准备了一场,我们便跟着曹局长一起来到了莎车木卡姆传承中心。
传承中心有一个舞台,看来是用来表演木卡姆的,如今已经成为一个基本的表演区。二楼有些乐器陈列室和各种图片。传承中心在乐舞表演方面,有一个基本的群众表演阵容,其中既有耄耋老者,也有垂髫小儿。
演出是由民间艺人承担的,节目很杂,唱歌的,跳舞的,走钢丝的,甚至还有维吾尔族歌手演唱戏曲。当然,压轴节目是《喀群赛乃木》,也是整台的高潮部分。
喀群赛乃木是山区赛乃木之意,意思是指位于昆仑山边的喀群乡人民跳的赛乃木。喀群赛乃木由于其独特的表演,让它与其他赛乃木有所区别,特别是两个不同声调的小鼓奏出来的鼓点儿,让其节奏型有了较易辨识的声音形态。在舞蹈方面,我印象最深的是它的行进路线,是围绕一个大圆圈行进的,舞者会正向跳几个回合,再反向跳几个回合,然后正反交替。他们的方向转换异常整齐,显然是有什么让他们处在一个共同的认知中。总起来看,舞者沿着一个方向或正向或反向地前行,每个人又都有着自己的舞蹈方式,较为自由。虽然都朝着一个方向,但却是对舞,一男一女面对面而行,也就是说,一个进,一个退,彼此间默契而自然。至于动态,我并没有太多地看到它和其他赛乃木舞蹈表演上的差异。大圆圈中,是几对较为主要的男女舞者在跳对舞。其中,居然就有那两位与温家宝拥抱的老者。他们虽然已不年轻,却仍然步履畅快、身轻如燕。他们显然是舞者的主心骨,带领着队伍自如地变换着方向和节奏。
喀群赛乃木一场跳下来好像是有着四个节奏型,起初最难掌握的一种是8/5的节奏,做起来就是三步一垫,一垫是两拍,加起来刚好是五拍。这种节奏在塔吉克族的舞蹈中也很普遍。也难怪,他们都是昆仑山的居民,只不过一个在山这边,一个在山那边。
喀群赛乃木的另一个特点就是黑色高帽,女士会把围巾从帽子顶部系下来,很有特色。听传承中心主任阿依拉江介绍,这种流传在山区的帽子有两个作用,冬天保暖,夏天隔热。帽子的长度据说是标示主人地位的,还因为帽子是纯羊皮做的,因此它又是财富和威严的象征。
亲自开车走一趟莎车,对南疆的路线也熟悉了不少,从叶城到泽普再到莎车和麦盖提,构成了喀什地区的“南四县”。这四个县的维吾尔族民间艺术有一致性,也有彼此的差异,既相互呼应又独立存在。
7月29号晴莎车一喀什
早饭后,我们驱车去看了莎车的阿曼尼沙汗纪念陵墓。这位叶儿羌汗国的王后,就是“十二木卡姆”的整理者,今天的九套曲目,都与她直接相关,是举世皆知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项目。
陵墓对面是规模巨大的古代王宫建筑群,也是非遗博览园,虽然里面的非遗内容并不多,但建筑壮观,可以想见当年叶儿羌汗国的气势。
之后,我们便驱车来到了位于60多公里之外的喀群乡。
喀群乡文化站前,当地组织的喀群赛乃木表演队伍已经集结完毕,国家级传承人伊明。依比布拉也穿戴整齐,严阵以待。从县上来的传承中心主任一声令下,鼓乐齐鸣,歌舞争艳,身着亮丽衣裙的维吾尔族姑娘小伙们便一起上了阵。一时间,热烈的气氛便立刻升腾了起来。
印象最深的就是,这里虽然也有老民间艺人,但更多是年轻后生,满场活跃着年轻的肢体,让人感悟到这个乡的非遗传承工作非常有基础。一问才知道,县里为培养喀群赛乃木的接班人,已经先后组织培训了三代喀群赛乃木的传承者。如今,第一代都已谢世,第二代剩下六位,都来到了现场,除了伊明,其他人都是七八十岁的高龄了,那些满场飞舞的则是第三代。
第三代传承者显然已经具有了非常好的表现基础,在他们身上的那种民族味道真挚而淳朴,丝毫没有任何粉饰,因此他们的一举一动都非常朴实动人。也许他们并不知道自己有多重要——有了他们,赛乃木才有了未来。
场上最吸引眼球的是一对76岁的老艺人,他们佩戴齐整,特色鲜明的民族服饰,让他们看上去非常有活力。他们的舞蹈动作也十分自信自如,一举手,一投足,都绝不含糊,成为场上没有折扣的主角儿。
正如从昨晚的演出中了解的那样,喀群赛乃木总体而言是一个圈形表演形式。几对出色的舞者会在圆圈的中央面对面而舞,动作程式差不多,但自由度较大。倒是音乐上的特点更大,因为在诸乐手的前面,端坐着一位鼓手,敲击两个音高不同的小鼓,声音高亢、清脆,掌握着场上的节奏形态。歌者在乐手的后面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乐队系统。还记得传承中心主任介绍说喀群赛乃木的动作是比较柔软的,但从现场观察,这一特征不知为何并不是很明显。
告别了喀群乡热情质朴的维吾尔族村民,我们近九点抵达喀什大学,观看其举办的刀郎木卡姆传承培训班表演。
刀郎木卡姆据说是十二木卡姆的前身,在喀什地区的麦盖提县三乡十分盛行,因此,眼前的刀郎木卡姆表演是十分有历史感的。
木卡姆这个概念我们从十二木卡姆中已经有所了解了,那么“刀郎”是何意?这是个音译词,刀郎是一个文化区的概念,沿叶儿羌河流域展开。刀郎人是维吾尔族中的一个支系,有着自己独特的文化特征。也就是说,刀郎木卡姆,就是维吾尔族刀郎人表演的木卡姆。
之所以麦盖提的刀郎木卡姆艺人都集中到了喀什,是因为喀什大学举办的“国家艺术基金2018年度艺术人才培养项目《刀郎木卡姆艺术人才培养》”在喀什大学举办。该项目集中了目前最为活跃的几代刀郎木卡姆民间艺人,年龄最大的已是八十开外,最小的是一位学员的儿子,才九岁。他们之中的直系传承很多,爸爸传儿子,叔叔传侄子,这种家族传承的方法,对于刀郎木卡姆的传世,是有直接好处的。
他们为我们表演了九套刀郎木卡姆中的五套。高亢的声调和凝重的神情,都分外吸引人。从他们的表演中可以看到,所谓“九套”,每一套只是某些唱词和旋律有些差异而已。在舞蹈方面,其动态基本是统一的,分成四个不同的节奏型依次展开.切克托曼、赛乃木、塞勒凯斯、色立尔马,再加上序(木凯迪满)和结尾时的竞赛式旋转,就完成了一套曲目的周始。据老艺人介绍,在最后一段的旋转中,舞者和乐者常常会相互竞争——谁先停下来就算谁先认输,因此这一段看起来是很引人入胜的,也是一个结束前的高潮。从上述刀郎木卡姆的节奏型结构中可以看到,我们这几天一直热议的赛乃木,不过是刀郎木卡姆中的一种节奏型而已。也就是说,赛乃木可以独立成章,也可以被集大成的木卡姆纳入到自己的表演体系中来。
此次观摩活动的最后环节,在热闹的麦西来普中结束了。
7月30号晴喀什一塔什库尔干(塔县)
在喀什,仍然住在其尼瓦克酒店。
中午12点半我们驱车前往喀什地区歌舞剧团观看表演,但只看了一个叫做《喀什赛乃木》的男女集体舞。从团长那里得知,这个团居然是1934年成立的,已有84年的历史了。该团目前有一百多位表演者,而且都是事业编,每年有多达350场的演出,但几乎都是政府出面购买。
这次行程的全过程好像都有这个情形:看原生态的非遗項目,我们总是十分兴奋;而看专业舞者的表演,却总是无动于衷。这是不是跟这些专业作品的创作观念和方法有关呢?如何从艺术的形式来展现我们原本就十分生动非凡的民间歌舞,这是需要我们进一步深思的。
午饭后,我们驱车前往一个此行中最为神秘的地方——塔什库尔干,我们通常也简称为“塔县”。
从喀什出发,大约要六七个小时才能到塔县。一路上不断有人要求下车拍摄,群山雪峰、湖泊溪流、牛羊骆驼,美到不可思议。
与塔县文化馆馆长都力昆老师联络,得知晚上在塔县有一场民间性质的篝火表演,届时会有当地群众自娱性的表演。经过了各种关卡和检查站之后,我们终于有惊无险地于商定时间抵达了塔县。
进入塔县,路边那些身着塔吉克族服饰的普通路人尤其吸引我们的视线,女性戴在头顶上的平圆小帽和围巾,民族特点十足。塔吉克族民族服饰本来就是国家级非遗项目,生活中呈现出来的韵味也的确无与伦比。近距离接触塔吉克族的男女,会立刻发现他们容貌上的独特性——塔吉克人是我国唯一的白种人,属于欧罗巴血统、高加索人种,因此他们的面孔特别像西方人。
我们到达时,已是晚上十点,天还是很亮,因为要点燃篝火,因此还要等待天黑。不过一拨一拨的塔吉克族男女老少已经慢慢聚拢了过来,天黑了,清脆的鹰笛声和激越的手鼓声响起来,身着盛装的塔吉克人动起来了,动感无限、富有特点的舞动迅速点燃了现场。不一会儿,一对“新人”出现了,他们在“亲戚们”的簇拥下,来到了红毯上。这可能是让观众感受他们的婚礼形式吧。塔吉克族婚礼也是国家级非遗项目,据说他们的丧礼也是。
塔县是拥有国家级非遗项目的大户,喀什地区有9个国家级非遗项目,其中6个就在塔县!我们要仔细了解和观察的“鹰舞”也在其列,除此还有塔吉克民歌等项目。
篝火被燃着了。随着音乐的不断推进,开始有人跳起带有“鹰”动态和气质的舞蹈,虽然不算复杂,但一看就是在模仿鹰的神态。塔吉克族自认为是鹰的后代,他们对于鹰的图腾崇拜简直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酒店毛巾上印有鹰的形象,大街上有鹰的雕塑,博物馆里有鹰的文化介绍,歌舞伴奏中有声音独特的鹰笛,塔吉克族与鹰的天然联系让你一眼就可以捕捉到。
“鹰舞”被列为国家级非遗项目,也是这一鹰文化的集中体现。
7月31日 晴 塔县
我们走进了塔县歌舞团,并受到团长苏琴女士热情的接待。在其安排下,我们观摩了两个舞蹈作品,一个就是大名鼎鼎的《鹰舞》,由四位男舞者表演;另一个是男女群舞《帕米尔的欢声》。说实话,这些作品中还是有上述提到过的看专业歌舞团时相同的感受。看来,对于非遗的认识,还有待于我们的专业编导深入思考,毕竟,那是文化的根。
那个男子四人舞《鹰舞》,显然是他们的保留剧目,毕竟这个团主打的就是当地特色。这个专业作品看上去显然是经过包装的,男演员身着统一的服装,灰白相间的宽大袖子,做成了齿状的鹰翅形状。服装是特意设计的,但审美效果并不太妙,甚至给人以装饰过度的感觉,而且还弱化了塔吉克族的民族服饰符号。
在结束前,歌舞团又安排我们去音乐排练室看了该团乐队的排练,乐手们用纯塔吉克式的乐器为我们演奏和演唱了《花儿为什么这样红》等歌曲,置身于这首歌的家乡,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只是不太明白为什么一定要用少数民族乐器演奏《喜洋洋》这类汉族通俗音乐,完全没有感觉。
位于歌舞团对面的是博物馆。博物馆里有一个民俗馆,里面关于塔吉克族文化的相关陈列,让我们大开眼界,也为我们解了不少惑。回想此行我们曾看过好几个博物馆,不管是地区级的,还是县级的,都很有价值,会让观者立刻掌握当地的基本文化情况。想来国家这些年来在文化设施上的投入是非常巨大的,各级文化部门几乎都会修建设计讲究、投入巨大的博物馆、文化馆等设施,许多博物馆的建筑都已经成为地方的地标。不过以过客的眼光来打量,似乎这些投入巨资的文化场馆尚未能发挥应有的作用。
都力昆老师为我们安排了去塔吉克族民间艺人家里探访的日程,午饭后,我们便径直来到了提孜那甫乡。
作为全国唯一的塔吉克族自治县——塔县,是一个拥有最长边境线的县,下辖有12个乡,大都分布排列于中巴和中塔边境地带,完全是地广人稀,以高海拔的山区为多。离县城最近的乡就是提孜那甫乡和塔什库尔干乡,这两个乡的人口也是最多的。
这是一家典型的塔吉克人家,老父母和儿子一家一起生活,儿子育有一儿一女,老父母的其他子女也都住得不太远。老父母的儿子在热情招待了我们之后,便和他召集来的艺人们盛装以待,等大家都装扮完毕,瞬间,醒目的塔吉克民族气质便漾满了周遭的环境。
一声鼓鸣,示意着歌舞表演即将开始了。顿时,鹰笛彻响,舞姿婆娑,热闹的气氛立刻蔓延开来。民间艺人们你方登台我再亮相,纷纷拿出自己的歌舞绝活。昨天在塔县歌舞团观摩时,听到编导阿里甫夏说过塔吉克族除了有著名的《鹰舞》之外,还有《鹰和孔雀舞》《鹅舞》《马舞》《刀舞》等,当时我们希望他能把提到的这几种舞蹈形态都简单地表现一下,他说他不会。没想到在民间场合,竟然看到了《马舞》的表演,类似于汉族《跑驴》的形式,演员套在一个有着马头的木质道具之内,表演起来其形态也类似于《跑驴》。我们看到的塔吉克族《马舞》,是由两个民间演员拥着两个马头道具在相互地绕着圈子,最后还手拉手地彼此嬉戏起来,给人以一种十分幽默、十分欢快的感觉。
盛装表演的塔吉克族民间歌舞,给我们留下了非常难忘的美好印象。
8月1日晴塔县·喀什
从文化馆馆长都力昆老师那里传来好消息,国家级鹰舞传承人买热木汗。阿迪力女士在他的劝说下从喀什回到了她的家乡——木林场,并接受我们的拜访。
远远地,一位身着黄色衣裙的妇女在路边站着。等我们的车抵近,才意识到,她就是买热木汗老人。66岁的年龄看上去依然健硕,黄色的塔吉克族服饰和首饰将她装饰得分外端庄。
买热木汗是2007年被授予国家级传承人称号的,这在新疆来说是一件大事。她家里摆着各种荣誉证书和图片,其中还有一张是2015年她被北京舞蹈学院民间舞系邀请去教鹰舞的图片。提起那些往事,老人十分动情,她那么真挚、自然,让人不由得感佩和动容。
当然,她真实的情感还反映在她对非遗项目的执着。她表示,愿意义务传授给新的一代她所掌握的全部。而围在她身边的许多孩子,也让我们看到了她努力的结果。孩子们说,她为他们购买民族服装,教他们跳舞唱歌,让他们把她的家当成自己的家。看得出来这是一位有爱心的民间艺人,对她的民族有爱心,对非遗项目有爱心,对祖国有爱心。别说,孩子们中还真不乏跳得不错的男孩女孩,相信伴随着他们的长大,买热木汗老人的心愿一定会在他们的身上得到回报,民族文化的基因也一定会在他們的心里开花结果。
身着艳丽服饰的小朋友们开始了他们的表演,在音乐声中,他们舞姿简单、充满了童真和稚气,却有着十足的民族味道。
这边厢,我们正在买热木汗的院子里与她的徒子徒孙们欢乐着;那边厢,不知何时多了一位老婆婆。这位塔吉克族老婆婆左胸前戴着一枚共产党员的红底黄字胸章,十分醒目。老婆婆起先只是默默地坐着,随着我们这边气氛越来越热烈,她好像也坐不住了,抬起一双渴求的眼神,希望我能请她一起跳。一跳起来,她舞步之轻盈、动态之美妙,完全出人意料。她投入地舞着,满足感十分明显,也感染着我们。跳了一阵,老婆婆歇了下来,她拉着翻译告诉我们,她曾经是个非常好的舞者,甚至比买热木汗都棒许多。当然,一旁的买热木汗对此颇有些不屑。只可惜买热木汗老人腰有伤病,不能全身心地跳舞,我们也就失去了一饱眼福的机会。买热木汗老人提到交孜克的鹰舞,据说已经有了很多变化和发展,但她非常不同意这种变化。但是交孜克则认为年轻一代自然应有年轻人的处理方法。这种代际差异,当然也是传承中常见的问题。新一代在传承非遗项目时,是否可以有自己的主张和做法,对于这个问题,不但非遗公约认为是可以的,我在实践中看到的情形也是没有问题的——目前所见的交孜克鹰舞仍然未脱离塔吉克族文化根基,是一种非常有民族文化主张的表达。
这可能就是非遗传承所面临的两难境地,一方面它要尽可能地保留住从历史上传承下来的文化遗产,另一方面又面临着时代的变迁、审美趣味的嬗变,孰重孰轻,是需要慎重掂量取舍的。
买热木汗老人坚定地希望将传统原样传续下去,为此,她付出了最大的努力:没有场地,她就在院子里带着孩子们跳;没有鹰笛伴奏,她就放录音;一些必要的花费,都是从她自己的腰包里掏。我们查了一下资料,发现买热木汗老人居然是贫困户,致贫的原因一栏中写的是疾病等原因。的确,她家的生活条件是非常简陋的,但买热木汗老人的精神显然是十分充实的,因为她不但有9个孩子和23个孙子辈,心中还有一份伟大的非遗保护事业。
临别时,我们的车启动了,老人松开紧握着的手,车子渐行渐远,那袭黄色的衣裙依然在风中飘曳……
8月2号晴阿图什(克州首府)-乌恰-喀什
南疆实在是太神奇了,每到一个地方,便能看到一种迥异的民族文化气质和景象。今天一踏进阿图什市的地界,便立刻感受到了柯尔克孜族的独特民族文化氛围和风景。
南疆总共有三个主要少数民族:维吾尔族(刀郎人)、塔吉克族和柯尔克孜族。到了阿图什,也就了了我们最后一个心愿:三个少数民族我们看全了。
克州的全名叫“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这么复杂的名字,一般人还真不易说明白,于是,大家都以“克州”称之。
我们的第一站是自治区歌舞团。
这真是一个非常气派的建筑,据说里面集中了四个馆、一个团。四个馆是:文化馆、美术馆、博物馆和档案馆,一个团就是自治区歌舞团。器宇轩昂的大楼有棱有角的,墙壁上镶嵌着柯尔克孜族的特有图案,据说是根据鹿角的形状设计而成的。身为柯尔克孜族的阿依佳老师介绍说,柯尔克孜族人民的动物图腾有鹿、鹰和雪豹,因此根据鹿角设计的图案就成为最为常见的民族符号了。
歌舞团虽然非常忙碌,但还是抽调人手为我们安排了几个歌舞节目:两个舞蹈作品,两个音乐作品。两个音乐节目非常棒,第一个跟“玛纳斯”有关,是一个创作性质的音乐弹唱。乐器很别致,柯尔克孜族特有的弹拨乐器——库木孜琴引起了大家的兴趣。第二个节目是库木孜表演,身着民族服装的七个弹拨手共同奏响库木孜琴,那种纯馥的民族馨香立刻在整个空间中回响,的确让人着迷。
相较于音乐节目的精彩,舞蹈节目就逊色了许多,一是舞者水平不高,二是编得也一般。此次南疆行,看过了不少专业的歌舞表演团体,虽然我对他们的表演状态很有微词,但表演阵容还是说得过去的。第一个作品叫《美丽的姑娘》,第二个是《库木孜情》,完全乏善可陈,只能算是看到了一些民族服装而已。因为这些服装头饰在设计包装的性质上已经非常舞台化了,从中也很难判断和捕捉到柯尔克孜族的文化符号及其意象。倒是表演之后的交流给了我们一些基本的信息。该团有61名团员,舞者有28位,每年的演出大都是政府购买服务,所以下乡演出是最重要的任务。对于创作,他们会根据如今观众的喜好,改造原来的一些固有表达方式,因此,会对民间舞的传统有所变化。
接着,我们又去到乌恰县。
来到乌恰文化艺术中心,一座挺不错的剧场,但管理很差,舞台地面翘起,天花板漏雨,的确是非常可惜。克州非遗中心的领导特意事先为我们安排了一些乌恰县的民间艺人,让我们得以近距离地接触到柯尔克孜的民间表演艺术。
据克州非遗中心领导介绍,克州共有一项“人类非遗代表作项目”,即“玛纳斯”和四个国家级项目:驯鹰、柯尔克孜服饰、库木孜弹唱和约隆。在排练场里,我们首先欣赏到了人类非遗代表作项目——玛纳斯,先后有几位男女“玛纳斯奇”(奇是“表演者”的意思)用他们的歌喉展现了这项世界闻名的表演艺术的风采。这是一种用一个固定的音律和句式来展现玛纳斯英雄行为的表演形式,据说一共有八部,如果全部唱完,几天几夜都不一定能完成。《玛纳斯》是由柯爾克孜族国家级传承人居苏普。玛玛依整理出来的,目前已经用多种文字翻译出版。
紧接着,我们又欣赏了口弦表演和库木孜演奏。口弦表演者的手上,牵了一根绳子,绳子分叉成三根绳,分别连着三个鹿形的小玩偶,表演者每弹拨一下口弦,三个小鹿便会被牵动。
库木孜的演奏是很让人开眼界的,技术之繁复、声音之动听,听上去非常具有艺术意味。之后由县文工团的四位女舞者表演了四人舞《鸳歌鸳舞》,里面大量的地方性舞蹈动态,给了我们一个了解当地柯尔克孜族舞蹈形态的机会。这四位没换舞台表演服装的县级女演员,其表演要好于上午看的州级歌舞团演员,至少是表演比较在状态,还是有一点“专业”感觉的。
考察团全部日程的最后一天,我们有机会看到了又一个民族的非遗现状,所看所感一定会直接作用到我们未来的学术认知及思考之中。
8月3号晴喀什一乌鲁木齐
小结:
九天,在一年中很不起眼,在人生中更是不足挂齿。我们一行人却利用九天的时间进行了一次难忘的学术考察。
目的地:南疆。
考察目的:非遗传统舞蹈的传承现状。
考察内容:南疆各族非遗传统舞蹈及其音乐。
路线:和田、喀什、克州(新疆南疆三州)。
人数:13人。
匆匆九天光景,通过走马观花的行走和观看,让我生出以下几点感受和认识:
一、对于非遗保护工作的认知与信心。
新疆,这片遥远的土地在我们固有的思维中总是拥有太多的侧面需要去用心揣摩,虽然多次到访,但要想完全撩起它的面纱、掌握它的各种不确定性却并非易事。因此,要对一个文化现象有一定的认识,必须在时空两个方面都花费一定的量才有可能获质。
南疆,相较于其他新疆地区更为神秘,对于这块土地上的文化现状的了解就更为迫切和难能可贵。通过九天的走访,我们看到了南疆在非遗保护工作方面做出的巨大成绩。各级政府文化部门都在很好地贯彻中央关于非遗保护的方针政策,让这一工作得到了有效的落实。
因为是少数民族地区,南疆的非遗舞蹈项目不少,我们一路看到的所有传统舞蹈项目,几乎都得到了很好的保护和传承。而每每看到非遗项目传承者在新一代中的崛起,都会让我感怀:有了这样的传承,还愁我们的传统舞蹈会变色、会消失吗?
因此,我们对于南疆非遗舞蹈传承现状的总体看法是积极的、乐观的。
二、反思与建议。
在各级文化部门,都设有非遗保护的专门机构和人员,他们的尽心尽力自然让当地的非遗保护工作得到了正面的评价和肯定。各层次传承人的利益都是能够得到保障的,因此,传承人也都能为这项工作付出自己的心力。然而,传承人也面临着很多困难,从传统舞蹈的角度着眼,传承人还是缺乏一些条件的保障,比如场地、伴奏、服装等,如果让传承人能得到这些保障,他们的积极性会被更好地激活,传承效果自然会更好。绝大部分传承人都会有十分自豪的心态和稳定的价值观,这当然会给他们带来正能量,但如果一些基本的相关物质条件不能保障,这个热情也会受到影响。
在上述的考察中,我们分析了在非遗分类方面某些项目所面临的尴尬和不妥。因此,更为科学合理的分类方式,会给我们的非遗保护工作带来积极的推动效果;反之,只会空耗我们的气力,形成不必要的浪费。
在较为基层的政府文化部门,由于人手不够和人力资源水平的不整齐,致使对政策的理解和对实际问题的操作都存在不太平衡的结果,这很大程度上制约了非遗保护事业的整体前行,应该继续合理地展开培训工作,让传承民族文化基因的宏伟目标更好地落地。
弘扬和宣传非遗项目,仍是非遗保护工作的重中之重,让广大群众“看见”非遗项目,会激发社会在保护工作上的积极性。应该团结所有可能的力量集中于这一事业,形成合力来推动这一事業的不断发展。
应该进一步大力推进非遗进校园的宣传力度,让更多的非遗项目作用到我们的育人环节之中,并从小培植出保护非遗的心智和自觉,这会对非遗保护事业的长久机制带来理想的土壤。
通过考察,我对设立“新疆非遗传统舞蹈生态保护区”的动议持积极支持态度,并相信新疆会成为非遗传统舞蹈保护的有力推动者和实践者。
短暂的新疆非遗传统舞蹈传承现状学术考察工作告一段落。行走和观察中,我们思忖着非遗保护工作的效果及其把控力度,这一工作必定会随着它在步骤和策略上的进一步完善而显现出对于我们国家在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方面所做的设计和努力的正确性,同时更会对中国人民不断增长的精神需求带来正面的呼应和满足。
路漫漫其修远兮,非遗保护工作是百年大计,呼唤着我们在思想认识判断和组织操作手段上的卓越才能。于此,南疆行给予了我们十足的信心。
(责任编辑:姜玉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