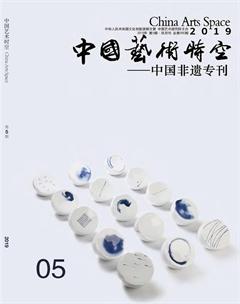现代生产与传统样式
唐然



【内容提要】新中國成立后,花丝镶嵌作为出口创汇的支柱产品之一,成为国家重点扶持和发展的特种工艺之一。在经过合作社、并厂等社会主义改造后成立的北京花丝镶嵌厂,其花丝镶嵌这门传统手工艺实现了工厂化的大型生产规模及管理运作方式。本文以对北京花丝镶嵌厂的生产模式、经营模式、分配模式的调查入手,结合对当年花丝厂生产的产品的样式设计及工艺表现特征的分析,探寻基于规模化“生产”和国家集中管理下的手工艺生产方式,对工艺本身、产品的设计及艺术质量等会产生怎样的影响,以期对传统工艺的现代生存方式提供参考。
【关键词】花丝镶嵌 现代工厂 艺术质量 传统样式 设计
花丝镶嵌,是“燕京八绝”之一,以金、银等金属材料,拔成细丝,经过堆、垒、织、编、掐、填、攒、焊等工序,并结合点翠、烧蓝(珐琅)等多种装饰工艺手法,制作成精致、纤巧、华美的金银制品。
花丝镶嵌一词是建国后在北京的手工艺生产合作运动中产生的,古代一般以“金银细金工艺”来指称各种与金银有关的制作技艺。在清宫造办处留存的档案中,可以看到当时有对累丝作、镶嵌作、錾花作等工种的记载。现在的花丝镶嵌工艺既是将这几种金银器制作技艺整合为一个行业的结果。
在新中国成立之前,除宫廷中特设的为皇家服务的内廷制造机构是进行有组织、有规模的集中生产外,民间多以个体作坊为主要产业模式,规模略大的有银楼,可以兼具生产和销售。建国后,工艺美术产品成为我国出口创汇的支柱产品,其中尤以特种工艺为翘楚。因此诸如花丝镶嵌这类特种工艺成为国家重点恢复和发展的行业对象。在政策和资金的倾斜下,北京的花丝镶嵌经过合作社、并厂等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北京花丝镶嵌厂(以下简称花丝厂),形成了千人以上的工厂式大型生产规模。这在我国金银细金工艺的生产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在这种集中的、规模化的对“生产”的追求下,对花丝镶嵌工艺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又生产出了什么样的产品,这是本文以对当年花丝厂生产的产品的样式设计及工艺表现特征的分析结合对花丝厂的生产模式、经营模式、分配模式的调查所想要探求的问题。
一、花丝厂概述
1955-1956年,北京的花丝镶嵌业由一家一户作坊式的个体劳动,相继组织起公私合营的北京花丝厂、北京第一和第二花丝生产合作社、北京第一和第二镶嵌生产合作社。在此基础上,1958年将北京花丝厂、两个花丝社和两个镶嵌社合并,建立集体所有制的北京花丝镶嵌厂,正式确立了以现代工厂体制进行花丝镶嵌工艺品生产的生产方式。
建厂后,花丝镶嵌工艺得以快速恢复,北京成为中国花丝镶嵌工艺品生产的主要产地,花丝厂成为出口创汇的主力军之一,为当时的新中国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花丝厂的生产进入巅峰时期。八十年代由于国际市场环境的变化,花丝厂的生产和体制曾遭遇波折,1984年7月,花丝厂分厂,划分为北京花丝镶嵌一厂、北京花丝镶嵌二厂、北京花丝镶嵌三厂和北京贵金属材料加工厂。1988年又合并为北京花丝镶嵌厂。在2002年花丝厂解体前,在厂职工尚有1400余人,厂区占地面积29325平方米。
二、现代生产与传统样式
对花丝厂的调查分为以下三部分:生产管理、业务运营、分配方式。
(一)生产管理
为了适应这种规模化、集中的工厂生产方式,北京花丝镶嵌厂在花丝镶嵌产品的生产方式、工艺及相对应的生产管理体制上做了一系列的调整。
首先对花丝镶嵌的制作流程和工艺进行拆解。在个体作坊生产时期,花丝镶嵌产品是可以在一个人手中完成全部部件的制作。到了工厂化生产时期,花丝厂把产品制作流程按照工艺实施步骤,分解设定为以下环廿.设计→打样→样品检验→制胎→花丝→黑胎检验→清洗→烧蓝→镀金→实镶→组装→质检
其次在人员及生产管理上,对每个环节都设置对应的生产组、车间,参与生产的在厂职工按照各组所需的人员数量,被编进各生产组。生产组又按照工艺、生产性质被编进不同的车间。
每个车间设有车间主任、调度、出纳、统计等管理岗位,分别负责车间的生产调度、人员管理及财务管理工作。车间主任和调度,根据订单和车间里生产组的具体情况来安排生产。有的订单由一个生产小组就可以全部完成,有的则需要两个甚至更多的小组来配合完成。每个生产组也有组长,负责统筹、分配组内的生产任务。至此,北京花丝厂初步建立了工厂化的生产和管理系统。
同时,这样一种分工明确、流水线式的生产方式还体现在花丝厂对于空间的划分及空间功能的设置上,在产品的形式和工艺上也有所体现。
1958年成立花丝厂以后,即从城里搬迁至通州区(当时称通县)大成街1号,原通州州治衙署及三教庙的区域,在古建的基础上按照工厂功能进行了拆改。因此花丝厂的厂区内既有四层的工厂生产楼,也有文庙、大殿、金水桥、燃灯塔等传统古建。80年代,花丝厂的占地面积达到29325平方米,建筑面积23802平方米。原用于生产的都是平房,在朱德两次视察后,亲批花丝厂盖造了四层的生产大楼。据当年在花丝厂从事管理工作的周洁师傅回忆,建筑的一层是原材料库房以及失蜡浇铸和蜡模加工;二、三、四层分别是工艺加工部分的一、二、三车间。一车间是镶嵌车间,二车间是花丝和胎活制作车间,三车间也承担大量的花丝制作。每个车间都设有检验组,负责车间黑胎的质量检验工作。另外还有负责烧珐琅、电镀等辅助工艺车间。除了这些主加工车间,花丝厂还设有原材料的检验室,原材料加工车间,机加工车间,包装组等辅助单位。除了这座集中用于生产的四层建筑,厂区内还配有烧制煤气的区域以及图书馆、培训教室等专门空间。
与上述生产流程及生产空间相对应的,当时的花丝镶嵌产品在设计、构成方面也都体现出分工协作的特征。
花丝厂产品主要为摆件和首饰两大类。摆件,又可分为动物造型、建筑造型、人物造型、花鸟鱼虫及器皿。所有的摆件构成均可分为两部分,一是主体部分,既以花丝镶嵌等细金工艺为主制作的、用以表现主要内容的部分;二是底座,一般是木质雕刻,在起到底座作用的同时,往往也会承担部分“配角”的作用,比如鸟兽脚下的“岩石”“树枝”,或是与鱼、莲一同出现的“浪花”“水纹”等。
这样的构成方式既在造型上合理,又具有了實现生产上分工协作和批量化的功能。花丝车间负责制作主体部分,与此同时,包装组负责去木雕工艺厂联系制作底座。主体完成、底座到位后再整体回到包装车间进行装配和包装。
具体到一件摆件的制作则会采用“单元”的方式,不同“单元”有时还会采取不同工艺和不同材料。以人物摆件为例。生产组会制作几种不同样式的手、头以及躯干、衣饰,然后进行不同“单元”问的排列组合,形成多样的产品序列。人物的手、头常采用象牙或骨头,以牙雕或骨雕的工艺制作,躯干和衣饰则为金银质地,以锤揲或者花丝工艺制作。同样的情况还被用在鸟类摆件的制作上。生产组往往会根据几种常用的鸟禽及其常见姿势,提前制作出相应的几种不同样式、规格的腿和爪,如抓握状的、伸展状的,然后在不同姿态的鸟形摆件上搭配使用。
“单元”做法也用在了成套系的首饰上。如一个椭圆状的“单元”,以螺丝、码丝或其他花丝手法围圈,中间镶宝石。这样的一个“单元”,后面焊接戒圈为戒指,后面接针为胸针,数个单元连缀,可成手镯或项链。
这样做的好处是节省了打样的时间和成本,丰富产品形式,通过不同的搭配组合可以衍生出整体一致、细节有差异的“系列化”产品,同时提高了生产效率。但也经常出现形象风格过于同质化的现象,如在仕女摆件中,来自不同时期、不同故事脚本中的女性面容、发饰及其服饰、装扮几乎如出一辙。
在生产工艺上,花丝厂对生产设备及具体工艺也相应进行了创新、引进和调整,以适应规模化的生产。
使用焊枪代替吹筒,并配比使用新的焊药,实现了较大型的花丝摆件产品的制作。1965年从意大利引进制链机,可以生产制作最小丝径为0.2毫米的细链;1971年,在拔丝、轧片的工序上实现了机械操作;同年,花丝厂还自主制造了机械套泡机和机制链点焊机,提高工效4.3倍;1973年又制成多功能掐边机、梅花瓣成型机、砸蓝机、轧丝机;1975年,制成掰蔓机以及自动套泡和轧条机;1976年采用中频熔炼并与拔丝、轧片设备连接建成生产线。
花丝厂通过技术改良和设备引进,在某些制作环节实现了机器化或半机器化的生产方式,配合分工协作、团队作战的生产管理体系,制作完成了很多按照传统制作工艺无法实现的花丝产品:如这一时期集中出现的《祈年殿》《故宫角楼》《黄鹤楼》等大型古建题材摆件。这在过去的技术和生产条件下是不可能的。
这些新的设备和工艺为实现数量大、质量稳定的产品奠定了技术基础,也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加工的成本,同时也拉开了产品序列问的差异。很多低档、小型产品的设计都会优先考虑使用机加工的工艺,比如一些小型摆件、器皿和首饰上大量使用的套泡丝等,既降低了产品的生产成本,又不失花丝工艺的特征。
同样,高效规模化的生产也带来了产品艺术质量的明显下滑。很多工人只能接触一件活的一部分,反复做同一个部件,不断使用同一种工艺,对产品的整体工艺配合和艺术完整性的认识就很难建立。因此在很多量产的产品里都可以发现件与件之间、产品与样品之间巨大的工艺和艺术质量的差异。
事实上,花丝镶嵌工艺在历史上已出现分工协作的制作方式,如造办处的档案中提到累丝作、镶嵌作既是如此,一件器物的完成也需要几个部门的工匠的通力协助。因此将当时的花丝镶嵌产品的艺术质量下滑完全归咎于分工的生产方式也是有失偏颇的。影响艺术质量的更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工厂化的生产管理方式所带来的质检标准也是工厂式的,即以可量化的生产技术指标为主要衡量标准。例如在北京花丝镶嵌厂参与起草的中国轻工总会批准实施的GB/T2062-1994号贵金属饰品标准里,对贵金属首饰产品的工艺、材料、重量都做了规定。只要这些技术上的硬性指标过关产品就算合格。涉及到艺术质量的语句表意抽象模糊,且多归到工艺要求中进行描述,如“掐丝流畅自然,填丝均匀平整”“錾刻花纹自然,踩錾平整,层次清楚”等。对于产品的整体造型仅有两条:“整体造型符合图纸要求,造型美观,主题突出,立体感强”“图案纹样自然,布局合理,线条清晰”。至于美观、自然、合理的具体标准就只能视检验者的审美标准而定了。
这与历史上对工艺美术的观念和评价体系十分不同。以清代为例。翻看清宫造办处留存的档案,会发现当时的统治者对器物的艺术形式十分重视。雍正一代将造办处的器物风格立为“内廷恭造式”,认为其是清朝统治理念和皇帝政治理想的一种延伸和象征。档案中记录了历任皇帝对于造办处所造之物的艺术形式创作的直接参与情况。以雍正帝的“雍正御笔之宝”为例,为了得到满意的印文“设计”,雍正命翰林张照、技艺人滕继祖、南匠袁景劭和刻字人张魁分别设计一稿,呈览后予以点评。四人得旨后又设计了两至三张样稿呈览,最后雍正取四人设计的优点集于一体,共同呈现在印章上。
“于正月十九日翰林张照篆样一张、技艺人滕继祖篆样一张、南匠袁景劭篆样一张、刻字人张魁篆样一张,怡亲王呈览奉旨:张照篆样文范,但笔画微细,照袁景劭篆书,其笔画另篆,再滕继祖篆样上‘之字篆法好些。”
“于正月二十二日翰林张照篆样三张、技艺人滕继祖篆样三张、南匠袁景劭篆样三张、刻字人张魁篆样三张,怡亲王呈览奉旨:准张照古篆‘雍正御笔之宝,将‘之字下横平平,选吉时照样镌刻,钦此。”如此这般的旨意还有许多。从中多少可以看到古人对器物艺术形式的重视,并会对其进行有针对性的、具体的指示和建议。
技术质量不仅是评判产品质量的标准,也成为了衡量工人技术水平的重要指标。在《中国细金工艺与文物》中杨小林老师整理了一份1983年北京花丝镶嵌厂对1-5级花丝工人制定的部分技术指标。表格中显示对于工人的技术评级,仅看是否能制作出相应的产品,而无对所制产品艺术性高低的标准和说明。在《18K金饰品工艺生产操作规程》中对各项材料、结构及技术都做了详细的数据化的要求,对艺术造诣方面则仅仅用了“艺术效果强,整体造型完整、布局合理;丝线条流畅”等抽象模糊的字眼。企业管理人员也基本以技术难度、作工粗细、工时多少来作为衡量和评定工艺品优劣的唯一(而不是某一方面)标准。有的外贸业务人员也以此作为评定收购价格的唯一(而不是某方面)标准。在对技术的不断强调下,整个社会逐渐形成了对工艺品套路化的艺术评价体系:栩栩如生、惟妙惟肖、巧夺天工。
(二)业务经营
花丝厂的业务经营范围与经营方式在建立之初就有其历史特殊性。建国后,我国急需外汇来支援国内建设,而工艺品是当时我国出口换汇的主要支柱产品。据《北京志。对外经贸卷·对外经贸志》的记载显示,1950年至1956年工艺品的出口额占总额比重100%,1957年占96%,直至1958年才由单纯的工艺品发展到纺织、粮油、土畜、轻工业、五金矿产等几大类产品。北京的工艺美术产品是我国扩大外贸出口,换取外汇的主要市场。花丝厂就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由外贸公司和工业部门协作,建立的一批专门生产出口商品的工厂之一。
1979年,北京工艺美术各行业产品70%用于出口换汇,经济效益较高。高换汇率和高收益使花丝厂这样的工艺美术生产企业成为国家的重点扶持对象,得到了国家政策和资金上的倾斜及支持。采访中,许如顺师傅就曾提到,六十年代花丝厂就可以得到国家特批的资金,用以购买国外的设备。这也是花丝厂能够实现千人以上规模化生产的主要前提。
在受到特别关注的同时,还应看到花丝厂是处于国家整体管理体制序列内的一个“单位”,国家通过建立单位问严格的上下级行政隶属关系,管控生产资料和利润分配,来确保生产资源的集中供给,确保生产的高效和稳定。在计划经济时期,国家对花丝厂等工艺美术生产企业采取“包产包销”政策,既有组织有计划地统一领取原材料,展开有计划的生产活动,所生产的产品由国家指定部门进行统一的、有计划地销售和经营。包括花丝厂在内的各工艺美术生产专厂,在订单、定价等经营环节受到当时的外贸体制和定价体制管控,没有自主权。
当时国家实行高度集中的外贸体制,国营的专业外贸公司垄断了国家的进出口贸易。1950年6月,成立北京市特种工艺公司,这是北京市首家经营进出口业务的国营公司。北京市的外贸实行计划管理,包括外贸收购、调拨、出口、进口、外汇收支以及其他各项计划。计划的编制采取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程序进行,确定后成为国家外贸计划的组成部分,由国家外贸部下达北京市执行。这些计划均为指令性计划。北京市外贸的对外经营,由国家各外贸专业总公司在北京市的分公司经营,集权于国家外贸专业总公司,由国家各外贸专业总公司和分公司按经营分工统一负责进出口贸易的对外谈判、签约、履约等业务活动,其他任何机构都无权经营进出口业务。北京市外贸的对内经营,实行出口收购制和进口拔交制。外贸公司在对外洽谈出口贸易前,预先向供货部门或生产单位以买断方式购进出口商品;生产单位同国际市场不发生直接关系,对出口商品的适销性、价格、盈亏等不承担责任。外贸公司在执行进口计划中,按照国家计委、对外贸易部下达的货单完成订货、承付、托运、验收等对外业务后,调拨转交给用货部门;用货部门可派人参加技术性谈判,但同外商不发生合同关系,不承担进口质量和效益的责任。
在产品的定价问题上,1992年之前北京特种工艺美术定价具体办法由北京市二轻局、北京市外贸局、特种工艺品工业公司、工艺品进出口公司、首饰进出口公司组成工作组制定。1973年,全国物价座谈会议本着扩大特种工艺品出口创汇的需要,提出“计划第一,价格第二”,“内外有别,分别作价”的原则。直到1988年,北京市物价局才开放了北京市场白银饰品的价格。
在这样集中的管理体制下,生产任务是计划性的,而不是市场性的。花丝厂生产什么样的产品,生产多少产品都是与“计划”和“指令”密切相关,而非来自市场的直接信息。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当时花丝镶嵌产品的题材、风格、内容都选择继承传统、模仿传统,艺术语言和形式表现单调、贫乏。
当时国外对中国艺术品的理解定格在明、清、民国贸易时传入的风格类型。基于换汇需求,在充分满足当时外国人对中国文化艺术想象的前提下,因袭借鉴过去的艺术传统是创作时比较直接和保险的办法。因此产品在题材选择、内容表现、装饰纹样等方面都会以中国传统文化艺术为模仿和借鉴的对象。例如祈求幸福、如意或表现生活兴旺繁盛,有吉祥寓意的民俗图像;古代器物或绘画、图像。如动物、花鸟鱼虫造型的摆件基本以中国画为本,构图、形式模仿花鸟画或器物上的画面,内容也为图画常体现的题材,如喜上眉梢、凤穿牡丹、鱼戏莲、鹤鹿同春等。器皿多模仿古代的瓷器和青铜器造型,如玉壶春、将军罐、双耳瓶、壶、爵、尊、觚等。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出土的陕西何家村窖藏金银器中的盘、碗也都是当时器皿产品仿制的对象。另外,古代戏曲、小说、民间传说也是这一时期花丝作品的重要灵感来源。例如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花丝创新产品仕女摆件就多以《红楼梦》《西厢记》以及“蚌仙”“洛神”“白娘子”“麻姑献寿”等为塑造对象。戏曲中角色的穿戴打扮,成为花丝产品在塑造人物形象时重要的参考依据。首饰题材和风格也有沿袭清宫传统款式的做法。如烧蓝大臂钏、编丝龙镯、银玉结合的錾花套镯等,还有为数众多的传统题材,如龙、鹤、花、蝴蝶、鸟等为表现内容的胸针、耳饰。
生产单位与市场不发生直接关系,会对市场信息的准确性和设计的时效性产生直接影响。周师傅在访谈中曾提到客户需求在经过外贸公司业务员、厂业务员等多人转述后,车间接到的生产要求其信息准确性僅有百分之六七十。白静宜在《我的一点意见》中也谈到生产单位和市场的脱钩,造成设计创作人员不能及时得到必要情报,而盲目进行设计生产,产品雷同,“仅寿星一种题材就生产了几十种”,最终库存积压,设计上也很难形成有时代气息的独特风格。
翻阅当年的工艺美术类研究刊物,可以看到有很多学者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有多位学者在《中国工艺美术期刊》中发文,提出特种工艺“解放后三十年还没有跳出乾隆手心”“把清代的艺术风格和整体的民族风格混为一谈”的问题;姜书璞在《当前创作设计中的几个问题》里就提到工艺美术反复“炒冷饭”的现象,男则武松打虎、老君炼丹,女则西施浣纱、天女散花,止步不前。事实上,当时负责进出口贸易的部门对国际市场也未能有全面、与时俱进的认识,对工艺美术产品的艺术属性和文化属性缺乏正确的认识,因此所下订单并不一定能够适销对路,最终造成库存积压,工艺美术产品在国际市场上一落千丈。
“计划”和“指令”在花丝产品设计上的影响还可以从当时有很多为完成各种展览、比赛等任务制作的“独一件”作品上有所体现。例如很多大型的金银花丝镶嵌摆件,常以较具代表性的建筑为表现内容,结合多种工艺,以“高、大”的造型彰显出社会主义新中国恢弘的时代气象。这些作品不惜成本和人力,挑战技术难度,汇聚大量的物力和时间而成,可以说是“奢侈品”。较有代表性的如《天坛祈年殿》《故宫角楼》《九龙壁》《岳阳楼》等。据当时参与制作的许如顺师傅回忆,《天坛祈年殿》当时就是一件为去香港参展而专门设计制作的作品。无需考虑价格,也无需考虑市场,设计者和制作者更加倾向于“炫技式”的作品,强调技术复杂程度及规模宏大而忽略艺术语言的创新和雕琢。
(三)分配方式
花丝厂除了在生产和经营上要受到国家的“计划”性管理外,在利润分配上也是如此。
花丝厂在集体经济时期,采取固定计时工资的分配方式,实行“大锅饭”的平均主义原则。工人入厂时是学徒,学制三年。学徒的工资是每月16.5元。三年后要参加定岗考核,定岗后成为一级工,工资每月32元。随着技术级别的增加,工资有一定的增长。周师傅在采访时谈到的“级别给你定完了,你拿80多,他拿30多,干的活都一样,但他就拿80,你拿30,因为给你定的工资就是这个。想多拿也没有”“多赚的钱也发不到工人手里,因为工资是死数”。
1979、1980年以后,中美建交、中日建交,像花丝厂这种做外贸、生产出口创汇产品的单位就率先在经济效益上有所收获。除了工资外开始有奖金。奖金用来奖励高效省工的行为。例如一件活预计需要五十工时完成,但工人三十工时就保质保量完成了,那么对于多出来的二十工时就会有奖励。年轻的工人通过加班可以获得较高的额外收益。据采访的周师傅回忆,当时结婚时的几大件——大衣柜、床、自行车等,依靠家里攒钱来购置非常难,但花丝厂的职工通过加班,一个月就可以购置一个大衣柜。
但是每月的奖金额度是固定的,例如一车间每月用于发奖金的额度是一万块钱,所有高效省工的工人根据自己所省工时多少来分这一万块钱。这就产生一个问题,既每工时的价值会随上报工时和人数的多寡产生价值的浮动。举例,这个月上报节省了3000.工时,那么每工时的价值为3.33元,下个月只上报节省1000工时,那么每工时为10元。因此工人在争取奖金时还要尽可能地琢磨到底省多少工时性价比最高。
“均质化”的分配方式也是造成产品摆脱不了传统题材束缚的原因之一。创新或者原封不动的所得结果是一样的,而原封不动显然更加省时省力。
结论
尽管不是在市场经济体制下進行生产和经营活动,但花丝厂确实将花丝镶嵌这样一种传统手工工艺,从手工作坊的产业模式带入到了现代工厂的产业模式。然而,新的产业模式并未给中国的花丝镶嵌工艺、产品带来革命性的创新和改变。分工协作、流水线的生产方式产出的依然是“龙凤呈祥”“麻姑献寿”。
以“官办”的方式对匠人或生产人员组织进行集中生产,并且在资源上有所倾斜,这种规模化的生产模式对当时花丝镶嵌工艺的恢复、提升和发展确实起到了积极作用。但也应看到在“创汇”“求效益”的标签下,使得从国家、社会到企业,所有的注意力都聚焦在“生产”上,对诸如花丝镶嵌这样的工艺美术产生了片面的“行业误解”,如何更快地生产出更多的产品,实现更高的经济价值,完成生产任务,成为了这个行业追求的目标。作为一个产业,追求经济效益和生产扩大本无异议,问题就在于对生产的过度强调和长时间对工艺美术的文化属性和艺术属性发展的弱视、忽视,导致花丝厂乃至整个工艺美术行业的设计创作人员时常将技术和艺术混为一谈,认为技巧复杂、繁复堆砌的就是美的。行业的质量标准、评价体系也完全偏向了技术和工艺要求。加上计划经济时期实行的“包产包销”“平均分配”等政策,使得从企业到设计人员个人都很难接触到市场和行业的即时信息而逐渐丧失了创新的动力和能力。
除了上述花丝厂时期在生产、运营、管理等方式上的原因,当时的社会文化状况和职业教育状况也都是造成花丝镶嵌等特种工艺对传统痴迷和模仿的原因。当时的工艺美术只能在传统的泥淖中摸索前行。
2002年花丝厂破产倒闭,这种大型工厂式的工艺美术生产方式随之瓦解。花丝镶嵌再次回到小规模和作坊式生产的产业模式。很多当时花丝厂的职工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室或者家庭作坊制作点,并且生产出了很多花丝精品。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花丝镶嵌的设计和艺术语言依然没能摆脱“乾隆的手心”。在笔者看来,这依然与社会对工艺美术的技术化倾向的评价体系有关,似乎脱离传统样式就不是传统工艺了,工艺不复杂就没有价值了。企业经营者是这样,从业者也是这样。这是应该值得警惕和反思的。
(责任编辑:赵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