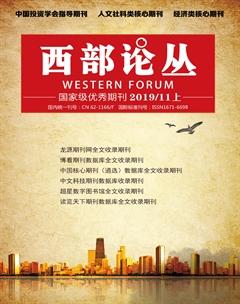从规范视角看人工智能创造物的著作权法问题
摘 要:人工智能可否成为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需要回归到法律制度和原理。易继明教授《人工智能创造物是作品吗?》一文中分析了人工智能的特点,主张人工智能应纳入作品的范围。从著作权法的规范上看,人工智能创作物并不符合作品独创性的实质内涵。此外,我国著作权法对于邻接权为列举式保护,不存在“法外空间”,难以对人工智能创作物予以邻接权保护,故而无法满足作品构成的必要元素。因此,以“机器符号”为本质的人工智能不应被认定为作品。
关键词:人工智能创造物;版权;创作主体;邻接权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进一步发展,现代人工智能的“高度智能化”与人力的不可替代性之间的冲突成为了发展过程中的主要矛盾,是否应当赋予人工智能以民事主体资格?人工智能创作物是否应当享受作品本身所应当享有的保护?这一系列应运而生的问题仍然在学界引发着不小的争论。从本质上讲,人工智能是一种关乎模拟、延伸和扩展人的智能的理论方法,是模拟人类的想象力而驱动的计算机软件程序。[1]关于人工智能在著作权法上的探讨,易继明教授在其一文的研究中,得出结论:虽然人工智能不是人,但人工智能创作物却构成版权法意义上的作品。[2]对此,笔者认为,人工智能的生成物考量应该回归到著作权法本身,并基于现有的法律法规和相关案例出发,才可以很好地认清人工智能生成物和著作权法间的关系。
一、人工智能生成物的权利归属
作品由自然人创作,且创作主体还包括由自然人集合而成的法人和其他组织。依据《著作权法》第九条的规定:著作权人包括:(一)作者;(二)其他依照本法享有著作权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就自然人而言,作为独立个体,依法享有民事权利,并承担民事义务,具备法律上的主体性资格。自然人具备自身的自由意志,有权决定通过某种行为而承担其行为后果,从而基于自由选择,而享有权利、义务、责任。[3]就法人而言,依据《民法总则》第五十七条对法人下了定义:法人是具有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依法独立享有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的组织。法人作为自然人的集合体,是具有独立意思机关的组织体,且该意思机关能够为法人提供独立的意志,能够独立于自然人的意志来支配财产并承担责任。
可见,在满足组织创作、体现意志、承担责任的要求下,法人和其他组织也可以被视为作者,从而成为著作权权利主体,但这并不是意味着否定著作权法中权利主体是具有自主行为意识的人这一观点,只是立法者设立了一种新的制度,将法人看做是一个个自然人意志的集合。同时,《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第9条规定,软件的著作权属于软件的开发者(雇主),而不归属于软件的创作者(雇员)。可见著作权法制度与专利法制度已为法人享有著作权提供了法条支撑和参考依据。易教授主张人工智能可以成为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主体,即人工智能具有深度学习的能力,并且这种能力可以使其摆脱内容创作辅助性工具的地位,[4]具有强大的智能作用,甚至可以超越现有的人类智慧。而目前我国法律并未赋予人工智能以公民或类似公民的身份,因此不能主观性地作类推解释,将人工智能视为著作权主体。
司法实践中,在北京菲林律师事务所诉北京百度网讯科技有限公司著作权纠纷一案里,原被告的争议焦点主要在于计算机软件创作的作品是否属于著作权法的保护范围。北京互联网法院认为,具备独创性并非构成文字作品的充分条件,文字作品应由自然人创作完成,自然人创作完成仍应是著作权法上作品的必要条件。[5]因此,人工智能作出的一系列近乎于人的行為,实质上同人类自身的意识、行为有着根本性的区别。在当下人工智能的阶段,人工智能无法等同于人类自身的智慧和心性,也就难以取得民法上独立的法律主体地位。
从我国传统著作权法体系中对作者的规定出发,人工智能生成的成果当然是不应当获得著作权保护的。换言之,即使人工智能的思维模式已经非常接近人脑,有自己的学习和创作能力,其创作物在形式上类似于或相同于人类的作品,其仍不属于我国《著作权法》中所称的“作品”。只有作为人的智力活动成果的作品,才能获得著作权的保护,这是著作权法的基本原则。故而人类在各类人工智能“创作”中是否发挥了作者的作用,是所谓的“人工智能创作物”能否获得著作权保护的关键。
二、人工智能创作物的可版权性
对于作品特征的认定,易继明教授在其文章中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判断标准:主张人工智能产物符合形式上的作品要件: 第一,属于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 第二,“表面”具有法律所要求的独创性; 第三,具有可感知性和可复制性,并认为版权法中的独创性判断标准应当向一种客观化判断标准倾斜。[6]
著作权的客体是作品,因此人工智能生成内容是否具有“可著作权性”,首先需要判断人工智能生成内容是否可以作为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依据《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二条的规定:著作权法所称作品,是指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内具有独创性并能以某种有形形式复制的智力成果。很显然,在该定义项下,作品首先是思想、感情的表现形式,是创作主体智力活动的成果和其思想、情感外化于作品的最终形态;其次作品须具有独创性和可复制性,这三者同时也是版权作品的构成要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五条规定:“由不同作者就同一题材创作的作品,作品的表达系独立完成并且有创作性的,应当认定作者各自享有独立著作权”,据此,我国通说认为,独创性包括“创造性+独立完成”两层含义[7]。该说法在司法实践中也得到反复印证,在任新昌与李中元著作权侵权纠纷案中,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独创性包括独立完成和创造性,不是抄袭而来,即作品烙上了作者的思想、感情、观点等个人印记。”[8]再例如,最高人民法院在孙新争与马居奎侵害著作权纠纷案中认为,“无论是何种法律传统,均要求作品必须是作者独立创作完成的,独立创作构成独创性的首要之义。”[9]
就创造性的认定而言,笔者认为,可以适当从客观角度出发,结合创作者的主观因素,即“独”和“创”两个维度,将“客体的独创性”和“创作主体的创作意图”联系起来考虑。
(一)人工智能生成物符合客观要求
从客观形式的角度来看,要求作品的表达形式具有一定的创新水平和新颖程度。依据“额头出汗”原则的表述,要求创作者在创作过程中付出辛勤的劳动,[10]即可达成作品的要求。“额头冒汗”原则不仅不符合我国著作权法对于作品构成的要求,而且也是对我国著作权法理论的对立。至少从现阶段来看,人工智能作品的语言算法主要基于的是他人所事先编辑的运行规则而进行,最终成果在表述形式上具有独特性和新颖性。但是,该规则在编入計算机算法之后,容易衍变为固定模式,而在后续中得到不断地引用。在每一次具体成果的生成过程中往往难以体现独特的创造力,并未实现实质上的创新性要求。
(二)人工智能生成物缺乏主观创造意图
从主观创作形式来看,创作不应该只是作品表现形式上的创新,还需要主观意图上的配合,是一种主客观相结合的过程。依据《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三条的规定:著作权法所称创作,是指直接产生文学、艺术和科学作品的智力活动。为他人创作进行组织工作,提供咨询意见、物质条件,或者进行其他辅助工作,均不视为创作。很显然,作为一种智力活动,创作者对于作品不仅寄托了主观的情感因素,更是一种主体个性和想法的外在表达。简单、机械的辅助、重复工作等缺少主体能动性的实践不应该被认定为著作权法下的创作活动,因其缺乏主观与客观间的联结和互动,所以,创作意图是认定是否构成作品的关键要素之一。易继明教授认为:人工智能最可贵的地方就在于“智能”,其不断地习得人类的智慧。[11]机器学习虽然是当前人工智能获取知识来构建算法的主要手段,但至少从目前阶段来看,人工智能并非如同人类一般,可以通过生理感官去感知现有但世界,其只有在相关内容被数据化处理之后,才能被机器所学习。因此,人工智能是基于计算机驱动所生成的算法程序,其运行逻辑主要基于事先地输入条件或者数据库所生成的结果,难以构成独立的主观创作
表达。
(三)人工智能生成物不符合“独立完成”条件
如前所述,“独立完成”作为独创性的内涵是我国立法和司法实践的通说。那么人工智能生成内容是人工智能独立完成的么?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一方面,作为独创性内涵的“独立完成”的主体只能是自然人,《著作权法》第十一条规定:“著作权属于作者,本法另有规定的除外。创作作品的公民是作者。由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主持,代表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意志创作,并由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承担责任的作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视为作者。如无相反证明,在作品上署名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为作者。”从该条可以看出,创作作品的主体——作者只能是公民(自然人),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才能成为作者,而人与人工智能分属于人与物的范畴,人处于权利的主体地位,物处于权利的客体地位,因而人工智能不可能成为“独立完成”作品的主体。人工智能虽然具有人的思维的一些特征,但这些特征不过是人设计的结果,不具有独立思维能力,无法开展智力活动。
另一方面,人工智能生成物也并非人工智能自身的“独立完成”。从现有的阶段看,人工智能是基于同一算法、规则、模版而输出的结果。以文学作品为例,人的创作过程,是对他人作品从文字、情感、背景等各方面进行体会后,并结合自己的感受、处境、理解进行的再创作。依据《著作权法》第三条项下规定的作品,无论是音乐、戏剧等传统文艺作品,抑或是杂技、舞蹈、摄影等现代艺术表现形式,均凝结着创作者自身的独特意识。人工智能无法领悟到文字所体现出来的情感、精神,更重要的是,其再创作的过程必须通过“诱发源”等机制才能显得具有“独创性”,而人的创作并不需要这一机制,其创作是独立行为。
三、关于邻接权的再阐释
邻接权制度的设置初衷是为了保护传播者的权益,激励作品的创作和传播,[12]以此促进著作权法价值目标的实现。在传统观念中,作品的传播需要创作者的亲力亲为,包括表演、出版等,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作为广义上传播者,包括表演者、录音录像制作者等,其地位显得愈发重要,如果不能实现传播者权利的有效保护,将间接地影响著作权人利益的实现。对此,《著作权法》第 36至46 条分别规定了四类邻接权:表演者权、出版者的版式设计权、录音录像制作者权和广播组织者权。可见,目前我国现行法律中已有的邻接权类型并不包括人工智能创作物。
此外,《著作权法》第1条明确规定了著作权法的价值目标:为保护文学、艺术和科学作品作者的著作权,以及与著作权有关的权益,鼓励有益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物质文明建设的作品的创作和传播,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和科学事业的发展与繁荣。该目标从直观上来理解:首先是为了保护著作权和邻接权,以此鼓励作品的创作、传播,最终目标则是促进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以私权的方式增进公共领域的文化福祉。因此,从维护著作权法的基本目标来看,无论是著作权抑或邻接权,还是鼓励作品的创作,均需服务于著作权法所设立的基本目标。
从邻接权的价值理念上来看,主体作出的演绎行为需要与作品之间存在关联,否则,没有作品这一大前提和基础下的演绎行为就好比是无本之源,也无法实现著作权法的价值目标。易教授在文中指出:人工智能对软件涉及的演绎行为是人工智能创作物产生的基础,一如表演者对剧本的即兴发挥,认为人工智能具有自主的演绎权。[13]其主张人工智能可以脱离作品而独立存在、独立演绎,似乎是脱离了著作权法关于演绎权的界定。
笔者认为,首先,人工智能不符合创作的主体资格要求,人类在学习了前人成果的作品之后,可以根据前人的作品继续创作,形成演绎作品,也可以受其启发,创作出具有新风格的新作品,这是人工智能所不具备的;其次,如果要赋予人工智能邻接权,其传播对象必须是带有稀缺性的作品,基于前文所述,人工智能的生成成果尽管在外观上同作品具有相似性,但不满足独创性要求,因此不存在邻接权的客体对象;最后,邻接权旨在规范作品的传播行为,邻接权是传播者所享有的权利。而人工智能创作物是人工智能本身和自然人创作行为的结果,但是在整个流程中都没有参与对外的传播,对于作品的传播不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和作用,从而也不能用邻接权来进行对创作物的保护。[14]故而保护人工智能的邻接权并无益处。
四、总结
“人工智能创作物”,究其根本的话,无非是一种拟人化的表达,是人类利用计算机系统或者计算机系统本身而自动生成的内容。从目前的法律理论和著作权法的管辖范围上来说,作品必须是具有“独创性”的人的智力成果。尽管人工智能对人类的某些类别作品的创作过程和创作效率会产生影响,但目前为止,上述的种种仍然没有改变这是人类创作行为的本质,虽然形式千变万化,人工智能依然是人的主导和引领,而非人工智能的创作。
参考文献
[1] 孙玉荣、刘宝琪:《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著作权问题探究》,《北京联合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第1期,第86页。
[2] 易继明:《人工智能创作物是作品吗?》,《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17年第5期,第146页。
[3] 李琛:《论人工智能的法学分析方法》——以著作权为例,《知识产权》2019年第7期,第16页。
[4] 同上。
[5] 参见( 2018) 京 0491 民初 239 号北京菲林律师事务所诉北京百度网讯科技有限公司著作权侵权纠纷一案民事判决书。
[6] 同注释2。
[7] 参见何怀文:《中国著作权法:判例综述与规范解释》,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6页。
[8] 参见任新昌、李中元著作权侵权纠纷二审判决书,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08)陕民三终字第 16 号。
[9] 参见孙新争诉马居奎侵害著作权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2016)最高法民申2136号民事裁定书。
[10] 冯晓青,潘柏华,《人工智能“创作”认定及其财产权益保护研究—兼評“首例人工智能生成内容著作权侵权案”》, 《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3期,第45页。
[11] 同注释2。
[12] 刘银良:《论人工智能作品的著作权法地位》,《政治与法律》第3期,第12页
[13] 同注释2。
[14] 陈虎:《论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邻接权保护——从立论质疑出发的证伪》,电子知识产权,2019年第9期第21页。
作者简介: 石亮亮(1996—),男,汉族,浙江宁波人,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经济法学、知识产权法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