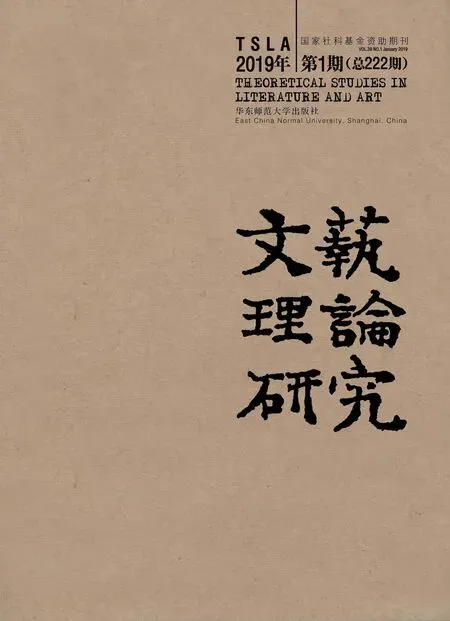叙事与诗史
——以清初三家杜诗注为中心
杨长正
自孟棨《本事诗》以“诗史”称杜诗,“诗史”就成为杜诗的关键词。在“诗史”的诸多意涵中,叙事无疑是其核心。宋人就直接将“诗史”与诗歌叙事功能相联系,如李复比之于史传叙事,“杜诗谓之‘诗史’,以般般可见当时事,至于诗之叙事,亦若史传矣。”又如李遐年视之为《春秋》笔法,“诗史犹国史也,《春秋》之法,褒贬于一字,则少陵一联一语及梅,正《春秋》法也”,这是从历史的叙事功能去衡量杜诗的叙事特征。到了明代,辨体意识增强,遂由杜甫诸体诗歌之叙事实绩拓展出诗歌叙事的一般理论。而清人陈沆则更抉发杜诗的比兴之义,进一步丰富了“诗史”说。
从叙事入手论证杜诗之诗史意义,似乎是清人论杜研杜的一种策略。清人所撰杜诗注本颇多,仇兆鳌《杜诗详注》、浦起龙《读杜心解》是其中较著名的两部,“叙事”二字在两书中使用频率非常高。《杜诗详注》的注语中,“叙事”共出现45次,除引述叶梦得、胡应麟、杨士弘、张綖、胡夏客、顾宸所言各1次,王嗣奭言2次,黄生言8次,余下的29次,都是仇兆鳌自己的评注,含1次评元结《舂陵行》。《读杜心解》的注语中,“叙事”出现58次,且均出自注家手笔。这些评注涉及到多种体裁的杜诗,五律如《登兖州城楼》《晚出左掖》《小园》《过洞庭湖》、七律如《蜀相》《严公仲夏枉驾草堂兼携酒馔》《闻官军收河南河北》《诸将五首》、七绝如《承闻河北诸道节度入朝欢喜口号》、五排如《奉汉中王手札》《大历三年春白帝城放船出瞿塘峡父居夔府将适江陵漂泊有诗凡四十韵》《哭韦大夫之晋》、五古如《陪李北海宴历下亭》《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北征》《石壕吏》《赠卫八处士》《鹿头山》《赠别贺兰铦》、七古如《天育骠图歌》《哀王孙》《桃竹杖引赠章留后》等。还有不少评注,虽未用到“叙事”一词,实际上却是在讨论叙事问题,如仇注中五律《诸将五首》、七律《江村》、五古《后出塞五首》、七古《丽人行》、五排《投赠哥舒开府翰二十韵》,浦解中五律《故武卫将军挽词三首》、七律《长沙送李十一衔》、五古《四松》、七古《魏将军歌》、五排《赠特进汝阳王二十韵》等。
清初吴瞻泰《杜诗提要》是一部“选读杜诗以教子弟”,着重讲求杜甫作诗之法的“读本”。由于作者认为“论杜者咸曰‘诗史’,吾谓杜不独善陈时事,为足当‘诗史’之目也,其诗法亦莫非史也”(《自序》 3)。故在具体讲解中论及杜诗叙事手法的地方,更为普遍。
本文拟考察仇、浦、吴三家注杜对杜诗叙事艺术的阐述,以了解清初学人的诗史观、叙事观,借以探讨诗歌叙事传统在清代传承与接受的某些方面。
一 以事统叙:仇、浦叙事观概说
仇兆鳌《杜诗详注》有着鲜明的结构意识,仿效朱熹《诗集传》章句式解读方法,围绕事、情、景三要素来概括章、段、联、句的大意,将杜诗看成逻辑严密、层次分明的叙述文本。
如仇注《哀王孙》,即以“叙”贯穿:首段四句,“忆祸乱之征”(310),“次段(十二句)叙事”(311),末段十二句为“叙言”(312)——其实所叙乃诗中人物之言,也就是叙事的一部分。浦解完全同意他的分段(247)。该诗写战乱中王孙逃难路遇行人,二人之对话,犹如演出了一幕小剧。乱离路中,有哭泣和倾诉,也有安慰、鼓劲和叮咛,正如浦起龙所谓“丁宁恻怛,如闻其声。”(247)以诗呈现史的真实片断,诗、史互渗互融。仇兆鳌说:“此章四句起,下两段各十二句,一头两脚,局法整严。”(312)浦起龙则说:“起用原题法”(247)“‘金鞭’以下一段,叙事法”(247)“末一段,化用咏叹法,笔笔开摆”(247),对此都有明确的认识。
作于乾元二年的新乐府组诗“三吏”“三别”,是杜甫“诗史”之代表,仇、浦对其叙事特征也都有揭示。仇在《新安吏》原注下按云:“此下六诗,多言相州师溃事。”(523)又引师氏曰:“从《新安吏》以下至《无家别》,盖纪当时邺师之败,朝廷调兵益急,虽秦之谪戍,无以加也。”(523)明确指出所“纪”为何“事”。浦则具体说明组诗的叙事特征:“‘三吏’夹带问答叙事,‘三别’纯托送者行者之词。”(55)“三吏”是第三人称叙事,叙事中有对话;“三别”是代言体,第一人称叙事。不妨以《无家别》为例,看仇、浦的叙事分析。
寂寞天宝后,园庐但蒿藜。我里百余家,世乱各东西。存者无消息,死者为尘泥。贱子因阵败,归来寻旧蹊。仇注:通章代为征人之语。首言乱后归乡,景情并叙。
久行见空巷,日瘦气惨悽。但对狐与狸,竖毛怒我啼。四邻何所有,一二老寡妻。宿鸟恋本枝,安辞且穷栖。方春独荷锄,日暮还灌畦。县吏知我至,召令习鼓鞞。仇注:此段叙事,言归而无家也。上六,说故里荒凉之状。下六,说暂归旋役之苦。
虽从本州役,内顾无所携。近行止一身,远去终转迷。家乡既荡尽,远近理亦齐。永痛长病母,五年委沟溪。生我不得力,终身两酸嘶。人生无家别,何以为蒸黎。仇注:此段叙情,言无家又别也。上六,伤只身之莫依。下六,痛亲亡之不见。(537-38)
仇氏评首段为“景情并叙”,此“景”是人事发生的背景,亦是诗所欲叙述的“事”之一部分。中段向细处描述,叙事至此,渐近高潮,也逼近了诗歌主旨。仇氏所说的“叙情”,其实是叙事结束前的总结。在其看来,杜诗的叙事既可含写景,也不妨抒情泄怨,三者既可分辨,又须融贯浑一。而在浦氏,这就叫“‘三别’体相类,其法又各别。一比起,一直起,一追叙起。一比体结,一别意结,一点题结。”(57) “诗史”叙事就是这样既记录一定的史实,又作出褒贬批评,并舒泄了感情。
五律《江亭送眉州辛别驾昇之得芜字》,题目已见所写之事。仇氏分析则以“事”“情”“景”并列。如首联“柳影含云幕,江波近酒壶”(999),景物描写在此承担了叙事的功能。次联,仇氏谓是“惜别之情”(999)。然而,在“异方”“会面”,席散人去,辛别驾就要踏上“征途”,也是实实在在的“事”。第三联是“临别之景”(999),但这个“景”同时也是事中人的观感,“沙晚”“天晴”涉及时间迁移、环境转换,实际上亦是叙事的必要因素。
杜甫很多诗题,即叙述了诗之本事,而诗句则包含着对此事的咏叹。如七律《严公仲夏枉驾草堂兼携酒馔得寒字》,由题可知,严武于仲夏之时携酒肴到浣花草堂看望诗人,二人饮酒谈天,还要分韵吟诗。题目交代清楚,诗便铺陈吟咏此事:“竹里行厨洗玉盘,花边立马簇金鞍”(904)。仇注云:“首句携馔,次句枉驾,此叙事也。”(904)接下去,便是杜甫对严武推心置腹的诉说。又如《惠义寺送王少尹赴成都得峰字》,仇注云“上四登寺,写景叙事。下四送王,即景言情。”(1001)本诗下四句的“骑马”“云门”二联叙述杜、王在惠义寺流连直到分手。因为有“此别惜相从”(1001)之句,当然可以说是“即景言情”,但要说是叙事,亦无不可。以送别之景写送别之事,因送别之事而生惜别之情,情、景、事实际上是混融难分的。再如《过南邻朱山人水亭》,仇注云“首联叙事,过南邻也。次联写景,见水亭也。下四言情,山人留饮也。”(762)本诗首联“相近竹参差,相过人不知”(762),其实是以景叙事。而颈联“归客村非远,残罇席更移”(762),仇注云是“言情,山人留饮”(762),其实“山人留饮”不就是“事”吗?而“留饮”又见出交谊款厚、不忍遽别的友情,则所谓“言情”,又岂与“事”无关?《将赴成都草堂途中有作先寄严郑公五首》,题目已说明本事,仇注依次谓“首章,重赴成都之故,八句皆叙事。”(1105)“次章,想春归景事。”(1107)“三章,写故园荒芜之状。”(1107)“四章,言故园虽芜,而严公可依。上四叙景,下四叙情。”(1108)“末章总结,叙草堂前后情事。”(1109)可见,在仇氏的意识中,诗之情、事、景本就混融互渗,皆赖诗人融铸而叙出之。又如《徐九少尹见过》,仇注云:“上四叙事,见自谦意。下四叙景,见喜客意。” (861)或叙事见意,或叙景见意,叙事、写景无不含有情感心意。在仇氏看来,情(意)、景、事是既有分别,又相通而互渗的存在,这既是他的叙事观,也是他的抒情观、写景观,对我们很有启示意义。
《杜诗详注》往往将杜诗按句、联标注成情、事、景三类,认为诗乃三者之交错融合。这种思路和做法其来有自,明代的张綖,前辈王夫之,皆有垂范。尤其是时代与之相近的黄生,将情、景、事的批评体系化,对仇兆鳌具有理论与方法上的启迪。
黄生《诗麈》论诗的内容要素,谓“诗有写景,有叙事,有述意三者”,还有很多例证分析。写景、叙事意思清楚,“述意”在有些情况下实与“抒情”“议论”“感慨”同义。且黄生将叙事写景述意与赋比兴相联系,说明他是将这三者放到诗歌表现手法的层面上考虑的。这对仇注的影响历历可见。如杜甫七律《野老》,黄生在《杜诗说》中评道:
前半赋景,后半写怀。当此时,对此景,抱此怀,捉笔一直写就,诗成乃拈二字为题,此类皆漫兴之作[……]前半写景,真是诗中之画;后半写情,则又纸上之泪矣。(310)
仇注亦云“上四写景,下四言情。”(748)并引黄生注语:“前幅摹晚景,真是诗中有画。后幅说旅情,几于泪痕满纸矣。”(748)二人分层一致,且都是以景、情分别概括诗歌内容。前二联所写的“景”,被誉为“诗中之画。”这里的“画”不仅有景物,也有人事活动。所谓的“景”,也有“事”在其中。后两联以抒情为主,触及的是诗人的心事。这“心事”,即老杜安史乱中避地成都初期的生活与心态,说它具有一定的“史性”,应不过分。再如五言排律《谒先主庙》十六韵。黄生《杜诗说》评曰“此诗分为三段。首六韵叙霸蜀之事,中四韵写祠庙之景,末六韵叙己因谒庙而生身世之感。”(402)依次以叙事、写景、叙感(述意)加以概括。仇注分段相同,对诗意的概括也高度相似。(1353-55)
仇注对黄注有明显承袭,又有推进,将情、景、事的批评方式进一步规范化。如其严格遵循分章分段的原则,在概括章、段内容大意时,按情、景、事依次分述,形成规范的体例。于叙事分析,更为精细,先总括所叙何事,接着说明视之为叙事的理由,再缕述所叙之事,乃至将这一模式推广应用到一句、一联之中。
仇注的体式又对浦起龙有影响。《读杜心解》多次提到仇注,且多处参考仇注的章、段层次划分,以“情”“景”“事”分类概括之。不过,浦氏又指出分层要视对象,《读杜心解·发凡》云:“书有圈点钩勒[……]触眼特为爽豁,故仿而用之。但钩勒只可施之长古、长排,彼八句亦截者,非法也。又如转韵古风,自宜依韵分截,节族天然,否则使读者缩脚停声,拦腰换调,多少不自在。”(10)一方面肯定划分层次的必要性,一方面又指出此法应限制在排律与长篇古体等长诗之间。
长诗叙事性较强,层次的划分使得叙事脉络清晰,读来“触眼特为爽豁。”浦起龙以“叙事”一词论杜诗凡58处,涉诗82首,题材则酬赠、咏物(画)、纪行、时事均有。这些诗的范围比“诗史”更大。
如杜诗五排《陪章留后侍御宴南楼得风字》八韵,浦注此诗云:
诗当是醉后所成。[……]分两截看:前言身遥世乱,而依人以老,是叙事;后言身世两忘,一托之于酒,是述怀。其陪宴赋诗,前后略带而已,故曰醉后诗也。(733)
浦氏谓此诗前半叙“身遥世乱,依人以老”之事,指的是广德元年夏末秋初,吐蕃入寇大震关,杜甫依附于梓州刺史章彝。浦氏谓诗的后半“述怀”,但从内容来看,因陪宴赋诗而引起身世飘零、思家忧国之情,叙事、写景、抒情融而为一。而就全诗言,还是叙述和描写的笔墨多,而抒情则赖由叙述出之。
再如五古组诗《八哀诗》之一的《故著作郎贬台州司户荥阳郑公虔》,全诗六十四句,是郑虔的一篇诗体传记。浦注云:“此篇一头一尾,中两段叙事,分一盛一衰。”(156)盛时一段二十二句,写郑虔博学多才,本段结尾:“沧洲动玉陛,寡鹤误一响。三绝自御题,四方尤所仰”(155),指郑虔的诗、书、画 “三绝”一事,也就是浦氏所云“邀主知而倾时望,此言其盛也,正是精爽处。”(156)衰时一段二十句,写郑虔为官经历,至“安史之乱”中被迫接受伪职,叛乱平定后被贬台州。“末段,哀之之文,反以最初游迹相形,见昔也京邑交欢,今也‘存殁’两地,愈益恻然。”(157)这正是“诗史”“诗传”与“国史列传体”的不同之处。
《湖城东遇孟云卿复归刘颢宅宿饮散因为醉歌》在七言歌行中不算很长,浦注云:“前十二句,叙事。后六句,感慨。”(253)十二句中的前八句,叙述语调惊喜欢快,友朋之谊,主人之慷慨热情,跃然纸上。接下来“且将款曲终今夕,休语艰难尚酣战”(253),写主人劝客,言辞之中见真情。“照室红烛促曙光,萦窗素月垂文练”(253),写室内外景致,同时也暗示了时间的流逝。事件、情景、气氛,已有充分表现,后六句转换话题:“天开地裂长安陌,寒尽春生洛阳殿。”(253)引入时事,昔日两京沦陷,今日重新收复,两句插叙,极为凝练而大气磅礴。然后又从国家大势转回眼前,想到明日分别,又岂能不感慨离合无常,后会难期。浦起龙的具体分析,再次证实所谓诗者,无非叙事、写景、述意三要素不同比例、不同方式的组合建构而已。
浦起龙批评抒情诗,还创设了“叙事体”“议论体”的概念。
《大历三年春白帝城放船出瞿塘峡久居夔府将适江陵漂泊有诗凡四十韵》(实为四十二韵,四百二十字),浦起龙评为“少陵长律中,此篇最为文从字顺。” (789)又论其结构云:“起四,结四,中间分五段写”(789),即开头、结尾各四句,当中的主要内容可分五段看。“五段之中,前三段就出峡所经言,是叙事体。后二段就此身漂泊言,是议论体。”(789)叙事体、议论体之名,即出于此。
何谓“叙事体”?浦氏没有解释。可从其对诗歌的分析试加理解。他解释前三段依次为:“叙峡内舟行之景”(789),“叙下峡经险之景”(789),“叙峡外旷淼之景”(789)。而在我们看来,这三段乃是敷演诗题所叙之事。按诗题,时间:“大历三年春”,事件:“(从)白帝城放船出瞿塘峡”,情节:“久居夔府”,“将适江陵”,而眼下则是在江上“漂泊”。诗题叙述十分清楚,但也留下了很多空白。浦氏所说的三段叙事,既紧扣诗题,又是题目之下可写而未写的内容。首四句“入舟不乐,解缆长吁”(787)刻画诗人的姿态和心情,接下来,在“叙事体”的三段中,进入惊险的三峡之旅。“叙事体”的三段,其“事”不过诗人坐船出三峡,一言概之可矣,但一路上景色的变换却叫人目不暇接,而景的不断变换正昭示着时间的流动、地点的迁移、船行的惊险和人事的进展。这样写诗,这样叙事,才成其为诗的叙事——否则,有诗题那段散文不就够了吗?
不但写景可以成为叙事的一种形式,就连抒情议论也常与叙事浑然不分。浦起龙说此诗后二段是“议论体”。凡议论,总得有个对象,诗中写到诗人此前的遭际、此后的打算,也写到安史作乱、朝廷窘困和他最关心的“黎民病”。这些充满感情色彩的议论,是大段叙事后迫切需要倾诉出来的,没有这段抒情味很浓的议论,全诗就不完整,诗一开头就出场的那位“入舟翻不乐,解缆独长吁”(787)的老者——本诗的抒情主人公和故事叙述者就形象有缺陷而不够鲜明和崇高。
浦起龙注释杜诗,尤其是针对习惯上被看成是“抒情诗”的诗作,提出“叙事体”“议论体”两个概念,反映了他诗歌观念的开放和辩证,对我们颇有启发,也有助于我们加深对中国诗歌贯穿抒情叙事两大传统的认识。需要说明的是,浦氏的做法并不是偶然的。他分析五律《暮春陪李尚书李中丞过郑监湖亭泛舟得过字韵》说:“通身叙事体。二李一层,过湖亭一层,泛舟一层,带暮春写湖景一层,美郑监一层,自述陪游一层,清楚而联络。”(575)何谓“通身叙事体”?就是说,整首诗全是叙事,几无一句非叙事之语。叙事之重已达到“体”(而不是一般表现手法)的地步。他说的“一层”又“一层”,其实也就是一件又一件的事,全诗八句六层意,叙事密度真是不小。或问:“春日繁鱼鸟,江天足芰荷”(575)明明是写景,也是叙事吗?答曰:正是,二句写游赏中人所见之物事,鱼鸟芰荷被赋予舒愉之色后收入画面,固然是景,但观景正是游赏之事的一部分,读此诗不仅可见鱼鸟芰荷的舒愉,更可见观赏鱼鸟芰荷者的怡悦。又问:称其为“通身叙事体”是否有抹杀抒情意味之嫌?答曰:非也,叙事之中,抒情在焉。尊二李,美郑监,乐游湖,畅晚兴,带酣歌,春意浓,鱼鸟繁,江天阔,芰荷足,洋溢的是一种多么轻松逸乐的情绪!哪里还需要再添直白的抒情话语。
二 以史法为诗法:吴瞻泰论杜诗之“叙”
仇兆鳌、浦起龙注杜诗,对于杜甫的表现方法、修辞技术,多有论述。除上节所述外,仇氏评杜诗章法尚有“叙”“起”“收”等语,浦起龙则有“逆局”“逆入”“顺叙”“追叙”“实叙”“虚写”之谓。不过他们并未就此作系统梳理,在这一点上,吴瞻泰比他们向前推进了一步。吴氏论杜诗,颇重诗法,不仅注意到诗中之“事”,尤重在考察杜甫的“叙法”,并对此作了系统总结,从而对仇、浦有所补充。
吴氏年辈在仇、浦之间,其杜诗学成果主要集中于《杜诗提要》一书,而《提要》论诗之旨归,即为诗法:
子美之诗,驾乎三唐者。其旨本诸《离骚》,而其法同诸《左》《史》。[……]至其整齐于规矩之中,神明格律之外,则有合左氏之法者,有合马、班之法者。其诗之提掣、起伏、离合、断续、奇正、主宾、开合、详略、虚实、正反、整乱,波澜顿挫,皆与史法同。而蛛丝马迹,隐隐隆隆,非深思以求之,了不可得。论杜者咸曰“诗史”,吾谓杜不独善陈时事,为足当“诗史”之目也,其诗法亦莫非史也。[……]故余尝选读杜诗,以教子弟焉。非求简,求其法而已矣。[……]虽然,诗以道性情,而法兼学力。使无离忧鬱结、香草美人之寄托,无以成骚赋之祖;无播迁夔蜀,刻不忘君之本怀,无以造乎“诗史”之宗。是以知子美作诗之本,不可学者也;子美作诗之法,可学者也。吾特抉剔其章法、句法、字法,使为学者执要以求,以与史法相证,则有从入之门,而亦可渐窥其堂奥。(《自序》 3—4)
吴氏以“诗史”视杜诗,这还是常论;但他反对拿杜诗与历史记载牵强比附,而强调杜诗作法近乎《左》《史》,将诗法与史法进行比照,而有所发现,且认为此法可学,这是他的高明之处。吴氏之前,曾有人指出过杜诗叙事借鉴史述,却未细致具体阐发。吴氏总结杜诗笔法,得上述十一种,将诗法和风格及创作成就相结合,使他的诗法论具备了某种理论色彩。下面具体看看吴氏对几种重要诗法的阐述。
《杜诗提要·自序》所谓的“提掣”,亦称“提笔”,书中偶作“提束”,其义则一,我们理解似近“插叙”或“补叙”。如至德二载八月,杜甫自凤翔去鄜州省亲,途经醴泉唐太宗陵墓,作五排《行次昭陵》,在赞美了太宗的开国之勋,接写“往者灾犹降,苍生喘未苏”(318)一联,吴瞻泰在句下注曰:“‘往者’二字,提笔,犹《史》《汉》之‘先是’字,《左氏》之‘初’字也。”(318)这里的“往者”,把诗的叙述截断,像史书以“先是”或“初”回溯到往昔,出现了一个顿挫。这有两个作用,一是回溯太宗功业,是他结束了隋的乱政,“往者”即指此而言;一是暗喻当前,安史之乱使唐朝国政与民生又回到了“苍生喘未苏”的“往昔”。双重涵义既是因身临昭陵,思念太宗而起,又与不满玄宗荒政导致动乱有关。意思复杂多层,语言却委婉曲折。吴瞻泰在诗末评语便进一步指出运用“提笔”的好处:“‘往者’二句,妙用提笔,盖诗恶直叙,而排律尤尚波澜,此处用力一提,便是两副叙法,既免太直之弊,而又陡起文澜。此以作文之法,用之于诗者也。”在此之后才叙及今日肃宗的“指挥安率土,荡涤抚洪罏”,祈愿太宗英灵保佑他的子孙,以“寂寥开国日,流恨满山隅”(318)的深沉感叹作结。
吴氏指出杜诗中类似诗例甚多。如评五排《奉送郭中丞兼太仆卿充陇右节度使三十韵》在前后两大段叙述中,以“三月师全整,群凶势就烹。疮痍亲接见,勇决冠垂成”(316)“四句提笔,追美昔日郭英乂之才勇”(316),追美的目的是敦促他今日既防边患,又平内乱。评《发秦州》“同谷反序秦州之前。而启行一段,另作提笔,序秦州之后。参错倒序,以乱其线。为诗文而不谙乱字者,其纽于整齐之法而不知变者矣。”(49-50)前文先铺垫,述向往“乐土”同谷及离开秦州的缘由,结尾“日色隐孤戍[……]苍茫云雾浮”(49)。 补叙半夜出发时的情景,进一步突出主旨——为了生计,不辞辛苦地踏上征途。
又如论主宾、详略之诗法,以七古《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为例,此诗前八句描写公孙大娘之舞,吴评:“凡舞之高低起止,无所不具,是何其详?”(138)接下四句由公孙大娘引出其弟子,但仅有一句“妙舞此曲神扬扬。”(137)诗题看似是以弟子为“主”,诗中却大力描叙其师傅,弟子成了“宾”,写弟子乃是为衬托师傅,于是吴瞻泰明白点出:“究之诗意,非为弟子也,为公孙大娘也。则公孙大娘固为主,而弟子又为宾,仍是主详宾略云耳。”(138)诗接下来写诗人与弟子交谈,“感时抚事增惋伤”(137),由此过渡到下文,回叙公孙大娘的遭际。最后抒发了与公孙大娘同命运的感慨。吴评指出,这首诗详略、主宾的巧妙搭配,做到了“主详”“宾略”,既突出了诗歌主旨,也起到“叙事以详略为参差”(138)的艺术效果。
再看“侧笔”,吴氏《自序》所谓“正反”诗法,即涵盖这种笔法,在一定程度上,可理解成今人所谓侧面描写、反面描写等。当然,这里的“侧笔”,是个相对的概念,正因人们惯用“正笔”,因而特意表彰“侧笔”。如《丹青引赠曹将军霸》,吴氏尾评云:
凡诗文正面写不出,必以反笔、侧笔、陪笔写之,精彩倍现。如此诗写将军处,首即抬出一魏武,后又引出褒公、鄂公二人,反面照射。其写丹青处,先以书法陪起,请出卫夫人、王右军二人为客,后又补出画工,及圉人、太仆与弟子韩干来。正如史迁序巨鹿之战,极力描写楚军,却偏写诸侯从壁上观,乃显得楚军以一当百也。史公之文,杜公之诗,吾不能测其所至矣。(130)
吴氏一一拈出本诗的“反笔、侧笔、陪笔”,以之类比《史记·项羽本纪》中巨鹿之战中诸军“作壁上观”的相关描写,亟称杜诗叙事笔法之妙。这里的“反笔、侧笔、陪笔”等等,其实也起到主次映衬的作用,有助于突出事件中的中心人物,避免单调的平铺直叙。书中分析侧笔的类似例子,还有不少。如评《哀江头》“写才人之弓箭,写才人之马,写才人之马之饰,写才人之射云,写才人之堕翼[……]若全不及贵妃者。而接以‘明眸皓齿’二句,乃知其极写才人处,正其写贵妃处也。用侧面衬正面,而正面益显。”(108)诗以浓墨写才人,衬出贵妃出场的气派场面,正与开头“昭阳殿里第一人”(107)照应,正侧结合,突出贵妃之荣耀。
除此之外,起伏、开合、断续、比兴,等等,都或多或少涉及了叙事的结构和手法。杜诗风格的形成,正是这些诗法综合作用的结果。“沉郁顿挫”是杜诗最重要的特征。吴瞻泰的理解是“其沉郁者意也,顿挫者法也”(《评杜诗略例》 5),顿挫的诗法正是《杜诗提要》想要揭明的地方。不过,说“顿挫”是诗法不十分准确,“顿挫”似更近于应用诗法所导致的风格特征,进而以此风格传达“沉郁”之意。检阅全书分析各种诗法时,很多都归结到“顿挫”二字,或以“波澜”“断续”“起伏”“不直叙”“错综”等词汇表述。如评《北征》云:
长诗之妙,于接续结构处见之。又于闲中衬带处见之,全在能换笔也。不能换笔,则无起伏。无起伏,则俗所云死龙死凤,不如活鸡活蛇也。此作有大有小、有提有束、有急有闲、有禽有纵,故长而不伤于冗,细而不病于琐。然又须看其忽然转笔,突兀无端,尤属神化。(31)
《北征》是杜甫五古长篇之代表,吴瞻泰认为该诗避免了冗杂琐碎,全在于“换笔”。在诗意层次“接续”的关键节点“换笔”,如“夜深经战场,寒月照白骨。”写完路途所见,按理接下来应是归家场景,却突然续道“潼关百万师,往者散何卒?遂令半秦民,残害为异物。”(29)吴注:“此处直可以接归家矣,却又陡恨到哥舒翰事。”(29)历史事实是哥舒翰率二十万士兵本可坚守潼关,因杨国忠催逼,勉强出战,结果不敌,伤亡惨重。插入此事,似乎中断了叙事,破坏了诗歌的连贯性,但由眼前所见“白骨”,要追溯缘由,必然联想到这一史实。接下来四句“况我堕胡尘,及归尽华发。经年到茅屋,妻子衣百结。”(29)潼关之败,长安沦陷,与杜甫流亡的命运密切相关,于是自然地接续到归途的现实中。这就是吴氏说的“笔势续断如游龙”(29),藕断丝连的插叙,有利于造成“起伏”的效果。要起到这种波折的效果,需要借助各类诗法,也就是“有大有小、有提有束、有急有闲、有禽有纵”,如在诗中“闲中衬带处”偶尔“换笔”,如“我行已水滨,我仆犹木末。”(29)注曰“写急归之状,妙从仆上衬出。”(29)诗人很着急回家,已到前头水边,而仆人倒是悠闲,慢腾腾地走在后面,这就是以“闲”衬“急”的写法。再如到家之后“序儿女琐屑入细,全从‘生还’快乐心坎中描出。”(30)又接“翻思在贼愁,甘受杂乱聒。新归且慰意,生理焉得说?”(30)注曰“‘翻思在贼’二语,又纵一笔,愈见‘生还’之可慰也。”(30)这里的纵笔就起到了“细而不病于琐”的作用。这些笔法的使用,使长诗的结构有变化起伏,形成了杜诗的顿挫风格。
在吴氏看来,杜甫运用各类诗法,追求一种“顿挫”之致,“诗恶排序而贵错综,其势合者必割之使分,联者必散之使断,或参之议论以疏其势,或假之景物以离其群。要在于平坡千里中,忽然奇峰耸起,岭已断而云联,如此则变化在手,头绪不棼。”(87)正是各种诗法的综合使用,才避免平铺直叙,达到顿挫之美。
上文所举诗法也可用来抒情,或者兼及叙事、抒情。例如《除架》:“束薪已零落,瓠叶转萧疏。幸结白花了,宁辞青蔓除。秋虫声不去,暮雀意何如?寒事今牢落,人生亦有初。”(174)吴评:“上七句,皆赋瓠架,结尾带出‘人生’。似上七句是主,八句是宾,题意只归重‘人生亦有初’一句。”(174)这里的主宾之法,主就是抒情,宾是叙事。再如《江涨》“江发蛮夷涨,山添雨雪流。大声吹地转,高浪蹴天浮。鱼鳖为人得,蛟龙不自谋。轻帆好去便,吾道付沧洲。”(185)吴评:“诗文扼要争奇,全在善用虚实,实处易写,虚处难写。此篇前六句皆实发江涨,结忽置身题外,虚神澹远,通体俱灵。”(185)叙事多实,抒情多虚。主宾、虚实等并不从属于抒情叙事任何一方,诗法分析的是如何叙事、如何抒情,两者不处于一个层面。
不过,吴氏以史法为参照推出诗法,主要还是强调杜诗的叙事。上列几种诗法,与史法多有相通,也都集中表现在叙事方面。吴氏也注意到杜诗的抒情方面,在这一方面,他更多的是以比兴论杜诗,兹不赘述。
三 叙事与诗史:诗史说的批评实践
上述三位清代学者关注杜诗的“诗史”问题,除了像一般“诗史”论者那样,从诗人经历、思想、精神,诗、史关联等方面着眼,更重要的是他们从“叙事”切入,不仅对“诗史”的内涵与外延作了更深入的揭示,且从写作的角度,细致描述了“诗史”的形成过程,使“诗史”之论得以真正落实。
叙事与诗史的关联,首先在于“事”的特质。仇兆鳌述及杜诗“诗史”云:“宋人之论诗者,称杜为诗史,谓得其诗可以论世知人也。”(《杜诗详注·原序》 1)其后又论及杜诗有所谓“诗之本”与“诗之实”。(《杜诗详注·原序》 1-2)所谓“诗之本”,指杜甫的思想与情感基础,是其诗内容的内在支撑;“诗之实”即诗歌的表现,指诗歌内容与艺术本身。对于论诗者来说,只能是由“诗之实”抵达“诗之本”,也即由诗而及人。这个“实”与“本”,在仇兆鳌的具体批评中,又会有所变化。如在总论杜诗时,是强调杜甫的半生漂泊、思君念阙为“诗之本”,由此而表现出的悲欢愉戚,则为“诗之实”,这是由“诗实”而至“诗本”,也即由诗而及于人和世的过程。杜诗之所以能被称为“诗史”,由于其“实”(诗中写到的事,也是一种“实”),能反映其“本”。即从事的角度来看,杜诗称为“诗史”,在于这些“事”皆包含老杜忠君恋阙之心,由个人升华到家国层面,别具思想内涵与现实意义。
“诗史”的属性在“诗”,而其之为“史”,则又自有方式方法。仇、浦、吴对杜诗的具体剖析,就在于指出以诗为史的独特之处。诗对于“事”,本有多种呈现方式,固有直接铺陈,更有只是写景、抒情。而杜甫“诗史”并不只是叙事诗,还有不少是抒情诗,这固然可以从心灵之史的角度来理解,仇氏在辨析杜诗“本”“实”之时,庶几就是这一思路。然而,当仇氏将写景、抒情也看成叙事的时候,则隐含着以“事”为根本,即景、情之所以如斯,乃因所包含的,或在其背后的“事”。这正是诗之为史的特点。那么,在仇氏那里,“本”“实”之辨呈现两个层次,对抒情写景之诗,“情”“景”之后有“事”,则事为“本”,“情”“景”为文本中可见之“实”,这其实就突出了诗史中的“史”的实在性;然而,这些又都是诗人家国情怀的切实表现,与诗人思想情怀比起来,则又成了“实”,“本”却是更内在、更抽象的形而上之物。
这样,仇兆鳌将“诗史”的精神层面与落实在文本中的写作实践层面进行了有效的贯通,也扩大了叙事的义涵。而这,正是中国诗歌叙事传统的实际,它绝不同于西方叙事学意义上的讲故事,其涵盖要宽泛得多。
浦起龙以“叙事”解“诗史”,更加集中于“叙”的方面。浦氏以史著为参照来论杜甫“诗史”,重视诗歌的客观与真实。《读杜心解·发凡》中论及其注杜诗对于时、地的考察和落实,“取衷于《唐书》,而证之舆图、统志以求其合”(7),即是视杜诗为史家之实录。其为杜诗编目,就贯彻了“将以还诗史之面目”(19)的想法。在具体评述中,又常称某诗“可作史补”(113),皆可见出其对杜诗“诗史”说的理解。
在具体批评中,诗、史的叙事比较,或者以史法来揭示诗法,也是浦氏的重要特点。《读杜心解·发凡》云“诗家之子美,文家之子长”(5),杜诗之为“诗史”,少不了“史笔”。浦氏评《义鹘行》云:“奇情恣肆,与子长《游侠》《刺客》列传,争雄千古。”(48)又说首段“叙事明净”,“斯须领健鹘”一句“手法矫捷”(48)。即是以史传叙事笔法来评诗歌。浦起龙以“叙”“事”“叙事”“记”等词评杜诗,正可视为浦氏“诗史观”的批评实践。在此“诗史观”的统摄下,浦氏注杜,往往指出多种笔法在杜诗中的融通互渗。比如评《奉赠射洪李四丈明甫》:“起四,用兴体叙相逢”(101),比兴承担叙事的功能,是“兴”“叙”相融;评《过郭代公故宅》云:“纯是论断体”(103),又谓前八句“总挈生平”(103),中八句“特表勋伐”(103),则是“论”“叙”一体(103);评《览柏中丞兼子侄数人除官制词因述父子兄弟四美载歌丝纶》为“颂体”(767),又具体分析云:“四句提,十二句叙,十二句赞”(767),则“赞”“叙”融合交错;[……]浦氏的论评,往往也混用各种表达方法。除了从一些表面写景、言情的地方揭示出叙事的实质外,其论叙事,也每兼及抒情、写景。如评《送率府程录事还乡》,有“叙携酒取别情事”(25)之语,评《述怀》,则曰“叙遥忆之情”(33),评《发同谷县》,点出“叙未发将发时情事”(82),评《故司徒李公光弼》,指明“叙其勋爵崇高”(147)[……]“叙”的宾语,可以是情、事、景,乃至人的地位与风评,且事也往往是和情、景融混不分,亦彼亦此。
浦氏以史传中的“叙”比照诗歌,从结构、章法、节奏等角度,揭示杜诗之“叙”的史笔;同时,也将情、景等纳入“事”的范畴,不过,他更多的是从叙述的角度,将其看成诗歌的客观表现对象。即杜甫的诗史不仅在于其纪实,还在于其是一种纪实式的表达方式,这可以说也是对“诗史”的一种理解。
吴瞻泰具有兼容、综合仇、浦二人的特点。他更明确地将对杜诗“诗史”的理解分为两个部分,一为“善陈时事”,另一则是深得史法。吴氏所概括的十一种诗法,其实也就是史著中普遍可见的著述行文之法。这十一种诗法中,有偏于叙事的,有偏于抒情写景的,然以兼及三者的为多。当然,吴瞻泰从诗法入手论杜诗叙事,一旦将“叙”法延展到大部分杜诗时,就不只是叙“事”,有时也包括叙“情”、叙“景”。将景、情都看成是可客观呈现的对象,具有事的性质,在这一点上,吴与仇、浦是一致的;与史传相比较,对杜诗叙述笔法的分析、梳理,吴在浦的基础上,做得更为深入、细致且系统,对于杜诗的“诗史”批评,更具有实践性。
综观三家,他们都是以笺注形式展开杜诗批评,可以说是“诗史”批评的落实,他们对杜诗的解读合情合理,也有力证实叙事与诗史确有天然的关联。杜诗叙事与诗史说互为发明,从某种意义上说,诗歌叙事分析,往往就是诗史说的批评实践。
注释[Notes]
① 李复:“与侯谟秀才”,《李复诗话》第九则,《宋诗话全编》(第一册),吴文治主编(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411。
② “一联一语及梅”指杜诗一联一语涉及梅花的诗甚多,而专门赋梅的仅2首。参见周煇:《清波杂志校注》,刘永翔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455。
③“世推杜陵诗史,止知其显陈时事耳。甚谓源出变雅,而风人之旨或缺。体多直赋,而比兴之义罕闻,然乎哉?今笺其古诗寄托若干篇,而律诗尚未暇及。”见陈沆:《诗比兴笺》,《陈沆集》,宋耐苦、何国民编校(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420。陈氏专门用比兴笺注诗歌,并选注了杜甫五、七古各31、12首。另外,关于杜诗叙事与“诗史”关系,亦可参张晖:《中国“诗史”传统》(北京:三联书店,2012年),该书纵向梳理并考察“诗史”内涵的演变发展,叙事是其中的一个主要内涵。笔者检阅《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杜甫卷》(上编 唐宋之部),华文轩编(北京:中华书局,1964年)、《金元明人论杜甫》,冀勤编著(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有关清前论杜诗叙事的文献,张晖书中已大体囊括。清代论杜史料丰富,仅就专著论,张忠纲等编著《杜集叙录》(济南:齐鲁书社,2008年)即收录416种,难以竭泽而渔,只能择取个案作为研究对象。
④ 数据统计依据杜甫:《杜诗详注》,仇兆鳌注(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杜甫:《读杜心解》,浦起龙注(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
⑤《杜诗提要》,吴瞻泰注,陈道贵、谢桂芳校点(合肥:黄山书社,2015年)。吴瞻泰是徽州同乡黄生的后辈,酷嗜杜诗,《提要》就是他的研究结晶,成稿于康熙三十五年(1696)之前,定稿在仇注(初次刊刻于1703年)之后。《提要》版本、特点、价值等见此书前言,同参张忠纲等编著:《杜集叙录》(济南:齐鲁书社,2008年),313-15。
⑥ 清初叶燮也是如此,认为万事万物“发为文章,形为诗赋,其道万千。余得以三语蔽之:曰理、曰事、曰情,不出乎此而已。”见《原诗》,霍松林校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20。
⑦ 黄生:《诗麈》,见诸伟奇主编《黄生全集》(第四册)(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9年),339。这样的表述,在《诗麈》论律诗中联作法时云“非写景,即叙事,或述意三体。”(312)在唐诗的选评本《唐诗摘抄》中,不少诗例就做了类似的分析,如评李白《闻王昌龄左迁龙标尉》“一写景,二叙事,三、四发意,此七绝之正格也。”参《黄生全集》(第三册),344。

⑨ 以吴瞻泰的理解是写玄宗时安史之乱,“又禄山之乱未远,而曰‘往者’,不忍斥言播迁也,微词也。”(《杜诗提要》 318-19),还有一说是写太宗时期的事。
⑩ 吴瞻泰阐述了比兴在杜诗“‘赋笔’的叙述结构中的意义”与“在杜诗叙事和意象营造中的结构意义”,叙事中插入比兴,“避免了过于粘着事实,缺少变化,而化直为曲,化平冗为顿挫,化板滞为灵动”,见周兴陆:“吴瞻泰《杜诗提要》研究”,《杜甫研究学刊》1(2003):55-56。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杜甫:《读杜心解》,浦起龙注。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
[Du, Fu.A
Kernel
Interpretation
of
Du
Fu
’s
Poems
. Ed. Pu Qilong.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61.]——:《杜诗详注》,仇兆鳌注。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
[- - -.A
Comprehensive
Interpretation
of
Du
Fu
’s
Poems
. Ed. Qiu Zhaoao.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79.]——:《杜诗提要》,吴瞻泰注,陈道贵、谢桂芳校点。合肥:黄山书社,2015年。
[- - -.Essence
of
Du
Fu
’s
Poems
. Eds. Wu Zhantai, Chen Daogui, and Xie Guifang. Hefei: Huangshan Publishing House, 2015.]黄生:《黄生全集》。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9年。
[Huang, Sheng.Complete
Works
of
Huang
Sheng
. Hefei: Anhui University Press, 2009.]张晖:《中国“诗史”传统》。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
[Zhang, Hui.Poetry
as
History
:A
Chinese
Literary
Tradition
. Beijing: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2012.]张忠纲等:《杜集叙录》。济南:齐鲁书社,2008年。
[Zhang, Zhonggang, et al.Record
of
Du
Fu
’s
Works
. Jinan: Qilu Press, 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