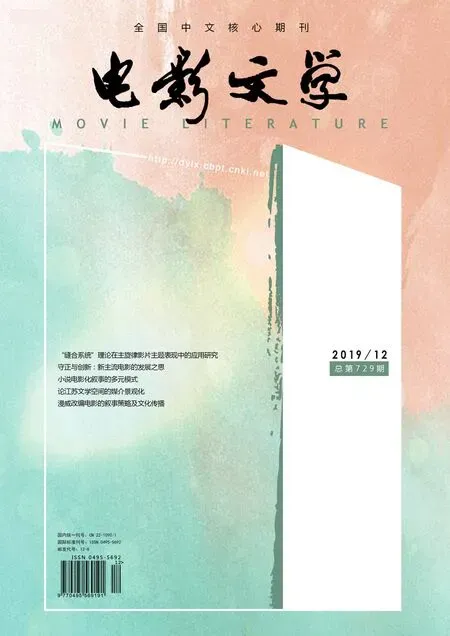《鬼乡》《雪路》:民族伤痕的“少女”式书写
郑殿辉(吉林师范大学 国际文化交流学院,吉林 四平 136000)
韩国电影历来注重对历史事件与民族情感的书写,这在慰安妇题材电影上表现得尤为突出。近年来上映的两部影片《鬼乡》(赵正来,2016)、《雪路》(李娜静,2017),与以往通常以纪录片形式展开叙述不同,影片注重慰安妇受害者的口述史实与艺术再创造相结合,运用历史与现实交叉的双线叙事模式,更突出的是强化了主人公“少女”形象的塑造,以少女的天真无邪反衬日本帝国主义的肮脏与罪恶,以少女的无辜遭遇映射了悲惨而不屈的民族命运,让观众在悲悯中铭记历史,一起关注当下幸存的慰安妇受害者的生存状态,集体声讨日本帝国主义所犯下的滔天罪行。《鬼乡》与《雪路》,不约而同地强化了“少女”叙事,呈现出鲜明的少女意象。本文将从人物形象、典型意象、民族象征等几方面,对韩国慰安妇影片创作呈现出的“少女”式叙事新趋向进行具体分析。
一、 少女像与“少女”形象
韩国NAVER《语学辞典》“少女”词条的释义为:“尚未完全成熟的年幼女孩儿。”从社会学角度看,“少女”还承载着特殊的文化含义。“少女是预备女性市民,为了孕育优秀国民和维系父权制,婚前在性方面其身体应当保持纯洁。”由此可见,“少女”在韩国社会,并不单指年龄上的幼小,在传统的儒家文化传统中,“少女”还是象征着爱情、纯洁的性别化产物。将“少女”与慰安妇联系在一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那便是遍布韩国的慰安妇“少女像”。事实上,在就慰安妇问题的对日声讨上,韩国民众的抗争从未停歇过,由“韩国挺身队问题对策协议会”组织的“周三集会”从1992年起几乎从未间断过,集会时常常有耄耋之年的慰安妇受害者参与其中,以自己的悲惨遭遇控诉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为纪念第1000次集会,2011年12月14日协议会在日本驻韩大使馆门前设立了身着韩服的慰安妇“少女像”,此后“少女像”陆续出现在全国主要城市、街区,迄今为止,已在全韩国范围内设立了74个少女像。这些少女像或坐或站,姿态不一,但相同的是身着韩服、年龄幼小,眼神透着伤感与无助。尤其是位于首尔的驻韩日本大使馆门前和釜山的日本驻韩总领事馆后门的两处少女像,具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这两处少女像造型也非常相似:身着韩服的小女孩儿端坐在椅子上,赤足踮起后脚跟,紧握的双拳放置于双腿之上,右边放着一把空椅子。韩服象征着民族精神,赤足暗示了少女被强征时的情景,踮起的后脚跟说明了少女的年少,坐在椅子上脚尚不能触及地面,而旁边放置的空椅子则更有深意。一是希望那些已经故去的慰安妇奶奶能够永远同在;二是希望来访的人们,看到少女像,能够坐在旁边近距离感受慰安妇少女的心声;三是希望后世的人们也能铭记这段悲惨的民族血泪史。众多少女像的设立,改变了民众内心的慰安妇形象,从耄耋之年的慰安妇奶奶逐渐转化为年幼被强征的慰安妇少女形象。这一改变,直接体现在了最新创作的《鬼乡》和《雪路》之中。
《鬼乡》开篇通过贞敏(姜荷娜 饰)与小伙伴玩捉迷藏和抓石子游戏,骑在爸爸的肩上唱着歌回家等画面,意在强调贞敏还是个充满童趣的孩子,玩游戏赢了小伙伴的护身符,遭到母亲的批评和体罚,说明她还处在天真烂漫的年龄阶段。《雪路》是以两个小女孩永爱(金赛纶 饰)、宗粉(金香奇 饰)为主人公展开叙事的,永爱家境优越,读日本学校接受日式教育,有着较强的自尊心和傲慢的性格;宗粉则因家境贫困只能在家帮助母亲料理家务,但她却总是替他人着想,并有着坚韧的性格,永爱和宗粉是当时韩国社会阶级现状的真实写照。影片还用宗粉偷吃给弟弟的土豆、永爱轻信去日本工作的谎言等细节,表现了二人还是不谙世事、不辨是非的孩子。贞敏、宗粉和永爱的社会阶层有别,但都是花季少女。虽然被强征的方式不同(宗粉和贞敏是被强行抓走、永爱是被骗加入挺身队),但命运都是一样。数十万计的朝鲜少女如她们般被拉上了通往满洲的火车,成为日本军国主义罪恶行径的受害者。虽然慰安妇受害者中也包括日本本土妇女,却与韩国和中国等国家的情况是截然不同的。“与日本人慰安妇都限定为21岁以上的卖春女相反的是,朝鲜慰安妇在伴随1938年生效的‘国家总动员令’产生的‘挺身队’名目下,小学生和中产阶级家庭出身的女性也被选拔出来,甚至连贫穷且教育水准不高的农村地区少女,也通过就业欺诈、强行掠走、绑架、人口买卖等多种非法手段被强征为慰安妇。”与以往的慰安妇题材电影相比,《鬼乡》和《雪路》在开篇增加了叙事铺垫,突出了主人公天真无邪的少女身份,用强征前后的命运落差作比,彰显了日军的残忍暴力与道德沦丧。
二、民族象征与典型意象
“少女”在韩国具有圣洁、美丽、爱情的文化内涵。两部影片以慰安妇少女的悲惨遭遇,象征了苦难而不屈的民族命运。韩国是单一民族国家,自古以来就竭力维系其民族的独立性与纯洁性,虽然历史上一直战事不断,并时常受到大国的威胁,但吸收了儒家思想的韩民族,一直保持着较好的民族自信心与凝聚力,偏安一方却恬然自得,就如同影片开篇少女主人公的生活状态一般。然而这样的平静终被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所打破,1910年日本强迫韩国签署《日韩合并条约》,韩国被日本强占,就如同慰安妇少女被强征一样,失去自由开始饱受苦难。“朝鲜人慰安妇大概达到20万名,占亚洲充军慰安妇的80%~90%。”慰安妇少女在慰安所被禁止说韩语,这也是日本在韩国殖民主义政策的一个缩影,强推日语代替韩语,妄图从根本上扼杀其民族精神。但韩国人民的反殖民抗争从未间断,一些进步人士私下里开设韩语学校、传承韩国文化,影片《雪路》中,宗粉在慰安所里跟永爱学认韩文,读韩文小说《小公女》,就是韩民族不屈精神的一个写照。1945年日本战败,韩国光复,但对慰安妇来说却不是黑暗后的黎明,日军为掩盖罪行,将很多慰安妇灭口,即使有少数逃回国内的幸存者,也不敢公开自己的遭遇,带着难以愈合的心理创伤度过余生。两部影片片尾慰安妇少女们被集体杀害,以及幸存者平生所承受的精神苦难都是历史的再现。慰安妇的命运象征着韩民族的命运,遭受磨难的少女象征着日本强占期遍体鳞伤的韩国。“影片的内涵旨意不仅在为受迫害的慰安妇们正名,并且更希望利用凝聚在女性身体上的‘受难’景观隐喻朝鲜民族和‘大韩民国’的前世今生。”
此外,两部影片还运用了典型意象——蝴蝶(《鬼乡》)与雪(《雪路》)——作为少女形象的隐喻,表现了少女的命运。蝴蝶有着美好、幸福、夫妻、变身、重生、灵魂等众多象征意义,这都是人们将蝴蝶种种生命特征和活动形式内化到人类自身生命之中的结果,“在东方,蝴蝶象征春天、纯真、幸福、美好、孤独和儿童,是希望开始的符号。”蝴蝶在《鬼乡》中是慰安妇少女的化身,日军军官面露狰狞地赏玩蝴蝶标本,招魂时客死异乡的少女们化蝶归乡,影片用蝴蝶表现了慰安妇少女的命运,隐喻了慰安妇少女的纯真美好、劫后重生。雪从手感上给人以柔软舒适的感觉,洁白的颜色象征着纯净无瑕,这与少女形象的内涵是一致的。影片在片头用洁白温暖的棉花与片尾逃亡冰冷的雪路相衬,隐喻了两个少女主人公被强征前后的命运对比。《雪路》开篇用一组永爱家弹棉花做被子的情节,描绘了一幅温暖和谐的生活图景,结尾处年迈的宗粉望雪兴叹,不由得回想起以前采摘棉花的美好记忆。身处慰安所的慰安妇少女们,是何等地企盼能够回到家乡盖上舒适暖和的被子,而归乡的路又是何等艰辛,永爱的鲜血染红了脚下的积雪,当永爱永远躺在雪地里时,宗粉只能为她盖上几捧白雪。影片片尾使用了超现实场景实现了命运的救赎:年迈的宗粉走在积雪覆盖的山冈上,她看到了年少的宗粉,看到了暗恋的永柱(永爱的哥哥),看到了妈妈拉着宗粉的手一起回家,导演用一个大远景镜头,让主人公与失去的自己、失去的亲人团聚,与错过的爱人、错过的历史重逢。这个结尾设置可见影片对历史现实未来的寓意:第一,表现了影片对历史事件的态度,号召民众一起铭记历史,不忘曾经遭受的民族劫难;第二,表现了影片对当下慰安妇命运的人文关怀,呼吁民众关爱幸存慰安妇受害者的生存状态;第三,影片预示了未来声讨日本政府慰安妇罪行的艰难,韩国民众对慰安妇历史事件的关注热度持续高涨,但影片中与这种炽热的情感相对应的却是冰冷的积雪,就如同韩国社会的极力控诉与日本政府一直以来的狡辩伪善一样,显示出极大的反差,韩国社会就慰安妇问题的对日声讨,注定困难重重,不是一方坦途。
与之前的慰安妇影片相比,《鬼乡》与《雪路》更强调人物形象的少女式塑造,这与陆续设立的慰安妇少女像以及由此带来的民众心中慰安妇形象的改变有直接关系,影片用天真、纯洁、善良、美好的少女形象来谴责日军所犯下的滔天罪行,收到了非常好的艺术效果。此外,两部影片都注重使用典型的意象来隐喻慰安妇少女的命运,强化了影片的主题,增加了影片的艺术表现力。然而,这种强调“少女”的书写也招来了女权主义的批评,“但是用少女来象征性暴力被害者的方式,是以将女性分为具有社会价值的女性和不具有社会价值的女性的偏见为前提的。这种分化是以包含‘性’意味的纯真和纯洁为基准的,但这个基准却是以肯定男性中心法则为基础的。少女的纯真虽作为强调被害当事人无辜的角色,但强调无辜的同时却排除了少女以外其他女性的故事。”这类观点认为,将少女以外的其他女性排除在外,无视这种对象的不完整性,只是一味强调被害女性的纯真和纯洁,这非但不是否定男性暴力,反而助长了男性暴力。的确,如果仅仅将慰安妇受害者聚焦在少女身上,并逐渐形成创作风格的话,这无疑是缩小了对慰安妇问题的历史认识,慰安妇问题是日本帝国主义对本国、占领区或殖民地女性的犯罪问题,这里的女性还包括成年女性,甚至包括一部分原本从事性工作的女性,只强调少女的纯真和纯洁,确实有可能将问题引向男性中心主义的层面。不过,《鬼乡》和《雪路》以少女为主人公,加大了被强征前的描写分量,无疑产生了鲜明的艺术效果,同时两部影片都采取历史与现实的双线叙事模式,用超现实的巫俗“鬼乡祭”和永爱相伴的魂灵打通时空隔阂,使得双线叙事能够有机结合,从而极大地提高了影片的观赏性和艺术张力,这些尝试对于唤起观众对慰安妇问题关注热度,还是具有非常积极的现实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