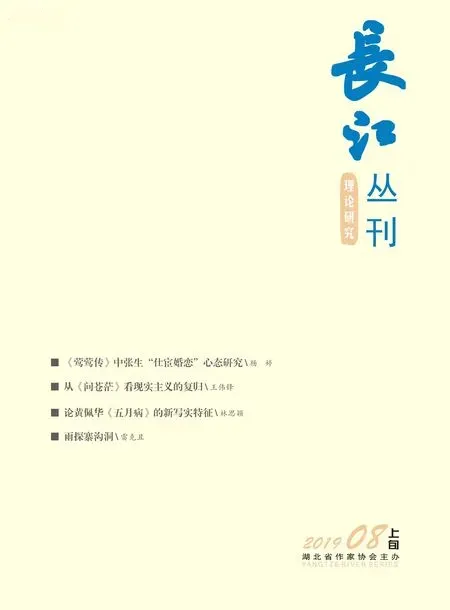女巫穿梭在沙漏中
——琳子诗论
■丁东亚
作者单位:长江文艺杂志社。
在诗歌内进行个人理性认知,似乎也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女性诗歌创作的一种新的探索。这种对自我内心与身体体验及情感体验的内省、书写,无疑是诗人最清醒的表述方式。所以对于“只有智慧的才是干净的,才具有清洗文字和人心的效力”的说法,我深为赞同。毕竟智者多思,只有智者才能窥探到自己与现实生活以及世界的联系,只有具有智慧的诗人才会理解所有瞬间即逝的东西,都只是一个譬喻,并在对灵感瞬间捕捉的时刻发现,一切都是生命意识体现的延伸。
如此,优秀的诗人又无时无刻不陷入一种自我怀疑的状态。他/她的怀疑也同样是生命意识深层的思考与挣扎,即传统与个性独创的衔接与矛盾究竟如何才能使诗歌回归到本真状态,在接近诗歌本质的过程中抵达自我。而诗歌的本质恰是不可定义的,诗歌只是通过语言“过渡”现实或表达诗人情感。诗人通过语言将思想或情感以诗歌的形式表述出来,是为了完成一种生命自身永恒的“超越”。当然,诗人十分清楚语言又是危险的,有时它会让诗人感到无力、羞愧。所以,在诗歌语言上,诗人主动抛却种种概念的围墙,自我构建诗歌空间,以自然的语言陈述或描写向世界阐明生命的语言和风格,在放弃刻意追求自我个性的同时,也便真正成为了自己。在这点上,琳子可谓独树一帜的女诗人。
首先,她在自我书写的探索中,更多关注自我的生活现实现状(这点在她的诗中尤为常见),是在个人生活领域去思考人生与现实的,并以小我的情感抒发拓展了诗人对生活的热爱,完成了对人生的深层思索;其次,她的诗没有故弄玄虚的征象,清晰自然,以最直接,最简单的语言向外界(或者读者)传达了最真实的内心情感,且没有娇嗔、无病呻吟,是在女性认知和体悟上以她敏锐的洞察力和犀利的笔触展示了一个小女人内心的巨大的力量和反叛(这点仅限于诗歌探索);而且,琳子的诗歌语言没有雕琢的痕迹,不讲究诗歌韵律,竭力避免在传统诗歌中借用或转用(这并不表示琳子放弃了对古典诗词的传承,只能说明她在诗歌创作中存有更深刻的清醒意识和自觉性),并尽力回避隐喻带来的误读,在语言中坚守着她女性本真的尖锐的情感表述阵地。这种属于女性独有的理性认知在琳子诗歌中淋漓的展现,不仅使诗歌自身回归了其自然本性,更重要的是她的诗让人读来畅然,甚至能轻而易举地引导我们回到生活事境中去。这点在她的诗歌中,若不经过洞察力和创造力并重的阅读,是无法感受到其诗歌作品内所具有的魅力和力度的(当然,若不如此,此时的阅读也必然导致诗歌残缺)。
那么,在小我文化处境基本判断中的大量创作,局限于自我情感的表述,是否会影响到诗歌的深度或深层表达,从而使诗歌自身的容量和境界过于狭小呢?琳子在以“女巫”一样的全知姿态,在她诗歌的“袖珍世界”里能否寻到诗歌“绝对的真实”与诗情,无疑是一个值得深讨的话题。这个问题似乎也是上世纪90年代女性诗歌创作中潜在的问题。
一、内省:事境或真相
优秀的诗人一般能够借助想象,在诗歌中借助生活意识将人们引向另一种生活,这同样也是诗人自我生活挖掘的一种写作深入的可能。只是诗人与生活之物存在着某种界限或者隔阂,诗人在竭力趋近生活本真的过程中即又被限制。海德格尔说,“哪里有限制,被限制着就在哪里退回到自身那里,从而专注于自身。”这表明诗人与事、物之间其实存有一种模糊的对立关系,事境或物在被诗人引入和嵌入诗歌时候,总又有着部分未被照亮的部分。然而,诗人是敢于冒险的,他们更想借助生活本身寻回自己本真的世界,寻到生命的真谛,甚至,抵达事境与物,企图寻找真相。自然,事物未被照亮的部分此时作为在场的形式被诗人诠释在了语言,个人视角的叙事或抒情在诗歌内暴露无疑。只是诗人琳子更专注于“直接性”,以冷静尖锐的语言表达了她对自己所叛逃或眷念的现实世界的真切情感,且这种情感是如此朴实自然。
我不能邀请你到我家来/因为那里有很多灰尘/那里的灰尘是我留给自己的(《扫灰日记》)
不能说自我封闭仅仅是女性对抗世界的一种形式,我觉得它更是诗人对抗自我的一种手段或方法。诗人首先是孤独的,当他与世界产生对抗情绪时,这时的孤独便到达了某个限度,而自我内心的封闭恰是自我安静下来的最佳途径。琳子通过诗歌写作其实就是为了改变自身,因为她深知诗是人类改造自身界限的知识,这也是诗歌创作的精神意义。在此诗中,琳子的简单书写(叙事)传达出了女性内心巨大的力量——反叛与对抗的力量,也表明了她敢于直面真实自己内心情感的勇气。至于她在回避的究竟是什么,无从知晓。就像她在另外一首小诗《夜里》所遮蔽的情感一样:“推开窗户/风铃响了/可这是在夜里。”在黑暗中,她瞪大“女巫”般闪亮的眼睛,看到的是希望还是绝望?那随风摇响的风铃声勾起的究竟是她的忧伤还是幸福?不过诗人通过这种静谧的意境,的确向人们传达了温暖而忧伤的矛盾情绪。此外,我又不得不提及琳子在诗歌中拒绝狂欢,感恩知善的诗人高贵品质,因为在她的一系列个人情感的诗歌中,都集中表现了这点。
一个人在外地想我/我确信我是一个有罪之人/可是在这样的夜晚/是我先醒来的/我确信那藏在花丛的人有一张善良的脸/善良的就像一阵蜂蜜和灯光(《无题》)
我一直惊讶于琳子这种自觉情感的表达方式,不露声色却让人遐思无限,情感看似宽泛却又紧凑有力。在诗中,那“藏在花丛的人有一张善良的脸”可以是丈夫、孩子,也可以是朋友、情人,可对于“我”而言,这属于远方的思念是对“我”的一种罪过,在假想的情景中,其实“是我先醒来的”,是“我”先想到他们的,只是诗人把这份思念之痛转化为了感恩,诗人内心的善良此时仿佛一团炽热的火团,一下便燃起了巨大的爱海。她通过某种真实的假想事境向世界敞开的便是这份内心的爱和善良,真相作为一种隐蔽的书写,随即被隐喻。此时,诗人作为惟一的在场者,是否还在遮蔽她黑夜下的无助与孤独?对于读者,与文本不期而遇的阅读,并非真正地能从诗人缄默无声的思想领域看到事物或者说是事境的真相,也许只有通过在场者被抛状态中的敞开性,通过恰到好处的语言表达,诗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和情感才能真实地被澄明。这点在诗人琳子的《在北京见到陈鱼》、《指甲草》等小诗中,都有着不同层面的阐发。而这类诗中,我觉得最能展现诗人思考,对事境与生命真相进行深刻内省的还数那首《阳台上》。
里尔克在《慕佐书简》中说,“死亡乃生命的一面,它规避我们,被我们所遮蔽。”死亡作为存在者直面的另一面真相,直面它无疑只会增加内心的感受痛苦。死亡本就是法则,一旦我们触及法则,进入其中,一切都注定被敞开,因为面对死亡,诗人是渺小的。琳子在此的书写显然亦是冒险的,“乃是那种有时比生命本身冒险更甚的大胆冒险”,不过她通过死亡的真相所传递出的信息并非是消沉与绝望,相反是一丝生机,是在追寻一种安全维度。此诗前三节,都是以相对的对比手法来作叙事铺垫,第四、五节时,诗人才真正诠释了自我真实的甚至有些自私固执的情感。
这是我的阳台/这里没有村庄/没有挖掘和雨水/也没有小虫子和牛粪。因此/我能容忍这里的花草没有花草的气味/没有花草的脾气/也没有花草规定的花期和死期
这一刻,在诗人面前,存有的只是那干净的阳台(事境),明媚的阳光以及她此刻对生命的思考。
因此/我看不懂它们在冬天开花是不是因为/寒冷是一种光明。在冬天死亡是不是因为/寒冷是一种黑暗
可在这里,诗人的情感通过语言所要诉之于世界的不再是异想天开的虚构,也不再是对现实领域的单纯表象的描绘,而是让生命的死亡真相作为一种无蔽的状态被澄明了。于此,敞开的诗歌领域才在存在者这里发光和鸣响,并显示了诗人在内省同时所体现出来的禅悟中的灵性所在。
二、释放:尖锐及本真
当诗人想要表达内心痛苦或信念时,抒情带来的流畅性不会使诗歌呈现它本该具有的张力,相反,将导致诗歌成为娱乐灵魂的手段,那么,这时拒绝自己而进入幻想或顿悟,遮蔽真实所带来的叙事,必然又在语言的驱动下倾向于生命本能之动力。而倾听作为对内心声音的回应,恰是女性传递自身信息最好的方式。
身体可谓女性最隐秘的家园,在这片辽阔而空旷的空间,琳子以“在场者”独有的身份和感受进入到自我内心,去窥视,倾听,走近她身体神秘之蓝色的过程,已是对自我的一次完成。这相对的完成仅是在意识上,至于其诗歌语言与情感在具体形象下向外的延伸,又是难以言明的了。琳子在以女性认知角度来观察生活的过程中,越来越成熟的叙事手法及以神性来度量自身的方式,从一定意义上来说,是在向诗歌维向的一次跨越。诗人何时自觉地承受此维向,便是自我存在的时刻了。
晚上/是服药的时间/灯光下/一切恍惚/蜂蜜不甜、黄连不苦、舌尖/上的白酒三钱/我是驱赶百兽的女人(《服药时间》)
诗中,诗人情感的纠结并非来自外在的病症,而是内心的无望。琳子在此诗中想要阐发的一种情愫,仿佛那恍惚的灯光,在黑暗里隐约可见,却无法起到镇定的作用,她便只好借用味觉间接地表达内心的苦痛了,“蜂蜜不甜、黄连不苦”,简洁的书写不禁流露出了她坚忍的心态。此时,释放作为她对抗时间的一次行为,被“现在”所替换,于诗歌语言中被完全诠释,因为“现在”就是诗人自身,或者说是时间自身。只不过琳子是以“驱赶百兽的女人”的身份来嫁接情感,向人们诠释她矛盾的心理的。这种显性的遮蔽,也在某种程度上加强了诗歌的力度。与以往不同的是,诗人琳子回避了“自我控诉“的消极态度,以冷静的方式将情感淡化,在女性本真的面目下,坚定地拒绝了悲悯与同情。
从根本意义上说,诗是诗人对情感,整个内心世界的表现。但琳子以诗人身份叙事或抒情时,有时是以旁观者的身份“在场“的,这样,她便更清晰地辨析出了事物原本的真相,更确切地切入到诗内,进行了准确的描绘与表达。在她的某些诗作中,一些情感在她心中所引起的感想并非是以感动人们为目的的,她冷静书写下所传达的往往具有些许凄然的味息。
我来自一个叫玉驾庄的小村子/你也是/我们在很小的时候恋爱/然后分手/二十多年过去/你还在北京/开始你是个小兵/后来你是个警察/现在你还是个警察/你在北京一住就是一辈子/你除了北京就是到过玉驾庄/我知道等你父母不在的时候你连玉驾庄也没有了/这真让人难过(《我的玉驾庄》)
若诗人自觉“以语言形式的复杂性和内在的紧张性来抵御现实生活的简单粗暴和外部世界的压力”,那么,情感的抒发便以“介入性”的重要方式呈现在语言,此时,诗人赋予语言的不再单纯是事境和形象,而是更多的可能性。但语言对于事物存在的间接性,有可能会在诗人表达的过程中消耗了诗接触现实的有效性和力量,甚至,会弱化语言所本该带来的激情。琳子在此处理方式则是让理性占据主导,只以冷静的态度和立场来描绘内心的情感。“你在北京一住就是一辈子/你除了北京就是到过玉驾庄/我知道等你父母不在的时候你连玉驾庄也没有了/这真让人难过。”这时“我”的情感是通过近似嘲讽的口吻来阐发的,揭示的是“我”对诗中那个人强烈的内心怀念之情愫,当情感的纠结转化为一种形式,被时间冲淡,“我”的爱似乎只能在随着岁月淹没在“玉驾庄”了。诗歌中,诗人的暧昧远远超越了我们的想象力,面对现实生活,琳子独立的“自我意识”不禁又引起了我们深入的思考:现实生活的复杂到底使我们变的坚强,还是更加怯懦了呢?
今天中午是一个特殊的日子/我不该梦你/我不该在国庆节的午时/梦见奸情/荒淫和/道德以外的高潮(《无题》)
从现实生活延伸至“道德”问题,琳子内心的尖锐一下便凸显了出来。这种不道德的属于女性的梦境本该使她感到不安和惊慌,可她笔下的“我”却是那么的冷静,这种冷静可以说也是对传统观念的反抗或挑战,“女性”的身体欲望也应是光明的,至少它在女性的想象世界或梦中该是“合法”的。而这个“特殊的日子”,我又该如何把我的欲望释放?于是,诗人在午后无比纠结的情感矛盾中只好借喻梦到的是别人的“奸情”,历史的“荒淫”以及“道德之外的高潮”。这近似无声呐喊的形式,也表明了诗人内心其实承受着巨大的痛苦与绝望。另外,琳子通过对现实生活真相的描述,揭示女性生存本相和处境的同时,也表明了语言在真实生活面前的空乏。因为诗歌是要直面生活的,是需要借助有形的日常生活事境来探测灵魂的。
三、情感:温暖与疼痛
情感作为诗人心理体验的主要积淀物,不仅时刻传达着诗人对外界的感应,也是诗人与日常生活时刻保持紧密联系的具体体现。不过,更多时候,诗人的情感是煽情、呼告或独白式的,在想象构筑的空间内传递的是种虚拟的信息,“真实性”此时作为被隐蔽的部分期待被召回。保尔·利科说:“正是凭借着感情,我们才居住在这个世界上。”那么,诗人内心诗意的栖居如何通过语言来构建,如何以质朴的感情传达诗人内心的热爱和关护,是一个诗人是否具有人文关怀的具体表现。琳子众多有关乡土与亲情的诗歌,在具体表述“我”之小爱的同时,带给读者的却又是一种大爱,只不过她更善于将强烈的情感转化为平淡的抒情,以大量的叙述介入,消弱情感,使诗歌看似散漫却凝聚着巨大的力量。
我怀念一个人低头掏炉膛的样子/只要想起他来/我就会很温暖/但那个人其实并不存在/炉膛也不存在/父亲母亲也早已回到乡下去了(《房间内》)
琳子喜欢在记忆中寻找温暖的事境,并以缜密敏锐的眼光将之归结为一种女性原始的母性的爱之情感诉之于语言,她所想歌颂或赞美的其实就是她内心的那份朴实的情感和善良。情感此时作为诗人的“晴雨表”,不再受制于时间,而是在诗人回归内心本真的一刻呈现为“现在”。“我怀念一个人低头掏炉膛的样子/只要想起他来/我就会很温暖”,当遥远的形象被表述为温暖,“现场“的感觉随之产生,仿佛诗人就站在炉膛门前观望着母亲掏炉膛的样子。这时,想象与情绪合流,诗情在急速跳跃和升华后又回到真实的现状,“但那个人其实并不存在/炉膛也不存在/父亲母亲也早已回到乡下去了”惟有情感留存于诗内,被无限延伸。她的《桐花开了》《油菜花开》《春天,新鞋子》等许多诗歌都具有着这样的形式和情感,某个时候,我们在其中似乎还能读到疼痛与忧伤,尽管这丝疼痛与忧伤被表面的温暖所覆盖。譬如《油菜开花》的最后一节:
爷爷的棺材后是长长一队哭泣的女人/那里已经烧着了纸马/那里填土的人发出巨大的声响
被时间淹没的死亡在被瞬间提及时候,诗人内心的纠结以疼痛的方式呈现,抒情与回忆便随即成为一种隐蔽的伤害,被袒露无疑。
在琳子大量的诗歌中,对于母性的捕捉和表述,颇为敏锐。在《生日写给母亲》的诗中,她通过对母亲的爱之畅想回到自身的母性,书写了两代人同样的命运,不同的生活现状,并以女性的尖锐将这份母爱形象化,使个人经验向诗意深入,人生的悲喜呈现本真之态时,令人感动又不禁深思。高尔泰说“人由于把自己体验为有能力驾驭自己的命运的主体,而开始走向自觉”,在诗歌与生活之间,生活作为诗之内容随即在诗人经过多重转换之后被生成。琳子在自觉走向自我的同时,以母性意识向读者传递的情感,并非是为了加强诗歌的感染力,相反,她似乎还有意减弱这种情感渲染,使读者看到的是一个女性在冷静状态下的思考深度。
我是怎么吸吮你又黑又小的乳头,妈妈/我是怎样从你的身体里/灰尘一样掉下来/我是怎样成为你的一块沼泽/我是怎样很快成为你身后的一座庙宇
此诗一开始便节奏迅疾,生命诘问式的书写似乎要将体内的情感全部释放,不给读者舒缓的空间,情感的向内敞开以及自我澄清,瞬间打开了诗人的灵性之门。当“我”“灰尘一样”从你的身体里“掉下来”,开始“吸吮你又黑又小的乳头”时,生命的最初形态和最初之爱随即以温暖的形式显现,之后“我”成为沼泽使母亲陷入,成为“庙宇”被母亲信奉的虚写,则又体现了诗人的自责或忏悔的心性,并以此回归“我”之现实,通过成长的叙事对母亲的一生进行阐释,这样偏重心灵史的叙事也从侧面反映了诗人琳子的细腻,尖锐的女性意识以及在现实生活中挣扎与呼喊。
我是怎样在落满枣花的门口/等待妹妹出生。我骄傲/妈妈,这个世界只有你才有生不完的孩子/你生过孩子之后/我又长高了一岁!妈妈
在这种直逼生命本相的心理叙事趋势下,诗人渴望一次淋漓的倾诉。张立群说“自觉地从伤害自己的记忆中发现诗意,是琳子成为一个诗人的基本潜质。”这种说法显然是十分到位的,只是琳子在自觉“退回”现实或记忆之后,并非以妥协的姿态面对,而是直接扑向被伤害的部分,进行言说,叙述,将其内心坚硬的部分得到展示。
我成人后的困倦在你身上又算什么/我只生育了一次。/我的贫穷是我没有一丁点土地/我住在一块煤上。妈妈/我的脚下有些空,已经空到了小腿/我用什么来掩埋我掉落的牙齿
在此,“我”的生育及贫穷与母亲的“富有”不再单纯的作为对比,更多的是以一种语言形式展现了对爱的赞颂。而生命之弦被奏响的一刻,优美的音符带来不论是痛苦还是幸福,只有诗人自己知道。那终究被埋葬的亲情作为一种生命音符,不会随着时间淡化,消逝,只会在血液里流动、延伸,任何时候都能传出刺心的声响。最后琳子以卑微的身份向母亲的臣服,似乎也验证了她对生命反省的觉悟,对“我”与母亲有着同样生命形态的欣慰。
四、结束语:在路上
当代诗歌的发展,从某个角度来说是抛弃了对古典的继承的,更多的诗歌创作是在西方诗歌里成长和发展的,诗人更多时候只能在西方诗歌的口味中谈论诗歌,如此,对传统或本土的诗性显然是应该被召唤的。琳子曾坦言说:“我不知道什么是诗歌”,而她又清醒的认识到诗歌是源于内心深处的,是源于生活经验与身体经验的。当诗人们热衷于谈论诗歌具体的物象和事境,以及如何准确的表达和叙事功能时,琳子返回记忆的乡土世界和女性的内心世界的姿态,就足以证明了她作为一个诗人对诗歌的担当。
刘小枫在《拯救与逍遥》一书中写道:“诗是存在的歌唱,生命本身的言说。诗的语言原初、直接地使生命形式和体验形式成为言语,使人的存在精神性地转化为透明或浑浊。”琳子在她的诗歌写作中始终保持鲜明的女性视角和立场,有着善于发现生活细微之处的敏锐度和洞察力,并能够抓住众多有意味的瞬间,以她智慧而灵性写作者身份对生活经验不断开拓和丰富,这样,在自我情感释放的同时,女性本真的尖锐性和生命的形态也被融进了诗歌语言,并以其独创性的形式构造,使生命经验和个人体验在书写中以透明而具体的形象呈现了出来。此外,琳子的一些童话诗也预示着她诗歌创作的一个新的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