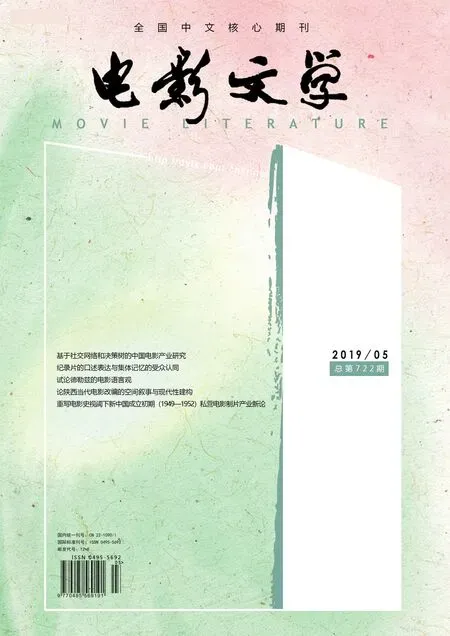新时期电影的传统伦理叙事及其“中国特征”
李慧君 (聊城大学 传媒技术学院,山东 聊城 252000)
20世纪80年代在许多研究者的笔下又被称为“新时期”,这一命名主要基于一种文化判断的“断裂观”,认为在“文革”前后的历史语境之间,存在着一场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各个层面的断裂与变迁。新时期中国电影与当时其他的文艺形态一样,在这一特殊的历史时段之内,经历了文化观念、艺术形态的剧变与转型。
“就电影作为一个大众媒体与观众接受、市场反响的关系而言,彼时的中国电影经历了最后的黄金时期。……在‘文革’结束之初的1979年,中国电影市场创下了全民平均观看电影达28次,全国观众达 293亿人次的空前纪录。”[1]在新时期能够取得票房与口碑双重成功的电影,首先必须要在电影的文化形态上契合大众的审美诉求,而中国大众的审美诉求又是由当时具体的历史文化语境和延续几千年的传统文化心理共同形构而成。从传统伦理的叙事动因出发,可以在一个大的历史语境下,考察新时期中国电影在叙事话语之间所呈现出的独特的“中国特征”。
一、传统伦理:文化观念与电影叙事
中国是一个有着几千年文明历史,又长期深受儒家伦理道德观念影响的民族,在漫长的历史积淀中,普通民众已经形成了以伦理道德为主导的心理结构。反映到文化取向上,包括电影在内,中国的文化产品要想得到大众的认可与欢迎,必须要充分考虑中国大众的传统文化心理,这是中国大众文化产品绕不过去的“中国性”与“中国特征”。
中国社会早期历史形成的独特性,造成了之后整个社会的思想资源和文化结构迥异于西方公民社会的建构。“传统伦理的逻辑原理与概念系统有三个基本的内涵:家国一体、伦理政治、人情主义。三者依次递进,形成中国伦理的基本构架,构成传统伦理‘中国特色’的基本内涵。”[2]这种“家国一体”的社会结构必然造成中国这样一个伦理色彩鲜明的社会,“内圣外王”“大学之道,在明明德”等儒家的伦理规范已经成为对社会大众的道德约束,并从一种外在的强加的道德意识逐渐内化为中国人自觉的伦理道德的心理结构,形构了大众的世界观、人生观与文化价值取向。
在电影观赏与接受的过程中,观众的世俗生活经验与传统知识谱系便成为他们审美选择的出发点。观众总是会从自身的生活经验与生存立场出发,进行对于外部世界的认知和解读。中国早期电影最早的剧情片之一,便是伦理教化色彩突出的《孤儿救祖记》。这部由郑正秋拍摄于1923年的电影,围绕着一个家庭祖孙三代之间的误会、纷争、冰释前嫌等情节,设计了一出典型的“父慈子孝”“家庭和睦”的情感伦理剧。之后中国早期电影商业属性的实现也大多围绕着满足大众的传统文化心理的主题选择,以及吸收民间文化的艺术形式而形成的“中国性”的大众电影文本。
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十七年”和“文革”时期,在“泛政治化”的历史语境下,中国电影也出现了高度政治化、政治活动与文化活动界限不清的局面。但是在这样一种“政治社会”的创作环境下,电影仍然为自身文化意义的生产争取到了狭窄的空间。当年许多受到大众欢迎的影片《羊城暗哨》(1957)、《今天我休息》(1959)、《大李、小李和老李》(1962)、《李双双》(1962)等,在今天看来几乎都是能够在主流话语的框架之内为大众文化的意义生产留存出一定“缝隙”的电影作品,观众就是在这些主导文化的缝隙之中发现了与自己的传统文化心理能够发生关联的文本意义。
新时期中国电影上承早期中国电影以及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电影发展历史的余脉,在中国社会20世纪80年代呈现出的独特的大众文化语境下,与西方的当代电影理论与思潮相结合,营构出了一个独特的电影文化格局。
二、政治与伦理的缝合:对观众传统文化心理的迎合与引导
新时期受到观众认可的主流电影,在叙事话语的选择上大多呈现出复合式的结构,一方面契合了政治话语宣传性的功能要求;另一方面又充分地利用传统伦理叙事吸引观众的观影兴趣。早自1979年的《小花》,晚至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主旋律”影片《焦裕禄》(1990)、《蒋筑英》(1992)等,无不在主流话语的叙事缝隙之中缝合进伦理道德的因素,构成吸引大众关注的主要原因。
《小花》(1979)这部影片的创作基点立足于控诉旧社会的万般罪恶,歌颂人民战争的无穷力量以及最终取得胜利的过程。但是整部影片真正成为观众的观影焦点之处,还是在于两个“小花”在交换身份之后如何回归到各自家庭的故事。这一故事的展开和收束分别将革命战争的低迷与胜利跟两个家庭的离散与团圆,形构为一个“家国叙事”的隐喻性结构。影片开头风雨交加的漆黑夜晚,在革命遭遇挫折的时刻,也正是小花的家庭因为贫困,无力抚养自己的孩子而不得不送出小花的时刻;经过一段充满戏剧性的找寻亲人与参加革命的阴差阳错的过程,最终在影片结尾战斗胜利之时,两个家庭也分别实现了各自的团聚。
这种将家庭的命运遭际与国家/民族的宏大历史进行同一性建构的叙事模式,在当时的许多主流影片中都或多或少地存在,其中尤其以谢晋的“反思三部曲”最为明显。《天云山传奇》(1980)、《牧马人》(1982)、《芙蓉镇》(1987)以“情感伦理剧”的类型模式成为接通电影艺术与大众观影欲望之间的桥梁,也成就了谢晋在中国电影史上的重要地位。
在中国具体的历史条件下,电影文化意义的生产过程往往是双向的,一方面国家主流意识形态所要求的时代主题可以借助电影的传播而得以实现其宣教效果;另一方面观众也不总是处在文化的被动接受地位,在主流话语的缝隙之间,观众也会基于自身的文化心理、情感态度、价值取向等,在电影中发现逸出主流意识形态的文化意义。
作为政治宣喻色彩鲜明的“主旋律”影片,其概念最先在1987年3月的全国故事片创作会议上被提出,“突出主旋律,坚持多样化”成为主流意识形态介入电影创作的政策导向。此后原先宽泛的“主流电影”的框架开始细分,“主旋律”电影成为党和国家电影政策下进行资金扶持的特定的历史产物。时至20世纪80年代末,“主旋律”电影相比新中国成立后30年间的主流电影,在商业性和大众化方面的处理显然要更为灵活。“前官方文化的道德是极度政治化、阶级化的,因而也是特殊取向的,而不是普遍取向的。作品中的正面主人公大都是爱憎分明的战士形象,这个形象身上体现的是一种特殊的伦理、阶级的爱憎(所谓‘亲不亲,阶级分’‘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人民的残忍’),而20世纪90年代主旋律影片中的正面人物开始向‘好人’形象转化,在‘好人’与‘战士’的差别中最重要的一条是:‘好人’的内涵更多地包含人类的共同道德与普遍价值,他/她身上体现的美德具有更大的普遍性与全人类性。”[3]
上述陶东风的论述中所谓的普遍价值并非简单的“人性”,而是中华民族的“伦理性”以及这种“伦理性”中体现出的“中国特征”。自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主旋律”电影也已经充分认识到了电影的大众文化性质的特殊性,在叙事内容上几乎都开始逐渐弱化了强硬、直白、刻板的政治宣教,在伦理叙事的框架之下缝合进政治话语的意识形态表述。
三、文化的惯性力量:传统伦理叙事的延续与变奏
在新时期改革开放的国家主导话语之下,由于经济、政治层面的政策调整,大众的文化心理也随之逐渐产生了一定的变化。带有鲜明时代色彩的显在的文化现象与民族传统文化心理之间,形成了一种表层结构与深层结构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一个民族的传统文化心理生成于长时期的历史过程之中,已经凝固为一种历史的惯性力量,具有根深蒂固的稳定性。许多深层文化结构的因素不会轻易地实现彻底的变更,于是在碰撞、吸纳、微调的过程之中便会显示出文化心理的复杂多样。
新时期的许多电影创作中已经出现了当时社会上所谓的“新人”形象,如《顽主》(1989)中的于观、杨重、马青;《轮回》(1988)中雷汉饰演的石岜;《雅马哈鱼档》(1984)中的阿龙、海仔;《女人街》(1984)中的欧阳穗红、白燕等。《顽主》的小说作者王朔曾经戏称于观等人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人”,这些“新人们”单从行为举止来看,已经显示出逐渐摆脱传统伦理观念束缚的迹象。
电影《顽主》中有一个情节段落讲述的是于观回家面对自己的父亲——一个退休老干部时,受到了父亲的质疑和奚落。当时父亲边在门后倒立边跟刚进门的于观说话,导演米家山在创作谈中明确地将这一画面的象征意义界定为“隐喻当代父子关系的颠倒”[4]。父亲因为对于观说话的态度不满意,而摆出家长的谱儿说道:“你忘了,小时候我怎么给你把尿的?”于观立刻回应:“咱们谁管谁叫爸爸?你要叫我爸爸我也给你把尿。”这一段话反映的不只是新的历史语境下父子两代人的隔阂,更重要的是通过儿子公然使用“大逆不道”的言论去反驳自己父亲的这一行为,对新的伦理态度的出现做出了隐喻性的指向。
虽然在这些具体的行为细节上,于观们几乎被塑造为新的历史语境下的一代“新人”,但是反观影片的整体架构却会发现一个近乎荒谬的悖论。整部影片的几个故事段落,几乎都在不遗余力地讲述于观、杨重、马青乃至后来加入他们的刘美萍,在一个开始显露出病态的社会中是如何保持自身道德品质的高尚,不但洁身自好而且乐于助人。而与他们相对应的影片中的另外一批角色,作家宝康、德育教授赵尧舜等知识分子,之所以会成为影片中的“反面角色”,是由于影片所给予观众的明显的暗示——这些人在道德上存在着严重的缺陷。可见,即使是一部明确地表现“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人”的带有解构性创作诉求的影片,无论从创作者自觉不自觉的主观思考还是影片所引发的客观效果,也还是使用了一套传统伦理道德的话语逻辑,对影片中的人物形象进行了明确的价值判定。
自中国儒家学说关于“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义利两分的价值观被提出以来,中国社会在漫长的文化论争、融合、建构的过程中,已经形成了重视伦理道德的非功利主义的文化精神,而且这一文化精神已经内化为中国人内心根深蒂固的传统伦理观念。中国电影只有在充分考虑到大众的传统伦理观念的基础上,才可以获得大众的情感接受,实现相应的文化功能。
四、结 语
电影作品要想俘获观众的观影兴趣,需要在影片的故事、情节、人物、画面等方面制造出与观众的观影诉求相关联、相贴近的因素。观众最基本的审美需求往往建立在自己最为感同身受的情感体验之上,而这种情感体验又保留着巨大的历史惯性的力量,内里潜隐着一头名叫“传统”的庞然大物。在今天回顾新时期中国电影,考察多种话语之中电影文化意义的生成与建构,可以从政治、历史、艺术等多个维度入手,其中传统伦理的因素紧紧贴近中国人的文化心理,在电影的艺术特征方面最具有“中国性”与“中国特征”。
将新时期中国电影放置于大众文化的视域下进行考察,基本的立足点便是20世纪80年代“不同以往”的“新时期”特征,但是在承认其“新时期”特征的同时,也应该考虑到传统文化强大的惯性力量,并非做一个简单的时间点的切分就可以将传统与现代截然分开。返归新时期的中国电影现场,将电影的创作、发行与接受的流程放置在当时中国那样一个驳杂的、复调性的历史场域之中,就会发现传统伦理的叙事因素在“新时期”直至今天的电影画面之间留下了深刻的历史印记。从传统伦理叙事的维度介入新时期的中国电影研究,可以为我们找寻到中国电影商业性与大众化发展至今的历史脉络,为当下的中国电影创作提供参考与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