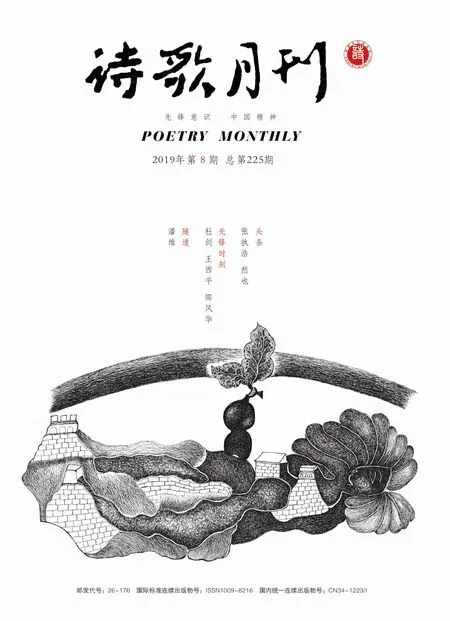张执浩的诗
张执浩
反刍的人
埋在米糠里的鸡蛋
封在坛子里的猪油
挂在屋梁上的腊肉
晾在簸箕上的薯干
摊在筛子里的腌鱼
倒扣在腌菜坛中的辣椒
堆放在火塘角落的花生
藏在竹林地窖里的红薯
悬在树丫上的丝瓜和葫芦
沉睡在草丛中的老南瓜
——哦,十根指头
已经不够用了
第十一根是香烟
供你在饭后反刍
第十二根是铁钉
好多年前就被钉在了墙上
好多年前它就已经生锈了
当它什么都不挂的时候
它连锈迹也挂不住
催咚催
打过菜籽的梿枷又打在了麦穗上
捅过猪的刀早晚会插进
牛的喉咙——牛拉着石磙
一遍遍在禾场上走——
闪亮的刀尖必须用血蒙住
而我们被尘埃蒙住了
快活的泥水从腮帮上滚下来
被大地稳稳接住
死亡是一把巨大的扇子
扇得越快风却越小
我蜷缩在星光下
听见扇子从你手上滑落
看见又多活了一天的牛
在黑暗中眨动着
妩媚的长睫毛
重返旷野
落满麻雀的树枝背后
北风在蓄力
落满麻雀的草垛上
太阳走过,无声无息
父亲用棍棒轮换抽打着肩膀
落满灰尘的公路尽头
北风醒了
麻雀往南飞
我在麻雀腾空后的树枝上
留下过人猿的记忆
我用父亲留下的棍棒
四处戳捣,漫无目的
太阳昏昏欲睡的时候
我依然保持着少年特有的警醒
泡木耳
你不知道我有多喜欢木耳
你没有见过
每当我把它们浸泡在水里时
我们同时心满意足的样子
像刚从梦中醒来伸伸懒腰
侧身望着窗外
昨晚又下过雨了
现在雨过天晴
木耳趴在湿漉漉的枝桠上
静静地聆听水滴
落在腐叶上的声音
你不知道我也曾这样
沉浸在遗世的欢乐中
以为我们都能像木耳这样
逆来顺受,生生不息
以为这世上最动听的声音
是我热泪盈眶地抱着熟睡的你
却终于忍不住
落在你脸上的泪滴声
树叶走路的声音
树叶在空中走动时
你不一定留心过
嫩绿是一步
枯黄是另外一步
你在树下来回奔波
直到一片叶子落下来
一树落叶在秋风中形成旋涡
你抬头时看见
天空已经发生了变化
从前长满树叶的枝桠上
落满了不知从哪里飞来的鸟
到了晚上,凌晨时分
大地上全是树叶的走动声
它们从树下跑到墙根下
它们集合又分散
多么像走投无路的人
走着走着
就消逝在了道路尽头
鸡冠颂
我喜欢看血红的鸡冠
锯齿一样长在公鸡的头顶
夕阳西下的时候
透过它就能看见
冬日里
雪地上
鸡群零散的爪痕
一只公鸡来回走在爪痕之上
拍打翅膀,警觉地
张望着
踢毽子的我们
河对岸的人也与我们一样
在忙腊月的事情
河对岸的公鸡打鸣了
这是庄严的时刻——
所有的鸡都往鸡笼附近归拢
唯有公鸡独自站在夜幕中
对着河水流逝的方向
鸣叫起来
我在公鸡的叫唤声中
进屋,拉上门闩
在火塘边坐下
周围都是黑夜
我喜欢那个坐立不安的人
墙壁上有他的身影
雪地上有他身体的凹痕
最遥远的雪
想起雪后的那些晚上
天空清凉,还有星星
我能看到你家的屋顶
以及屋后黛色的竹林
半夜里旷野上传来
树枝脆断的声响
有人踏雪归来,含着痰
想起我们在一起的日子
阳光刺眼,看不清
雪人明晃晃的表情
只有胡萝卜是橙黄的
只有桃核做的眼睛圆睁着
我们走在结冰的塘面上
身前身后都是冰面的炸裂声
想起你至今没有上岸
最后的雪积在人去屋空的檐下
每天静静地化一点
我忍不住朝天边探了探身体
停止生长的脚
我穿41 码的鞋子
40 码找过我
42 码找不到我
我穿我妻子给我买的鞋子
好像只有她知道
什么样式适合我的脚
我穿皮鞋,运动鞋
几乎从不穿凉鞋
走在你也走过的路上
只有当我赤脚时
我走的路才是我自己的路
我不穿鞋的时候我的脚
在回望那条路
我不穿鞋的时候那条路上
有我深深浅浅的脚模
我的拇指总爱那样翘着
当它往下抠时
我一定正陷在泥泞中
我已经很多年没有赤脚走路了
我最后一次在岩子河里洗脚
是在哪一年的隆冬?
那一年我的脚已经停止了生长
我母亲还活着
我记得她把我的鞋样夹在了
一摞废弃的高考复习资料中
此后只有指甲在生长
只有鞋子在重复着脚的形状
有一次
有一次我决定
自己动手缝一枚纽扣
打开针线盒
找到了针和线
我来到窗边找到了
线头,和针孔
我一次次调换针线的角度
以为自己不会认输
有一次我决定
不再帮妈妈穿针了
我厌倦了需要她照顾的生活
我以为我已经赢得了生活
再也用不着为一枚
掉落的纽扣发愁
有一次我衬衣上的第三颗纽扣掉了
我拿着纽扣在书桌上转动
母亲在桌前的相框里微笑
她以为我永远不会服输
更好的人
晨起熬粥的人在鸟鸣声中
喝下粥,他清楚地听见
送奶工把手伸进了奶箱盒
晨起看日出的人在山顶的浓雾里
眺望浓雾,哦浓雾
晨起讨生活,终究还是晚了
更好的生活已经名花有主
更多的人像我一样
在梦里艰难地挪动
更好的人配得上这样的
一天——既新鲜又世俗
他将在碌碌无为中享用
身体里塞满了懊恼与满足
他配得上这样的白日梦
谁也不会去打搅他
他也不会去说服谁
武汉在下雨
武汉在下雨
我能告诉你的是
我穿着T 恤
感觉到了冷
我能告诉你的是这种冷
不同于上一次
上次我们还在一起
你总是先抱紧自己
然后才犹豫着
跑过来
让我抱紧你
吊扇之诗
头顶上的这台吊扇
已经在我的头顶上盘旋了二十多年
木质的,四叶的,电动的
每次搬家我都带着它
它一定明白我的新居也是它的新居
因此总是格外卖力
从来不曾罢过工
春天已近尾声
热浪逼近
我刚刚把它打开了
用了最小的档位
它仍然是无声的,徐徐的
这么好的风
才配得上写诗的凉皮肤的人
回答
你要我给你写首诗
这很容易。写诗不过是
石头落地,危险又美丽
但我心存另外一块顽石
上面刻满了致命的纹饰
什么时候我能把它举过头顶
什么时候你跑出了它的阴影
发现天边不过是
另外一座陨石坑
发现我不过是一个人
站在坑洞里重复干着
一件化险为夷的事情
关于我的睡姿
我没有见过我的睡姿
当我像虾米一样
蜷曲,或者像那个人
被钉在十字架上
我能感觉到身体正在挣脱
梦中人赋予它的原形
我总是在入睡前翻来覆去
而入睡后难道会像一片云?
我这样设计过
与你同床共枕
的情景——两朵云
如胶似漆叠加在一起
雨在下面,雨一直在下
我一直这样保持着干涸的模样
像你小时候在泥塘里见过的
那条挣扎着的鱼
当它放弃了挣扎
也就完成了命运对它的塑形
在一起
1986 年我的父亲母亲在黄鹤楼下
留下过一张合影。没想到
这成了他俩现存的唯一的
一张合影
母亲去世后,父亲把它翻出来
父亲去世后,我们把它翻出来
打算用在他们的合墓碑上
从去年清明节开始
我们计划着这件事
但按老家的规矩
得在三年之后才能落实
现在每次回去我都要
先去母亲的坟前劝她再耐心点
再去父亲的墓前劝他不要着急
现在每次看到这张合影
都感觉有一把看不见的尺子
在丈量着他俩生前的距离
死后的距离,以及
他们与我之间的距离
在一起的愿望从来不曾如此强烈
汇合
如果没有风
玉兰树的叶子永远没有机会
与香樟树的叶子在大地上相逢
当它们在暮春的清晨
被两把笤帚扫到一起
如果不是因为身处困境
笤帚的主人可能不是他们
每天清晨我听见楼下传来
笤帚划过大地的刺啦声
一个从楼后,一个从楼前
它们汇合的时候曾有过片刻的宁静
之后像两个久别重逢的人
高声谈论着生活的见闻
如果落叶能听懂他俩的方言
就不会奇怪造物主的安排
两把笤帚在清扫完成之后
被归并到了蓝色的垃圾桶内
如果此时我还能入睡
一定是因为我太孤单了
已经接受了被人类抛弃的理由
暮色四合之地
很难再见暮色四合之地了
晚风徐徐,晚霞淡去
亲人们在鸡飞狗跳声中归来
父亲蹲在水边先擦拭农具,再将
洗净的脚塞进湿滑的鞋帮里
母亲把干透的衣服拢成一堆
扔进姐姐们的怀中
很难再见我那么肮脏的脸上
浮现出来的干净和轻盈
只有黑暗在无声无息中包围住我们
却不知房间里的光从哪里亮起
在雨天睡觉
我能把握的幸福已经很少了
在雨天睡觉算是一种
窗外大雨瓢泼
我已经醒来却还在等待
另外一个梦成型
哪怕再也无法入睡
只是闭上眼心平气和地
想一想:我与他们
有什么不一样?有什么
是我行至人生中途还能把握的
云团挣脱天空
雨点收不住脚
来到大地上的事物相互混淆
我已经有过长久的浑浊
现在我想变得清澈些
就像现在这样
窗外在下雨
看样子还会下下去
这大概就是你说的幸福
我能预感某张亲切的脸
正从虚掩着的门缝里看我
却不惊扰我
替我回家的人
替我回家的人给我带回来
三样东西——
松香、桃胶和地衣
每一样都酷似我记忆中的样子
每一样都有出处和来历——
松香照见了黑松林里的
那座几乎平塌的孤坟
桃胶透亮,像一簇挣扎着
从桃树内部挤出来的光
我记得最可口的扁桃
长在活死人门前的堰堤上
夏夜里,他就睡在树下
楠竹凉床吱吱作响
而一场雨后,被践踏过的
青草翻山越岭来到了
我即将离开的故土
大地空蒙,蹲踞其上的
是深秋的草木
从天末吹过来的凉风
让捡地衣的母亲想到了我
她抬头望望飞奔的云朵
她低头加快了手中的动作
乌龟之徙
一只乌龟从雨后的柴垛里
爬出来,举着可笑的脑袋
在它到达目的地之前
没有人知道它的目的
一只乌龟缩在我的记忆深处
它一动不动的时候
我的记忆一片沉寂
晚霞收敛于一朵蘑菇上
蘑菇会在夜晚生长
乌龟也会在黑暗中爬行
那一年我并没有生活
我在生病,求生的欲望
让我在夜晚依然竖着耳朵
谛听人世的动静
一只乌龟从暗中爬出来
它慌不择路的时候
我正走在胡乱求医的路上
那时候的天空真是蓝啊
乌龟举着脑袋
慈祥地看着
我在生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