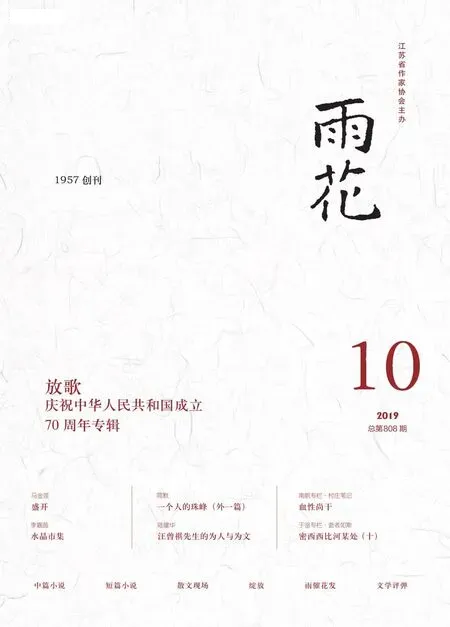经世学问与禅机
黄复彩
嗑瓜子
长桌上铺着毡子,一方很大的石砚,看上去有些年头了,一杆毛笔浸在墨洗里,主人像是刚刚离去。靠墙处的博古架上有文玩、铜佛,还有一两只罐子,粗陶的那种。茶桌就安放在屋子的中间,茶具看上去有些古旧,却是景德镇的老窑。捧在手里,蛋青色的杯壁映着杯中微黄的茶色,温润而又清凉。
一僧三俗,都是相交多年的朋友。僧是翠峰寺的印刚和尚,余者三人是应和尚之邀请前来议事的。和尚开始熟练地洗着茶具,泡茶,玩着他带点禅意的幽默。茶是大红袍,倒在杯里,呈淡黄色,呷在口里,有一股荷叶的清香。这时,门锁咔嚓一响,进来一人,正是这屋的主人。先是一愣,很快便满面春风。和尚反客为主,招呼室主就坐,说:“此刻你应该在想,我的领地怎么来了这么一干人?”主人说:“贵客驾到,欢迎,欢迎。”看了看茶桌,又说:“喝点寡茶?”说时,便从抽屉里拿出一样又一样来,小子花生,姜丝,一碟西瓜子,还有黄山茶干,茶好,人好,佐茶的小吃又好,谈兴一下子就浓了起来。
这几年,接触些文人雅士,也学会了喝功夫茶,一小口一小口地呷,一丝一丝地品。想着竹峰《衣饭书》中各种写茶的文章,便佩服他小小年纪,却如此精于茶道,当然是“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你只管妙笔生花,却不会有人说你写得不对。就如我上面所说“一股荷叶的清香”,鬼又知道呢?
喝功夫茶是有闲阶层的事情,嗑瓜子也是有闲阶层的事情。想着年轻时挖塘泥,推板车的时候,又何曾想到老了却做了有闲阶层?我家里有一个人总是说我“有福不会享”。她之所指,是说我老都老了,还在没命地写作,没命地工作。但她不知道,我的福,都是我年轻时积攒的,正是那时候的苦,为我的中年培植了福报,而中年的苦,亦为老年培植了福报。我现在依然在努力着,在辛苦着,如果真有来世,我就为来世积攒更多的福报吧,免得我再像今世一样,整个童年过得人鬼不知。
我的苦债,三十岁前算是尝尽了,他人又岂能知道?我现在之苦,乃是我自找的苦,但凡自家乐意的,就分不出何谓苦,何谓乐。想我之一生,只做对了一件事,为了这件事,从少年做到中年,如今老了,却依然在做,且做得还算不坏。一个人为自己的心性而努力着,又何苦之有?九华山肉身殿有一副对联:福被人物无穷尽,慧同日月常瞻依。于我者,余下的,是要学会珍惜。惜福,惜福,没有人生的大境界,又何谈惜福?
几个人相聚而来,原是要商讨一件事情的。喝着茶,嗑着瓜子,话题就走开了,话也是有一搭、无一搭的。瓜子是好东西,嗑着瓜子,听着瓜子从牙缝中发出来的咔嘣咔嘣的声响,就像是一段慢板中的爬音,是一曲长调的一部分。瓜子颗粒不大,但嗑起来,却是满舌生香。主人每人面前发一张餐巾纸,嗑过的瓜子壳就吐在上面。自从多了一颗假牙,我多年不嗑瓜子了,嗑出来的瓜子壳细碎而杂乱,但看一旁的彼们,却全是一瓣两开,完整得像艺术品。便叹道,世间的事,哪一样都是经世学问,就如这嗑瓜子。
室雅何须大,花香不在多,一室,五人,一僧,四俗,喝着茶,嗑着瓜子,逝者如斯,天色渐暗,遂四散而去。一直等走出山门,冷风拂面,忽然想起,呀,大家相聚于一室,原是要聊一件要紧的事情的,结果却什么也没有聊。满嘴却是茶的清味,瓜子的余香。甚好甚好。
吃黄烟
父亲吃了一辈子的酒,也吃了一辈子的烟。不错,是吃酒、吃烟,父亲就是这么说的。他不说抽烟,也不说喝酒,就说吃酒,吃烟,父亲那一代人都是这么说的。在那个年代,吃是多么重要的事情,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人都懂得这“吃”字是性命攸关的大事,是人生之第一大事。吃烟、吃酒、吃茶、吃斋、吃请、吃累,更有骂人的话:吃枪子的,吃白饭的,如此等等。
父亲吃酒也无讲究,而吃的烟,大部分是老家里他的那些老弟兄们自制的黄烟。吃这种烟,纸媒子便是必需的物件。每隔几天,父亲总要把时间大把地花在搓纸媒子这件工作上。将大表纸一张一张地裁好,再用手搓成纸媒子,纸媒子须搓得细细的,长长的,不空不实,恰到好处;搓纸媒子是一门学问,吹纸媒子是另一门学问。点燃了的纸媒子先是暗火,用时,嘴唇微微一合,舌头恰到好处地轻轻一吐,口里“噗”的一声,纸媒子就点着了,点成一粒如豆的焰火,父亲就用他的包着铜皮的烟袋杯子凑到这一豆焰火上,深吸一口,再很享受地喷吐出来,屋子里顿时弥漫起一团呛辣的黄烟味。
有时候,是在半夜里,我从睡梦中醒来,看到床那头光闪明灭,幽暗的火光照着父亲下巴上的胡须,衬着父亲因瘦而显得棱角分明的脸,还有额头上沟壑一般的皱纹。父亲的棉袄就搭在我的肩头,闻着父亲棉袄上松木刨花的香味,想着父亲的不易,想着父亲一生中所经历的苦难、屈辱和辛劳,泪水悄悄地滚到腮上。我赶紧把头缩进被窝。
我喜欢看父亲吃烟,喜欢看父亲那“噗”的一口,“噗”的又一口,纸媒子在他的手里像变戏法一样,要明则明,要暗则暗。我也曾学着父亲,“噗”,一口,“噗”,又一口,可就是不能吹出如豆的火焰来,父亲便说:“世间的事,哪一样都是经世学问,哪一样都轻视不得。”
螳螂
为了一本书稿的最后修订,我住到头陀岭下九珍农庄的一间木屋里。在这个深秋季节,木屋四周虫声唧唧,云雀从屋顶上飞过,丢下一片尖锐的叫声;不断有成熟的果实从树冠上落下来,打在灌木上,声音是夸张的,我想,这大约就是《五灯会元》里所说“溪花含玉露,庭果落金台”的亘古禅境吧。
我是在吃完早饭回来的路上看到这只螳螂的。当时它趴在墙垛上,一动也不动。围墙不高,正好齐腰,另一面却是悬崖或深渊,被层层灌木覆盖。我曾经分不清蚂蚱与螳螂,并将它们混为一谈。后来知道,螳螂是螳螂,蚂蚱是蚂蚱。应该说,我喜欢蚂蚱,喜欢蚂蚱那略显肥胖的身姿,喜欢它通体美丽的斑纹。童年时,我们用草绳拴住蚂蚱,看着它贴地飞翔,却又逃不出我们管控的滑稽姿态,或者将蚂蚱扔进油锅,那是一道美食。而螳螂,不要说那两把令人生畏的大刀般的前臂,单是那单调而不成比例的体型就足以让人远离了。
在我的生活中,螳螂并不是什么稀罕的东西,但也并不常见。正因为如此,当看到一只螳螂一动不动地趴在光溜溜的墙垛上时,便习惯性地打开手机,准备拍几幅螳螂的图片。我尽可能小心翼翼,以免惊动了这只体型壮硕的螳螂。我从各个角度一连拍了十几幅图片,那只螳螂依然趴在那里,一动也不动。如果不是看到它的触须在我的眼皮子底下轻微地摆动了几下,我还真以为这是一只没有生命的螳螂。
我再次经过这条路时,已是三小时后。那只螳螂居然还蛰伏在那里,蛰伏在光溜溜的围墙垛上。我之所以换一个名词:蛰伏,是觉得用这个词更能准确地形容那只一连数小时趴在一个地方不肯挪窝的螳螂的坚毅和耐力。想起那个著名的成语,我开始仔细地观察四周,至少,在它四周一公尺内,我没有发现任何可疑的猎物。然而云雀的叫声让我意识到危险的存在,我很想将它移到墙垛另一面的深渊中去,那里应该是一个安全的所在。然而又想,是云雀,总是要吃螳螂的,是螳螂,总是要被云雀来吃的。生物界的因果法则,没有谁能够逃脱,就像螳螂注定要以蝉为食一样。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成语出自《庄子·山木》,而其后对这一成语作最生动诠释的是西汉时刘向的《说苑·正谏》:一个孩子用肢体语言演绎了这条成语,从而阻止了一场即将爆发的战争。这则故事的意义就在于,一次生动的演绎要比一百套理论说教的方案更有用。
看过一个科普动画片,是关于螳螂夫妇之间残忍的交配活动的。在交配过程中,雌螳螂一边享受着性爱的快乐,一边却将她的夫君一点点吃掉。而奇怪的是,那只雄螳螂明知这是一场致命的绝杀,却宁可选择在极致的快乐中死去。我想只有两种可能,其一,追求性爱本能的雄性螳螂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去尝试性爱的。毕竟,对于一个有情生命来说,性爱是一种快乐,其次才是延续后代。想起我熟悉的一个孩子在其叛逆期与父亲的一场争吵中回敬父亲的话:我不过是你们一时快乐与激情之后的产物。其二,为了延续和繁育后代,这只雄性螳螂宁可赴死。它静静地待在这里,等待另一只异性同伴的到来。这样的死,是带着某种悲壮色彩的,由此可见生命之庄严,之伟大。如果真是如此,这位勇敢赴死的螳螂便是一位伟大的父亲。
我再次用手机对准这只雄性螳螂肆无忌惮地拍了几幅近景。回到屋里,当我将手机中的照片放大,第一次近距离地观察一只雄性螳螂时,我意识到,以前对螳螂的认识是错误的。这只螳螂简直就是力的化身,单是那两只大刀般的前臂,就足以展现出一只昆虫的雄性之美。这种美,是一点也不逊于四肢发达的人类的。
我走出木屋,我要再去好好看看那只螳螂,我对那只长时间蛰伏在那里的螳螂不能不生起特别的好奇心。我想象着它蛰伏在那里,是在等待一只雌螳螂的到来吗?或者,在我发现它之前,这里已经发生过一次生死之爱,但它却是一只侥幸存活下来的螳螂。它蛰伏在那里,是因为一场激战过后的疲惫?是因为庆祝一次不死的劫难?或者都不是,它只是经过那里,就像人类一样,唯有经过生死之劫,方才意识到“生命好在无意义”(木心语)。又想起赵朴初先生的一句诗:“作善有善报,作恶有恶报,莫羡忉利天,转眼泥犁掉。”这只长时间蛰伏在这里的螳螂是否像人类一样,在经历了一场决战之后,终于石破天惊地悟出了某种禅机呢?
然而当我再次走到那围墙垛前时,螳螂已不见了。
我写下这篇文章,以纪念一只以某种神秘意义出现在我生活中的螳螂,还有那个奇妙的上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