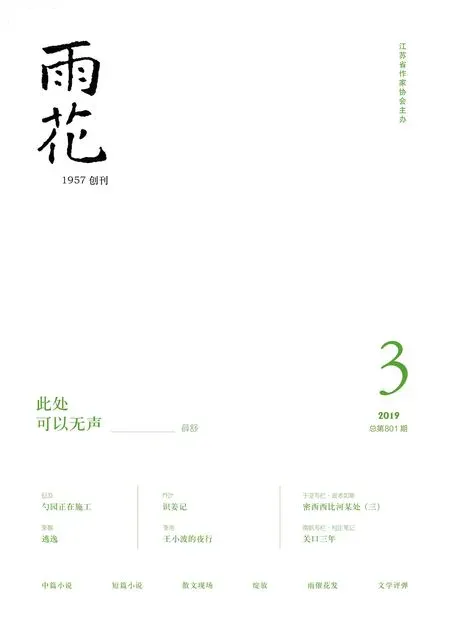识姜记
1
也许在很多人的感觉里,怀这个字的核心之旨便是怀抱的怀。于我的记忆而言,怀的第一要义却是怀庆府的怀——怀庆府,是家乡焦作的古称。小时候,每当听长辈们说起咱们怀庆府如何如何,我心里总是有些抗拒地腹诽着:都什么年代了,还府啊府的,听起来就很腐嘛。还有,府,这就是个大院子的感觉,明显不如“市”的气派大呀。
直到现在,才慢慢品出“怀庆府”的意味,实在是比“市”要深远,也比“市”更有温度——“我们都是怀庆府的人”,和同乡这么叙起来的时候,俨然共用着一个家门,可不是更有温度?
因为怀庆府的缘故,我们这一块豫北平原,还有一个别名,就叫怀川,又叫牛角川,因它是牛角状的。这一块由狭至宽的丰腴之地,四季分明,日照充足,地下水丰富,无霜期长,雨量适中,不客气地说,是种什么什么就好,极有代表性的特产就是四大怀药:菊花,牛膝,地黄,山药。尤以山药最负盛名,对,就是铁棍山药——就是那个男人吃多了女人受不了、女人吃多了男人受不了、男女都吃多了床受不了、种多了地受不了的铁棍山药。
除了这四大样,还有许多好东西。比如怀姜。
如同有羊的地方都认为自家的羊肉最鲜美一样,凡是种姜的地方,似乎也都认为自家的姜最好——不管别地儿的姜怎么想,反正我们怀庆府的人就当仁不让地认为:怀姜是全中国最好的姜,也许没有之一。
史载怀姜迄今已有1600多年的种植史,晋代诗人潘岳任怀庆令时,就留下了“瓜瓞蔓长苞,姜杆纷广畦”的诗句。这姜,在这样的地方,被种了这么长时间,如今又成为了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怎么可能不好呢?
不过,说来惭愧,吃怀姜吃了这么多年,却从不曾见过它生长时的模样,唯一知道的是它和树没啥关系。唐代有个段子,叫《楚人有不识姜者》:“楚人有生而不识姜者,曰:‘此从树上结成。’或曰:‘从土地生成。’其人固执己见,曰:‘请与子以十人为质,以所乘驴为赌。’已而遍问十人,皆曰:‘土里出也。’其人哑然失色,曰:‘驴则付汝,姜还树生。’”
虽然主角是楚人,但我着实怀疑这故事产自我们怀庆府,因为其中提到了驴,我们怀庆府的沁阳就盛产驴,其特有的美味就叫做怀府闹汤驴肉。
2
终于,这个秋天,十月末,和几个朋友一起,在当地土著带领下,我在博爱看见了怀姜的第一现场。
怀姜又叫清化姜。所谓清化,就是博爱县城的所在地清化镇。因此以我非常粗线条的理解,怀姜约等于博爱姜。当然博爱本土对此还有着极其精微的认定,说到姜,博爱人有句口头禅:“前乔篓,后乔筐,苏寨萝卜,上庄姜。”前乔、后乔、苏寨、上庄都是村名儿,这么说来,上庄姜一定是顶顶好的。不过依我的浅见,总觉得它有点儿被神话的意思。同在一块大地上,相隔又不远,即使不是上庄,那其他村子的姜应该也会很不错吧。比如眼前的西金城村。
当家的地主老兄说,这片姜田有三百亩,属于他的有八十亩。一眼看去,果然是很大的一片地。湛蓝的天空下,姜田里呈现着悦目的秋香绿。有的姜苗已经倒地了,有的还在挺拔地生长着。横着也好,竖着也好,横竖交织出一种油画的质感。
我们撒欢似地奔到地里——不得不承认,我骨子里就是一个农民,看见地,心就跳得格外厉害,不,应该是伪农民,要是真正的农民,应该会表现得很淡定吧。伪农民首先做的事就是庸俗地拍照。整株的姜苗高度及膝,叶片的形状有点儿像竹子。我揪着一片叶子闻了一下,一股子不那么浓烈的,清爽的新鲜的姜香。又好奇姜花是什么样儿,有朋友说,姜花是白色的,有点儿像剑兰。
远远地,一些人花花绿绿地散落在姜田里忙碌着,应该是本地的农妇们吧。走近,果然是农妇们正在拔姜、摘姜。跟她们搭讪,她们只是憨厚地笑笑,不怎么接话。我们便来到她们不远处,学着她们的样子弯腰去拔姜。拔姜拔姜,拔这个动词,听着就有游戏的意思,似乎不用付出太大的体力。可是我们拔一下,拔两下,姜依然在那里。再加一把劲儿,拔出来的姜块却是断裂的。
“不是那么拔的。”她们笑起来。连忙告诉我们,是应该用犁把土松一下,再去拔。
“那边的田垄有犁好的,你们去拔吧。”
好嘞。我们就去那边拔吧。
3
这下果然好拔了,几乎不费吹灰之力。于是我们拔啊,拔啊,拔了一会儿,便把姜们排成排,又是很庸俗地拍照,拍,拍,拍。和姜拍够了,又想和正在摘姜的农妇们合影,人家都不怎么情愿。是,我们这样,也真是讨人嫌,耽误人家干活儿呢。实在被我们纠缠不过,她们才勉强跟我们配合一下。合影的时候,她们笑得倒也是很开心。
拔够了,就摘。我们识趣地把摘下的姜块放在她们的姜堆上,聊作弥补——不,不应该叫姜堆,应该叫姜山。小小的,山。想到张娇,就凑成了一句:姜山如此多娇。把这小姜山放在一个塑料桶里,就叫做一桶姜山。只管让那个“一统江山”磅礴去吧,咱们这一桶姜山,要的就是一个稚拙可爱啊。
摘姜就更简单,就那么轻轻一掰,姜块就乖乖地离了根茎。刚摘出来的姜,带着一点点嫩嫩的胭脂红,似乎有点儿害羞,非常漂亮。她们的身上还有一点点儿浮土,可那浮土是那么干净,一点儿也不脏,反而使得她们的胭脂红更为动人——不由自主地,就把姜称为了“她们”,可这样的小模样,不就是少女才有的神韵?再一琢磨,姜,这个字,看起来就是美女的简写嘛。
——被人嘲笑过几次,不敢妄自揣测,连忙查了度娘。度娘说,姜,字从羊从女。“羊”,意为“驯顺”,与“女”相合,意为“驯顺的女子”。这么说,从造字本意来看,姜是指像羊一般温顺的女性。作为姓的姜,身份就更为贵重,她起源于母系社会。姓和氏在古代有严格区别,姓代表氏族的血统,称为族姓,是区分血缘的识别标志,所以最早的姓,如姚、姬等皆从女。
原来,姜还真是有性别的。果然就是女。
4
那么,“姜是老的辣”的老姜,又有什么讲究呢?农妇们告诉我们,把鲜姜存放起来,存放个半年以上,最好是一年以上,就是老姜了。总之,是得隔年。隔年,就意味着这些少不更事的鲜姜最起码要经历春秋冬三季,把这世上的风霜雨雪尝个差不多。
然后,就真的老了。
然后,就真的辣了。
然后,就像《吕氏春秋·本味》里说的那样,成为了“和之美者”——调和食物的美味。
朱熹在《论语集注》中的夸赞更给力,他说:“姜能通神明,去秽恶。”毫无疑问,有这等强悍功能的姜,必定是老姜。
什么又是最好的老姜?农妇们给我们找出一排嫩姜下面牵连着的那块姜,说这就是最好的老姜。每到种姜时节,她们会挑选出上好的姜,把她当作母亲。而这些姜做了母亲之后,又会被激发出最大的能量,从而成为了最好的老姜。
也就是说,能用来做母亲的姜,就是最好的老姜。这些个老姜,就叫做姜母,或者母姜。
“女子本弱,为母则刚。”这话,说的原本就是姜吧?或者,可以换句话说:“女子本弱,为母如姜”?
和娇嫩的子姜们相比,这块老姜已然是一副老母亲的模样,黯淡,沧桑,沉着。她不美。不过,用美不美来形容她,也是不适合的。极不合适。这最好的老姜,已经超越了美。或者说,她有着最大的美。
告别时,农妇们仍在田地里默默地忙碌。最后和我们合影的是一位脸膛黑红的农妇。看我贴在她的身边蹲下,她让我离远一些,说她的衣服脏。怎么会脏呢?我紧紧地挨着她。她叫什么名字,我不知道。我知道的是,她一定是一位母亲。
5
中午吃的是鲜姜炒肉片,自然是鲜得掉眉毛。有行家在,一路涨知识,听他们条分缕析地讲怀姜的好,就更觉得口口美妙。和别家的姜比起来,怀姜到底好在哪儿?他们说,怀姜有几个“格外”:味道格外辛辣,丝格外细,还格外耐煮,简直是百煮不烂。有人感叹,只是这姜再好,大多也不过是用来厨房调味的配角,炖汤,炒菜,这些用度都微乎其微。相比起来,感冒时熬姜汤喝它倒是主角,可谁整天感冒呢?这姜再好,也不能为了喝它而整天感冒吧?
“喝姜糖膏嘛。”
是啊,怎么把姜糖膏给忘了呢。姜糖膏装在一个小小的瓶子里,有点儿蜂蜜的样子,一入口,你就会知道,它和蜂蜜很不同。既是姜熬出来的膏,自然是姜的精华,这精华的效用就近乎于可爱的保健药:驱寒,发汗,化痰,止咳,补中,养肝,解酒,止吐,防暑,除湿……对于女人尤其好的是,可以用来暖:暖宫,暖胃。我胃寒,喝它用来暖胃正对症,所以常在手边放着,想起来就冲一杯喝。有时候喝咖啡,也用它替代蜂蜜,居然也有很不错的口感。
“想亲手熬吗?一会儿带你们去感受一下。”
我一怔。从来没想到要亲手熬它。熬,想起来就觉得艰难。尽管我好奇心很强,对这件事却还是知难而退。若不是这一天来博爱拔姜,我想这辈子也不会去做这件事。
确实有些出其不意,好在准备起来也很简单。等我们到了操作台前,黄澄澄的姜汁已经备好在玻璃瓶里,众目睽睽中,四个人各执一瓶,很有些仪式感地一起把姜汁倒入锅中。行家们在旁边指点着,我们用勺子搅啊搅的,等到稍微热了一些,就放进了一块红糖——是一大块,砖头那么大的块,说是古法红糖,赤黑里微微泛红,让人一看就口舌生津,仿佛尝到了一股凝固的甜。
按说这么一大块糖放进锅里,肯定会融化很长时间吧?实际上并没有。如冰遇火,只过了一会儿,糖就完全不见了,汤汁粘稠了许多,颜色也深了许多。于是就再用勺子搅啊搅啊,眼看着汤汁越来越热,越来越热。按说那么大一块糖融进去,汤肯定也会显得多吧?但却不知怎的,一点儿都不多。
到底是有些单调的劳动,最大的娱乐就是边熬边尝,我们聊着,搅着,隔一会儿尝一小口,再评判着。汤汁是宁静的,可尝到舌尖上却让人惊心动魄:那么辣,那么甜!这辣,不是辣椒的辣,辣椒的辣,是急吼吼的辣;也不是胡辣的辣,胡辣的辣,是粗鲁的、浓烈的辣。这就是怀姜的辣。这姜的辣,是细腻的、内敛的、含蓄的辣。
汤汁越来越浓。熬了有个把小时之后,我们暂停,把汁重新收回到了玻璃瓶里,恰好还是四瓶。多了砖头块大的红糖,居然还是四瓶。这真是有些奇妙啊。
我们各自带回去一瓶,说是要继续熬,把它熬成膏。也不知道他们熬了没有,反正我第二天就自己熬了。
6
我是用煮花茶的玻璃壶熬的,为的是看。熬起来才知道,根本看不清,汤汁在玻璃壶里,一片雾一样的混沌。
那就不看吧。且任它熬去。这边看两页书,那边熬半个小时,就停一停。再写几行字,那边再熬半个小时,就再停一停。总之,是这边做着事情,那边任它熬着。
心,越来越静了。
突然知道了为什么以前会认为熬有艰难的意思,那是因为熬的前面总有一个字,是煎。《说文解字》里说:“煎,熬也。凡有汁而干谓之煎。”如此说来,有汁不干就是熬了。再去辨析,煎和熬果然有细微的不同:因汁干了,煎和火的距离就近,热的速度就快,脾气就爆,性子就烈。不是有个词叫“急煎煎”么?熬呢,就不那么快,不那么爆,不那么烈。只要有汁,有耐力,有静气,有时间,那就按照自己的节奏来吧。所以,也有个词,叫“慢慢熬”。
从上午到下午,一整天,这点儿姜糖汁,我居然熬了七八个回合。加上在博爱熬的,算起来,该有四五个小时了。等到汤汁越来越少,到了玻璃壶的最低限,它开始报警,这表示它实在是熬不动了,我又不想这时候再加水,于是方才意犹未尽地终止,把熬好的姜糖汁一勺子一勺子地收到了玻璃瓶里——不能倒,太粘稠了——居然只装到了瓶的四分之一。
这时,我终于可以确认:汁成了膏。
晚上,有朋友来访,问我,你家这是什么香气?
有香气吗?
很浓。你还真是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
不是芝兰,是姜糖膏。
哦,是姜香啊。她感叹着,在客厅里转来转去,突然指着一个瓶子里插的东西问,这是什么?我说是姜叶。拔姜时,我顺便把一束新鲜的姜叶带回了家,就插在了这瓶子里。
怪不得呢,这叶子也有姜香哩。她笑道,怀姜这名字,意思就是姜香怀抱着你吧。
我拼命点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