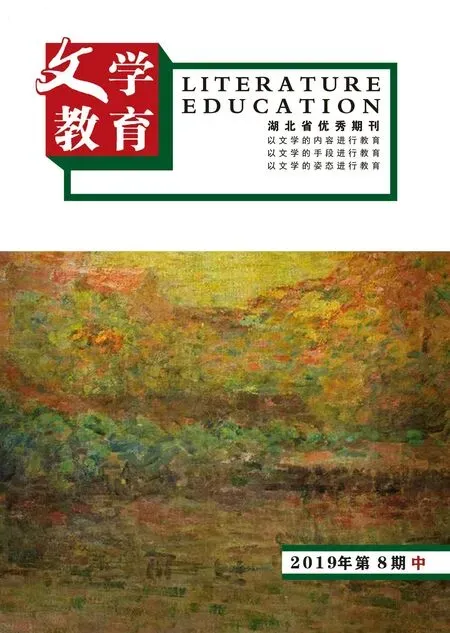从道家灵性哲学看“木石前盟”与“金玉良缘”
王 宁
《红楼梦》第五回贾宝玉神游太虚幻境时,警幻仙子命众仙姬为宝玉演奏的曲子中有一支《终身误》:“都道是金玉良姻,俺只念木石前盟。空对着山中高士晶莹雪;终不忘世外仙姝寂寞林。叹人间,美中不足今方信:纵然是齐眉举案,到底意难平”,即道出了“木石前盟”、“金玉良缘”两种关系的矛盾统一。曹雪芹在《红楼梦》中创设了幻境与现实两重世界,“木石前盟”与“金玉良缘”来自不同世界,存在前世与今世的时间差异,却因人物的相遇、关系的发展而发生碰撞。
所谓“木石前盟”,是指林黛玉本为西方灵河岸上三生石畔的一株绛珠仙草,追随赤瑕宫神瑛侍者下凡,用自己一世的眼泪回报他的灌溉之恩。而贾宝玉既是神瑛侍者在凡界的化身又是女蜗补天剩下的五色灵石变化为“通灵宝玉”的肉身寄托,宝玉之玉上所刻“莫失莫忘,仙寿恒昌”,与宝钗金项圈所刻“不离不弃,芳龄永继”两句正好成对,成就众人眼中美好婚配的“金玉良缘”。
书中描写了此对关系由萌芽、发展、高潮至悲剧结局的全过程,第一阶段为第三回至第十八回,黛玉、宝钗相继来到贾府,第五回提到黛玉、宝钗的判词“可叹停机德,堪怜咏絮才。玉带林中挂,金簪雪里埋。”暗示人物命运与关系走向。第二阶段为从十九回至二十六回,宝黛二人随着年龄增长,思想趋向一致,爱情也不断发展,黛玉与宝钗接触增多、摩擦加大。第三阶段为二十七回至八十三回,宝钗、黛玉裂隙加深,“木石前盟”与“金玉良缘”对比性大大增强,在各自轨道上迅速向前发展又彼此牵绊,第三十六回写宝玉随便睡在床上,宝钗坐在身边代袭人刺“鸳鸯戏莲”,不久宝玉昏昏入梦,在梦中骂道:“和尚道士的话如何信得?什么是金玉姻缘,我偏说是木石姻缘!”宝钗听闻不觉怔忪近乎直白地说明了“木石前盟”与“金玉良缘”的冲突走向尖锐化、激烈化;第四阶段为第四阶段八十四回至九十八回,黛玉抱憾辞世,宝玉与宝钗成婚后痴傻更加乃至出家,随着人物走向结局,“木石前盟”与“金玉良缘”的关系也走到终点。
从上述木、石、金、玉关系发展的脉络来看,“木石前盟”与“金玉良缘”处于对立统一、相互成全又相互毁灭的悖谬状态,抽象概括了人生无可奈何的悲剧,暗示了出路。
1.悖谬关系
《道德经》第二章“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盈,音声相和,前后相随,恒也。”道出了万事万物悖谬统一的存在,“木石前盟”与“金玉良缘”的关系亦是如此。
若无“木石前盟”的存在,也不会有“金玉良缘”的相逢;若无“金玉良缘”的阻隔,绛珠仙草也不会流尽一生眼泪,“木石前盟”也难以达成。贾宝玉、薛宝钗大婚完成“金玉良缘”,林黛玉怀着无限悲伤离开尘世,重新回归太虚幻境,宝玉出家之后也复其本来面目,依旧回归于三生石畔呵护那令人“心动神怡,魂消魄丧”的绛珠仙草,再续前盟。“木石前盟”与“金玉良缘”相生相和、相互成全,但又相互毁灭,从事件的发展经过来看,两种关系的存在直接造成了彼此的悲剧。宝黛二人一片深情,心心相印,却备受金玉之论的困扰。宝钗的出现转移了宝玉部分注意力,也让贾府长辈们看到了更合适的儿媳人选,使得“木石因缘”的实现被重重现实压力围困,日久天长难逃破灭之殇;另一方面,宝玉、宝钗大婚看似实现了众人眼中“金玉良缘”的圆满,但宝玉出家斩断俗世牵累,顺应“木石前盟”的呼唤,随同茫茫大士渺渺真人飘然离去,留下那“勘探停机德”的宝钗过着“焦首朝朝还暮暮,煎心日日复年年”的生活,不能不说是“金玉良缘”的荒唐。小说到结尾,有盟的未能成为眷属,却带走了对方的心;有缘的虽成了眷属,却永远也找不到精神的归宿。“木石前盟”是没有婚姻的爱情,可伤可悼;“金玉良缘”是没有爱情的婚姻,可悲可叹。
从人物来看,宝钗是现实中的胜利者,又是精神上的失败者;黛玉是现实中的失败者,却是精神上的胜利者。而宝玉神瑛侍者与通灵宝玉的双重身份造成了他在“木石前盟”与“金玉良缘”两重世界张力之下的尴尬,他既倾心于黛玉的灵慧与气质,又迷恋宝钗的雍容与风度,追求心灵的慰藉与追求现实的家庭生活两种不同的爱情与生活模式相互冲突,相互补充,无论是心甘情愿还是身不由己,宝玉始终在悖谬的关系中挣扎,最终顺应本心、回归自然。
2.悲剧实质
“林黛玉焚稿断痴情,薛宝钗出闺成大礼”是“木石前盟”与“金玉良缘”对立冲突的高潮。“洞房花烛夜”是人生四大喜事之一,生离死别又是人生大不幸大悲哀,大喜与大悲两种极致的情感交织一起,生死荣华铺陈一处,形成悖谬性的双峰对峙。曹雪芹通过极端冷静的叙事,探讨了客观真实与个人意志之间的冲突,即存在与能动的矛盾。这种悲悲喜喜的交织融合其实超越了一般的悖谬存在,直指人生存在的悲剧性与人性挣扎的复杂性。
这种复杂性首先表现为自然性与社会性的对立,玉石冲突是人的自然本性与社会属性冲突的变形。《道德经》第二十五章“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法自然”既可释为“道从自然,自然为大”又可释为“道性自然,无所法也”,前者突出了道的自然性,后者突出了道的本源性。
“木石前盟”是神瑛侍者与绛珠仙草的自然关系,“金玉良缘”是通灵宝玉与辟邪金锁的人饰关系。石乃自然之物,草亦自然生长;玉乃人饰之宝,金也需费人力雕琢。“木石前盟”顺应了自然法则,“金玉良缘”迎合了人世伦理。“木石前盟”象征人性的自由浪漫,是不带任何功利色彩的两情相悦;“金玉良缘”则是合乎礼法的门当户对,代表了世俗的理想规范,不可避免会有对本性的约束与挤压。“木石前盟”象征的自然性与“金玉良缘”象征的社会性随人物命运的不同也有不同的发展,黛玉这个象征自由浪漫的个体被现实社会排斥与驱逐乃至走向毁灭,表现了自然性在社会性的发展中易被破坏、易遭摧残的柔弱一面,而宝玉的出家遁世,象征了自然性的回归,暗示了顺从本心、顺其自然乃是人生的最终出路,表现了自然之韧,“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道德经》第四十三章)。”而“木石前盟”之“盟”与“金玉良缘”之“缘”的区别,表现了本源与偶发的差距。“盟”即“盟约”,产生于主观能动性的作用,是一种发于内心、根深蒂固且刻骨铭心的精神认同,“缘”则是“缘分”,是一种决定于外部条件、随机的人生遇合。道的本源性强调“无所法”、“无所恃”,“金玉良缘”成长于外在世界,当外部条件被摧毁(四大家族凋亡)自身也难以存在,而发自本源、生于自然的“木石前盟”却能在彼岸世界精神长存。
其二是内在追求与外在环境的对立,主客观的二律背反永恒存在。《道德经》中有诸多关于自然中两种运动此消彼长、此长彼消、相背相反规律的阐述:“企者不立,跨者不行;自见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无功;自矜者不长。(第二十四章)”“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敝则新,少则得,多则惑。是以圣人抱一为天下式。不自见,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长。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第二十二章)。”不单空空道人的至理名言:“好便是了,了便是好。若不了,便不好;若要好,须是了。(《好了歌》)”和太虚幻境牌坊两边的对联“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体现了这种朴素的辩证法精神,“木石前盟”与“金玉良缘”的对立冲突,也是这样永恒存在于宇宙人生的二律背反。就“木石前盟”与“金玉良缘”本身来看,作为悖谬存在的两方,此消彼长、此长彼消。而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正如王国维所言:“金石以之合,木石以之离,又岂有蛇蝎人物,非常之变故行于其间哉?不过通常之道德,通常之人情,通常之境遇为之而已。”而这“通常之道德”、“通常之人情”、“通常之境遇”当是主体与社会交融互摄,外在环境对内在追求的通常反应。当社会文化强调伦理本位、规范意识,便会挤占个体的生存空间,个体在抗争的过程中自我压缩直至自我意识牺牲,伴随自我消失社会也趋向崩溃。主观与客观的相互选择时刻进行,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身处的社会无法为青春的生命提供更多成长和发展的空间,个体生命与环境的冲突碰撞中一同粉碎、破灭。
3.永恒转化,归于自然
贾宝玉在“木石前盟”与“金玉良缘”两处挣扎,其命运轨迹也昭示着悖谬关系的发展。《红楼梦》初名《石头记》,其实展示了由“石”变形为“玉”再回归为“石”的三部曲,演绎人世的悲欢离合和生命的阴阳消长。宝玉本是顽石,“天不拘兮地不羁,心头无喜亦无悲”,历尘世十九年终于顿悟,小说结尾交代了宝玉的归宿:“那僧道仍携了玉到青埂峰下,将‘宝玉’安放在女娲炼石补天之处,各自云游而去。”宝玉的人间游历之路如一条抛物线,行至最高点之后,开始向相反的方向回落,这一回落也是向“心头无喜无悲”的本真生存状态的回归,静啸斋主人在《西游补问答》中对此有过精辟分析:“四万八千年俱是情根团结,悟通大道,必先空破情根;空破情根,必先走入情内,见得世界情根之虚,然后走出情外,认得道根之实。”这来于自然又归于自然的过程显现出道家循环理论的文化内涵,“反者道之动(第四十章)”“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静曰复命。复命曰常,知常曰明。(第十六章)”“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溪。为天下溪,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第二十八章)。”如何从“木石前盟”与“金玉良缘”的悖谬关系中脱身?道家灵性哲学回答返归自然、恢复本初乃是人生出路,《红楼梦》以家族悲剧和个人悲剧的双重书写警醒世人与“情天孽海”保持距离,勿忘自然之心才是主客观二律背反永恒斗争的长久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