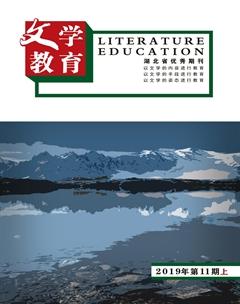批评与自我批评:布鲁克斯与沃伦的《杀人者》分析
内容摘要:布鲁克斯和沃伦对海明威的《杀人者》做出批评的同时,也对新批评做了自我批评。他们首先通过批评,使“自我批评”成为一种显示自我的批评,对新批评的宗旨、思路、理论倾向做了梳理、应用和审视。其次,他们使“自我批评”成为一种反思自我的批评,对新批评以文本为中心的局限进行了反思和突破。在“自我批评”的过程中,布鲁克斯和沃伦表现出了新批评基于“文本”理念所表现出的复杂性,并最终通过批评暗示了当中所蕴含的更根本的批评观念,即对社会、时代的关怀和责任感。
关键词:布鲁克斯 沃伦 《杀人者》 新批评
新批评派的重要成员布鲁克斯和沃伦,对海明威的短篇小说《杀人者》做了出色的分析。他们揭示了《杀人者》的主题,这首先是日常生活中发现并应对邪恶的成长主题,其次是人生根本情境的主题,其中包括了生存世界的粗暴混乱,以及人的勇气、诚实、忠贞、律己等纯朴美德。这篇文章除了新批评的鲜明特征(比如“细读法”)之外,还显示出了布鲁克斯和沃伦想要拓展新批评研究范围的努力。这也就意味着,我们在这篇文章中,不仅可以看到批评家对作家作品的批评,也可以看到新批评派的自我批评。
在文章中,布鲁克斯和沃伦聚焦于新批评最富有价值又饱受诟病的文本中心研究。这一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过分考证、过分注重作者原意(“意图谬误”)以及批评家自我膨胀(“感受谬误”)的问题,但从反面来说,这又使新批评自身拘囿于文本的狭小天地,与作者、世界乃至读者产生了断裂。
一.批评:显示自我的批评
新批评派的重要成员布鲁克斯和沃伦,对海明威的短篇小说《杀人者》做了出色的分析。而批评者在对小说进行批评的同时,自然也会显露出批评自身的特点。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就不仅可以把这篇评论看做是批评家对作家的“批评”,也可以将其看做是批评家的“自我批评”。也就是说,这是他们对自身理论的一次梳理、应用和审视。具体来看,这至少体现为四个方面:
首先,批评的开头表明了新批评的宗旨,即细节要通向主题。在这里,布鲁克斯和沃伦列出了小说某些“值得一提”的特点。显而易见,这些特点虽然直观,但也需要仔细的阅读和观察。当读者用“细读”法去分析作品时,就很有可能像布鲁克斯和沃伦所说的那样,陷入繁琐细碎的细节漩涡之中。因此,布鲁克斯和沃伦意欲将读者从这些“值得一提”的细节泥沼中拉出来,将他们引向新批评的真正方向:“这篇小说讲的是什么?”[1](P425)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布鲁克斯和沃伦试图传达一个信息,即他们并非“为细节而细节”。对细节做出分析,是为了发掘文本的主题。这是一种有导向、有意识的分析。可以说,“整部《理解小说》的要素分析,都是围绕解读作品‘意义和‘价值这个问题展开讨论的……布鲁克斯‘小说细读的出发点是从分析小说形式技巧入手,最终目的是解读意义和价值,这是‘新批评细读法与‘纯粹形式批评的最大区别”[2](P24)。
其次,新批评的分析以层层剖进的方式进行,这使得《杀人者》的主题与细节构成了一种有机整体的关系。具体说来,布鲁克斯和沃伦在提出“这篇小说讲的是什么”之后,便开始解释小说经场景暗示出来的结构。他们将其视为“大”结构,从中分析出小说的基本主题之后,再探索“小”结构,即分析细节及其意义,以此对主题进行“检验”。他们提出,如果主题正确,那么这些细节的意义都会“指向”这个主题。在这个具体的批评实践中,我们看到了新批评的理论基础,比如亚里士多德的“有机论”:“情节……的事件要有紧密的组织,任何部分一经挪动或删削,就会使整体松动脱节。要有某一部分可有可无,并不引起显著的差异,那就不是整体中的有机部分。”[3](P43)我们还可以看到黑格尔关于形式与内容互转的“有机论”:“内容非它,即形式回转到内容;形式非它,即内容回转到形式。”[4](P261)但更重要的是,我们从中看到了新批评的总体分析思路,即要在“有机整体”的视角中进行细读。
再次,布鲁克斯和沃伦对小说中的人物,即暴徒和贝尔太太进行了分析。这里体现出了“有机整体”的形成机制,即反讽和张力。暴徒的生活“超越了小城镇的天地”,但暴徒们又来到小城镇上,与小城镇形成了千钧一发的冲突。这显示出了虚构性和戏剧性,造成了一种反讽和张力。而贝尔太太作为正常生活的象征,以一种波澜不惊的状态,与暗流涌动的现实生活形成了一种反讽和张力。对于新批评派而言,“反讽”和“张力”是他们对辩证关系的理解。这不仅是诗学、美学意义上的辩证,也是现实关系意义上的辩证。[5](P45-60)由此,新批评开始展现他们对人生、世界的看法,展现出他们的理论对外界的关注。
但是,他们这种关注人生、世界的倾向最终突显出一种以文本为中心的理论倾向。布鲁克斯和沃伦将新批评的形式—世界观融入到了对作家的形式—观念批评中。他们认为海明威的“简短的节奏、首尾相连的并列复合句、和通常避免主从关系……使人联想到一个土崩瓦解、四分五裂的世界……可能表示了他对于用理智来解决人类问题所持的怀疑”[1](P434)。而新批评派内部也有许多类似的说法。比如布鲁克斯和沃伦提出,“诗一方面自存自足,另一方面却又使我们‘更意识到外界的生活”[5](P17),而这种外界生活,正面临着理性过剩的问题。若前面的分析更多是用批评理念来显现文本内涵,这里则更多是用文本内涵来显现批评理念。可以说,布鲁克斯和沃伦以这种方式表达新批评文本中心的理论倾向,形成了一种对自身理论的深入审视。
而他们不只有这种正面的审视,还有反思的审视。即使是在他们对自身理论的顺向梳理中,也能看到这种反思的痕跡。比如新批评派不承认或不注重读者感受,但在《杀人者》分析的开头,却出现了大量谈论读者反应的文字。在后文部分,布鲁克斯和沃伦还写道:“如果要说服读者相信作者写下去自有道理,就必须回答读者的问题。”[1](P428)实际上,这句话除了谈论读者之外,还有种要转向作者、打破“意图谬误”的意图。
二.批评:反思自我的批评
在批评的深入阶段,布鲁克斯、沃伦体现出了对新批评更明显的反思。这种反思有着明显的标志:“以上对《杀人者》的讨论是从事情之间的关系以及从人物的不同态度这个角度来看小说的结构,但是,下述这些问题还有待回答:海明威对他的题材抱什么态度?这种态度是怎么表现出来的?”[1](P429)显而易见,布鲁克斯和沃伦试图从文本中心向外拓展,向作者的方向靠拢,突破新批评原有的局限。
首先是“考虑一下海明威最感兴趣的情境和人物”[1](P430)。在这里,布鲁克斯和沃伦不再研究《殺人者》这个孤立的文本,而是把视野投向了海明威的其他作品,如《太阳照常升起》、《向武器告别》、《丧钟为谁而鸣》、《你永远不会这样》、《乞力马扎罗之雪》等,概括出了它们的世界设定和人物形象,提炼出了“暴力世界中的硬汉人物”这一特征,再对《杀人者》中的人物形象加以说明,对《杀人者》的故事主题进行阐释。而在这个过程中,布鲁克斯和沃伦做出了另一突破性的举动,即引入其他作家(史蒂文斯)的文本,而且是大篇幅的文本,来突显海明威人物形象的内涵。
其次,布鲁克斯和沃伦没有止步于对情境、人物的理解,他们进一步挖掘了海明威对这种情境和人物的态度。在这里,他们再次引入其他作家作品,比如将华兹华斯的世界和海明威的世界进行对比,从中得出了海明威的态度。这里还出现了评论家的身影,也就是说,出现了一种超出小说文本的现实话语。当布鲁克斯和沃伦提到格特鲁德·斯泰因对海明威的评论:“我读过的小说中,海明威是最羞涩、最高傲、最清香的一位作家”[1](P434),布鲁克斯和沃伦显示出了某种传记式批评的倾向,而这恰恰是新批评派最为反对的批评方法之一。由此可见,布鲁克斯和沃伦对新批评的反思,有一种执意切中要害的意味。
但做出这样的一种反思,并不意味着布鲁克斯和沃伦真正突破了新批评的局限。他们的自我批评,仍然具有新批评的思维程式。首先,这体现在跨文本的实践上。在这里,布氏和沃氏虽然摆脱了孤立的文本,进入到作家更大的文本世界中去,但他们却是以“模式”思维来归纳和处理文本的。换句话说,他们将《杀人者》的世界和人物形象视作海明威作品总体设定的一种体现。比如,他们思考的是“涅克·亚当斯是否符合这个模式”,结论是“涅克的故事……在海明威的其他作品里也屡见不鲜”[1](P433)。正如有的学者所说:“文本间关系尚有一个极重要的方面,即文学的历史演变问题。新批评派的极端文本中心孤立批评方法论使他们拒绝讨论这个问题。布鲁克斯的批评名著《精致的瓮》讨论了从邓恩到叶芝三个世纪内十个诗人的十首诗,都从‘反讽入手解剖,似乎它们是在同一时期写成的,似乎三百年的文学没有任何变化,至少没有在艺术形式上留下任何值得分析的各自的特点。”[5](P97)可见,布鲁克斯和沃伦的互文式批评,仍然具有分析单个文本时的那种封闭自足的特点,偏向静止的结构和模式。而布鲁克斯和沃伦对史蒂文斯文本进行引用,虽然在内容范围上稍有松动的迹象,但其在形式上大篇幅的“块状”存在,又有意无意地暗示了新批评派的模式化的思维方式。
其次,华兹华斯和格特鲁德·斯泰因的在场也同样揭示了新批评的一些思维定势。就华兹华斯而言,他的存在说明了布鲁克斯和沃伦依旧是沿着新批评派的浪漫主义传统前进的。在《理解诗歌》中,布鲁克斯和沃伦就对华兹华斯等浪漫派诗人的诗歌做了高度的评价,而在新批评派的整个发展历程中,新批评者们对浪漫主义也是相当的熟悉。因此,布鲁克斯和沃伦对华兹华斯的“邀请”就显得自然而然,但也正是这种“自然而然”使布鲁克斯和沃伦不自觉地踏入了新批评的舒适圈。另外,就格特鲁德·斯泰因来说,布鲁克斯和沃伦引用她的话,看似有种传记式批评的思想倾向,但斯泰因言论的具体内容,无论是“羞涩”、“高傲”还是“清香”,都是围绕作品风格来谈的。而布鲁克斯和沃伦对斯泰因的引用,仍然包含着“我读过的小说中”这样的句式。除此之外,他们也精确地论述道:“或许能够这样来概括隐藏在海明威作品里的态度。”[1](P434)
但布鲁克斯和沃伦对新批评的反思,在表现出局限性的同时,也再次突显了新批评以“文本”为核心的根本特色。布鲁克斯和沃伦曾经提出,一部小说的诞生,涉及三个世界,即“我们的实际生活世界,作家的实际生活世界,作家为读者创造的想象世界”[6](P427)。他们转向的作者(包括史蒂文斯、华兹华斯乃至斯泰因),都体现了或指涉了“隐含作者”的意味,看重的是“作家为读者创造的想象世界”,也就是文本本身;他们没有离开自己的批评传统,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停留在批评过的文本系统之中。回顾之前的读者转向,我们也可以发现,这里的“读者”相当于是“隐含读者”,是虚构的读者,仍然是为文本本身服务的“读者”。
因此,布鲁克斯和沃伦再次将我们带回到了新批评的轨道上。对于他们自觉的反思行为,我们表示赞许,而他们在反思中不自觉流露出的新批评气质,则使我们深刻地感受到了新批评基于“文本”理念所具有的复杂性,也就是一种围绕着文本中心既即又离、既离又即的状态。而这也促使我们更深入地思索和探讨新批评的存在。
三.批评:自我批评的价值观念
布鲁克斯曾在《小说鉴赏》中说过这样一句话:“一篇成功的小说结尾,常常把一种可取的总的人生观留给了我们。”[6](P55)如果说在对《杀人者》的分析中,他通过不断改进批评方法,深入发掘了海明威的人生观,那么他在这篇出色的评论中,在批评与自我批评,以及自我批评自身的来来回回之间,也多少留下了一些可取的批评观。对于布鲁克斯来说,这种批评观,或许才是自我批评最终的价值取向。
我们一般认为,新批评派主要是着眼于文本本身。无论是从新批评派在文学史上的地位,还是从我们眼下所做的分析来看,都可以证明这一点。然而,我们也可以发现,布鲁克斯和沃伦通过“文本”,通过他们对待文本的复杂态度,还向我们传递了更多的信息。
首先,他们向我们说明的不只是注重文本本身,还有从中透露出的批评家的品质。这种品质,可以说是一种矫枉过正的勇气和理性,正如海明威作品中的硬汉那样,他们“无不做出豪迈的努力,以期挽救这一世界杂乱无章和毫无意义的状态:他们力图把某种外在的标准强加于他们的混乱生活……这一外在体系总是略有欠缺,不足以制约世界,但忠于这一标准却使得失败带上了英勇豪迈的性质”[1](P431)。布鲁克斯可能是精心选择了海明威这个例子,就像有人点评他的诗评:“布鲁克斯此文虽看起来凿凿有據,但难道不是他精心选出的诗例符合他的目的?退一步说,难道不是他的解说把这两个诗例与其结论联系起来?”[1](P313)新批评派的祖师爷艾略特就曾认为世界是混乱的,无秩序的,认为“艺术的功用就是在日常生活上强加一个秩序,从而诱导出一种现实的秩序感”[5](P37)。因此,当我们回顾上面那句对硬汉形象的解读,就会发现硬汉的品格变成了新批评派自身的品质:“从精神本质上说,布鲁克斯用他那有限生命扮演的就是他认为不得不扮演也值得扮演的悲剧式硬汉。”[7](P119)具体说来,这种品质就是新批评家的社会关怀,是他们对大行其道的工业理性、科学理性的抵抗。他们以静止的艺术理念“强加”于生活之上,以自足的文本理念“强加”于文学批评传统之上,但“有人望文生义,用那高傲的眼睛一看他的书名《精致的瓮——诗的结构研究》,就认为他把流动可变的、动态的诗结构比作形状固定、毫无变化、静止的‘瓮,根本没有理解他以此与流俗对抗的深意”[7](P117)。
其次,新批评派相应地提出了一种“平衡”的批评标准。由于受南方文化思想的影响,新批评者通常感到“感性世界受科学压迫而衰微”[2](P8)。因此,他们希望通过“强加”的方式来恢复人们的感性,以感性反抗理性。但是,他们受到了南方“崇尚和谐、平衡和稳定的人际关系”的文化影响[2](P9),又对浪漫主义的过分感性有所顾虑,所以他们实际上追求的是感性与理性的平衡,从感性中发展出理性来。因此,我们才可以理解文章中的“只有从阅历丰富、久经锻炼的人的内心深处挤出来的怜悯,才是能够接受的”[1](P434);我们也才可以理解他们试图解读和传达的那种“根本情境”和“纯朴的美德”[1](P435),以及他们为何强调代表这种原始处境的符号同样要经过精雕和细琢。最终,我们便能理解他们为何着眼于“有机完整”的文本本身,着眼于文本的基本态度与题材的有机结合。
可见,布鲁克斯和沃伦想要表达的,不是对批评技术的单纯思考,而更关乎文学批评的一些根本问题,比如文学批评的关怀意识。通过这一点,我们发现,新批评派并不像通常所说的那样文本中心和自我封闭,他们以自身的独特方式关注着社会和时代,从而造成了新批评基于“文本”理念所表现出的复杂性。可以说,这是一种以艺术理念来表达现实关怀所产生的矛盾与张力。
而布鲁克斯和沃伦仍然在本质上坚持着他们的核心理念:回到文本。这不难理解,因为这是他们关怀意识的宿地,就像他们对海明威的分析:“为了制造某种全面效果而发展了符号这一目的语言风格。”[1](435)他们对自己的批评是这样的专一和认真:“一个好作家不会向我们提供花样繁多、琳琅满目的主题。他大概会反复地写他在现实的生活中和对现实的观察中感到最为重要的少数几个主题……不断地力图发现并且表现他心目中的生活的真实。”[1](P436)他们希望读者对新批评采取一种自信的“专一”态度,希望读者在新批评反复做出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中能够发现,对于新批评,“我们几乎总能更深地发掘它和理解它”[1](P436)。就先述来看,这种“更深地发掘和理解”,能够使新批评的理念态度得以充分展现,最终揭示出更为根本的关注现实的批评观念。
综上所述,布鲁克斯和沃伦通过对《杀人者》的批评,呈现了新批评的方法、价值与局限,从中自觉或不自觉地表现出了新批评基于“文本”理念的复杂性。而这种复杂性实际上涉及到批评理论对时代、社会的关怀和责任感,展现出了新批评者试图以静穆的艺术抵抗流俗、以艺术理性观照生活感性的关怀意识。或许正是因为这种关怀和责任感,新批评发展出了经典的批评理论,成为文学理论中总被“重访”的重要存在。由此可见,文学批评的生命力,不可避免地从现实中来,而存在于对艺术的尊重与追求之中。
参考文献
[1]赵毅衡.“新批评”文集[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2]胡珂.布鲁克斯“文本细读方法”研究[D].南京:南京大学,2012.
[3]亚里士多德.诗学,修辞学[M].罗念生,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
[4]黑格尔.小逻辑[M].贺麟,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5]赵毅衡.重访新批评[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9.
[6]布鲁克斯,沃伦.小说鉴赏[M].主万,译.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2.
[7]程亚林.布鲁克斯和“精致的瓮”及“硬汉”[J].读书,1994(12):116-119.
(作者介绍:钟圆,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中文学院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2016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英美文学与比较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