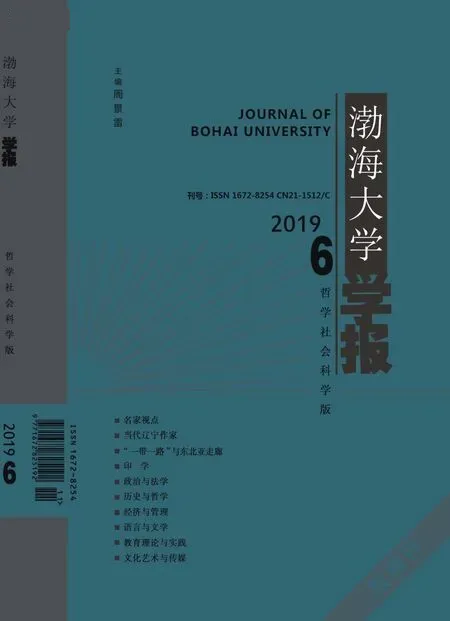《光明》杂志与九一八国难小说
高 翔(辽宁社会科学院,辽宁沈阳110031)
1936年6月创刊于上海的《光明》杂志,是一家回应时代呼唤、满载着九一八国难文学作品的左翼文学期刊。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鲜明提出“救亡与救穷”的宗旨。置于创刊号首篇、由洪深执笔的《光明的态度》直言,“中国的当前急务,是救亡与救穷”;我等“摇笔杆的书生”所要努力的,就是“去做那些救亡救穷反帝反封建的工作;用我们用熟了的文艺形式——小说、戏剧、散文、漫画、木刻等等——描写出时代的危机,希望读者诸君们,对于时代有深刻的认识,因以坚强大众底斗争求生存的决心!”①其二,诞生于文学期刊繁荣的时代。茅盾在1934年8月便预言:“杂志的‘发展’恐怕将要一年胜似一年。”这种“发展”更多表现为“杂志种数的增加”②。《光明》正是在这种“文学期刊出版潮”中应运而生,更多地显示着现代文学期刊人忧国忧民的炽热情怀。
1936年春,左翼文学阵营适应形势做出调整,主动解散“左联”等各左翼文艺团体,以组建抗日统一战线文学组织,随即成立了中国文艺家协会等组织。《中国文艺家协会宣言》开篇言道:“光明与黑暗正在争斗。/世界是在战争与革命的前夜。/中华民族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所谓“光明与黑暗”,《宣言》称:面对日本“强暴的侵略”,“不是对他们作战,便是向他们屈服”;而只有“武力抵抗”才是光明的选择。有无意识之中,《光明》杂志的取名,正回应了《中国文艺家协会宣言》的开卷之语。
鲜明可见,《光明》始终以文学抗战为宗旨,不断地呼唤:“寇深矣!愿从事文字工作的人努力多写点救亡的文字罢。”③因而与九一八国难文学发生着无法割裂的联系。
在《光明》所刊发的诸体裁作品中,小说创作无论在数量还是质量上,都占有重要地位。《光明》创刊伊始,便据体裁设计栏目。创刊号的栏目有创作、诗、报告文学、翻译等。此后,又有评论、随笔、剧本、散文、杂文、通讯、童话、木刻等栏目。其中,“创作”栏目虽未明确标示“小说”,但编者均视其为小说作品④,并在目录编排上将其置于各栏目之首。
1936年10月25日出版的第一卷第十号《光明》目录页上开始明确标出“创作小说”,随后出版的第二卷第七号标出“小说三篇”,第二卷第八、九、十号直接书为“小说”,第三卷第一号写作“创作小说”等。据《光明第一卷总目录分类索引》⑤,将第一卷各期“创作”栏目中的作品统一标为“创作小说”。又据其统计,《光明》第一卷计12 期,登载“创作小说”43 篇、“集体创作”“小说”2 篇,“另册附录”《东北作家近作集》收录小说5 篇,共50 篇。数量上远超诗歌(35 题首)、剧本(9 部)、散文(含报告文学、杂感、通讯等38篇)等体裁的作品,并表现出这一时期《光明》的不凡品质和特征。
一、对国难中不同民族人物的命运的关注
《光明》创刊号刊出小说四篇。除茅盾的以五卅运动为题材的《儿子去开会去了》和沙汀的以掠夺如匪的国民党军为描写对象的《兽道》外,开刊伊始,便不同程度地把目光投向国难中的少数民族人物。这在舒群的《蒙古之夜》和戴平万的《满洲琐记》中有独特表现。舒群的《蒙古之夜》讲述的故事,发生在“开始游击的战争许久”“我们第一次在败走”之际,抗日武装“几乎败到顶点,毁灭了半数的马匹,士兵”“一百多人全散乱了,几乎没有五个以上的伙伴”。战斗中负伤在身、“很难拖出一步”的我,终于倒在路上。幸有一位蒙古族姑娘赶着勒勒车路过此地,将“我”运回蒙古包家中救治。然而,瞬间敌兵又近,开始逐一搜查蒙古包。紧急时刻,在蒙古族姑娘的指挥下,“我”换上“另一件衣服,鞭打着羊群去了”;她还叮嘱“我”:记住这蒙古包住所。然而,当敌人离去、“我又鞭打着羊群回来”时,看到的竟是蒙古族姑娘身上“涂染了几条血流”的“没有一处伤痕”的“完整的尸身”。小说中的蒙古族姑娘耿直善良,亦不乏少女的柔情。作者通过“我”与蒙古族姑娘的一系列对话的记录,呈现出蒙古族姑娘的人性之美。学界普遍的看法是,抗战文学的宣传性导致对人性的简单处理。而舒群的《蒙古之夜》确属高扬人性旗帜之作。作者笔下的蒙古族姑娘,战争是非意识是模糊的,认为战争双方都视民为狗,遭遇强奸致“姑娘媳妇不知死了多少”,对“我”深怀敌意。然而在知道“我”的军人身份并身负战伤后,以无悔之心热心救治。作者这样叙述蒙古族姑娘救助“我”的情景:
当她扶助我起来的时候,......她被我也看得清清楚楚:她比我低下些,她那被风卷起的散发,刚刚触到我的耳边,她的头高扬着,直对着我,没有一掌的距离,她呼出的气息温暖而且湿润,由我的下颚都感受到了。她的脸上裹着一层月光,浓重的两条黑眉和一对活跳的眼睛。
……
她给我解下枪支弹带后,她的手握住我的手,她血流中的热经过两只相握的手,传遍了我的全身;在这清冷的晚间,我开始又感受了人类的温暖。
……
突然她像抱起一个包裹似地把我抱起来放在车上了⑥。
正是这种人性之美,引发出“我”心目中一幅充满诗意的美图:
天上轻松的白云,一块连着一块地浮过月亮,浮向远远的天边去,淡了,散落了。车轮不停地进行着;任随车轮的转动怎样的加快,永远永远有一条天线绕裹在我们的身外,保持着固有的距离⑥。
而这种诗意的美,与蒙古族姑娘遭遇摧残的血腥场景形成巨大反差;作品以蒙古族姑娘至死一只手还握住“刀柄上铸着兵工厂的名号和‘××’字样的年号”的刺刀做结尾,真切告知人们,致蒙古“姑娘媳妇不知死了多少”的,正是日本侵略者。作者摒弃了经世致用的语言和情节预设,在极其人性化、生活化地融会政治教化功用中,高扬中华全民族共赴国难的无畏之举,显示着人类自我生存和精神存在的在场;民族质素的充盈,叙事艺术的细腻,人道主义的丰硕,令人感叹。应当说,舒群对这类题材的表达,是以其切身的生活体验为基础的。早年的舒群曾参加抗日义勇军,对国难中的少数民族或战争中的域外民族人士,有过深切的接触。这种体会在其后来的作品中都有所体现,如《没有祖国的孩子》《沙漠中火花》等。
与舒群笔下的蒙古族姑娘不同的是,戴平万在《满洲琐记》中精心塑造的人物是朝鲜族姑娘佩佩。作者后来于1941年出版短篇小说集《苦菜》时,收入这篇小说,以“佩佩”之名作为这篇小说的题目,更凸显了佩佩的主人公地位,当在情理之中。
《满洲琐记》以第一人称倒叙手法展开情节:“我”在间岛应约与游击队的朋友见面,带路的一位年仅十五六岁的高丽姑娘,竟是“我”在沈阳居住时的邻居。由此,引出“我”与这位姑娘佩佩一家的往事。半年前,“我”来到沈阳,“想多了解一些社会的情况”“决定在沈阳逗留一个充分的时间”,便经朋友介绍,“搬到隔离沈阳十多里地”的一位李姓铁路工人家里居住,对外与李姓工人以亲兄弟相称。而李宅的隔壁便是佩佩的家。佩佩家中只有母女两人,以母亲“打草绳子”为生。受生活所迫,母亲逼佩佩卖淫,姑娘不从,母女为此吵架不已。佩佩无奈,经“我”帮忙,在纱厂觅得一份工作。上班不久,便遭女工贼举报,被纱厂以“不用高丽人”的种族歧视之规为由,赶出工厂。女工贼的恶行引起佩佩好友的愤怒。她们一同找告密者理论,却遭野蛮回骂。一怒之下,众姐妹痛殴告密工贼,竟遭厂方追究,被迫逃至间岛。正是在此,佩佩的人生之路有了重大转折:她投奔到游击队中,成为一名“没有国界的女战士”。作者通过如下一段对话,表达出自己内心的意愿:
佩佩:“我的妈妈也可怜,她只知道要活,可是一点也不知道怎样活下去。”
“我”:“那末,你就知道怎样生活下去吗?”
佩佩:“当然啦!”“要是不,我现在怎会来给你带路呢!”⑦
作者在此形象地喻告读者,以武装对抗侵略者,才是包括弱小民族在内的被奴役者生存的唯一出路。
与《满洲琐记》相联系的,是黑丁的《原野》。作品生动地塑造了活动在吉林磐石富太河流域抗联武装朝鲜族战士的英雄群象。金氏姐弟三人——金狄叔、金锐、金明都从事着抗击日本侵略的斗争。从朝鲜寄来家信,母亲病重盼儿归,然金锐大义在肩而毅然不回;姐姐金狄叔舍弃怀中的婴儿,追随抗联部队而去;弟弟金明几个月前“还在为我们失去土地的同胞,每天做一些惊人的事迹”,而今在敌人的刑场上,他“箝在那两簇浓黑的眉毛下的一双明朗的大眼睛,鼓跳着两支发怒的火光在灼闪着,扫射着,显示着他的最后的顽强”。金明牺牲后,金锐只身潜入日官公馆,杀死“两个家伙”,以雪兄弟被害之仇。作品题名“原野”,乃战士牺牲之地,也是生存不应“踌躇”之所,还是“我们”奔向之处。“原野”意象,既展现着国家与民族广袤而独立的天地,又隐喻着抗日战士为民族的独立与自由砥砺前行、义无反顾的昂扬气势和无畏精神。
与舒群的《蒙古之夜》、戴平万的《满洲琐记》、黑丁的《原野》有所不同,黄华沛的《模特儿静子》则塑造了战争背景下日本少女静子的形象,依然以第一人称展开叙事。“我”是在日本留学的美术专业学生,因习画而与静子相识。她是一位生活贫寒、家庭惨淡、待人“恭敬而谨慎”、为生活所迫从15 岁即进入社会的职业模特。在收入难以为继之时,静子做出了其人生的一项重大决定——赴“满洲国”讨生活。临行前,静子前来我和同学林君的寓所告别时表白:“我的确将成为您们的仇敌,至少您们两个人!唉,这且没法,我,大后天吧要到‘满洲国’去,从民国的国土被划开出来的一个国家。恕我!幸而我不是到那里杀人,我是到那里讨生活的。我不能继续做模特儿了,因为我每月除去车钱只能赚到五六块钱,自然连伙食还不够。——恰巧‘满洲国’的新事业中——自然老板都是日本人,需用大批日本女子:食堂,澡堂,大会社啦,我就是这批中的一个人。……除此一法而外再没有别的可以维持我的生活,……我是个没有‘国家’顽观念的人,我同情像您们一样的民国人,但我如您们一样地讨厌那些军阀,不论帝国的或民国的。然而我却到您们大家认为痛心的地方去了。为了‘生活’,我该喜欢;然而也为了‘生活’,我不知怎样地惆怅,不安,而痛苦呢?——”⑧后来,她到了沈阳,先后写来五封信,告知先做“日本商店的卖物员”,后做“一个澡堂的差役”,此后便无音信了。“我”想,“大约她不会摆脱了这种她所讨厌的日本人的圈套”“干着不正当的丑业,为了‘生活’——虽则不会杀人”。小说以静子的生活悲剧,展示了侵略战争带给日本人民的贫困生活和所引领的灾难之路。
无独有偶,郑伯奇的小小说《另一种难民》,塑造了一个另类难民形象——日本人北川。这是一个在上海拥有一家花店和一座花园的“殷实小商人”。虽与当地弄堂里的市民关系尚洽,但终归身为日本人,当“八一三”战事发生,北川“看见一群一群的中国难民,心中不觉起了一种快感。”然而,随着“战局一天一天紧张起来”“市面的空气也一天比一天险恶起来了。米吃完了。柴也烧完了。北川家简直要断炊了。”求救无门的北川“暗暗寒心,不自禁地诅咒起日本军部来了。”无奈之下,北川“收拾了一些金银细软”,携家人逃离上海;却因断失交通工具,又正遇因痛失家园、怒火中烧的中国人拒而相助终未成行。侵略战争使日本人成为了“另一种难民”,小说极具反讽的意味。
综合而论,通过中国现代作家之笔绘写出的蒙古族姑娘、朝鲜族抗日战士、日本底层女子和日本小商人等人物形象,《光明》编者在有意或无意间,从期刊的整体配置上,呈现了二战时期东方战场东亚人民各种不同的历史画面,反映着东亚人对各自生活的选择,提供了那个时代东亚文化共同体建构的文学依据,显示了东亚文学抗日叙事的厚重资源。
二、真切映现中华民族受难与抗争的图像
“九一八事变”后,以文学形式向国人传送国土沦丧、民众受难图景的,当属逃离沦陷区、聚集于上海的东北流亡作家群。《光明》则强力担负起这一群体创作传播的媒介平台。在这一作家群体中,罗烽是一位以书写东北受难民众为己任的作家。《呼兰河边》所描述的血腥场面令人震颤。驻守呼兰河桥的日本铁道守备队防守所,毫无缘由地抓捕了一个年仅十三四岁的孩子和他放牧的“一条棕黄色的牛犊”。当孩子的母亲到防护所来寻找自己唯一的儿子和牛犊时,见到的是“草丛里”“牛的骨头”和“一个孩子的尸身......”《狱》是以伪满监狱为题材的作品。在“要犯”们集体越狱失败之际,敌伪加倍报复,开始了灭绝人性的大屠杀。这是作者对伪满监狱的切身体验之作。1934年6月后,罗烽两度遭敌伪逮捕。这刻骨铭心的监狱生活经历,成就了罗烽创作上的丰收。除《狱》外,罗烽的长篇小说未竟之作《满洲的囚徒》,便是其狱中生活的详录。此外,还有《累犯》等篇什。罗烽妻子白朗则有散文集《域外集》等,印载着白朗前往探监并为解救丈夫多方奔走的生活时态。
《第七个坑》展示的是“九一八事变”后两天的城市景况。作者笔下的沈阳,已是一座死城:“每个角落,每个罅隙,都有没有完全凝干的血迹”;郊外一处“僻静的场所”,“人体的腹部流出来的肠子”“头部迸裂出来的脑浆”“每处灰白色的肢解的地方”,与乌鸦、老鼠和蚂蚁争抢人肉组成的血腥场面,令人惨不忍睹。作者又以悲痛的笔调,绘叙据守沈阳市区的日本兵对市民即杀即埋的残忍画面。日本兵在沈阳城内杀人如麻,皮鞋匠耿大被强迫挖坑掩埋尸体,目睹着一幕幕惨剧。尤其是耿大与舅舅生死离别的场面,令人泪涌:
“太君哪!我是好人;我是看我外甥去呀!”
皮鞋匠耿大被这最后一声唤醒了。那苍哑的喉音,分明是他的舅舅。于是他停下工作,伸直了腰,用他失神的眼睛通过浓厚的黄昏。
“舅舅,舅舅啊!”皮鞋匠耿大失声地叫起来。
“呃!你为什么也在这?......外甥,你快逃吧!”
“舅舅,你,你快逃吧!”
一股血如同一枝冷箭,从舅舅的胸膛喷射出来,随着一声痛吼就向后颓倒了⑨。
目睹了“一对年青的夫妇”和他们怀中“不满周岁的男孩子”遭受荼毒,耿大颤栗的心在不断回问:“谁能那样凶残:活生生的一对呼救连天的夫妇,活生生地倒埋在两个坑里?谁能那样凶残:埋了之后,又用刺刀划开那女人的下体?谁能那样凶残:一脚把个不满周岁的孩子踢个脑浆迸裂?谁能那样凶残......”⑨其实,《第七个坑》中所显现的日军屠杀画面,是颇具典型意义的。另一位东北作家孙陵的小说《祖国》,以“我”为叙事视角,通过“同号”“监犯”的“我”与“老年人”在“满洲国”监狱的系列对话,记述这位老者在祖国关内和“满洲国”均被抓捕入狱,竟然被冠以同一罪名——“危害国体罪”,再现了“老年人”在“满洲国”抗战遭禁、在祖国关内报国无门的心酸遭遇。作品曾这样叙述“日本兵活埋中国人的照片”,有着与《第七个坑》相同的情节:“他们知道命令将死的人自己去掘坑,——而且要掘得距离,角度全一般齐,——完了便自己头朝下鑚进去,由第二个掘坑的人埋了他。这样再来第三个,第四个......轮流了下去。”⑩《特别勋章》中,不甘亡国为奸的“警备队第一中队第二连全连哗变”,中队长郭念华等28 名战士惨遭杀害,伪满皇宫内则“军乐大作,满朝欢腾祝舞”。
辛劳的《强盗》展现的是更为血腥的画面:日军来到一座有着美丽山水和“苍郁碧翠的松林”的村庄,强行买断进行林木砍伐,并在村西一棵老榆树上张贴告示,警告百姓不准反抗;若遇强盗要报告,否则枪毙论处。不料这告示被人撕扯,日官中村逼村长即刻查交撕扯告示者。年幼的村长儿子三敏因在空草场拔下一面小红旗而被抓,竟以“小强盗”的罪名被活活剥皮,钉在新贴在村中榆树上的告示的对面,那里还“滴滴地渗着血......”小说结尾写道:“‘强盗’的字眼在他们(人们)心里响着。谁也不敢看人皮,谁都带着惨痛......强盗?谁是强盗呢?”故事作了斩钉截铁的回答。
与东北作家的国难文学书写相呼应的,是关内青年作家的国难叙事。他们在《光明》中形成揭示九一八国难的合声共音。艾芜的《孤儿》是再现日本侵略者的间谍行径之作:日伪特务“袁大叔”,将在“一·二八”战事中亲人全部蒙难、孤苦生活而沦为流浪儿的小三子纳入旗下以侦察中国军队情报,但又拳打致其昏迷。醒来的小三子“上身精光,又冷,又痛,又饿”“四望漆黑”,孤独无人,不禁“ 啜泣起来”。作品在揭露侵略者刺探情报行径的同时,又叙说着侵略战争带给人们的惨痛生活。
牧心(执笔)、力禾、辛波的《大演习》,把创作视阈置于抗战早期的日军演习区。当时的日军演习区确有其地,实有史记。据史料记载:“1936年9月,日本中国驻屯军在非法侵占丰台后,即以中国军队驻地为目标,开始进行频繁的挑衅性军事演习。演习的次数由每月或半月一次,增加到三至五天一次;演习的时间由白天扩大到昼夜不停;演习用弹则由空包弹发展到实弹。10月26日至11月4日,日本中国驻屯军在北平西南郊举行秋季大演习,步兵、骑兵、炮兵、坦克协同配合。这是以夺取北平外围卢沟桥、宛平城等要点,最后攻占北平为目标的一次预演。”⑪足现《大演习》背景的真实性,故事就发生在此:年幼的虎儿因与一群孩子在街头唱歌,受到日本兵的驱逐和毒打而致病。爸爸李一挑只得从已被日兵抢劫过的白菜畦子里再挑出几棵“青头货”运到城里贩卖,用卖菜钱给奄奄一息的独生子虎儿抓药治病。未料,在演习区里白菜即被日兵抢走,自己也被抓进兵营干苦力。当他两手空空回到家中时,孩子和老婆惨遭日兵蹂躏,已成为“像棒子似的”僵尸了。万念俱灰的老李准备自杀,在“几个庄稼小伙子”和青年学生的开导下幡然转念,走上了反抗复仇之路。小说以此为结尾。其实,作品所展现的并非仅此一个家庭悲剧。作者笔下的日军演习区,片片荒凉,处处苦难:四处响起惊扰的枪声,百姓的菜、米、柴无不被抢;田地里的“高粱根全被刈除了”,仅有的几棵棉花“孤立地立在地里,似乎在悲叹着那些横欹竖倒的伙伴,但‘桃子’却裂开嘴仰天苦笑”;马路上“庞大的坦克车,都蒙着黄布,乌龟似的爬行着”;那演习过后的土地,现着“密密麻麻的深坑”。令人费解的是,日军演习区竟有国军士兵受长官之命来为日兵“打水,做饭,伺候那些‘雄’”。更血腥的是,一深坑处,裸露着一具“刚被野狗扒出来的”男性老人尸体,已失去了“一支手臂”,另一支手也“只剩拇指了”,“腿部弯曲着,渗透出模糊的血迹”,嘴巴周围是“烧焦的胡髭”。更有令人惊悚的场面:一个孩子突然举起右手高喊:“打到××帝国主义!”却被日本兵“猛烈的戳倒地上”“那庞大的‘乌龟’(坦克)”“从他身上爬过去了”,眼前是“一堆血肉模糊”的东西。家仇国难尽呈毕现。
田涛的《乡村》与《大演习》题材相近:日军把村庄作为军事演习的靶场,强行将村民赶入山中。大美搀扶重病的父亲、一家祖孙三代四口人相携而行,上山躲避。待几天后演习结束、一家人下山时,大美身上背着的是父亲“僵硬的身体”,后面是“披头散发哭咽的妻,牵着小美子的手”。作品悲痛控诉着侵略战争带给人民的苦难,格调凄恻苍凉,民俗中猫头鹰嚎叫的不祥意象贯穿始终。
对国难的展示,旨在激起国人的民族斗志与精神。《狱》中的“胡”,在被行刑之时,勇敢地亮出自己的身份,以激励后人:“再见吧,同胞们!现在我要说明了:我不是强盗,我是反满抗×的义勇军。”《特别勋章》中反叛伪满的郭念华,面对死亡“毫无惧色”,与同行的“二十八人齐呼中国万岁”。《第七个坑》中的耿大在生命受到威胁时,终于“运足他全身所有的力量,抡起那锋利轻快的军用锹,突然向那个兵的头部劈下去”。
舒群的《回到哈尔滨去“做人”——纪念我们未来的九月》,讲述的是在那个时代怎样“去做人”的故事:“我”从军队败逃到哈尔滨,在一家报馆做记者,并帮助昔日军中好友申龙谋得同职。9月18日,哈尔滨市伪政府在公园内举行“庆典”,申龙在“我”极不情愿状态下一再劝说,参加庆典并帮助其传运一只柳条包,告诉我:“这正是叫你去做人。”事后得知,申龙借记者身份参会,并从我传递的柳条包中取出一枚炸弹在会场引爆。回到家中的“我”,检视申龙在柳条包中留下的另一枚炸弹,又不禁想起他的那句劝言:“这正是叫你去做人。”
林珏的《血斑》,则从另一独特视角告诉人们怎样“去做人”。驻守阵地的四个伪满士兵,不甘做敌伪炮灰去“打祖国的同胞”,商定杀死同守一个阵地、监视并“有临时处理他们(按:伪满士兵)死刑的权威”的五个日本水兵。行动中黑大个子不幸战亡,小魏则带领两个伙伴,冒着追敌的枪弹逃离阵地,然终于未能摆脱噩运:“丛密的弹头断决了”“祖国万岁”的声音;“在沉寂白净的原野上,涂抹着三个新添的血斑”。显然,作者是将这种反侵略的大无畏精神,以为“做人”的内涵了。
更多的小说则倾力塑造着不屈者的形象。郑伯奇的小小说《一个明朗的故事》,鲜明刻画出一位普通卡车司机王根发的抗日英姿。受米店胡老板的指派,根发将运送一卡车白米。当得知这白米是借同仁俱乐部名义购买、经日清洋行再转送给东洋司令部时,他愤怒异常,在行驶到聚集了众多难民的“大千世界”门前时,根发毅然跳到卡车上,“用他从来没有过的那么大的声音喊道:‘各位逃难的朋友!这是卖给东洋人的白米,大家分......’”“看见卡车空了,他才跳进了开车的座位,向大家打了个招呼:‘各位朋友!我王根发今天才做了一件痛快事。现在,我要把车开到前方去了。’”⑫叙事语言、故事情节确如标题所示,给人一种特有的简洁澄澈的明朗之美。
凌鹤的《火线外》,再现的是战场之外的场景。从与敌人正面交战的火线上撤离到伪满地界察哈尔境内的四名抗日战士,极度的饥饿致使他们抢吃了“半锅野菜伴着面粰”,被告密于汉奸军队,诬为“马贼”“共匪”而遭枪杀。刑场上抗日战士小傻子呼喊:“咱们兄弟们,死不完的!杀不完的!”《光明》的《社语》中,称其为“不苟且的力作”⑬。
李稚青的《校门前的壁画》,被编者视为“本月创作中杰出的作品”⑭。“九一八事变”后,关内一学校门前巷道的墙壁上出现了一幅壁画:如中国版图的秋海棠叶,东北角上“画著几个恶魔似的家伙,撑着大旗和刺刀,作一种本杀过来的神气”。可不久因有日本人来参观,为避免留下中国人“不讲和平,不讲亲善”的印象,壁画被强行涂掉,但在异常悲愤的学生们的心中,这“图画到底刷图不掉”的。
同样为揭露“涂掉”行径的,是宋之的的《□□□纪念堂》。从小说开篇提及的大青山、昭君墓、归化城、大黑河等,明显提示读者,这是发生在内蒙古地区的故事。生活在大黑河上游沙岸柳丛中夹着的浅溪对面的村庄的乐匠郭三娃子,随泥水匠老平到城里“修筑‘九一八纪念堂’”。在九一八这一天“举行落成典礼”时,侵略者闯进来,强令涂掉纪念碑和烈士碑上的“九一八”三个字。这使“熟悉这纪念堂每一块砖,每一粒土”的建筑工人们觉得“比毁掉自己还难受”,“愤怒的火”“燎原一样的爆发了”:工人与鬼子扭作一团,“在吼声的巨浪里,有枪声混杂着呻吟声响起。”然而,“‘九一八’三字却终于在血迹了涂掉。”泥水匠老平在搏战中惨遭杀害,乐匠三娃子“在老平的灵前吹奏着那凄恻的笛子”,而鬼子“还安然住在那空漠的大院里。见人鞠九十度的躬,立刻就亲密的和你攀谈......”⑮
柯灵的《未终场》是一部记叙演艺界抗日活动小说。在一家可容纳1500 余人的剧场内,当“观众的情绪正被戏剧的浪潮冲击得很高的时候,幕布却像毫无礼貌的暴客,突然降了下来。”正在租界剧场上演的独幕剧《走私》,因有“东北是我们的领土”等内容,而先是被责令修改后再演,继而又强令禁演。剧场瞬间燃起“愤怒的火焰”,变成“沸反盈天的咆哮的海!”作品以女演员“柳”(一位出生在长城外、不甘“身受种种亡国的惨痛”而漂流到上海、在剧中扮演“一个失去了家乡的东北的女人”的角色)的内心呼喊“没有自由的奴隶!吼起来吧,吼起来吧!你们将要和东北的人民得到一样的运命了”⑯为结尾。全篇充满激情,再现着无以泯灭的民族斗志与精神。本期《社语》写道:“这一期的《未终场》是《走私》等禁演事件的形象化,读者当能在其中感着半亡国奴的悲哀而有所奋起。”言之不虚。这也正切合了《光明》编者的意图:国难当头,我们“更需要有‘以牙还牙’的决心和勇气的抗争者”“充满着那坚强的求生的志愿,与那不动摇的抗战的胆量——为了争取民族的生存而抗战!为了争取我们的子孙的生存而抗战!为了我们自己的‘少死须臾’而抗战!”①。
三、对国民劣根性的深刻剖挖
《光明》编者深感自身担负民族救亡和启蒙之责的双重任务,“中国老百姓的冤对头是外国经济势力,和那与这种势力结托的封建剥削。”①视反帝与反封建同等重要。“编辑人”洪深如此述说自己的切身体验:“去年(按:1935年)十一月间,华北正在闹伪自治问题的时候,我颇有机会和一些老百姓接谈。他们对于中国一大块土地将要被敌人割裂的危险,并不见得怎样惊心。我对他们解说亡国的惨痛,指出那在帝国主义者底下做奴隶做牛马的非人生活,他们也只有报以嗟叹。我甚至疑心到其中一部分人还暗藏着‘真能如此,未始不佳’的心理。”①在洪深看来,这虽然“不能说他们是丧心病狂,不知道爱国,更不能说他们是汉奸”①,但是,深重的国民劣根性确实严重禁锢着民族救亡的前行,《光明》作家理应肩负铲除之责。
如前所述,舒群提出的在那个时代如何去“做人”,确是切中时弊的命题。李澄的《得业的悲剧》、赵代铭的《忏悔》从各自独特的视角切入,真切地回答了这一问题。《忏悔》中的“我”是在日本留学的中国学生,因生活所迫,领取“满洲国”的津贴,由一个有民族意识和社会良知的青年学生,逐渐转变为“满洲国”驻日本大使的鹰犬,干着侦查和告密的勾当。终受良心谴责,不甘在“满洲国”大使的威逼下继续作恶,吞服多量安眠药自杀。告别生命前,以一篇《忏悔》把自己的罪孽告诉世人,“作最后一次忏悔”。这对于抗战早期便出现的数量惊人的伪军和汉奸,无疑具有着警示意义。《得业的悲剧》中的主人公雷新如,是一家洋布店跑街的伙计,以专销日货为业。“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他立誓“砍掉我的头也不跑日本货”,且因告发以日货改面冒充国货的奸商而坐牢。失业后的新如,经朋友介绍到上海一家洋布号跑街。虽薪酬丰厚,但在发现这家洋布店依然以日货充当国货后,毅然辞职。不幸的是,等待新如的,是被秘密押解和生命的消失。小说在塑造雷新如正义形象的同时,展示了弃民族大义于后、利欲熏心的奸商“乔黑辣子”和同为跑街者却出卖朋友的章根的残忍而无耻的形象。忠告人们,在反抗日本侵略者的战斗中,对自身民族劣根性的改造亦刻不容缓。
李辉英的《募捐》,勾绘着与救亡主潮相悖的另类画面。进步学生为抗战举行募捐活动,蕴华与素萍来到一富庶家庭,盼望“能够捐到手一笔巨款”;然事与愿违,竟然遭到雇有管家和佣人,曾为修庙、求子捐款200 多元、“客厅里摆着不少古董,还有些名贵的书画”的这户人家的拒绝,直告“一个铜子没有”。作者极形象地描绘出佣人的愚昧、管家的市侩、老爷和太太的无情,与油漆工人、车夫、商贩、学徒工的慷慨解囊、主动捐赠,形成强烈反差。管家四先生所言的“我们不知道什么叫‘救国’,什么叫‘民族’,我们是谁来替谁纳贡”,让我们感知到了国民性改造的艰巨与路长。细心的读者会发现,紧随《募捐》之后,《光明》的编者在“读者之页”栏目中,刊发了读者刘映元的《绥远的文艺界》一文。其言:“在绥东炮火声中,我想先生和许多读者很愿意知道最近绥远的文坛”⑰。《募捐》显然也是我们目睹绥远文坛的窗口。
①洪深:《光明的态度》,《光明》第一卷第一号,1936年6月10日。
②兰(茅盾):《所谓“杂志年”》,《文学》第三卷第二号,1934年8月。
③《社语》,《光明》第一卷第十一号,1936年11月10日。
④参见编辑整理的《光明第一卷总目录分类索引》中的文体分类,见《光明》第二卷第二号,1936年12月25日。
⑤《光明第一卷总目录分类索引》,《光明》第二卷第二号,1936年12月25日。
⑥舒群:《蒙古之夜》,《光明》创刊号,1936年6月10日。
⑦戴平万:《满洲琐记》,《光明》创刊号,1936年6月10日。
⑧黄华沛:《模特儿静子》,《光明》第一卷第六号,1936年8月25日。
⑨罗烽:《第七个坑》,《光明》第一卷第七号附录《东北作家近作集》,1936年9月。
⑩孙陵:《祖国》,《光明》第二卷第十一号,1937年5月10日。
⑪于兴卫:《有关抗日战争几个不容置疑的结论》,《红旗文稿》2014年第17 期。
⑫郑伯奇:《一个明朗的故事》,《光明·战时号外》第一号,1937年9月1 号。
⑬《社语》,《光明》第一卷第三号,1936年7月10日。
⑭《社语》,《光明》第一卷第六号,1936年8月25日。
⑮宋之的:《纪念堂》,第一卷第四号,1936年7月25日。
⑯柯灵:《未终场》,《光明》第一卷第三号,1936年7月10日。
⑰刘映元:《绥远的文艺界》,《光明》第二卷第二号,1936年12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