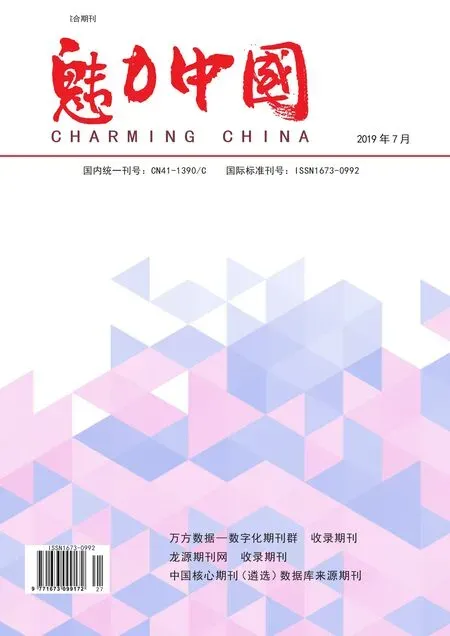行间泣血,通篇言志,盛世危言
——《报任安书》折射出的汉武帝时代
郝明康
(郑州大学,河南 郑州 450000)
一、上溯:予书和报书写作原因时间考
对于任安予书和司马迁报书的原因与目的,学界自古已有长期的研究讨论。原文有 “曩者辱赐书……今少卿报不测之罪,涉旬月,迫季冬”之语,因此任安在入狱之前早已向司马迁赐书。而司马迁回信之缘由和主旨,根据文章内容,可以从中了解到任安予书的目的是劝告好友虽受宫刑,仍应忠君侍君。而通过文章中司马迁大篇幅的自述与表态,又可以看出司马迁本人在任安临刑之前报书的目的不仅仅是回复这封长期“阙而不报”的友人来信,更是通过一种绝命书似的决绝言语,向好友阐述了自己绝不曲意逢迎,而要秉笔直书的史官操守。
近来学者研究表明,任安予书为天汉三年司马迁任中书令到征和二年戾太子事件之前,此时任安担任益州刺史一职,并未下狱。而司马迁报书的时间应当为太始四年十一月。这样的考证与解释,使我们将这篇文学作品的写作背景进一步明确(李陵事发,子长受刑,巫蛊之祸,任安临刑),写作时间进一步限定(汉武帝统治中后期),有利于我们更好的解读这篇文章,发掘其文献价值。
研究中亦提出,当今通行的“任安于戾太子事件之后狱中求援好友,司马迁回信婉拒”这一通行说法始于清代学者傅会,随后被大多数主流学者奉为圭臬,此种说法尤以赵翼《廿二史札记》和王鸣盛《十七史商榷》为代表。近现代以来虽有王国维先生《太史公行年考》对于此考证,认为任安抱罪“当坐它事”,但由于缺乏对任安予书的内容和原因以及报书的具体写作原因和意图的详细论证,因此没有形成较大影响。此类研究与《汉书》中有关《报任安书》记载和唐人颜师古的《汉书》注释相印证,为我们更好透过这篇椎心泣血的文章,一窥汉武帝中后期政治状况提供了极大帮助。
二、简述:汉武帝时代整体情况
武帝即位之初,西汉经过70余年的休养生息,到武帝即位时,社会已是一番盛世景象:“至今上即位数岁,汉兴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但在这种繁荣的下面,却有危机的因素存在。盛极一时的盛世,其国力达到巅峰,但同时也酿造了该朝代由盛转衰的隐患。司马迁沉痛地指出了这一点:“当此之时,网疏而民富,役财骄溢,或至兼并豪党之徒,以武断于乡曲。宗室有士公卿大夫以下,争于奢侈,室庐舆服僭于上,无限度。物盛而衰,固其变也”。大地主横行乡里,上层社会争相奢侈,说明在盛世之中,隐藏着衰败的因素和迹象。
在这样暗流涌动的时代,出现了与《报任安书》密切相关的李陵事件和“巫蛊之祸”。名将李广之孙李陵带五千步兵出战匈奴,由于兵力悬殊和后援不至最终战败被俘,部将建议其仿效前人赵破奴先假意投降保全自身,之后再图大计。而消息传到大汉朝堂,汉武帝大怒,要杀李陵全家。此时与李陵并无交情的司马迁秉持公心为李陵辩护,却更加触怒皇帝,最终李陵全家被杀,司马迁遭受宫刑后迁为中书令(多由宦官担任)。任安在益州任上知晓此事,写信勉励朋友,希望其依旧尽职尽责为皇上推贤举能。但司马迁内心的愤懑无以平息,直到任安因“巫蛊之祸”中自保不出兵救援而下狱,司马迁终于在即将与好友阴阳两隔的悲痛之中写出了《报任安书》,既是劝慰,又是自表;既是回复,又是诀别。
在《万石张叔列传》、《汲郑列传》、《匈奴列传》、《李将军列传》、《卫将军骠骑列传》、《酷吏列传》等篇章中,司马迁用了比较曲折的笔法,揭示了武帝统治下的政治危机。重用酷吏,迷信巫蛊,最终汉将降北和“巫蛊之祸”的先后打击,使得汉王朝元气大伤。在《平津侯主父列传》中,司马迁还直接引用了主父偃、徐乐、严安等人对汉武帝的上书,对汉武帝的遣将欠妥的穷兵黩武政策提出了批评。
三、详析:绝命书与“盛世危言”
任安虽是一个政治斗争中的明哲保身者,却也是一个有气节的忠心耿耿之人。宁为大将军麾下不受青眼马前卒,不做骠骑将军帐前趋炎附势之小人。作为将死之重囚,临行之前可以看到此书的可能性是极小的。司马迁也遭宫刑,史书草创未就,只凭一份执念坚守。因此,他借书信抒发自己的不幸遭遇与愤懑不平,以破釜沉舟的勇气,椎心泣血的行文,寥寥数语间不仅揭露了当时酷吏横行草菅人命,严刑峻法泯灭人性,朝政腐败以钱赎罪,皇权专断刚愎自用,歌舞升平策马开边下的乌烟瘴气等。
(一)刚愎自用之君
文帝时期,汉朝就废除了“诽谤罪”、“ 妖言罪”,可到了武帝时期,这些罪名又盛行起来,甚至发展到“腹诽罪”。武帝大权独揽,内侍们也大多依附皇权而存活。此情助长了汉武帝刚愎自用,独断专行的残暴。“天子始巡郡国。东渡河,河东守,不意行至,不辨,自杀。”司马迁因替李陵说了几句公道话而得罪汉武帝, “明主不晓,遂下于理。因为诬上,卒从吏议”。汉武帝此次征讨匈奴只是为了给自己的宠姬李夫人的兄长李广利一份功劳,从而名正言顺地使其飞黄腾达。因此李陵的失败不仅有自身深入敌军兵力悬殊的主观因素,还有大后方君主态度冷漠,遣将不利支援未到的原因。司马迁上书辩护,触怒汉武帝的不是为李陵的开释,而是其中暗含的对于当今圣上自私用心的批评。因此汉武帝龙颜大怒,而司马迁遭受的奇耻大辱和惨痛的教训令他永生难忘。因而司马迁在信中和史书中扬弃 “为尊者讳”的陈腐教条,本着 “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 的宗旨,秉笔直书,毫不留情地揭露和批判封建统治者的污行劣迹,不作任何违心的人为修饰,也不因自己遭受严苛刑罚而怀恨在心,坚持其秉笔直书的历史原则。
(二)苛政严刑之吏
司马迁罹祸后,“见狱吏则头抢地,视徒隶则心惕息”,“独与法吏为伍,深幽囹圄之中,谁可告诉者”。在狱吏酷刑的淫威下受尽折磨,对其灭绝人性的兽行刻骨铭心。于是借论述酷吏而针砭时弊,他记录了酷吏杜周、王温舒等人谄媚逢迎,惯于奉承皇帝意旨行事的罪恶行径。杜周治狱 “不循三尺法,专以人主意指为狱”。不管被捕者按照庙堂法律是否有罪,不问是非曲直,不分善恶,盲目阿谀取媚主上断案, “上所欲挤者,因而陷之;上所欲释者,久系待问而微见其冤状”。广平都尉王温舒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善事有势者,即无势者,视之如奴。有势者,虽有奸如山,弗犯;无势者,贵戚必侵辱”。横行霸道,无恶不作,任意屠杀生灵,杀人杀得血流成河。朝廷法令规定立春之后不能行刑,这个嗜血成性、草菅人命的刽子手气得 “顿足叹曰”: “嗟乎!今冬月展一月,足吾事矣!” 这样狐假虎威的人竟“迁为中尉”,有更大的权力戕害黎民苍生。西汉十大酷吏竟有九个出在汉武帝一朝,使得人心惶惶。“巫蛊之祸”原本只是一场皇室内部政治风波,但是在酷吏的严刑逼供和推波助澜下,成为了一场血流成河的国之灾难。
(三)内奢外竭之态
汉武帝此时也是荒淫享乐,劳民伤财,他在秦代皇家园林上林苑的基础上大肆扩建,占地达余里,内有连绵的亭台楼阁和人工湖泊,蓄养着大批宫女歌优,直至武帝晚年,上林苑的土木工程都没有间断过。汉武帝建明堂,垒高坛,树“ 泰一”尊神,大搞顶礼膜拜,并且靡费巨资。多次封禅出游,令大批人入海求蓬莱真神,只是为了寻神求仙长生不老。这样的大兴土木,加之连年对外征战(起初是为了解决边患问题,之后竟成为了为求大宛宝马,为给宠臣功勋的竭财之征),“虏数万人皆得厚赏,衣食仰给县官,而汉军之士马死者十余万,兵甲之财转漕之费不与焉。于是大农陈藏钱经秏,赋税既竭,犹不足以奉战士。”到了汉武帝执政中晚期,社会矛盾空前激化而民变频发,王朝上下怨声载道,政权与国运危机四伏。
(四)腐败作恶之官
武帝用亲信桑弘羊执掌全国财政,将盐铁实行垄断专卖,“作官府,除故盐铁家富者为吏。吏道益杂,不选,而多贾人矣。”并出卖官职爵位、允许以钱赎罪。“家贫,财赂不足以自赎,交游莫救,左右亲近不为壹言。”而这样做使吏制进一步腐败。有钱有势的豪强与高官可以以钱换命,肆无忌惮的鱼肉百姓欺压平民。在这样的土地兼并中,“富者连田阡陌,而穷者罔立锥之地”。腐败官僚又与地方豪强相勾结,广大贫苦农民不堪官府和豪强的双重压榨,于武帝统治的中后期接连爆发起义,且愈演愈烈。
四、后记
在这样短短的《报任安书》中,司马迁将其所见所闻所感的点点滴滴融入字里行间。其内涵既不在于回复友人来信,也不在于大倒人生苦水。他通过这样一种诀别式的信件,将自己遭受飞来横祸后的心境和盘托出,点出自己暗淡无光的未来里闪光的责任与使命,更鼓起一腔生命中所有的勇气写出了歌舞升平下的危机与黑暗。《报任安书》终成绝响,而这份盛世危言也成了黑暗吞噬它的最佳理由。《汉书 司马迁传》中记载其生卒年及死因不详,而多种文献亦载司马迁“下狱死”。王国维先生认为其可能生存下去,但是在写就《报任安书》之后便隐姓埋名销声匿迹。坊间亦有司马迁或是一生东躲西藏,或是死后族人遭到追杀甚至要变更姓氏(“同”姓与“冯”姓)的口耳相传。太史公一生命途多舛,如今余下浩浩通史与一篇绝命书。西北风抹去他走访四方潜心著史的所有痕迹,也吹红我们的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