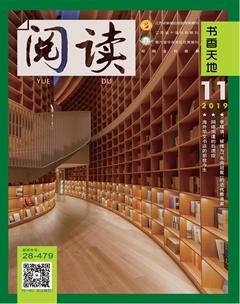李瑞清:被推为“东南冠冕”的近代教育家
徐有富 苏姝雅



李瑞清先生(1867-1920),名文洁,字仲麟,号梅庵、梅痴、阿梅,喜食蟹,自号李百蟹,民国时期称清道人。江西临川县温圳杨溪村(今属进贤县温圳)人。清末民初诗人、教育家、书画家、文物鉴赏家。他是南京大学等几所南京高校的前身—两江优级师范学堂监督(校长),是中国现代高等教育的奠基人之一,也是中国现代美术教育的首创者。辛亥革命后,李瑞清鬻书上海,成了二十世纪书法界“金石书派”的领军人物。他在现代教育与书画领域都成就卓著,影响深远,是被推为“东南冠冕”的近代教育家。
一、家学渊源与玉梅花庵
李瑞清先生出身于三代为官的书香门第,父亲李必昌教子极严。李瑞清先生自幼喜爱书法,从伯祖父习字,钻研六书,尤好大篆,这为他后来成为书法家打下了良好基础。
清光绪十七年(1891),李瑞清在湖南参加乡试,因不合乡籍被注销。光绪十九年(1893),李瑞清回原籍江西南昌参加乡试,中了举人。次年(1894)进京参加会试,中了进士。又次年(1895)在京参加殿试,置二甲朝考一等,选翰林院庶吉士。三十一年(1905),以候补道到江苏。时值江宁(今南京)发生学潮,他奉命前往疏导劝谕,平息风潮,任两江师范学堂(今南京大学等校前身)监督(校长)。
1905年,他兼任两江优级师范学堂监督,1906年到任。几年时间内,他言传身教,成绩斐然,使两江师范成为名副其实的江南第一学府。
但关于“梅庵”的来由,则别有一段故事。李瑞清先生为两江师范学堂监督时,以“梅庵”名其宅。两江师范虽几次易名,校内为其专建“梅庵”。新中国建立后南京师大又建“梅庵亭”于校园,缅怀他的办学功绩。临川人民将他生前住过的“府前街”改名“梅庵路”。
劉成禺《世载堂杂忆·清道人轶事》称:“梅翁籍隶江西,而生长读书皆在湖南。少时蓬头垢面,有如呆童,饮食起居,毫无感觉。自言自语,视人则笑,蜷处攻学,余无所知。匿不外出,彼不愿见人,人亦无与彼议婚事者。常德畲公,为长沙学官,闻而往视,觌面问话,触其所学,条对口如悬河。畲公曰,此子将来必成大名。太原王氏所谓‘予叔不痴者,即此子也,以其长女(梅仙)妻之。”
刘氏所述,基本属实,但畲蓉初非“长沙学官”,而是常德朗江书院的主讲。
但梅仙早逝。光绪庚寅为1890年,李瑞清时年二十四岁,与畲玉仙结婚。光绪癸巳为1893年,李瑞清时年二十七岁,畲玉仙就病死了,李瑞清从此终身不娶。于此可见,妻子对他是多么体贴,多么留念。夫妻间天人永隔是多么痛苦。
李瑞清爱梅,也爱玉,所以他号梅痴、梅庵,也号玉梅花庵,如1912年4月21日《神州日报》曾刊出《玉梅花庵道士鬻书后引》,同年6月12日该报还刊出过当时李瑞清的住址:“李梅庵,新靶子路横滨桥北首路西玉梅花庵李寓”。他的临古诸跋题为《玉梅花庵临古各跋》,他的论书著作题为《玉梅花庵书断》,都说明了这一点。
显然,李瑞清号梅痴、梅庵、玉梅花庵都是为了怀念他已故的妻子梅仙和玉仙。
1915年,在两江优级师范学堂旧址,成立南京高等师范学校。
1916年,校长江谦为纪念李瑞清主持两江师范学堂的功绩,在校园西北角六朝松旁,用带皮松木造了三间茅屋,取名“梅庵”。门前木匾上有李瑞清写的“嚼得菜根,做得大事”八字校训。
1933年,茅屋改为砖混结构,面积204平方米。匾额“梅庵”二字为柳诒徵书,所署时间为“民国卅六年六月九日”。
曾熙、胡小石等在李瑞清墓附近还建了玉梅花庵。将纪念李瑞清的建筑取名为“玉梅花庵”可谓善解人意。
1916年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江谦为纪念李瑞清,于六朝松畔,建“梅庵”。梅庵于20年代曾是会议、讲习场所。梁启超、胡适之曾在此开讲论学。梅庵亦为当年共产党、社会主义青年团经常活动之地。1921年7月,恽代英在此召开少年中国学会年会。1923年8月,瞿秋白、邓中夏等参加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曾在此举行。中央大学期间,曾为音乐系琴房,亦称音乐馆。现为艺术学院所在地,位于南京东南大学四牌楼校区西北角,六朝松旁。
二、两江师范监督,办学功勋卓著
光绪二十五年(1899),李瑞清的父亲在云南任职,李瑞清于这年春天入滇省亲,由于闲居多暇,便写了《梅花赋》、《日赋》、《秋月赋》,特别是《秋月赋》,一时传颂,纸为之贵。
晚清重臣魏光焘(1837-1916)字午庄,湖南邵阳人,光绪二十六年(1900),调任云贵总督,魏光焘便在光绪二十八年(1902)阴历十月聘请李瑞清任云南学堂教习。胡思进《退庐文集·送李梅庵南归序》谈到了这一点:“壬寅(1902)十月,邵阳魏公氶诏开云南学堂,聘梅庵为教习。”
那时中国文化思潮风起云涌,御外侮求变革的呼声日益高涨,“兴学育才”“兴学强国”的主张受到重视,废科举、办学堂已成为大势所趋。
1901年,刘坤一和张之洞联合上奏,酝酿新学制,亟欲培养近代人才;1902年,以两江三省之财力,以师范学堂取代旧式江宁府学,在鸡笼山下明朝国子监旧址建立三江师范学堂;1903年,三江师范学堂正式成立,次年开学;1906年,三江师范学堂更名为两江优级师范学堂。
魏光焘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二月改任两江总督,遂延揽李瑞清入幕。1905年,李瑞清先生上任三江师范学堂后,夙兴夜寐、惨淡经营,终于使学堂面貌一新, “教育成绩评者,推为东南冠冕”,三江师范学堂成为当时全国优级师范学堂的楷模。
其间,张之洞曾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八月二十九日上《查明周馥参款折》,反映学潮问题。针对学潮问题,李瑞清上任后对考生采取了区别情况分别对待的方法,风波很快平息了下去。
1905年5月24日《中外日报》以《招考传习生出榜》为题作了报道:“师范传习所总办李梅庵观察,前月下旬,会同学务处司道,分期考选本籍、客籍各士子,现已将试卷评定甲乙,出榜晓示。计生员正取五十名,副取八十名,童生正取三十名,副取五十名。凡不愿入所肄业者,仍准按月考试,书院以资赡养而示体恤。”
正因为李瑞清处理师范传习所风波卓有成效,所以很快就被周馥任命为三江师范学堂的代监督,1905年7月6日《时报》以《委代三江师范学堂监督(南京)》为题作了报导。
李瑞清是教育救国论者,他在《与张季直(“季直”,张謇字)书》中说:“中国前途,除办学外,更无第二条生路,公不可不注意也。”
其《与伍仲文书》复云:“救社会,舍教育外,更无他法。惟一二英杰投身教育,不但不可有富贵思想,即名誉思想亦不可有。当如老牧师,除救世外,无他思想。”
“吾辈果能舍身教育中,牺牲富贵名誉,无论国不亡便可致富强,即便亡,亦有翻身之一日,不能尽铲除吾人之爱国心也。如无教育,便無人,安有国?吾教育诸人,人人皆有此责,愿以此贡之。”
1.上任伊始,整顿学风
他上任伊始,就大刀阔斧地整顿了三江师范学堂的校风与教学秩序。
1905年8月的《中外日报》以《整顿三江学堂新计划》为题作了报导:“三江师范学堂规模既大,用钦浩繁,教习委员,不下百人之多,滥竽充数者,既不乏人。兼差支薪素不到堂者,亦复不少。代办监督李梅庵观察,特订新章。各委员所司之事,无论其冗滥与否,暂不予以裁汰。惟须终日在堂,不准无故擅离。倘有自旷职守者,一经查明,立予撤差,断不姑容。至各教习亦悉仍其旧,但属令自认愿教何许学科,设认定后如不切实教授,亦即屏退,已分别传知各委员教习遵照。”
三江师范学堂的校名是张之洞取的,他于光绪二十九年正月初八日所呈《创建三江师范学堂折》称:“兹于江宁省城北极阁前,勘定地址,创建三江师范学堂一所,凡江苏、安徽、江西三省人士皆得入堂受学。”可见“三江”即指上述江南三省。
以张謇为代表的江苏的官绅们认为既然名为两江总督,当然应当名为两江师范学堂,于是两江总督周馥顺应众议,依据《奏定学堂章程》条例,于1906年5月将三江师范学堂易名为两江优级师范学堂,并任命李瑞清为两江优级师范学堂监督。
2.广延名师,创新理念
接着,李瑞清于1906年3月东渡日本考察教育,并选聘日籍教师。李瑞清赴日本考察的事,1906年5月份的《时报》以《两江师范学堂续聘东教习(南京)》为题作了报导。
王德滋主编的《南京大学百年史》对聘请日本教习的情况也作了简要的叙述:“1906年3月,李瑞清带着修改后的聘约章程亲赴日本,通过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嘉纳治五郎,聘请了总教习松元孝治郎和另外两名教习。松元总教习4月抵达两江后,又增聘小野等3位日本教习,加上留任的2人,改制后的日本两江师范学堂聘请10名日本教习。”
当时的两江优级师范学堂名师云集,著名学者王伯沆、柳诒徵、刘师培都曾执教于此。据1909年所作《第一次教育统计图表》,学堂内的教员中有本国毕业者12人,外国毕业的本国人士15人,此外还有外国教员3人,可见教员中接受西方教育者比例较高。
3.改革学制,添置设备
李瑞清从日本考察教育回来,首先改变了学制,开办优级本科之“公共科”与“分类科”。“公共科”主要修读人伦道德、群经源流、中国文学、东语、英语、逻辑、算学、体操等通识课程。“分类科”包括理化数学科、农学博物科与图画手工科。
其中图画手工科为两江优级师范学堂首创,对我国现代美术人才的培养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李瑞清的弟子姜丹书在《我国五十年来艺术教育史科之一页》一文中指出:“监督李瑞清眼光远大,且自己擅长书画,故提出主张,同时学生竭力争取,于是呈准学部,特别添设了国画手工科。”
学校有分类科、选科、补习科共十余个班级,又附设中小学堂以作教育见习之用,学生多达千人。李瑞清先生提倡国学、科学和艺术,重视学习与劳动的结合,改博物科为农业博物科,购置农田耕牛供学生实习之用。又创设图画手工科,设画室及工场,并亲自教授图画课,增设音乐科,培养了中国最早的美术师资和艺术人才,国画大师张大千、著名书法家胡小石皆出其门下。李瑞清先生是中国美术、书法教育领域的拓荒人,也是中国近代美术、书法教育事业的奠基人。
李瑞清先生在教育理念上走在时人前列,兼具继承与革新的特点。他清醒地意识到,民族的强盛离不开人才的培养,而西方教育可以作为中国效法的参照。因此,对于来自欧美、尤其是来自日本的教学制度、课程设置、教科书和教育方法,他都加以注意。引进西方先进教育方法后,他将其与中国传统教育相结合,付诸教育实践。
三、 “视教育若生命,
学校若家庭,学生若子弟”的教育家
李瑞清先生出任两江师范监督后,为学堂事务四处奔走,全力以赴,始终不渝。他抱负非凡,以“视教育若生命、学校若家庭、学生若子弟”为办学宗旨,以“嚼得菜根,做得大事”为校训,致力于造就“中国之培根、笛卡尔”。
办学关键在于选用优秀教师。为此,李瑞清先生带领同仁出国考察,聘请了一批来自日本的饱学之士来校任教,传授西方科学。学堂的修身、文史、地算、体操等科则皆由中国教师出任。为了聘请专治地理的姚明辉先生,李瑞清先生亲自前往嘉定,备筵席为之接风,竭尽礼遇之仪。姚明辉为报知遇之恩,上课不负众望,讲得深入浅出、生动幽默,受到学生的一致好评。有时候上晚课,蜡烛连烧三五支,一讲就是3小时。
李瑞清先生认为,师范教育的对象是为人师者,关系风化,因此,不应只是言传,更应注重身教。以一校监督之尊,他不居洋楼,安居三间茅屋之中,并以“梅庵”名之,不仅以“嚼得菜根,做得大事”的校训诲人,更用于律己。他还常常深入课堂,坐在学生中间,认真听讲并做笔记。既检查教学质量,又沟通师生关系。某日大雨倾盆,他和学生同离课堂,忘记携带雨具,便和学生一起淋雨回到住所,期间有工友赶来欲为他撑伞,被他拒绝。他说:“学生能吃苦,当监督的更应该吃苦。”由于李瑞清先生的身体力行,两江师范形成了一种勤俭节约、刻苦学习的校风。
李瑞清也承担着其他课程的教学任务,并认真批改学生的作业。
《清道人遗集》还保存着《诸生课卷批》,如谓:“此卷颇喜其有言论自由、学术独立之概,故尤乐与详论之。”“文笔沉痛,识解超越。所云秦汉而降,专制习深,此未为知言也。秦为法家之一完全专制政体,明亦实行专制者也。汉唐宋皆带有杂质者也。”此类批语当然能对学生起鼓励与指导作用。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还注意在阅卷时发现人才并加以培养,胡小石的助教郭维森所撰《胡小石先生传略》说:“小石师以其家传的书法和深厚的旧学功底,引起了梅庵先生的注意。有一次,李先生出题测试学生,题目出于《仪礼》,小石师曾读过家藏的张惠言的《仪礼图》,所以一点也不感到陌生,做了一篇很好的文章,受到李先生的激賞,成了李先生悉心指导的入室弟子……1910年2月,师从两江师范学堂毕业,因梅庵先生之介,留校任附中教员。李先生还同时介绍他与同学胡翔冬拜于陈三立(散原老人)门下,学习诗学。”后来胡小石与胡翔冬都成了南京大学历史上研究古代文学的著名教授。
这绝不是个别现象,还有个南京学生叫张通之,喜欢临摹晚清书法家张裕钊(号濂亭)的书法。李瑞清看到后,称赞他临到神似,并说:“学校饭堂里的‘规则是我用濂亭体写的,但远比不上你。”
他每次遇到张通之,都用手作写字状,并问道:“课后还写张濂亭字吗?”通之说没有写,他总是鼓励道:“写写写,毋懈毋懈。”张通之著有《庠序怀旧录》,第一篇写的就是李瑞清。后来,张通之在书画方面颇有成就,这与李瑞清的鼓励与教诲是分不开的。
李瑞清办学成就显著,正如柳肇嘉《清道人传》所说:李瑞清“以身作则,视诸生若家人子弟,提倡科学、国学、美术,不遗余力。中外教授及江南弟子千数百人,服其诚悫,教育成绩,评者推为东南冠冕。”苏云峰《三(两)江师范学堂:南京大学的前身,1903-1911》亦云:“它不仅是江苏省的最高学府,其规模可与京师大学堂比美,日本东亚同文会就说这是‘清国之两所大学校。”
在李瑞清的悉心主持下,两江师范学堂成为江南地区规模最大、声誉最高的学府,学生成绩为江南各高校之冠。著名学者如柳诒徵、刘师培、夏敬观、姚明辉、雷恒、萧俊贤、松本孝次郎皆执教于此。并培养出了许多著名的学者、专家,如生物学家秉志、教育学家廖世承、戏曲史家陈中凡、艺术教育家吕凤子、国画大师张大千、著名书法家胡小石等。
任两江优级师范学堂监督期间,李瑞清除了津贴之外几乎没有别的收入,但他却常常把津贴拿出来帮助经济条件较差的学生。他曾经表示:“家里既没有冬天御寒的衣裘,也没有可以长期典当的有价值的物件。”但是,一旦有人需要帮忙,他从不吝惜。
1911年,武昌起义,全国震动。江苏独立后,不少达官贵人弃职逃离,但李瑞清先生坚守职责,学校照常敲钟上课。战火蔓延、兵荒马乱之时,他受命于危城之中,拨巨款购米赈济难民。美、日领事及传教士邀请他登上外国军舰暂避,李瑞清先生坚持不去,说:“托庇外人,吾所羞。吾义不欲去,使吾后世子孙出入此城,无愧可矣。”
四、归隐与身后事
大局平定后,清亡而民国立。李瑞清先生回到两江师范,学生奔走相告,欢迎他主持校政,但他自视为清朝命臣,决意离去,上书请辞两江师范监督职务。临走时,他看到有些学生衣衫褴褛,生活困难,便变卖自己的车马,将所得钱财分发贫困学生,然后两袖清风,飘然而去,隐居上海,号“清道人”,以卖书画维持生计。
光绪三十二年(1906),李瑞清曾将多年的积蓄捐出,加上地方富绅的襄助,在上海创办了短期的留美预备学堂,企望着“送一人出国,将来救中国就多一个人的力量”。在学堂任教的好友吴瀚涛生活窘困,他将“清白钱”百余两白银送至吴府,宁与良友共用之,而不肯赠予达官贵人。
1912年,李瑞清辞去两江师范学堂监督职务。离校时,见有些学生生活贫困,心中十分痛苦,随即卖去自己的车马,将钱散发给贫穷的学生,两袖清风,飘然而去。
李瑞清晚年寓沪,以卖字画过活。为了养家,他甚至将多年来用心收藏的经史、金石书籍也卖掉换钱。晚年的他得了严重的高血压,常常头晕目眩,但依然为了多卖出几张字画换钱而不懈执笔,几次昏厥过去。即使如此,一旦他人有难,他仍然热心襄助。当时,安徽、湖南地区闹饥荒,不少难民逃到上海,李瑞清将卖画所得钱款悉数用来帮助难民,而家里则几近揭不开锅。
李瑞清妻子早逝,一生无子女,在上海所养家小,皆兄弟之寡妇孤儿。妻子名梅,乃自号“梅痴”、“梅庵”。当时,有黑帮慕其旧名,以为其曾为高官,家中必有旧财可诈,于是写信敲诈,要他奉送银票三百。李回书称自己“卖字为生”“自顾不暇”,“无妻妾之奉而有家室之累”,所谓盗亦有道,当时的黑帮调查后竟自惭形秽,反送了他300元养家。
1920年9月12日,李瑞清先生在南京逝世,享年五十四岁。逝世后,其同乡挚友曾熙、学生胡小石办理丧事,将他葬在南京南郊牛首山梅岭罗汉泉,墓旁值梅三百株,筑室数间,题名“玉梅花庵”,以志其号。
抗战后几经战乱,李墓已非常破败,墓碑也散落在外。后来,江宁区一生产队长程吉富发现后,将散落在外的墓碑和碑前的香炉拾回家,为了防止别人将其拿走,细心的他还把墓碑字朝下地摆放。2002年初,程吉富将原碑无偿地捐献给了南京大学档案馆,原碑已根据文物维修的惯例放置在了墓区内。
2002年4月29日,中国近代著名教育家和书法家、南京大学前身“两江师范学堂”校长李瑞清墓修竣揭碑仪式在南京江宁牛首山举行。
李瑞清先生的办学理念是“视教育若生命,学校若家庭,学生若子弟”,他以“俭朴、勤奋、诚笃”为校风,倡导“匡时而振俗”,主张融会贯通中西之学以造就“中国之培根、笛卡尔”,这些都奠定了近代大学的品风之雏形。
“嚼得菜根,做得大事”为校训,这既是李瑞清先生提出的治校之训,同时,他也用自己的一生践行着这一治学理念,为我们树立了气节长存的典范。
九十九年后,当年的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如今的东南大学校园六朝松畔,依然有由柳诒徵教授题匾的“梅庵”。而南京大学仙林校区里,“两江路”“瑞清路”和“菜根潭”等地名,默默讲述着两江师范优级学堂和李瑞清先生的故事。
世事沧桑,六朝松依然挺拔。不知今日走在这里的你,会不会想起近百年前,那位抱负非凡、言传身教的老校长。
(摘编自江苏人民出版社《南大往事》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