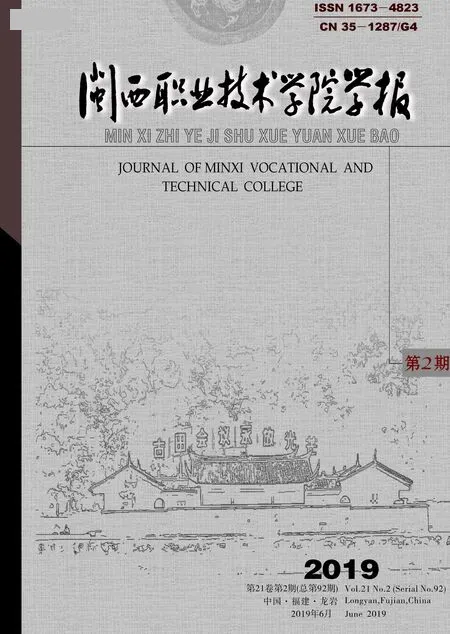从形式判断到实质判断:CISG与PICC根本违约条款之比较研究
殷 涛
(苏州大学,江苏 苏州 215000)
享誉世界的《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以下简称CISG)为许多国家所接受,并且在国际贸易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CISG的根本违约规则却因过于抽象、模糊而时常受到批判,这势必会贬损公约促进统一之目的。相较之下,尚未被各国普遍接受却被学界奉为圭臬的《国际商事合同通则》(以下简称PICC)与CISG存在较大差异。本文将从两方面对二者进行比较,一方面对CISG和PICC关于根本违约的立法进行横向、纵向的比较,甄别其差异;另一方面通过归纳实务中CISG和PICC对根本违约规则各自的解释、后者对前者的参考意义,探讨判定根本违约的合理标准。最后,在前述分析的基础上总结其对中国制定相关规定的启示。
一、根本违约立法的纵向、横向之比较
(一)CISG之下根本违约的立法变迁及启发
CISG第二十五条的规定乍看十分笼统:它没有指明根本违约强调的是当事人违反了重要的合同义务,还是其违反行为本身的恶劣程度;对于实质剥夺守约方依合同所享有的预期利益,CISG亦未提供相应的界定标准或列出相关的考量因素;关于可预见的时间点,CISG也是选择留白。这些问题由来已久,一直困扰着历代立法者的规则制定。
CISG中根本违约条款的出台历经坎坷,其立法变迁体现了以下趋势:其一,立法者试图平衡买卖双方的利益;其二,立法者更倾向于支持合同的效力;其三,坚持实质性判断是根本违约条款未来的发展方向。从立法的措辞之变化来看,由违反重要义务到根本地违反义务再到违约,前两者既无法涵盖根本违约的所有情形,也不总能“水到渠成”地导致相当的损害从而构成根本违约,故最终的立法挣脱了违约形式的桎梏,转而以损害与可预见性的判断来界定根本违约。同时,CISG第二十五条的留白或许是为得到广泛接受、保持一定灵活性而有意为之。
(二)PICC与CISG立法之比较
在有违约行为的前提下,CISG判定是否根本违约一般进行两方面的考量:一方面违约必须造成损害——不仅包括守约方遭受的客观损失,还包括其被剥夺的、依合同所应享有的主观预期利益[1];另一方面违约的后果必须是可预见的,违约方和处于相同情况的同等理性人均可预见到。
相较之下,PICC 的四个版本(1994、2004、2010和2016)关于根本违约的立法是一致的,且其考量的因素更为多元化。PICC并未使用“根本违约”的措辞,而是以“未根本履行”代替。所谓未履行,即指一方没能履行合同约定的任一义务,包括不当履行和迟延履行。在判断是否构成未根本履行时,除与CISG相同的规定外,PICC还添加了新的因素,即(b)、(c)、(e)项的规定。其中,(b)项明显偏向于当事人的意思自治,有利于守约方根据合同约定终止合同;(c)项注重违约方的主观恶劣程度;(e)项体现了对违约方利益的考量,增加了守约方终止合同的难度。
比较两者,不难发现PICC与CISG有四点不同。第一,PICC对于根本违约的判定更加具体、更有可操作性,裁决者不能天马行空地自由裁量,而必须特别考虑法条所列出的情况是否存在。第二,PICC将CISG平衡买卖双方利益的追求直观地体现在条文中。PICC列出的因素中既有降低守约方终止合同难度的(b)项、(d)项,也有相反的(e)项。第三,在CISG中,实质损害对认定是否构成根本违约具有决定性作用,但其仅是PICC所列出的因素之一,即PICC综合考量现实的复杂情况,更加科学。第四,PICC列出的需特别考虑的因素是非穷尽性的,其在增加确定性的同时也保留了灵活性,裁决者仍有自由裁量的空间。
如果说CISG中根本违约条款是从形式判断转变为实质判断,那么PICC则是在CISG实质判断基础之上的“更进一步”。
二、根本违约的解释之比较
既然每个案件都应根据其自身的具体情况具体分析,那么简单罗列所有的案件结果就毫无意义。将案件类型化整理,同时进行不同类型间的比较分析才有价值。实务中,不当履行和迟延履行更易发生,故下文以这两类违约为例,对根本违约规则的解释及实质损害标准发挥的作用进行探析。
(一)CISG根本违约规则之解释
CISG第七条规定了公约所有条文之解释需遵循的原则,故释法者在解释第二十五条时应受到第七条的约束。第七条第一款包含了“国际性特征”“促进统一”和“诚实信用”三个因素,第二款属于兜底性规定。此外,解释还应坚持“支持合同”原则(saving the contract)。这主要体现在:第一,当违约不构成根本违约时,守约方享有请求实际履行和请求减价等解除合同之外的其他救济方式;第二,若要寻求解除合同的救济,守约方必须证明违约满足第二十五条所规定的要件。
综上,释法者在解释根本违约的规则时,既要防止向国内法逃逸[2],也需要关注类似的判例以保持判决结果一致[3],同时还应秉持“支持合同”原则,不轻易认定违约行为构成根本违约。笔者认为,“支持合同”原则实质上暗含了比例原则的理念。因为支持合同不是无限制地支持,它更强调违约的救济与违约所造成的后果相适应。鉴于守约方可选择的救济方式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其自由意志,违约后果的严重性一定程度上也取决于合同的内容即当事人的意思自治,“支持合同”原则其实既包含对意思自治的支持,又包含对意思自治的限制。到底是东风压倒了西风,还是相反,都取决于具体个案中平衡买卖双方利益所得出的结论。因此,CISG第二十五条规定具有模糊性是有必要的,虽然模糊,但是其解释并不是任意的,要受到解释原则的限制。所谓“磨刀不误砍柴工”,梳理解释原则有利于为个案的解决提供先行经验。
1.迟延履行与根本违约
迟延履行(不涉及履行宽限期)的情况下,法院判定是否根本违约适用了两种不同的标准。
卖方迟延履行不等于根本违约的标准尚未被确立,存在例外。当卖方交付货物的时效性对买方来说构成特别的利益时,如双方就按时交付的重要性进行了约定,那么卖方迟延交付就构成根本违约[4]。此种重要性的判断自然有赖于合同的措辞。此外,还需借助货物自身的性质、交易惯例和其他因素。但买方迟延履行不等于根本违约的标准已基本得到确立,即使买方迟延较长时间后履行义务也能得到宽容。标准的差异主要源于平衡双方利益的考量。当货物处于卖方控制之下且卖方迟延履行时,根本违约的救济方式才能为买方提供充分、必要的救济;而当货物处于买方控制下且买方迟延履行或虽然货物处于卖方控制下但买方迟延履行时,损害赔偿足以救济卖方的权利,也更有利于国际贸易高效、安全地进行。此种差异体现了支持合同所暗含的比例原则之理念。当事人对按时交付重要性的约定未必能直接推导出迟延履行构成根本违约的结论,但凡当事人事先如此约定,将来法院的关注点必将会聚焦到“特殊利益(special interest)”的认定上,且依据诚信原则,当事人的意思自治与特殊利益之间是相关联的。
2.不当履行与根本违约
在判断不当履行是否构成根本违约时,有程序性和实体性两方面的注意事项。前者要求裁决者解释、适用相关规则时避免向国内法逃逸,后者则要求裁决者在判断实质损害时主要采用守约方遭受的实际经济损失的标准。一些法院仅根据不当履行的比例或估算的修理费用占货物总价值的比例进行判断(比例越高越有利于守约方解除合同),一些则采用适销性分析,各法院的分析标准有所不同。[4]
德国上诉法院在处理错误颜色织物案时就未重视程序性的注意事项[5]。法院认为卖方交付了部分错误颜色的织物构成未履行,实际上援引了国内法的相关概念。接着,受德国民法典BGB第三百二十六条规定的影响,法院仅因买方未通知卖方宽限期就停止分析,得出卖方不构成根本违约的结论。事实上,CISG中的宽限期并非守约方宣布整个合同无效之前提,在卖方只交付一部分货物,或者交付的货物中只有一部分符合合同约定的情形下,即使宽限期届满,守约方寻求第四十六条至第五十条的救济也仅适用于缺漏部分及不符合同规定部分的货物,而非整个合同。虽然最终的裁判结果是正确的,但法院并未围绕本案的争议焦点“对症下药”。
至于实体性的注意事项,各国法院普遍注重实际经济损失的判断,但不同判断标准之间仍存在着差异。美国法院在Delchi v.Rotorex一案中基于不符货物的比例高达93%、空调压缩机的制冷效果以及能量消耗是判断产品价值的重要标准这两点原因认定卖方不当履行构成根本违约[5];采用适销性分析的德国法院在镉超标贻贝案中,则认为镉超标不影响货物的相符性,因为水产的镉含量标准不同于肉类,后者仅具有行政指导的作用,同时考虑到贻贝不会在短期内被大量食用,即使超标也无损于人的健康,故卖方不构成根本违约;同样采用适销性分析的法国法院在掺糖酒案中认为,卖方通过给酒加糖篡改了酒的性质,也违反了法国的规定,故掺糖后的酒在法国市场不具有适销性,卖方构成根本违约。法国法官并没有像德国同僚那样考虑货物在国际市场的适销性[4]。这类案件中当事人或多或少都会对货物的质量在合同中进行约定,根据比例进行判断的结果往往与质量条款相一致,不符质量的货物达到一定比例就会导致卖方根本违约;而采用适销性分析,则加大了买方依据质量条款宣布合同无效的难度,同时也体现出支持合同的原则。那么若当事人约定“违反质量条款会导致合同无效”呢?笔者认为需判断此类约定是否属于合同的技术性规定。实质损害要比技术性规定更具决定性[1],若属于后者,则此类约定仅应作为需要考虑的因素之一,并且其优先性应让步于违约的总体影响,以体现公平。
由此,适销性分析与卖方迟延履行构成根本违约的判断标准具有相似性,二者都含有对当事人意思自治(质量/按时交付的重要性)及实质损害(特殊利益/其他用途)的考量。所不同的是,有时只要当事人约定或知晓及时交付的重要性,便足以证明特殊利益的存在。比如买方在合同订立时便告知了卖方其将在特定的日期将货物转售并交付给第三方,那么卖方及时交付对买方来说就具有特殊利益,无需旁证。而即便当事人对货物质量及其重要性有了明确的约定,卖方违反该约定也无法直接证明货物不能被买方用于其他用途,除非买方在合同订立之时就约定了特定的用途。在判断迟延履行和不当履行是否构成根本违约时,法院认定实质损害的标准大相径庭,故最终的判断结果也不一致。
(二)PICC根本违约规则之解释及其对CISG的参考意义
因PICC尚未被普遍接受,其可供参考的案例十分有限,而南非在适用“实质性违约”判断标准时恰恰显示出了其对PICC第7.3.1条的(a)项、(b)项及(c)项规定的认可[6],故下文将以南非的案例为引,进而论证PICC相关规定的实用性。又因PICC第7.3.1条的(a)项部分吸收了CISG的规定,通过案例法的研究,或能总结出PICC之解释对CISG的借鉴意义。
关于迟延履行,南非法院在判断及时履行具有重要意义时会考虑货物是否受价格波动影响、是否具有季节性特征、是否耐保存或者守约方要求对方及时履行是为了履行自己在另一个合同的义务等因素。从本质上看,迟延履行只有造成严重后果才构成根本违约。在Cowley诉Estate Loumeau一案中[6],由于买方及时付款对于买卖标的(破产财产)特定目的之实现至关重要,因而法院认为买方的迟延付款构成根本违约。该案中法院没有包容买方的迟延付款,但可以肯定的是南非法院的判断标准与CISG的是一致的,二者都认为在及时履行对守约方具有特殊利益时,迟延履行会造成实质损害并最终构成根本违约。
关于不当履行,在Sweet诉Ragerguhar案中[6],法院认为无瑕疵交付固然是重要的合同条款,但标的物的尺寸、性质、用途的不符以及被第三方非法占有的事实仅证明违约方未遵守重要条款的程度,第三方非法占有给买方造成实际损害——阻止买方迁入或妨碍其正常经营——才最终导致卖方根本违约。南非法院判定不当履行构成根本违约的标准与CISG亦是相同的,即重要合同条款之违反仅在造成实质损害时才导致根本违约。
涉及到综合考量多个因素的典型案例当属Aucamp诉Morton案[6]。该案中,从实质损害的角度看,违约行为导致腐烂的木材数量不大,不会对守约方的森林造成损害,且违约行为易被补救,违约导致的实际损失通过请求损害赔偿能够得到充分救济;从当事人依合同享有的合理预期看,合同没有明确约定被砍下的木材于何时被搬走也是违约行为不构成根本违约的原因之一;从故意/过失的角度看,违约系违约方员工的过失所致,而非违约方有意为之。法院综合考量后认为,违约方没有根本违约。不过,由于本案各因素的分析结果是同向的,最终结论的得出并不困难。
结合本案与CISG的相关判例,笔者认为在PICC之下,实质损害仅是法院判断的因素之一,但其仍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因主观利益损害(b项、c项、d项)的判断具有抽象性,难以衡量和把握,而客观利益损害(a项、e项)的判断更加科学、公正,也更易把握,故在前种损害严重而后种损害轻微时,违约行为不构成根本违约,反之则构成根本违约。至于前种损害内部各要素之间,主观恶劣程度以外的其他因素不存在优劣之分,应综合各因素的判断来整体界定前种损害的严重程度;但后种损害内部的两个要素之间,守约方遭受的实质损害之考量应优先于违约方的。当然,实务中违约的形式千变万化,PICC列举出的所有因素未必存在于每个案件。同样,个案所要考虑的因素也未必在PICC列出的清单中,但万变不离其宗的是实质损害之考量的主导地位。
三、根本违约规则之比较对中国的启示
PICC在吸收了CISG精髓的同时,又列举出了其他因素以更全面地判断是否根本违约,具有进步性。而实质损害在PICC中仍发挥着主要作用,这也表明PICC受到了CISG的深远影响。也许PICC根本违约的规则不会被普遍接受,但其尝试至少表明我们应始终坚持CISG实质判断之标准,并使其朝着更客观、全面、合理的方向发展。
实务中,最高人民法院在审理蒂森克虏伯冶金产品有限责任公司诉中化国际(新加坡)有限公司一案时,其论证就充分展现出中国法院解释、适用CISG根本违约规则的方式。第一,最高人民法院谨慎衡量买卖双方的利益。考虑到HGI指数仅为当事方约定的七项指标之一且其他指标双方均无异议、HGI指数为32的石油焦虽然用途有限,但是仍具使用价值以及买方后来以合理价格将该批石油焦成功转售这三点原因,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卖方的违约并未造成实质损害。第二,最高人民法院还参考了他国法院裁判时对CISG根本违约规则的理解,且参考得出的结论与前述的结论是一致的。因此,最高人民法院的说理与CISG根本违约规则的解释原则和适用方式是一脉相承的。
至于中国关于根本违约的立法,合同法虽未使用“根本违约”的措辞,但实际上吸收了根本违约的制度——具体体现在第九十四条[2]。第九十四条的规定十分有趣,一方面它的规定较CISG更为具体,条文列举出了四种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具体情形;另一方面第九十四条将合同目的不能实现作为判断标准,与CISG一样具有模糊性:致使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的其他违约行为如何界定、违约至何种程度才算合同目的不能实现我们不得而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三)》(以下简称为司法解释(三))第二十五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理解和适用》就试图去澄清有关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的问题[7],这表明中国的立法正朝着多元化、实质性判断的方向发展。首先,司法解释(三)第二十五条摒弃了以违反的合同义务的重要性定夺违约后果的做法,与CISG的立法发展趋势一致。其次,在判断时要综合考量六个因素,与PICC多角度判断的规定方式相似,且六个因素间的关系具有复杂性。例如,第一个因素与第二个因素是一般与特殊的关系;第三个因素和第五个因素分别针对不同形态的根本违约之判断,既非并列关系,亦无优劣之分;而第四个因素是所有案件都要考虑的。从内容上看,这六个因素与PICC的因素存在差异,但其均可按主客观利益的属性进行划分。
既然中国与PICC的规定模式都是多元化的,那么中国在界定根本违约时是可借鉴PICC列出的因素。同时,当一个案件涉及多个因素的考量,而各因素的分析结果相反时,应秉持实质性因素优先的原则以最大限度地确保公平。另外,中国也应在已有规定的基础上效仿CISG定义根本违约(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的概念。不论是合同法还是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中国均采用列举的方式来规定根本违约,这样看似周详,实则存在问题:第一,列举的规定方式缺乏体系性,可能导致人们只知根本违约包含哪些情形而不知何为根本违约;第二,非穷尽性的列举式规定会导致法律的不确定性,赋予释法者过大的自由裁量权,使其能任意地对未列举出的事项进行解释;第三,采用定义加上列举的规定方式可以很好地解决前述问题,兼顾法律的确定性与灵活性。
四、结语
从CISG根本违约规则的立法变迁看,实质判断的标准愈发占据主导地位,且灵活性的保留是必要的。虽然立法具有模糊性,但是CISG解释原则的限制使释法者任意解释的风险得到了控制。PICC将CISG的实质损害作为判断根本违约的因素之一,增加了具体性与可操作性,但是,这些因素是非穷尽的而且因素之间的关系尚不明晰,故PICC仍然延续了CISG的灵活性。
总结迟延履行和不当履行两类案件后可知,CISG在判断根本违约时既会考虑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又会考虑实质损害。所不同的是,当事人对按时交付重要性的约定更易被证明具有特殊利益,即使当事人对货物质量及其重要性有了明确的约定,卖方违反质量条款也未必构成根本违约,二者举证难度的差异导致了实质损害认定的差异,进而影响根本违约最终的判断。在多因素考量的PICC中,实质损害仍发挥重要作用。客观利益损害的判断应优先于主观利益损害的判断。至于主观利益损害内部的各要素,主观恶劣程度之外的其他因素无优劣之分,应综合考量各因素来界定整体的主观利益损害;但客观利益损害内部的两个要素之间,受害方遭受的实质损害应优先于违约方遭受的实质损害之判断。中国立法应采用定义加列举的规定方式,以更客观、全面、科学地界定根本违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