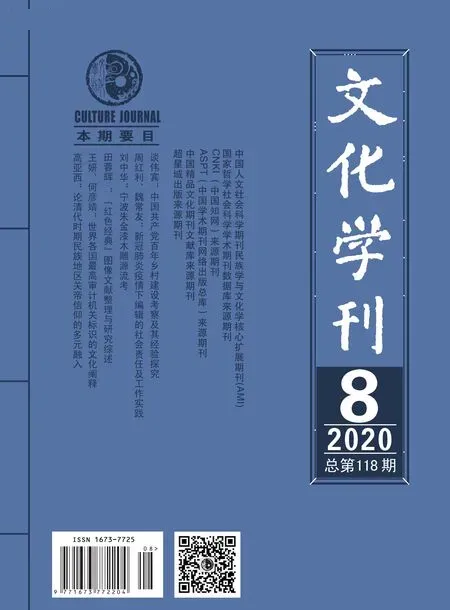伯明翰学派与法兰克福学派文化理论比较研究
马 健
伯明翰学派与法兰克福学派都是以新马克思主义为基础,对大众文化进行各自的解读与研究。对比两个学派的异同点,可以从更深层次上把握大众文化的研究历程以及他们的理论研究对当下的影响,一方面可以完善当下的理论研究,另一方面也能为日后的文化研究提供新思路。
一、共通性:起源与认同
伯明翰学派和法兰克福学派共同营造、推进了20世纪新马克思主义研究在实践与理论上的文化转向,他们从不同方面都认为要回到马克思。法兰克福学派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旗帜,在漫长的理论研究中形成了对社会文化的批判思想,但他们却很难走出精英文化的桎梏;而伯明翰学派则是通过对西方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打破了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之间的壁垒,并以此来探究文化与大众的相互关系。
首先,虽然伯明翰学派与法兰克福学派有诸多不同的文化见解,但他们都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旗帜,这一点毋庸置疑。马克思主义认为存在决定意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也就是说一定的文化研究需要在特定的社会存在和生产方式下进行,即只有在特定环境下进行研究才更具有意义。法兰克福学派与伯明翰学派在这点上持相同意见。虽然两个学派都将文化作为研究对象,但他们却不只局限于对文化的研究,文化仅是一个关注的面向,对与文化相关的领域进行深入探索可以更好地对资本社会的政治、经济等诸多方面进行批驳。简单来说,将文化同社会现实相关联能够解决很多理论上的疑问,而且这些研究都旨在批判和挖掘资本主义更深层的矛盾。
其次,对大众文化的商品化认可。认为大众文化具有商品化特征是两个学派的一致观点,他们都认为大众文化有商品的属性。在工业社会当中,利润当然是大众文化的主要追求,为了拓展文化工业,只能不断追求利益。在法兰克福学派看来,大众文化不再是一种高雅文化,相反,大众文化作为一种商品渗入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虽说伯明翰学派也认为大众文化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有像其他产品一样被生产的趋势,但他们看到了这种文化商品化的特殊之处:一方面,文化的商品化契合大众的部分利益;另一方面,它们也满足了大众在消费层次上的需求。
再者,法兰克福学派与伯明翰学派的批评方式同属于文化主义范畴,他们肯定了文化对社会的联结与整合作用,以及文化在连接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方面的能动作用。这种方式将文化与唯物主义相互结合,以此来摆脱唯物主义同唯心主义的简单化模式。
最后,他们都强调大众文化本身所拥有的实践功能,他们相信艺术可以使个体发生改变,并对社会产生影响。他们的文化理论并非毫无干系;相反,他们从不同的思路看到了大众文化的两面,看到了大众文化本身固有的压制与抵抗的双向运动[1]。
二、相异:文化观念、受众以及方法
从伯明翰学派与法兰克福学派的发展来看,两派在众多文化理论的研究上意见相左,在大众文化的价值、研究范式、理论视角等方面都呈现出不一样的观点。
其一,文化观念不同。一般而言,我们所言的大众文化是“popular culture”。法兰克福学派对其认定带有明显的否定色彩,他们将大众视作乌合之众;而伯明翰学派对大众文化则持比较认可的态度。大众文化在法兰克福学派那里多指工业文化生产的那些规模化商品,这些商品充当了欺瞒大众的工具,他们更愿意将大众文化称作工业文化;相反,伯明翰学派则认为大众文化是为普通民众所喜爱、享有的流行文化,他们能融入大众的生活。
阿多诺认为的大众文化是在工业社会中被批量复制生产出来的文化产品,这些产品以大众为主要消费对象。他与霍克海默将文化工业视为一种流水线生产、复制性的文化工业体系,这些商品能够悄悄地消解并控制大众的观念,成为统治者掌控极权的一种方式,这种控制主要表现在文化宣传等方面。在法兰克福学派这里,大众文化不再能提供太多有用的价值,它们只不过用娱乐的方式掩盖了自身的本性。霍克海默与阿多诺之所以用文化工业这个概念来言说,也许在他们看来,大众文化可能被错误地理解成从大众生活中自发形成并被大众所用的文化,这样的解释遮蔽了其本质,而文化工业则巧妙地表现了资本主义文化生产的本质。
因此,法兰克福学派坚持认为文学艺术的生产是人固有的、独立的创造性活动,在工业社会,文学艺术正在成为一种娱乐性商品,不断沦为供大众消遣的道具。他们往往通过怀念各种高雅艺术来批判大众文化,这也意味着他们蔑视工人阶级的文化,在大众文化问题上呈现出一种悲观主义的态度。他们把大众文化置于所谓的真正的艺术的对立面,并且认为只有高雅文化才具有批判力量,而其他的一切大众文化都是意识形态化的、低俗的,无法被置于大雅之堂。
伯明翰学派虽然在批判工业社会的规模化复制以及对人自身的压制上与法兰克福学派意见相同,但他们并没有完全否定大众文化,他们乐意为大众文化这一文化形式正名并积极推崇。“霍加特在《识字的用途》中指出:文化是大多数人的事情。”[2]在霍加特看来,大众文化是普通民众在其生产生活中生发出来的,大众文化可以被看作他们真实的经历,而不是阿多诺口中所说的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用来蒙蔽、欺骗大众的文化商品。
此外,伯明翰学派的理论研究还借鉴了社会学、人类学、媒介理论等学科成果,将一些思想文化观念、阶级或者种族问题置于广阔的社会历史现象中,以此来寻求解答。霍加特曾指出大众文化代表的是一个实在的、触手可及的世界,它向世人展示出了巨大的激情与活力。此外,威廉斯还认为社会精英所掌握的文化都具有传统性与纯净性,但是那些在传统中比较容易被世人掌握的文化却不在精英文化当中。而且,伯明翰学派非常明确地赞扬大众文化,强调大众文化是一种与社会现实紧密联系的新兴文化,其理论直接促进了大众文化研究学科化的进程[3]。由此可见,理解大众文化必须深入到日常生活的实际,而非纸上谈兵。
当然,造成两个学派文化观念不同的原因有很多,两个学派产生的社会背景是其中重要一点。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者们大都出身上层社会,对底层社会的关注不够,并且他们也缺乏全面的认识,这让他们忽略了底层人们的力量;相反,伯明翰学派的理论家们许多出生于工人阶级家庭,他们受阶级运动的影响较大,因此,当他们参与政治实践的时候,自然也就与工人阶级形成了密切的联系。
其二,对待受众的态度相别。在法兰克福学派看来,文化工业的特征之一便是对大众的选择进行控制。在工业社会中,工具理性取代价值理性,艺术创作不再拘泥于自身的独立空间,而是转向关注日常或者是迎合大众的喜好,它向大众展示的只是虚假的快乐,欺骗性的自由,其目的还是控制大众的选择。阿多诺曾说,文化工业让人置于文化社会的控制之中,而且它还阻碍了人自身的解放与发展,让个体拘泥于生产带来的惰性,无法全面进步,“即使有时候公众偶尔会反抗快乐工业,这种反抗也是软弱无力的,因为快乐工业早就算计好了”[4]。
与法兰克福学派不同,伯明翰学派提出了积极受众的观点。他们关注受众在文化工业社会当中的自我表现与主动性,并认为受众有能力抵抗文化工业的操纵,而不是任由其摆布。在这一点上,费斯克的积极受众观将受众置于有利的一侧,并且肯定了受众在文化社会中的作用。他提出了生产者文本概念,并认为大众能够对文本进行创造性的生产,不断参与进来,这种参与感也可以让受众获得快感和喜悦。
法兰克福学派和伯明翰学派代表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转向中的两种不同的理论方向,他们由消极受众走向了积极受众,把受众逐渐放到了一个很高的位置。这明显体现出了两个学派对待文化工业受众的不同态度,即“从同质的受众到差异的受众,从被动的受众到积极的受众,从自上而下的整合到自下而上的抵抗,从文化工业的欺骗性到大众日常生活的革命与大众文化的抵抗政治”[5]。法兰克福学派习惯性地站在精英主义的角度对大众文化进行彻底批判,他们虽然强调受众有一定作用却没有注意到在文化产品的消费过程中也需要受众的帮助,更没有意识到受众自身的能动性。伯明翰学派则发现了受众的主体性及其在文化产业各个方面的能动性,他们关注受众在产品消费过程中的作用,并将大众文化纳入文化的研究范式,以此来探究大众获得启发和实现一定自由的可能性。
其三,研究方法的差异化。一般而言,民族志的研究方法是研究者在较长的时间内参与人们的生活当中,观看他们发生了什么,聆听他们说了些什么,这种田野调查可以对大众文化进行剖析,以此来解释一系列文化或社会问题。囿于阶级出身,法兰克福学派不可能深入社会进行民族志研究。与之不同,伯明翰学派的众多理论家都会深入社会底层,深入工人阶级,对社会、阶级进行现实的感受与理解,从而为文化理论提供支持。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法兰克福学派与伯明翰学派文化理论的差异,这是马克思主义在当代西方社会中进行文化转向的必然结果,虽然两个学派对大众文化的价值认知不同,在理论研究方向上也有很大出入,但两个学派的研究脉络、理论基础却可以为以后大众文化研究提供众多思路及参照,通过对比分析,也可以从中借鉴不少经验来应对当下的文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