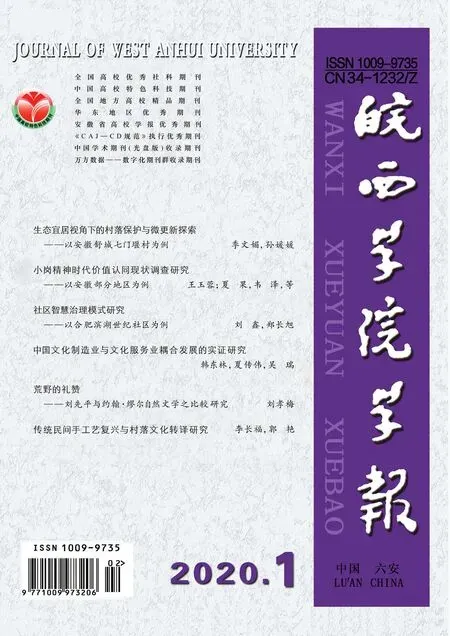荒野的礼赞
——刘先平与约翰·缪尔自然文学之比较研究
刘孝梅
(安徽大学 外语学院大学外语教学部,安徽 合肥 230601)
自然文学作为文学流派,是以自然为主题,以探索人与自然的关系为创作内容,一般以散文、随笔、日记、游记、诗歌等为主要文体,语言清新质朴。作家主要以第一人称、写实的方式,描述其亲近大自然所获得的身心体验,从而唤起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生态意识以及对个人精神和人类文明的思考。美国自然文学产生于17世纪,并于20世纪80年代形成文学流派。中国自然文学继承“天人合一”的传统自然观,顺应世界自然文学的创作大潮,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产生。约翰·缪尔是美国自然文学的先驱,他以在美国西部山岭孤身跋涉几十年的经历,创作了十几部著作,他所提出的自然拥有权利和万物关联论已具有现代生态整体观的萌芽。中国现代自然文学的开拓者安徽作家刘先平与缪尔经历极其相似,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起,他在祖国的高原山川、沙漠盆地、雨林群岛等探险近四十年,创作了几十部优秀著作,还率先提出了“生态道德”理念,呼吁人们树立生态理想、建构生态人格。作为中美自然文学的开拓者,约翰·缪尔和刘先平既体现出超越时代、跨越文化的相似性,如热爱自然、投身荒野;又都具有超越时代的生态忧患意识,在作品中都高度关注生态破坏和环境恶化,致力于唤醒公众环保意识等。但由于时代、中西文化传统及思想源流的不同,他们对自然的认知及自然书写也存在不少的差异。总的来说,他们是同中有异,异中有同。中美自然文学的对比研究既可促进相互之间的交流和融合发展,又可发挥文学的文化引领作用,在全球环境持续恶化、灾难疫情频发的当下,有助于树立全民生态理想,实现全球生态文明。
一、荒野情结——源于内心的呼唤与来自理性的思考
不同于其他文学形式,自然文学写作首先要以自然考察为基础,作家要亲历现场、亲身经历。他们一般以自己的家乡、特定地域为支撑点,或者进行野外考察,观察、记录、书写自然。而在中美自然文学作家中,缪尔和刘先平的野外探险无论是在地域的广博性、时间的长久性、荒野的冒险性及对自然的科学探索上都具有空前的超越性和相似性,但缪尔对荒野的热爱主要源于内心的精神需要,刘先平则更多来自于科学考察所获得的对自然的理性思考。
缪尔称自己是“一个无可救药的山野之人”[1](P81),他一生几乎踏遍美国中西部所有的山峦冰川,几乎所写的作品都与山有关,为与美国东部以写鸟著称的约翰·巴勒斯区别,人们称他为“山之王国中的约翰”。缪尔对自然的亲近与其童年的成长环境密不可分,他1838年出生在苏格兰的乡村,从幼年起就喜爱一切野性的东西。十几岁时,缪尔全家移居美国的威斯康星州的一个农场,近十年的农场生活中,“荒野的课程”教授给他的不仅是动植物的生长习性,更是对自然的热爱,他觉得“农场生活最大的好处之一就是可以把动物当成同等的生物来了解,学会尊重它们,爱它们,甚至赢得它们的爱”[2](P69)。成年后缪尔入读威斯康星大学并对地质学和植物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离开大学后,缪尔开启漫游生活,足迹遍布美加东南部、欧洲、中国等亚洲国家、非洲,但他终其一生最热爱的还是探索美国西部的山峦冰川、森林湖泊、草原峡谷。
缪尔以强烈的科学精神在野外进行艰苦的探险,但在他看来,走向荒野,实际上是走向内心,是一种精神上的回归之旅。地域感(sense of place)是美国自然文学的特征之一,每一个自然文学家都在特定的地域,观察他身边的自然,融入自己的所思所感。但缪尔无疑是其中最贴近自然的一个,与梭罗安于宁静的康科德不同,缪尔面对的是西部粗犷而残酷的自然。他常常在荒野长途跋涉,风餐露宿,晚上在山坡上满天的星斗下入睡,但他还遗憾自己不能像星星那样永远凝视天地万物。为了近距离观察约塞美蒂瀑布,他曾手脚并用,紧扣光滑的峭壁爬到瀑布的下面。当见证瀑布从巨大的峭壁飞流而下时,他觉得为这一狂喜而死都是值得的。此外,美国自然文学家大多安于一隅观察自然,贝斯顿在科德角海滩、威廉斯在大盐湖、艾比在犹他州沙漠,缪尔却长达十一年在美国中西部的广袤山区如内华达山脉和大盆地地区徒步考察冰川、森林以及野生生物等。区别于其他自然文学家,缪尔既具有自然博爱之心又具有科学理性,具备比较系统全面的动物学、生物学、生态学、地理学等科学知识,从而让他更好地考察自然,理性看待人与自然的关系。
而在中国自然文学作家中,像刘先平那样在大自然中探索四十余年、自觉从事大自然文学创作三十多年的,绝无仅有。他多次登上青藏高原,四次探险怒江大峡谷,三次穿越塔克拉玛干大沙漠,两次横穿中国大陆……,创作了几十部描写大自然探险的作品。刘先平“热爱祖国的每一片绿叶,每一座山峰,每一条小溪”[3](P198),他对自然家园的热爱来自于他童年时期家乡自然环境的陶冶。刘先平1938年出生于巢湖北岸长临河西的一个小村,父母早逝、物质匮乏,但在美丽的巢湖里嬉水、沙滩上游戏、捉蟋蟀、寻云雀窝、夜晚用篾笼罩鱼,在作家幼小的心灵里埋下了走向大自然的种子。作家曾深情回忆:“这片充满生机、熙熙攘攘的湖边世界,给我幼小的心灵倾注了无限深厚的爱。爱是种子。以后,我常常去崇山峻岭、大漠戈壁、雪峰冰川、江河湖海,寻找它生出的绿叶、开出的紫色小花、飞出的鸟群……”[3](P91)。成年后他以自然文学创作“将大自然赠给每个人作为故乡”[3](序)。
刘先平自然文学也都是基于野外考察探险,具有目击性、纪实性、现场性,而且他对自然的探索在地域范围、地貌特征及生物种类上都非常广泛多样。刘先平的大自然文学之旅起始于20世纪70年代与科学家去皖南考察,自此后,祖国各地的山川海洋、沙漠湿地、高原海岛都是他探险考察的对象。在大自然中跋涉近四十年间,他遇到的种种艰难险阻从他谈论登山之难的这句话可见一斑:“必要的话,用嘴也要咬住石棱,你才能上到高山”[4](P17)!此外,刘先平的科学素养使他能够更好感受大自然,描写大自然。他的大自然探险主要是与科学家一起参加科学实地考察,这使他学习到了很多关于生物学、植物学、地质学、天体学等诸多学科领域的专业知识,提高了他对人类生存的外在自然世界更深层次更加自觉理性的认识。1979年,他写了中国第一部在梅花鹿世界探险的长篇小说《呦呦鹿鸣》,然后又先后在鸟类世界、大熊猫世界、猿猴世界探险并进行文学创作。更重要的是,“荒野大学”教给他的除了更多的科学知识,还让他一点点领悟到人与自然应该如何相处,以及认识到自己的使命——呼唤生态道德。
自然文学作家张炜曾说作家就是一些与自然保持紧密接触的人。正是源于幼年培养起的对自然的热爱和成年后的经年累月的野外探索及思考,缪尔和刘先平成长为中美自然文学的先驱。当今,由于经济的快速发展及人类对物质的无尽追逐,环境急剧恶化,伴随而来的则是人性的异化。发挥自然文学的文化渗透力、审美感染力和教育感召力,让每一个人,尤其是少年儿童,都能发自内心热爱自然,呵护我们的精神家园,变得迫在眉睫。
二、荒野意识——神性自然的超验主义影响与“天人合一”的古典哲学观影响
在长期的自然探险过程中,缪尔和刘先平逐渐认识到荒野的价值,重新思索人与自然的关系并积极进行环保实践。缪尔认为自然也拥有权利,且自然与人类皆属同一共同体,共同体内一切成员平等,并且相互依存。而刘先平三十多年的自然文学实践“其实只是在做一件事:呼吁生态道德”[4](P3),即人与自然相处时应遵守一定的道德行为规范,从而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他们都以超前的忧患意识提出了人与自然平等、和谐的生态伦理思想,但由于受到基督教及超验主义思想的影响,缪尔的自然观带有浓厚的宗教神秘主义色彩,刘先平的生态道德思想则体现出“天人合一”古典哲学观的影响下对重建诗意栖息的精神家园的愿景。
缪尔对生态伦理学的巨大贡献是提出了“自然拥有权利”和万物关联论。长期以来西方的哲学思想认为自我与环境、物质与精神是相互对立的二元关系。19世纪时爱默生在《论自然》中首先提出了“自然是精神之象征”,引领人们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缪尔继承了爱默生的思想,认为自然界的万物都是上帝精神的投射,并且“在上帝的荒野里蕴藏着这个世界的希望”[5](P131),所以他深入美国西部崇山峻岭、冰川湖泊,时而眺望远处山峰,时而跪下来凝视一朵雏菊。正是一次在荒野中邂逅一片开在深山,“无人亦自芳”的百合花,疲累饥饿的他得到了激励和鼓舞,喜极而泣,领悟到“大自然肯定首先是,而且最重要的也是为了它自己和它的创造者而存在的。所有的事物都拥有价值”[6]。也就是说,万物都有其自身权利、自在价值,因其自身而造。缪尔称刺柏为“岩石居民”,蚂蚱为“大山里最快乐的孩子”,而自己则是熊的“人类兄弟”,万物皆平等,共生于自然界。“当我们试着单独挑出一个事物的时候,我们发现它和宇宙中其他一切都有关联”[7](P161)。他还进一步思索人与自然的关系,认为正如羊身上的那些细羊毛离不开那粗羊毛一样,人类与自然、文化与自然也是一种类似的息息相关、共生共存的关系。缪尔的初具生态伦理萌芽的思想不仅推进了爱默生和梭罗的思想,也为后来利奥波德具有生态整体观的“土地伦理”的提出奠定了基础。
缪尔的环保实践主要体现在他促进了美国国家公园制度的建立。作为20世纪初美国环境保护运动的先驱,缪尔以其前瞻性和超前的忧患意识,积极进行环保实践,被称为“美国自然保护运动的圣人”。首先,缪尔是国家公园制度的倡导者。在西部山野的探险中,缪尔痛心于荒野所遭受的破坏,于是积极撰文呼吁建立国家自然保护区,最终促成了1890年优胜美地国家自然保护公园的建立,所以缪尔又被称为“国家公园之父”。此外,他还组建了民间环保组织“山岭俱乐部”去保护内华达山岭的自然环境。缪尔关于自然生态保护的思想还很大程度上影响了20世纪早期的自然保护活动,并最终促使美国在1964年出台了《荒野法案》,以立法的方式确立了对联邦土地的荒野价值进行特别保护。作为荒野的卫士,缪尔的自然文学作品和他参与保护自然的实践,逐步唤醒了公众的生态意识。
刘先平对生态伦理学的杰出贡献在于倡导人与自然相处时应遵循的“生态道德”思想。中国文学作品中,描摹自然的壮美秀丽,人在自然和谐相处的佳篇不胜枚举,但自然界的美丽景观、动物植物却总是屈从于人之需要。常年的自然探险让刘先平的自然意识不断增强,在他看来,万物之灵的人不过是自然万物中的一员,人类必须走出以人类为中心的传统误区。他以高山榕树和青梅树为例,表达了其万物平等,自然界一切生物各有其价值的思想。高山榕树将种子寄生在青梅树上,侵占青梅树的水分、阳光、空间,最终导致青梅树枯死而高山榕树繁茂生长。人们痛恨高山榕因为其木材低劣而青梅树则价值较高,作者却为高山榕申辩:“它不是也应该有生存的权利吗?”[3](P3)可见,刘先平与缪尔的“自然拥有权利”的思想不谋而合,人们不应该以人类的善恶标准去评判自然界生命,而要从生态的整体及自然法则去敬畏自然。当今全球环境急剧恶化,仅靠法律、行政法规规范人们的行为已远远不够,刘先平的“生态道德”思想主张通过促进人思想道德意识的改变去重塑人与自然的关系,消除环境危机,建设人与自然的和谐。
刘先平的环保实践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开展大量的科学考察实践活动,一是发挥自然文学作品本身的思想教化作用,积极推动大自然文学的研究。国内自然文学作家中,刘先平的自然考察地域最广阔,足迹遍布祖国的山川、海洋、沙漠、湿地、高原、海岛等。他说:“我要写的是原旨大自然文学,因而把考察大自然看作第一重要,然后才是把考察、探险中的所得写成了大自然探险文学”[4](P9)。因而他的作品中,各种地质地貌、各种动物、植物、微生物,应有尽有,仅《山野寻趣》描述的动物就多达百余种,竭尽所能地展现了大自然的壮美与优美,从而潜移默化地引导人们逐渐对自然环境持有新的观念和态度。为进一步扩大大自然文学的文学影响力,刘先平积极推动大自然文学研究,2010年成立了“刘先平大自然文学工作室”和“大自然文学研究所”,还召开了大自然文学国内、国际研讨会。此外,为了在全社会呼唤树立生态道德,作家在文学之外积极奔走实践,为保护美丽巢湖提议案,举行大自然征文比赛、读书会等等。
正是得益于长期的荒野考察,刘先平和缪尔对自然的意识不断觉醒,以其超前的忧患意识,从中、西各自思想文化出发,形成了对荒野价值、生物的自身权利、万物平等及共同体相互依存的生态伦理思想的认知。更难能可贵的是他们不仅是自然的观察者,还是坚定的环保实践者。正如作家胡冬林所说:“当人类利益与野生世界发生冲突时,我永远站在野生世界一边”[8](P332),这也是所有自然文学家们对待自然的共同态度。
三、荒野叙述:大自然的永恒神圣律动与自然万物间的和谐动态平衡
自然文学作家一般以一个特定地理环境如山脉、湖泊、溪流、沙漠为视角来观察自然,同时将自然的风景与其在自然中的内在体验相结合,形成了文学史上特有的抒写自然的“荒野叙述”。缪尔和刘先平的荒野叙述在思想内涵、语言文体风格方面具有很多相同点,如荒野的冒险经历书写、倡导生态整体观、表现自然的动感等,但他们也存在不少的差异。
(一)“神性自然”与“自然之歌”
缪尔的作品中,“神性自然”及万物关联论是他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再探索及对超验主义思想的继承与超越。自爱默生宣称“我们在丛林中重新找到了理智和信仰”[9](P6),“自然是精神之象征”成为美国自然文学思想内涵的基础。缪尔继承了爱默生和梭罗的超验主义自然观,试图在西部荒野中寻找神性的力量,于是自然界的一切在他眼里都闪烁着神性的光辉,呈现宗教神秘主义色彩。在其代表作《夏日走过山间》中,当他初次走进优胜美地山,就像是走进了“自然的教堂”,“整个世界看上去就是一个大教堂,而这大山,就是圣坛”[7](P253)。神性自然成为缪尔作品思想内涵的一个显著特色。尽管缪尔吸取了爱默生、梭罗的超验主义思想,但他对荒野价值的认识和体验更深刻、更广博,缪尔的作品中已体现出生态整体观的萌芽,包含了大自然拥有权利且人与自然息息相关等思想。此外,缪尔在山野冰川的冒险经历拓宽了他的文学视野,他将荒野开拓精神与超验主义相结合,从荒野对人的意志的磨炼来评判荒野的价值,即人能从自然中寻求到更深层次的精神上的宁静和愉悦。
刘先平自然文学作品的内涵主要体现为展示自然之美,并表达人对自然的敬畏。同时,在长期的大自然探险过程中,他逐渐认识到其他生物的生命权,形成了以生态整体观为视域的自觉创作意识。首先,刘先平的自然文学作品实现了由人性关照到大自然关照的转变,山川草木、鸟兽虫鱼、自然界的生物成为叙事的主体,他的作品“不再只讲人性,而是要讲兽性、禽性、山川河流花草树木之性”[4](P59),重新唤起人们对于自然的与生俱来的亲近及敬畏之心。其次,作家以大自然的生态利益为最高描写价值,作品中对破坏生态平衡、践踏野生物种生存权的行为予以批判,从中表达出他对大自然所有生命的关爱与悲悯之心。无论是赞美自然,还是表达人对自然的敬畏,刘先平始终以生态整体观为立场,进而提出了人与自然相处时应该遵循的“生态道德”问题,这既是对中国古典“天人合一”自然观和传统价值观的传承和重申,也是顺应了世界自然文学的生态立场。
(二)“流动着的自然”与自然界的动态平衡
缪尔和刘先平都不仅描写自然的静态,还都从不同的侧面描述了大自然中的激烈动态。“鲜活和动感是缪尔笔下自然的特色”[10](P168)。不同于大多数美国自然文学作家,缪尔长期跋涉在西部严酷的自然中,经常风餐露宿,不时面临生死考验,鲜活、刺激的冒险经历和探险精神使他笔下的自然充满动感,作家常常用一连串的动词去描述永远处于流动变化中的自然万物以及人在自然中的活泼动态。除了强调自然的动感,缪尔也描述了大自然的宁静和庄严,以及“大地上所有的景物之间的联系和整体性”[7](P243),使大自然的动、静相辅相成。刘先平的作品也是一首大自然动、静结合的协奏曲。“静”首先体现在人与自然的和谐需在静态中获得,即人类不能违反大自然的规律去破坏大自然,而是需要保持共同体的完整性、平衡性及相互间的联系。其次“静”还表现在自然界内部本身具有的奇趣温和的一面。但自然界的生态平衡静和动相辅相成,竞争是大自然保持平衡的法则。刘先平的作品充分描述了大自然的激烈竞争、弱肉强食,如野猪与斑狗群的殊死搏斗、熊猫与红狼、黑鹰与小兔的战斗等,这种对作家在历险中亲身观察到的自然界的残酷与生命的顽强的真实描写,使得刘先平的文学作品“在风格上充满了阳刚之气”[4](P48)。
(三)精确优美的叙述与融合多样的“大自然文学体”
在语言、文体风格方面,他们都将科学性与诗意表达相结合。缪尔的文体朴实、语言优美,如描写溪流,语言凝练、充满动态美:“这些溪流发出叮咚声奔流着,形成一个个欢乐的漩涡,流过阳光,淌过树荫,在水潭里闪烁,汇聚它们的激流,激荡着,舞蹈着……”[7](P99)。另外,缪尔还将其掌握的丰富的自然科学知识与文学创作紧密结合,对自然拥有了更多的洞察力,从而“不仅以一种科学的精确性再现了自然的外在肌理,而且以一种强烈的精神力量阐释了自然的内在价值”[11]。缪尔的这种写作风格启发了美国一代代自然文学作家。同样,刘先平多年跟随科学考察队考察,因而能以科学精神客观具体地描写自然中各种动植物的生态习性以及大自然的客观规律,同时还将其在自然中的切身体验转化为诗意的话语,如“山谷中纵横飞掠的白腰雨燕,不就是朵朵盛开的白杜鹃?……鸟是开放在天空的花朵!”[3](P43)后期作家还将抒情性话语和哲学思索相结合,表达其对现代生态整体主义哲学的思考。此外,刘先平积极探索新的文体和风格,在其探险纪实散文中,构建了包括传奇故事、探险小说、报告文学、游记散文等不同文体并存的复合式的叙事模式及多种语言风格交织的独特的“大自然文学体”。
可见,缪尔与刘先平的自然书写的不同主要体现为三个方面。在作品的思想内涵上,受基督教及超验主义思想影响,神性自然成为缪尔作品内涵的特征,刘先平的作品则传承了“天人合一”中国古典哲学思想,表达了对自然的赞美、敬畏及呼唤人与自然的和谐。其次,缪尔的作品侧重于描写“流动着的自然”,刘先平的作品则更关注自然界生物间的激烈的动态平衡。最后,他们的作品都将精确描述与诗意的表达相结合,而刘先平的“大自然文学体”则是对自然文学文体的一次有益探索和创新突破。
四、结语
作为中美自然文学的先驱,刘先平和约翰缪尔对荒野的热爱、对自然的认知及对自然的书写都体现出跨越文化的相似之处。常年的野外考察和探索思考使他们得以从各自的思想文化出发,形成了对荒野价值、万物平等及共同体相互依存等生态伦理意识的共识,而这些荒野冒险经历和荒野意识,拓宽了他们的自然文学的创作视野及自然保护实践。他们的作品都倡导自然拥有其自身权利,都不仅描写自然的静态美,人与自然的和谐美,还关注自然的动感,都注重将对大自然生物的精确描述与诗意的散文语言结合。但由于时代、文化传统及思想源流的不同,他们的作品在思想内涵和风格特色上也存在差异。缪尔的作品体现出神性自然的特征,刘先平则传承了中国古典哲学思想,表达了对自然的礼赞和敬畏。其次,缪尔的作品超越时代局限已经体现出现代生态整体观的萌芽,而刘先平的自然文学继承中国传统自然观并以现代生态整体观为基础,率先倡导树立“生态道德”,是中国自然文学对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重要贡献。缪尔的作品抒写了大自然的永恒律动,刘先平的作品则更多着墨于自然界生物之间的动态平衡。缪尔以朴实的文体和风格启发了后代自然文学家,而刘先平的“大自然文学体”以新的文体与语言风格对书写自然进行了积极的探索与实践,具有重大的创新意义。在全球化时代,人类的可持续发展面临着共同的环境压力和“共谋全球生态文明”的需求,而生态文明的建设离不开生态文化的熏陶。中美自然文学之间的比较研究可以加强相互间的交流和发展,从而充分发挥自然文学在认知、审美、教育等方面的引领作用,促进实现全球生态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