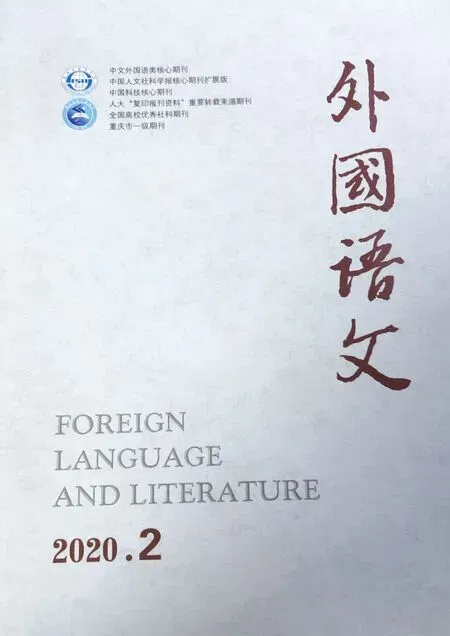傅兰雅与益智书会的译名统一与标准化
张美平
(浙江树人大学 人文与外国语学院,浙江 杭州 310015)
0 引言
中国现代化进程关涉的问题很多,其中以西学移植最为重要。欲通过翻译实现西学移植,必须使国人准确理解传达西学知识的关键译名(或曰“术语”“名目”)及内涵,否则,势必影响西学移植的效果。清末系统的译名统一与标准化工作肇始于益智书会。作为一家由热心中国现代化事业的西方来华传教士创办的著名西学传播机构,益智书会在傅兰雅(John Fryer)、狄考文(C. W. Mateer)等主持下,为译名统一做了大量奠基性的工作,为译名的标准化、现代化做出了贡献。
傅兰雅是来自英国的著名翻译家。他于1861年来到中国香港,担任圣保罗书院校长,从此开启了在华传播西学的活动。傅兰雅作为中国现代化运动最早、最重要的参与者之一,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受到学界重视。其译名统一工作也广受学者们关注,如袁锦翔(1984)、夏晶(2011)、张龙平(2011)、黎昌抱、杨利芳(2018)等。这些成果从不同层面讨论了傅氏的贡献,对其在益智书会20年(1877—1896)的译名统一工作虽有提及,但缺乏深入研究。本文将结合现有研究,对傅兰雅即其贡献进行更深入的探讨。
1 益智书会创办前译名统一与标准化中存在的问题
近代中国最早从事与译名有关的工作是英国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他于嘉庆十二年(1807)来华,历时16年,于1823年出版了中国第一部英汉汉英字典——《华英字典》。近代中国有组织的译名统一工作则始于由部分在华西人创办的出版机构“益智会”。1834年,该会即编制已有的中文科学译名,厘定统一标准,供其会员从事译事的参照。此后,徐继畬的《瀛寰志略》(故宫博物院,2001:111)、何秋涛的《朔方备乘》(编纂委员会,2002:271)以及京师同文馆(Fryer, 1880)等对译名问题都有关注。1877年之前,西学尚未在中国广泛传播,系统掌握西学知识的人寥寥无几,且学习西学的场所仅限于为数不多的教会学堂和由奕、李鸿章等创办的外国语言、科技和军事学堂。政府或民间的机构还没有对译名的统一问题做出具体规定,因而译名创制缺乏统一标准,从事译书的机构或个人各行其是,译名混乱现象尤为严重。傅兰雅在《金石中西名目表序》中指出同一事物汉译后存在“名目不同”的状况。
美国代那作《金石识别》书。同治八年,玛高温译以汉文,所定金石之名,初时未曾列表,故考究矿学者往往既得金石只有西名,而无华名,即不能从已译之书索其底蕴,且后人续译化学、矿学等书,因无金石名表,故不免另立新名,由是金石家更以名目不同为憾。(Dagenais,2010:356)
这种“名目不同”,即译名不统一的现象,在清末翻译界可以说是常态。例如,Algebra一词,中国古代称作“天元”,现译“代数学”“代数”,但在明清时期却有“借根方”(耶稣会士译)、“代数学”(伟烈亚力译)、“代数术”(傅兰雅译)等不同表达。Science一词,今译“科学”,清末则被译作“博物”(合信译)、“格致”(伟列亚力、李善兰译)。又如,韦尔司(David Wells)的PrinciplesandApplicationsofChemistry(1872)一书,被广州博济医局医生嘉约翰(J. Ker)、江南制造局翻译傅兰雅和京师同文馆教习毕利干(A. Billequin)分别译成《化学初阶》《化学鉴原》《化学阐原》,不明就里者还以为是系列化学丛书。
译名创制除了存在“名目不同”,还有误译、错译、乱译等问题。例如,美国法学家惠顿(Henry Wheaton)的ElementsofInternationalLaw(中译名《万国公法》)一书中,该书译者丁韪良将real and personal property(不动产、动产)译为“植物”“动物”;将the form of government(政体)、Congress(国会)、House of Representatives(众议院)、Senate(参议院)分别译为“国法”“总会”“下房”“上房”(Wheaton, 1936:52-102; 惠顿, 1864:49-72)。此类让今人啼笑皆非、不知所云的译名,在该书中俯拾皆是。
这些翻译乱象的产生,有些是客观问题,如译名创制本身的难度。惠特莫尔说,科学家都有自己的专属语言,不为其他领域的人所熟悉。这些语言都经过仔细选择,比日常的语言更精确、更谨严,非专业人士所能轻易读懂(Whitmore, 1955:185)。此外,还有译者的见识或水平、中文修养以及当时没有更多的词语可供选择等问题。但更多的则是主观态度问题,如一些译者态度不认真、急于求成、信息封锁、不屑互相往来与沟通等。1890年5月,傅兰雅在第二次全国传教士大会上发表关于译名统一问题的演讲,严肃批评了这些现象:
实现现代科学与现存译名有效嫁接的唯一困难是就我们自己所做的工作进行沟通时采取了非科学的态度。我们总是急于求成,急匆匆地将一本从中国人的角度看是很不合适的科学书籍,不成系统地用新造的名称或表达法意译或音译出来,以便省去查找已经用了几个世纪或当下翻译家翻译的现成译名……几乎每一位翻译家或编者都有一套自己的有关技术、地理或传记学的译名表,但他们秘而不宣……混乱逐年递增……这不仅是因为明确、一致的译名创制体系无法建立,也因为那些翻译家传播科学知识时匆匆忙忙、不假思索、缺乏互通信息的缘故。( Dagenais, 2010: 386)
近人杨选青曾提及由于主观态度造成的“混名之弊”。他说,合信的《博物新编》中已有“淡(氮)气”之定名,但仍有人将“前人所定者置于不论”,译为“轻(氢)气”,造成“淡(氮)气、轻(氢)气之议几难分辨”。他还说教会系统将造化万物之主译为“天主”“真神”“上帝”,“尚且混名如此,其他可以类推”(上海图书馆,2016:314)。孙维新也说:“所用名目意义不同,最易混阅者之目。”(上海图书馆,2016:92)译名混乱必将导致读者理解困难,解读错误,徒费时间和精力,从而扼杀了他们学习和掌握西学的兴趣,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中国移植西学的效果以及对西方文化的借鉴。而且,学校教科书上的译名错误,极易造成混乱,导致传播的知识被错误解读。借助学生这个媒介,贻害更是无穷无尽。
2 傅兰雅与益智书会的译名统一与标准化
最热心统一译名者为西人,其中又以傅兰雅为最。孔慧怡将傅兰雅和李提摩太、林乐知、丁韪良列为清末最重要的在华西人译者,并指出正是傅兰雅启动了译名标准化、编撰译名表等工作 (Huang, 1999: 235) 。
1877年5月,在华新教传教士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为了给华人提供学习汉语和西方知识及思想的机会” (Bennett,1967:60) ,在傅兰雅等人倡议下,大会成立学校教科书委员会(The School and Textbook Series Committee),决定由傅兰雅和时任江南制造局翻译兼外文教习林乐知(Allen Young)分别负责编纂初级和高级两个系列的教科用书,内容涵盖数学、化学、天文学、历史学、语言学、地理学等十个领域。教科书委员会要求教科书的译名必须统一。
为了给教科书编译和教会学校的教学提供遵循,该委员会自觉承担起译名统一与标准化工作,由傅兰雅、林乐知负总责。委员会成员负责收集已有的各个学科的译名,制成有中西对照的译名表,尽快寄给委员会秘书处汇总,然后将经委员会审查认可的译名列表打印,编成《译名指南》 (vade mecum),寄给各译名的收集者或译者。如不适合通行使用,则由委员会另行组织力量编订。傅兰雅负责工艺制造方面的译名,林乐知负责地理、传记学译名,伟烈亚力(A. Wylie)负责天文、数理译名,麦嘉缔(D. Macartee)负责收集日本人所曾使用的译名。1879年10月,学校教科书委员会更名为“益智书会(The Useful Knowledge Book Society)”。傅兰雅出任书会总编辑。翌年3月,益智书会在上海召开书会出版委员会会议。根据会议记录,傅兰雅向书会提交他多年以来收集的各种科学译名和专有名词样本。他准备出版其中的一部分译名集。除傅兰雅以外,伟烈亚力提供了数学、天文学、机械学方面的译名,艾约瑟(Joseph Edkins)提供了佛教译名,察麦尔(Dr. Chalmers)提供了道教译名,李凤苞(时任驻柏林公使)提供了约25 000条地理译名。这些地理名词系他与江南制造局翻译金楷理(Dr. Kreyer) 共同编译和收集而成。这是在傅兰雅主持下,益智书会译名统一工作取得较有成效的时期。
但自那时起,益智书会的译名统一工作进展迟缓,一直没有新的成果面世。为了扭转这一局面,1887年4月,益智书会在上海召开会议,其通过的决议称:鉴于译名不统一会引起不方便的缘故,委员会同意将花更多的精力编撰一本《翻译指南》。今后任何新书若没有中西对照的译名表,一概不予出版。傅兰雅按照书会要求,编制了多部有中西对照的译名集。1889年,在上海格致书院举行的春季考课中获得超等第一名的孙维新在其课艺中专门提及并肯定傅氏编制的译名表。他说:“论矿石之类极详,惟名目与他书有异。后傅兰雅集成《中西名目表》一册,与《金石识别》之名及他书内之名并列。每查一名,即知他书内用何名。”(上海图书馆,2016:81)《金石识别》是美国传教士玛高温(Danial Macgowen)与中国科学家华蘅芳合译的矿物学译著。傅兰雅将他们创制的不少时人难解的译名,制成附有中西对照的译名表,极大地方便了西学知识在中国的传播。但由于益智书会是一个没有强制力的民间组织,因而关于没有译名表的书籍“一概不予出版”的刚性规定很难真正得到响应,落实效果较差,因而无法改变译名统一工作进展缓慢的局面。到1890年为止,书会仅出版了傅兰雅所编的四份《翻译指南》小册子,内容涉及矿物、化学、医药卫生、蒸汽机等学科。就在这一年,益智书会决定改组,其英文名称更名为The Educational Association of China(中华教育会),但中文表述不变,仍沿用原来的“益智书会”。傅兰雅除继续担任该会总编辑以外,还兼任执行委员会主席和出版委员会委员等职。
傅兰雅不仅躬行实践,而且在译名创制理论方面也有建树。1872年,傅兰雅(1988:170-171)在《化学鉴原·华字命名》中提出了以单字命名和音义结合的化学元素命名原则。1880年,他发表《译书事略》(Account of the Department for the Translation of Foreign Books at the Kiangnan Arsenal, Shanghai)一文,指出“译西书第一要事为名目”,并提出关于“名目”创制的三件“要事”( Fryer,1880)。1890年5月,傅兰雅发表《科学译名——当前的混乱状况及实现统一的路径》(Scientific Terminology: Present Discrepancies and Means of Securing Uniformity)一文。该文共分四个部分:(1)科技译名与中国语言的关系;(2)中国科技译名体系的基本特征;(3)现有科技译名混乱产生的原因及表现;(4)避免混乱产生的路径。傅兰雅在第三部分中详尽讨论了译名创制的原则及其路径。其主要观点如下:(1)尽可能译义,不能仅是音译;(2)尽最大可能遵循汉字构造规制,发掘和利用生僻字;(3)音节不宜过多,应当简明扼要,定义需准确、清晰;(4)必须与其他同类译名有相似之处;(5)不能死扣规则,须有灵活性(Dagenais,2010:376-405)。这是傅兰雅最详尽、最重要的译名创制理论文献,在中国译论史上具有一定地位。他提出的理论被中国本土译者所借鉴,用于指导翻译实践,其中的化学、地质学、数学、机械学、医学等多个领域的不少译名一直沿用至今,如与徐寿合译的《化学鉴原》中,共创制65个化学元素汉文译名,其中铝、钡、钾、锂、铀、锑等36个元素至今仍在通行。这些译名成为人们从事科技翻译及教材编撰的重要遵循,有力推进了西学知识在中国的推广与普及。
1891年11月,益智书会出版委员会在上海美华书馆召开会议,对译名统一工作进行了详尽擘画,其重要举措之一,是增设人名与地名委员会,专门负责收集在华西人出版物中的地理学、传记学等学科译名。傅兰雅担任委员会主席,成员有金曼(H. Kingman)、赫士(W. Hayes)和巴修理(W. Barber)等。根据该委员会的安排,他们将着力做好如下工作:(1)尽可能完整地收集英文地理名词。以此为基础,尽量配上从传教士教师业已出版的中文地理译名表以及从中外书籍中获取的译名;(2)建立音译人名与地名系统;(3)修改现存的译名,既包括所有的圣经、地理译名,也包括古代和近代的一些重要译名;(4)译名表以江戴德(L. D. Chapin)、傅兰雅等人收集或编订的译名为基础。益智书会还决定收集技术译名,该项工作由狄考文任主席的出版委员会直接进行。其具体工作由狄考文、傅兰雅、李安德(L. W. Pilcher)等负责。其中,傅兰雅负责收集化学、物理学、矿物学、气象学、造船学、工程学等多个领域的技术译名。傅兰雅是唯一参与两个委员会工作的翻译家,且担任其中一个委员会的主席职务。
1895年,中国在甲午战争中惨败,中日之间包括武器、技术在内的多个领域的巨大落差促使国人惊醒,彻底改变了社会对西学的认知,人们重新认识到实施改革和学习西方先进科技的重要性,“多年前他们曾接触到的西方科学及其孪生姊妹宗教,已再次引起人们的注意并被人们所接受。全国上下都在疾呼学习西方科学知识”(Dagenais, 2010: 418)。虽然洋务派创办的各类新式学堂和西方传教士创办的教会学堂,培养了一批通晓外文的科技人才,但人才依然极其紧缺。通过译本则成了学习西方科学的主要路径。因此,傅兰雅等人主持的江南制造局等机构翻译的科技书籍被销售一空。傅兰雅说,在格致书室,销售的益智书会编译的教科书是去年(按:即1895年)的两倍,在上海和其他地方印制并销售了许多质量参差不一的科学书籍(Dagenais, 2010: 418)。但限于当时的条件,这些书籍中的译名错误比比皆是。而此时的译名统一工作依旧进展缓慢,直至1896年,在傅兰雅与潘慎文(A. P. Parker)负责工艺名词,狄考文与赫士负责科学名词,谢卫楼(D. Sheffield)负责人地名词的编译工作启动时,情况始略有进展。
惠特莫尔说,译名统一工作非常重要,因为科学史上的一些事件都可以通过译名来检索。译名之所以流传下来,是因为其重要和使用方便(Whitmore, 1955: 189)。但由于中国是科技落后的国家,几乎没有舶自西方的科学技术的对应表达,因而将西方科技术语转换成本国语言是非常艰难的。所以,译名统一是一项十分艰巨和复杂的工作。虽然徐寿、华衡芳等华人翻译家在译名创制方面做出过重要贡献,但此项工作主要还是由在华的西方传教士在推进。然而,这些传教士仅凭热情,却没有官方机构那种号召力与执行力,因而译名工作的推进依旧缓慢,译名混乱问题没有得到很大改善,以至于有读者投书《教务杂志》等刊物,批评译名乱象,如“Arabia”等词竟有三四个不同的译名。傅兰雅、李佳白(Gilbert Reid)、薛思培(J. A. Silsby)等西人传教士相继呼吁重视译名统一工作。在各方积极推动下,益智书会成立科学名词和人地名词两个委员会,从事科学、人名、地名等的译名统一工作。傅兰雅、狄考文、嘉约翰等负责科学名词,谢卫楼、施美志(G. B. Smyth)等负责人地名词的编译。
1896年5月,傅兰雅发表《中国科学术语展望》(The Present Outlook for Chinese Scientific Nomenclature)一文,再次呼吁重视译名统一,要求益智书会尽其所能编撰一部《中英译名字典》,新当选的出版委员会委员分工合作,每人负责一两个学科的译名。此外,他对自己在益智书会的译名统一工作做了扼要总结:
作为出版委员会成员之一,在时间和环境许可的范围内,我已完成分配给我的那部分工作,相信同事们的工作也完成得很好。我已收集现有的药物学、化学、矿物学、蒸汽机等学科的译名,分别编成各科的《中西名目表》,内容已相当完备,并由我个人出资出版发行。我还收集了地质学、植物学、地理学、生物学、造船学以及其他学科的译名,但尚未出版,因为我仅收集出版委员会认可的那些译名。现在展示给你们的那个样本,是一本又大又厚的植物学译名集。这样的译名表我还有六份。(Dagenais, 2010: 419)
傅兰雅在华期间,与他的中外同事合作编制了多个专业名词译名汇编,其中有些是为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编译,有些是按照益智书会的要求另行编译的,还有些是在翻译馆编译、以益智书会的名义出版的,现列举如下:《汽机中西名目表》《西药大成药品中西名目表》《金石中西名目表》《植物学词汇中西对照表》《化学术语中西名目表》《地质学术语表》《地理学名称中西名目表》《外国人名中文音译表》《专有名词中西对照表》《机械、物理术语中西对照表》等。
由于希望和家人团聚等原因,傅兰雅于1896年6月离开中国,前往美国加州大学任教。定居美国后,傅兰雅虽然也经常回到他念兹在兹,生活并工作了35年的中国,继续从事西书翻译等工作,但他已几乎告别了译名统一工作。
3 傅兰雅译名统一与标准化工作的成效、问题及成因分析
作为“那个时代最著名的学者之一和最杰出的翻译家”,傅兰雅以益智书会、江南制造局等为平台,做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工作,为近代国人形成世界意识,正确地认知世界、理解世界创造了条件。
1902年,在译名统一问题上常与傅兰雅意见相左的益智书会主席狄考文在致益智书会和中华博医会术语委员会的信中曾专门提及其译名的采用情况:
傅兰雅博士的化学书籍出版后,京师同文馆的毕利干教授也出版了一本化学书,所用译名是全新的,这表明毕利干和同文馆的顾问们对傅兰雅博士的译名是不满意的。最近,福开森先生以雅致的风格出版了一本化学书。他没有偏向任何人,而是采取折中的态度,遇到嘉约翰和傅兰雅不同的地方,采纳嘉约翰的有5次,傅兰雅9次,有2次谁的译名都不采用,只用毕利干的。聂会东博士(Dr. Neal)最近出版了一本初级分析化学,有10次采用傅兰雅的译名,3次采用嘉约翰的。(Dagenais, 2010: 444)
从狄考文提及的情况来看,傅兰雅的译名质量并非无可挑剔。但从福开森和聂会东两人采用的数据情况来看,傅氏译名的质量还是超过嘉约翰和毕利干的。必须指出,同文馆不采用傅兰雅,而采用本校教习毕利干的译名,并不能证明后者的质量一定比前者要好。福开森、聂会东应该不会有什么倾向性,他们更多地采用傅氏的译名,至少说明其质量不会差。
1899年,益智书会召开三年一次的年会,大会秘书薛思培在其报告中指出,大会要求潘慎文调查傅兰雅先前提及的该会出版的书籍被盗印一事,并通过英美驻华领事馆、混合法庭,采取罚没、征收罚金和损坏赔偿金等必要的行动。这一事实说明,盗版现象已相当严重,需要英美驻华领事馆等机构的介入。这一事件反衬出傅兰雅主持译介的书籍质量已为国人所认可,出现供不应求的情况。梁启超(2005:1161)曾批评毕利干翻译《化学阐原》,拒不采纳傅兰雅和徐寿合译的《化学鉴原》的译名,“乃不从其所定名”,以致“不可读”,间接肯定了傅、徐译名的质量。山西大学堂校长苏慧廉(Soothill,2011:142)说傅兰雅等人在翻译教育用书方面做了出色的开创性工作,这些书籍是未读过大学的中国学生唯一的知识来源。李三宝(Li, 1973: 771)指出:“十九世纪,西洋科学书籍中译本每因名词术语不统一而混乱不明,读者苦之。傅氏于1888年出版《译者手册》为科学名词之统一开先河。此手册且成为十九世纪末提倡科学者不可少之工具书。傅氏所译化学、医学、矿学等术语皆经缜密思考而成,至今仍多沿用。”更为重要的是,傅氏所从事的工作,标志着近代中国“术语汇编之发端”,其部分名目表开“双语科学字典汇编之先河”(夏晶,2011:65-67)。
然而,从清末译名统一工作的全局来看,傅兰雅及其团队所做的工作还存在差距。费正清(J. Fairbank)肯定这一时期出版了许多科学书籍,但也指出在译名创制方面存在不少问题。
20世纪中国人反对基督教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其要求与现代科学的结果不一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19世纪将西学引进中国的角色主要由新教传教士来充当。实际上,虽然新创制的中文词汇存在不少专业的问题,但新教徒出版的科学、数学书籍要比所有其他非教徒出版的书籍加起来的总和还要多。(Fairbank, 1980: 578)
毋庸置疑,费氏虽未明说,但同样直指所傅兰雅主持的益智书会。
译名问题的产生有多方面的原因:首先,译名问题与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状况存在关联。当时中国最大的西学翻译与传播机构——江南制造局翻译馆落户上海,为傅兰雅从事西书译介创造了千载难逢的机会。但由于自我封闭了几个世纪,除晚明清初耶稣会士引进少量的书籍以外,中国毫无西学基础可言,傅兰雅等人纯粹是白手起家,几无先例可循。其次,除傅兰雅、丁韪良等少数人以外,大多数西人对中国的语言文化、风俗习惯、政治制度等都不很了解,而他们中的大多数是传教士,传教是其主业,从事译事可谓勉为其难。即便是傅兰雅,对中国语言、文化的理解也未必能达到极致,其所翻译的绝大多数领域都是他所不熟悉的。而且,“他的外方同事也没有一个是精通科学的”(Wright,2000:239)他只能一边学习、一边翻译。再次,除了翻译,傅兰雅还有很多事情要做:主持格致书院的日常工作;为江南制造局翻译西方科学书籍;创办并编辑中国最早的科技期刊《格致汇编》以及经营格致书室等。此外,他还在广方言馆、操炮学堂等机构担任外文和西学的授课任务。
除了译名创制的难度、傅兰雅等人工作繁忙以及语言、文化等方面的障碍以外,益智书会成员之间的意见分歧,也导致了译名统一进程缓慢的局面。作为益智书会总编辑、执行委员会主席的傅兰雅与益智书会主席狄考文等人在译名统一的问题上常龃龉不断。其矛盾主要集中在化学及数学术语翻译、翻译方法及视角等问题上。例如,狄考文建议将geometry译为“形学”,将algebra、arithmetic译为“代数学”“数学”等。他还建议引进阿拉伯数字,并将数学书的书写方式由竖排改为横排。这一切都被傅兰雅否定。傅兰雅与嘉约翰在化学译名的问题上也存在分歧。虽然傅兰雅于1896年6月离开中国,益智书会在狄考文主持下,译名统一工作出现一定转机,但成效依旧有限。直至此后随着一大批中国留学海外的知识分子归国,他们凭借熟练的外语以及较好的母语功底,逐渐成为译名统一工作的生力军。自19世纪末开始,盛宣怀筹设的南洋公学、刘坤一和张之洞合办的江楚编译局、作为京师同文馆后继的京师译学馆等官立译书机构以及译书交通公会等私立书社纷纷投入到统一译名的工作中去。1909年,清廷学部奏设编订名词馆,聘严复为总纂。从此,以西人主导的译名统一工作逐渐改由国人主导,西人最终淡出这一领域。
译名问题是一个多面镜,它所反映的是西学知识在近代中国传播的多个面向,既包括西学在中国传播的广度,也包括中国社会认知和接纳西学的深度,实非一蹴而就之事(1)清末民国的译名统一工作虽经傅兰雅、狄考文、徐寿、严复等中外学人长达六十余年的努力,但仍未达到理想的效果。1931年,国际联盟教育考察团来华考察,对中国教育的现状提出了批评,并指出“科学上之专有名词,应予确定……以中文确定科学上之专有名词,实为教育部应当提倡之一种最迫切之工作”(国联考察团,1986:221)。,需要无数人的艰苦尝试,傅兰雅即是先驱者之一。自1868年进入江南制造局担任首席翻译时便开始关注译名统一工作,特别是1877年益智书会成立后主持教科书编译,一直到1896年离开中国前往美国定居为止,在近20年的时间里,傅兰雅孜孜矻矻,殚精竭虑,多次呼吁重视译名建设,主持统一译名的工作,编订了多部内容涵盖多个学科的译名表,为中国科技译名规范化和现代化建设做出了贡献,也为后来由国人主导的译名统一工作打下了坚实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