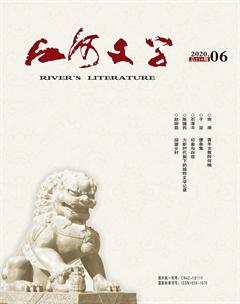印象与存在
石泽丰
竹木的风骨
准确地说,这是我第二次来花亭湖。第一次来,我只在湖边的凤凰山脚下远眺过湖面,没能上得山去。凤凰山上有寺,名曰西风禅寺。相传,西风禅寺因内有西风洞而得名,为唐朝的古刹,禅宗五祖弘忍大师道场,由法智禅师开山创寺,千百年来,灯传不绝。这次,我一定要上山去看看,不为礼佛,只为风景。我始终认为,人们对宗教的信仰,祈求菩萨的保佑,无非就是希望心中向往的事情早日实现。
上得山来,寺庙庄严,竹木立林。我与老查、老纪、老施一行登石级,折小径,一路看青松翠竹。这些竹子和树木,从石缝里长出,盘根错节,枝葉繁茂,须仰视才能看到顶梢。行走于此,像入了“野芳发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阴”之境。我是喜欢这样的环境的,仰头细看树梢和竹梢随风而动,风来摇摆,风休则静。由此,我想到“随缘”一词,不刻意,不强求。山石虽坚,但竹木可石缝生长,这也许是千百年来,寺庙之所以多依山而建,需兴竹木之林的缘故吧。
寺因僧侣而显神灵,僧侣因修行而受人尊敬。修行在山水间,就是悟山水之道。我想,西风禅寺也不例外,西风禅寺的僧侣也是如此。我边打量边思索,这些风餐露宿的竹木,活得十二分自在,把清贫作为一种美德和境界,作为自己从生到死的圆满通道,不需要额外的雨露,不需要刻意的养料,有土就好,随遇而安。许多人不明白其中的道理,求佛,佛背靠青山,不语,目光越过中门,直视眼前的竹木。
竹木的心,佛能读懂,竹木把自己与生俱来的个性摆在山间,从来不需要巧言令色和语言的装饰,长成自己的模样,哪怕是死也要站着死,不被环境左右。这就是一种刚正的气概,一种哲人的箴言,以身示范,不多言、不多语,缄默成风景。许多人很难做到这一点,原因就是缺乏向竹木叩问的悟心,看重的是花花世界,在乎的是七情六欲,歌自己的功,颂自己的德。
上次听一位朋友说,自己在工作岗位上任劳任怨,辛勤付出,成绩得到了外界的认同,却没有得到自家单位领导的赏识。我说,你不妨到山间去走走,看看那些竹木它们一辈子不挪窝,无欲中活出了一种境界。朋友听了我的话,游山归来之后,跟我说了六个字:它们堪为人师。从此,他变成了一个释怀的人,不随心换境,不为环境而悲欣交集。
这次,我们在凤凰山健步于台阶之上,不时用手机拍下美景。台阶有些潮湿,同游者说,这台阶是后来修建的,看得出来有仿古的痕迹,这未必不是败笔。旁边的一棵古树提醒了我。古树参天,枝叶繁茂,当地林业部门在树前立了一块牌子,上面标有树龄——约500年。由此,我想到人的自私,在很多的场合,一些人想急功近利,模仿时间的爪印,以显厚重。然他们自欺欺人的想法和做法,不时遭到古树的嘲笑,一棵古树历尽沧桑,活了数百年,什么事没有见过?这满山的翠竹和松树,本来就是厚重之笔,就是自然教人以法则的落笔之处。
早年,在一些山里,我看到不少的竹木毁于锯斧,剩下一截一截的桩子袒露在野外,我不免就心痛起来,有一种窒息的感觉。为一时之利一己之利,很多人忘记了竹木能护水土流失,能为人类提供氧气和绿荫,砍之伐之,最后换来一场场灾难。
在大自然的面前,人要警醒呐。
印象记
回到屋场,我总是要到左邻右舍去串串门,递上一根香烟,问候几句。话虽有些客套,但乡亲们并不以为然,觉得这“孩子”懂事,每次回来没忘记拜望乡亲。这次回乡,我当然不会例外。否则,乡亲们会在背后指着脊梁骨地议论,这“孩子”,在城里还没生活三天就不认得人了。言外之意就是说我有些吊儿郎当。面对这样的认定,我自然领受不起,所以我要求自己,回去之后,即使时间再紧,也要在屋场上转转,看看一些老人。
就在前几天回村,我看到几个老妇坐在灿颜婶家门口聊天,我便走了过去,递上香烟(尽管她们有的不抽烟,但也得要递),她们很是惊喜。无意间,腊珍大婶在我当面说:泽丰身体比以前养好了些,就是人老了不少。这是当下我在腊珍大婶心中的印象。一个近四十岁的人,容颜怎么能跟过去二十多岁时相比。老是人生的常态,不老,岁月才不肯放过你呢!我笑着说,我当初的孩子气没有了吧。
谈到我当初孩提时代,她们个个记忆犹新:调皮,倔强,不服管教……她们现场嬉笑着举出的例子,如被保存得尚好的茶叶,虽是一些陈年旧事,但依旧新鲜无比。为了要吃到小叔家招待客人的唯一一碗红烧肉,年幼的我不顾羞耻地赤裸着全身,在室外的泥泞地上打滚,逼着母亲红着脸去讨要……这些于我,并没有多少记忆,我只记得我当初非常惧怕一个人,那就是屋场上的老木匠强中太公。这次本想去看望他一回,婶娘们却说,他在多年前去世了。
强中太公有一把锋利的斧头,它有着雪白的刃口,厚实的斧背,再加上他那双壮实的臂膀,每每在伐树之时,只见木屑飞溅,树应声倒下。斧刃钝了,强中太公便捋起袖子,将斧头在月牙般的磨刀石上磨砺开来,并不时地用大拇指横刮刃口,试其锋利。斧口磨好了,他便用一块旧抹布将斧头抹干净,或继续作业,或收拾进工具箱。我惧怕他,就是怕他那把斧头。每每在我倔强调皮到不可收拾的时候,应父母之请,他便拿着这把斧头走了过来,说是要割我裆下之物。我看到斧头在他手上,上下舞动着,有一股难以控制的架势,我便惊慌地撒腿就跑,生怕那斧头一不小心真的伤到了我。那时,我虽不知道裆下之物对我有着多大的使用价值,但那种利刃割肉的疼痛,让人可想而知。
在我“无法无天”的童年里,我被强中太公征服了,我乖乖地听他的话,就像人一出生,就得乖乖地按照上帝的要求,匀速地朝着终点奔跑,老木匠强中太公也是。
渐渐地,我长大了,在我心中,那把斧子已不再成为威胁之物,但强中太公的斧子、凿子、锯子、锛子、刨子、角尺、墨斗……却依旧堆在了我的记忆里。这些营生的家当,强中太公让他一茬又一茬的徒弟们挑过,最终还是他自己,接过来,歇在了自个家中。记得那一天,他从工具箱里取出所有的工具,将它们磨锋利时,我好奇地问,太公,为什么将它们全部重新磨一遍呀?强中太公说,我要给自己造房子。说完,我看到一颗苍老的泪滴从他眼睑滚落。事后我才知道,那房子是他在另一个世界的归宿,人们叫它棺材。莫非他早就知道,总有一天,他会被时间伐倒?那是一定的。
没有送出的那句英语
那是我上初中时刚接触英语的日子。
新学期开始只有一个多星期,便到了教师节。开学第一周,我们见到了所有教我们课的老师,他们上第一堂课,都是先作自我介绍,然后,按点名册的顺序一一点我们的名字,让我们次第站起来,算是相互之间熟悉一下。但英语老师没有这样做。
我很清楚地记得,英语老师姓祝,近三十岁。她带着甜甜的微笑走进我们的教室,刚一踏上讲台,随口说出一句:good morning,class!当时,连26个字母都不会读的我们,面对这样一句问候语,如听天书。随后,她并没有介绍自己,也没有点我们的名字,而是用一种征求的口吻对我们说:“我们暂时不作相互了解吧!如果以后大家学好了英语,算是我们之間有缘分,到那时,我们再了解对方也不迟……”面对这样的开场白,我像一个好吃的孩子一下子被一颗甜糖粘住了自己幼小的心灵。
教师节将至,我真想送她一样东西,最后得到一位师兄的点拨:就送她一句英语吧——“Happy TeachersDay!”待我弄清这句英语的意思之后,我觉得这真是一件最好的礼物。于是,我在心里预演着,一遍、两遍、几十遍……我梦见了那一瞬间的情景:她走进教室,在将要打开书本之时,我举手站了起来,脸一下滚烫,大声地说了一句:“Happy TeachersDay!”顿时,教室里响起了掌声,她微笑着频频向我们点头,眼睛有些湿润,然后走到我的身边,问起了我的名字。
我想我的这一举动会在她的教学生涯中添上一笔。于是,我天天盼,好不容易盼到了教师节,那天上英语课之前,我早早地坐在自己的座位上,静静地等待着,像是在等一张我多年梦寐以求的奖状。上课铃终于响了,同学们像以往一样雀跃着跑进教室,这一刻,谁也不知道我心里暗藏着一朵芬芳的“鲜花”,我将要把它送给我的祝老师。等待中,时间一秒一秒地过去了,祝老师还没有来到教室,我想她大概也是在为我们准备着什么吧。可我等了十几分钟,最后,走进来的是我们的班主任,他告诉我们,祝老师今天到县城去参加考试了,叫我们大家自习,那一刻,我的眼泪一下子涌出来。
三个月后,因为被更绚丽的未来召唤,她悄悄离开了我们,到县城一中去任教了。我记得她给我们上最后一堂课时,没有带上自己的教本,在例行的问好之后,她笑着说:“我们相处有三个月了,三个月来,我发现我们都是有缘分的,今天这堂课我们有必要相互作个了解。”然后,她生动幽默地开始介绍自己。可万万没有想到,这一堂课,竟是她教我们的最后一堂课。
祝老师走了,她带着三个月来我们曾经相处过的画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