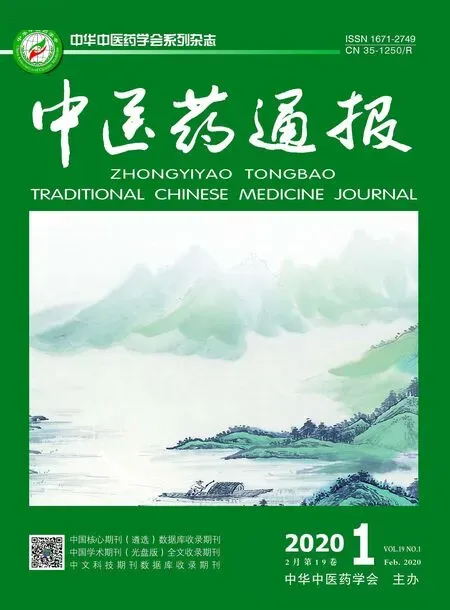中医学兴衰的史学探源
——在中华医学会医史学分会第十五届三次学术年会上的发言
●李致重
中医学(即中医药学)是世界传统医学中基础理论体系最完整,临床辨证论治技术体系最成熟,医疗疗效最可靠、最卓著的传统医学,也是世界上可以与主流的西医学(即现代医学)相匹配的传统医学。两千多年以来,中医学对中华民族的繁衍昌盛做出了令人瞩目的突出贡献。然而在当代的生存、发展中,却因长期的被改造、被西化而伤痕累累。尽管以往在中医学编年史、断代史研究上有不少成果,但是对产生中医学的文化底蕴却研究甚少。当今的中国正迈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时代。民族复兴以文化复兴为依托,文化复兴以民族复兴为动力。从源头上研究产生中医学的历史与文化背景,将可能焕发出推动中医学传承、创新的内在动力。
弗朗西斯·培根曾经说过:“史鉴使人明智”。一个学科形成和延续的历史越久远,孕育这一学科的历史研究便越重要。明辨“中医学我是谁”和“我是怎么来的”,无疑是当代中医学史学研究首要的课题。为此这里谈一些个人的看法,衷心希望与会同仁们批评指正。
1 无定义和西医化的当代中医学
在数以千百计的人类哲学、科学之林里,每一门具体的学科都有自己的定义,唯独中医学是一个例外。按照通行的逻辑学原则,学科定义一般是由一个判断句来完成的。在这一个判断句里,包括被定义项、定义联项、定义项三个要素。比如,“中医学”三字属于被定义项;“是”字属于定义联项;需要揭示的中医学的本质特点与属性,属于“定义项”。定义项中的本质特点与属性,指的是该学科的研究对象及方法。其中研究对象,尤其不可或缺。而且在定义项只能用名词来表达,是不允许使用形容词的。
长期流行于书面的类似中医学定义的说法大体有四种:“中医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中医学是我国劳动人民长期与疾病作斗争的经验结晶”;“中医学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瑰宝”;“中医药发源于我国,是中国各族人民几千年在同疾病作斗争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是人民群众集体智慧的结晶”。而流行于人们口头上的,以形容词称谓中医学的习惯性说法则更多。诸如“独特”“瑰宝”“宝库”“结 晶”“特 色”“优 势”“特 点”“规律”“精髓”,还有“深厚科学内涵”“宝贵财富”“原生态的”等等。以上这些说法都是正确的、积极的,但是在学术上并不能视为中医学的学科定义。
中医学基础理论体系中的藏象经络、四诊合参、病因病机、治疗原则、方剂组合、中药针灸这六大范畴当然是瑰宝,而在中医学基础理论体系成熟之前的一方一药,一针一艾,以及民间流行的一己一时之经验,也常常被人们称之为瑰宝。然而,基础理论体系与一己一时之经验,是有巨大差别的。诊疗技术以及一己一时之经验,不能脱离基础理论的指导,更不能与基础理论体系相提并论。在中医学定义明确之前,指意不清的“瑰宝”之说极可能造成学术发展方向的莫衷一是,令中医学陷于“守财奴困死在珠宝洞”的窘境。首先厘正“中医学我是谁”“我是怎么来的”这两个核心学术难题,才会使中医学跨越生存与发展窘境,把握好传承、创新的方向罗盘。
中医学西医化,是困扰中医学传承、发展、创新的另一个大难题。长期以来,我们把创造新医学、新药学的愿望;把临床上的中西药混合杂投;把西医学的还原性研究方法用于对中医学的验证、解释、改造;把西药常用的提取方法用于从中药材里提取有效成份的研究;把中医教育上中、西医课程双管齐下的做法;把管理西医的法规用于中医药事业的管理;把懂得西医也懂得一点中医的人员等等,统统美其名曰“中西医结合”[1]。这种一个“结合”,多种解读,连续多年,不加反思的问题,是国内外学术界极其罕见的一大怪现象。
尤其离奇的是,在至今没有准确回答“中医学我是谁”“我是怎么来的”前提下,从1982 年起“中西结合医学科”已经被确定为我国“一级学科之一”。接着于“1992年11月1日,又将‘中西医结合医学’作为一个新学科列入国家技术监督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GB)·学科分类代码》。该标准于次年1 月1 日起正式实施,标志着‘中西医结合医学’(代码为360.30)已经成为我国一门独立的学科”[2]。
这里之所以用“离奇”二字,一方面因为中西医结合医学是在中医的学科定位未完成的前提下产生出来的。由于失去了“结合”的先决条件,自然不可能成为一个名符其实的“独立的学科”。另一方面,三十多年来中西结合医学并未形成不同于中医学与西医学的概念(范畴)体系,即独立的基础理论系统。至今基础理论是一个空白这一条,即决定了中西结合医学绝对承受不起“独立的”“一级学科”的地位的。第三,开办近二十年的中西结合医学专业的课程里,没有中西结合医学专业基础课程;其临床教材全是从中医学与西医学的教材中剪贴、拼凑而来的。至于中西结合医学研究生的专业课与毕业论文,几乎是与中医学不靠边的西医实验研究的内容。这当然不能称之为中医学创新。至于今后何去何从,其实早已是燃眉之中事。
当今的中医学,已经被学术界几十年的云谲波诡,涂改得面目全非了。网上有人说:中医学是近代中国科学领域里输得最惨的一门学科。这句话听起来令人不舒服,仔细想却觉得并没有错。六十多年来国家为推动中医的发展,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却因为没有重视中医学科学定位的研究和中西医结合的捆绑而举步维艰。面对用无数人、物、财而换来的当代中医学的衰落,这是我们今天所在的新时代必须深刻反思的天字第一号的重大学术问题。
2 两次文化高峰和两种医学的回顾
发展是历史的,也是现代的,归根结底是内在于传统的历史性演进。一个学科存在的越久,它的历史越值得人们牢记,越值得人们研究。从常理上讲,科学所揭示的规律是超时空而存在的,纵横四海,历久弥新。忘记了它的历史及其内在的科学规律,就意味着衰落的开始,意味着历史的倒退。成熟于春秋秦汉之际并在中华民族繁衍昌盛中做出卓越贡献的中医学,当然也是这样。怀着这样的信念,笔者从1980 年以来一直醉心于中医科学学、软科学的研究。研究的重点,始终集中在中医学的学科定位以及中医西化的深层思考上。
近年来,笔者在诸多论文和已出版的《丘石中医系列》专著里,遵循《周易》“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的论断,多次提到人类文明进步中“两次文化高峰”的见解。
第一次文化高峰出现于春秋秦汉之际;第二次文化高峰在欧洲文艺复兴以来。
第一次文化高峰以哲学的成熟为代表;第二次文化高峰以物理学、化学的成熟为代表。
哲学的价值在于认识世界,提升智慧,安排人生,充实人类的精神生活;物理学、化学的价值在于改造世界,获取材料,制造器具,丰富和繁荣人类的物质生活。
把古今中外哲学体系下的科学和近代物理学、化学体系下的科学,统一纳入人类科学体系的立场与观念,称之为大科学观。
基于以上见解,中医学研究的是形上性的证候(象、现象)变化之人,西医学研究的是形下性的结构、功能人;中医学运用了由综合到演绎的逻辑思维方法,西医学运用了由分析到归纳的实证实验方法;中医学是哲学体系下的医学科学,西医学是近代物理学、化学体系下的医学科学。
为了加深对上述见解的理解,《浙江中医药大学学报》于2006 年第6 期发表了笔者《中西医之间的公理性原则和人类医学革命》[3]一文。接着香港《明报月刊》于2007年第8 期以《中西医之间的公理性原则》[4]为题,摘要介绍了上文的部分观点。这里谨从其中摘录“自明就是公理性”一节,原文如下。
按照亚里斯多德、阿奎纳的哲学思想:自明的,即无须证明的;而无须证明的,就是公理性的。台湾著名的哲学家罗光先生也说:“公理应该具有普遍和永久的真实性,因为出自人性和自然界的自然律;公理的成立或存在,不是由人的推理证明,而是由于学术思想的先天程序,必然而有的”。所以在中国乃至世界上,对于中西医学术发展和事业管理而言,以下五条原则的公理性,毋庸置疑。
第一,《易经》关于“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的论断,是人类科学史上最早、最准确的科学分类的公理性标准。因为人们所观察到的客观世界,不是事物的运动过程,就是物质的形态结构;不是事物运动的时间特征,就是物质结构的空间特征。从古到今,仅此而已。因此,第一条公理性原则是:只要地球不毁灭,万事万物呈现在人们面前的形上与形下两类研究(认识)对象,将不会改变;人们研究(认识)万事万物而产生的形上与形下两类科学的总体格局,也将不会改变。
第二,人是天地万物之灵,与天、地并列为“三才”;天、地是极其复杂的,人也是极其复杂的。天地万物分为形上与形下两大类,人则具有形上与形下二重性。而且在天地万物中,人的二重性是最全面、最突出、最典型的。因此,第二条公理性原则是:只要地球不毁灭,只要人类尚存在,人的形上与形下二重性必将不会改变;人类医学上形上与形下两种科学体系的格局,也将不会改变。
第三,中医学是以综合(系统)性方法研究人的形上(亦即亚里斯多德所指的“原形”)属性而形成的医学科学体系;西医的生物医学是以分析(还原)性方法研究人的形下(亦即亚里斯多德所指的“原质”)属性而形成的医学科学体系。因此,面对中医走向世界和人类医学未来的发展,第三条公理性原则是:“人的形上与形下二重性”、亚里斯多德的“原形”与“原质”原理、“综合与分析”两类研究方法——只要是此三者任何一者所包含的两个方面,都不可能合二为一。由此医学中并存的中医与西医两者,则在地球毁灭之前不可能合二为一。
第四,形上与形下两种医学在科学层面上的差异,是各自的本质特长,也包括各自不可避免的局限。彼此的特长和局限,也反映在各自的临床技术与临床经验层面上。因此,第四条公理性原则是:面对各有特长和局限的中医与西医,两者只能是不同医学资源在临床应用层面的“中西医配合”。这种“配合”,不同于将两种医学“合二为一”的“中西医结合”,而且这种不同医学资源在临床应用层面的“配合”,必将是长期的,甚至是永远的。
第五,当代生命科学和医学科学上的最大偏见和失误有三:其一,企图把复杂的、活着的、具有形上与形下二重性的人,与人所制造的、简单的、非生命的、形下性的机器相混淆。其二,企图把复杂的具有形上与形下二重性的人的生命过程,统统归结为物理学、化学的现象来解释。其三,企图把以物理学、化学所代表的分析(还原)性的科学观念与方法,作为实现“中医现代化”“中西医结合”的至上信条和唯一标准。而按照亚里斯多德的哲学思想,这些观念与方法原本是用来解释“原质”的,用于解释非生命领域的。依据以上公理性原则,这里需要重申第五条公理性原则:只要今后人类仍然不能用物理学、化学的方法合成或者制造出生命,西医就不可能解释生命科学领域的全部课题;只要西医不可能离开物理学、化学的观念和方法,它就无法克服自身的局限;只要西医存在一天,中医的独立存在不仅是合理的,更是必须的。
当代中医的全面衰落不仅是学术问题,也是社会问题和管理问题。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是:医治国人的传统文化自卑症,重树中医学的科学信念;尊重中医学的原理和特点,营造“和而不同”的学术氛围;保护学术民主、学术自由,倡导学术争鸣,以推动中医的复兴;遵照《宪法》“发展现代医药和中国传统医药”的规定,革除中医学术与事业中形形色色违背科学和宪法的行为。
2014年,《中华中医药杂志》第2 期发表了笔者的《中医西化违背哲学公理》[5]一文。该文将界定中西医关系的公理性原则,进一步由上而下地总结为以下十条:两次文化高峰、两类研究对象、两种研究方向、两类带头学科、两类科学体系、形而上与形而下二重性的人、医学研究的两类方法、两种医学的界定、两种医学的概念范畴体、两种医学的不可通约性。第一次将当代流行的中医西医化,定性为一种违背哲学公理的重大学术性错误。
该文发表之后,引起了不少人的关注。为此,围绕界定中西医关系的上述十条公理性原则,在香港及境外一批学生中展开了深入的讨论,笔者并进行了详细的答疑。后来将《中医西化违背哲学公理》一文以及当年的讨论与答疑进行了文字整理,一并列入《正医》一书的第一章,即“告别中医西化的师生讨论”。
3 春秋秦汉时的哲学是中医学之母
80 年代笔者初读“古希腊三哲”以及《西方哲学史》《科学史》时,总有一种感觉在心头:欧洲人把历史文明视为永久的财富,我们却把历史文明视为落后的根源。一百多年来的传统文化自虐、自残,使中华民族患上了传统文化自卑症。在造成传统哲学贫困的同时,也形成了群体性逻辑思维能力的下降。中医学的兴衰存亡史,关联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史,关联着引领文化传承发展的哲学史、科学史。正在围绕着我们的时代性科学观残缺不全的现象,也与这一段历史直接相关。
按照当代辞书关于科学的定义,“科学是关于自然、社会、思维的科学体系”。这里所讲的科学,除了物理学、化学体系里的近代自然科学之外,从属于哲学体系的社会科学、思维科学和近代自然科学之外的其它自然科学,也在这一定义的囊括之中。可见当代辞书定义的科学,是包括物理学、化学体系的科学和哲学体系的科学在内的广义科学。而且从历史的角度上讲,哲学更应当是科学的科学。为什么至今一些人仍然要把哲学体系下的中医学排斥于科学的大门之外呢?为什么至今仍然固执地用近代物理学、化学的观念与方法对中医进行验证、解释、改造、排斥呢?为什么至今还要将这种错误的做法称之为推动中医科学化、现代化呢?因为持这种立场的人深深地陷入近代科学主义的思潮,也由于陷得太深太深,至今几乎难以自拔。
由此可见,人们要真正从源头上认识中医学,必须在中国传统哲学上下一番功夫。中国文明史上的经书都源自于春秋秦汉时期,《黄帝内经》则成书于以上经书之后。要想从源头上认识中医学,就应当回到春秋秦汉时代,重温人类第一次文化高峰时代的中国传统哲学。
清代的《四库全书》按照经、史、子、集的分类原则,把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典籍尽收其中。其中的经部书,即习惯上所说的十三经。包括诗、书、礼、易、春秋、左传、公羊传、谷梁传、礼记、孝经、论语、孟子、尔雅。除尔雅是解释词意的专书之外,其它的十二经皆是春秋秦汉时期中华民族在哲学,以及与哲学直接相关的人文、历史方面的经典名著。
《四库全书》里的子部书,主要包括了人文、历史方面,哲学以及与哲学直接相关的名著,也在其中。哲学方面的名著有老子、公孙龙子、韩非子、墨子、荀子、庄子以及周易参同契、鬼谷子等。另外,还有佛家的心经、金刚经、六祖坛经。由哲学孕育的中医学第一部经典名著《黄帝内经素问》,也在子部之中。
后世流传的四书五经,是在十三经的基础上集要、补充而来的。四书包括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五经包括诗、书、易、礼、春秋。其中的大学、中庸,是揭示哲学认识论的名篇。以“格物致中”“致中和”为代表的内容,当属中国哲学认识论的基本理论范畴。随着十三经和四书五经在中国广泛深入的传播,历史将《周易》推到了“群经之首”的地位。两千多年来,《周易》一直主导着中国的自然、社会、思维领域,带领着中国传统人文、历史的进步与发展。
西汉的司马父子将之前的哲学家分为道家、儒家、名家、墨家、阴阳家、法家如此六家。这里参考西方哲学体系结构的原则来讲,道家主要讲的是哲学中的自然伦理,儒家主要讲的是哲学中的社会伦理。前面提到的佛家,主要讲的是的是哲学中的生命伦理。中国哲学里的名家,当属哲学中的知识论、逻辑学部分。公孙龙子、墨子、庄子、荀子等人的专著里,都有不少逻辑方面论述。而中国传统哲学的集大成者,当然非《周易》莫属。
《周易》包括《易经》与《易传》两部分。《易经》貌似占筮,实则是先民思维智慧的产物,是中国哲学中的知识论和思维逻辑的结晶。如果排除人们的无知和唯心论的偏见,我们的先祖借揲耆成爻,从无极中看到了两仪、四象、八卦;继而从八卦、六十四卦的数学平方式的拓展中,揭示了天地事物变化的哲学原理;倘若再从六十四卦的数学平方式拓展出4096 变,天地间万事万物无穷之变,那一变都尽在人们思维的网络之中。如果将这些知识论、思维逻辑和哲学原理与儒家的“格物致知”,与道家的“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与佛家的“有无相生”“色不异空、空不异色”相比,《易经》从“易有太极,是生两仪”而展现的知识论、思维逻辑和哲学原理,则更准确,更彻底。尤其两仪之间“阳主阴从”“生生之谓易”的运动变化的原则,更突显出万事万物自我发生、发展的内在动力。如果将《周易》运动变化的原则与亚里斯多德的《第一哲学》(亦即《形而上学》《后物理学》)相比,可以说中国人在知识论、思维逻辑和哲学原理方面的成熟,可以与亚氏的《第一哲学》相比肩。这里举例说明如下。
比如,两仪、四象、八卦、六十四卦的本身,就是“第一原理”(同一律、排中律、不矛盾律)和“真、善、美”原理的体现。
又如,“阳主阴从”的运动变化,与《第一哲学》中“现实与潜能”“原形与原质”“存在与本质”的原理完全一致。而且这些原理在《黄帝内经》中无处不在。诸如“阴静阳动,阳生阴长,阳杀阴藏,阳化气、阴成形”;“阳气者若天与日,失其所则折寿而不彰”;“阴在内、阳之守也,阳在外,阴之使也”等等,皆是《第一哲学》上述原理的体现。
再如,莱布尼兹发明的数学二进制,里.查德发明的模糊数学,艾什比提出的信息论,贝塔朗菲提出的系统论,这些近代新兴科学的智慧之源,早已在《易经》的知识论、思维逻辑和哲学原理之中。
《易传》是孔子或者孔子的学生对《易经》哲学思想的诠释和发挥。它同样是中国哲学体系的代表性经典。《周易知识通览》一书从《易传》中列举出20 个范畴和命题[6],这就是:彰往而察来,三材之道,刚柔相推而生变化,位、中、时,消息盈虚,变通,太和,乾元和坤元,天行健、地势坤,天地絪缊,天地之数,生生之谓易,神无方而易无体,几者动之微,立象以尽意,一阴一阳之谓道,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太极、两仪、四象,穷理尽性以至于命,易与天地则。以上这些范畴和命题,充分表明中国哲学在那时候已经达到了成熟的水平,而挺身于人类文明的前列。
这里可以肯定地说,中医学的基本哲学思想源于《周易》,中医学中的许多词、术语也彰显着《周易》的光辉。诸如中医理论中的木、火、土、金、水五行,风、寒、暑、湿、燥、火六气,寒、热、虚、实、表、里、阴、阳八纲、望、闻、问、切四诊;方剂中的大、小、缓、急、奇、偶、复七方,汗、吐、下、和、温、清、消、补八阵,宣、通、补、泄、轻、重、滑、涩、燥、湿十剂;药物中的升、降、浮、沉四性,酸、苦、甘、辛、咸五味等等。正如唐代大医孙思邈所说:“不知易,不足以言大医”;明代大医张景岳也说:“《易》者易也,具阴阳动静之妙;医者意也,合阴阳消长之机”。无奈的是今人不学易,于是耳不聪、目不明、心不思、智不开。以致寄身于中医西医化的歧途不思回头,岂能不令人伤悲嘛!
通过以上三方面讨论,从中西医两者的本质特点上讲:中医学与西医学的区别不是东方与西方的问题,不是传统与现代的问题,不是非主流与主流的问题,不是宏观与微观的问题,不是实践与实验的问题,不是主观与客观的问题,不是经验与科学的问题,不是落后与先进的问题,更不是不科学与科学的问题。中医学与西医学的根本区别,是由各自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的不同而决定的。站在历史的维度来看人类医学的发展,那么中医学与西医学两者之间并存并重、共同繁荣的格局,必将古在、今在、往后仍在。用前面的一个说法,“只要地球不毁灭,只要人类尚存在”,人类医学的总体格局只能是“中西医并重”。
讨论中医学兴衰的史学探源,我总在想:丢掉了传统便不会有任何发展,欲求发展则一定要洞悉传统,忘记,就意味着背叛。
一百多年对优秀传统文化的自虐和自残,对传统哲学和中医学的横扫和冷落,相信都将成为过去。习近平主席多次讲到:“中医药是中华文明的一个瑰宝,凝聚着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博大智慧”。今年10 月25 日召开的全国中医大会之际,他又特别强调:“要遵循中医药规律,传承精华,守正创新”[7]。遵循就是守正,传承重在规律。只要守正,中医学的规律、精华才会再现。期盼已久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时代,是文化回归传统,回头是路的时候了。今天的中医人应当懂得,实现中医学的复兴,首先要复兴中华民族的大智慧。而这种大智慧,就蕴藏在中华民族传统的哲学经典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