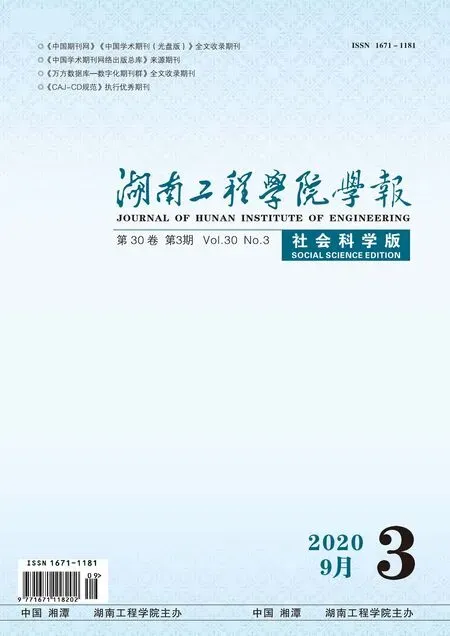通过环境共治走向生态文明
曾 哲,李 轩
(西南政法大学 行政法学院,重庆401120)
一 日臻完善:中国环境宪法规范体系
2018 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以下简称《宪法修正案》)于2018 年3 月11 日举行的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该修正案的一大关注点是扩充了有关生态环境的条款,新修订的条款与原本的条款共同构成了环境宪法规范体系的基本框架。①
(一)修改前的环境宪法规范体系
2018 年的《宪法修正案》通过前,环境宪法的规范体系较为零散、单一,内容包括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珍贵动物和植物的保护、土地的合理利用、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的保护和改善、污染防治和植树造林等方面。此外,有不少学者认为宪法中的人权条款亦可作为环境宪法的构成部分。[1]
修宪前的环境宪法规范全部分布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下简称《宪法》)的总纲部分,分别为第九条第二款、第十条第五款和第二十六条。宪法总纲对于整个宪法框架具有提纲挈领的作用,一般规定了我国的国体、政体、国家结构形式以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外交和军事等各项基本制度。[2]修改前的环境宪法规范可以看作是我们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的基本制度。基本制度可以理解为国家积极进入社会生活的许可证,构成了现代宪法的基本内容。基本制度是“国家发展的指南”,是宪法中国家机构条款和人权条款外的“第三种规范”。[3]值得注意的是,《宪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国家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是综合性的统领其他环保基本制度的国家目标条款,但也仅赋予国家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保护的职责与义务,并没有过多的重视生态环境保护;而其他条款则是其他个别环保领域的国家基本政策,仅仅规定某一局部,并不能涵盖所有的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内容。
(二)2018 年的《宪法修正案》对环境宪法规范的完善
2018 年的《宪法修正案》新增了三条有关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的规范,完善了我国环境宪法的规范体系,分别是:(1)《宪法修正案》第三十二条将生态文明建设提升到与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建设相同的高度;(2)《宪法修正案》第三十二条新增“美丽”作为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3)《宪法修正案》第四十六条赋予了国务院领导和管理生态文明建设的职权。此次宪法修改,分别在序言部分和国家机构部分增加环境宪法规范的规定,内容虽少,却极大地充实了环境宪法规范体系,也使得我国环境法治紧紧围绕环境宪法为根基去构建。
在宪法序言中引入“生态文明”的新观念,使之统筹环境宪法规范体系,解决了生态文明建设这一顶层设计与宪法规范之间的衔接问题。[4]我国宪法序言是有效力的,并且效力高于总纲的效力。基于此,“生态文明”规定在宪法序言中,弥补了环境宪法规范缺乏纲领性条款引领的缺陷,亦更加突出建设生态文明的重要性。因此,“生态文明”条款这样具有根本性、价值宣示性的条款不能在宪法序言中缺席,因为生态文明建设已经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国家存续发展、个人福祉保障存在重大关联。并且,此次宪法修改,将“生态文明”提升到与“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相同的高度,是对我国此前“重发展、轻环保”错误思想的纠正,将环保与发展并重,标志着我国对发展与环境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5]体现了深邃的政治智慧和战略思维。
在宪法序言中新增“美丽”作为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亦是作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总目标。“美丽”一词虽然简朴,蕴意却非常丰富。“美丽中国”,不仅是我们环境保护和建设生态文明的总目标,是我们对青山绿水、蓝天白云、江河安澜的自然风光的希冀,也是我们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方面的要求。“小康全面不全面,生态环境质量是关键”[6]。而在国家机构的国务院的职权中加入“领导和管理生态文明建设”,并非多余。国务院作为国家最高行政机关,自然而然地享有领导和管理生态文明建设的职权。此次宪法修改的意义,更多的是强调和突出的作用,将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工作和城乡建设并重,表明了政府治理环境和对污染的防治决心,也是对过去政府“唯GDP”论的深刻反思,也认识到了经济与生态应该作为发展的两条并行的主线。
(三)环境宪法规范的价值蕴含
通过对上述规范的分析,可以将环境条款分为三种类型。一是国家目标类,《宪法修正案》第三十二条修订的推动生态文明协调发展,把我国建设成为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便是我国宪法在环境保护方面给国家设定的总的目标。将生态文明发展提升到与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和社会文明建设相同的高度,体现了我国在环境保护和生态环境问题认识上的深化,同时也为我国环保的立法、执法和司法提供了最高的价值目标。二是国家义务类,如《宪法》第九条第二款、第十条第五款和第二十六条分别从自然资源的利用、珍贵动物植物的保护、土地的利用、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的改善和保护等方面,赋予国家特定的义务。这一部分均在宪法文本的总纲部分规定,宪法总纲具有极强的规范性和纲领性,通常以基本国策或者国家目标为其表现形式。国家为了达致该目标,必须通过特定国家行为,此即为国家义务。三是国务院职责类,《宪法修正案》第四十六条新增了领导和管理生态文明建设作为国务院职权之一,形成了生态文明建设的宪法规范体系的一个闭环,使得国务院为最高行政机关更积极、有效地履行领导和管理生态文明职权提供了宪法规范上的依据。
至此,我国形成了以“建成美丽中国”为目标,以“生态文明建设”为顶层设计的完整的环境宪法规范体系。环境宪法的规范效力得到进一步加强,我国环境法治也得到了宪法层面的规范根基。
二 殊途同归:“生态文明”与“环境权”条款
在2018 年的《宪法修正案》通过前,我国环境宪法规范体系缺乏统筹规范的条款。此时有两种路径选择:一是规定“生态文明”作为最高的价值宣示;二是在我国基本权利体系中加入环境权。最终的政治抉择是选择了第一种方案,将“生态文明”规定在宪法序言中作为最高价值宣示。虽然宪法没有直接明确地规定我国公民享有“环境权”,这与我国宪法学者呼吁多年的“环境权入宪”,将环境保护作为公民基本权利的规范建构的主张,有一定的出入。[7]但是,通过对宪法中环境宪法规范的解构和体系解释,可以得出“生态文明”与“环境权”在价值、功能上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均是对国家义务提出相应的要求。以上条款通过有机结合,作为我国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以及公民环境权的根本规范,如何将他们之间的关系梳理清楚,通过宪法释义的方法,将宪法规范上升为规范宪法,成为对环境宪法研究的重点。
(一)环境权的缘起
环境权的缘起,最初是从人权理念推导而来的,认为环境权应当属于人权所应涵盖的部分,进而构建环境权体系。而环境权在我国成为一个“问题”被讨论,最早可追溯到武汉大学凌相权教授1981 年发表的《公民应当享有环境权——关于环境、法律、公民权问题探讨》,这是我国第一篇专门研究公民环境权的论文。凌相权教授亦是从人权的角度出发,并认为环境权是其他基本权利实现的基础性权利,并从完善人权的角度出发,建议在1982 年即将进行的宪法修改中确认和加入环境权。[8]紧接着,同样任职于武汉大学的蔡守秋教授于1982 年发表了《环境权初探》,这是一篇对于环境权理论在我国扎根具有重要推进作用的文章。作者通过对美国、欧盟、日本、泰国和伊朗等国家对环境权的保护理论和实践,得出了完善一国的环境保护法律体系的核心在于确认环境权作为公民基本权利的结论,并且认为这也是世界各国环境宪法发展的必然趋势。[9]随着环境权的意义不断被挖掘,越来越多的学者重视环境权的研究,甚至有学者认为“环境权入宪将是生态文明建设的最高制度表达”[10]。
环境权对于维护公民的环境利益、建立政府环境责任制度和发展环境公益诉讼有着重要意义和作用。[11]赋予公民环境权,可以调动公民参与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的积极性。现代社会越来越强调公民在国家事务中的作用,同样,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亦不能由政府包办。对于公民来说,权利意味着利益和收益,赋予公民环境权,意味着公民享有与环境相关的权益和利益,满足公民对舒适环境的向往,提升公民的环境幸福感,从而促进公民参与生态文明建设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公民环境权是公民生而为人之生存所必需的、基本的、不可剥夺的权利,虽然公民环境权直到现在才越来越被重视,这是因环境恶化以及人权观念的深化而引起的。
(二)环境权的独特性质
与传统的基本权利不同,环境权作为新兴权利,有着自己独特的性质,具体表现在:
1.公益性。人类居住在同一个地球上,分享同一片天空,呼吸同样的空气。环境保护,是关涉到每一个人的事情,从大的范围上讲,亦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事情。其他的基本权利都只关系到个人的权益,而环境权则是关涉一个地区、一个国家甚至整个地球公民的权益。因此,环境权天然的与其他基本权利不同,具有公益性的属性。公众的环境权与国家环境行政权都是为了维护公共环境利益,公益性是其显著的特征,这也是公众环境权与公民其他民事权利区别的标志。[12]正确理解环境权的公益性特征,从而建立以政府和公众共同参与的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模式,有利于将我国现行的“环保靠政府、轻公众”的管理模式转变为“政府主导和公众参与相结合”的合作模式,从这个角度出发,有利于实现全体国民的环境正义。②[13]
2.人权性。环境问题是伴随着经济发展、人口数量成爆发式增长问题而产生的,在当今世界,大气、土壤、水源以及粮食等人类生活的各种不可或缺的资源正在受到不断的污染,生态平衡正在受到不断的破坏,长此以往,人类的生存必将受到威胁。有鉴于此,当今世界正在展开一场防止公害扩展、推进环境保护的世界性范围的运动。环境权正是在这场风起云涌的环境保护运动中所产生的一种新型的人权观念,并已经为现代宪法学所关注。
所谓环境权具有人权性,可以追溯到第三代人权中的环境权的概念,可见于1972 年6 月联合国召开的人类环境会议所通过的《人类环境宣言》。作为一种第三代人权③[14],指出人类有权生活在尊严和福利的生活环境中,同时指出享有该权利的人亦有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使得人类世世代代都能永续生存的庄严义务。但自《世界人权宣言》之后,环境权的保障并没有有效地纳入国际人权保障体系。[15]我国宪法中虽然没有正面规定作为公民基本权利的环境权,但从环境权所具有的为人之生存所必需的、基本的、不可剥夺的性质上来看,环境权可以认定为人权的一种表现形态。
(三)“生态文明”与“环境权”功能的同质性
环境权未被写入宪法,在理论上会出现:法律是以权利—义务为结构和内容的社会规范,宪法也是这样,宪法亦是由基本权利—国家义务为结构构建起来的,当环境权作为一种新兴的基本权利未规定在宪法内,那么相对应的国家义务又应做如何的解读,这是迄今环境宪法所面临的一个理论上的难题。
上述难题并不构成一个问题。无论是“生态文明”抑或是“环境权”被写进宪法,都发挥着同样的作用——赋予相关国家机关一定的义务。通过相关国家义务的履行,“生态文明”或者“环境权”方能实现。首先,学者呼吁“环境权入宪”,将环境权规定在宪法中成为基本权利,是为了体现怡人的生存环境对于人们生活的重要性,与此相对应的人类的环境利益才能落到实处,环境宪法规范才能找到“本源性”的基础。更重要的是,设定环境权这一基本权利,可以更为有效地对国家课以相应的义务,促使国家为了保障环境权的实现而积极作为。
但环境权不同于传统的消极权利和积极权利,而是属于新兴的社会权。按照耶利内克对基本权利的划分,环境权是公民对于国家处于积极的地位,从而派生出“对国家的请求”的权利。环境权是一种积极型、追求实质平等的权利。基于此,环境权在实践中并不能具有主观权利的权能,即不能司法化。目前国际上通行的做法是将环境权确定为不可诉的国家基本国策,使其通过立法、行政和司法得到具体的实现和作为国家机关活动的衡量标准,从而发挥其应有的规范效力。再者,传统基本权利理论认为只有公民个人基本权利受到侵害或者有被侵害的危险时,国家才有义务予以救助。而环境权具有的天然公益性特征,传统基本权利理论不能很好地对环境权进行保护。
实际上,一个国家的基本权利规范依据其性质不同,可以划分为主观权利规范和客观法规范。[16]国家宪法规范均可以分为主观权利规范和客观法规范。“生态文明”条款和“环境权”条款之争的问题,本质上可以理解为环境宪法规范体系的最高价值宣示,应该由主观权利规范还是由客观法规范来实现。主观权利和客观法规范的区别,主要在于是否可以通过诉讼的方式获得救济。而环境权属于社会权的一种,并未赋予其主观权利的可诉性功能。即环境权的实现,亦需通过国家机关履行一定的义务,这与国家目标条款规定并无二致。而以国家目标的表达方式构建环境宪法规范的最高价值宣示,继承了宪法的原有的体系安排,更有利于法律秩序的稳定。
三 解构和建构:环境宪法的国家义务体系
我国环境宪法规范体系呈现的一种客观法规范。该种客观法规范的实现,需要国家履行相应的义务。国家环境义务的推导,不能简单根据保障基本权利—国家义务体系进行演绎推理,而应从国家目标和基本国策的现实需要,有目的地进行推理。一般说来,国家义务体系根据国家权力的划分,分为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各自应履行的相应义务。但由于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本身存在的特殊性,国家机关即使很好地履行其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的义务,亦很难实现建设美丽中国的国家目标。此时,应该对传统的国家义务重新整合,构建以国家环境保护义务为核心的、由社会和个人共同参与的环境共治体系。
(一)传统国家义务的解构
环境宪法规范所对应的传统的国家义务,可以分为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的义务。传统国家环境保护义务的实现,相对应的分为三条路径:
一是立法机关通过创制法律,从而实现宪法规定的国家目标以及将国家政策推进的具体义务。因为宪法规定的环境目标和基本国策具有高度的抽象性,须由立法机关制定法律对环境权进行具体化,这在理论上被称为“宪法委托”。事实上,我国已经形成了较为完善的环境法律体系,包括具有综合性、一般性的《环境保护法》(2014),也包括具有专门性、特别性的《大气污染防治法》(2018)、《水污染防治法》(2017)和《海洋环境保护法》(2017)等20 余部单行立法,内容涉及大气、水、土地、野生动植物保护等方面,基本涵盖了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的全方面。
二是行政机关通过切实有效地执行法律,达到法律实现的状态。政府在领导、组织、协调环境资源保护工作,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资源节约型社会中具有重要的、关键的、不可替代的作用。[17]法谚有云“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任何制定良好的法律,均需要被有效地实行方能产生效力。行政机关无疑是法律实现最重要的渠道。我国行政机关的环境义务主要体现在行政机关的相应职责上,如编制环境保护的财政预算、对影响环境的项目进行审批、规范自然资源的利用、对环境进行监测和查处环境违法行为等方面。虽然行政机关的职权和职责规定较为完善,但却仍阻挡不住“环境日益恶化”。
三是司法机关正确适用法律的义务。司法是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其职责主要包括两个方面:(1)通过司法解释弥补立法机关制定法律的不足或者对法律中的概括性、抽象性的条款予以具体化;(2)在具体的环境诉讼案件中秉公执法,实现个案中的环境正义。
实际上,传统国家环境目标的实现,主要是以政府是否履行相应义务而进行评价的。而政府一方面承担着快速发展经济的任务,另一方面又得承担环境保护的任务,在实践中常常表现为政府过于重视发展经济而忽略环境保护。而由于环境权并没有司法化,如果出现环境问题,常常是以个人提起民事侵权诉讼去维护个人的人身和财产利益。而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不仅保护消极的环境污染的处罚和治理,亦包括积极的改善生态环境。而传统的国家义务体系并不能很好地发挥改善生态环境的积极效用。
(二)构建新型国家义务体系
传统国家义务体系过于依赖政府对于环境保护职能的发挥,并且往往注重环境污染的事后防治,不能很好地实现“建设美丽中国”的目标。因此有必要对国家环境保护义务进行反思,从政府防治环境污染的重心转向政府支持、鼓励社会团体和个人共同参与,从而达到环境共治的目标。
新时代的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是一项巨大的系统性工程,传统的政府主导环保的模式已经不能完成这一项任务。因此,政府在继续做好污染防治的环境保护义务的同时,必须转变思维,充分鼓励、调动社会团体和公民个人的力量参与其中。例如,2016 年蚂蚁金融服务集团在支付宝软件上上线了“蚂蚁森林”项目。该项目通过鼓励用户低碳生活(步行、公共出行)进而积攒虚拟的“绿色能量”,在手机里种植虚拟树木。虚拟树木成长到一定阶段,支付宝和中国绿化基金会等公益合作伙伴就会在中国的甘肃、内蒙古等地种下一棵真实的树木,或划定相应面积的保护地,以激励用户的低碳环保行为。至2018 年底,该项目已经在上述地区种植并养护真树5552 万棵,总面积超过76 万亩,实现碳减排308 万吨。[18]这一方式,不仅鼓励该项目参与者低碳生活,并且以企业的身份承担植树造林的义务。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是非常艰巨的任务,若想打好环保攻坚战,必须充分调动政府、社会团体和公民个人的积极能动性。
四 结 语
2018 年的《宪法修正案》共二十一条,其中涉及生态环境保护的条文有四条,可见党和国家对环境保护问题的重视。修宪之后,我国形成了以“建设生态文明”和“建设美丽中国”为核心,包括自然资源、土地利用、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的保护与改善等完整的环境宪法体系,使得生态文明建设有了根本法上的依据。我国环境宪法规范体系呈现的一种客观法规范,即需要国家履行相应的义务方能实现。对国家义务的解构,得出国家对环境保护义务的不足。而从环境共治的视角,使得政府、社会团体和公民个人积极参与其中,最终通过环境共治走向生态文明。
注释:
①部门宪法是与传统的国家宪法相对应的,从社会部门的认知,去探求宪法的规范。从部门的宪法规范,再回头去整合宪法的价值秩序,确认基本权的核心内容。环境宪法就是一种部门宪法。
②所谓环境正义,是指人类社会在处理环境保护问题时,各群体、区域、族群、民族、国家之间所应承诺的权利与义务的公平对等。
③第三代人权是“二战”之后反对殖民主义压迫的民族解放运动中所提倡的各种权利,其中包括各个国家或民族的生存权、发展权和民族自决权等所谓的“集体权利”。参见林来梵著《宪法学讲义》,清华大学出版社,2018 年版,第327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