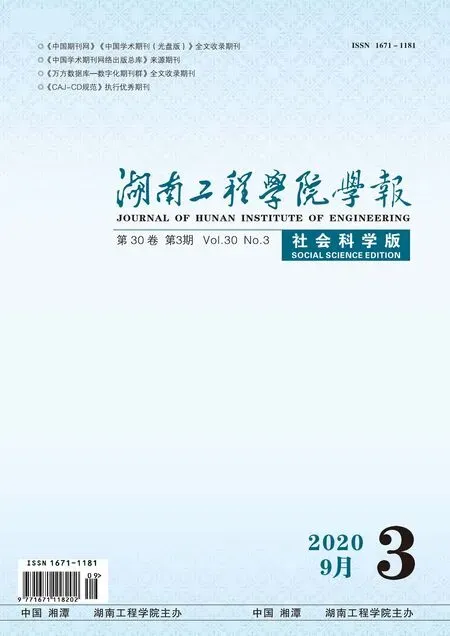不安抗辩权与预期违约制度比较与立法选择
朱 奕
(中南大学 法学院,湖南 长沙410083)
不安抗辩权制度的创立源于欧陆法系,而有着相似功效的预期违约制度的创立则来源于普通法系,二者皆为降低一方违约给另一方造成的损失。目前,各国对这两种制度都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引入,例如法国和德国引入了不安抗辩权制度,美国引入了预期违约制度。两种制度在民法中的功效突出,均有实用价值。
为了适应我国日新月异的经济发展以及贯彻民法中的诚信原则与公平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在引入传统欧陆法系不安抗辩权制度的同时,又创造性地引入普通法系的预期违约制度。近年来,对于这两种不同法系的法律制度能否融汇在一部法律中,是全盘否定还是各取所长,我国学者对此展开了较为广泛的讨论,学者们各抒己见。有学者持存预期违约制度而废不安抗辩权制度的观点,也有学者持存不安抗辩权制度而废预期违约制度的观点,另外也有学者认为两种制度并存且加以修善才是折中之道。在司法实践中,这两种制度的同时出现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司法实践中的不确定性,不利于我国司法的发展。
因此,对于这两种制度,该如何磨合或是取其中的一种并加以完善是值得我们深入研究的,对我国的司法实践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一 不安抗辩权理论
(一)不安抗辩权制度的渊源
不安抗辩权起源于中世纪的罗马法,[1]但罗马法中并没有现代意义上的不安抗辩权,却有“不履约的抗辩”。其来源于“约因”学说,主张一方的义务是另一方的约因,故而一方不履约为另一方不履约提供了法律依据,[2]不安抗辩权也由此衍生而来。第一个确立现代意义上的不安抗辩权的国家是德国。而后,不安抗辩权制度在欧陆法系国家予以确立并不断完善。在欧陆法系中,不同国家对于不安抗辩权制度的具体规定也各异。例如,法国的《民法典》规定,不安抗辩权唯能适用于买卖合同关系里的卖方,不能适用于买方,这体现出法国倾向于保护卖方权益的价值取向。相比之下,在德国《民法典》的规定中,不安抗辩权存在于所有双务合同之中,不只是买卖合同,其适用范围更为广泛,也就更加有利于债权人利益的维护。此外,意大利、瑞士、奥地利等国家的相关民事法律都对不安抗辩权制度进行了规定。
(二)不安抗辩权的构成条件
首先,双方因双务合同而互相担负义务。所谓双务合同是指双方都负有义务的合同。买卖合同便是典型的双务合同,此外还有租赁合同、承揽合同等。其次,双方义务的履行有先后的次序,其中一方履行的日期已经届至。最后,在合同正式签订之后,在后履行一方的履行义务的日期届至之前,后履行义务的一方有丧失或可能丧失履约能力之情形,且先履行义务方有确切足够的证据加以证明。
二 预期违约理论
(一)预期违约制度的渊源
预期违约制度起源于普通法系,它诞生于英国1853 年的Hcohster 诉De La Tour 一案。在这个案 件中,被告De La Tour 与原告Hcohster 在4 月12 日约定,自6 月1 日起雇佣原告Hcohster,雇佣的期限约定为3 个月,然而在6 月1 日之前,被告De La Tour 告知原告Hcohster 将不再履约。其后,原告起诉请求赔偿,而被告De La Tour 主张自己违约还未实际发生,称原告Hcohster 无权起诉。最后法院认为既然被告De La Tour 已确切表示将不履行合同,此时原告Hcohster 如果就这样一直等着对方实际违约的到来将不能另觅工作,这对原告Hcohster 来说既不公平又不切实际,因此法官判决原告Hcohster 胜诉。[3]自从此案发生后,英国创建了明示预期违约规则,并规定了预期违约中受害人的诉讼权利,保障了权利人的权利。而后出现的一些案例使得以判例法为主的普通法系国家的预期违约制度趋于完善。在1894 年英国“辛格夫人诉辛格”的案例中,默示违约规则得以确立。在这个案例中,被告在与原告结婚之前,就向原告承诺过结婚以后将自己的一套房产转赠给原告,然而事实上,被告却将该套房产有偿转移给了他人,导致他先前许下的允诺无法兑现。最后法院认为此种情况下,原告有权利解除合同并要求被告提供赔偿。[4]现如今,许多国家及地区对预期违约制度都有所规定,《美国统一商法典》便是一个值得借鉴的典范。其中,第2-610 条规定在明示毁约下,非违约方享有救济权,而且此法典也确立了默示毁约情形和认定条件。
(二)预期违约的构成条件
因为普通法系主要以判例法为准,因此法官在判例中创建了两项关于预期违约的规则,也即明示预期违约与默示预期违约的规则。
1.明示预期违约的构成条件。首先,明示预期违约的时间点应符合合同签订后、履行期限届至前。如果在这个时间点以前,可能会构成缔约上的过失,如果在这个时间点之后,则会构成实际违约。其次,预期违约人的违约表示应确切、自愿而又肯定,如果其说法模棱两可、似有似无,不能准确表达其不履约的意图,也无法成立。再者,预期违约人违约是针对合同当中的主要义务,其违约行为将导致双方的合同目标不能达到。最后,预期违约人需无正当理由而违约。假设其正在行使同时履行抗辩权或是主张债务已经过诉讼时效,亦或是违约是由于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的发生,这些理由属于正当理由,均不符合条件。
2.默示预期违约的构成条件。默示预期违约与明示预期违约的构成条件大致相同,比如在时间点及违反的义务类型等方面相同。在时间点方面,二者都是在合同签订之后,在约定的履行日期届至之前。在违反义务类型方面,二者都是得违反约定的主要义务才能成立。不同的是默示预期违约只能通过未违约人主观性的推测来确定,当然,这种推测并非毫无依据,预见的一方必须有确凿的证据来支撑其推测,否则很有可能损害到非预见方应得的权益。而明示预期违约是通过违约人自己明确的表达来确定。除此之外,前者若需成立还需要被预见违约的一方不愿提供适当的担保,这样的规定合情合理,可以用来防止权利的滥用。例如在我国《合同法》当中的第六十九条就有相关规定,一方当事人在预见另一方无法或不履行合同以后,需向对方提出履行担保的请求,唯有当另一方未在合理期间内提供担保时,才能构成默示违约。
三 不安抗辩权与预期违约的比较
(一)不安抗辩权与预期违约的相同点
第一,两者发生的时间点相同,均为合同成立后,履行日期届至之前,这是前提条件。第二,两者都侧重保护债权人的权益,维护他们的可期待利益。第三,预期违约制度中的默示预期违约制度与不安抗辩权都在一定程度上建立在一方当事人的推测上,具有一定主观性,当然这种推测也都必须有确切的证据来支撑,否则难以成立。
(二)不安抗辩权与预期违约的区别
笔者先举出一个典型的案例,进而更清晰地分析两者的区别。甲有限公司是一家生产实木家具的公司,乙有限公司是一家销售实木家具的公司。二者在2017 年9 月23 日签订了一份承揽合同,也即乙有限公司向甲有限公司定做317 套沙发,交货日期为2017 年11 月13 日,但在2017 年10 月11 日,在甲有限公司已经生产了123 套沙发之时,当地的消防部门对甲有限公司进行检查后发现其生产存在非常大的安全隐患,故要求其停产整改。甲有限公司也因此无法按时履行乙有限公司的承揽合同。乙有限公司在得知此情况后于2017 年10 月15 日向当地的法院起诉,要求甲有限公司承担违约责任。但是甲有限公司辩称乙有限公司只能主张不安抗辩权。那么,这个案件究竟是适用预期违约还是不安抗辩权,是这个案件的关键之处。
这两种制度是有区别的。(1)两者的性质有区别,不安抗辩权属于抗辩权,它归属于形成权,该权利的行使无需对他人提出请求,而主张预期违约的权利属于请求权。(2)两者的权利主体不一致,前者的救济主体为先履约人,后者的救济主体则为双方当事人的任一方。(3)两者的前提条件不一样,前者的行使以合同有先后的履约顺序为要件,而后者则没有此限制。(4)前者适用于当事人客观上丧失履约能力的情况,而后者则侧重于当事人主观上不履行合同。(5)两者产生的后果不尽相同,前者先产生中止合同义务履行的效果,抗辩权人可要求对方提供适当担保,如若对方拒绝提供或是在合理时间内还没有恢复履约能力,那么权利人此时是否可以行使解除权,各个国家对此有不同的规定,分为肯定说与否定说。肯定说认为此时权利人可以行使解除权,而否定说认为此时权利人不能行使解除权,我国是持肯定的态度。而预期违约制度的救济权是多样的,权利人可选择继续等待对方履行,如若对方到了履行期仍不履行,权利人可以要求解约并请求赔偿,权利人亦可直接选择解除合同。(6)两者侧重追求的价值不一样。前者更侧重于追求公平价值,而后者则更侧重于追求效率价值,因为后者的救济力度强于前者,更有利于纠纷的快速解决。
再来回顾一下甲有限公司与乙有限公司的案例,大致来看,这个案例似乎既符合预期违约规则也符合不安抗辩权的规则,但若将甲有限公司不能履约的事由稍作分析,便可得出结论。在此案中,甲有限公司是因为消防部门要求整改而导致的不能履约,这属于客观的因素,而在上文中已分析到不安抗辩权适用于客观不能履约的情况,而预期违约则侧重于当事人的主观不履行。因此,本案应适用不安抗辩权规则,也即乙有限公司只能先中止履行自己的合同义务,并要求甲有限公司提供一定的担保,不能直接行使解除权。
四 我国《合同法》中的不安抗辩权制度与预期违约制度
其实早在1985 年,我国就有一部法涉及到了不安抗辩权制度,那就是已经废止的《涉外经济合同法》,但该法并不要求双方当事人有先后的履行顺序。因而,《涉外经济合同法》的精神其实更接近于预期违约制度的规定。
如今,在我国民法中,不安抗辩权制度规定在《合同法》第六十八条和第六十九条,而预期违约制度规定在《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二项和第一百零八条。我国的不安抗辩权制度相较于欧陆法系中的传统理论有一定差别,其适用范围更为宽泛。首先,欧陆法系的传统理论认为,不安抗辩权主要存在于“资产减少以致不足以履行义务”的情况,而我国《合同法》第六十八条对此规定了四种情形,结合列举法与兜底条款的方式,较为完整与全面,这样就可以更加充分、有效、完整地保护债权人的权益。其次,欧陆法系的传统理论称不安抗辩权属于抗辩权的一种,是一种带有防卫功能而非进攻功能的权利,因此抗辩权人通常只能中止己方合同的履行,但是我国为了提供抗辩权人更为有力的保护,赋予了权利人解除合同的权利。当然,我国《合同法》为了有效防止先履行义务人滥用权利,而给债务人的利益造成损害,也为这种解除权提供了一定的限制,即抗辩权人不能直接行使解除权,而应该先中止合同的履行,同时让对方提供一定的担保,只有对方拒绝,才能解除合同。抗辩权人不能因为对方拒绝提供担保而让对方在履约日期届至前就履行合同。另外,相比较于欧陆法系的不安抗辩权,我国的《合同法》在赋予抗辩权人权利的同时,也为其规定了两项主义务之外的义务,一是通知对方自己要中止合同的义务,另外一个是证明对方无法履约的义务。
关于预期违约,我国的规定和普通法系中其他国家的规定也有些许差别。第一,我国规定的适用范围更窄,在明示预期违约这一方面,我国和其他国家类似,但是,在默示预期违约方面,我国又只规定了用自己的行为表达自己将不履约,而其他国家却规定了当事人可通过合理判断对方当事人不履约的情形。第二,救济措施不同,在其他普通法系的国家,债权人在对方明示预期违约的情形下有选择的权利,也就是既可以解除合同,也可以等到约定的履行日期届至时再采取救济措施。在默示预期违约的情形下,国外大多只赋予权利人中止权,在违约人没有给出担保之时才可以解除合同,但是我国在默示预期违约的情形下同样赋予了权利人直接行使解除合同的权利。
此外,我们更应看到我国对于两种制度规定的不足之处。这两种制度在我国合同法中的同时出现,实则是两大法系的碰撞与融合,但这种法律移植的过程却出现了诸多问题,背离了立法的初衷。
对于不安抗辩权,我国的规定具有局限性。第一,不安抗辩权中先履行义务人的义务较重,不仅要通知对方中止履行合同,还要负担举证的责任。但实际上,要对对方的财产状况、盈亏状况作出举证是较为困难的,这不利于保护先履行义务人的权益;第二,我国对于不安抗辩权制度的规定不太确切,我国的合同法规定权利人中止合同后未提供适当担保的可解除合同,其中,关于“适当担保”并没有出台相应的司法解释,使得实践上难于操作。
对于预期违约,我国的规定也有一些疏漏。第一,我国对预期违约的规定不是特别集中。《合同法》将此分别规定在第六章(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与第七章(违约责任)这两章,这种分散的规定不利于《合同法》的系统性与条理性。第二,我国对预期违约并未规定具体明确的标准。《合同法》第一百零八条仅仅将预期违约的行为描述为“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合同义务”,这在明示预期违约方面还能够判定,但对于默示预期违约方面则过于模糊,难以认定,导致司法实践上有一定的任意性与不稳定性。第三,我国未对明示预期违约与默示预期违约区分开来,尤其是在救济措施上。《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二项规定,无论违约方是何种预期违约情形,被违约一方均可以解除合同,这明显是不合理的。当一方当事人发生“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的情形时,另一方当事人的主观臆断性很强,这使得一方当事人口头表达的内容和另一方当事人根据当事人行为推测得到的结论具有一样的法律效果,令人难以接受。并且如果当合同的一方以自己的行为表示不履行时,对方就径直解除合同有违公平原则,因为合同的一方有可能在履行期限到来之前恢复履约的能力,从而得以继续履行义务,如果赋予权利人直接解除合同的权利不利于我国经济的稳定发展。《合同法》第一百零八条的规定同样未对两种预期违约的救济措施作出不同的规定,均规定为要负担违约责任。
笔者认为,既然明示预期违约与默示预期违约的违约方式存在差异,那么其在救济措施上也应当有所区分。另外,预期违约与不安抗辩权两者规定的界限模糊、粗疏,因此在法律适用上会产生分歧。例如当后履行义务人出现《合同法》第六十八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的情形,即转移财产、抽逃资金以逃避债务时,后履行义务人可依据《合同法》第六十八条主张先履行义务人应援用不安抗辩权,暂停履约,请求己方提供担保,而不是直接解除合同。而先履行义务人则可以按照《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二项规定,也就是可以认为后履行义务人是在履约日期届至以前,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义务而援用预期违约主张解除合同。此时便出现了法律适用上的冲突,这不利于法官的抉择,也不利于案件判决的统一,从而会让民众怀疑司法,有损司法的权威。而且在司法实践中,遇到这两种制度竞合的情形,出于鼓励交易、维护交易稳定的宗旨,法官也通常会适用不安抗辩权制度,因为适用不安抗辩权的效果是必须先中止合同,而不能直接解除合同,如若这样,默示预期违约也就难以有用武之地,相当于是形同虚设。
五 完善我国预期违约制度的建议
关于我国《合同法》中预期违约制度与不安抗辩权制度的融合是创新还是败举,学术界存在很多争议。大致分为三种观点:一种是以李永军教授为代表的,主张只保留不安抗辩权制度,认为不安抗辩权制度能完全解决预期违约制度所能解决的问题,没有必要冒着逻辑上产生的不太严谨的风险,再去引入预期违约制度;[5]一种是以王利明教授为代表的,认为预期违约是不可替代的制度,其移植是势在必行的,应当同时引入两种制度;[6]还有一种观点建议只保留预期违约制度。笔者更加倾向于去除不安抗辩权制度并保留预期违约制度的观点。其原因就在于不安抗辩权相较于默示预期违约而言,适用的条条框框更多,适用的范围又仅仅局限于双务合同之中,且能够援引的人只能是先履行义务的一方当事人。[7]这些条件不利于对出现其他情形的保护,例如出现单务合同时就没有救济可援用,即使在双务合同中,后履行义务一方的权益也无法得到保护,而相比较于不安抗辩权制度,预期违约制度的救济措施更为完善。
对于如何完善我国的预期违约制度,笔者提出如下几点建议:
首先,应当在我国立法中区分明示预期违约与默示预期违约,并为其制定认定标准。在明示预期违约方面,需违约方“确切表示”,也就是违约方应自愿、确切地作出意思表示,且“不履行”为不履行双方约定的主要义务,或者不履行的行为对非违约方的利益有重大影响,会导致其合同目的落空。在默示预期违约方面,可以参照适用不安抗辩权的情况加以列举,当然也需要加上最后一项兜底条款,有了这些明确的规定,预期违约适用条件就能进一步具体化,在司法实践中也能较好地把握,法官应用起来会更加得心应手,这样也有助于纠纷的解决,实现司法保障公平正义的作用。
其次,应当将预期违约制度更集中地罗列在一起,避免出现法条的逻辑混乱。预期违约成立的时间段在合同成立后,履约的日期届至前,因此可将有关预期违约的规定全都放在“合同的履行”这一章节,因为预期违约也不一定就必然会导致合同的终止,因此把此类规则全都放置在“合同的履行”里,更有利于《合同法》整部法的逻辑清晰以及严密。
再者,应当为明示与默示预期违约两种制度分别制定救济措施。在默示预期违约方面,应该借鉴不安抗辩权制度的救济模式,即当有一方违约后,另一方只能先暂停履行,而非直接解除合同,并要求对方提供一定的担保,当违约方在过了合理期限之后还没有提供担保并且不履行义务时,非违约方方可行使自己的解除权。这里的合理期限,可以参考《美国统一商法典》的标准(30 日),[8]这样的救济模式才有利于保护和平衡合同双方当事人的利益。而在明示预期违约方面,则可以按照原规定不变。
最后,应当在明示预期违约中增加撤回制度。因为随着情况的变化,预期违约方或许会想改变自己先前的预期违约行为从而想和对方继续履行合同,此时,即可为预期违约方设立撤回权,除非受损方在对方违约后已解除合同,或已严重改变地位,或已用其他方式表明他认定违约无法逆转,否则,违约方在其应履行的下一项合同义务届至前,可以撤回已作出的违约。[9]这样可以促进合同的交易,促进交易的灵活性。
六 结 语
综上所述,预期违约制度比不安抗辩权制度更具灵活性和实用性,两者的并存不仅不会充分发挥两者的特色,还会给法律适用造成一定的困难,对我国相关立法进行完善是势在必行的。废除不安抗辩权制度而进一步完善预期违约制度,这样不仅能迎合法律发展的国际潮流,也能更好展示合同法的价值。
——以实体法与程序法为透析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