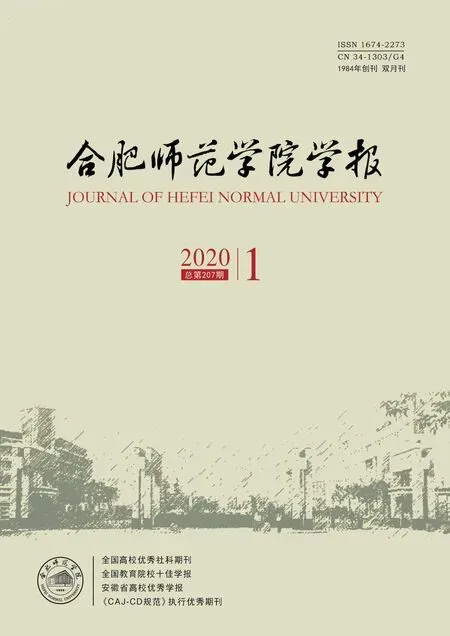《甲乙事案》与《圣安本纪》之混淆与辨别
毛艳秋
(黑龙江大学文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 150080)
明清时期的笔记作品十分丰富,文人乐于运用笔记这一较为自由随意的文体形式记录生活,日常所感、闲谈逸闻、亦或是野史杂谈,皆可入笔记之中。到了明末清初时期,历史背景和社会背景的巨变,促使许多遗民作家选择以笔记的形式将自己在这一特殊时期的经历记录下来,而鉴于明末清初历史时期的特殊性,诸多此类笔记作品的流传都受到环境的影响,在传播过程中不免出现讹误的现象,《甲乙事案》和《圣安本纪》就是其中的代表,两书之间的讹误一直持续到近代时期,最终通过学者们的不断勘对、比较,才得以正确区分。
一、《甲乙事案》与《圣安本纪》文本概况
《甲乙事案》为明末文秉所著,所记历史自崇祯十七年(1644)四月史可法等誓师勤王,至南明弘光元年(1655)十一月鲁王监国止,关于是书创作原因及书名由来,作者在该笔记的序言中对此有所解释:“偶读《弘光事略》一书,见其间邪说充塞,黑白倒置,深恐讹以传讹,误当年之见闻者小,而淆千古之是非者大,遂撰是书。”而作“甲乙”之名,是因本书所记录史实的起始时间从崇祯十七年甲申到弘光元年的乙酉,故而谓之“甲乙事案”[1]。全书模仿朱熹《资治通鉴》纲目体例,有纲有目,记录史实之后继以“发明”,借春秋之义加以评价,又作“附录”,列举同类史实。是书史料丰富,有补于历史之不足,但是鉴于作者东林后裔的身份,故而后世学者在评价其所叙之事时,认为其言不免有门户之偏见。然而该笔记笔法独特,逻辑清晰,谢国桢先生曾在《增订晚明史籍考》中对该笔记做出“脉络详明,前后情势,斐然可观”的评价,不仅道出该笔记记载历史的客观性,也从文学角度出发对该笔记的叙述手法给予了肯定。
关于《甲乙事案》的版本,在傅璇琮先生所编著的《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有记录:
有抄本多种,卷数不一,同治《苏州府志·艺文》载有一卷本,缪荃孙《艺风堂藏书记》载有二卷本,朱希祖、谢国桢所见有三卷本。坊间另有讬名顾亭林而题《圣安本纪》之六卷本,据朱希祖考证,实亦本书之别本。”[2]133
傅璇琮先生此处所提到的关于《甲乙事案》的版本信息,朱希祖先生在《明季史料题跋》中也有记载:
六卷本《圣安本纪》,实为《甲乙事案》之足本,同治《苏州府志·艺文类》文秉《甲乙事案》一卷,缪荃孙《藏书记》《甲乙事案》二卷,钞本《甲乙事案》三卷,皆非足本,而足本六卷,仅赖伪讬顾氏之书以传,是亦可谓幸存矣。[3]32
这两段材料恰好可以相互佐证,为《甲乙事案》的版本信息提供了有力的证据。而关于与《甲乙事案》产生讹误的《圣安本纪》,此处也有必要对其版本和内容进行简要的梳理。
《圣安本纪》,顾炎武撰,二卷,《日知录》及《明季稗史》中皆有收录。《亭林遗书汇辑》中此书又名为《圣安纪事》。是书所记弘光帝一朝史事,起自崇祯十七年四月史可法督师淮上,至弘光元年六月弘光帝被俘至北京,因隆武帝上弘光尊号曰圣安帝,故以此为名。朱希祖先生关于《圣安本纪》亦于《明季史料题跋》中有所介绍:
《圣安皇帝本纪》二卷,刻于《明季稗史汇编》者,持以与《南疆逸史》、《圣安帝纪略》对校,十同七八,足徵温氏《纪略》即采顾氏《本纪》而作,《稗史》本似非伪书明矣。《亭林文集》有《与戴耘野书》,言:‘昔年有纂录南都时事一本’,盖即此二卷本之《圣安本纪》也。吴县朱记荣刻《亭林全集》,中有《圣安纪事》二卷,亦即此二卷本《圣安本纪》所改名。[3]32
朱希祖先生通过一系列的堪比和考证,明确了《圣安本纪》的版本,对于因书名改动而在传播过程中产生的讹误,也通过一些史料中的信息进行佐证并给予了更正。而关于其与《甲乙事案》之间的混淆和辨别,同样是通过一些史料信息的搜集来展开。
二、《甲乙事案》与《圣安本纪》之间的混淆与辨别
《甲乙事案》与《圣安本纪》之间的讹误混淆一直持续于近代,直至朱希祖先生对两书进行辨别,才得以更正。
朱希祖先生提到收录于《荆驼逸史》的六卷本《圣安本纪》,为清道光年间刊刻的活字本,题为昆山遗民亭林氏顾炎武撰,因为与《甲乙事案》内容一致,故而后世常误认此书作者为顾炎武,而实际由顾炎武所撰的《圣安本纪》,却另有它作,内容与《荆驼逸史》中所收录的六卷本《圣安本纪》内容完全不同。根据《荆驼逸史》序跋中的内容所载:“《圣安本纪》六卷本,乃出自文秉《甲乙事案》”。此处,编撰者并没有给出具体区分。朱希祖先生也在《明季史料题跋》中提到 “六卷本《圣安本纪》与二卷本《圣安皇帝本纪》,前贤皆以为顾炎武撰,无有疑之者”,并提到“如李慈铭博览南明史籍,精于鉴裁,然于此二书亦无分别。”可见纵然是李慈铭这样遍览南明之书、精于裁度之人,关于二书之间的混淆,也没有明确的判断。
《钞本甲乙事案跋》中摘录了李慈铭关于《圣安本纪》的评论:
《圣安本纪》六卷,昆山顾炎武著……用大书分著法,又有发明,前有亭林自序,较《明季稗史》本多。”,又“其书有附录,有发明。据亭林自序,谓其著作于昆山叶氏搆难避居之时……有斤斤以书法为主,又倣之作发明,不特于本纪之名不相应,而踵《春秋胡传》之陋,拾尹起莘辈之唾,颇近无谓,且动引经传以讥二奸,亦迂而不切,固由宁人少年所为,犹不脱明人学究气。[3]34
由此段记载可观,李慈铭对《圣安本纪》的创作及文笔,也有诟病,认为此书为顾炎武年少时所著,文字和结构与后来顾氏文风十分不符。 至于“作于昆山叶氏搆难避居之时”这一自序,确为毫无根据的臆测。顾氏在昆山叶氏避难之时,已经年过四十,并非少年。但是,遗憾的是李慈铭并没有对此存疑,故而其间之混淆,也未能引起关注。
《明季史料题跋》中关于两本书的混同,通过三个方面进行了辨别,首先是文本写作手法的对比,六卷本《圣安本纪序》与《甲乙事案序》完全相同,只有序末的署名“南雲庵”易为“昆山遗民亭林氏顾炎武撰”,文秉在其所著《烈皇小识》序文末所题亦为“竺坞遗民文秉书于考槃之煮石亭”,又根据其序文的词句语调与《甲乙事案》序文的语调十分相似,而且其与顾氏之文笔绝不相同,可推测出二者皆出于一人之手,即为文秉所作。
其次是根据时间和史实的推断,《甲乙事案序》中提到:“予遭仲氏之难,列在官府者幸荷宽政,或托至戚者反难密网,孑然数口,屏迹深山。”《苏州府志·文震孟传》记载:“乘字应符,隐山中,有诬其与吴江吴易通者,逮至官,乘不辩就死。”朱彝尊为文点墓志云:“处士长州文君点,以疾卒于郊西之竺坞。”文点即为文秉之弟,文秉自称竺坞遗民,原因即在于此。而关于顾炎武,朱先生提到:“虽亦于弘光元年七月遭昆城之难,生母折臂,二弟皆殉,然其家于崇祯十七年十二月已迁居常熟,常熟城破后其母亡,九月迁至嘉定,至次年十二月,往闽中赴职方之职,未尝屏迹深山,历吸风茹霜之苦境也。”由此可断定,此序文为文秉所作,而六卷本《圣安本纪序》中将《甲乙事案序》:“偶存《弘光事略》一本,见其间邪说充塞”易为“《圣安事略》”,朱先生认为其是 “为《圣安本纪》作张本耳”。
另外,从文本的细微处分析,亦可见其中的差异。《甲乙事案》中记载:“崇祯十七年六月丙寅,予故大学士文某等谥。”又“温体仁所摧抑正人,宜谥文某文肃,罗喻义文介,姚希孟文毅”。而《圣安本纪》中改“文某”为“文震孟”,朱希祖先生认为:“此处作伪者改易以名,此尚是其精审之处。”六卷本《圣安本纪》中有一段记载:“弘光元年六月辛卯,落发令下,中书文震亨时寓阳城,闻令下,自尽于河,家人救之,绝粒六日而死,遗笔有‘谨保一发以见祖宗于地下’之句。”这段记载在残本《甲乙事案》中已经缺失,文震亨为文秉叔父,朱希祖先生推断《甲乙事案》之中此节的缺失,可能是作者出于避讳或者敬缺的考虑。又《南疆逸史·文震亨传》中,亦有“绝粒六日而死,遗言曰:‘我保一发下觐祖宗,儿曹无堕先志。’”之语,朱先生认为这足可证明《南疆逸史》亦是参考《甲乙事案》而成,其中有相当之部分是对《甲乙事案》的采择,而且文秉记载家事相较于他人必定更加详尽确切,因文秉亲见叔父遗笔,故而有“谨保一发以见祖宗于地下”之句,此亦能证明六卷本《圣安本纪》实为文秉所撰。
除了以文本内容作为出发点来堪比,也可从作者创作习惯和文本所呈现出笔法的纯熟程度进行考量。六卷本《圣安本纪》在文体上充分体现了“事案”二字,而且又有“发明”,十分合乎《甲乙事案》之体要,而顾氏绝不会以“本纪”之名,作“纲目”之体。再则,文秉也不至于著名不副实之书。关于两书的混同,也存在其他猜测,比如刻书者为盈利,利用顾氏之名,虽然也存在这种可能,但相对而言,从文本本身和历史资料角度出发,朱希祖先生借助文本内容的推测,以及历史史料的具体分析,佐证更加充分翔实,更加具有说服力。导致两书之间出现混淆讹误的作伪之人,或是出于当时政治的压力,为避讳或躲避政治迫害的无奈之举,或者只是出于牟利之目的,借顾氏之名气以博得更多的关注,尚不得而知,但是可以确认,六卷本《圣安本纪》确为《甲乙事案》。
三、《甲乙事案》与《圣安本纪》讹误之原因
由两本书之间的混淆可见明代笔记作品在传播过程中,“讹化”现象并不少见,导致这种混淆的原因也比较多,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思考。
首先是社会环境的角度,明清易代的历史环境之下,新政权为实现对旧有政权打压和摧毁的目的,最主要的途径就是在思想文化领域的钳制,这就为明清之际易代文学的传播造成了极大的阻碍,甚至是毁灭性的打击,以《四库禁毁书丛刊》为例,其中收录内容即为编修《四库全书》期间被抽毁和全毁的书籍。所禁毁的史部书籍中,尤以涉及辽东与南明史实的著作为多,这是满清统治阶级为实现政权的稳固而采取的手段,运用抹杀、毁灭、篡改历史史实等方式来达到掩盖历史的目的,这就对类似《甲乙事案》和《圣安本纪》这类历史书籍的传播产生影响,故而,为躲避政治打击,传播者通过更改作者的方式以自保,也是情理之中的选择。
除却政治因素的影响外,经济利益的驱使,也是影响明清文学作品传播的重要因素,可以用明清小说文本在传播过程中作伪现象的出现为考量。明清小说刊刻是书坊主牟利的重要手段,为达到“售多而利速”的市场效果,书坊主采用了很多作伪的方式对小说文本进行加工,比如对小说原著稍加修改之后易名以冒充新作,或者是以“原本”、“古本”等字样来吸引读者,而实际阅读起来与刊本小说并没差异。而对于那些遭到禁毁的小说,书坊主往往通过更改书名、作者,并对文本细节之处多加改动,以求减少漏洞,与伪本相一致。这与六卷本《圣安本纪》对《甲乙事案》的冒伪极为相似,更改书名、作者以及文本中的细节,达到以假乱真的目的,利用作者的名气和文本的内容来吸引读者的关注,以求获取更多的经济利益,但同时也导致文本在传播过程中讹误现象的发生。
通过老一辈学者鉴别文本的经验来看,可知辨识文本的真伪,不仅要从文本出发,还要依靠史料记载相互佐证,才能辨析作品之间的异同,从而全面客观确定文本真伪。在明代笔记整理和研究过程中,尤其是明清朝代更迭之际的笔记作品,颇多文本之间的混淆和讹误,研究者应当承袭前辈学人求真求实的治学态度,以期夯实自身文献功底,提升文学素养,为文学研究道路的扩展提供坚实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