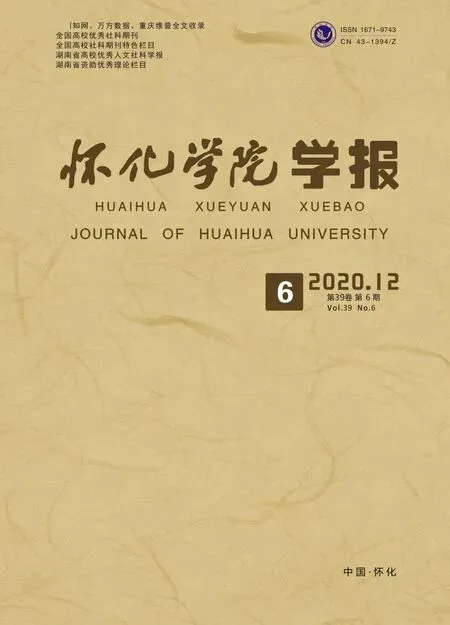空间观与文化空间意义探讨
——兼论鄂伦春人空间逻辑的文化养成
尤明慧, 柳 娟
(哈尔滨商业大学财政与公共管理学院,黑龙江哈尔滨150028)
一、范式与认知: “ 空间 ” 与 “ 空间观 ”
在人们的认知体系里, “ 空间 ” 常常被用来指与 “ 区域 ” “ 范围 ” “ 规模 ” 等意涵有关的表达。据《说文解字》记载:空,孔穴,字形采用 “ 穴 ” 作偏旁部首,采用 “ 工 ” 作声旁,本义是名词,用来指人工建造的居所。 “ 间 ” ,缝隙。字形采用 “ 门/月 ” 会义,本义是动词,指入夜后在屋内休闲、歇息。被阐释为 “ 与时间相对的一种物质客观存在形式,由长度、宽度、高度、大小表现出来。通常指四方(方向) 上下 ” 。与 “ 空间 ” 相对应的西方语义词汇是 “ space ” , 源于拉丁文, 被阐释 为 “ something measurable in length,width,or depth,distance,area,or volume that can be used or filled by a physical object,room. ” 基本都是指向物质的存在维度,也就是物理学意义上的 “ 处所 ” “ 形状 ” “ 距离 ” 等,总体上的内涵特征表达的是抽象的狭义空间概念。美国社会学家华勒斯坦提出空间在某种意义上实际是社会的产物,时间和空间不仅是社会发展的变量,而且是社会科学发展的变量[1]。由此可见,华勒斯坦突破了传统上人们对狭义空间的认识,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种广义的空间观。
广义的空间则更为具体,英文中对应的词汇是 “ 处所 ” (place) 一词,相接近的词汇还包括 “ 位置 ” (position)、地点(site)、场所(location) 等,这些词汇在社会学意义上更多地是指某种 “ 经验的建构 ” 。因此,广义的 “ 空间 ” 概念更具有 “ 开放性 ” 和 “ 实践性 ” 。在广义空间意识基础上产生的空间理论思维模式主要是将事物置于空间背景下探讨其在场性、构成性及其文化功能,多在人文社会科学视域下被采用。 “ 空间 ” 的现代意义被阐释为是与环境、与地域、与物质、与时间以及与人类相互建构、相互影响的各种关系,这些关系在人文活动中都被统一在 “ 空间概念 ” 之中。人们对 “ 空间 ” 的认识是通过对自然或物体对象的具体定位而形成的一种对空间认识的直接经验,而并不是从这种直接经验中抽象出来的理论体系。如早在上古时代,中国人就在 “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 的生活常态中,形成了由 “ 东 ” 和 “ 西 ” 构成的最早的 “ 二方位 ” 空间认识。其后,人们又逐渐形成了由 “ 东 ” “ 南 ” “ 西 ” “ 北 ” 构成的 “ 四方位 ” 空间认识,这些空间理念在甲骨文的相关记载中都有体现,如在早期人们的祭祀仪式中所指的 “ 四方 ” “ 四风 ” 等。人们在生产、生活的实践过程中又进一步丰富了对空间的认识,如《周易·系辞传》记载: “ 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 ”[2],此时人们已由 “ 四方位 ” 的空间意识发展成了 “ 八方位 ” 体系。
在人们的 “ 空间 ” 认知体系里,除了体现 “ 方向 ” “ 位置 ” “ 顺序 ” “ 关系 ” 等意涵外,还与 “ 宇宙 ” “ 自然 ” “ 地理 ” “ 天地 ” “ 方圆 ” 等关键词关联起来。如 “ 奄有四海,为天下君 ”[3]此处的 “ 天下 ” 在古时多指君王统治范围内的所有土地,《淮南子·原道训》记有 “ 横四维而含阴阳,紘宇宙而章三光 ”[4]。东汉高诱注: “ 四方上下曰宇,古往今来曰宙,以喻天地 ”[4]。这里的 “ 宇 ” 可以理解为无限空间,而 “ 宙 ” 则是指无限时间,包含宇宙间一切物质及其存在形式的总体。《庄子·齐物论》中也有关于天地四方、宇宙空间的记载: “ 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六合之内,圣人论而不议。 ”[5]而《管子·五行》中的记载: “ 昔者皇帝得蚩尤而明于天道;得大常而察于地利;得屠龙而辨于东方;得祝融而辨于南方;得大封而辨于西方;得后土而辨于北方。皇帝得六相而天地治,神明至 ”[6]。此处的 “ 六相 ” 即是包括了天与地等更深层次的空间意识。中国古代先民是在与环境和自然互动的过程中形成对万事万物的认知体系的,古人认为自然蕴含着无限能量,这些能量随规律而运转,体现在时间上就是 “ 天时 ” ,周而复始,不竭不休,因此古人用 “ 天圆 ” 来描述时间的特点;而描述空间则用 “ 地方 ” ,来自 “ 四面八方 ” 的空间观,因此 “ 天圆地方 ” 就是讲时间和空间,体现了中国人早期原初的时空观念。此后,在人们对空间的不断认识中,自身意识逐渐觉醒,并将自身加入这个立体的空间维度,强调人的空间本体地位性,体现在古代《诗经》中记载的 “ 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7]。将空间概念和帝王的权力以及君主在统治上的地域范围进行了关联,并逐渐形成了以帝国为天下中心的理念,即 “ 中国 ” 。
“ 空间 ” 一直以来都是哲学反思的命题,人们也是从哲学开始真正意义上的认识 “ 空间 ” 。古希腊哲学家对本体论的问题颇感兴趣。德谟克利特认为, “ 一切事物的始基是原子和虚空,原子是不可再分的最小物质微粒,虚空是原子运动的场所,因此空间首先是相对的 ”[8]。柏拉图则认为宇宙的本源可以溯源为三种类型,即 “ 理性原型、可感事物或载体 ”[9],其中 “ 载体 ” 指的就是 “ 空间 ” ,并进而将 “ 空间 ” 阐述为 “ 一切生成物运动变化的场所,感觉无法认识,而只能依靠一种不纯粹的理性推理来认识。 ”[9]亚里士多德对 “ 空间 ” 的理解是将空间与事物的本体分别开来,并对它们之间的联系与区别进行了说明,阐发了空间的相对性与有限性,可以说是把原始性实用空间加以体系化的初步尝试[10]。在人类时空认识史上,亚里士多德的相关阐述可以称得上是第一个较科学的理论,奠定了近现代时空理论的基础。法国哲学家笛卡尔探讨了空间与物质的关系问题,认为空间是物质的空间,而物质是以存在于一定的空间为前提的[11]。德国哲学家康德将空间看作是事物存在直观的、普遍的形式,而理智则是自然界普通秩序的来源,人类认识的一切事物都必然受理智的法则支配[12]。黑格尔在讨论空间概念时,结合了对时间的认识进行了阐述,认为空间和时间都属于运动,运动是空间和时间的直接统一,体现了他对事物存在方式的某些合理论断[10]。早期先哲们对于空间的思考和论说奠定了我们通过空间的概念认识和理解世界的理论基础。
二、空间转向与人类学的空间经验
当代空间理论伴随着西方社会文化思想理论的转向与变迁得以诞生,开启了西方哲学的实践论转向。1974 年,亨利·列斐伏尔的《空间的生产》以及米歇尔·福柯的《权力的地理学》的出版,开启了当代空间理论研究的新篇章。当代空间理论弥补了传统空间理论经验直观或超验抽象的缺陷,具有建构性与整合性,成为学术界备受关注的热点题域,因此被称为 “ 空间转向 ” (spatial turn)。列斐伏尔的相关学说主要体现在他的《空间的生产》一书中,他着重阐述了马克思的生产理论,并以此为基础提出了应当将空间理解为人类生产实践的产物,同时列斐伏尔提出了他的理论研究核心概念,即 “ 空间生产 ” (production of space)[13]。在此基础上,列斐伏尔又陆续提出了 “ 空间实践 ” (spatial practices)、 “ 空间表征 ” (representation of space)、 “ 表征空间 ” (representational space) 等空间概念和逻辑构成,在理论上实现了历史性、社会性与空间性的统一,同时也对空间问题进行了哲学反思,为空间转向提供了系统化的理论知识。与列斐伏尔相比,福柯更为关注的是空间与权力之间的关系,倾力于对历史建构的空间场域进行知识考古学研究,以此建构关于权力的空间理论[14]。继列斐伏尔、福柯之后, “ 空间 ” 问题的相关讨论引起了学术界的普遍关注, “ 空间 ” 也发展成为学者们建构理论逻辑的基本维度之一, “ 空间转向 ” 最终推动了现当代人文社会科学思维范式的转型。
“ 空间 ” 问题也引起了众多人类学家的关注和探讨,美国人类学家克拉克洪和凯利探讨了 “ 文化空间 ” 的含义,将其阐释为 “ 一种渊源于历史的生活结构的体系,包括语言、传统、习惯、制度,以及有促动作用的思想、信仰和价值 ”[15]。古典进化论代表人物摩尔根在对美国印第安人进行深入观察思考后,探讨了空间与人类的亲属结构和社会结构的关系,为之后文化功能论的研究及其家屋空间的探讨奠定了民族志基础。功能主义学派马林诺夫斯基很早就认识到空间的文化性,进而提出人类的活动体系以及对物质文化的应用都是有组织的,并得到完善配置,也就是说一切空间构成都有其文化上的需要,试图探索不同的空间现象和空间建构的文化机制或象征意义。社会学家涂尔干将空间视为基本的分类概念之一,是了解自然、社会以及人类思想精神等问题起源的基础,他认为空间范畴是一种社会性形成,与社会分类之间密切相关,空间概念是了解人类社会结构和文化逻辑的媒介载体,人类是经由空间概念了解、阐释和重塑社会结构与文化观念的。结构主义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认为 “ 原始的野性思维知识和现代科学知识尽管长期分离,但终将在一定时空中汇合:要么通过通信活动迂回到物理世界,要么通过物理学迂回到通信世界 ”[16]。他在讨论 “ 时间的可逆性 ” 时已在事实上论述了空间作为时间运动的前提。格奥尔格·齐美尔借助对 “ 桥 ” “ 门 ” “ 都市 ” 等的细腻描写,揭示出空间的社会属性(独占、分隔、固定、距离和运动等) 及其在形塑不同环境中生活的人的个性特点所赖以建立的心理基础。葛兰言从上古时期中国的仪式集会入手,认为空间(包括山川地带、节庆集会) 完全是人类的性质,人们正是通过空间(节庆、祭祀等仪式) 来确定和谐的空间秩序。
虽然不同学派的人类学家对空间问题的探讨不尽相同,但人类学空间研究的历程却始终贯穿着一个理论观点:空间是社会和文化的建构,各社会文化可建构不同的空间结构与秩序,但在不同的空间结构与秩序中,却存在许多相当普遍的空间概念,这些空间概念用来建构各社会文化特殊的空间分类与结构,乃至空间的象征系统,也因不同人的实际使用产生不同的实际意义。在人类学学术传统里,较多使用 “ 文化空间 ” 这一概念。 “ 文化空间 ” 也称为 “ 文化场所 ” ,是对 “ the Culture Space ” 的不同译法,也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时使用的一个专有名词。 “ 文化空间 ” 这一概念首先是亨利·列斐伏尔在《空间的生产》一书中提出的,意指特定族群进行文化创造和文化活动的地域范围,这个概念基本上是沿用地理学上的 “ 空间 ” 概念。人类学家在运用 “ 文化空间 ” 进行文化现象阐释的时候,常常结合了特定人群的文化传统、文化形式、文化活动,因此是文化与空间的结合体,涵盖了文化模式所表达的文化意涵,寓意一个特定的地域或地方而又并非一般意义上的空间概念或一种具体表现,而是人类文化行为存在、传播和记忆的载体,因此这里的 “ 文化空间 ” 是一个具有文化意义的 “ 隐喻性空间 ” (metaphorical spaces),兼具时间性、空间性和文化性,是民族社会衍生、传承、发展、变迁的前提和基础。
也有学者认为 “ 文化空间 ” 不仅具有历史性、风土性、地域性、民族性等特征,而且囊括了现有时空中实际生活运行的状态, “ 文化时空 ” (cultural space and time) 似乎在语义学上比 “ 文化空间 ” 更为合适。因为文化本身是纵横交织在时间领域(纵向性、历史性) 和空间领域(横向性、地域性) 之内的,任何事物的空间和时间都是一体的,文化也是如此[17]。由此文化空间应该是综合了时间与空间两大要素,涵盖了某一时间段与某一地域范围内的所有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包括人、物质、环境、信仰观念等,具体呈现的文化要义体现为以下几点:首先,文化空间具有时间上的延续性,人类的文化行为如仪式、活动、聚会、演示等的周期性、时令性、季节性的展演,这种传统习俗依靠族群代际传承于文化传统或有关民族文化历史之中;其次,文化空间是一个独特的文化场域,指一个族群的文化习俗与其传统生存环境融为一体;最后,就其表现形态而言,文化空间可以是古村落、庙宇等文化场所,这一场所表现的民间和传统文化活动是某族群的独特文化传统且具有典型代表意义。可以概括地说,文化空间是由场所、意义符号和价值载体共同构成的表意系统和具有象征意义的主体行为叙事空间;是结合生态环境、历史传承、季节流转、岁时传统、价值认知、生命智慧的人类行为的文化场和自然场,蕴涵着丰富的历史和人文意义。
三、鄂伦春人空间逻辑的文化养成
我们试图从人类学的视角来探讨鄂伦春人的空间逻辑及蕴含在其中深刻的文化意义。鄂伦春人居住的大、小兴安岭,具有独特的地理环境,这里峰峦叠起、江河纵横、森林茂密,林中栖息着各种野生动物,这些都是他们赖以生存的空间环境和衣食之源。通常情况下,人类为地方命名会涉及对地方的人文与地理空间的认知和理解,鄂伦春人常以某地方的山势、河流的自然特征、野生动植物或民族历史上的某次事件作为命名的依据,建立对此区域的理解和认同。山林河流和各种类型的动植物构成了鄂伦春人的基本生存空间,因此在鄂伦春语中表示山或河的名词大多以动植物或地理方位命名,如 “ 查拉班河 ” ,意为河边多白桦树; “ 依沙溪河 ” ,意为河道弯曲像动物的肩胛骨; “ 干玛山 ” ,意为 “ 在小河口的下游 ” ,等等。在狩猎生活中,鄂伦春人经常跋山涉水,对于山林的地形地势了如指掌,因此也留下了一些据此而来的地理名词: “ 塔河 ” 是 “ 挡住 ” 或 “ 阻碍 ” 前进方向的意思; “ 二根坎河 ” 是指不好走的地方; “ 沙拉根河 ” 是有近路可以走的地方。在鄂伦春人的价值观里,优秀的猎手和民族英雄是应该受到尊敬和爱戴的,因此他们也会以一些历史人物来命名,如 “ 蒙克山 ” “ 里格布山 ” “ 红布耶河 ” 等,这些名字往往源于远古时代的神话传说,同某个英雄猎人的事迹相关联,例如 “ 多布库尔河 ” 就源自一个关于哥哥多布和弟弟库尔战胜蟒猊,英勇牺牲的神话传说[18]。
在传统生存环境里,山林是鄂伦春人活动的场域,他们长期使用这片土地,饮用山林里的溪水,明了山势脉络、河流走向和自然界的生态变化,这里不仅是他们狩猎的场域,更是他们生活的地方,因此他们和我们在山林环境里的感受是截然不同的。猎人视山峰、溪谷、岩壁为可见的天然界线,虽然口语上惯用行政地域的指称,但与地图上的行政界线不完全相符,他们在这里生活,守护这块土地,使用这里的一切。笔者曾经采访过一位80 多岁的老猎人,他非常熟悉关于山林的一切,他以河流作为方向的基础,能够画出整座山的河流和支流,标出各山脉的名称,并且说出河流在哪里有拐弯,哪里有分支,能准确记得河流蜿蜒的方向和位置,依林中听见的流水声以及山形坡度判断正确的方向。山脉、河沟的走向和命名以及动植物的分类背后有着深层的文化意义,从这些意义中可以透视一个民族共同体的文化实践和文化叙事与其行为方式、认知体系之间的功能关联,进而建构一个民族信仰自然力量和超自然力量的宇宙观。大兴安岭上的每座山、每条河都承载着一个神奇的故事,都流传着一个美丽的传说,被鄂伦春人一代代地讲述着、传扬着,当一次又一次被提起的时候,这些故事和传说也自然地被赋予了民族情感和民族记忆。一种关于文化信仰与行为规范的观念,民族的历史、信仰、风俗、习惯、民族性格、伦理观念就在一代又一代人中形成民族共同体的集体记忆与文化认同。
我们再来分析鄂伦春族猎人传统的特质。他们通常从13 岁起就要与族人共同上山,对山林地理环境、植物的利用详加了解。猎人必须了解动物,认识各种动物的脚印,从中分辨公母、重量。他们要训练个人的体力、耐力与技艺,养成对大山的信仰、敬畏。猎人是不善言辞、不喜吹嘘的,他们就在山林大地之间,和自然对话,和山林共处,和动物赛跑。猎人总喜欢坐在帷帐前,双眼凝视着山峦,手抚摸着刀或枪,思考着大地,他们相信山林会赐予他们一切猎物,他们对山林表现的敬畏与虔诚会指引他们找到猎物,因此他们谨守勿语的规则,上山不能开玩笑,更不能有任何污秽或亵渎的语言。猎人狩猎的时间有时是两三天,有时可能要一两个月,依据猎物的情况而定。当猎人下山与族人分享猎物的时候,是他们的狂欢时刻,他们享用过丰美的晚饭后,就一起围坐在篝火边,分享山林中打猎的区域和遇到的各种状况。大家也会谈起过往事情,讲故事或者表演民族音乐、舞蹈:摩苏昆、赞达仁等,他们的话题往往围绕着英雄或祖先,或者部落大事、历史。当鄂伦春人参与其中的时候,他们的神情表达出对祖先和传统生活的景仰和认同,与平日随意开玩笑的态度截然不同,他们想象着祖先的生活,与长辈都曾感受火的灼热、背后的寒风以及动物的声音。猎人讲述着故事,怀念着自己的祖先,他们将自身和这些故事融入这个地方空间,亲临此地的氛围,成了开启猎人记忆的钥匙,让他们不由自主地回想和思念自己的祖先和历史。狩猎是猎人与山林最直接的交往方式,也是族人缅怀祖先的途径,猎人依着地方文化的脉络,经由独一无二的身体经验,透过空间的氛围唤起记忆,以最贴近的方式为地方建立意义。
因此,当检视鄂伦春人的狩猎文化时,狩猎活动发生的场域,诸如山林、溪谷、猎场等空间概念,文化、社会的意涵均在其中刻上了深刻的痕迹。鄂伦春人对于部落、山林及猎场的传说、禁忌与经验,均能反映文化的意涵,鄂伦春人的信仰、家族观念与世界观都可以从中窥见。
四、文化空间的意义与价值体系
鄂伦春人生活的地理区位、自然环境、社会组织、生活方式、风俗习惯等构成了一个人群聚落的社会形态要素。具体表现为一个族群的人们在祖先遗留下来的土地上共同生产、生活,有共同的信仰,每个节日庆典都要举行祭拜仪式,严格遵守仪式的规程和禁忌,这也许就是格尔兹所谓的 “ 常识 ” ,即 “ 地方性知识 ” 。然后以我们熟知的形式展现出来,展现为每个人都能够也都应该认识的世界,就此使得这种知识具有了社会性、文化性和实践性等。而 “ 空间 ” 则是 “ 知识 ” 实践的地方,人们在其间的所有行为都受到 “ 地方 ” 的规制和形塑,这些行为和行为的空间只有在当地的背景下才有意义,即具有 “ 地方性 ” 的意义,由此文化空间具有地方性。狩猎文化空间借助山林、树木、猎物、器具等一系列公共象征符号及围绕符号展开的祭祀、庆典等仪式活动形成了一套在地化知识体系:狩猎的方式与技巧;猎人的培养;故事、歌曲、舞蹈的传承;山神的祭拜及祭品的供奉;猎物的分享;节日的欢庆以及此外许多活动构成了一个狩猎民族的地方性文化系统,并使之作为一种传统与传承持续下去,明确了个体的族群身份和族群的文化边界,进而形成 “ 地方感 ” 。 “ 地方性 ” 不仅指特定的地域或地理环境和历史条件,知识生成的情境和语境更多的是关于文化阐释的路径、方式,人群共同体的立场、视域和价值观,并在特定的群体中得到认同[19]。
文化空间是地方性知识的依托,亦是地方性知识的建构,而地方性知识大多需要借助符号在特定的空间里传递文化信息,记录社会变迁,形成象征系统,由此空间成为文化的重要载体和形式。在此意义上,文化空间又可以看作是由各种类型的符号构成的,包括图腾、服饰、建筑、器具等等,因此可以说文化符号是空间和地方性知识最直接的表现形式[20]。这些符号在构筑空间的同时又形成于空间,符号在文化中的功能大概体现为交流、表义、象征等,文化空间借助于符号塑造民族共同体相似的情感,形成一个族群的集体记忆和历史记忆,从而保证一个民族文化文脉的繁衍生息。一个民族文化的延续与传承也与集体记忆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现代社会背景下,诸多民族,尤其是人口较少的族群面临着文化空间的转变,集体记忆便失去了建构的环境和条件,而集体记忆的断裂不仅是民族历史的遗失,更是民族未来的危机,文化空间若缺失了历史记忆,也将失去其原真文化的特质。正如列斐伏尔所认为的,空间是民族环境和民族文化的建构,同时空间也为民族的延续和文化的展演提供场所、条件和背景[13]。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 空间 ” 生产出集体记忆和文化认同,并为它们实现其文化功能及其相互之间进行关联提供了可能性。
文化空间的意义也体现了民族共同体的核心价值观,核心价值观涵盖了一个民族的精神创造和文明积淀。在鄂伦春人的文化空间中,尽管行为叙事多种多样,诸如狩猎、采摘、制作、祭祀、聚会、分食等,这些多角度、多层次的行为叙事都体现了共同的价值观:天人合一、人神共处、重义轻利、集体意识和吃苦耐劳的精神。对于一个狩猎民族而言,他们所生活的自然环境,所拥有的生态资源不仅仅为他们提供了衣食来源,而是具有生命意义的存在,孕育了世间万物,并且是作为超生命的存在,支配着一切,包括人类。鄂伦春人认为他们来源于自然,生存于自然,将来也消亡于自然,因此他们是与自然融为一体的,本能地顺应自然并与自然有一种亲近感。狩猎空间将人类与自然界融合为了一个整体,应和着中国传统文化中 “ 天人合一 ” 的理念和价值观。季羡林先生据此认为中国文化的特点在于天与人配合,所以 “ 天人合一 ” 是中国文化对人类最大的贡献,是中国传统文化所表征的最高境界,其反映的必是人类普遍的理想追求[21]。狩猎文化空间作为一种地方性的观念、认知,凝结了群体的集体记忆和情感归属,而这一空间的社会边界比自然边界更为重要,它是一个历史的、变化的、过程化的空间体系以及据此形成的一种认知方式、群体记忆和地方认同,是某一地方的人群共同体共同拥有的知识体系和价值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