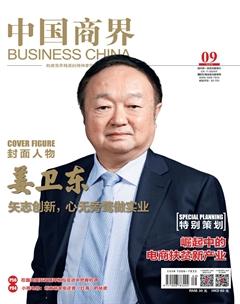驭势2020:“刺激”还是“救济”权威专家把脉经济复苏
邓大洪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造成经济停顿,让中小微企业的生存受到严重的威胁,“发不起工資”、贫困人群和低收入人群生活受到严重影响。如何渡过当前的难关,是大搞基建刺激经济,还是给中小微企业减免税费、给居民发放消费券直接救济中小微企业和低收入贫困人群?专家学者纷纷建言献策。
刘世锦:需激发经济“绿色复苏”潜能
“中国经济的恢复,更重要的是‘绿色复苏”。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说。“绿色发展在应对疫情冲击、经济复苏和高质量发展中的作用至关重要。”
刘世锦介绍,在近期组织专家开展的相关研究中,专家们经常提到的一个词就是“绿色复苏”。专家们认为,中国有效应对疫情冲击,在全球率先恢复增长,应抓住疫后经济恢复的机遇,在坚持绿色发展上表现出远见和定力,争取实现绿色复苏,为全球疫后经济复苏和发展起到示范作用。
刘世锦认为,“十四五”期间应抓住机遇,形成包括发展理念、政策目标、重点领域、体制机制等在内的绿色发展基本框架,实现经济社会生态协调发展,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生态资本共同建设,包括但不限于环境保护,形成包括绿色消费、绿色生产、绿色流通、绿色金融等在内的完整绿色经济体系,以及与绿色发展相协调的政策激励机制。
“有人认为经济形势好不好,主要靠宏观政策,这种看法有很大的片面性。”刘世锦分析说,“宏观政策充其量是减少波动,营造一个稳定增长的环境,现阶段我国经济增长主要靠的是结构性潜能。”
刘世锦解释说,所谓结构性潜能,是指中国作为一个后发经济体,在技术进步、产业结构和消费结构升级、城市化进程等方面的发展潜能。
首先,是追赶潜能,或者说是跟跑的潜能。中国目前年人均GDP1万美元,发达经济体多数在4万美元以上,美国是6万多美元,这中间至少有3万美元的差距。“发达经济体已经做了、我们应该也可以做但尚未做的事情,正是我们增长的潜能所在。”刘世锦说。
其次是新涌现的潜能,这是与发达经济体同步、有可能并跑,甚至领跑的潜能,如数字经济和绿色发展。
林毅夫:保中小微企业生存就是保中国渡过难关
“保企业也就是保护我国的就业和维护我国经济的根基,此事宜急不宜缓,出手要快,不能迟疑。”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南南合作发展学院院长、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林毅夫说。疫情让中小微企业的生存境遇异常严峻,需要给予更大力度的支持,比如减免租金、减免税收、减低税率、推迟社保医保缴费、推迟偿还贷款本息、提供新的贷款等。我们一定要重视中小微企业,因为它们提供了大量就业,破产倒闭会带来失业等严重问题。而且它们是很多全球产业链的重要组成部分,企业若是破产了,要重建会有许多困难,保它们的生存就是保中国渡过难关,是维持全球制造业大国地位的必要举措。
林毅夫认为,只要应对得当,利用近几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所创造的有利政策空间,采取积极的货币政策稳定金融体系,增加信贷资金帮助实体企业渡过难关,采用积极的财政政策进行新基础设施等建设,并对受到疫情不利影响的城市和农村低收入、贫困家庭提供必要的生活资助,以扩大内需,在危机中保持稳定、增长和就业,那么全面脱贫的目标在今年就能完成。
“只要做到这些,我国经济未来增长的质量就会提高,并且还能以防疫经验和物资帮助其他国家防控疫情,以我国的增长助力其他国家走出衰退或萧条。”林毅夫说。如果能够做到这样,也将像2008年那场国际金融经济危机一样,进一步提升我国在国际经济中的比重、地位和影响。
许小年:疫后最紧迫的是救济而不是刺激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终身荣誉教授许小年认为,有关经济决策的一些讨论似乎迷失了方向,“现在最为紧迫的是救济而不是刺激。谁最需要救济?是中小企业。”
许小年说:“对小微企业的救助和支持政策是对的,但是还远远不够。我注意到,在政策层面上人们还在争论新基建、财政刺激的力度,以及财政赤字是不是可以货币化等问题,这些争论没有落到目前经济和民众生活最紧迫的事情上——财政和货币政策的焦点不是如何刺激经济,而是如何救济经济。”
许小年进一步分析指出,欧美国家的政策就是救济,他们把钱发到中小企业和个人的账户上,这是有道理的。如果还是传统的财政刺激,搞基建投资,通过产业链一环一环地传递到中小企业和个人手里,那是需要时间的。可以想象一下,如果通过基建刺激,比如建特高压,电网公司下了订单,由电器厂去做电缆、做变压器,然后变压器厂去采购铜线钢板,再由钢铁厂去采购矿石和焦炭,产业链延伸下去要多长时间?现在每天不知道有多少中小企业倒闭,我们是在和时间赛跑。因为疫情所造成的经济活动的停滞,中小企业的资金链已经很紧张了,如果采用投资拉动的方式,等着产业链一环一环地传递到基层,那可能已经来不及了。
“企业一旦倒闭,想恢复起来成本是非常高的。所以现在最为紧迫的是给老百姓发钱,给中小企业发钱,那样比基建拉动见效要快得多。”许小年说。
许小年还指出,强调救济重要性的另一个原因是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不畅。如果说实体经济中的供应链是财政政策的传导机制,那么中小金融机构就是货币政策触达中小企业的传导机制。货币宽松,银行放款,一般都放给了国企,有相当规模的民企也能拿到一些,而大部分中小企业要么无法受益,要么只能做国企的供应商或合作者而间接受益。
许小年认为,在经济活动放缓、付款拖延的情况下,中小企业的资金周转已越来越困难。政府虽然一再强调金融服务实体,要增加对中小企业的贷款,但大型商业银行从本质上讲不适合做小微贷款,“捉老鼠要靠灵活敏捷的猫,狮子干不了这个活儿”。
许小年建议,央行应该直接给中小金融机构提供无息资金,中小金融机构再向中小企业发放低息或无息贷款。也可以把消费券发到老百姓手里,消费券见效要比财政刺激、基建拉动更快,钱会直接流到服务、餐饮、旅游等现金极度紧缺的小企业那里,而不必通过基建那么长的产业链。
“再说一遍,我们是在和时间赛跑。这次疫情和以往的经济危机不一样,它直接造成了经济活动的停顿,不是放慢,而是马上就停顿。服务业、餐饮业、小型商贸企业已经倒了多少?它们的现金储备也就能支撑两三个月。没有现金流入,企业就办不下去了。所以,救济紧于刺激,当下的政策讨论在方向上出现了偏差。”许小年强调说。
陈志武:保住中小企业才是稳就业的根本
“我知道有不少人一谈起‘新基建来就很激动,他们认为这可以帮助中国经济走出疫情的影响。其实客观讲,这不能解决正在恶化的就业问题,也不会给那么多因为疫情失业的人、因为疫情关闭的小微企业带来直接的实质性好处。2020年不会,2021年也不会。”耶鲁大学金融学终身教授陈志武说。
陈志武指出,主张靠“新基建”来刺激中国经济的这些人和企业,主要是可以直接从中受益的群体。但很遗憾的是,除了最前面的 100家或者200家大型高科技公司直接受益以外,那些在这次疫情中面对生存挑战的千千万万小餐馆、千千万万夫妻杂货店并不能从中得到什么帮助。它们被关停了两个月,勞工成本照花、租金照付,但是没有收入,他们怎样活下去?这些中小微企业每年创造了80%到85%的新增就业岗位,如果这些企业活不下去,那么老百姓的就业马上就会出现问题。
“决策层要看到,新的东西、尖端的东西是蛮好的,但现在不是要靠发展尖端技术救经济的时候。那些尖端技术如果成功,也要等很多年才能为整个社会带来帮助,但正在和将要受疫情冲击的老百姓和小微企业该怎么度过2020年、2021年呢?”陈志武强调说。从这次疫情中,很多人更加领悟到,简单追求经济增长数字是没有意义的,更重要的是让生活的方方面面更全面发展。尤其是,一旦发生像新冠肺炎疫情这样的风险事件时,人们今后也能过好生活,不用再面对无路可走的局面,这才是现在稳定经济过程中重点要发力的地方。
张明:政策重点应在企业和家庭
“政府应把钱用在直接补贴企业和家庭上,而不是全部用于基建领域。”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投资研究室主任张明说。
张明认为,财政政策放松对宏观经济而言是一个重要的稳定器,今年财政政策应该是发力的主体。从全球范围来看,当前美欧日政府都采取了非常宽松的财政政策,中国政府目前也释放了非常积极的信号。今年中央政府财政赤字占GDP的比率可能提高至4%左右,特别国债规模可能达到2万亿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年度规模,之前市场预测的是2.5万亿到3万亿元,目前来看可能会到4万亿元以上。上述大致估算表明,今年中国政府的财政宽松可能会额外带来5万亿元的资金,相当于GDP的5.0—5.5%。
张明希望本轮财政政策放松的资源能够更多地投放到受疫情冲击比较明显的企业和家庭补贴上,而不是全部用于基建。因为把资金投资于基建虽然能够拉动经济增长,但能够从中获益的只是少部分企业,而且还是本身情况都还不错的国有企业。
在这次疫情中,受冲击最明显的是中小企业,是中国的中低收入居民。所以说,如果想让疫情对中国经济的微观基础冲击最小化的话,扩张性财政政策的重点应该是去做转移支付,去减免税,而不是去搞基建。基建当然要做,但财政宽松的重点要放到转移支付方面。
张明进一步分析指出,新基建现在很热闹,但是目前市场热议的一些所谓的新基建不是基础设施投资,而是具体行业和产业,比如工业互联网和充电桩。新基建该不该做?该做。那该由谁来做?该由企业来主导,而不是地方政府来主导。2009年4万亿元的教训告诉我们,当时地方政府主导的那一批所谓的新基建后来都变成了老基建,无一例外地遭遇了产能过剩、地方债务与银行坏账。所以我们要吸取教训,避免重蹈覆辙。
对于货币政策,张明的观点是当前的货币政策应该按照中国自己的节奏来放松,而不应该跟着美、欧、日亦步亦趋。货币政策是一个总量工具,而且目前的传导还面临着很大阻塞。即使降低了准备金与利率,钱最终能不能到最急需支持的中小企业和中低收入家庭那里,还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我觉得今年大概有四到五次降准,目前已经有三次了。当然,最近这次是非常明显的结构性降准,主要针对中小银行。”张明说。在今年剩下的时间里,可能还会有两次降准。值得一提的是,中小银行因为结构性降准比较多,现在准备金已经降到历史上比较低的水平,未来的降准空间已经没有头部银行那么大了。
在降息方面,张明认为,未来央行应进一步通过中期借贷便利、贷款基础利率的渠道来降息,借此诱导商业银行降低企业贷款利率。调低基准存款利率的必要性不太大。
张明还认为,随着通胀的回落,未来货币政策操作的力度可能会加大,通胀回落之时,可能就是货币加码之日。但是,“我还是希望货币政策放松能够相比于财政政策放松更加审慎一些,尽量避免2009年和2010年的信贷大潮重演。”张明说。
管清友:社会基础要适应疫情新常态
或许,“疫情防控常态化”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现实问题,社会急需一套与之相匹配的 “后疫情运转系统”。这套系统将承载我们在疫情新常态下的工作、生活与学习之运转。它可能长什么样尚无定论,但需要试图找到平衡“疫情防控与复工复产”的相关解决方案。甚至,边试水边纠错,循序渐进。这是金融研究院院长管清友的观点。
“我们目前的社会基础设施还是无疫情状态下的一套系统,应对疫情的诸多改变也大多是临时性的,或者说没有改变社会基础设施的基本状态,例如工作、交通、管理制度、应急等等。”管清友说。但华山医院感染科医生张文宏此前撰文指出,在国外,“新常态”就是伴随着每日有新增病例,但照样开工、复学、复市。对于我国而言,就是全面恢复经济、学校、开放公共场所,但又不得不面对输入性疫情的风险以及相应的较大防控压力。
管清友认为,如果要和病毒长期共存,那么社会基础设施的改变在所难免,不过,当务之急是需要在经济和抗疫之间至少保持一个脆弱的平衡。“怎么改,如何变?且思且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