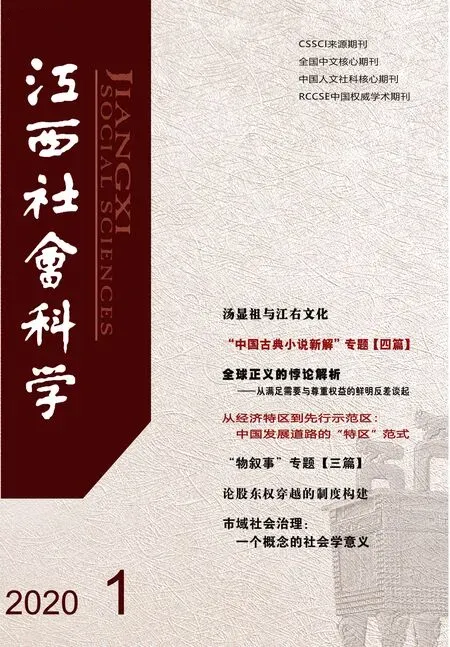《金瓶梅》的哲学问题
《金瓶梅》哲学问题的核心是“天道”,其试图以天道中的善恶有报因果论和乐极悲生论来治理社会重病。西门庆、潘金莲这些恶人得的病不轻,明朝社会得的病不轻,他们的命运轨迹,还有善者吴月娘、孟玉楼的命运轨迹都在演绎中国先贤哲人的“天道”哲学观念,人都必须遵循“顺天者存,逆天者亡”这一规律。《金瓶梅》哲学问题的来源是古代诸子哲学的思想和价值判断,如先秦时期道家的“道法自然”、寡欲以保身养生,儒家的中庸之道、中和节欲观、寡欲以养心,杨朱一派的适欲顺生观,还有佛家的“色空观”和“因果论”等。《金瓶梅》的哲学命题,给我们留下了有益的启示:一是认知生命与欲望之间关系的合理性,二是认知自然人与社会人之间关系的和谐性。我们应该从哲学的层面去认知《金瓶梅》丰富和有积极意义的价值。
一、问题的提出
本文所论及的“哲学”,是中国古代的哲学,或者说,是中国古代思想家对世界与人自身的一种认知,一种充满了有关世界和人如何治国理政、如何待人处世的思想智慧,它在内涵上与现代“哲学”这个概念所指的内涵多有相同或相近之处,所以今人借用“哲学”这个词,还要借用“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些说明“哲学”的词来讨论有关的问题。
文学的创作源自于作者的思想,有思想,当然就有三观(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也就有了哲学范畴的问题。中国古代流传于世的小说名著之所以得以流传,有的成了经典,不仅是因为人物故事和写作手法或者小说题材有流传的价值,作品本身具有的思想或者说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有流传的价值,总能反映出那个时代人们的思想或者说社会的智慧,流传的岁月越长久,说明作品思想智慧的价值越普遍甚至相对永恒。因此,讨论经典小说,不讨论小说的哲学问题,就不可能把小说的讨论引向深入,既不符合小说作者、作品和读者之间的关系的实际,比如思想的影响、审美的存在,也不能解决我们对小说文本自身研究的认知问题。
中国古代社会盛行的道德、伦理这两个概念的内涵,实际上是一定时期社会的思想认知在人的言行准则上的反映。传统的经典小说,其哲学内涵与道德内涵有统一之处,哲学的内涵往往依靠道德的内涵具体地表达出来。但二者也有不同,哲学重在思考,道德重在实践;哲学是一种思想的智慧,道德则是一套行为的准则;哲学是永恒的命题,道德是特定时期的规定。在一些人看来,《金瓶梅》这样的书有很大的道德问题,它是谈不上有思想,也就谈不上有哲学。这最容易使文学作品污名化,自然是研究不出文学的规律和问题来的。也有人认为,《金瓶梅》反映的人生观、价值观无非就是“欲”,这种观念能谈得上是哲学思想?这是一种片面的理解。《金瓶梅》是不是就是“欲”暂且不论,即使论“欲”,这是人之本性本能之一,正是属于人必须面对并处理好的哲学本体论的范畴;而人的止欲、禁欲、纵欲都属于哲学认识论的范畴,需要人们的智慧来理解并对待它,这都是哲学要讨论的重要问题。如果说,《红楼梦》的哲学重大命题之一是“盛极必衰”,那么《金瓶梅》的哲学重大命题之一就是“欲极必亡”。这是在研究《金瓶梅》哲学问题之前,必须说的第一个问题。
《金瓶梅》研究到今天,广度越来越大,内涵也越来越丰富,但是还必须向深度开掘。研究它的创作思想,研究它的哲学问题。否则,没有理论的研究,没有哲学层面的研究,《金瓶梅》的研究就缺乏应有的深度,它的价值也就得不到应有的判断。《金瓶梅》作为中国古典长篇小说中第一部世情小说,作为很多古今中外学者都已认定的一部有深刻思想内涵和丰富社会内容的作品,其哲学的内涵必然十分丰富,而且很有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它作为影响了后来的世情小说创作,特别是直接影响了《红楼梦》创作的一部具有开创性的作品,研究它的哲学思想,是研究者的一项重要课题。这是必须说的第二个问题。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国内《金瓶梅》的研究和讨论逐渐形成热潮,到21世纪初,又渐趋平静和理性,研究和讨论《金瓶梅》的内涵的成果越来越丰富多样,其中也有学者开始涉及《金瓶梅》的哲学问题。在笔者查阅到的为数不多的相关的论文中,这些研究大致可以分成三类。
一是在分析小说的时代背景时直接切入到当时的哲学命题之中去,分析明代理学、心学,特别是阳明心学、李贽“童心说”、社会由于经济的发展出现的反传统道德、人性的回归等所谓“进步”的思想对作品创作的影响作用。
二是在分析小说的人物形象和故事情节时,把理学、心学作为分析的武器,进而为肯定小说主要人物的行为及其命运寻找根据和说法,寻找时代的合理性。
三是在讨论小说的思想内容时,触及人之生与人之死的根本问题,也涉及与生死密切相关的纵欲和禁欲问题,讨论时,更多的是为了说明人物的行为特征和故事的具体情节。
这些研究无疑都是很有价值的,对《金瓶梅》研究领域的扩大和深入具有开拓性的意义。这些研究和讨论,更多的是从微观上,从人物形象和故事情节上来说明某一种哲学概念的内容。因此,它更多的是把哲学的解释作为文学分析的附庸来使用。
《金瓶梅》哲学问题的讨论,并不是纯哲学本体的讨论,而是哲学与文学的关系讨论,可以是两种角度:一种是以文学作品为主,兼论哲学,把哲学作为附庸,作为一种行为的思想解释;还有一种,把哲学看作是文学(小说)创作的思想动力,即作者如何把哲学作为自己的创作动力、创作意图来进行创作的。今天我们讨论《金瓶梅》的哲学问题,不只是从微观层面即说明人物故事如何表现某些哲学(理学、心学)概念或命题,而且更要从宏观上来回答:作者为什么要用这种逻辑来写这个人、这件事、这本书?本文所做的研究正在于此。这里所讲的哲学与文学的关系并不是要肯定所谓的“主题(哲学问题)先行”,而是作者的思想与作品创作之间的关系。
中国哲学的基本问题,在经典作家看来,是人与世界的关系问题。这个世界的“世”,有自然世界的意思,但主要还是社会的“世”,是“人世”。冯友兰在《中国哲学简史》中讨论“中国哲学的问题和它的精神”时首先说道:在很多哲学家讨论的问题中,包括像释迦牟尼、柏拉图等外国哲学家在内,把哲学的问题首先放到了人与世的关系上,有主张“出世哲学”的,也有主张“入世哲学”的:
许多人认为,中国哲学是一种入世的哲学,很难说这样的看法完全对或完全错。从表面看,这种看法不能认为就是错的,因为持这种见解的人认为,中国无论哪一派哲学,都直接或间接关注政治和伦理道德。因此,它主要关心的是社会,而不关心宇宙;关心的是人际关系的日常功能,而不关心地狱或天堂;关心人的今生,而不关心他的来生……中国传统哲学的主要精神,如果正确理解的话,不能把它称作完全是入世的,也不能把它称作完全是出世的。它既是入世,又是出世的……入世和出世是对立的。[1](P6)
这“入世”和“出世”两个出发点,可以归结到一个基本的问题,那就是人和世界的关系问题。了解这个“世”,就可以明白中国古人用自己的话语系统讨论更多的是天地人及其关系问题。因为,中国人要处理好“人与世”的问题,必须处理好或者说要借助“天时、地利、人和”,这就把“人与世”之“世”又与自然世界接上了关系。另一个很重要的哲学命题也就提出来了,即天、地与人的关系。虽然这种“天”“地”与人的关系即自然与人的关系,但“天”与“地”也不是纯然的自然主体,因为古人对“自然”这个概念的解释与西方的解释和今天人们的普遍认知很不相同,“自然”的意思更多的不仅是今天所说的“自然界”的自然,而是由“自己的那个样子”逐渐演变成“本来的样子”。比如“道法自然”,不是说“道”还要听命于“自然”界的“自然”,而是“道”要听命于它自己本来的那个主体。所以“道”就是“自然”,是最高的主宰。古人讲的自然的主体中已经浸透了中国人对人对天对地的混合性理解,到汉代逐渐发展起来的“天人合一”的思想和广泛传播在官方与民间的“天道”“天理”已经把对自然的考察深深打上了社会和人的精神烙印。中国哲学中的天、地、人就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自然界的天空、大地和个别的生命体,而是具有密切关系的、相互依存的三个我们今天所讲的既具有自然属性又具有社会属性的主体,“天”和“地”人格化了。
中国哲学中的天、地、人这些概念及其之间的关系在历史的进程中不断进入到芸芸众生的思想之中,也表述在小说文本的字里行间。诸子百家当然是最丰富的,而且在思想论和方法论上已经创造出了不同的流派。《春秋》三传、历代史书及后来的名家经典、政论篇章,也多有哲学问题贯穿,启迪和教育后人。即使是八股时文,大凡优秀的科举高中者,“代圣人立言”,中国哲学的问题也是举子们思考和写作的重要内容。诗词歌赋文章小品也时时可见哲学的命题,屈子的《天问》,《诗经》中的《七月》,唐代大小李杜、韩柳的诗文,宋人苏辛词、黄陆诗,到元明清载道明道的戏曲小说,让人品咏再三,感叹不已,不仅是因为其中的情感、意境、故事和韵文表现出来的文学美,更是作品中的思想观念,是其中为人处事、治国理政的思想和道理,是其中的哲学内涵。即以章回小说论之,《三国演义》突出强调“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既是历史政治的视野,也是以自然天地之理来分析社会世道的变化,其中历史循环论的正确与否暂且不论,但绝对是一种历史哲学的世界观。《水浒传》不论讲它是英雄世界还是强盗绿林,还是说它是农民起义还是投降主义,都生动地反映了社会上不同阶级、阶层人们之间利害取舍、伦理关系的,这些人生观、价值观也正是哲学的基本内涵。《西游记》更是形象地把天上、人间、地下(水下)诸路人、神、妖、魔统统汇聚起来,以人的关系的视角来看待一切,阐述天、地、人之间和神、魔、人之间的基本关系问题,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都直露无遗。《红楼梦》的哲学问题可能是比较丰富的,其中最重要的是“盛极必衰”的历史哲学,想说明的是人的社会性终究归属于更为广泛更有力量的自然性、自然规律,人算比不得天算。还有更多数量的话本和拟话本,作者并不一定是思想家、哲学家,甚至也不是思想者和哲学者,写这些小说故事时根本就没有想到虽然早已存在而后来才有的哲学概念,但是我们都可以在这些故事中,在人物的命运中,发现种种具有千差万别的人生难题和解决这些难题的“三观”智慧,发现经典哲学的传承,这都是哲学问题。
《金瓶梅》的哲学问题有与其他同时代的各类小说共同的,也有它独特的。共同的哲学问题,也是全书最直接提出来的就是“因果观”。这种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贯穿全书,各种人物命运无一能逃出这一逻辑。《金瓶梅词话》的三篇序跋都直接指出了小说的这一命题。
欣欣子《金瓶梅词话序》中说得很明白:“祸因恶积,福缘善庆,种种皆不出循环之机。”所谓“循环之机”就是因果报应的规律。廿公《跋》也说得透彻:“中间处处埋伏因果,作者亦大慈悲矣。”再看东吴弄珠客的《金瓶梅序》:“余友人褚孝秀,偕一少年同赴歌舞之筵,衍至霸王夜宴,少年垂涎曰:‘男儿何可不如此!’孝秀曰:‘也只为这乌江设此一着耳。’同座闻之,叹为有道之言。若有人识得此意,方许他读《金瓶梅》也。”
因果论是传统社会中广泛流行的哲学观念,有很多的文学作品,特别是今天我们还能看到的宋元以后的戏曲小说大众艺术,往往是用因果关系来设计作品的结构和故事,目的在于劝诫人们止恶行善。《金瓶梅》是一部世情小说,写现实生活的,自然也就选择因果论作为自己的人物观、故事观,也就是人物的命运逻辑和故事的现实逻辑。
《金瓶梅》独特的哲学问题讨论的是人的生死问题和与生死密切相关的自然的人与社会的人的关系,即天与人的关系。
二、《金瓶梅》哲学问题的核心是“天道”
兰陵笑笑生在全书结尾的下场诗中讲得很清楚,他为自己的这部小说作了一个十分重要的总结:
闲阅遗书思惘然,谁知天道有循环。
西门豪横难存嗣,经济癫狂定被歼。
楼月善良终有寿,瓶梅淫佚早归泉。
可怪金莲遭恶报,遗臭千年作话传。
“天道”是因果循环的主体,因果循环只是“天道”的一种裁决形式,是“天道”表示存在的一种方式。《金瓶梅》中的主要人物西门庆、陈经济、潘金莲、李瓶儿、春梅都是违背“天道”而受恶报的人物;而吴月娘、孟玉楼则是因为顺从“天道”守善而得到善报的人物。全书所有的人物故事及其命运归属都在演绎这个“天道”,因此“天道”是《金瓶梅》哲学问题的核心,它既是小说世界观的核心,也是小说人生观、价值观的标准,是恶因恶果与善因善果的分界线。顺着“天道”这个核心和标准去观察书中的所有人们,自然而然地可以看到两支不同的队伍:遵守“天道”者,总是节制着自己的人生欲望,违背“天道”者总是放纵自己的欲望。用潘金莲的一句话来解释,就是“算得着命,算不着行”(46回),潘金莲直率而又肆无忌惮地说出了她这一类人的“三观”,生动地阐明了一种人生哲学:命运,命和运不是一回事,命是天定的,运是自己选择的,也就是行。如果用传统的哲学观来看,要顺从“天道”,也就是顺从“天命”,个人的行为的“运”必须和“命”保持一致,才会有自己符合天道的命运,至于命运将会如何,“运”就要听从“命”的安排,才有可能是好的命运。否则,就会得到恶报。而潘金莲一类的人是认命却不从命的人,承认有“命”,也就是有“天道”,但我行我素,该怎么活就怎么活,不受任何“命”的约束,被吴月娘说是个“原不是那听佛法的人”(51回),结果身遭恶报“遗臭千年”。还可以用西门庆那段有名的话来解释:“咱闻那佛祖西天,也止不过黄金铺地;阴司十殿,也要些楮镪营求。咱只消尽这家私广为善事,就使强奸了嫦娥,和奸了织女,拐了许飞琼,盗了西王母的女儿,也不减我泼天富贵。”(57回)西门庆总认为自己有钱,有钱就可以不怕“天”,不怕“天道”,结果遭到“天道”的恶报,死得十分痛苦悲惨。
那么,作者铺排出这么一些人物命运逻辑,要说明的是什么“天道”呢?
中国古代经典哲学已经认识到人有两种属性,用今天的话来说,一是自然属性,一是社会属性。古人不讲自然界的自然属性,但认为自然属性是天生的,与生俱来的,古人称之为“天性”。“天性”支配着人的自然成长,人的成长与自然界所有的物质,比如五谷六畜、阴晴圆缺、风霜雪雨、春夏秋冬的变化一样,都有自己的规律和规则,这个就被称为“天道”。社会属性是后天的,是一个人在特定的成长环境中获得的,被称为“人伦”,或者说是“伦理”。“伦理”约束着人们为人处事的言行,道德是伦理实践的具体标准,如仁义礼智信、忠恕孝悌慈等,这也是有规律和规则的,中国哲学把它也归纳到“天道”或“天理”。
早期经典哲学家,并没有把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分析得很清楚,这种有意或无意的模糊方法也许正是中国古人认识世界、解释世界、利用世界的一种方法。“天”的内涵就十分丰富:
在中国文字中,所谓天有五义:曰物质之天,即与地相对之天。曰主宰之天,即所谓皇天上帝,有人格的天帝。曰运命之天,乃指人生中吾人所无奈何者,如孟子所谓‘若夫成功则天也’之天是也。曰自然之天,乃指自然之运行,如荀子《天论篇》所说之天是也。曰义理之天,乃谓宇宙之最高原理,如《中庸》所说‘天命之为性’之天是也。《诗》《书》《左传》《国语》中所谓之天,除指物质之天外,似皆指主宰之天。《论语》中孔子所说之天,亦皆指主宰之天也。[2](P55)
由此解释的“天”而得来的“天道”观,自然很有权威,包括“天性”“天命”“天理”等概念的内容也随之权威起来,丰富起来。
孔子是讲天命的。“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3](P177)范蠡有云:“天道盈而不溢,盛而不骄,劳而不矜其功。夫圣人随时以行,是谓守时。天时不作,弗为人客,人事不起,弗为之始。”[4](P641)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对“天道”作了很大篇幅的解释,说明天道就是天的规则,这个规则,不仅有人们在长期的农业劳动中发现的自然规律,也有人们通过自然规律而认识到的社会规律。所以这个规则是永恒不变的,其中既有天性,也有人伦:“天之道,有序而时,有度而节,变而有常,反而有相奉,微而至远,踔而致精。一而少积蓄,广而实,虚而盈。圣人视天而行。”[5](P333)因此,人们要依天道而行,君王要视天道而治。“为生不能为人,为人者天也。人之人本于天,天也人之曾祖父也。此人之所以乃上类天也。”人是上天造就的,所以人的一切都必须遵守“天道”。董仲舒的“天道”观有一系列的上天规则:“人之形体,化天数而成。人之血气,化天志而仁。人之德行,化天理而义。人之好恶,化天之暖清。人之喜怒,化天之寒暑,人之受命,化天之四时。”[5](P318)董仲舒的这套学说,当然集纳了他之前诸多先贤,如孔子、孟子等人的说法。这其中,董仲舒的目的在于阐明君权天授,“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一国则受命于君”[5](P318),以定国尊。用当时的人们无法清楚地认知的自然之理来说明社会之理,强调人伦纲常。这种哲学思想及其方法论影响了后来两千年的中国,到明清时期已经浸透在知识分子读书作文、科举选官而盛行的“代圣人立言”的八股时文和民众文化的戏曲小说以及人们从小就开始熟记的儿童启蒙读本《三字经》《弟子规》和《增广贤文》之中。
《金瓶梅》展开的故事,是一个按照传统哲学思想以“天道”观中的善恶有报的因果论和乐极悲生论来治理社会重病的故事。西门庆、潘金莲这些所谓的“恶人”得的病不轻,明朝社会得的病不轻。他们的命运轨迹,在与善者吴月娘、孟玉楼的命运轨迹形成对比的同时,都在演绎中国先贤哲人提出来的哲学观,人都必须遵循孟子说的“顺天者存,逆天者亡”[6](P168)。欣欣子在序文中也有云:“故天有春夏秋冬,人有悲欢离合,莫怪其然也。合天时者,远则子孙悠久,近则安享终身;逆天时者,身名罹丧,祸不旋踵。人之处世,虽不出乎世运代谢,然不经凶祸,不蒙耻辱者,亦幸矣。吾故曰:笑笑生作此传者,盖有所谓也。”
三、《金瓶梅》哲学问题的来源是诸子哲学
目前学界认定,《金瓶梅》最早的版本是《金瓶梅词话》,成书时间约为嘉靖中期至万历初年。故事所写的空间乃为当时商业经济和市民阶层最为发达的中国东部运河山东段,具体的地点是临清及附近。这个时间与空间上都是商业经济和城市文化发展的结点,人们生活和思想都与传统不同,因为人们的“三观”在经济的推动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们对欲望的追求与传统有了很大的差别,形成了冲突。《金瓶梅》所反映的正是这种现实。《金瓶梅》不是一部哲学著作,而是一部通俗小说。它不研究哲学的本身,当然也不研究“天道”本体,它的哲学问题是通过生动的形象、情节和讲述的人物命运来体现的。《金瓶梅》中的传统哲学,以“天道”观作为自己的核心,用以观照批判的对象,说教的力量是十分强大的。因为“天道”观不仅是中国古代哲学的世界观,也是民众认同的世界观,人们认识到“天道”中包含的“天性”与“人伦”之说,可以解释人们的“纵欲”与“止欲”的矛盾问题。
《金瓶梅》哲学问题的核心“天道”,及其衍生出来的一系列说法是从哪里来的呢?我们在追溯《金瓶梅》哲学问题的源流时,仍然可以在中国古代早期哲学思想家那里找到答案。
一是先秦时期道家的“道法自然”观,寡欲以保身、养生。老子是主张“道”的,所谓:“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漠!独立不改,周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吾强为之名曰大。”[7](P100)老子并没有把“道”置于“天”之后,他甚至接着说:“道大,天大,地大,王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处一。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7](P102)老子把天降格了,在这里的“天”是自然之天,是自然中的一部分。而道比天还重要,因为道是万物生成之母,也是天地之母。“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7](P174)但是,道也是法于自然,自然是最高级的主宰。老子虽然不说“天道”,却给后人一种逻辑,世上万物都必须效法道,这种道来自于自然,这里的自然,正如前文所论,不完全是我们今天理解的自然界,而是饱含了道的“本来的样子”在内的自然。这在哲学的思想论意义上开启了后人的“天道”之说。这种思想构建了他的“返朴归真”和“无知无欲”。“不上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盗;不见可欲,使心不乱。圣人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7](P14)老子这种愚民不知以达到无欲的哲学,过于理智,在当时“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现实就行不通,在后世就更行不通了。但是其中说到物欲的缘起和节欲在社会伦理中的意义以及“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终归自然的思想却是启发了其他的哲学家,并极大地影响了后人。《金瓶梅词话》中也就有了不少说教,如:“宽性宽怀过几年,人死人生在眼前。随高随下随缘过,或长或短莫埋怨。自有自无休叹息,家贫家富总由天。平生衣禄随缘度,一日清闲一日仙。”(第49回)
与老子不一样,庄子把寡欲同贵生、养生结合起来。庄子追求“逍遥游”,但他深知“以有涯随无涯,殆已”,追求保身、全生、养亲、尽年。[8](P42)庄子继承老子的“道”,遵循“道法自然”的思想。庄子认为人生有涯,实质上是肯定人的自然属性,所以其所说的保身、全生、养亲、尽年,讲的是自然之身的保养,与儒家通过寡欲来获得道德的完善不同。“夫富者,若身疾作,多积财而不得尽用,其为形也亦外也。夫贵者,夜以继日,思虑善否,其为形也亦疏矣……今俗之所为与其所乐,吾又未知乐之果乐邪?果不乐邪?”[8](P258)轻欲重生,止欲而贵生,这些思想对后人的影响非常大。《金瓶梅词话》中的《四季词》宣扬的就是寡欲养生的境界,而书中不少的说教也是宣扬延年保命。所以欣欣子《序》中说:“合天时者,远则子孙悠久,近则安享终身;逆天时者,身名罹丧,祸不旋踵。”
二是儒家的中庸之道,中和节欲观,寡欲以养心。儒家从孔子开始,讲“道”。在《论语》中有数十次说到“道”,不过《论语》中的“道”词义比较复杂,说到道德、规矩、规律、制度、礼义的不多。但有一点必须明白的是,孔子的学说中,不直接讨论“天道”。“子贡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3](P47)但有时会和“天”放在一个语境中说明问题,比如“天下有道”之类,认为天道就是礼制,是他崇拜的周礼,也是一种规矩、规则:“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3](P174)这个“天下有道”,从理解上看,实质上也是说整个社会有礼有制的问题,周天子掌握实权,诸侯个个听命,制度、礼仪、规矩才会有人遵守。此处的“天”,是指社会、民众,不是自然的天。而他的“畏天命”中的“天”,还有“五十而知天命”中的“天”是一种意志,“天命”是自然的规律和社会的规则的结合体,既有自然之伟力,也有社会之约束。孔子自己就很守这个规矩:“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3](P13)孔子从四十岁开始,不惑、知天命、耳顺、从心所欲,懂得了“不逾矩”,知规律,守规则,不乱来。儒家不主张禁欲,“食色,性也”[6](P255)。但不走极端,反对过头、过分。强调用伦理规范来约束人的男女关系及其各种欲求,同时又使这种约束作为一种修养来促进人的道德的完善。“养心莫善于寡欲。其为人也寡欲,虽有不存焉者,寡矣;其为人也多欲,虽有存焉者,寡矣。”[6](P339)寡欲存善,多欲失善,养心在于存养善性。“子曰:‘《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3](P31)孔子首倡“中庸”,并把它提高到最高道德的高度,以至于后来有“中庸之道”一说:“子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3](P65)儒家学说,虽然有鲜明的政治内涵,但其中讲究中庸之道,对于人的自我修养和为人处事,仍然有它独到之处。这就有了后来的中和节欲观,有了寡欲以养心的主张。朱熹深得孔子学说的精髓,《中庸章句》开篇,就把孔子在《论语》中没说的“天道”说透了,把孔子的“天命”与“天”和“道”紧密地结合了起来:
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无一不本于天而备于我。)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道者,日用事物当行之理,皆性之德而具于心,无物不有,无时不然,所以不可须臾离也。)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是以君子既常戒惧,而于此尤加谨焉,所以遏人欲于将萌,而不使其滋长于隐微之中,以至离道之远也。)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喜怒哀乐,情也。其未发,则性也,无所偏倚,故谓之中。发皆中节,情之正也,无所乖戾,故谓之和。大本者,天命之性,天下之理皆由此出,道之体也。达道者,循性之谓,天下古今之所共由,道之用也。此言性情之德,以明道不可离之意。)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9](P17)
再接下来读《中庸》几句,就可以明白《金瓶梅》的哲学意味:“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9](P18)从《金瓶梅词话》的道德说教主旨看,西门庆、潘金莲这类人都坏在反中庸而纵人欲,且是肆无忌惮地纵欲。欣欣子《序》评论说:“譬如房中之事,人皆好之,人皆恶之。人非尧舜圣贤,鲜不为所耽。”但应“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东吴弄珠客在《序》中说,不可似“金莲以奸死,瓶儿以孽死,春梅以淫死”,“奉劝世人,勿为西门之后车可也”。《金瓶梅》序跋中的这些观点,正是《中庸》中所谓的“中和”节欲观的具体运用。
三是杨朱一派的适欲顺生观。杨朱生活于墨子与孟子年代之间。冯友兰认为老庄之学中也有杨朱之余绪[2](P179)。当道家强调“道法自然”,寡欲以保身、养生,儒家强调中庸之道、中和节欲观、寡欲以养心之时,杨朱的适欲顺生观也是一种很好的哲学补充。养生、养心和顺生,正是流传两千年并普遍而又顽固地存在于人们生存观念之中的哲学思想。
杨朱之学没有保存自己的文本流传下来,但有很多哲学观主要保存在《吕氏春秋》的《重己》《贵生》《情欲》等篇中[10],也有保存在《列子》[11]中的。冯友兰认为《吕氏春秋》中保存的这些片断比较可信,主要是阐述了杨朱的适欲顺生哲学思想。而《列子》中的《杨朱》不可信,其中的极端享乐主义的哲学观与《吕氏春秋》中的适欲顺生观大相径庭,不会是出自一人之手:“今《列子》中《杨朱篇》乃魏晋时人所作。其中所言极端的快乐主义亦非杨朱所持。”[2](P168)这个判断很有道理。及时行乐的思想在先秦时期不是主流,而在魏晋时期倒是时代的一种特征和文人的一种时髦。杨朱有一句很出名的话,“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2](P169),即不为天下而只为自己的“贵己”与“轻物重生”。杨朱认为人欲与人的生命存亡密切相关:“凡生之长也,顺之也。使生不顺者,欲也。故圣人必先适欲。”[10](P7)“适欲”就是适当的、合乎自然规律的、并不妨碍人的生存的欲望,适当的欲望,适宜的欲望,不是随心所欲,更不是纵欲。“适欲”是有节制地行欲,因此,“适欲”就是“节欲”。“圣人深虑天下,莫贵于生。夫耳目鼻口,生之役也。耳虽欲声,目虽欲色,鼻虽欲芳香,口虽欲滋味,害于生则止。在四官者,不欲利于生者则弗为。由此观之,耳目鼻口不得擅行,必有所制,譬之若官职不得擅为,必有所制。此贵生之术也。”“所谓全生者,六欲皆得其宜也。”[10](P14-15)在杨朱看来,贪心与欲情是人天生的,人要生存,必须节制天生的贪心和欲情。圣人修节止欲得到的就是不过节之情,于是得以生存;而未能得生存者是因为不能修节止欲,失去了不过节之情,放纵了欲望。“俗主亏情,故每动为亡败。耳不可赡,目不可厌,口不可满,身尽府种,筋骨沉滞,血脉壅塞,九窍寥寥,曲失其宜。虽有彭祖,犹不能为也。”[10](P16)西门庆纵欲而亡的惨状不正是如此么?料事如神的吴神仙也无可奈何,“不能为”也。
除了道家和儒家这两个在中国古代占主流地位的哲学观,还有佛家的哲学观。佛教的“色空观”是佛家哲学中十分重要的世界观,而佛教的“因果论”不仅极大地影响到了中国本土的经典哲学,丰富了道家和儒家的“因果”思想,也直接构建了中国民间大众的世界观及其思维方式。所以中国社会的“三观”也多以此三家马首是瞻。到了宋代及此后,儒道佛(释)三家的思想论和方法论形成了宋明理学的哲学基础。印度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在影响中国本土哲学的同时,也得到了中国哲学的浸染,中国的佛教已经是中国化了的佛教,远不是单纯的原始佛教哲学。原因很明白,一方面,佛教中人的文化根底是中国的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另一方面,宗教中人已经根据社会的需要努力将三教合一。而在民众当中,更是难以分清楚各教之间的区别,多以捡拾各家有用的语录信条适用而已。《金瓶梅》 中,中国化了的佛教哲学思想一直在左右着作者塑造书中的各色人物,善者多信佛,如吴月娘。①
四、《金瓶梅》的哲学问题反思
《金瓶梅》中的哲学问题来自于古而有之的中国哲学思想,或者说是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它同样具有重要的文化价值,对我们今天的生活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这也是《金瓶梅》的审美价值所在。就以人们所说的书中大量的道德说教来论,《金瓶梅》的道德说教是通俗的、大众的,有落后、消极的成分,但其道德说教思想基础是中国哲学命题,作为一种长期积累的文化思考,对人类的文明进程仍不失其重要的现实意义。②
显然,明朝中后期社会经济的发展、市民阶层的壮大和新的思想的扩展都对人们的生活带来从未有过的大变,特别是在商业经济率先发展的东部京杭大运河沿线的城镇,这种表现更为突出。“山势使人塞,水势使人通。”大运河交通不仅便利了朝廷漕粮的输送、官员的巡走和社会物质的南来北往,弥补了中国东部交通东西方向有余而南北方向不足的短板,更重要的是促进了人员的迁徙和城镇的发展以及由此而迅速出现的思想的更新。当时,传统并没有逝去,甚至还谈不上衰落,只不过它迎接了又一轮更大的挑战。社会在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上,在人们的思想和价值观上都出现了新的自然转型或者说新的分野和矛盾冲突。传统的依然传统,保持着原有的保守、稳定与高高在上,而新的事物与新的人物、新的思想、新的行为虽然步履蹒跚,但是在发展欲望的支持下,总是不顾一切地冒尖和表演出来。《金瓶梅》就是这种大变的真实再现。③
旧的传统总是滞后的,不一定代表了发展的趋势,它一定要受到新的现实的扬弃,在受到批判和淘汰的同时,又因为是历史的积淀,是反复经受过各种时代的检验、淘洗而流传下来的,是文明发展的结晶,也是文明发展的必然,有它自己的合理性,其中的精华还有它的永恒性。新的变化总是耀眼的,但耀眼的并不都是金子,不一定都有积极性,它还需要沉淀,需要历史的考验和证明,需要过去的传统、今日的现实和未来的必然对它的扬弃。于是在出现《金瓶梅》的现实的同时,必然出现兰陵笑笑生。兰陵笑笑生不论是一个人,还是一群人,都是很了不起的小说作家。他(们)洞察了现实的大变,也洞察了现实中的种种人以及他们的内心;他(们)又有相当深厚的传统文化认知,不仅有着和其他小说家同样的道德伦理情怀,更有着很多小说家没有的或者说不如的哲学(智慧)思辨。他(们)写《金瓶梅》并不在于欣赏还是批判西门庆、潘金莲,也不在于一般的道德说教,分辨孰廉孰耻,指出谁对谁错,而是借这么一段故事和几个人物的命运,对社会指出一个终极的关乎人自身命运存亡的认知问题,这个问题是一项大学问,是一个大智慧,用今天的话来说,即人自身的哲学问题。人的人生中最大的问题就是如何认知自身,我们应该从中得到启发。
一是认知生命与欲望之间关系的合理性。《金瓶梅》 的作者面对着一个由于理性压抑而扭曲了人性但又由于经济发展而欲望膨胀的世界,传统的伦理秩序受到冲击,传统的道德规范也失去了曾有过的约束人心人行的力量。“文以载道”“文以明道”,作者的道德说教当然可以宋代理学作为标准,也可照搬明代官方理学的文本,但作者选择古代经典哲学关于生命和欲望之间关系的辩证说法,反对贪酒贪色贪财使气以节欲,节欲以保身,实现生命与欲望的和谐。
实现欲望,可以满足人的自然的生理需求和社会的心理需求,但是,实现欲望也有可能摧毁人的意志和肉体。肉体的成长与死亡,是自然的规律。人的欲望是意识活动,是无限的,而且会不断膨胀。以有限的自然生命之体去追求无限的欲望,必然导致肉体的崩溃。寡欲、节欲和适欲的意义正在于此。生命与欲望之间关系的合理性,就是合乎自然规律性和社会的伦理要求,合乎“天道”。《金瓶梅》正是要说明这么一种人生观、价值观。其批判西门庆毒害人命,占人妻女,腐蚀官吏,得财枉法,还是属于表层次的道德批判,深层次的批判在于他对自身的自毁,他那难以抑制的纵欲在破坏社会伦理的同时,也在消耗甚至摧残他自己。他求胡僧给他那百十粒春药丸如同他以肉体生命为赌注的筹码,以纵欲来消耗自己生命的赌博,每一次都是失败的,用去一粒春药,就是失去一个筹码,最后必然药尽命丧。作者为了强调这一点,对西门庆临死时的惨状作了突出的渲染(潘金莲、李瓶儿、春梅这些纵欲者的死,也一个个凄惨吓人)。我们在这里并不是讨论这种死是不是恶报和这种恶报是进步还是退步,而是必须客观地肯定这种死对生命与欲望关系做出的合理的解释。之所以肯定它是合理的,是因为这种解释在“封建社会”和“封建社会”前前后后,在西门庆、东门庆、南门庆、北门庆身上都是合乎事物的普遍规律而具有积极意义的。
二是认知自然人与社会人之间关系的和谐性。人与自然之间关系和谐地发展,是人类社会永恒的哲学命题。人与自然的和谐,不仅是人与动物世界、植物世界,与山地河流、海洋极地之间符合自然规律的共生共存,也是社会的人与自然的人、欲望的人与肉体的人之间合乎规律的生存与发展。人本身就有自然属性,人就是自然中的一员,人应该通过自己的理智控制自己超越自然之体的承受限度的欲求行为,实现健康生存。尤其是在一种束缚人的自由发展、完全扼杀人的自然欲求的时代行将结束,而新的伦理道德尚未成熟之时,人的欲望在财富与权力的支持下,必定会肆无忌惮地喷涌出来,人与自然和谐的命题就更为重要,肯定人的生活欲求与自然生命的和谐就具有了现实的意义。四百年前的明代社会,不可能有我们今天这样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深刻的认识,但是中国古老的哲学在上古时期就已经用朴素的智慧在探讨这些重大的命题。《金瓶梅》的道德说教运用中国哲学智慧作为指导,通过若干小说人物及其命运故事来提出问题并对人们进行告诫,一方面具有了阐释自然的人与社会的人之间应有的和谐关系的哲学意义,一方面又有很大的社会实践意义。尽管书中的节欲观带有浓厚的传统道德色彩,但节欲并不是禁欲,进行道德说教不等于扼杀人的天性。我们不否认明清时期以官方理学为武器的道德说教对人的生存与发展的束缚,有的甚至具有压抑人性解放和个性发展的弊病,但是针对一伙在金钱、权力和肉欲的支配下可以失去理性的人群,不能把人应有的自我约束和社会应有的理性都看作是封建的枷锁。
强调享受生活的权利,古已有之,也是现代观念,以此观念去批判中世纪西方的禁欲主义和东方的以维系天命纲常为目的的禁欲思想是对的、进步的。但即使在现代社会,享受生活的权利也并不等于无节制的纵欲。恰恰相反,享受生活更重在对生命的珍重,古老的、传统的寡欲、适欲、保身、养生、养心、顺生的哲学观是古人留给我们的生活智慧。因此,我们在批判禁欲主义对人的正当生活欲求无情遏制时,不能把人的纵欲行为说成是积极的、进步的、合理的,否则,就等于是从理论到实践上否定了我们作为自然人与社会人结合体的价值。强调个性的解放,褒扬爱情自由和婚姻幸福,不能等同于颂扬随心所欲地违反自然规律和社会伦理的行为。否则,悖论的价值观不仅毫无意义,而且会使新的文明陷入一个新的否定怪圈之中,难以做出合理的解释,不利于个体的人健康地成长和若干个体的人结成的社会自身合乎规律地发展。
五、结语:应从哲学层面充分认识《金瓶梅》的价值
《金瓶梅》的哲学问题给它带来了丰富和有意义的价值是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的,它带给我们的启示通过讨论生命与欲望、自然的人与社会的人的关系问题,直接说明的是哲学的基本问题,是人的自身生存与发展的智慧。如果不从哲学的角度去审视《金瓶梅》,《金瓶梅》不仅是被污化的问题,其许多有意义的价值会被书中百分之一篇幅的性描写及其引起人们的道德批判所淹没,而且会产生很多悖论:今人评价《金瓶梅》,从文学史小说史的角度,肯定的多,否定的少;从道德和普通人阅读效果的角度,则否定的多,肯定的少。三十年前,我们谈论《金瓶梅》,惊讶的多,认知的少;今天谈论《金瓶梅》,不知道的少,不想看的少,但不以为然的多,依然蔑视和污化的多。这些悖论,只从文学分析的角度不能解决阅读效果的问题;只从文学理论、小说理论的角度不能解决认同效果的问题;只从道德批判的角度,不能解决如何实事求是地面对小说创作、文学审美、道德规范等诸多的问题。如果我们从哲学的角度(包括我们还可以展开讨论的美学角度)去审视《金瓶梅》,把它的哲学问题提到现实的议题上来,这些悖论是可以得到解决的。至少,我们可以从《金瓶梅》哲学问题的角度去更加关注人自身的生存和发展的问题,关注人的需要与需要伦理的关系问题。一部小说,能够让读者去观照这个世界,观照人自身的生存与发展,认知自己应该处理好作为一个自然人的需要与作为一个社会的人的需要的伦理的关系,这个意义和价值就非常大了。
注释:
①《金瓶梅》中的哲学问题不仅有哲学的内涵,还有丰富的佛教、道教内涵。这里就不再多作分析,请参见本人发表在《争鸣》1993年第4期上的《〈金瓶梅词话〉对理学和宗教的选择》,此文已经收进江西人民出版社2014年9月出版的《陈东有〈金瓶梅〉论稿》。
②关于《金瓶梅》中的道德说教的研究,请参见本人发表在《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3期上的《〈金瓶梅词话〉道德说教中的哲学命题》,此文已经收进江西人民出版社2014年9月出版的《陈东有〈金瓶梅〉论稿》。本人的《〈金瓶梅〉文化研究》(《古典文学知识》2003年第1期)也有相关探讨。
③请参见本人的《运河经济文化与〈金瓶梅〉》(《萍乡教育学院学报》,1989年第3期);《再论运河经济文化与〈金瓶梅〉》(《江西大学学报》1991年第2期);《〈金瓶梅〉的平民文化内涵》(《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期)。三文皆收入《陈东有〈金瓶梅〉论稿》,江西人民出版社2014年9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