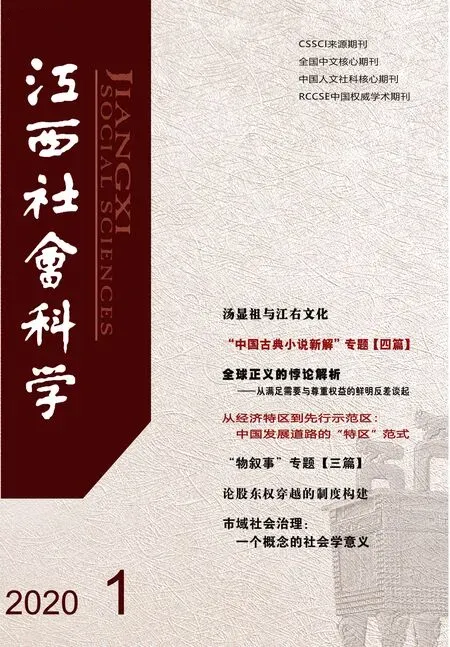建构短篇虚构叙事“谜”的分类学:面向物的视角
短篇虚构叙事之“短”,使该文类更善于用来表达生活存在的瞬间,展示刹那间的顿悟或困惑。缘此,很多理论家都认为,短篇虚构叙事这一文类的核心是包含一个待解的“谜”(mystery)。然而遗憾的是,鲜有理论家对短篇虚构叙事中的“谜”加以系统研究,从而成为这一文类研究中缺失的一环。那么,短篇虚构叙事中的“谜”有哪些可能的再现方式?笔者借鉴西方新近出现的“面向物的哲学”(object-oriented philosophy),尝试提出并分析短篇虚构叙事中“谜”的四个基本类型。
一、短篇虚构叙事中的“谜”
已经有很多作家和批评家指出,短篇虚构叙事(the short narrative fiction)的“短”不单是一个篇幅长度的问题,更是定义了短篇叙事的文类特征①。与长篇小说(the novel)不同的是,正是因为短篇叙事的“短”,让其更擅长于通过描写生活的瞬间,来揭示生活中刹那间的魅力所在,也就是透过再现“生活切片”(slices of life),来暗示生命与存在的神秘之处。关于这个神秘,短篇叙事理论家和作家们都将其与“真实”(real)联系,这样,短篇虚构叙事的核心特征就是通过描写生活片段向读者展示神秘的“真实”所在。如胡利奥·科塔萨尔(Julio Cortazar)认为,短篇小说最重要的一个“常数”是在描述真实或者虚构的事件时,有一种超越事件本身的神秘属性。[1](Pxvii)短篇小说研究专家迈克尔·特拉斯勒(Michael Trussler)也表达过类似的观点:“如果长篇小说探索的是社会现实,那么短篇小说关注更多的则是私密的、也许是超自然的(因而也更具“神秘性的”)现实。”[2](P239)海明威著名的“冰山理论”正好诠释了短篇虚构叙事的这个特征。在他看来,“冰山运动的尊严之处就在于它只有1/8露出水面”[3](P1201),换句话说,好的作品应该只再现事物的极小部分,而将其真实隐藏起来,让读者自己去探索。再如,20世纪七八十年代风靡美国的极简主义短篇小说家雷蒙德·卡佛(Raymond Carver)在一次访谈中这样说道:“每个故事都有神秘之处,表面下别的事情正在发生。”[4](P6-15)而这表面下发生的“别的事情”也就相当于海明威所说的隐藏在水面下的冰山。借用英国V.S.普里切特(Pritchett)对短篇小说的定义,即短篇小说是“从眼角匆匆瞥见的东西”。卡佛认为,短篇小说家的任务就是“全力以赴给那一瞥赋予意义”,使用“智慧和文学技巧”来告诉读者“事物的真相,以及他本人怎么看待这些事物”。[3](P1196)因此,如果玛格丽特·阿特伍德是正确的,即作家必须要有一种讲述的急迫感(“这是我必须要讲给你听的故事”),那么,短篇小说想要急迫讲述的就是作家体悟到的真实,正如英国著名短篇小说家伊利莎白·鲍文所言,作家创作是因为他发现并沉迷于某种“真实”,迫不及待地“想要其他人也意识到”。[3](P1195)这样,在短篇小说这一叙事文类中,作家往往是通过营造并解决一个“谜”来告诉读者他心目中的“真相”。
关于短篇小说的这一特征,美国知名短篇小说理论家查尔斯·E.梅(Charles E.May)说得更为明确,他认为短篇小说最重要的主题就是“瞬间神性……神秘而梦幻般的显现”[5](P139]。所谓“神性”(deity),其实就是不易捉摸但又最为深刻的“真实”。在他看来,短篇小说是“最充分的文学形式,让我们得以在某个最深刻的瞬间面对感知到的真实”[5](P142),他提出短篇小说可以揭示两类“真实”,即神性的真实(在这里,真实显现为充实多样)和荒诞的真实(在这里,真实显现为虚空)[5](P133)。在这里,梅虽然提出了“神性的真实”和“荒诞的真实”之分,但他没有对其进行深入讨论。本文借鉴近10年西方哲学界兴起的“面向物的哲学”(object-oritented philosophy),对短篇虚构叙事中“真实之谜”进行更详尽的讨论,并试图建构一个更宽泛意义上的短篇虚构叙事“谜”的分类学。
二、面向物的哲学
无论在哲学领域,还是文学批评领域,对“物”及其真相的探讨都是近十年的学术热点之一。“物转向”已经出现了多种形式:以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及简·本妮特(Jane Bennett)为代表突显“物”的主体性和能动性,以格拉汉姆·哈曼(Graham Harman)为代表突显“物”的本体实在性,以伊丽莎白·格罗兹(Elizabeth Grosz)为代表突显身体的“物质性”,以比尔·布朗(Bill Brown)为代表突显我们“物无意识”(material unconscious)的“物”理论,等等。虽然这些哲学家和理论家各自解决的问题不同,因而有不同的主张,但究其实质,他们均认为“物”具有独立于人类的生命及活性,在本体论上与人类完全平等,人类应该超越常规理性,对“物”进行想象。就哲学领域而言,2007年在伦敦大学金匠学院一次学术会议上首次使用的“思辨实在论”(speculative realism)成为这一热点的代名词,这一新兴的哲学流派主要代表人物有昆丁·梅亚苏(Quentin Meillassoux)、格拉汉姆·哈曼、雷·布雷希亚(Ray Brassier)、利维·布赖恩特(Levi R.Bryant)等。虽然这些哲学家的理论框架多样,甚至相互矛盾,但思辨实在论最重要的靶子就是梅亚苏所谓的后康德“关联论”(correlationism),即在通向物自体的道路上,总要凸显人类认识中介的作用,从而使哲学搁置本体论,转向认识论。思辨实在论认为,20世纪出现的很多转向,包括语言学转向、符号学转向、叙事转向、认知转向等,从某种意义上都是“关联论”思维方式的结果,因为这些“转向”共享一个理论预设,即客体不存在(或不可认知),而只是人类语言、文化、叙事或思维的建构。这种“建构”立场虽然在某种意义上打破了本质主义偏见,但也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对实在客体的关注,对客体而言是另一种形式的暴力和操控,其结果是让我们无视客体的存在,而单方面地凸显人类作为认识主体的重要性。思辨实在论试图绕开关联论陷阱:它相信物自体的存在,因此是“实在的”;它相信通过想象(而非理性)可以抵达物自体,因此是“思辨的”。这样,思辨实在论的主要任务就是最大限度摆脱人类理性框架的局限,去探索实在的“物”本体世界。当然,思辨实在论追求的“实在之物”(real object),有别于之前认为人类可以完整把握物世界的“幼稚实在论”(naive realism),是更为复杂的“物”本体存在方式。在通向“实在之物”的道路上,不同哲学家有不同重点,甚至不同立场。比如,梅亚苏、布雷西亚旨在想象没有人的“广大世界”(the Great Outdoors)的模样,认为物的存在前提是偶然性和非理性,哈曼的重点是指出物自体的无穷尽性,认为物与人、物与物之间的关系都无法穷尽物本身,而伯古斯特(I.Bogost)、布赖恩特等则将重点放在对物的运作、物与物互动关系的描述上。
与本文讨论话题最为相关的是哈曼的“面向物的本体论”(Object-Oriented Ontology,简化为OOO)。OOO是思辨实在论最重要的分支之一,试图解决“物的实在性到底是什么(或不是什么)”这一问题。与思辨实在论一样,OOO首先承认世间万物均有实在性,但这个实在性隐退于人类或其他物的认知,也就是说,无论是人类的理论或实践,还是物与物之间的相互作用,都无法穷尽物的现实,因为物“拒绝任何形式的因果或认知把握”[6](P183-203)。当人们以为已经完全认识或把握某物的时候,物会通过“坏掉”(broken)这样的方式来彰显其深不可测的现实。不难看出,OOO与俄国形式主义对文学性的认识有异曲同工之妙。俄国形式主义认为,文学性基于陌生化感受,“正是为了恢复对生活的体验,感觉到事物的存在,为了使石头成其为石头,才存在所谓的艺术”[7](P11)。换句话说,艺术就是通过恢复或刷新物的感性特征,让读者得以感觉到“真正的物”,而不是因日常语言遮蔽而被自动化的物。陈晓明也认为,“文学需要进入到人性更隐秘的深处,需要在生活变形和裂开的瞬间抓住存在之真相本质,文学性的意味只有在这样的时刻才涌溢出来”[8],在这里,“生活”与“真相本质”构成一对矛盾,“真相本质”只有在“生活变形和裂开的瞬间”才能得以捕获。这种说法与OOO在本质上也是相通的。
为了更清楚地解释物的表象与本相之间的差异,哈曼提出了“四面物”(quadruple object)这一概念,认为物有四个面向,即“实在的物”(real objects)、“感性的物”(sensual objects)、“实在的特征”(real features)和“感性的特征”(sensual features)②。其中,“实在的物”指人类和其他物永远都无法穷尽的物之本相,“感性的物”指物展现给认知主体的表象(也就是胡塞尔现象学中的意向之物),“实在的特征”指物区别于其他物的本质特征,“感性的特征”指物展现给认知主体的特征。在日常生活或日常语言表述中,我们往往不会注意到这四个面向之间的冲突[9](P140),但是,文学艺术(尤其是这里讨论的短篇虚构叙事作品)恰恰就是要在这些面向之间制造鸿沟和冲突,让读者看到物的真相③。
哈曼讨论了这四个面向之间最突出的四类冲突:(1)实在的物与感性的特征之间的冲突(在这里,通过感性的特征来指向实在的物);(2)实在的物与实在的特征(在这里,通过实在的特征来指向实在的物);(3)感性的物与感性的特征(在这里,感性的特征让物远离我们认识中的物);(4)感性的物与真实的特征(在这里,真实的特征让物远离我们认识中的物)。在哈曼看来,“实在的物”与“感性的特征”之间的冲突最令人着迷:比如铁锤坏掉之时就正好体现了“感性的特征”与“实在的物”之间存在着不可跨越的鸿沟,而这种鸿沟的出现是一种诱惑(allure),间接地指向物的真相。哈曼认为,“诱惑是所有艺术,包括文学的核心现象”[6](P183-203),也就是说,艺术旨在通过揭示或运作“实在的物”和“感性的特征”之间的冲突关系,来诱惑读者瞥见物的深不可测的实在性。但正如下文即将分析的那样,虽然运作“实在的物”与“感性的特征”这一冲突关系的确是很多短篇叙事作品中的“谜”的魅力所在,但其他三类冲突在短篇作品的“谜”诗学建构中同样重要。
三、短篇虚构叙事“谜”的分类学:四种类型
借鉴OOO区分的四类冲突,我们可以将短篇虚构叙事作品赖以存在的“真实之谜”分为两大类,即“积极的谜”(positive mystery)和“消极的谜”(negative mystery)。在第一大类中,物并不出现,小说通过描写物的感性特征或实在特征来暗指(allude to)难以直接接触的实在的物,无论成功与否,这都是一种肯定的、积极性的揭示,读者读完之后,会或多或少地瞥见“真实”,因此可称为“积极的谜”(positive mystery)。与此相反,在另一类“真实之谜”中,感性之物出现,通过大量的感性特征描写,使感性之物逐渐远离真实的物及真实的特征,这是一种否定的、消极性的揭示,读者读完之后,发现“真实”不是原来认知的那样,因此可被称为“消极的谜”(negative mystery)。值得注意的是,梅区分的“神性的真实”和“荒诞的真实”虽然与本文区分的“积极的谜”和“消极的谜”有一定重合之处,但并不完全一样。在梅的概念中,“神性的真实”指真实全部显现,而“荒诞的真实”指真实显现为虚空;在笔者的区分中,“积极的谜”是指作品通过某种方式给读者指向“谜”背后隐藏的(通常是不为人所知的)真实,但这个真实不一定全部显现(事实上,多数短篇小说的谜底都不会全部显现),而“消极的谜”是指作品通过某种方式否认读者通常认定的某种真实,却并不指向(也不暗示真实是什么)。
“积极的谜”又可细分为两类:(1)通过运作物的感性特征与实在物之间的冲突,来指向实在的物(积极谜-I型);(2)通过运作物的实在特征与实在物之间的冲突,来指向实在的物(积极谜-II型)。“消极的谜”也可细分为两类:(1)通过运作感性之物和感性特征的冲突,使物远离其实在(消极谜-I型);(2)通过运作感性之物和实在特征之间的冲突,使物远离其实在(消极谜-II型)。这样,关于短篇叙事作品中的“谜”,我们就能区分出四种不同的基本类型(在很多作品中,这些类型可能互相组合,从而形成更加多样的“谜”的形态)。下文将分别论述短篇虚构叙事中“谜”的这四种基本类型。
(一)积极谜-I型
在这类作品中,拥有真实之谜的物不直接出现,也就是不直接对读者在场,但该物的感性特征通过故事中的人物叙述者间接得到描述。用哈曼的术语来说就是,读者被这些感性特征所“诱惑”,(成功或不成功地)瞥见被隐藏起来的、“黑洞”一样的物的真相。
哈曼本人对美国恐怖作家H.P.勒夫克拉夫特(Lovecraft)的研究表明,该作家在描写神秘的超自然怪物(最为著名的就是他笔下的克苏鲁)的时候,往往并不让其直接出场,而是通过目击者-人物的转述,让读者获得关于它的感性特征,但又无法把握其本真所在,从而造成恐怖的阅读效果。笔者认为,雷蒙德·卡佛也是创作“积极谜-I型”的高手。在他的很多小说中,真正的谜被隐藏起来,读者只得到关于此物的只言片语,却无法见到物本身,从而实现其“表面下有别的事情在发生”的“少即多”的美学意图。比如,在《阿拉斯加有什么》(What’s in Alaska?)中[10](P83-93),我们读到的是两对夫妇(杰克-玛丽;卡尔-海伦)在客厅的闲聊。我们通过杰克这一近乎没有反思能力的人物的眼光,从闲聊中出现的26次“笑”,瞥见了卡尔-玛丽之间的非正常关系(说“瞥见”,是因为这种非正常关系从来就没有得到正面描写)。小说的最后,对于人物聚焦者杰克而言,他似乎明白了这种关系,但又无法确认并理解这种关系:这就构成了卡佛小说的“谜”。在卡佛另一篇小说《这么多水离家这么近》(So Much Water So Close to Home)中[10](P212-37),叙述者柯莱尔(Claire)的丈夫斯图尔特(Stuart)和三位朋友在河边发现了一具年轻女尸,围绕着女尸,这对夫妇开始激烈争吵,柯莱尔最后驱车200多英里去参加那个死去女孩的葬礼。毫无疑问,这篇小说中的核心谜团就是那个死去的女孩,但小说并没有直接描写这个女孩,而是通过夫妇俩的猜测和争吵,让读者隐约地瞥见关于女孩的(不确切的)真相。威廉·福克纳(William Faulkner)的《献给艾米丽的一朵玫瑰》(A Rose for Emily)是另外一个著名的例子。在这篇小说中,读者关于艾米丽的所有信息都来自小镇居民的讲述,纷至沓来的关于艾米丽的感性特征描写隐隐约约指向关于她的“真相”,但这个神秘的“真相”就像标题中那待解的“玫瑰”的含义一样,被深藏起来,吸引了无数读者和批评家去探索。
(二)积极谜-II型
在这类作品中,拥有真实之谜的物依然不出现,更有趣的是,该物的感性特征也不出现,仅仅给出高度抽象的实在特征(或许仅仅给出一个名字)去暗指物的真相。面对这样的谜,读者虽然受到诱惑,但很难发现真相,从而造成一种与世界割裂的阅读效果。
虽然并不是短篇虚构叙事作品,但塞缪尔·贝克特(Samuel Beckett)的戏剧《等待戈多》较为显著地体现了该类型“谜”的特征。在该剧中,什么也没有发生,谁也没来,谁也没去。剧中明确提及了戈多的存在(也就是全剧的谜),但没有对戈多的感性特征做出任何描写,仅凭“戈多”两个字,读者根本无法破解其真相。与《等待戈多》非常相似的是中国作家余华的先锋派短篇小说《十八岁出门远行》。在这里,对18岁的少年而言,出门远行的目的变成了谜,对这场远行的目的地所在,全文没有任何解释。开始的时候,第一人称叙述者在路上漫无目的地走着,“觉得自己应该为旅店担心”,接着想“搭车”,但这些都很难成为他出门远行的理由。读者知道叙述者“我”出门远行一定有某个目的,但这个目的一直隐藏在叙事的黑洞后面,不显真容:与《麦田里的守望者》不同的是,“我”这次出门远行似乎没有获得任何意义上的成长,因此这篇小说可被阅读为“反成长”小说。在这样的叙事中,读者已被告知物具有某种真相,受其诱惑希望在阅读中找到确切答案,而终不可得。
(三)消极谜-I型
在这类作品中,感性物出场,而且其感性特征如火花般给出,令人眼花缭乱,但这些特征叠加起来产生的效果,却是让读者更加远离了对该物的常规认知,与该物形成认知疏离,使之成为我们阅读中的谜团。这种效果有如立体画:将物打破,单独突显其组成部分的特征,这些特征合在一起,读者反而难以还原其整体并识别它[7](P40)。
英国著名科幻作家J.G.巴拉德(Ballad)的《淹死的巨人》(The Drowned Giant)是一篇典型的“消极谜-I”型叙事。在该小说中,巨人以一种不容置疑的真实面貌出场:“暴风雨后的早上,一个巨人的躯体给冲到了距这座城市西北5英里的沙滩上”[11](P233)。“早上”“这座城市”“5英里”等细节言之凿凿,将一个属于超自然世界的巨人引入现实世界。接着,巨人先是被描写为“看上去比一只在岸边晒太阳的鲨鱼大不了多少”[11](P233);随即,“他的身体闪闪发亮,就像一只海鸟的白色羽毛”[11](P233);最后,当两个渔夫壮着胆子靠近巨人,“巨人的脚立起来至少是渔夫身高的两倍,我们立刻意识到,这位淹死的庞然大物的体积和轮廓相当于最大的抹香鲸”[11](P234)。这是小说第一人称叙述者从远处对巨人的描写,在短短的一段中,巨人从不同角度分别被貌似客观地描写为鲨鱼、海鸟和抹香鲸,这样的密集而自相矛盾的描写让巨人的外形究竟是什么样子变成了一个谜。同样,关于巨人的来历,小说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些相互矛盾的线索。小说首先暗示巨人可能是从神话世界来到人间,但很快又让读者看到一张“被擦伤的肿胀的脸”,皮肤虽然已被漂白,但是“已经不再光亮”,而是沾满了“肮脏的泥沙”,“一团一团的海藻填满了他的指缝”[11](P238)。从下面看,巨人的脸已经“全然没有了风度和镇静,拉下的嘴巴和抬起的下巴……就像一艘触礁巨轮的船头”,他的脸因此变得就像一副面具,“疲惫而无助”[11](P239)。这样,读者心目中神话般不死的巨人形象被破坏无遗,巨人到底是谁,就成为文本中的不解之谜。用这种似是而非的方式来揭示巨人的真相,完美地实现了达尔科·苏文(Darko Suvin)所谓的科幻小说“认知间离”(cognitive estrangement)效果[12](P37)。与《淹死的巨人》类似的小说还有唐纳德·巴塞尔姆(Donald Barthelm)的《气球》(The Balloon)、赫尔曼·麦尔维尔(Herman Melville)的《书记员巴尔特比》(Bartleby the Scrivener)等。在《气球》中,悬挂在纽约上空的气球从多个不同角度被描写,最终在读者眼中变成了一个与常规认知完全不同的存在;在《书记员巴尔特比》中,对巴尔特比的聚焦描写,也让他越来越不像我们熟知的书记员,从而脱离了我们对他的认知把握。在这些小说中,无论是巨人、气球还是巴尔特比,作者否定了读者对他(它)们的惯常认知,让读者觉得他(它)们还有隐藏在认知之外的实在性,却并不引导读者去发现这些实在性,从而让他(它)们变得格外神秘起来。
(四)消极谜-II型
在这类作品中,感性之物在场,但不像“消极谜-I型”,作品运作不是物的各种感性特征叠加起来如何摧毁了读者对物的惯常认知,而是试图揭示这些感性特征都不是物的真实特征。也就是说,通过揭示物还具有一些不为人所见的真实特征,从而使物从我们的感性认知中逃逸,并被神秘化。
在纳撒尼尔·霍桑(Nathanial Hawthorn)的小说《我的亲戚莫里纳少校》(My Kinsman,Major Molineux)中,叙述者乡村少年罗宾初次进城,希望得到亲戚莫里纳少校的提携。他游走城里的大街小巷,四处打听莫里纳少校的住处,得到了各种关于莫里纳少校的虚假说法,最后发现莫里纳少校被一群暴民拖到街上游行。小说的最后,罗宾眼里(也就是读者眼里,因为读者跟随罗宾的眼光)的莫里纳少校的感性特征瞬间融化,但在其真实身份闪现后,小说并没有花笔墨来详细解释莫里纳少校的真实特征,而是马上结束,给读者留下了惊诧和回味的空间。美国当代著名短篇小说家德波拉·艾森伯格(Deborah Eisenberg)的后9/11短篇小说 《超级英雄之黄昏》(Twilight of Superheroes)与《我的亲戚莫里纳少校》如出一辙,透过一位乡下少年的眼光来观察居住在纽约的姑姑和姑父一家,他们看似光鲜,却在9/11后显示出他们虚伪和猥琐的真实面目。类似的小说还有乔伊斯的《阿拉比》(Araby)、康拉德的《黑暗的心脏》(Heart of Darkness)、卡佛的《大教堂》(Cathedral)等。在《阿拉比》中,叙述者“我”关于浪漫爱情的幻想在最后一刻被狠狠击碎,内心充满了愤恨和痛苦;在《黑暗的心脏》中,关于文明的神话消失在不为人所知的黑暗之中;在《大教堂》的最后,盲人罗伯特的形象在叙述者心目中变得不可思议地高大起来。在所有这些小说中,人/物都被先赋予了某种特征,然后让叙述者(或读者)发现,这些特征背后其实还隐藏着更深的不易觉察的真实特征。
四、结语与讨论
“谜”可以说是短篇虚构叙事的核心特征,但一直以来理论界忽略了对它进行充分研究。借鉴思辨实在论,尤其是“面向物的本体论”相关视角,本文区分了短篇虚构叙事“谜”的四个类型,分别是“积极的谜-I型”(即通过感性特征去暗示物的真相)、“积极的谜-II型”(即通过真实的特征去暗示物的真相)、“消极的谜-I型”(即通过感性特征去否定惯常认为的物的真相)、“消极的谜-II型”(即通过真实特征去否定惯常认为的物的真相)。这样,“积极的谜”和“消极的谜”分别对应我们阅读短篇虚构叙事的两种基本体验,即:“原来真相是这样!”“原来真相不是那样!”
毫无疑问,我们面对短篇虚构叙事的阅读体验往往更为复杂,这意味着我们在实际批评实践中还应该对短篇虚构叙事这四种基本类型的“谜”进行更加细致的分析,本文尝试提出这类分析的三个可能的维度:
一是四种类型的不同组合:叙事开始的时候可能采用积极型,即不让物出场,只通过人物叙述者的转述指向物的真实之谜,但随着叙事的发展,让物出场,随即转为消极型,通过大量描写物的感性特征来否定我们对其已经形成的印象,从而再度让物变得神秘起来。菲茨杰拉德的《了不起的盖茨比》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先通过尼克的转述指向盖茨比的真相,然后让他出场再否定前面业已建立的真相,到小说最后,读者(包括人物叙述者尼克本人)都无法获得关于盖茨比的全部真相。
二是真相揭示或遮蔽的程度:叙事中物的真相可能全部揭示出来,或者犹抱琵琶半遮面,或者完全遮蔽起来,这都会影响读者的阅读体验。乔伊斯《都柏林人》里几乎所有小说,最后似乎都揭示出了真相,但读者(或人物)又无法明确说出这种真相,这非常符合现代主义作品云山雾罩的叙述风格。
三是真相对谁显示或遮蔽:叙事涉及隐含作者、叙述者、人物、读者等多个实体,物的真相对谁显示或遮蔽(以及显示或遮蔽的程度)是作者修辞意图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产生不同的效果。如果真相只对读者显示,而对人物遮蔽,这就会形成反讽的叙述效果,比如,爱伦·坡的《一桶白葡萄酒》,叙述者蒙特莱赛因为福图纳特侮辱了他,于是设计将他活埋,这一看似合理的报复举动,背后隐藏的却是叙述者冷酷变态的真相,但蒙特莱赛对此毫无觉察,沦为叙事反讽的对象。
为了阐明以上观点,笔者以中国著名的盲人摸象故事为例进行简要分析。这个故事大家耳熟能详,大体是这样的:有四个盲人很想知道大象是什么样子。可是他们看不见,只能用手摸。胖盲人先摸到了大象的牙齿。他就说:“我知道了,大象就像一个又大、又粗、又光滑的大萝卜。”高个子盲人摸到的是大象的耳朵。“不对,大象明明是一把大蒲扇!”矮个子盲人大叫起来。“你们净瞎说,大象只是根大柱子。”原来他摸到的是大象的腿。而那位年老的盲人,却嘟嚷:“大象哪有那么大,它只不过是一根草绳。”原来他摸到的是大象的尾巴。四个盲人争吵不休,都说自己摸到的才是大象真正的样子。
这则寓言故事中,大象出场了,并被给出了众多感性特征(大萝卜、大蒲扇、大柱子、草绳),但这些感性特征合在一起,反而让读者远离了真实的大象,因此,这个故事是典型的“消极-I”型。四个盲人都自信地宣称自己把握了大象的真相,但作为读者,我们知道大象的真相远比他们知道的更多,因此本寓言显然是在讽刺对这四个以偏概全的盲人。然而,倘若我们接受面向物的本体论,相信任何物的真相都无法穷尽,我们作为认知中介对物的任何把握都只能是片面的,那么我们或许可以对这则寓言做一个反转式阅读:隐含作者把物的(片面)真相显示给了四位盲人,而反讽了自以为全部把握了物之真相的读者。不难看出,对短篇虚构叙事“谜”的解读,可以让读者瞥见物的某种真相,但作为读者,我们应该万分谨慎,因为探索短篇虚构叙事“谜”的过程充满了各种风险和不确定,稍不留意,我们就成了那几位争吵不休的盲人。
注释:
①本文交替使用“短篇虚构叙事”和“短篇小说”两个术语,不做特别区分。
②参见G.Harman.The Quadruple Object.Winchester,U.K.:Zero Books,2011.
③必须看到,哈曼讨论的“物”的含义是宽泛的,既包括无生命之物,也包括人类在内的有生命之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