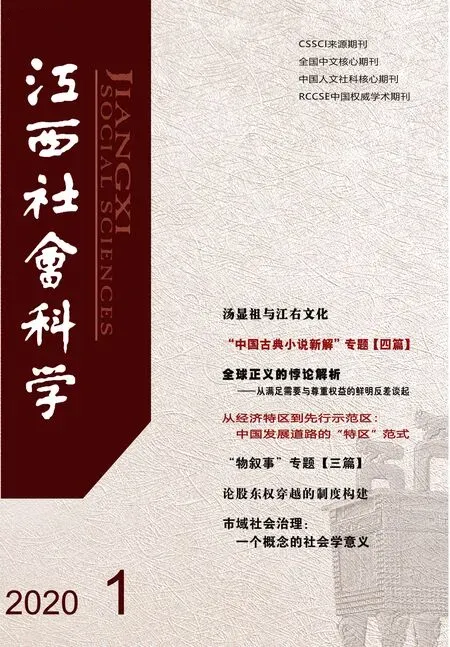回归物本体的生态阅读
自后现代主义以其碎片化、无深度感以及各种解构范式流通以来,文学批评和阅读也似乎离文学自身的本真状态越来越远而深陷批评者和读者自身的理解和接受之中,出现了各行其道的理论和批评思潮,但唯独忽视了文学自身的生态环境。笔者提出“阅读的生态”这样一个概念,以期回归文学自身的生态环境,进而提倡“生态的阅读”,以期回归文学中物的本真面貌,探讨以物为本体的文学的生态阅读。
文学阅读的生态就是通过阅读对文学产生一种类似于关于家的认识,即把文学作为家来认识,认识到构成文学的各个因素就仿佛家的成员,其自身都固有自己的内在价值,就像大自然中水、火、土、空气、山脉、树木、动物等都有其自身价值一样。这就是按文学本身固有的价值及其本真的面貌,也即文学本身固有的生态环境来认识文学。那么,文学固有的价值是什么呢?什么才是文学的本真面貌和生态环境呢?人文主义者声称,文学以及任何一种艺术,具有“使人成为人”的审美价值和道德价值。爱默生在讨论自然美时曾说:“对于其他的物,我将其作成诗;而道德情操则将我作成诗。”[1](P49)自然美并不是终极的,它只是一种内在美和永恒美的先驱,只有将自然美内化,使欣赏美的人达到灵魂的升华,使美的自然价值与美的道德价值合二为一,人才能成为诗一样的艺术品,并据此创造出高于自然美的艺术品,这就是“道德情操将我作成诗”的意味,同时也是美的真正价值,抑或是所有文学艺术的真正价值和本真面貌。
在某种意义上,文学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可以给我们提供这样一种类似于自然美的东西,并通过记忆、象征和类型来揭示人类经验中那些难以磨灭的东西,那些曾经发生过的事、曾经遇到过的人和曾经读到过的物。这些事、人和物首先以本体的形式存在,就像爱默生笔下的自然,自然界中的花朵、河流、山脉、树木、风云、日出、日落、彩虹、月光和飞鸟。他们本真的存在展现了美的不同侧面、不同维度,而一旦成为人的认识对象,成为人的智力活动的客体,就会呈现出更加完善或更加美的形式,现代神经科学已经证明了大脑的这种内化作用,即将自然美客观化的作用,这也是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历经两千多年来所讨论的阅读、阐释和审美判断等问题,构成了自然与人类精神活动之间出乎意料的聚合点,进而演化为文学和艺术创作中的不同类型。
从文学本体研究的角度看,这些不同类型就是我们在阅读中随时随地都能识别出来的文类和故事架构。当一个故事中具备了下列五种因素时,我们就知道这是一个与寻找圣杯的故事相类似的故事:探索者、要去探索的地方、被交代的去探索的理由、路上经过的一系列考验和挑战、最后揭示出来的去探索的真正理由。这个真正理由最终总是被揭示为——认识自己。虽然经过多少世纪的演化,尤其是经过现代主义者和后现代主义者的恣意翻新,文学的基本类型仍然没有多大的改变。就“探索”主题而言,如果14世纪的《高文爵士和绿色骑士》和16世纪的《仙后》是早期英国文学中两部伟大的探险故事的话,那么,20世纪美国小说家托马斯·品钦的《拍卖第四十九批》也无疑属于这个类型:只不过书中的探索者已经不是骑士了,而是一个后现代女性:她要离开旧金山附近的家去南加州;她离开或外出的理由是她被指定为前男友皮尔斯的遗嘱执行人;所经历的一系列考验和挑战是遇到各种各样的危险人物,并卷入了一场巨大的阴谋;最终揭示的真正理由可以用她的名字来说明:“Oedipa”,从词的发音和形态我们一下子就能将其与古希腊悲剧《俄狄浦斯王》中的“Oedipus”联系起来。众所周知,这位王子的真正悲剧是不知道自己是谁;品钦的女主人公的悲剧在于她不了解周围的男性,他们最终证明都是虚伪的和不可靠的,最终她发现唯一可靠的、可以依赖的就是她自己,这就是她对自我的新的认识。
这里我们看到,探险故事并不在探险本身,而在探险后获得的一种新的认识,对人与世界的更深刻的认识,对自己的一种全新的认识,最终是一种关于真理的揭示。于是,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初步的结论,即故事并非为了讲述而讲述,而是为了揭示某一生活真实。在英国的鬼怪故事中,《哈姆雷特》中父亲魂灵的出现是要让儿子为他复仇,进而揭示人性的内在腐败;狄更斯的《圣诞颂歌》是要从一个非常怪诞的角度表达人们对美好社会的向往;而在《化身博士》中,怪医海德不仅仅代表了人性中邪恶的一面,而意在说明人性中并非非善即恶,非恶即善,而是善恶并存,而在这两股力量之间,邪恶的力量始终要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机会削弱善的力量,进而破坏善、消灭善。文学中的食人魔、吸血鬼、女淫妖、幽灵或精灵的出现大多是出于削弱别人的力量而壮大自己的力量;利用别人达到自己的目的;剥夺别人的权利来满足一己之私欲;把自己的丑恶欲望置于他人的生命之上。这就是人性中的丑恶在吸血鬼身上的具体体现。
毋宁说,这是一种类型化了的结构。只要读者在阅读中碰到了相似的结构,也即类似的故事情节、类似的人物、类似的命运、类似的结局,读者就会有似曾相识之感。这似曾相识之感从何而来?从记忆中,从阅历中,从自童年就开始的阅读生活中。对于热爱知识、乐于从阅读中获得智慧的人来说,读书就是生活本身,而文学阅读构成了这种阅读生活的大部分。久而久之,读者就通过这种阅读生活建构起了关于历史、文化和文学的知识宝库。优秀的创作和阅读都来自于这个丰富的知识宝库。正如加拿大批评家诺斯罗普·弗莱所说的,文学产生于其他文学。不存在一种完全独立和完全创新的文学。这就是为什么阅读中会出现上述讨论的类似的识别。当有了足够长的阅历,并对所阅读的内容予以了足够多的思考,人的大脑中就会储存足够多的类型、原型和重复的画面。它们不仅仅是文学的,也是历史的、现实生活的。事实上,文学和历史从来是不分家的;历史本身就是故事。文学中的人物本身就是历史中的人物。在这个意义上,文学就是历史的化身,或者,文学产生于历史,是在与历史的对话之中产生的。而这种对话一旦出现在文学内部,那就是新文本与旧文本之间的对话,或新作家与老作家之间的对话,也即文本与文本之间始终在进程之中的互动,这种互动会深化和丰富阅读经验。读者越是意识到当下的文本在与其他许多文本对话,就越能发现相似和对应之处,文本也就越鲜活,越具有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而从影响论的角度来说,文学中的影响源也就越加清晰。在英国文学中,莎士比亚就是这样一个巨大的影响源。在托·斯·艾略特的《普鲁弗劳克的情歌》中,那个神经质的胆小的主要人物普鲁弗劳克可能是哈姆雷特,可能是伯纳多和马塞卢斯(最先看到哈姆雷特父亲鬼魂的人),但也可能是罗森克朗茨和吉尔登斯坦(被双方利用、最后被无辜送上断头台的人)。不管是谁,读者都在普鲁弗劳克与这些人物之间看到了共性,即他们的无助,他们的摇摆,他们意志的不坚定。艾略特似乎要用哈姆雷特来说明普鲁弗劳克的困境,但他并没有明目张胆地拷贝已成定论的经典,而是改写了哈姆雷特,其目的是要通过改写消除时代的隔阂,掩盖旧时代的痕迹,同时融入新时代的内容。莎士比亚作品中的人物(哈姆雷特、福斯塔夫)、情节(罗密欧与朱丽叶的爱情悲剧)、政治性(奥赛罗和各种历史剧中的政治阴谋),尤其是其魔幻般的语言,在他之后的文学中层出不穷。读者一旦识别出文本与文本之间的互动,一旦发现了普鲁弗劳克与哈姆雷特等人物的关联,便参与了新作家对旧作家的改写,参与了这种改写所必不可少的创造性想象,因而也参与了意义的创造,即根据自己的理解重新构筑新与旧之间的关系。想象并不是作家和艺术家的专利;创造性的阅读也必须有创造性的想象力;读者参与想象;读者参与创作。
在犹太教-基督教世界中,《圣经》的影响似乎更大,以各种变体出现在作品之中。莫里森的《宠儿》有一个情节中出现了四个骑马的人,当他们来到女主人公塞斯的门口时,塞斯明白世界末日到了。乔伊斯在《阿拉比》中描写了天真的丧失,而天真的丧失就意味着堕落:亚当、夏娃、蛇和苹果,至少还要有一个花园。这在霍桑的《拉帕奇尼的女儿》中应有尽有。《圣经》为文学提供了母题、人物、主题、情节,乃至引语,其影子无处不在。可以说,《圣经》中的故事与更为古老的神话传说以及讲述风雷雨雪等自然现象的故事一样,已经深藏于我们的记忆之中,它们不仅给故事提供了起源和深度,而且丰富和强化了阅读的经历。虽说程度不同,但它们都覆盖了最大范围的人类生存环境,包括现世和“来世”的生活,个体的人际关系或非个体的治理关系以及肉体、心理和精神等近乎所有的个体经验。然而,当我们用神话指我们所讲的“故事”时,我们所说的其实是一种并非不同于哲学、科学和物理地看待世界的方式,最终也是我们如何看待自己的方式。它不仅深藏于我们的记忆之中,构成了我们的文化,反过来又通过文化塑造我们。神话中的人物尽管有些高贵、神圣,但也和人类一样并不都是神,也常常会犯下人类常犯的错误:妒忌、贪婪、淫欲、卷入纷争和战争。诞生于公元前12-8世纪的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原本是描写农民和渔夫的故事,后来他们成了神,这从一个侧面提醒我们,伟大就寓于平凡之中,不论我们的世俗环境多么卑贱。何况《伊利亚特》的情节也是通过描写阿喀琉斯的愤怒而把一件绝非高尚的小事转变为流芳千古的史诗。但荷马绝不是为了讲故事而讲故事,而是以神话的形式呈现人类的四种斗争:与自然、与神、与他人、与自己的斗争。
罗马帝国盛期,维吉尔以这些荷马英雄为原型塑造了罗马始祖埃涅阿斯,于是,便有了罗马史诗。公元1922年,詹姆斯·乔伊斯写出了《尤利西斯》,用布鲁姆代替了奥德修斯,用茉莉代替了佩涅罗佩,把史诗中漫长的艰苦岁月紧缩成都柏林的一天一夜,而这部现代爱尔兰史诗描写的却不是奥德修斯(《奥德赛》)的辉煌和光荣。1990年,加勒比海小说家沃尔科特发表了诺奖作品《奥梅尔洛斯》,重讲了三千多年前荷马讲的故事,宣告了三千多年前荷马宣告的人类需要:保护家人(赫克托耳)、维护尊严(阿喀琉斯)、忠贞不渝(佩涅罗佩)和不畏艰难险阻归家的决心(奥德修斯)。荷马史诗和其他希腊罗马神话就这样丰富和深化了读者的文学经历,同时也使现代文学具有了古代神话的神圣性和魅力。
这种神圣性和魅力也体现在文学中的物上,如风花雨雪,地理状貌。这些物都属于故事背景的组成部分。然而,它们一旦出现在文学作品中,就不仅只是背景了,而是天气非天气、雨非雨、雪非雪了。整个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的文学传统中,诺亚方舟的故事以各种变体广泛流传,其中的雨、洪水、方舟、鸽子、橄榄枝、彩虹,总能给人类带来劫后余生的救助,雨后的彩虹总能给古人(乃至今人)带来安慰,传达超验的信息,给人类以希望:不管上帝怎么愤怒,他都不会彻底抛弃人类,都会在人接近灭绝的时候给人留出一条生路来。而最重要的雨、洪水等自然现象,尤其是自然灾害,表达的是人类的内心恐惧,而水又是人类生存的最基本的物质保证,因此也就进入了人类最深切的记忆之中。在《吉尔伽美什》史诗、不同民族的创世史诗(如中国的《山海经》和《大禹治水》)和神话故事中,水、洪水与溺水都代表着新旧交替,旧的被荡涤,新的得以建立。这一象征在现代文学中更是比比皆是:普希金的《青铜骑士》、劳伦斯的《虹》、海明威的《告别了,武器》等。在乔伊斯的《死者》中,故事结尾处加布里埃尔的妻子讲述了她年轻时的一位追求者身体虚弱,但仍然在雨中为她唱歌,表白爱情,最终死于肺结核的故事。这里,年轻、疾病、荒芜、希望、绝望、死亡聚合在一起,最终表达的是热烈的悲惨的爱。最具讽刺和象征意味的是,早年的雨在现实的故事中变成了雪:在《死者》的最后一段,主人公达到顿悟:他发现自己经过一夜的内心折磨,似乎对自我有所觉醒,然后推窗望去,看到一夜之间大雪覆盖了整个爱尔兰,于是突然意识到,大雪就像死亡,是最大的整合者,它落在爱尔兰大地上,“寂然无声地穿过宇宙,悄然下落,像落向它们的最后归宿,落在了所有生者和死者身上”,掩埋了他们,同时也掩埋了加布里埃尔的愤怒和嫉妒,使他在白雪中看到了宽容和永恒。
上述阐释意在说明一个道理,即一切文学都是解构的写作;一切阅读都是解构的重写。作家在创作时必须对他所写的人和物进行解构的分析,采纳适于他所处时代的视角,也即社会的、历史的、文化的、个人的视角,以便有效地使用手头的素材;而读者在阅读时,也必然以同样的方式对待所读的文本,即掺入了读者自己所处时代的主观认识。这样一来,文学赖以存在的本体的物就被淹没了,其本真的存在便被带入了作者(读者)自己的各种偏见之中。因此,基于文本、作者乃至读者自身理解的阅读,就都不是有效而本真的阅读。有效而本真的阅读应该使文学回归到它自身的本真生态,是要祛除文学中对自然、生存和心理现实的非现实再现,祛除对物自体的象征性表达,直接触及对物自身的描述,以回归文学阅读的生态环境,而这需要我们进行一种生态的阅读。
什么是生态的阅读?简单说就是根据物自体的实际状貌和价值来阅读文学中的物。如果说人类对自然界的认识经过几千年甚至几万年的进化而导致了科学的发展,反过来促进了对人类自身的认识,这两种认识在记忆中得以保存,又通过语言和文字流传至今,同时也把物带入了文化、学问、诗歌、艺术、经验乃至政治表达等人类思想的生产之中,那么,物自身的存在与人自身的生存就不可避免地被混淆在一起了,抑或是物的存在或多或少被人的生存掩盖了。而在西方哲学传统中,物只为人而存在,用哲学话语说,就是客体只为主体而存在。康德以后,伯克利的主观唯心主义认为物仅仅是储存在观看物的主体心中的感性数据;黑格尔的绝对唯心主义认为世界就是它呈现给自觉之精神的那个样子;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认为物外在于人的意识,但它们只为人的理解而存在。而后结构主义者德里达则认为物从未完全呈现在我们面前,它们只是在特定语境中以差异和延宕的方式不确定地接近但又远离每个个体。而无论是哪一种,按照布鲁诺·拉图尔的说法,物的世界都被切割成两半,一半是人类,另一半是自然。[2](P4)人类文化是多维度和复杂的,而自然或物的世界则仅仅是单一的。即便我们在谈论人与自然的关系时,我们也始终把人放在主体的位置,完全或几乎忘记了物的存在;也就是说,物自身的复杂性和多面性从一开始就被忽视了,而人从一开始就被置于中心和主导的位置。
古典哲学之后的一些认识论从不同角度强调物自体的重要性。格拉汉姆·哈曼根据海德格尔的存在哲学提出了面向物的哲学,认为海德格尔提出的物的“工具性”不是把物解作为单纯的物,而与目的关联起来了:一只锤子如果不是用来钉钉子而与更大的目的(造房子)关联起来,便毫无意义,除非作为抽象概念而存在。[3](P49)哈曼认为物的这种工具性是一切物体的真实,但是,物的这种真实并非被全部呈现出来;物的内部总是隐藏着一些东西,不可接近,无法言喻。因此,物并不仅仅通过人相互关联,而是通过用途,包括一物与另一物的关系。此外,物不仅是最基本的构成因素,如夸克或中子;物,无论大小、规模和秩序如何,它们相互间都是平等的。而且不仅物与物相互间是平等的,物与人也是平等的。
此外,怀特海关于世界即过程说影响了当代西方哲学的所谓物的本体论,如德勒兹的生成论、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理论、福尔曼的后人文主义动物论、环境主义的生物平等论、维斯曼的后人文主义动物研究以及米歇尔·波兰从植物的视角看待世界的研究,这些都没有改变从人的主体间性来看待物的视角。直到2010年4月23日,美国佐治亚技术学院召开了一次可能会成为划时代事件的一次会议,即全世界第一次“面向物的本体论研讨会”(Object Oriented Ontology Symposium,简称OOO),此后,“OOO”拉开序幕。这种以物为导向的本体论把物置于存在的中心:人类是世界的组成因素,而且是具有哲学兴趣的因素,但绝不是唯一的因素。世间一切都是平等的,无论是科学自然主义所说的碎片,还是社会相对论所说的人类行为,在存在的天平上都是平等的。即便人类有能力改变这个世界,但也只能改变自己占据的小小角落,也只能与宇宙的一颗微粒发生关联。从这种新形而上学的角度来看,物并不为人类而存在;物只为其自身而存在。[2](P6-9)
那么,这种新的哲学与生态阅读有什么关系呢?如果物在世界中有其自身的存在价值,那么,在文学中它们就必然有其被描述的价值。如果本体论是关于存在之性质的认识,那么,对存在之性质的描述就可称为本体书写(Ontography)。什么是本体书写?从形而上的视角看,本体书写旨在揭示物体间的关系而不提供关于物之种类的清理和描述,是一种进行总体描写的方法,以便揭示单个物的丰富性以及物与物之间的物体间性(interobjectivity)。[2](P38)如果说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旨在达成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和谐关系和共融,因此使得主客体和谐地相处,那么,在字面意义上,物体间性就意在其反面,突出物与物之间的和谐和流动,而反衬物与人之间的不相容性和断裂,也即二者间相异的孤立而非流动的生成。于是,语言和存在之间的链条被割裂,而用以实现这种割裂的手段就是列出作品中物的清单,突出物自身的故事,以便消除作为主体的人的痕迹。以往的文学阅读和批评注重所谓的文学性,因而局限于语言和再现的牢笼。但如果把重心转向包括语言在内的物品清单,文学以及文学所呈现的物便失去其文学表现性而世俗起来,成为一个个独立的物,尽管微不足道,但却是日常生活中经常得见的、与人发生短暂的亲密接触的物。这种短暂的亲密接触能够祛除传统阅读和传统批评所寻求的读者与文本中人物的认同,进而展现出(包括人在内的)物与物之间相容而依赖的关系。
文学批评家伊安·伯格斯特在《异现象学,或物的样子》中举罗兰·巴特的《自述》为例:
我爱:生菜、桂皮、奶酪、辣椒、巴旦杏面团、割下的干草气味(我希望一个“鼻子”能制造出这种香水)、玫瑰、芍药、薰衣草、香槟酒、淡漠的政治立场、格林·古尔德、非常冰冷的啤酒、平展的枕头、烤糊的面包、哈瓦那雪茄、亨德尔式的适度的散步、梨……马克斯兄弟、早上七点离开西班牙萨拉曼卡城时的山影,等等。
我不爱:白色狐犬、穿裤子的女人、天竺葵、草莓、羽管钢琴、米罗、同语反复、动画片、阿瑟·鲁宾斯坦、别墅、下午、萨蒂、巴托尔……舞台、首创精神、忠实性、自发性、与我不认识的人度过夜晚时光,等等。[4](P72-73)
在巴特自己看来,这一切“对任何人来讲没有丝毫的重要性……没有一点意义”。但这一切却意味着“我的身体与您的身体不一样”。[4](P72-73)在伯格斯特看来,这番叙述能帮助读者更好地认识巴特。而更重要的是,通过列一个清单,读者的注意力被吸引到巴特其人之外的世界,其文学批评之外的世界,以及其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理论之外的世界。或者说,这个清单打破了巴特以往的结构主义建构,而把自己的生存空间破碎化了,把一些不受欢迎的、相互矛盾的碎片堆在了读者脚下,以编目的方式揭示了他自身之外无限扩展的物质世界[2](P41)。这个方法抛弃了以往以人类为中心的叙述,而转向了众多世俗的细节,给传统的文学叙述撒了胡椒,以出乎意料的辣味颠覆了故事,并且以丰富的物的形象和记忆埋葬了作为作者的巴特,以实例宣告了他提出的“作者之死”。
在乔伊斯的《死者》中,主人公加布里埃尔从一开始就为主显节的聚会和晚宴心存焦虑,许多焦虑,其中之一就是他精心准备的演讲可能会被误解,因为听众要么没有文化,要么欣赏能力很低,根本不会听懂他将要引用的罗伯特·勃朗宁的诗句。但在宴会前,一件件在他看来无足轻重的小事出乎意料地打击了他的自我,人们热烈谈论的表现活生生的都柏林不同侧面的事例,尽管他不屑一顾,却也都不甚明了,这表明他和其他任何人没什么两样,都是都柏林这个慵懒、残缺、瘫痪的社会中的一员,而唯一值得人们赞赏和保留的就是这个破落家族的好客了。这里,乔伊斯恰到好处地安排了这样一段冗长的描写:
一只焦黄的肥鹅摆在餐桌的一头,另一头呢,一张垫了一层香菜的皱纸上放着一条大火腿,外皮已经去掉,一层碎面包屑撒在上面,一张干净纸围着火腿胫骨的边。火腿旁边有一块放了香料的大牛排。……合上的方形钢琴上,一只黄盘里的布丁等着客人分享,盘后面是三堆黑啤酒、淡啤酒和矿泉水瓶子,按不同酒类的颜色分放开来,前两堆是黑色,附了棕和红两样标签,第三堆是最少的一堆,白瓶子上拦腰系着绿色丝带。
我们看到,这段描写其实不亚于上述巴特的“自述”。很少有哪位作家如此细心地注意到宴会餐桌上的食物,也没有人像他这样如此着力于食物的“分类”和“编目”。这样一种布阵列队式的描写不会没有原因的:首先,出于故事本身的需要,读者会情不自禁地相信餐桌上诱人食物的现实,而不自觉地参与其中。其次,晚宴前的紧张局面得到了缓和,喜欢流行音乐和不喜欢流行音乐、亲英派和非亲英派、高雅阶级和低俗阶级等两军对垒的局面(或许食物就是有意按照这个军事布阵排列的),以及读者在阅读中感觉到的紧张和担心,在如此美味面前统统烟消云散了。而最重要的原因则是,每一个人都是参与主显节“灵交”的一员,大家都是这个聚会的组成部分,而且,这些食物是全体人员都有权分享的(如同所有基督教信徒分享上帝之灵一样)。从这个意义上说,餐桌上的食物就与从故事一开始就间或提及的白雪一样,在故事以加布里埃尔对妻子隐藏多年的爱情故事进行移情思考之后,看到整个爱尔兰都覆盖着白雪,在它下面,生与死都没有区别了,就仿佛在众多食物面前,众人之间所有的差别也都消失了。那么,人与人之间的隔阂,意见的相左,乃至矛盾的斗争,又有什么不可消除的理由呢?宽容的主题便幡然可见了。
例如,奥罕·帕慕克可以说是把“编目”做到极致的人。2002年,他开始写作百科全书式的《天真博物馆》(2008年出版),这是关于失去的爱和家庭的一部长篇小说,以字典条目的编排方式历数了女主人公芙颂的物品。20世纪90年代中期,帕慕克就开始为写这部小说搜集小说中提到的物品,而在小说发表后,帕慕克竟然在伊斯坦布尔建立了真正的“物品博物馆”,展出了他所搜集到的小说中描写的全部物品,包括芙颂抽过的4 313只烟头和行车驾照等。2012年,博物馆目录以《天真的物品》为题出版,其中包括了74条物品条目。书封里标题下是引自蒙塔莱的《柠檬树》的几行诗:“请凝望,这种寂静/庸琐退去,仿佛/天地也将泄露出永恒的秘密”。除了物本身蕴含的永恒秘密外,帕慕克还认为物能给人带来慰藉,因为物有“灵”,火、风、水和森林都有“灵”。这“灵”是什么?亚里士多德早就说过,植物和动物都有“灵”,只不过在量上不同于人的而已。在文学中,当物被减缩为物自身的时候,物就失去了自身携带的故事,并由于祛除了污染(也即作者或读者的偏见)而变得清白了。这清白,这天真,就是帕慕克借用萨满教的信仰所说的“灵”,即物之灵。帕慕克的“天真博物馆”(无论是小说、博物馆实体还是博物馆目录)都是建立在既要讲述物的故事、同时又要还物以清白的矛盾欲望之上的,这也是每一个作家和艺术家所共有的一种矛盾。然而,清白也好,天真也好,文学的生态阅读就是要在人与书、书与物之间建立起没有任何污染的联系,使之回归到一种原始的生态环境,便于我们理解物之本性的一种生态环境。毕竟,我们每时每刻都在进行各种联系,建立各种关系,都努力把我们周围发生的事件与我们心灵中突发的奇想或灵魂的震颤联系起来。
这种生态阅读超越了以往所要达到的目的,比如类比的、道德的、意识形态的、历史的、直义的以及各种“主义”的阅读,而深入物自体的层面,不仅在《安娜·卡列妮娜》的小说中读到一个个悲壮的切近生活的情节,而且要揭开这些情节背后的物质世界,那就是托尔斯泰浸透着种种人情世故和心理活动的栩栩如生的世俗生活,而不必非得把托尔斯泰说成是一位会讲故事的道德家,还他一个以物述物的世俗作家;不仅看到博物馆墙上挂着的或忧郁或亢奋的不同风景和人物,还要看到这些人物周围的每一件人人都使用和熟悉的物品,正是这些物品触及了人类的共同命运,因此也关切“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造。
最后,笔者想回答每个读者都必然会提出的一个问题,那就是,作为人,我们无法不从人的角度、无法不用人的语言来讨论和描述物和物的本真状态;我们无法逃脱语言的牢笼,更无法逃脱主客体关系的限阈,因为这是我们作为人而必然落入的人的悖论。但我们可以从一个新的视角重新审视人与物的关系,努力摆正我们在宇宙中的位置,摆正我们与物的关系,祛除任何偏见地(人的偏见)看待文学中乃至生活中的物,从而回归对物的本真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