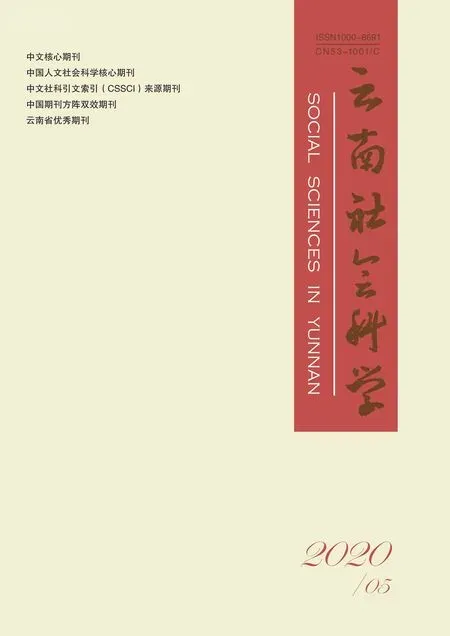萨满教与边疆:边疆文化属性的再认识
曲 枫
“边疆”概念在一般意义上很容易被理解为远离政治中心的国家边缘地区。但许多学者发现,这一对“边疆”的地理性理解并不准确。比如福建、广东等东南各省虽地处东南边缘,但在中国人日常观念中却是经济发达的中心地带。吴文藻早于20 世纪40 年代就已明确指出,边疆兼具政治与文化的双重涵义,如其所言:边疆的定义包括“政治上及文化上两种意义,兼而有之,才属恰当”,边疆“一面是国界上的边疆,一面是民族上的边疆”。①吴文藻:《边政学发凡》,杨圣敏、良警宇主编:《中国人类学民族学学科建设百年文选》,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9 年,第77 页。李安宅也谈到:“国人之谈边疆者,多系指文化上之边疆,非国界上之边疆。如东南各省以海为界,本系国界,而吾人均不视为边疆,川甘青康地在腹心,反称之为边疆,诚以农耕畜牧之不同,乃正统文化与附从文化之所以分也。”②李安宅:《实地研究与边疆》,《边疆通讯》1942 第2 期。转引自孙勇、王春焕:《中国边疆研究中的‘边疆性’问题探讨——以李安宅的边疆性概念解析为例》,《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社版)》2019 年第2 期。范可发现,边疆概念与民族概念在中国形成了互构关系,由于边疆地区的居住者主要为非汉民族,因此对边疆的研究就是对当地非汉民族的研究,“边疆”与“民族”于是在日常表述中呈现出反身性。③范可:《边疆与民族的互构:历史过程与现实影响》,《民族研究》2017 年第6 期。
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中国大部分北方边疆民族都以萨满教为传统信仰,尤以通古斯-满语族、蒙古语族与突厥语族为典型。甚至可以说,萨满教信仰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民族文化形态,并使之成为中国北方边疆民族的重要文化特征之一。④参阅吕大吉、何耀华总主编:《中国各民族原始资料集成:鄂伦春卷·鄂温克卷·赫哲族卷·达斡尔族卷·锡伯族卷·满族卷·蒙古族卷·藏族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年;郭淑云:《原始活态文化:萨满教透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年。与此类似的是,萨满教也是欧亚大陆与北美许多其他国家边疆民族的传统信仰,如俄罗斯西伯利亚原住民、北欧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北端的萨米民族以及美国阿拉斯加与加拿大北极地区的原住民等。然而,对中国学术界而言,虽然与“民族”和“文化”互构的“边疆”已经“构成了学术范式”①范可:《边疆与民族的互构:历史过程与现实影响》,《民族研究》2017 年第6 期。,但令人吃惊的是,对萨满教信仰与实践的研究在边疆范式中几成空白②目前仅见的将萨满与边疆概念相联系的论文系纳日碧力格:《“绝天地通”与边疆中国》,《学术月刊》2013 年第6 期。。这必然导致对边疆概念的常识性认知缺失,其中的道理不难让人理解:如果仅仅从地理边界、主权等政治角度而忽略文化属性来研究边疆,就会出现理解上的偏差与误判;与之同理,如果对许多边疆民族视为其族群灵魂的萨满教信仰视而不见,对边疆文化的理解就会流于空泛并限于表面。
那么,代表着民族文化灵魂的萨满教是否与边疆概念组成了互构关系?萨满信仰与实践如何塑造了民族文化并进一步成为边疆民族认同的标识?萨满教是边疆民族的独有现象还是同样存在于政治、文化的中心区域?萨满教究竟是个体宗教师的心理学现象还是以公共仪式为特征的社会现象?萨满教是一种古老的、“原始的”,随人类社会的进步、发展而渐趋衰亡的宗教形式吗?果真如此,边疆萨满教为什么会在当下的信息社会中强劲复兴?当下流行于欧美中心区域的“新萨满教”是否意味着边疆民族文化与全球化趋势形成了合作呢?这些问题正是本文所要探讨的内容。
一、萨满教与边疆民族互构的形成与解体
一般观点认为,西方文献中的萨满教最早由来自俄罗斯和欧洲的传教士和旅行者于十六七世纪发现于西伯利亚③参阅Flaherty,G.1992.Shamanism and the Eighteenth Century,p.23.Princeton & New Jerse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同时,欧洲旅行者在美洲原住民中也发现了类似的文化现象④参阅Narby,J.& Huxley,F.2001.(ed.) Shamans through Time,pp.11-12.New York:Jeremy P.Tarcher/Putnam.。法国哲学家狄德罗(Denis Diderot,1713—1784)在18 世纪于巴黎出版的大百科全书对萨满所做的定义中,直接将萨满教与西伯利亚地域连接,认为是西伯利亚原住民的特有文化现象。⑤在1751 至1765 于巴黎出版的大百科全书中,狄德罗在西方学术史上首次对“萨满”进行了定义:“萨满,名词,阳性,复数,是西伯利亚居民为那些行使祭司、魔法师、占卜者和医生职能的骗子所起的名字。这些萨满声称能够对魔鬼施加影响,与之咨询可预测未来、治疗疾病、对无辜和无知的民众施展似乎是超自然的魔法。做到这些他们会用力敲鼓,以惊人的速度旋转。”Narby,J.& Huxley,F,(ed.) Shamans through Time,New York:Jeremy P.Tarcher/Putnam,2001,p.32.这样,萨满教概念在西方文献中确立之初,就与世界边远地区土著民族联系在一起。
20 世纪初的西伯利亚民族志均将萨满教作为重要的民族文化特征施以重墨加以描述⑥作为早期中国民族志的杰作,凌纯声于20 世纪30 年代出版的《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同样将萨满教作为民族文化的重要内容加以考察论述。笔者在下文中还将述及此作。参阅凌纯声:《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 年。,其中最有影响的著作应为俄罗斯弗拉基米尔·博格拉斯(Vladimir Bogoraz,1865—1936)的《楚克奇人》⑦Bogoras,Vladimir.1904-1909.The Chukchee.Publications of the Jesup North Pacific Expedition Vol.Vii.Memoirs of the American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 XI.、俄罗斯弗拉基米尔·乔切尔森(Vladimir Jochelson,1855-1937)的《科里亚克人》⑧Jochelson,Vladimir.1908.The Koryak.Publications of the Jesup North Pacific Expedition Vol.VI.Memoirs of the American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 XI.、波兰玛丽亚·恰普利卡(Maria Czaplicka,1884—1921)的《西伯利亚原住民:社会人类学研究》⑨Czaplicka,Maria A.1914.Aboriginal Siberia:A Study in Social Anthropology.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以及俄罗斯史禄国(Sergéi Mikháilovich Shirokogórov,1887—1939)的《通古斯心智复合体》⑩Shirokogoroff,Sergéi M.1935.Psychomental Complex of the Tungus.London:Kegan Paul,Trench,Trubner &Co.,LTD.等。恰普利卡的《西伯利亚原住民》对西伯利亚民族文化做出了综合性描述。全书分为四大部分,其中对萨满教的叙述占据了整个第三部分。在其研究中,恰普利卡将萨满教视为西伯利亚和北极地区寒冷环境下地域性心理文化现象,并将萨满的出神心理状态(ecstasy或trance)看作是萨满教的核心特征①Czaplicka,Maria A.1914.Aboriginal Siberia:A Study in Social Anthropology.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这一观点对后来的史禄国和伊利亚德(Mercia Eliade,1907-1986)都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正如瑞典宗教史学家奥克·赫尔特兰茨(Ake Hultkrantz,1920—2006)所言,对萨满教的心理学解释“直到20 世纪的最后10 年仍然掌控着整个研究领域”②Hultkrantz,Ake.1998.On the History of Research in Shamanism.In J.Pentikainen,T.Jaatinen,L.Lehtinen & M.R.Saloniemi (ed.) Shamans,p.59.Tampere:Tampere Museums.。
史禄国所聚焦的通古斯语族跨越中俄边界,其北部区域属于俄罗斯的西伯利亚边疆,南部则为中国的东北边疆。其涉及民族包括今天的鄂伦春、鄂温克(埃文基)、赫哲(那乃)、锡伯、满族等。虽然史氏延续了恰普利卡的心理学研究范式,但与之不同的是,他将萨满教置于民族学的大框架中予以讨论。史氏在人类学史上首次提出了族群(Ethnos)概念,以与国族(Nationality)概念相区分,从而突显了边疆民族文化的异质性。他提出的“心智复合体”(Psycho-mental Complex)概念将物质文化与社会组织看作特定民族单位(Ethnic Units)对环境生物性适应的结果,显然深受当时西方流行的功能主义学派的影响。在这一适应性过程中,族群的精神、心理活动与社会制度、经济形式、物质文化、习俗、仪式密切互动,形成了一个综合各种民族文化要素的、以心智为核心特征的社会文化复合体。在史氏看来,最能体现通古斯心智特征的文化要素莫过于以祭仪、献牲、自由通神为特点的萨满教信仰与实践。可以说,如果没有萨满教,通古斯语族的“心智复合体”就无从谈起。③Shirokogoroff,Sergéi M.1935.Psychomental Complex of the Tungus.London:Kegan Paul,Trench,Trubner &Co.,LTD.中文有关研究可参阅于洋:《史禄国和他的通古斯萨满教研究》,《吉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 年第2 期。
正如美国宗教史学家兹纳孟斯基(Andrei A.Znamenski)所评论的那样,史氏的“心智复合体”完全植根于“有机生物学”(Organic Life)与“人类生物学”(Human Biology)。④Znamenski,Andrei A.2007.The Beauty of the Primitive,p.108.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史氏对“萨满”概念的定义也基于这一生物学和心理学视角,他认为真正的萨满是一定神灵的操控者,同时具有进入出神状态(Ecstatic State)的技能。⑤Shirokogoroff,Sergéi M.1935.Psychomental Complex of the Tungus,p.274.London:Kegan Paul,Trench,Trubner & Co.,LTD.虽然史氏一再强调萨满教是包括满族在内的通古斯语族的特有现象⑥Shirokogoroff,Sergéi M.1935.Psychomental Complex of the Tungus,p.275.,但他的心理学趋向则成为伊利亚德推行萨满普遍论(universal shamanism)的理论基石。
罗马尼亚裔美国宗教史学家伊得亚德的专著《萨满教——古老的出神术》至今仍然在世界范围内对萨满教研究领域保持着非同寻常的影响。伊利亚德直接在萨满教与出神术之间划上了等号,认为萨满就是具有出神技术的个体。⑦Eliade,Mircea.1964.Shamanism:Archaic Techniques of Ecstasy.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一方面,与史禄国不同的是,伊利亚德将萨满教现象上溯到旧石器时代的欧洲大陆,并提出了一个“底层”(Substratum)概念,认为旧石器时代的欧亚大陆存在着一个萨满教文化的底层⑧Eliade,Mircea.1964.Shamanism:Archaic Techniques of Ecstasy,pp.503-504.。基于这一底层概念,美国人类学家弗尔斯特(Peter Furst)与美国华人考古学家张光直(1931—2001)又分别提出了“亚美萨满教”(Asian-American Shamanism)模式⑨Furst,Peter T.1976.Shamanistic survivals in Mesoamerican Religion.Actas,XLI Congreso Internacional de Americanistas,México,2 al 7 de septiembre de 1974 Vol.2:151-157.和“玛雅—中国连续体”(Maya-China Continuum)模式⑩张光直:《中国古代文明的环太平洋的底层》,《辽海文物》1989 年第2 期。,主张亚洲与美洲的萨满教文化共同来自这一旧石器文化底层11参阅曲枫:《张光直萨满教考古学理论的人类学思想来源评述》,《民族研究》,2014 年第5 期。。另一方面,基于出神术理论,伊利亚德认为萨满教是一个世界性现象,不仅存在于亚欧大陆和美洲大陆的原住民社会,也存在于主体民族的古代社会。令人注意的是,史禄国的出神概念既包括萨满的灵魂出游(Soul Flight),也包括神灵附体(Spirit Possession)现象。但伊利亚德则将附体排除在出神概念之外,将出神术的定义仅限于灵魂出游。之后的学者如英国人类学家路易斯(I.M.Lewis)等则延续了史禄国的出神概念,同时采用了伊利亚德对萨满概念的定义,即将包括灵魂出游与附体现象在内的出神状态视为萨满教的定义性特征,最终使萨满教概念无限泛化,使之成为一个存在于人类历史上任何时期和全球上任何地域的普遍性现象。①Lewis,I.M.1971.Ecstasy Religion:A Study of Shamanism and Spirit Possession.Baltimore:Penguin Books.20 世纪80—90 年代的萨满教研究学者更流行采用心理学术语——“意识改变状态”(Altered States of Consciousness,ASC)来代替Ecstasy 和Trance②Atkinson,J.M.1992.Shamanism Today.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Vol.21:307-330.。美国人类学家迈克·哈纳(Michael Harner)提出“中心萨满教”(Core Shamanism)概念,认为现代文明中心社会的个体通过学习ASC 人人皆可成为萨满,从而获得自我疾病治疗和身体调节的能力。③Harner,M.J.1980.The Way of the Shaman:A Guide to Power and Healing.New York:Harper & Row.哈纳提出的“中心萨满教”又称“新萨满教”(New Shamanism)。这一将萨满概念无限泛化的理论趋向不仅使萨满概念的定义陷入危机之中,也使萨满教与边疆以及民族文化的互构趋于解体,导致边疆概念近乎消失在对萨满教的研究之中。
二、中心与边缘:萨满教在边疆话语体系中的困境
边疆首先因国家边界以及政治中心的存在而得以构造,边疆民族文化也因与国家主体民族文化显示出一定的差异性而存在。吕文利认为,边疆具有三重空间上的意义。首先是地理意义上的空间性,边疆是相对于政治中心而言的;其次是历史主体构建的历时空间性,政治中心与边疆的关系通过政治主体权威的展示和运作得以建立,二者形成了支配性与被支配性的关系;其三是现实主体的拓展性、想象性和文化性,边疆的确立需要不同群体的想象性认知,既需边疆民族的自我确认,也需要主体民族的确认。④吕文利:《何谓“边疆”——论中国“边疆”概念的三重空间》,《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 年第4 期。对边疆的叙事因此离不开对中心与边疆二元关系的探讨。
在中心与边缘二元结构关系中与萨满教相对应的是中心地域主体民族的制度化宗教。对于俄罗斯、美国、加拿大以及北欧国家来说,代表主体民族信仰的是基督教,与边疆民族的萨满教构成了二元关系。正如主体民族与原住民之间构成了强势对弱势的关系一样,基督教与萨满教的关系也形成了强/弱结构。自17 世纪至20 世纪,萨满教空间在基督教的强势挤压下逐渐缩小,甚至消失。从中国历史来看,作为汉族的主体民族以儒教、佛教和道教为传统信仰,与北方边疆民族的萨满教形成对照。然而从中世纪开始,随着北方民族王朝政权的建立与更迭,制度化宗教与萨满教的二元关系呈现出更为复杂的情形。
从中国文献记载来看,记录萨满教的最早典籍当属南宋史学家徐梦莘(1126—1207)编撰的《三朝北盟汇编》,其中有如下描述:“兀室奸猾而有才,自制女真法律、文字,成其一国。国人号珊蛮。珊蛮者,女真语巫妪也。以其通变如神,粘罕以下皆莫能及。”⑤(宋)徐梦莘:《三朝北盟汇编》(卷3),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年。文中所提“珊蛮”应为女真语及满族“Saman”一词的音译,今称“萨满”,证明了萨满教在金代女真人中的流行。不过,据朱子方的研究,在有关辽契丹王朝的汉语文献中为契丹皇室服务的太巫、大巫和巫其实就是萨满。这些契丹宫庭中的萨满是神职人员,组织和主持各种献祭,并有跳神仪式。⑥朱子方:《辽代的萨满教》,《社会科学辑刊》1986 年第6 期。如若这一推论成立,那么,这一现象说明至晚在辽代,萨满教已与王朝的政治中心联系起来。考虑到后期清朝宫庭的萨满活动,契丹宫庭萨满的存在是可能的。然而,需要注意的是,辽代开国皇帝辽太祖耶律阿保机自916 年建国伊始,便大兴佛教,皇族与贵族信佛、礼佛蔚然成风,佛寺在全国范围内大量修建,以满足民众需要。在辽王朝的统治范围内,萨满教与佛教形成并行的二元关系,那种现代民族国家中与中心/边缘相对应的制度化宗教/萨满教二元结构并不成立。⑦参阅黄凤岐:《辽代契丹宗教述略》,《社会科学辑刊》1994 年第2 期。显然,现代民族国家理论中的边疆话语体系在这里遇到了解释上的困境。然而,如果从包涵中原政权与北方政权在内的更广阔的文化框架中来看,无论对契丹辽朝还是对中原宋朝来说,以儒教、道教和佛教为特点的中原汉人社会仍然代表着文化主体。这个文化框架就是前现代中国社会的传统天下观,它为中原王朝和北方民族王朝所共认。这样,在传统天下观框架下,中心/边缘二元结构仍然存在。传统的契丹民族活动区域即使是辽帝国的中心区域,但因与中原相距甚远,仍然是天下观框架下的边缘。同样,在契丹人中流行的萨满教与中原的儒教/佛教/道教仍然构成了二元关系。
孙进已与孙泓推测,“萨满”之称虽始见于南宋(金代)时文献,其萨满信仰与活动应早已流行于辽代的女真人中。①孙进己、孙泓:《女真民族史》,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年,第155 页。女真于1115 年建立大金政权,其皇族仍然延续了祭天祷祝的萨满教传统,同时,其于春分、秋分、夏至、冬至举办的祭节性祭天活动也明显吸收了中原汉人的传统。与辽代契丹人相似,进入中原的女真贵族也同样开始崇信佛、道,同时也接受中原术士的占卜预测。在进入中原的女真贵族发生信仰转变的同时,传统萨满教仪式则仍然在东北故地流行。②王可宾:《女真国俗》,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1988 年,第300—305 页。因此,从辽金两朝的宗教实践来看,北方民族政权的建立并未导致天下观框架下中原/边疆二元关系的解体,反而更加固化了文化边疆这一以中原汉人社会为历史主体的想象性建构。
如果说萨满教与中国边疆以及边疆民族形成了互构③范可:《边疆与民族的互构:历史过程与现实影响》,第58—73 页。,那么,从一般逻辑上来说,它与国家中心以及汉文化也许存在着一种相互排斥关系。然而,随着清朝满族于17 世纪中期自东北边疆入主中原,萨满仪式也随爱新觉罗皇族进入紫禁城中。萨满教与帝国政权的合作使中心(制度化宗教)/边疆(萨满教)二元结构又重新陷入边疆话语实践的困境之中。
传统满族职业萨满分为两类:家萨满和野萨满。前者又称氏族萨满,后者也称安巴萨满(安巴在满语中意为“大”)。两者区别在于,前者主持氏族的祖先祭祀,以击鼓、歌舞和祝祷为主要内容,没有降神附体表演。后者主持动物神等自然神祭祀,以击鼓、歌舞为降神手段,具备附体的技能。④姜小莉:《清入关前满族萨满教改革论析》,《黑龙江民族论丛》2008 年第2 期。清初入关之前,由于被视为巫术以及杀牲过多等原因,野祭被太祖皇太极明令禁止,但家祭不在禁止之列。⑤参阅宋和平、孟慧英:《满族萨满文本研究》,台北:五南图书出版社。爱新觉罗家族的家祭入关前设于盛京清宁宫中,宫外亦建有堂子用于祭祀。入关后皇族祭祀设于紫禁城坤宁宫中,堂子祭祀设于紫禁城外东南。除皇帝斋戒日、国忌日、浴佛日等个别日期外,坤宁宫每日行朝祭与夕祭,由女萨满主祭。堂子祭则包括元旦拜天、出师凯旋告祭、月祭、春秋大祭、堂子浴佛祭、春秋马祭等。⑥姜相顺:《神秘的清宫萨满祭祀》,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5 年。坤宁宫祭祀从形式到内容与一般满人家族祭祀无异,可以视为爱新觉罗皇族的家祭。不过,堂子祭祀则不同。清初入关前,皇太极严禁满族各姓再行堂子祭祀,只有爱新觉罗一族才有资格举办。入关后,堂子祭祀逐渐演变为国家祭祀大典,如元旦拜天和出兵凯旋等重要仪式由皇帝主祭,文武百官出席,跳神仪式已弃而不用,代以祝、诵神辞。⑦参阅杜家骥:《从清代的宫中祭祀和堂子祭祀看萨满教》,《满族研究》1990 年第1 期。一方面,坤宁宫祭祀显示出萨满传统与作为边疆民族的满族之间的不可分割性。随着边疆民族对中心的占据,萨满传统也试图跨越中心与边缘之间的界限,甚至试图使界限弱化。比如,坤宁宫的朝祭神为如来佛、观音菩萨和关帝⑧参阅姜相顺:《神秘的清宫萨满祭祀》,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5 年;杜家骥:《从清代的宫中祭祀和堂子祭祀看萨满教》,《满族研究》1990 年第1 期。,这种对汉文化的吸纳并不意味着满族文化的汉化(Sinicization),而是体现了宫庭萨满教试图在中心与边缘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的支点。另一方面,堂子祭祀呈现出对萨满祭祀的制度化、政治化与国家化特点,隐含着重构中心内涵的意图。正如美国清史学家尼古拉·迪·科斯莫(Nicola Di Cosmo)所言,爱新觉罗家族已将一家之祭上升为一国之祭。⑨Di Cosmo,Nicola.1999.Manchu Shamanic Ceremonies at the Qing Court.In Joseph P.MeDermott ed.State and Court Ritual in China,p.376.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乾隆十二年(1747),乾隆皇帝钦定编撰的《钦定满州祭神祭天典礼》(以下称《典礼》)满文本修成,并于1778 年刊印。随后,汉译本也于1782 年刊印。富育光等人认为《典礼》代表着清廷对满族全民族家祭的统一规范⑩富育光、孟慧英:《满族萨满教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 年,第54—58 页。,但姜小莉发现,《典礼》并未颁行民间,其制定的真实目的是比附前朝古礼,将其收到《四库全书》中借以永载史册①姜小莉:《〈钦定满州祭神祭天典礼〉对满族萨满教规范作用的考辩》,《世界宗教文化》2016 年第2 期。。因此,进入国家中心的萨满教已完全陷入到结构性两难境地之中。一方面,萨满教要依赖自身的存在维护来自边缘的民族文化认同,另一方面,它又试图超越这种边缘的异质性,使边缘因素在避免汉化的前提下得以中心化。英国人类学家卡罗琳·汉弗莱(Caroline Humphrey)也敏感地意识到了宫庭萨满教所面临的困境。如其所述:
清代朝廷一直致力于解决仍然存在于边疆(Frontier)的满族地方文化与被征服的中土政治制度、正统(Classical Tradition)之间的矛盾,其历史进程因此一直很不稳定。实际上,王朝所保留的古老的满族式意识形态与业已汉化的政体制度是格格不入的。萨满教被选择用来振兴满族社会的本质,乃是因为它与有关满族特色的社会认同原则(祖先神灵)有着直接关系。问题在于,正如已深刻汉化的城市满族人也许会意识到的那样,民族的差异性并不会成为有助于满族统治的准则。②Humphrey,Caroline.1994.Shamanic Practices and the State in Northern Asia:Views from the Center and Periphery.In Nicholas Thomas & Caroline Humphrey Eds.Shamanism,History,and the State,p.216.Ann Arbor: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上述文字译自本文作者。
宫庭萨满教也引起学者对“萨满”及“萨满教”定义的争辩。史禄国依据其心智复合体模式,认为包括宫庭萨满在内的氏族萨满因不使用出神技术而不应认定为真正的萨满,只有具有表演出神术的宗教师才可以名至实归,称作萨满。③史禄国认为,家萨满因为不具备神附体和掌控神灵的技能只是名称上的萨满。详见Shirokogoroff,Sergéi M.1935.Psychomental Complex of the Tungus.,p.145.London:Kegan Paul,Trench,Trubner & Co.,LTD.然而,汉弗莱则反对将出神术视为萨满的定义性特征。在她看来,宫庭萨满仪式中的杀牲献祭、击鼓、唱颂、祝祷都是典型的萨满教特征,因此没有理由不称其为萨满仪式。④Humphrey,Caroline.1994.Shamanic Practices and the State in Northern Asia:Views from the Center and Periphery.In Nicholas Thomas & Caroline Humphrey Eds.Shamanism,History,and the State,pp.213-214.Ann Arbor: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抛开定义问题不论,宫庭萨满教与东北边疆萨满教的相异性是显而易见的。然而,其相异性最重要的体现并不是学者们所聚焦的出神术问题,而是迵异的社会、文化、政治情境。前者体现的是与民族身份认同、重塑中心秩序紧密相关的政治性策略,后者则体现了与宇宙观、环境和维持日常生活秩序密切相关的生存性智慧。因而,在中心/边缘的二元结构中,与文化边疆相对应的是政治中心而非文化中心,与政治中心相对应的并非政治边疆而是文化边疆。换言之,中心/边缘二元结构的本质即政治与文化的二元共生关系。历史上,二者可以构成合作关系,也可以形成冲突的双方。
三、拒斥式认同与主题式认同:边疆萨满教的复兴实践
据富育光与孟慧英的调查与研究,有清一代,关内满族各姓的家祭经历了一个渐渐衰亡的过程。但在东北松花江中游、乌苏里江沿岸及图们江口等地,野祭仪式得以保存或在清末得以恢复,并在民国年间继续流传。在东北一些设置了都统衙门的满族地区,满族家祭传统得以保存,并在民国年间得以沿续。⑤富育光、孟慧英:《满族萨满教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 年,第61—62 页。20 世纪30 年代,人类学家凌纯声对松花江下游赫哲族人的社会生活进行了田野考察,并出版了中国第一部人类学意义上的民族志。书中较为详细地记载了赫哲族萨满诸如领神、治病、跳鹿神、求子、祭天、祭星、家祭、占卜等萨满仪式和活动,说明至晚在民国年间,东北边陲的萨满教活动仍然兴盛不衰。⑥凌纯声:《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 年,第114—140 页。
边疆民族的萨满教传统在新中国建立后由于曾被视为“文化糟粕”而被否定,直至“文革”期间被迫彻底中断。改革开放以后,政策放开,民间萨满活动逐渐得到恢复。自20 世纪80 年代开始,学者们对边疆民族的萨满活动进行了大量田野调查。调查发现,一些在“文革”期间放弃萨满活动的老萨满又应族人之邀重操旧业,通过仪式为族人治病、祈福。20 世纪的八九十年代,学者们普遍认为萨满教是一种古老的传统,是“活的化石”,在新时代潮流中很可能难以为继,因而将田野工作视为对民族传统文化的抢救性发掘,做了大量的文字记录、录音、录像工作。然而,进入21 世纪,随着老萨满的离去,萨满教文化并没有绝迹,反而在满、锡伯、达斡尔、鄂温克、蒙古等民族中继续流传,甚至出现了强劲的复兴之势。与家族制度密切相关的萨满祭祀活动流行于黑龙江和吉林省的满族大姓家族中。达斡尔族与鄂温克族的萨满祭祀常常将祭天与祭祖融为一体。一些大型萨满祭祀仪式,如鄂温克族的“奥米那楞”祭典、达斡尔的洁身祭等已成为全民参与的公共性活动。另外,萨满医疗术也赢得了越来越多的信众。①参阅色音:《中国萨满教报告——萨满教在当代中国的复兴与发展(1917—2013)》,邱永辉主编《宗教蓝皮书·中国宗教报告(2014)》,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 年,第318—335 页。
俄罗斯西伯利亚萨满教经历了一个与中国类似的历史过程。萨满教在前苏联时代被禁超过半个世纪之久。苏联解体后,西伯利亚各民族萨满教迅速复兴。沉寂多年的老萨满重操旧业,收徒传承,使传统得以延续。大型公共萨满仪式,如萨哈人(Sakha)伊雅克(yhyakh)祭日仪式、汉特人(Khanty)的熊祭以及为新生儿名字的占卜仪式、布里亚特人(Buryats)的台尔甘(Taylagan)萨满献祭仪式等都得到了恢复。②参阅苑杰:《传统萨满教的复兴——对西伯利亚、东北亚和北美地区萨满教的考察》,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 年,第118—163 页。此外,西伯利亚的地方政府也加入到支持萨满教复兴的行列,如布里亚特共和国在宪法中明确规定萨满教为国家传统宗教。③参阅塔米尔:《中俄布里亚特人的萨满教复兴现象比较研究》,《世界宗教文化》2017 年第2 期。萨哈共和国还将伊雅克祭祀规定为国家性节日。④苑杰:《传统萨满教的复兴——对西伯利亚、东北亚和北美地区萨满教的考察》,第140 页。
无论在当代中国还是在北欧、俄罗斯与北美国家中,边疆与主流社会的文化差异已重新引起学者的强烈关注,边疆民族自身也愈加重视地方知识传统与族群认同。边疆文化与主流文化之间既形成了张力,同时又呈现出一种不易觉察的合作态势。边疆的族群认同因而具有双重含义。一方面,边疆民族顺应主体社会有关他者的想象,与主体社会形成充满矛盾性的合作;另一方面则要突出民族文化的异质性,建构一个“边疆我者”的形象,进而追求价值上的平等。因而,边疆族群认同既体现了来自边疆内部的自我认同,也体现了来自主体社会的外部认同。美国社会学家曼纽尔·卡斯特(Manuel Castells)将现代社会的认同分为三种形式,分别为合法式认同(Legitimizing Identity)、拒斥式认同(Resistance Identity)和主题式认同(Project Identity)。合法式认同是指对支配性权威的认同。拒斥式认同是对支配性逻辑所做出的逆反式行为。而主题式认同则是社会行为者基于一个专门的主题项目及有关文化资料,建立新的认同机制借以重新认定其社会地位,如女权主义运动、环境主义运动对权威的挑战与自我认同。卡斯特认为主题式认同虽然从拒斥式认同中派生出来,但在与主体社会制度的互动中有可能化身为理性化的合法性认同。⑤[西班牙]曼纽尔·卡斯特:《认同的力量》,第3—5 页,夏铸九、黄丽玲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年。在该中文译本中,Project Identity 被译为“计划性的认同”。本文认为“主题式认同”更贴近英语原意,故采用后者。
萨满教的地方性特点显然区别于女权主义和环境主义的主题式认同。不难看到,它既具有按主流社会想象塑造自身的特点,也强烈体现出边疆民族对自我文化认同的确立和对异质性文化价值的追求,具有多元性认同的特点,与卡斯特提出的“拒斥式认同”模式基本吻合。在卡斯特看来,认同的建构来自“历史、地理、生物、生产与再生产制度、集体记忆及个人的幻想、权力机器及宗教启示”等多方面的材料。⑥[西班牙]曼纽尔·卡斯特:《认同的力量》,第4 页。萨满教实践与以上诸因素均密切相关,因而,不难理解为什么它会成为边疆民族“拒斥式认同”的标志性现象。
萨满教虽然立足边疆,但却具有包容性和开放性特征。清代满族家祭对如来神、观音和关帝等佛教神与道教神的吸纳就说明了这一点。今天的萨满教实践秉承了以往的开放性特征,与主体社会以及国家的合作因而成为“拒斥式认同”的一个特征。换言之,萨满教的文化“拒斥”可以借由主动合作来实现。长春九台市小韩屯与东哈屯石姓(锡克特里氏)家族的萨满祭祀(包括野祭与家祭)已有300 年的传统。①于洋、郭宏珍、苑杰、孟慧英、锡克特里氏(石姓)家族:《满族石姓龙年办谱与祭祀活动考察》,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 年,第59—77 页。2007 年6 月,石姓家族委托长春师范大学萨满文化研究所向吉林省政府申报的“九台满族石氏家族祭祖习俗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正式获批。此后,多家大学和研究单位如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吉林省博物馆、吉林师范大学、长春师范大学、大连民族学院等将石氏家族所在的小韩屯和东哈屯作为萨满文化研究基地。2015 年,在长春师范大学申请到的吉林省政府“高教强省非遗保护专项资金”的资助下,用于萨满祭祀的家族祠堂在小韩屯的一处老宅院得以筑建,并于2017 年竣工。②以上资料来自笔者于2017 年9 月27 日对石氏家族族长石光继的访谈。民族文化在与主体社会的合作中实现了社会身份的重塑和价值的实现。
石氏萨满与吉林市满族博物馆的合作案例说明存在着可以化解矛盾空间的合作方式。2007 年,吉林市政府组建吉林市满族博物馆,并设计了萨满祭祀物质文化展览厅。博物馆于2009 年对外开放。同年5 月,时任副馆长的满族学者何新生邀请东哈屯23 岁的年轻萨满石光华来馆内工作,从事萨满文化讲解和表演。半年后,在何新生的大力争取下,石光华萨满作为特殊人才引进,成为事业编制国家公职人员。迄今为止,石光华也许是中国唯一一个以国家公职人员身份工作的职业萨满。③以上资料来自笔者于2018 年4 月30 日对石光华萨满和何新生先生的访谈。
如果进一步分析,不难发现,这种边疆民族文化与国家及主流社会对接的成功显然取决于主题(Project)的介入。在吉林博物馆与石氏萨满的合作案例中,主题是围绕着博物馆建设而展开的。石氏家族萨满基地建立的案例包涵了两个清晰的主题:一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申报,二是研究部门和大学的科研项目。在这里,可以看到卡斯特所归纳的主题式认同模式。萨满文化的建构本来自于所谓的拒斥式认同,然而由于主题的介入,合作从而产生,地方文化为主体社会接纳,从而进入到合法式认同的模式中。
在主题式认同中,非物质文化遗产对于边疆民族来说显然是一个有着吸引力的主题,尽管迄今为止人们对它的负面作用缺乏一定的评估。无论如何,它的有效性之一在于这是一个为全球主流社会和边缘土著社会所共认的世界性主题。2003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第32 届会议通过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为日益陷入濒危境地的土著文化带来了一线生机。许多包含萨满教要素的口头传统、表演艺术、仪式、节庆活动和传统手工艺被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以及“优秀实践名册”。④苑杰:《传统萨满教的复兴——对西伯利亚、东北亚和北美地区萨满教的考察》,第20—93 页。中国文化部和各省(市)、自治区的文化部门也迅速将确认国家级和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纳入工作职责范畴。2005 年3月26 日,国务院颁布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申报评定暂行办法》,对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定义做出了界定⑤牟延林、谭宏、刘壮主编《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论》,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年,第25 页。。以内蒙古莫力达瓦旗达斡尔族为例,民族舞蹈“达斡尔族鲁日格勒舞”于2006 年成功获批进入国务院公布的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从萨满文化而言,2011 年,该旗“达斡尔族萨满敖包祭”被成功列入内蒙古自治区级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⑥沃泽明:《中国达斡尔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形势分析及对策研究》,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达斡尔学会会刊《达斡尔论坛》第二部(下),呼和浩特:内蒙古文化出版社,2016 年,第327—353 页。此外,“博舞”“博乐”“蒙古族安代舞”“阿拉克苏勒德祭祀”“察干苏力德祭祀” 等与萨满祭祀有关的蒙古族项目以及鄂温克“鄂温克萨满服饰与神具”均被列入内蒙古自治区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再以黑龙江宁安市满族为例,依兰岗满族村“满族萨满家祭”、东升村“杨氏家族萨满鹰神祭”、满族文化传承人傅英仁先生传授的“满族萨满神话”、宁古塔满族说部《招抚宁古塔》、来自多个家族的“满族祭祀音乐”都被列入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除了上文提到的“满族石氏家族祭祖习俗”,吉林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还包括“满族关氏家族祭祖习俗” “满族杨氏家族祭祖习俗”“满族赵氏家族祭祖习俗”“九台满族石氏家族萨满传说”乌拉满族萨满音乐”“乌拉满族瓜尔佳氏家祭”“乌拉陈汉军续谱习俗”“伊通满族萨满文化遗存”“满族萨满骨质神偶制作技艺”等项目。①色音:《中国萨满教报告——萨满教在当代中国的复兴与发展(1917-2013)》,邱永辉主编《宗教蓝皮书·中国宗教报告(2014)》,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 年,第326—328 页。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主题式认同中,可以看到外部想象与内部构建两种因素的紧密结合。显而易见的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主题并非直接产生于边疆民族文化的内部,而是来自外部和主体社会对边缘的想象性建构。然而,这一外部主题的形成显然与拒斥式认同的坚持有关。与其说是世界与国家为边疆民族提供了主题式认同的机会,勿宁说是边疆民族的拒斥式认同为世界主题的形成提供了素材。
四、地方性知识与全球化逻辑:当代萨满教的两种类型
萨满教在伊利亚德的心理学模式中被视为人类历史上最古老的(Archaic)宗教实践,在现代社会中只是留存于边缘地区的民族文化之中。这种萨满教研究中的原始主义观点在中国学者中也较为普遍。如富育光与孟慧英认为:“萨满教是以东亚、北亚为中心的一种宗教形式,它产生于原始社会母系公社的繁荣期,一直延续至念今但已经衰落”②富育光、孟慧英:《满族萨满教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 年版,第273 页。。石光伟和刘厚生认为:“烧香典仪中的中跳神,是满族萨满教祭祀尘埃的核心……反映出许多生动而真切的原始文化现象,故许多学者称其为人类远古社会的‘活化石’。”③石光伟、刘厚生:《满族萨满跳神研究》,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2 年,第1 页。
萨满教在中国北方和西伯利亚等地区的强劲复兴使原始主义理论陷入到解释的危机之中。首先,萨满教是否出现于主体社会的史前时代仍然缺乏充分的考古学依据。至于早期进化论者提出的“母系社会”假说更是得不到考古学资料的支持。萨满教究竟始于何时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④参阅Feng Qu,Anthropology and Historiography:A Deconstructive Analysis of K.C.Chang’s Shamanic Approach in Chinese Archaeology.Numen (2017) 64/5.6:497–544.其次,从文献资料可以看出,历史上萨满教的衰退总是与主流社会的挤压有关,包括政治上的压制、制度化宗教(如基督教、佛教)的冲击等等。而在社会环境较为宽松的时候,萨满教总会在边疆地区结合新的社会环境重新流行。
需要强调的是,人类如今所生存的社会已然不是那个以天下观为体认的帝国社会,而是一个具有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所称的“晚期现代性”(Late Modernity)或“高度现代性”(High Modernity)特征的网络社会⑤Giddens,Anthony.1991.Modernity and Self-identity:Self and Society in the Late Modern Age,p.3.Cambridge:Polity Press.。在这一高度现代化的社会中,全球化裹携着资本与权力的快速流动形成了非地方性逻辑,边疆民族不得不承受来自国家中心与全球化的双重支配性力量。边疆与国家中心的传统二元关系常常转化为地方(或边缘)与全球的现代二元关系。为抵抗全球化所导致的地方文化的被同质化和边缘化,历史记忆、边疆特色、传统价值、仪式实践被边疆民族所重构和营造,并形成一种卡斯特所说的“自立性”。⑥[西班牙]曼纽尔·卡斯特:《认同的力量》,第411 页。在这种民族文化的“自立性”塑造中,萨满教起到了一个非常突出的作用。
依据伊利亚德的出神术模式,学者们将萨满教视为个体心理现象,认为任何现代个体通过训练掌握出神技术均可称为萨满。萨满教因此成为跨越主体社会与边缘社会的同质化现象和一种全球性逻辑。⑦参阅Harner,M.J.1980.The Way of the Shaman:A Guide to Power and Healing.New York:Harper & Row.苑杰将当今世界上的萨满教分为两种形式。第一种是传统意义上的萨满教,出现于历史上本来就拥有萨满教的地区与民族中,包括北亚、中亚、东北亚地区及北美和南美的爱斯基摩人与印第安人,还包括非洲、东南亚和大洋洲等拥有与萨满教类似现象的地区。第二种是在欧美国家的城市中出现的,“把传统萨满教的特定技术拓展为特定心理治疗手段的‘现代萨满教’”。⑧苑杰:《传统萨满教的复兴——对西伯利亚、东北亚和北美地区萨满教的考察》,第5 页。苑杰的“现代萨满教”即哈纳的“中心萨满教”或“新萨满教”。如果说传统萨满教代表着边疆或边缘民族的地方性逻辑,那么,“现代萨满教”则代表着主体社会的非地方性逻辑或全球化逻辑。“现代萨满教”有意忽略与传统萨满教之间的区分,以出神术的使用为主要手段,以治疗疾病、调节身体及追求个体灵性化(Spirituality)为目标,将萨满教缩减为个体灵修方式和特别的医治策略,与欧美社会兴起的反文化运动(Countercultural Movement)、新纪元运动(New Age Movement)息息相关,本质上是现代社会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框架下的神秘主义(Esotericism)的再现。与传统萨满教相似的是,“现代萨满教”同样构成了对主体社会主流传统价值观的抵抗与挑战,但它并非产生于民族文化内部,并且与民族文化复兴有着截然不同的旨趣与目标,因而是全球化逻辑的有机组成部分。如丹麦宗教学家奥拉夫·哈默尔(Olav Hammer)所说的那样,新萨满教是新纪元运动中个体主义(Individualism)与精英主义(Elitism)的体现。①Hammer,Olav.2015.Late Modern Shamanism:Central Texts and Issues.In Siv Ellen Kraft,Trude Fonneland,and James R.Lewis ed.Nordic Shamanisms,pp.13-29.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
以出神术为定义标准而将传统萨满教与“现代萨满教”混为一谈是对萨满教概念的误解与误用。在边疆(边缘)民族文化中,萨满虽然经常使用出神术与神灵世界交通,但萨满教实践的最典型特征是建立在部落或氏族社会组织之上的公共仪式。萨满首先是组织并主持祭礼的宗教师,是在公众面前击鼓舞蹈、唱赞祝祷的专家。与史禄国的心理功能主义观点不同的是,俄罗斯布里亚特学者道尔吉·班扎罗夫(Dorji Banzarov)在早于1846 年发表的论文中以一个土著人的视角指出,西伯利亚萨满首要的职责就是主持部落的献祭活动。②Banzarov,Dorji.1981.The Black Faith,or Shamanism Among the Mongols.Mongolian Studies,Vol.7 (2):82-83.匈牙利民族学家米哈伊·霍帕尔(Mihály Hoppál)也提出了与伊利亚德学派不同的看法,认为萨满教是一种包涵有关神灵知识、特定语言记忆及活动法则在内的复杂信仰系统。③Hoppál,M.1993.Shamanism:Universal Structures and Regional Symbols.In M.Hoppál & K.D.Howard (ed.)Shamans and Cultures p.184.Budapest:Akadémiai Kiadó.因而,更确切说来,萨满教是边缘民族的部落社会或家族社会所持有的地方性知识体系,并具有较为稳定的传承性。
“现代萨满教”并不具备公共仪式特征,也并不是产生于民族文化内部的地方性知识。然而,植根于边缘与兴起于中心的两种不同的“萨满教”并未形成鲜明的对立与冲突。反而,二者之间可以互动。1993 年,俄罗斯的图瓦共和国与哈纳以及他创办的萨满教研究基金会联合举办会议,并试图借助“新萨满教”来确认图瓦的萨满,进而恢复传统。④苑杰:《传统萨满教的复兴——对西伯利亚、东北亚和北美地区萨满教的考察》,第165 页。作为全球化新萨满教运动的一部分,北欧新萨满教(Nordic Shamanism)兴起于20 世纪70 年代。然而,自90 年代末期开始,以位于萨米人传统居住地特罗姆瑟(Tromso)的“萨满教协会”(Shamanistic Association)为代表的北欧新萨满教实践者转而探求与地方民族文化合作,吸收古挪威人与萨米人的传统萨满教知识,试图将以全球化为特征的挪威新萨满教向地方性的边疆传统回归。⑤Fonneland,Trude.2015.The Rise of Neoshamanism in Norway:local Structures-Global Currents.In Siv Ellen Kraft,Trude Fonneland,and James R.Lewis ed.Nordic Shamanisms,pp.33-54.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这些例证说明地方性知识与全球化逻辑之间的界限并非固定不变,而具有流动性和变化性。当然,它们也同样说明,传统萨满教不仅固化了边疆或边缘的文化想象,还使文化边疆与地方性知识的价值更加有力地显现出来。
——以吉林省为例